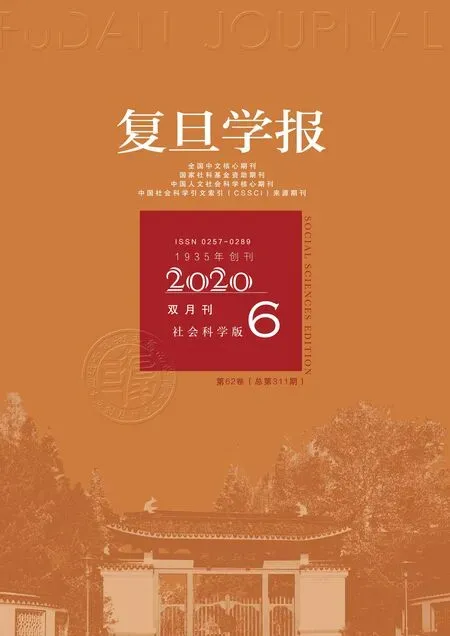屠岸贾考论
郭万金 赵寅君
(山西大学 国学院,太原 030006)
传统文化素以忠奸相对、泾渭分明的对立模式屡见不鲜。从《诗经》的美刺再及《楚辞》的比拟,以封建伦理为关注的忠奸对立历来是文化史最为寻常的话题,作者乐此不疲,读者满怀兴趣,每于文学愉悦之外,更得道德浸润,熏染刺提,见于立身行事,影响至巨。然而,以文学为依据的道德评骘并无太多的史实关注。各种情节的放大缩小、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本是文学对于历史的承载常态,进入伦理层面的文学述说更不惜增饰删改以凸显道德的张力。故而,忠奸话题中的历史人物常被粉墨涂抹,黑白对立,作者的情节展开因之流利,读者的道德期望随之满足,习以为常的文学表达中却不免于古人有“诬”。
历史中的“陈世美”与文学中的“负心人”相去天壤,英雄未必完美,奸恶也非全坏。文学叙述中的“坏”多半被放大、夸饰,但绝少向壁虚造,多少有迹可循,蛛丝马迹中总有些思想的轨迹、态度的烙印。探本溯源,并非刻意好奇的翻案,只是努力地逼近真相,还原当时的文化生态,更为深刻地辨析其中的文化史意义与思想史价值。
作为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大反派,屠岸贾无疑是中国奸臣谱系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传统社会素有“祸不及妻儿”的宽容,斩草除根的残酷冷血使屠岸贾成为“忠良灭门”的始作俑者,更在后世的文学叙述中成为奸恶之臣的典范样板。首彰其恶的正是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1)[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167 页。所赞不虚。《史记》文直事核,垂范后世,固不待言。因搜罗广博而具有的评判视角加之不虚不隐的实录精神,更形成了“不雷同以偶俗”的价值取向。对于屠岸贾的叙述,《史记》的笔调颇是平常,极少形容。见于《赵世家》的全部叙述不过千余字,关涉屠岸贾的文字不过数百字,本色当行,语气平实,并未有片语评骘。“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2)[清]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979页。读《史记》须于文字之外寻觅宗旨,自古已然。详细考索这段叙事中的“微情妙旨”,于屠岸贾的本来面目下论其言行得失,于文字之外觅得太史公的真实态度,是否受“诬”?何以成为“奸恶”典范?发明于细处,得意于言外,亦可略窥文史之间别具深意的思想张力与文化寄寓。
一、 据其职论其言
晋景公三年,即公元前597年,屠岸贾为晋大夫,具体官职为司寇,据《史记·赵世家》所言“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今按,晋灵公元年为公元前620年,灵公在位十四年,于公元前607年为赵穿所杀。据《史记·韩世家》,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复赵武田邑,再续赵氏祀。则屠岸贾被诛,当在此年左右。由前620至前583年,屠岸贾的政治生涯,从“始有宠”的小臣而至晋国司寇,历灵公、成公、景公三世,近三十余年,因“有宠”而得“有权”的过程并非如寻常宠臣般的一帆风顺。宠信屠岸贾的晋灵公并未赐其高官,或者说,尚未来得及重用,便已被赵穿所杀。“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成公在位七年,与赵盾有姻亲关系(3)《史记》载:“(赵)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史记志疑》则言:“‘姊’是‘女’字之误,或‘成公’是‘景公’之误耳。”,对于灵公的宠臣多半没有太大兴趣。更为重要的是,成公时期,主持国政者正是赵盾,屠岸贾即或未因“有宠于灵公”而受重责,但在成公之世不被重视,升迁受阻亦是情理之事。
《史记》载,“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虽未明确何时,但后文言晋景公之三年,赵朔为晋将下军,按照春秋世袭之制,由此约可推断,赵盾之卒,当在晋景公初年,至晚不过晋景公三年。《韩非子》曾举一事,其云:
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相室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4)[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80页。
由此例可知,“中大夫”虽为晋国要职,但普通之“士”经由当地长官推荐便有机会升任,而“相室”则有着重要的建议权。以晋国而论,正是上卿职守,屠岸贾成为晋国司寇,时间虽无明言,就《史记》所载而推论,则大体亦在此时,或多或少地暗示出屠岸贾在赵盾主政时期的受抑,直到赵盾去世之后,屠岸贾才有机会升任司寇一职。由此而论,屠岸贾忌恨赵盾亦在情理之中。
作为“司寇”的屠岸贾,仍为晋大夫,不及为卿。据《周礼》所载,司寇为刑官之属,设“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5)[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11页。可知,屠岸贾当为“小司寇”,系“中大夫”。关于“中大夫”,若依《礼记·王制》所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列为诸侯之属的大夫分为上、下两等,士则分为三等,并无所谓“中大夫”。清儒沈彤释曰:“《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为一等、中、下大夫为一等,何也?曰:《典命职》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别言三孤命数,则并孤于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则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与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为一等也。”(6)[清]沈彤:《周官禄田考》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孙希旦亦言:“《周礼》大夫与士皆有上、中、下,此上大夫以下惟有下大夫者,盖在王国则三等之士殊命,而中、下大夫同命,在侯国则三等之式命虽同,而禄则异。中、下大夫命既同而禄亦同,故士区为三等,而大夫则以中从下而止为二等也。”(7)[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0页。可见,春秋之际,诸侯之大夫有上中下之别。上大夫即卿,中、下大夫差别不大。
由此而论,《周礼》中的“司寇中大夫”实则与先秦文献中的“下大夫”并无差别。依周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夫五人者,崔灵恩所谓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司空、小司寇,司马事省置小司马一人是也。分言之曰卿曰大夫,合言之则三卿为上大夫,五大夫为下大夫。”(8)[清]夏炘:《学礼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记》中的“晋大夫屠岸贾”,无论其地位权势,还是身份俸禄(9)《周礼》:“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都是与上卿相去甚远的次要人物。以大夫身份担任的“司寇”一职,为司空之下的司寇大夫,即《周礼》中的“小司寇”。
“司寇”之官,古已有之,掌刑狱、纠察等事。其“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1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2页。谋及百姓的司法程序自是德治礼教的思想折射,按照不耻下问的贤者思路,此处的“万民”更是一种涉及多等级、多阶层的全面覆盖。自庶民而上,士大夫诸等亦在其列。《疏》曰:“外朝之职,朝士专掌。但小司寇既为副贰长官,亦与朝士同掌之耳,故云‘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者,案下文,群吏并在内,而此经独云致万民者,但群吏在朝是常,万民不合在朝,惟在大事及疑狱乃致之,故特言之也。”(1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2页。可知,依照《周礼》,对于“国危”“国迁”“立君”这样的大事,需要在极大程度上、尽可能宽泛的社会阶层中充分讨论,以便最终决断处理。此外,如《礼记·王制》所载:“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可知,遇到“事可疑难断”的疑狱也须广泛讨论。而小司寇的职责便是主持询问讨论。 其职既明,反观《史记》中屠岸贾的行为:作为司寇的屠岸贾“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在讨论中,不顾韩厥的反对,坚持追究赵盾的弑君之罪。就“将作难”而论,歧义在“难”之理解,大略有二,一为发难变乱之义,一为责难诘问之义,二说皆通。若以司寇之职、以及后文的“遍告”“争论”而言,则“责难诘问”之释更为贴切,文义亦更通顺。所谓“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正是责难诘问的内容,关键字眼则在“贼”字,屠岸贾的定罪问责是否有牵强强加之嫌?是否僭越其职?以“灵公之贼”加于赵盾,是否恰当?以此治罪,是否过分?赵盾弑君系春秋时期一大公案,《左传》载之颇详,论之亦切: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12)[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7~598页。
事实的隐晦不明、史家的笔法不隐、经解的伦理辩护,诸般错综,各执一词。孔子平议董、赵,以求中道。后世学者的考订辨析暂且不论,对于孔子鲁司寇的身份却须留意。鲁以“三桓”当国,季孙恒为司徒,叔孙恒为司马,孟孙恒为司空,皆为卿(上大夫),孔子为司寇下大夫,命禄职守正与屠岸贾相当。赵盾弑君,作为一代公案,自会引起孔子关注。当然,圣贤之审视角度、评价态度自非常人可及,更不是身当其事的屠岸贾可以比拟。就伦常而论,“赵盾弑其君”的史家笔法自然不错,就人情而言,赵盾尚有辨析余地。对于司寇屠岸贾这样的刑狱官吏而言,如何定罪执法则是本职所在,倒无僭越。史家既书“赵盾弑其君”,法吏自当追论其罪,韩厥“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的辩护,实则无力,潜台词已然认定赵盾有罪当诛,不过是“先君以为无罪”的法外开恩才得以赦免;而且,这位先君正是赵盾所迎立的晋成公黑臀。如此一来,“无罪”之说便更加无力了。由此而论,屠岸贾的“不听”亦非完全的专横。
对于赵盾的“弑君”,后世论者多就史家之“弑”的笔法而讨论,或索隐史实,或取舍褒贬,或诠释孔圣之论,大体在经学、史学间流转。章太炎曾言:“《春秋》书‘弒’,盖亦当时法律然也。虽然,必拘于法律,盾之‘弑’转无以实之,故赵盾书‘弒’,非良史不能;许止书‘弑’,直一法吏能之矣。若原其本心,止固与盾有异。”(1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8~309页。所论诚是,于经史法度中别有一种切实的法家视角。笔法在史家,褒贬在经学,论罪则在法吏。既然史官已笔书为“弑”,作为司寇的屠岸贾并无不问之理,赵盾家族的弑灵公、立成公,涉及“国危”“立君”,“三询”居其二,所谓“追论”正是职责所在。明儒万斯大即言:“《史记》屠岸贾事未可信,独所云‘治灵公之贼’,盖并案弑灵一狱,追论灭赵盾之家,由是观之,赵盾弑君,公论为昭,子孙所不能改者也。”(14)[清]张尚瑗:《左传折诸》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既言“未可信”,又称“公论为昭”,所以矛盾处,系因屠岸贾仅见于《史记》,无以为据,而视为“公论”的判断则承认其追论弑君是合乎礼法的行为。
因事而论,赵盾家族的弑君自是违法越礼之行,然而却始终无人为此负责,孔子作为后世同行的事件关注,兼顾国法人情,不以一定之法问责,指出赵盾之失,推扬董狐之书,史之褒贬实是胜过法之惩恶的选择,隐于其后的正是一以贯之的道德关注。《史记》沿之,称:“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太史书于前,君子论于后,司马迁有意的次序颠倒,除去强调史笔直书的合法合理之外,更隐藏着一层现实关注。因君子所论,赵盾之“弑君”可以成立,史家笔下的褒贬之外,自有法吏的追责论罪。其伏笔所设,正在于屠岸贾。
以职而论,小司寇屠岸贾据职以询,论法追案,实难称过,如其所言:“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首先承认赵盾的不知情,并未歪曲强加(15)后代学者,多有疑赵盾为知情者,甚至为弑君主谋。宋儒多主此论。,因其身为正卿,为赵氏家族之长,故其必须承担“贼首”的职责,此中亦包含着“反不讨贼”的追问。对于“以臣弑君”这样的大逆行为,赵氏子孙非但没有任何责任承担,反而在朝为官,无疑是对法令的践踏,“何以惩罪”的责问之中,正见其对律令的维护。赵盾为正卿,权倾一时,当其在世时,无人问责;屠岸贾作为新任小司寇,或有新官上任之表现心理,或有多年沉抑的宣泄情绪,但据其职论其言,其追论赵盾弑君之罪,并无不妥,正在本职本分之中。
二、 据其行论其理
司寇屠岸贾据职问责,无可厚非,“遍告诸将”的讨论惯例,韩厥争辩的意见发表,皆可视作合乎程序的规范行为。尤应注意的是韩厥的言辞对象,其言“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可知,韩厥之语,乃是针对“诸将”而言,并非专对屠岸贾所云。
《周礼·夏官·序官》:“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16)[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37~2241、2237~2241、2212页。《左传·襄公十四年》:“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春秋列国,诸侯多有违制。以“强国”为借口的军事扩张,使得礼制僭越成为诸侯间颇为普遍的现象。是否建构“六军”,并不在礼制的许可与否,而在国家军事实力的能否承担。以周制而论,“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17)[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37~2241、2237~2241、2212页。。晋国军制,每军有佐,佐又为卿,故“清原之蒐,五军十卿”。晋作六军,即有十二卿。《左传》杜注云:“韩厥为新中军,赵括佐之。巩朔为新上军,韩穿佐之。荀骓为新下军,赵旃佐之。晋旧自有三军,今增此,故为六军。”可知,六人为新晋之卿,加之旧有三军六卿,则有六军十二卿,此十二卿,正为屠岸贾、韩厥所言“诸将”之主干。此外,又有师帅、旅帅之属,亦在“诸将”之数。所谓“六军之将,或以乡大夫为之。”(18)[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37~2241、2237~2241、2212页。以小司寇之职,“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传》云:“刺,杀也,三讯罪定则杀之。讯,言也。”(1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7、915页。所谓群臣,即卿大夫、士,“诸将”即在此列。由此而论,屠岸贾的“遍告诸将”可视作“三刺”之一的“讯群臣”,亦是合乎司法程序的行为。
“三讯”之外,又有“八辟”,所针对的是《礼记·曲礼》所云的“刑不上大夫”。郑注“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张逸云:“谓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贤者犯法也,非谓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若脱或犯法,则在八议,议有八条,事在《周礼》。一曰议亲之辟,谓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议故之辟,谓与王故旧也。三曰议贤之辟,谓有德行者也。四曰议能之辟,谓有道艺者也。五曰议功之辟,谓有大勋立功者也。六曰议贵之辟,谓贵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七曰议勤之辟,谓憔悴忧国也。八曰议宾之辟,谓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后也。(2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9~80页。所云“八议”,即《周礼·小司寇》之八辟,疏云:“此八辟为不在刑书,若有罪当议,议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罚也。”(2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7、915页。以赵盾而论,自在“八辟”之列,屠岸贾、韩厥、诸将的争辩议论正是“有罪当议,议得其罪”的程序体现。韩厥面向“诸将”的争辩,并未奏效。“三讯”“八辟”的讨论以屠岸贾的“不听”告终,追论赵盾弑君之罪,获得认同,所谓“议得其罪”也。
罪名既定,即有执法追责之行为。《史记》称:“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其中的“不请而擅与”和“皆灭其族”为关键所在。《礼记·王制》载:“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征、杀有别,因周天子所赐而不同。晋文侯虽受弓矢,不得鈇钺,故可以征伐而不得专杀。征伐者,“以其弓矢之赐,州内有臣杀君、子杀父,不请于天子,得专征伐之”。(2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4页。晋国因有此赐,故有“不请而征伐”之便宜,却无擅杀之权。赵盾弑君之罪名一旦被屠岸贾与诸将议定,赵氏家族既有“臣杀君”之行为,则可以“不请于天子”而征伐,但不得“擅杀”。此处“不请”的对象,当为并未实权的周天子,并非操控晋国大权的晋景公。如此征伐要事,自当获得景公许可。如无景公之许可,屠岸贾之后的“索于宫中”则无从谈起。屠岸贾的“不请”或可寻得依法执行的依据,但“擅杀”则是僭越之行,于礼法不合。
“擅杀”已然违制,“灭族”更系酷虐。“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23)[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5页。上古,兵刑不分,鸿荒之代,异族征伐中间或存在集体杀戮的酷虐,自是初民社会的野蛮表现。文明渐浸,刑杀止而礼乐兴。古之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并无“灭族”之刑。一般而言,对于一族成员的群体性惩罚方式大体有流放、收孥、诛灭诸种,作为集体杀戮的“灭族”最为酷虐,极少使用。(24)关于“族刑”“灭族”,因“灭”之方式、“族”之范围,颇有歧义。详参《中国古代族刑研究》。《尚书》所载,《甘誓》《汤誓》皆曰“予则孥戮汝”,《费誓》亦言“汝则有无余刑”,杀气十足的话语仅见于军旅之誓,“将与敌战,恐其损败,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也。将战而誓,是誓之大者”。(25)[汉]孔安国,[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作为严肃军令的威慑之词,乃是特殊情境下的约信誓戒,并非普遍执行的条令法制。《泰誓》则在指斥商王罪行时,有“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之辞。二罪并言,所强调的乃是商王的善恶不辨,奖惩无度。(26)所谓““罪人以族”,《传》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正义》据秦政“三族之刑”解释为“一人有罪,刑及三族”。系后代诠释,并非实情。与孟子所称赞的文王治岐“罪人不孥”,正相对照,其所体现的乃是人文演进中仁德民本的一以贯之。无论是人类文明的自我反省,还是社会进步的相互尊重,更不用说仁爱恻隐的民族心理,历史叙述中似乎随处可见“丧家灭族”的暴行,一旦严格于史料,辨析于法制,折衷于仁爱,其数量亦颇为有限。《左传·昭公二十年》所引《康诰》即明言:“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以《汉书》所载:“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27)[汉]班固:《汉书》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96页。,则族刑之始,在商鞅之后,春秋时,并无此法。
“灭族”之酷,法令所无。虽然数量有限,却非绝无仅有。《左传》之中的“灭族”行径,虽非常见,却也屡次出现。较之《左传》数以百计的杀伐弑乱,不过七八次的“灭族”尚不算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的“灭族”,多半有着“尽杀”“尽灭”的行为,系最为残酷的集体惩罚。论其缘起,多半系诸侯大夫间的权力倾轧,纠缠于政治利益的善恶标准似乎难定一是,但无辜罹难的后果却是不争事实。如“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28)《左传·宣公十三年》。当时君子即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縠之谓乎!”《正义》曰:“先縠之罪,不合灭族。‘尽灭其族,为诛已甚’,亦是晋刑大过,是为大恶。君子既嫌晋刑大过,又尤先縠自招,故曰‘恶之来也,己自取之’。恶之来也,言大恶之事来先縠之家。”(29)[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9页。究其关键,则在“尽”字。“尽灭其族,为诛已甚”,有罪则罚,然“尽灭”之行,则滥施无度,况且又系诛杀重刑,一旦执行,则无回旋余地。“为诛已甚”的君子评判大体折射出传统社会对于“灭族”的基本取向,无论罪责如何,波及他人的惩罚都被视为过分的法外酷刑,更与儒家的仁政理念相左。《尚书·大禹谟》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诗经·商颂》云:“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左传》申而论之:“‘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宁僭无滥”的取舍态度正是民族思维的普遍路向,特殊情景下的容忍与底线正是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滥刑”本就为文明所排斥,作为法外酷刑的灭族更为传统所不容。
赵氏之祸,《左传》所载不过“晋讨赵同、赵括”。寥寥数字,然韩厥既言“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又引《周书》之“不敢侮鳏寡”。自可为赵氏灭族之证,至《史记》则书以“皆灭其族”。最为关键的区别便在作为“司寇”的屠岸贾。《左传》仅“晋讨”二字,《史记》则详论其情,屠岸贾“不请”违礼,“擅杀”无度,虽在其职,其心不仁。同为司寇,同论其罪,孔子既已惜之,绝无违礼之行,更不会滥杀灭族。屠岸贾之失,不在执法问责,而在惩罪之刚愎不听、酷虐不仁。需要注意的是,“灭族”之祸系诸将所为,如《史记》所言“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实际的屠杀者也多半是这些动机不良——希望能削弱赵氏、借机扩张权力——的卿大夫。屠岸贾不过为中大夫,调兵攻伐之力自然有限,但其以司寇之职,执法滥刑,系始作俑者。古之治民,劝赏畏刑,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屠岸贾“既僭且滥”,悖于仁道,以职而论,固然无可厚非;以行而论,则已远离宽仁之德,不容于传统之义。
三、 据其名论其义
司寇屠岸贾,其人如何?史家之笔,素以精核为要,《左传》不言,惟《史记》据其职,载其言,述其行,但于其人,并无渲染;后世的文学叙述虽然丰富,亦称饱满,却多半是忠奸情绪下的粉墨装扮。还原屠岸贾,自然要以更为贴近历史原态的资料入手,有限史料中的言行记载外,还应关注的便是“屠岸贾”三字。
古之姓氏,混一分合,随世演变。“姓氏之称,自太史公混而为一。”(30)[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氏族》卷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79页。《史记》载记屠岸贾言行,未论其姓氏。后世姓氏牒谱,颇有论之。唐《元和姓纂》“屠”姓条曰:“《左传》晋大夫屠蒯,《礼记》作杜蒯,又屠羊说,楚人。晋将屠岸贾。”(31)[唐]林宝:《元和姓纂》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0页。成书于宋代的《百家姓》中,并没有“屠岸”的复姓。屠岸为复姓之说始见于郑樵《通志·氏族略》,然归于“凡复姓有不知其详本者”(32)[宋]郑樵:《通志》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6页。,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综而论之:“屠、杜二氏,本为一,盖皆出杜伯之后,故《左传》晋之屠蒯,《檀弓》作杜蒉。而屠岸别为复姓,《国语·晋语》:里克及丕郑父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狄。韦注:屠岸夷,晋大夫也。其后有屠岸贾,见《史记》晋、赵世家,岸夷、岸贾二名无义,自以屠岸为氏。《庄子》及《韩诗外传》《说苑》诸书所称楚之屠羊说,盖亦同族,谓以屠羊为业者,子家缘饰之臆说也。余又疑两屠岸皆当作屠羊,岸、羊字相似而误。屠岸贾《汉书·古今人表》作屠颜贾,颜、羊亦一声之转。晋之有屠羊氏,犹羊舌氏之比。《元和姓纂》、《广韵》、王氏《姓氏急就章》皆只载屠姓,而系屠岸夷、屠岸贾、屠羊说于屠下,盖未之思也。惟《通志·氏族略》载屠岸复姓,最为得之。”(33)[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盦日记》第11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7907~7908页。
复姓之设,在于明别分族。所谓“凡复姓者,所以明族也。一字足以明此,不足以明彼,故益一字,然后见分族之义。”(34)[宋]郑樵:《通志》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0页。“屠岸”氏既然寥寥,则是否复姓,暂可不论。然“屠岸”与“屠”同源,皆是“以技为氏”,颇具启发之意。郑樵称“以技为氏,此不论行而论能。巫者之后为巫氏,屠者之后为屠氏”。如“屠蒯者,晋之膳宰也。屠氏之职,以割牲为事。”(35)[宋]郑樵:《通志》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70页。割牲之用,大抵在祭祀、饮食。以屠氏而论,《庄子·让王》载楚人屠羊说,《管子·制分》称:“屠牛坦,朝解九牛。”《淮南子·齐俗训》作“屠牛吐”。据《周礼》而论,六牲各有专人所掌,论其所职,多在祭祀,亦有饮食之涉及。李慈铭以“岸”“羊”字形相似、一声之转,认为“屠岸皆当作屠羊”。然“岸”“羊”字形相差颇远,倒是“岸”与“犴”通。“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36)[梁]萧统:《文选》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51页。由此而论,与“岸”相通的“犴”,乃是犬属,“屠岸”即为“屠犬”之列,与“屠牛”“屠羊”并为“屠氏之职”。《周礼·秋官·犬人》:“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瘗亦如之。凡几、珥、沈、辜,用駹可也。”所谓几、珥、沈、辜,皆系衅礼,“衅,谓杀牲以血血之”。(37)[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1页。自然涉及屠宰行为。磔犬之俗,亦颇见于《礼记》《风俗通》等记载。由此而论,则“屠牛”“屠羊”“屠岸”当为《周礼》中“牛人”“羊人”“犬人”之属,其职专为断斩刳磔,屠杀牛、羊、犬。
字义讨论外,屠岸贾其人与犬亦颇有渊源,以官属而论,“犬人”隶属“秋官”,为司寇所掌,属于“犬人”之列的屠岸贾能因晋灵公之宠,获得提升,最后进阶为“小司寇”,倒也合乎情理。此外,《左传》述晋灵公不君,曾“嗾獒”加害赵盾。晋灵公以一公之君,固不能亲自训犬,训此大犬,自当熟悉犬性。所谓“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则大者为犬,小者为狗。”(3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可见,犬人所养,正为大者。以“屠犬”为职的犬人“屠岸”正得其选,故而,后世戏曲小说,皆将“训犬害盾”归责于屠岸贾,虽有附会之处,却多少透露出“屠岸”之氏的特殊意味。
屠岸之义,既已清晰,则可追论“贾”字。“屠岸”既为“秋官·犬人”之属,则《周礼》所载“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十有六人。”(3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卷3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0页。便当留意。所言之“贾”,于周官中常见,《仪礼》中多称“贾人”。“《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贾。案:知物贾,谓知贾直之贵贱。其字今别为价,古通以贾为之。此贾亦庶人在官者。凡诸官有市买之事者,并有贾,列府史下,胥徒之上。此及大府、玉府、职币、典妇功、典丝、泉府、马质、羊人、巫马、犬人十一职是也。”(40)[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页。凡涉及购买事务、需了解市场者,大半归责于“贾”,故有多达十一职设有“贾”,(41)《礼记·王制》对于“不粥于市”有诸多规限,足见其繁复。作为从事采买的专职人员,自然需对采办之物有着较为全面的理解,由物性而市场,若为犬人之属,则当熟悉犬性,方为称职。以“知物贾”为职的“贾人”并没有一般商贾互通盈利的商业追求,只因其拥有“在官”的身份。
贾人的“在官”毫无后世皇家买办的显赫,仍系庶人。庶人在官者,因有一技之长,为官长选用,有别于无职之庶民。贾人系庶人得官,其为官长所授职,不在九命之内,位既不尊,禄亦有限。孟子论周代爵禄,称,“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赵岐注曰:“庶人在官者,未命为士者也,其禄比上农夫。士不得耕,以禄代耕也。”(4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贾人,“依《周礼》之内云‘贾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属,受禄于公家”(4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1页。。列于府史胥徒之间,其禄则在六七人之间,诚然有限。贾人其禄既低,其位亦卑。如《仪礼·聘礼》疏云“贾人是庶人在官者,故云贱不与为礼,”(4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2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9页。不命于君,未得正禄,“礼不下庶人”,贾人虽在官为职,于礼却与无职庶民相同。“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45)[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趋避而已,难得亲近。“自士以上有庙者必有寝,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寝者则无庙。”(4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2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7页。宗庙之制,亦见尊卑。“庶人在官者”,其禄略低于“下士”,其礼则略同于“士”,所谓“至于民庶,亦同行士礼,以礼穷则同之。”(47)[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2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1页。于禄低位卑的“庶人在官者”而言,降至最低的礼仪要求已无“在官”“在民”的区别,实与平民相差无几。“不与为礼”的品位限制下,贾人不仅受人轻视,其自视亦薄,每自称“小人”。
姓氏关系宗法,“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48)[清]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21册《原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5页。作为贵族等级、血缘身份之重要标志,庶民多半与姓氏无缘。文献中,每有介之推、舟之侨、庖丁、屠牛坦之类名号,多半系“在官庶人”,或以其乡,或以其职,因其言行有长,故得载入史籍。屠岸贾即是此类名号,“屠岸”为技,“贾”为其职,这位禄薄位卑的“在官庶人”并没有自己的姓氏。再以“屠岸夷”为例,亦可略见。“屠岸夷”见于《国语》,未言其职位。今考《周礼》载“夷隶”一职,其“掌役牧人养牛马,与鸟言。其守王宫者,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49)[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85页。。与犬人同为司寇之属,系“胥徒”之列,职位略低于“贾人”,亦相差无几,其得名应如屠岸贾,屠岸为技,“夷隶”为职,简略为“屠岸夷”,亦“在官庶人”而已,并无姓氏。
据名而论,屠岸贾原是“犬人”属下的一名“贾”,系“庶人在官”,职位低下,或因有功,机缘凑巧,为晋灵公所宠,得以进阶为“士”,而后为中下大夫,列官“小司寇”。近三十年的升迁历程,历下士、中士、上士、中下大夫数等,固然有得宠之捷径,却不能忽视其以庶民进阶的攀附努力。对于屠岸贾这样连姓氏都没有的小人物,其升迁艰辛,较之赵氏的贵族世卿,自不可同日而语。“屠岸贾”三字之中,所涉及的“屠”与“贾”素来为人所轻视,屠户之中,似又以“屠狗”最下。后世常以屠沽、屠贩、屠博当作微贱之职,尽管其中不乏隐士,亦有如樊哙拜将者,但一般语境中,多半仍用于对出身微贱者的蔑称。若张良称秦将曰:“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50)[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37页。先言“屠者”,再蔑为“贾竖”,不屑之情,溢于言表,无意中的“屠”“贾”关联所流露的正是轻蔑出身的一般心态与“屠”“贾”为贱的社会认识。
以义而言,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工商素被压抑,屠者多杀,商贾贪利,所职多与传统道德不合,常为世人所轻。其辈多半混迹下层,史载有缺,不得其闻。如屠岸贾者,因偶然机遇、特殊事件而为史籍所载,若论其出身家世,则无从谈起。屠岸贾由“吏”而“官”,由“庶人”而“大夫”,虽得官守,却无根基。下宫之难,虽因屠岸贾追论赵盾罪责而起,但实由“诸将”主导,灭族、杀杵臼与假孤,皆诸将为之。当为韩厥之众所胁,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更“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晋国乱政,上及国君,下至公卿,彼此争斗,权势倾轧,翻覆之间,出身卑微的屠岸贾已然成为政治斗争之牺牲品。由“犬人”之“贾”累升为大夫司寇,毫无身世背景的屠岸贾希望以追论赵盾弑君这样的重案来巩固个人地位、博取晋升资本,不免有哗众取巧之嫌,更有权欲膨胀之私。位卑禄薄的屠岸贾,在利禄推动下步步深陷,最终身死族灭,却未能在自己的名利悲剧中博得同情。较之屠牛坦之明理,屠羊说之自足,诚为可叹。虽留名于史,终究为人所轻。只言片语、三五动作的史家叙述为后世文士敷衍铺陈为精彩的戏曲小说,已然成为宠臣奸佞的屠岸贾,背负千古骂名,却甚少被人知晓其作为小人物的艰辛与悲剧。
四、 结 语
作为司寇的屠岸贾,据职论法,追责重案,或谓尽职无过;微贱无名的屠岸贾,执法越礼,“擅杀”无度,略见其心不仁。虽然如此,屠岸贾还算不得十恶不赦,毕竟位卑权轻,虽为赵氏灭族惨祸之始作俑者,却非实有其力的行为主导。晋国乱政,君卿倾轧,勾心斗角。“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51)[汉]司马迁:《史记》卷3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88页。“严”“刻”走向下的晋国政治生态,自然给严苛执法者以发挥空间,屠岸贾应运而起,论法无情,执法无义,虽据职而行,实为“酷吏”之始。所以为“酷”,既有三晋重法之传统,亦有晋君集权之权谋,更夹杂着各种势力的争斗,其文化幕景则是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酷吏屠岸贾的追责论罪,虽有灭族之酷烈,并未造就如董狐“赵盾弑其君”的文化穿透力,隐于其后的正是严刑酷法与史笔褒贬的价值评判。较之举族罹难,五字之书的笔法惩戒无疑更符合道义尺衡,更具人文关怀,更为深刻久远。
小人物屠岸贾的昙花一现,夹杂着太史公的特殊情怀。司马迁对于世卿贵胄并无特别推崇,对于庶民百姓的不凡,却每有关切。屠岸贾并不因其出身卑微而被忽略,着墨不多的叙述中并无抑扬之词,真正的褒贬态度暗藏于笔底微处。首见于史的屠岸贾,并非所谓的“爱奇”推动,而是有过切肤之痛后的反思。《史记·酷吏列传》述本朝而略前代,素以继任《春秋》为志的司马迁,自然有着藏于笔底的褒贬关注。《赵世家》中司寇屠岸贾以“酷吏”姿态一闪而过,非详细讨论,难识太史公深意。如同董狐史笔,司马迁的道德褒贬有着贯穿古今的文化穿透力。从小人物的卑微到晋司寇的酷严,再到戏文中的奸佞,屠岸贾以“恶”的形象渗入传统,脸上的粉墨涂抹也愈加厚重。探幽索微,洗去脂粉,还以本来面目,于逼近真相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发生的原态、作者的苦心孤诣,看到民族心灵的容忍与底线,明白道德的关注、价值的流变,隐于深处的正是中华文明最为深沉的道德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