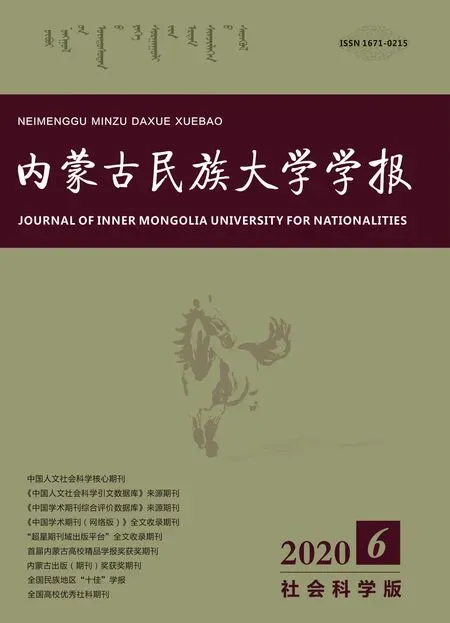浅析科尔沁民歌中的女性形象
王金双,赵红霞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作为科尔沁文化乃至草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尔沁民歌是勤劳智慧的科尔沁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和社会生产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它是展现科尔沁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面镜子。科尔沁民歌具有承载和传播科尔沁人民的历史、文化、思想的作用,是研究科尔沁乃至草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科尔沁民歌最初起源于13世纪至15世纪哈萨尔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尔沁”一词出现在东部草原上,这一阶段可称为科尔沁民歌的萌芽期;15世纪初到16世纪末为科尔沁民歌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科尔沁部落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为科尔沁民歌发展期,这一时期的科尔沁民歌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主题多以英雄叙事和女子远嫁思亲类为主。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女子的命运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娜布其公主》《孤独悲伤的珊丹》等等;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科尔沁民歌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时期是科尔沁民歌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科尔沁民歌中的女性受到新文化的影响,草原上的女性开始觉醒,她们有了独立思想,敢于做自己的主人,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时期出现了《阿列》《森德尔姑娘》《韩秀英》等歌曲;20世纪90年代至今科尔沁民歌完成了它与时俱进的任务,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科尔沁民歌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到现在的现代化、多元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其中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科尔沁民歌的一大转折点,科尔沁民歌主题经历了从屈从于封建礼教制度到反抗封建、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重大转变。此前,科尔沁民歌中塑造了众多被封建礼教所迫害的女性形象,上演了一幕幕婚姻悲剧。民歌《金珠尔》中的金珠尔姑娘远嫁受苦。[1]324在民歌《高小玲》中高小玲在远嫁的路上由于好奇丈夫是何等人而问其嫂子,嫂子开玩笑告诉她,其是个粗陋无比之人,高小玲信了嫂子的话用嫁妆中的绣花剪刀刺破喉咙身亡。[1]324—325到了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时代,科尔沁女性不再是社会政治的附属品,她们提倡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民歌《海棠白棠》中,海棠姑娘与东山二人克服困难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二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科尔沁民歌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始终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完善和更新自己,吟唱着新时代的主旋律。
科尔沁民歌从题材上分为英雄叙事类、思乡情怀类、婚宴嫁娶类、痴男怨女类等。由于科尔沁民歌涉及到科尔沁地区的方方面面,学术界从历史、社会、音乐及文学的角度入手,已经有了诸多成果。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学术界从民族性、时代性、融合性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2]从社会变迁的角度阐释科尔沁人民面对新社会的变化、自身生活方式及思想方式的变化,但通过对诸多科尔沁民歌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后发现,研究者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对科尔沁民歌的思想内容、文化特色和艺术风格上,鲜有关注女性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成果占比来看,对科尔沁民歌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关注度不高。
一、科尔沁民歌中的母亲形象
古代时期,草原并不安定,常年战乱。草原各部落争抢土地和牛羊,无论男子是否成年,战争爆发之时必须出征应战。直到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平息战乱,建立蒙古汗国,使蒙古草原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在日常生产劳动中,男女分工明确。男性负责制造日常家用工具,女性负责支配使用这些工具,同时承担着教育子女的重任。她们坚毅果敢、勤劳智慧的美好品格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如1240年载于《蒙古秘史》的《诃额仑兀真赞歌》唱道:
贤能的诃额仑兀真,
抚育着自己的孩子们。
带上高高的固姑冠,
束起长长的衣裙,
奔波在斡难河畔。
采撷杜梨稠梨糊口呵,
日夜操劳不辞艰辛。
刚强的诃额仑母亲,
教诲孩儿坚毅果敢。
她手持桧木长剑,
挖掘地榆、狗舌子,
备好每日三餐。
吃过山韭野葱的孩子们呵,
如今已成为尊贵的可汗。[3]
这首歌曲是在铁木真成为可汗之后的作品。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尔在铁木真九岁时被塔塔尔人毒害,之后家道中落,在一边讨生活一边还要躲仇家的危机情况下,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兀真带着孩子们艰难度日,她教育孩子们要坚毅果敢,最终吃过山韭、野葱的孩子成为了可汗。
在科尔沁民歌中伟大、智慧的母亲形象并不少见,如民歌《母亲的恩情》唱道:
母亲给我生命光环,
把我降在五彩人间。
母亲精心修剪枝叶,
辛勤浇灌幼小心田。
母亲用心培育幼苗,
盼望花朵美丽鲜艳。
母亲祝我顶天立地,
驰骋人间有所奉献。[4]14
这首民歌中所表现的是母亲给孩子生命、精心培育孩子使其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为社会做出贡献。虽是用最简单质朴的语言表现,但不难看出歌中的母亲是一位伟大智慧且无私的女性,她的伟大在于赋予自己的孩子生命,她的智慧在于她教育孩子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她的无私在于她用心培育了孩子。
科尔沁民歌发展到近代,蒙古族母亲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农耕文化传到科尔沁,科尔沁草原从纯游牧生产转为农耕或半农半牧生产。受到与农耕文化的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的影响,近代科尔沁民歌时期母亲的形象不再是坚毅果敢、勤劳智慧、能够撑起一片天的高大形象。由于无法抵制物质的诱惑,民歌中的母亲逐渐变得现实化、物质化,甚至为此不惜干涉儿女们的婚恋,如民歌《白虎哥哥》唱道:
六根飘带六种颜色的荷包啊,白虎哥哥,
我在六月的热天里一针针缝,
本想送给心上人白虎哥哥,
妈妈却给了那该死的阿拉坦巴根佩戴。[5]233
在民歌《白虎哥哥》中茹叶玛的母亲为了得到钱财,拆散茹叶玛和白虎哥哥二人,不顾自己孩子今后的生活,只为自己享乐,女儿对美好爱情的幻想被母亲无情地阻断,此时的母亲形象已经变成对青年男女美好爱情的扼杀者。古代蒙古时期的母亲形象是光辉伟大的,但随着蒙古部落衰败,清朝开始控制东部草原导致蒙古母亲被封建思想及封建礼教所影响,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也很难保证将封建的残余清理干净,而其中部分母亲已经成为封建家长的典型代表。此时的科尔沁民歌中的母亲形象多数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害人者。一方面,她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被封建包办婚姻所扼杀;另一方面,当她们成为家长后,变得更加虚荣,为了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根本不在乎儿女们的婚姻是否美满。她们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传统,对自己的子女横加干涉,最终酿成悲剧。
民歌《韩秀英》中的母亲是整个故事的推动者和悲剧的制造者。如旁白中斯扎布和韩秀英二人在家聊天之时,韩秀英的母亲外出归来,看到斯扎布,立即扔掉拐杖,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唱道:
喜鹊和燕子叽喳飞的不正常啊,
肯定是看上我家的屋檐了吧啊?
那边的单身汉纷纷到我家来啊,
是想把纯洁的韩秀英拐走吧啊?
旁白说到韩秀英的母亲骑上驴子到隔壁村给其谋了另一桩婚事,让韩秀英不得如愿。其母亲因在都格扎布家贪杯喝醉后承诺将韩秀英嫁给粗鄙的都格扎布,婚后韩秀英并不如意,回家哭诉道:
羊角有两个对称才好看啊妈妈,
如果只有一只那不好看啊妈妈,
女儿秀英哪里对不住您啊妈妈,
怎让我嫁给不喜欢的都格扎布?[6]196
近现代科尔沁民歌中的母亲形象从外在打扮到言谈举止都被“丑化”描写。如科尔沁民歌《万丽》中,有一段旁白是描写万丽母亲的,当万丽姑娘的父亲从左邻右舍那儿听到万丽姑娘与大喇嘛在一起的闲话之后,回到家中,将马鞍重重地扔在地上,对其母亲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就你这样的妈能生出什么好东西”。万丽母亲见状,坐在火炕正中间,将嘴巴咧起来吸了一口烟嘴,呼出去,随后从门牙缝里吐了一口痰,门口的取暖火盆发出“嘻日”的声音,而后大声说道:“堵不住别人的嘴,还是先教育自己的姑娘”。[6]762这样的母亲形象非常多,如《韩秀英》的母亲以及《白虎哥哥》中茹叶玛的母亲。似乎到了近现代科尔沁民歌时期,烟嘴、头巾、弯弯的拐杖、佝偻的背和警惕的眼神成为了蒙古母亲的典型标签。
二、科尔沁民歌中的女儿形象
科尔沁民歌塑造的女儿形象,多数都是受苦受难型。或是出于政治原因,或是出于经济原因,一些女儿被迫嫁到远方。虽说都是在草原上,但由于当时地广人稀,路途遥远且交通极不发达,很多女儿嫁出去之后再也无法回家重见父母亲人,且在异乡受尽苦楚,甚至凄惨地死去。长篇叙事民歌《娜布其公主》讲述了满金太太的女儿娜布其公主备受封建政治联姻制度迫害而悲惨死去的故事,揭露了当时动荡的社会和官员的腐败。娜布其公主因政治联姻从敖汉旗远嫁到阿拉善,由于遇人不淑,善良的娜布其公主遭遇了灾难。受难后的娜布其唱道:
兄妹三人父母生,
远嫁阿王独我身,
深陷牢狱受苦难。
命运不济恨不争?
手足兄妹父母心,
远嫁阿王独我身,
由我独受辱苦难,
吾路何在?[6]491
在动荡年间娜布其公主作为女儿为自己的家族远嫁,牺牲自己,在他乡受辱之时不禁为自己的命运喊出一句“吾路何在?”可见,在当时即使是贵为公主,也不见得能摆脱悲惨的命运。
到了近现代时期,科尔沁民歌中的女儿形象绝大部分不再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婚姻恋爱中,女儿的形象都是以正面形象示人,她们单纯善良、活泼灵动。在民歌《八月玲》中:
院子中的大榆树,
绿葱葱映入我眼中。
年迈的妈妈的叮嘱,
时时刻刻牢记我心中。
登上山巅极目远眺,
乌珠穆沁家乡就在眼前。
在深夜的睡梦中,
年迈的母亲就在身边。[5]385
民歌《八月玲》中的八月玲远嫁之后思念故乡、思念母亲,在当时远嫁的姑娘是极其孤独和悲凉的,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父母去陌生的婆家。思念家乡的女儿们只能将自己的思乡情寄托给鸟儿、榆树、高山、微风等自然环境,用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乡情,给人一种新奇美妙的感觉,却也不胜悲凉。
民歌《美丽的山峰》通过侧面描写女儿坐在山峰前的唯美画面来表现出女儿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
美丽的山峰的前坡,
蒲公英盛开花儿金黄。
近邻村子里的羊群,
放牧在崎岖的山冈。
在缓缓移动的羊群旁,
端坐着一位姑娘。
姑娘穿针引线,
正在绣时髦的云子花样。
姑娘黑黝黝的眸子,
注视着峭崖上的羊。
扁圆而白嫩的手指,
捻出缨穗荷包上镶。
姑娘用天鹅绒的边条,
编织图案绣花忙。
在这空旷的山野,
为谁把巧工用在荷包上?[5]394
民歌《美丽的山峰》刻画了未出嫁的女儿在山峰前绣荷包的祥和画面,从而表现出女儿美丽的外表,通过描写绣荷包的举止动作来表现出女儿娴静的性格。
在科尔沁民歌中的女儿不管是外在形象描写还是内在心理描写都偏于理想化,对女儿形象进行了“美化”。在民歌《万丽》中用诙谐幽默的旁白形容万丽姑娘,乌黑的长发自由地飘在肩后,银饰耳坠带在耳朵上,站在镜子前画一画,三个画匠顶不过,一双明亮乌黑的眼睛被画了又画,樱桃小嘴被抹得红彤彤,虽有幽默调侃之意,但不难看出民歌中对女儿外表美的赞扬。再如,民歌《森德尔姑娘》唱道:“博王旗的,斯日斤扎拉嘎的女儿森德尔,十八岁的时候,因俏皮美丽而远近闻名。”[6]617科尔沁民歌中女儿形象多与银饰、玉器、绸缎、绣鞋以及俏皮的动作和灵动的眼睛连在一起。女儿形象的性格多为积极向上、追求自由,这与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科尔沁民歌中的恋人形象
科尔沁民歌中女子的婚恋问题从形式上分为两种,即封建婚恋和自由婚恋,从题材上分为悲剧性和喜剧性两种类型,封建婚恋大部分为悲剧性,自由婚恋大部分为喜剧性。悲剧性民歌中有由女性独唱如意恋人被拆散而被迫听从父母意愿嫁给他人的,如《佟岭哥哥》讲的是佟岭哥哥因战乱入伍、二人不得已分开的故事;《小龙哥哥》讲的是冯阳高佬和小龙哥哥的爱情悲剧故事。喜剧性民歌多为姑娘的婚恋由自己做决定,最终有情人成眷属。此类民歌语调欢快,语句幽默诙谐,深受听众喜爱,如《乌尤昂嘎》《海棠白棠》《努力格尔玛》等。
悲剧性民歌中由于父母之命而不能跟心爱之人走在一起的女性,自己唱出自身的苦闷与绝望,如《佟岭哥哥》中女主人公唱道:
望那纷飞的尘土,
好似灰白马跑得快,
匆匆忙忙看远处,
好似佟岭哥哥到来。
脖子上的黄纱巾,
唰的一声拽下来,
黄脸的道尔吉我不嫁,
哭着闹着把纱巾摔。[5]217
“好似佟岭哥哥到来”,女主人公盼望着自己的恋人可以快些到来,但那纷飞的尘土并不是因她的恋人而起的,表现出主人公内心的焦灼与苦闷,同时为自己的婚事担忧,告诉世人黄脸的道尔吉她是不会嫁的,唱出了自己的无奈和不甘。
民歌《小龙哥哥》唱道: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
青年当中挑国兵忙。
挑选国兵真是凑巧,
小龙哥合格把兵当。
要是结了婚成一家,
送到新兵营理应当。
正因为两人私下爱,
只能是送到军车上。
黑布鞋帮硬邦邦的,
刺刺扎扎针通不上。
当兵出发的小龙哥,
头也不回我好心伤。[6]436
女主人公还未成婚的恋人被迫参军,由于未成婚没有办法正大光明地去送站,她埋怨着当时的动荡社会和封建礼教,同时因自己没能在恋人入伍前与其成婚而懊悔,又因恋人的举动而感到心酸,三种情绪交织在女主人公身上,巧妙地反映了其复杂的内心世界。
由女主人公与多人对唱的民歌《乌尤昂嘎》是以1912年札萨克图旗发生叛乱为时代背景而产生的。穷苦人民无法生活,扎兰艾里的宝日吉格的老头,领着老伴儿宝日玛、女儿乌尤套上勒勒车,拉上所有东西避开战乱,搬迁扎鲁特旗海日罕山下的宝茹尔金庙附近安家。在那达慕大会上舍登喇嘛与乌尤昂嘎相遇之后开始了一场具有争议且欢乐的恋爱故事。当乌尤和舍登在一起之后师傅骂舍登是不守清规戒律的混蛋时,乌尤唱道:
赛跑再快的好走马,
母马生下长大的吧,
活佛和圣人也都是,
从娘肚子里生下的吧!
天空升起的红太阳,
没有云彩遮挡明亮亮。
博克之首舍登喇嘛,
不胖不瘦真是好模样。[6]78
由此可以看出,乌尤昂嘎是个勇敢活泼、不顾世俗的眼光、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女性,舍登和乌尤昂嘎是自由恋爱。
再如民歌《海棠白棠》是打破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恋的典型例子。在民歌《海棠白棠》中主人公海棠姑娘和东山二人与海棠的养父却吉喇嘛斗争,最终,虽然东山失去了双耳,但也换得了知己。海棠养父却吉决定将其嫁与兵头子甘达尔章京时海棠唱道:
高高的青天啊,保佑我海棠吧!
我视那贵族之家的子弟如粪土。
把我嫁给沿门乞讨的乞丐又怎样?
让我嫁给思念中的东山哥哥吧。
但是天意弄人,甘达尔章京得知此事之后百般捉弄东山,最终将东山的两只耳朵割下才肯罢休,痛失双耳的东山唱道:
甘达尔章京割去了我的两只耳朵,
我接受心底坦诚的海棠姑娘的真心。
来日越高山过溪涧到处流浪,
你我白头到老一起生活。[7]228
《海棠白棠》中海棠和东山的爱情故事不管中间多波折,终是以二人如愿以偿为结尾,海棠崇尚自由婚恋,不被有强烈物质欲望的养父所控制,不被封建礼教所控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四、科尔沁民歌中的妻子形象
妻子是一个家庭中的重要角色,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看出,科尔沁民歌塑造了众多有代表性的女儿形象、恋人形象和母亲形象,与此相比,对妻子形象的塑造则显得相对单薄。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歌《阿拉坦苏和》中阿拉坦苏和的妻子努力格尔玛这一形象,《阿拉坦苏和》是长篇叙事民歌,以内地发生农民起义、清朝政府为镇压起义招兵买马为时代背景。阿拉坦苏和得了官令无法抗拒,只好前去当兵。故事开头,阿拉坦苏和与努力格尔玛婚宴正在进行之时,官府来令让年纪轻轻的阿拉坦苏和去参军,之后留努力格尔玛与阿拉坦苏和的父亲及其继母在家中,阴险的婆婆三番五次刁难诬陷努力格尔玛,但努力格尔玛始终尽心尽力地做着家务、孝敬公婆,无奈婆婆实在容不下,将努力格尔玛赶出家门,回到自家路上努力格尔玛唱道:
我把神圣的香火点燃,
向佛祖祈求平安无灾。
我被撵回娘家不要紧,
祝愿心上人平安归来。
在阿拉坦苏和参军之后其母亲整日虐待努力格尔玛,即使尽力服侍婆家也依然不招待见,三年过去阿拉坦苏和仍未归来,其母亲便起了恶念,将努力格尔玛送回了娘家。努力格尔玛唱道:
思念的人儿充军去远方,
妈妈的性情就变了花样。
送去开水时说成是冷水,
我成了眼中钉向谁去讲。[4]40
当努力格尔玛被送回娘家之后不久阿拉坦苏和便归来,将其接回家中。努力格尔玛将传统的忍辱负重型、隐忍型的妻子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中努力格尔玛的妻子形象较为清晰,她对被迫入伍的丈夫忠贞不贰,孝敬难处的公婆,传统妻子应有的美德都在努力格尔玛身上表现出来。
五、科尔沁民歌中的女英雄形象
科尔沁民歌塑造了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形象,她们保家卫国,冲锋陷阵毫不畏惧,例如在民歌《嘎达梅林》中的女英雄牡丹形象就比较典型。嘎达梅林为了保护土地,反抗军阀不幸入狱,之后牡丹组织众人精细谋划,将嘎达梅林救出监狱。牡丹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士,她为了不连累他人,自己舍生取义,被敌人抓捕。嘎达梅林战败之后,牡丹被一名叫胡宝山的人救起并与其成婚,1944年她与丈夫胡宝山参加抗日战争,1948年牡丹让自己的女儿参加解放军,民歌《嘎达梅林》中牡丹形象是典型的保家卫国的伟大女英雄形象。《额日古勒黛》中的额日古勒黛为了给自己的父亲报仇独自走了二十九天到达王府,拿王府三十六匹马换了父亲遗失的一匹马,后赶回家中并且招兵买马,攻入王府且取得胜利,额日古勒黛是不畏权贵、有勇有谋的女英雄形象。
民歌《刘石山》中的刘石山妻子梅荣在刘石山保家卫国不幸身逝之后唱道:
走在这大道上啊梅荣,
定要咬牙坚持住啊呵,
被恶人杀害的丈夫仇,
定为丈夫报仇雪恨呵。[1]315
梅荣是一个善于射击骑马、有决心且有义气的女英雄形象,这一形象疾恶如仇、行事果敢,在丈夫刘石山被害之后她依然临危不乱,最终为丈夫报仇雪恨。
结语
从以上对科尔沁民歌中的女性形象衍变情况得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科尔沁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受苦受难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科尔沁民歌中体现出了女性的觉醒。大体而言,科尔沁民歌从悲痛的哀唱转向了欢乐的颂歌,歌颂党和人民、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歌颂科尔沁人民当下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新的社会制度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正如民歌《好社会》中唱道:“在那旧社会,哪里有自由?我们穷苦人,有话没处说。走进新社会,完全获自由。财产重登记。要念谁的?崇高的共产党,作战命不顾,走完长征路。”[7]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