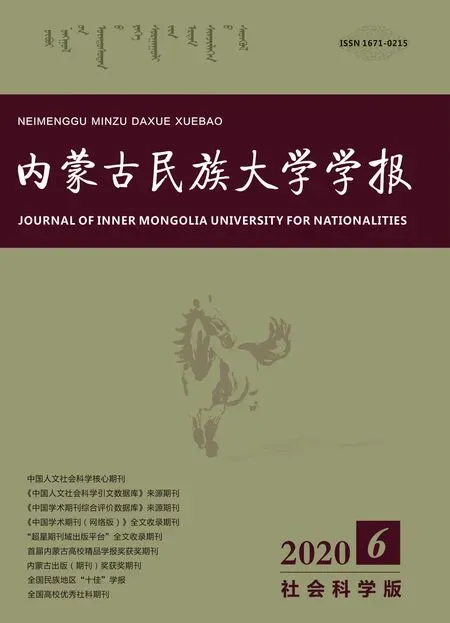周双利教授的治学品格与学术贡献
于东新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周双利教授在1968年毕业后即支边来通辽师范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前身)报到。按照当时中文系的安排,周先生被分配到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这种看似偶然的安排决定了他一生的治学走向,即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用力钻研,而本专业古汉语竟成了副业。今天梳理周先生的学术成就大体有两端,一是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领域,二是他不忘导师陆宗达先生的教诲,在古汉语及文字学方面也多所用心,而前者成就最著、贡献最大。直到退休前,周先生关于元代以来少数民族作家诸如萨都剌、杨景贤、贯云石、耶律楚材、马祖常、哈斯宝等研究成果有30余篇(部)公开发表,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专著《萨都剌》(中华书局1993年版),以及论文《杨景贤生平思想与创作》(《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元蒙古族作家马祖常评述》(《内蒙古社科学》1988年第6期)等。即便退休以后,他依然笔耕不辍,陆续完成了相关成果几十篇论文。可以说,他是学界较早关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的学者之一,尤其在萨都剌研究方面影响最著,也是较早秉持并伸张“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理念的学者之一。
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章黄学派“无征不信”的治学品格
作为20世纪50年代追求进步的学子,受时代风气的熏染,周先生曾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著作,感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因而成为他治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在《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的精神与方法》一文中,他高度赞扬马克思的治学精神,认为学者治学就应该像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工作”,“我们应当向马克思学习,科学工作不是为了个人的金钱、荣誉、地位。怀抱私欲的人,到头来只能在科学阵地上爬行。无私才能无畏。我们应以马克思为榜样去从事科研工作。”[1]7他钦佩马克思在治学路上的勤奋和执着,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勤勉与刻苦,对我们这些想做马克思学生的后人来说,是一种鞭策,我们应当从中受到教育,发奋图强,努力工作。”[1]8最重要的,周先生在文章中认真梳理了马克思的治学方法,即如恩格斯所总结的:“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也即从唯物主义出发,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服从于真理的追求。在具体的方法上,周先生认为马克思的研究路径是“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并且以辩证法为思维方法,即如列宁所指出的:“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3]所以,“马克思的治学精神与方法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文章中周先生告诫所有学者,当然也是告诫自己:“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精神,把科学研究视为严肃的事业,我们必须为真理负责,要有理论上的良心。”正因为有了如此信念,他的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从来都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式的研究,总是立足当时的历史语境,“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从不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详细占有材料”,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所以,他认为萨都剌是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少数民族汉文作家,正是有像萨都剌这样一批民族作家的创作,才使得元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推动了元诗“由宋复唐”的转变。“萨都剌不仅一扫往宋萎靡之弊,同时也一扫虞集缓弱之弊,使元诗由宋反唐过程中,显示出了应有的成绩。”[5]52并且,萨都剌等民族作家的汉文创作,对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汉文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6]16这些不凡的识见,是与周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掌握历史辩证思维方法大有关联。由此就不难理解在八九十年代,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学界在评价僧格林沁时一度许之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时候,周先生则清醒地提出:“对于僧格林沁这个近代史上的历史人物应当如何评价?我认为应当历史地、全面地分析这个人物,即不是看他在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抹杀其对历史、民族有贡献的另一方面。”[7]156这种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是周先生治学的利器,也是他能走在所处时代前列的原因。
不仅如此,周教授于1964年至1967年间,问学于黄侃弟子陆宗达先生门下,遂为乾嘉学派之章黄弟子。所谓乾嘉学派,即指清代乾隆、嘉庆之时发展兴盛起来的以考据为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其重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小学”,亦长于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之学,代表人物有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俞樾、章炳麟(太炎)、黄侃等,这是一个构建了清代、近世三百余年学术史的著名学派。亲炙陆先生绪论的周双利教授自然秉承章黄学派的治学理念,践行实事求是的求证之法和细致专一的治学路径,关注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无征不信”,注重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同时又追求融会贯通,博雅通达。梁启超曾有言:“凡欲一种学术发达,其第一要则,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周先生正是秉持这种中国传统的“精良研究法”而从事他的北方民族文学研究的,比如在《杨景贤戏曲著作考辨》一文中,周先生就对杨景贤《刘行首》《西游记》等19种戏曲著作以及部分散曲的创作情况,做了翔实的梳理,充分发扬了章黄学派细致缜密的考据功夫,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再如有关萨都剌的家世及族属问题,周先生也有深入考辨,所用材料充分,逻辑缜密,尤其以为“干文传与萨都剌彼此以朋友相称”这条材料最具说服力,所以他断萨都剌的生年为1282年。对此,著名元代文学专家杨镰先生评价说:“感到今人周双利所拟生年,即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比较接近实际情况。”[8]所以说,“无征不信”的治学之法,周先生承自先贤,并恪守终身。
同时也要看到,周先生的治学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他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都很熟悉,不用说中国古代经典的诗学理论,就是西方一些重要的理论,诸如康德的哲学、黑格尔的美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等等,他也能随手拿来为己所用,这一方面显示出他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也使他的研究视野通透、富于学理的深度。比如关于诗的意境,他说:“在我看来,就是诗歌创作时的典型化问题。社会人生和生活的实境(包括大自然的景物),经过诗人的加工与提炼,化为笔下的艺术境界,处在这种境界中的人物思想与感情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情与境、意与境的和谐一致,就是意境。”[9]这样就打破了一谈到意境就非得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起的惯常理路;再如在谈萨都剌诗歌意境的时候,他认为萨氏“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出诗意,然后又构成美的意境。”为此,他就以歌德的理论来伸张:“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作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10]通过周先生恰当地引用,足见出中外理论家的共同智慧。他还说:“在诗人(萨都剌)的笔下,幽花能哭泣,老鹤会听琴、听棋,山能嘲笑,云会喜爱诗客,甚至猿通人情前来索饭,好山展笑脸送迎客人,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世界。这样写的结果,自然是像黑格尔所说的‘人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物里’‘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11]诗人将自然物人化或者将环境人情化,其结果是显示了诗人心灵的美与生活的诗意。论及创作中的模仿,周先生就以美国学者约瑟夫·T·肖的《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来论证:“使读者受到真切的美的感染,产生独立的艺术效果的作品,无论借鉴了什么,都具有艺术独创性。有独创性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发明家或别出心裁,而是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糅进新的意境,在造就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12]如此这般,中西互感,古今对照,在周先生的著述中可谓是司空见惯的常态。
总之,在周双利先生的学术世界中,章黄学派的“无征不信”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无违和,反而达到了和谐一致,即都注重实事求是,都从文献出发,全面考察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详细占有材料”,从而辩证地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古今中外先进治学理念的有机融合,成为周先生可贵的学术品格。因此,可以说,周先生的治学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有民族气派,又有世界眼光。
二、领一时风气之先的萨都剌研究
梳理周双利教授近五十年民族文学研究的历程,就会发现他在元代少数民族汉文作家研究方面起步早,水平高,因而最有成绩。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关注北方民族政权时期的古代文学情况”[13]的研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学界一片沉寂,像周先生这样踏实而清醒的研究者并不多。可以说,周先生是开启新时期元代文学学术转型帷幕的学者之一,虽然他后来并不是学界走红的学者。据笔者统计,他关注的元代少数民族作家达67人之多,几乎囊括了有元一代大部分少数民族文人,对其生平家世、创作情况、艺术面貌都有认真的研究,尽管由于传世文献所限,或详或简,篇幅长短未免参差不齐,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属于元代文学的前沿研究了。他的第一篇成果《杨景贤的生平思想与创作》即刊发在《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上,起点颇高。这对于一个身处经济社会欠发达、信息十分闭塞的北方边陲小城的研究者,是十分不容易的。
其中,最惹人瞩目的是萨都剌研究。从时间上看,周先生确是国内较早开展萨都剌研究的学者,80年代中后期,其研究成果先是以论文的形式在《固原师专学报》《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等期刊上发表,然后,1993年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虽然篇幅并不算宏大,但关于萨都剌的基本问题都做了深入讨论,包括萨都剌的家世与族属、萨都剌的生平思想与时代、萨都剌年谱、萨都剌的诗歌创作情况、萨都剌的诗歌艺术风貌以及萨都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贡献等,几乎囊括了萨都剌研究的各个方面,可谓领一时风气之先,为学界的萨都剌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基础。其成绩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萨都剌的族属问题、时代与生平的研究。周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以来那种以“萨都剌”的蒙古语读音而定其为蒙古族,是孤证单行,显得勉强。他通过较充分的文献梳理与考索,提出“萨都剌为回族人”的结论。同时针对萨都剌在《溪行中秋玩月》一诗中自述“有子在官名在儒”,其以儒自居,似乎与其伊斯兰教的信仰龃龉不合,周先生辨析说:“他们(回回人)虽从根本上保留了伊斯兰教精神,但为了生存,也同佛、道、儒和平共处,所以萨都剌以儒自居或同佛、道应酬周旋,也是可以理解的。”[14]这是根据元帝国多族文人和平相处的时代语境所做出的判断,即如查洪德先生所看到的“元代有数量众多的蒙古、色目文士、诗人,他们……置根中原文化,师从中原大儒。……具有相同的国家观念与文化观念,有着共同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15]23。由此周先生就较好地诠释了萨都剌的族属与信仰表面矛盾的问题,因而结论是可信的。
关于萨都剌时代、生平的研究,这是周先生研究的立论基础,他的关于萨术贡献的考察,都是以元代社会时代景象和萨都剌立身行事的人生经历为基础的,即“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恩格斯语)。尽管他的一些提法还时有阶级分析法的烙印,但他对萨都剌生活时期元代文化特征的把握还是颇有识见的,即“由释、道兼容,到尊儒崇尚宋元理学”,但他又清楚地看到:萨都剌“在元代不是以理学家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而是以抒情诗人的身份活跃在元代。萨氏以‘情’而同理学家的‘理’相抗衡,这在元代,是引人深思的。”进而提出“我们应当从这个背景下,去研究萨都剌的思想和创作。”[6]19同时,他将萨都剌的生平划分为三个阶段给予观照,即穷困潦倒的青年时代、仕途蹭蹬的中年及其消极避世的晚年,认为他的文学创作由此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关于萨都剌的思想,周先生也有探究,认为萨都剌以“儒”自居,但他又不是宋元理学的儒,而是“读书识礼的士大夫”,信奉“忠孝仁义”的儒学观念;同时,他迷信道教,相信羽化登仙之术,也像李白一样慕道参禅,幻想着“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或者慕陶潜之为人,归隐田园了。对于这种消极思想,周先生辩证地指出:“萨都剌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思想,还不能一概以迷信而论之,应当看到他对现实的不满,只能在虚空与避世归隐中来寻找寄托了。”[6]26
二是,周先生萨都剌研究最重要的成绩是对萨都剌文学创作的深度阐释。他认为萨都剌是“把一生的精力用在了诗歌创作上”的少数民族诗人。其《雁门集》存诗800 余首,数量虽不多,但内容相当丰富。就《雁门集》中的诗体周先生做了详细的统计:“七言绝句230首,七言律诗208首,五言律诗138 首。七言古诗100首,五言古诗36首,五言绝句28首,六言诗6首,此外又有乐府歌行体古诗15首,又有‘曲’19首,‘谣’2首,还有宫词8首(其中七言古诗4首,七言绝句4首)。《雁门集》还收有萨都剌的长短句,即词14首。”[7]109由此认为,萨都剌的诗“诸体俱备”。如以题材来论,萨都剌诗有家国幽思之作、身世感怀之作,以及“宫词”和“艳情”之作等三大类。在书写家国幽思的作品里,既有刺时政之得失、忧民生之多艰、反争战之残民等堪为“诗史”的作品,也有山水、怀古与边塞诗,诗人咏边塞风光之奇异,写山水之壮丽,是“《雁门集》中独具特色的创作”。在身世感怀的诗作里,诗人主要写经商之艰苦、身世之贫困,以及恋亲思乡、病苦求仙乃至仕与隐之间徘徊矛盾,见出元代社会一个一生都在“贫困中挣扎”的下层文人丰富、敏感的心灵世界,因而具有“元代文人精神史”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萨都剌还写了许多“宫词”及艳体诗,见出其创作的复杂与丰富,杨维桢《宫词序》就认为萨都剌“《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周先生则提出:“对于萨都剌的艳体诗,我们还不能仅从艳情去理解,需要深长思之”[7]106。上述研究,可以说是学界对萨都剌诗歌内容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梳理,其意义自不待言。
关于萨都剌的诗歌艺术特征,周先生先看到,萨都剌“一生都处于刻苦写诗的境界中,是一位典型的苦吟派诗人。”[7]101但同时又指出:每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都是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诗人的一生,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雁门集》中,可以看到除了清新俊逸之外,萨都剌有的诗像陶渊明那样冲淡,有的又如李白那样豪放,还有的显示出李贺式的奇谲。在这种多样性的风格中,清新奇特、俊逸流丽贯穿始终,在他一生中是比较稳定的特色。”[7]105周先生还专门就萨都剌诗歌的意境做了细致的探究,认为“他一反宋代诗人多以议论入诗的常态,他在诗的意境构成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具体的:一是“融情于景,情从境出”;二是“从平凡的事物中找出诗意,并熔铸成优美的意境,这正显示出他作为诗人的本领。”[7]109与此同时,还对萨都剌的诗法进行了归纳,认为有“直中曲”、“静景动写”、“移情式”、对比以及运用了比喻、通感等各种修辞手法等。
三是,关于萨都剌诗歌艺术的渊源问题,周先生赞同翁方纲的观点,认为要考察萨都剌的诗歌创作,应从汉魏乐府到唐代刘禹锡、王建再到元代的虞集、杨维桢等人来看萨都剌所受的影响。“从唐、宋、元三代甚至从整个诗歌发展史上来考察萨都剌的诗歌,这个见解还是十分正确的。”[7]116并且经过细致的对比分析,他提出萨都剌诗是“转益多师”的结果,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继承了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才形成了他自己艺术风格的。“作为萨都剌的诗风来说,萨都剌就是萨都剌”。他“既继承了古代诗歌的优秀遗产,同时又以‘未信玄晖独擅能’的气魄,发展了我国古代的诗歌艺术。”[7]117细读里的古今对照,考据背后的情思点染,显示出研究者的识见——这样的研究在今天也是经得住推敲的可信之论。
四是,萨都剌的影响研究。作为有元一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汉文诗家,萨都剌深受时人及后世好评,周先生利用考据之法,排比事类,考镜源流,通过对《雁门集》文献的考证、爬疏,既厘清了《雁门集》历代刊刻情况,也让人窥探到萨都剌在后世的影响。关于萨都剌诗歌艺术的贡献,周先生著有专篇,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萨都剌在元代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元诗“由宋复唐”的转变。“萨都剌不仅一扫往宋萎靡之弊,同时也一扫虞集缓弱之弊,使元诗由宋反唐过程中,显示出了应有的战绩。萨都剌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于虞、杨、范、揭之外,别开生面,自成一家。”[5]52其二,萨都剌在元代,通过诗歌创作的“长于情”,对抗宋元理学家的“理”,发展了我国诗歌的进步传统。提出:自宋以来,理学家以“理”入诗是“诗言志”的厄运。理学诗倡自邵雍,而周敦颐、张载、程颐等相继而作,他们掀起的诗风使诗既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发展轨道,同时又使诗歌创作脱离了形象思维,离开艺术创作的规律,使理胜于情,只会产生虚情假意的作品,“是诗歌发展的末流。”[5]52就在这种诗学背景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一度破坏了汉族的“风雅”,同时也冲乱了理学家的禁锢。自元好问开始诗学宗苏东坡,以其“凌云健笔”的才气与热情,对抗理学家的方巾气。萨都剌在元代并非理学家的门徒,他一生以诗人自居,而不以卫道士自任,很有点纯文艺家的味道,他的创作使诗歌创作回归诗言情的轨道上来。因而可以说,萨都剌“缘情而歌,表现出了某种民主精神,发展了我国诗歌的进步传统。”[5]54同样的见解,还可见于十年后李延年在《试谈萨都剌别开生面的妇女题材诗》中所做的相类表述:“萨都剌妇女题材诗涉及范围广体裁多样,通过对妇女命运的关注表达了一定的政治见解,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妇女观和民主主义思想,并‘最长于情’,未染道学气,客观上表现了以情抗理的进步倾向。”[16]其三,萨都剌在诗歌艺术上发展了唐代以来意境派的创作路线,推动了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唐代发展起来的诗的创作讲究意境,到了晚唐已成为理论上的自觉,而萨都剌在创作实践中,发展了“意境”在诗学上的运用,因而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这是他的贡献之一。“萨都剌在元代既然以‘唐音’‘唐体’为诗歌创作追求的最高目标,这就在艺术上,一反宋人之道:不以文字为诗,不以才学为诗,不以议论为诗。他在诗歌创作不是抽象派,而是意境派。”[5]55可以说,周先生就是这般,从文献的细节出发,借助他所掌握的理论武器,总是在别人忽略的角落,提出问题,寻幽探密,揭橥了“事实历史”的真相。因此,他的研究获得了学界认可。如元代文学研究名家查洪德先生在《辽金元文学研究》一书中就指出:“80年代后半期,周双利对萨都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7]刘嘉伟也看到:“周作注意到了萨氏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详尽分析了萨都剌常用的艺术手法,并指出了萨诗在元代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是此一时期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成果。”[18]
三、群星闪耀的杨景贤、耶律楚材等作家的研究
萨都剌研究只是周先生元代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他心中似乎有一个元代文学民族作家创作的全图,所以他对众多少数民族文人都有细致的梳理,这众多的点组合在一起,犹如群星闪烁,构成了元代文学多维立体的璀璨星空。
第一,关于杨景贤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对杨氏的生平、思想及创作面貌皆有清楚的观照。周先生连续发表了《杨景贤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论杨景贤的哲学思想》(《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杨景贤戏曲著作考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三篇论文,涉及到杨景贤戏曲著作考辨、杨景贤的生平、哲学思想与创作等方面。作为元末时期一位蒙古族汉文作家,杨景贤用汉文创作了不少杂剧与散曲,周先生通过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主题倾向,梳理了杨景贤的思想面貌,即不满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仰慕神仙生活;具有市民阶层的思想,同情受压迫最深的妓女,怀疑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甚至对天道循环、因果报应也多所质疑等。由此看出,杨氏是一个离经叛道、具有批判现实精神的少数民族作家。并且对于杨氏思想,在《论杨景贤的哲学思想》中周先生做了深入的讨论,这也是其杨景贤研究的重要成绩。他认为杨景贤在政治思想上,反映出一些民主主义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他对剥削者的残暴不仁表露出极端的不满,以及对功名富贵思想加以否定。而其哲学思想更多地代表了市民阶层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对天命论的大胆怀疑、宗教观中带有民主倾向、以人性的“情”同理学的“理”相抗衡。对此,罗海燕提出,周双利先生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去评判杨景贤的哲学思想,既肯定了其民主性的精华,同时也指出了其带有封建性的消极的一面。”[19]76关于杨景贤的创作情况,周先生也有较为详细的文献考证。应该说杨景贤杂剧著作的归属问题,在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杂剧《西游记》一度被认为是元代吴昌龄所著,《刘行首》也可能不是杨景贤的作品,其著作权宜归于无名氏[20]等。为此,周先生对杨氏所存的19种杂剧:《天台梦》《生死夫妻》《玩江楼》《偃时救驾》《西湖怨》《为富不仁》《待子瞻》《三田分树》《红白蜘蛛》《巫娥女》《保韩庄》《盗红绡》《鸳鸯宴》《月夜西湖怨》《大周东岳殿》《海棠亭》《两团圆》《刘行首》《西游记》等以及一些散曲的创作情况均做了全面的梳理。对于周先生的贡献,罗海燕说:“有关杨景贤杂剧著作的归属以及篇目诸问题,由之基本得以解决。”[19]76
杨氏杂剧《西游记》的地位和文学史价值,是周先生用力较多的研究。他指出,该剧出现在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之前,对《西游记》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推动作用,但杂剧《西游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吴昌龄的作品,杨景贤长期湮没无闻,周先生以为“这是不应该的”。经过仔细的文献考据,他提出:“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到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的诞生,这中间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21]137认为“文人加工创作的《西游记》只能从杨景贤创作的《西游记》杂剧来进行研究,因为杨氏杂剧提供了完整的内容与艺术形象,因而它在《西游记》演变史上,便不能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了。”[21]138具体的,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在推动吴承恩《西游记》小说创作的发展上,至少起到以下几方面的作用:第一,在思想上,杨景贤的《西游记》保持了孙行者这个反叛者的形象,……但这个剧的核心是唐僧取经必须收服一个反叛者孙行者,由他作为护法行者,战胜妖魔,才能取得真经,这本身便是意味深长的。……通过这个艺术形象,比较曲折地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讽刺态度。这些地方,在吴承恩的小说中有所发展,也有所变化。第二,在构思上,杨景贤的杂剧为《西游记》提供了全部完整的情节,它已将神猴的故事与唐僧取经的神话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杨景贤的杂剧里,神猴大闹天宫与唐僧取经的故事融为一体,已成为完整的艺术结构,为吴承恩写作小说《西游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杨景贤杂剧中的人物稳定化,为吴承恩创作小说《西游记》的人物形象提供了蓝本。认为“到了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取经人物已固定为唐僧、沙僧、猪八戒与孙悟空。在杂剧中,孙行者一出现,降妖捉怪,排难解纷,唐三藏已退居次要地位,孙行者却成为英雄,这在西游故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演变。杨景贤杂剧中的神猴,更接近早期的传说,但又有新的发展变化,它不同于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的孙行者,但吴氏小说中的孙行者,正是从话本与杨景贤杂剧的神猴吸收来的。”[21]139同时也看到,杨景贤笔下的神猴,更多些“野性”与“妖气”,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更完善,更具有反抗性。“这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杨氏杂剧与吴氏小说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第四,杨景贤杂剧《西游记》的诙谐、幽默的风格,对吴承恩小说《西游记》艺术风格的形成也起了良好的影响。而后21世纪有云峰[22]、张大新[23]、陈霞[24]等人对此问题也有新的探究,尽管时有开拓,但基本观点还是与周先生有许多相近之处的。周先生甚至这样提出:“《西游记》杂剧与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明时期并驾齐驱的长篇巨作。”[21]140这样的结论在学界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响,如荣苏赫等主编《蒙古族文学史》在论述杂剧创作时,就将杨氏杂剧《西游记》列为专节,指出:“杨景贤作为著名蒙古族杂剧作家,以他的杂剧创作,特别是《西游记》,对元杂剧内容形式的发展,对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
第二,耶律楚材是蒙古帝国初期杰出政治家,也是开创元代文风的领袖人物,周先生对他也有专文讨论。在文章中,他肯定了耶律楚材引导成吉思汗、窝阔台汗采纳“汉法”的作为,认为他是蒙古帝国由武力向文治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是“蒙古统治时期具有远大眼光的政治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文作家。”为此,周先生总结了耶律楚材诗歌的特点:“耶律楚材的作品,诗歌创作的成就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散文。观《湛然居士集》,其诗内容不外谈禅、抒怀与纪事三类,在三类中,记事尤为重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较富有文学性。”[26]关于耶律楚材诗歌的艺术,认为有两大特点,一是“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二是“以议论入诗,使诗显示出理性的美”,并提出:耶律楚材“开创的诗风对元初粗豪、质朴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他是一位开一代诗风的作家。”不仅如此,周先生还对耶律楚材家族其他成员的文学创作做了探究,梳理了耶律铸、耶律季天、耶律柳溪等人的生平与创作情况,尽管还是粗线条的梳理,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家族文学研究的意识,其前沿性还是让人感佩的。
第三,贯云石是出身于贵胄之家的维吾尔人,是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他有文武之才,曾拜姚燧为师,为元仁宗之子硕德八剌(后为元英宗)的“潜邸说书秀才”,官居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后辞官,“卖药隐居钱塘市中”。卒后获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京兆郡公,谥文靖。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不仅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还是书法家和音乐戏曲名家。为此,周先生对贯云石的文学贡献做了较细致的考察,认为贯云石的诗词与散文创作,“在艺术风格上属于浪漫主义这一流派的,唯早年豪放瑰奇,晚年诗风冲淡”,“顾嗣立说他的风格是‘绮丽清新’,其实,贯云石的诗作虽然绮丽,但仍不失豪放,其清新绮丽之处,正补苴元初诗风的过分粗豪。”并且,贯云石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散曲,他堪称“曲中状元,词家妙手”。归纳起来,贯云石散曲的思想内容大体有三方面,一是对隐逸生活的赞美,二是对闺情和离情别绪的吟咏,三是关于写景、咏物的曲作。在艺术上,“其以散曲写景、抒情、议论,造语妖娇多姿,真如少美临杯。”因而周先生提出:“贯云石不仅以其独特的散曲艺术,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因为他深通音律、擅长戏曲,影响所及,他又是戏曲声腔——海盐腔的创始人,故他在我国戏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27]9
第四,马祖常被认为是元代少数民族代表性诗文作家之一,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较多。周先生也对马祖常著有《元代雍古作家马祖常评述》一文予以讨论,文章考察了马祖常的族属问题及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民族特色,以及马祖常的宗教信仰与政治思想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等,并指出马祖常的诗中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性,又受着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两者的统一才反映出马祖常思想的复杂性和完整性[28]87。此外,周先生还观照了马祖常的父亲马润、叔父马世德的创作情况,以此表明其家族成员之间文学创作是相互影响的。
第五,除了像萨都剌、杨景贤、耶律楚材、马祖常、贯云石等名家以外,周先生还花大气力对一些名气并不大的蒙古族或色目文士做了认真的研究,约有六十余人之多,其目的就是要表明,少数民族文家就像群星一样闪耀在元代文坛之上,“千灯互照”,共同构建了元代文学的繁华局面,在中华文学史历史长河中他们也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比如琐非复初,西域人,精音律,其生平事迹不详。关于他的创作情况,主要依据的文献是周德清《中原音韵后序》,周先生由此推论说:“琐非复初出身于贵胄之家,整日笙歌盈耳,伶女满堂,这使他熟识歌舞之道,又加上读书西域,这就使他对音乐歌曲的爱好更富理性色彩,所以周德清把他当做‘知音’来对待,绝非偶然。在序言里,由他对《大德天寿贺词》的吹嘘来看,生活态度不出贵胄之习,文章虽不乏文采,但对于乐理阐明,要胜于对文章的表达。从文字表达来看,也不过是停留在一般‘读书士子’的水平上,不算特别杰出?”[7]245但根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的断语,周先生还是肯定琐非复初的艺术影响,认为琐非复初在政治态度上,是“贯云石一类人物”,“在词曲的爱好上,又是清代纳兰性德的先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琐非复初还是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的”[7]245。再如贴里越实,《元诗选癸集》不载其事迹,《元史》一百二十四卷《塔本传》附《迭里威失传》。迭里威失之曾祖为塔本,伊吾庐人。“伊吾庐即古伊州,在今新疆哈密县附近、贴里越实为合鲁温氏。”周先生认为他是维吾尔族,并据《元史》推断,迭里威失是元代中期能干的官吏,其生活时期为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年间。其创作仅有诗一首传世,见于《保宁府志》与《元诗选癸集》,题为《王望山》。周先生还分析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虽是一首短诗,却也不乏神韵”[7]243。这样的小作家人数众多,再如塔不䚟,或作塔不台,字彦辉,一作彦翚。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元史》《新元史》等历史文献中,周先生通过爬梳文献,认为他主要活动在武宗时期,“大约活了五十多岁。”至于他的族属,“《元诗选癸集》说他是河南人,但那是后来他定居河南,并不能证明他是汉族人。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指出,塔不台为‘伯牙吾氏’,伯牙吾氏为西域钦察人。”并根据《元诗选癸集》所录的五首诗,提出“塔不䚟,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其“船浅碧流如坐镜,客依银汉若乘槎”(《安流晓渡二首》其二)诗句,“意境优美,道人所不能道”,“塔不䚟的诗才,堪与元代汉族诗人媲美。”[7]249凡此种种,周先生通过考据、辩证之法,考察了这样许多名气不大但确是构建元代文学景观不可或缺的少数民族文学家,这对我们了解元代文学整体风貌、对元代文学做通观性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种追求“事实的历史”之真[29]的研究,也为后世的元代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四、“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理论的探索与践行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并于次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其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在这个实体里各民族都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其实,早在费孝通之前,历史学家张博泉也提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及“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样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其中“中华一体”是指元明清时段。[30]可见,元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之一。此期政治、经济、文化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即具有一种“多民族共有文化精神”[15]23,如今这些理论已是学界的共识,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31]。而在此理论形成过程中,费孝通、张博泉等一些著名学者自然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但周双利教授等边地的学者则结合自身民族地区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也分别做出了自己的理论探索,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大合唱中的重要音符。周先生就明确地主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以文学创作来说,在古代,我国各民族的优秀儿女,都曾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汉文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6]16而这正是他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初心,也是他一直奉行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的具体落实,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
如前文所说,周先生对马、恩经典著作是下过功夫的,对马、恩、列宁的民族理论也做了认真的探究。他和王坤合著《论马克思的民族观》一文,发表在《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上。文章集中阐述了作者开放、圆通的民族观念,可以看作是其民族文学研究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必须对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认识、掌握它的发展规律,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处理许多重大的民族问题。”[32]44提出“民族问题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贯穿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32]44因而,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他们还提出:“我们学习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思想和他的民族观,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同国内兄弟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32]45—46“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32]47正是这种民族观,周先生的民族文学研究才有了立论的准的,才使他能够圆通、包容地看待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文人的独特艺术才能和不凡的文学成就。
(二)少数民族文人为元代文学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元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亦然。正如查洪德先生所指出的,元代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大元气象”。“元代文学以各种方式张扬大元国土、国力之大,气象、气势、气魄之大。因‘大’而有包容,而和谐。……又因‘大’而宽松,有利于思想文化及文学的自由发展。”只有“把握这一时代精神,才能认识元代文学的特点”[33],而这也是周双利教授治元代文学的基本观念。他每每探究元代少数民族文家的创作,总试图在一种通观的视角下,去处理元代文学“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具体的,他承认元代文学的兴盛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诗人、文家共同造就的,正是由于“多元”才最终形成了元代文学的“一体”。比如研究萨都剌时他认为萨都剌“缘情而歌,表现出了某种民主精神,发展了我国诗歌的进步传统。”[5]54“萨都剌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于虞、杨、范、揭之外,别开生面,自成一家。”[5]52并特别强调萨都剌对元代文学“一体”形成所做的重要贡献:“当年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及其儿孙,他们的战马曾驰骋欧亚大陆,他们后来的梦想也不过是统治天下的雄心,而蒙古铁骑踏成的帝国,并未永世长存,但带来的却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元代出现了吐蕃、康里、畏吾儿、唐古特、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诗人,萨都剌是作为回族诗人,为祖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萨都剌《雁门集》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它证明:我国的文学,即便是用汉语汉字创造书写出来的文学,也不仅仅是汉族努力的结果,我国各族的杰出作家,都为我国文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5]56。他研究贯云石时则坦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不能以正统文学观念来看待元代的文学。从正统文学出发,只有古文诗词算作文学,头脑里只有虞、杨、范、揭所谓元诗四大家。我们也应看到,散曲、杂剧也是我国文学的正宗。元代的时代潮流与文学潮流造就了贯云石这样的散曲作家。贯云石以他特有的才能,推动了元代文学的发展;他又以他的声腔音律影响到后世戏曲的发展,我们应对他的文学艺术的业绩给予公允的评价。”[27]9对于马祖常,他提出“马祖常以绮丽清新的诗歌,在元代唱出了民族团结的新声,仅此一节,也是应当肯定的。吴梅先生在《辽金元文学史》中论及马祖常时指出:‘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云。’又说:‘其诗才力富健,如《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迥薄奔腾,具有不受羁鞫靮之气。至元间,苏天爵请于朝,刊行其集,自为之序,称其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效慕之。与会稽袁桷、蜀郡虞集、东平王构,更迭唱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其推之者至矣!’吴梅先生也对马祖常评价甚高。他的评价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28]90而对于李齐贤,他提出:“研究元代李齐贤这类域外词人,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我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并不仅仅是汉族作家的努力的结果,我国各民族的成员如蒙古族、藏族、满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汉文作家,还有如今是其邻国的作家,他们的汉文诗文作品,对中华文化的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课题。像李齐贤这样的作家,就以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明证。”[7]412上述种种足以说明,在周先生的心目中,元代文学是多民族文人“多元一体”共同创造的结果,没有各民族文人智慧和才情,就不可能产生元朝一代文学的繁盛,即如查洪德所看到的“不同民族文人书同文、文同趣,体现了元代文学精神风貌深层次的一体性。”[15]23
(三)少数民族作家参与了中华文学史的建构
周先生甚至还从更为广阔的时空去看待中华文学发展过程中“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在古代,我国各民族的优秀儿女,都曾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汉文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南北朝,《敕勒歌》唱出了鲜卑人的心声,这首诗曾被诗人元好问誉为‘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在唐五代,被称作‘多慷慨之音’的李珣,其先为波斯人,他的词作也被后人所欣赏着。越到后来,少数民族作家从事汉文创作的,已经越来越多了。”[6]16所以,他还关注元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少数民族文人的创作,如清代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哈斯宝、古拉兰萨、萨岗彻辰、贡桑诺尔布、藏族著名诗人仓央嘉措,尽管考察的数量不多,但这也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热爱,以自己的非凡才华和艺术创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辉煌的成就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周先生这样评价尹湛纳希:“尹湛纳希首先是蒙古族的杰出儿女,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在积弱不振的中国,希望通过呼唤蒙古族的英灵,来唤醒蒙古族,让受压迫、受歧视的蒙古族人民,不再喘息于满族、汉族统治阶级的重压之下。他的这种意识,不仅有利于蒙古族,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欺压中华民族所发出的反抗呼声!他的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首先是从民族的历史与民族的文化中去吸取精神力量。”[34]他这样说古拉兰萨:“他把汉诗的五、七言诗如绝句、律诗移植到蒙古族诗歌园地中。他的诗讲究较严格的格律,讲究押韵、对仗。诗的语言精练、形象,他把蒙古族古典诗歌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7]388他还肯定贡桑诺尔布:“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应当自立于世界强大的民族之林,这种思想同样表现在他(贡桑诺尔布)的诗里。”[7]395他也认真分析蒙古族小说家哈斯宝《新评红楼梦》及其回批,“独具慧眼,不落入旧红学家的俗套”,并分别从主题、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技巧等方面揭示其“红学”成就,他得出结论说,哈斯宝《新评红楼梦》“再一次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蒙汉文学的交流,形象地表明《红楼梦》对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起了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35]所有这些少数民族文人都是中华文学史的创作主体,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审美观念、民族心理都融进艺术的创造里,以一种非凡的“边缘的活力”丰富了中华文学审美内涵,拓展了中华文学的版图。
综上所论,作为一个身处北部边地的学者,周双利教授立足边疆,建设内蒙古,五十年来秉承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章黄学派“无征不信”的治学品格,以一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学研究领域默默耕耘,努力工作。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发表成果,由萨都剌、杨景贤、贯云石等名家至一些声名不显的诸如琐非复初、塔不䚟等人,由元代少数民族文人而拓展至尹湛纳希、哈斯宝等清代民族作家,对“中华一体”形成收官期——元明清民族文学的成就做了全方位、多维度的考证、爬梳与艺术阐释,尽管成果数量并不是很多,他也不是学界走红的学者,但他的研究从小的方面看,对于内蒙古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就大的方面而言,对于“中华大文学史观”的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一个边地学者应有的贡献,成为新时期元代文学研究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是值得学术史重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