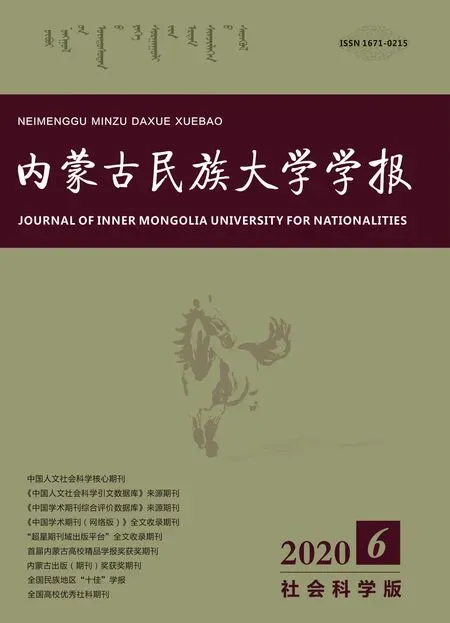论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及其特点
慈志刚,崔 勃
(内蒙古民族大学 法学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028000)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苏丹正处于历史上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如土耳其人、埃及人和英国人在苏丹形成的外来统治集团,另一方面则来自苏丹传统社会的分裂。从苏菲主义信仰到部落社会结构,在苏丹实现国家独立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成为了抗争型政治的旗帜。与其他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苏丹通过马赫迪信仰最终实现了对苏菲主义的超越,为独立民族国家提供了新的政治整合工具。
一、马赫迪运动的历史背景
第一,埃及未能形成对苏丹的有效治理。19世纪20年代,苏丹尚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其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多次派兵征讨苏丹,到1879年苏丹基本被埃及政权占领,埃及利用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维持对苏丹的管辖。苏丹被征服的同时也终结了利开林克(Likailik)的维齐尔、夏基亚(Sha’iqiyya)部落和马穆鲁克人(Mamluk)之间的激烈权力争斗,但埃及的占领并没有使苏丹完成统一,也没有对此新征服地区实现有效控制。苏丹领土辽阔,国内遍布沙漠、沼泽和激流,错综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利于军队的有效活动。另外,苏丹还存在着悠久的部落社会传统,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不利于中央政府实行集权统治。这些因素导致埃及总督既在经济上无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征服者对苏丹控制的有效性。在埃及人的势力无法触及的地方,就有可能形成权力真空,这些区域便成为本土居民反抗外来统治的动员场所。
来自埃及的统治集团是由非埃及的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克斯人、亚美尼亚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商人组成的一个成分复杂的精英团体,而真正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往往在军队、行政和宗教部门的下层机构任职,因此,真正对苏丹进行统治的是外来集团。我国学术界在讨论马赫迪起义的斗争指向问题时,往往也会因统治集团的复杂性而陷入争论。传统观点认为,马赫迪运动是一场反抗英国殖民的起义,实际上这样的定性分析较为模糊,并不能够完整反映马赫迪运动的本质内容,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注意到马赫迪起义的发展变化过程,早期指向埃及占领者,后期指向英国殖民者,[1]而美国学者埃里克·吉尔伯特也认为,艾哈迈德(即马赫迪)鼓吹将土耳其人(当时泛指外国人)赶出国土的必要,[2]这里所说的“埃及占领者”和“土耳其人”实际上都是指上文所说的成分复杂的外国精英集团。在苏丹人的观念中对入侵者的看法便不再仅限于埃及人,而是扩大到整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他们背离了伊斯兰信仰,并与信仰基督教的异教徒合作。从开罗派遣而来的官员和士兵对苏丹人极尽压迫与搜刮之能事,这更加深了本土居民对奥斯曼帝国的普遍愤恨。还有一些从北方来的埃及人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因而加重税负和征召奴隶入伍,这些都成为盘剥苏丹人的手段。行政体系内部人员变动频繁,从1825年到1885年,喀土穆的总督不少于25位,他们的任期都非常短,[3]这种涸泽而渔的治理政策使苏丹的形势更加复杂。
第二,埃及统治者的经济压迫。在埃及征服苏丹之前,苏丹窘迫的经济便已经使部落冲突加剧,并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尼罗河流域的可耕地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再加上部落内部争斗频繁,这是18世纪的达纳卡拉部落(Danaqla)和19世纪初的贾里因部落(Ja’liyin)出现移民现象的主要原因。土耳其人的到来使北方部落居民南迁至上尼罗河州和加扎勒(Bahr el Ghazal)地区,他们或从事奴隶贸易或在奥斯曼-埃及军队中服役。而人口流动的另一个原因是穆罕默德·阿里准许征召奴隶入伍的政策,进一步刺激了奴隶贸易。此外,苏丹人去麦加朝觐的频率更加密集,客观上使苏丹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更加频繁。特别是科尔多凡地区靠近象牙、树胶和奴隶等重要商品的原产地,人口的流动和贸易的活跃使当地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这种人口流动现象极大地破坏了传统部落社会的凝聚力,再加之部落本身掠夺成习,使得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加。
部落社会结构瓦解的最主要结果就是城市化进程加速,传统部落社会权威快速衰落,一些本土精英进入到埃及人的政府中当官。他们为了获取权力而为虎作伥,严重削弱了他们作为部落首领的威望和声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部落社会合法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侵蚀。另外,埃及人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对部分家族和苏菲教团进行笼络,在政府中委以官职,从而达到在部落和宗教层面分化本土社会的作用。
第三,苏丹伊斯兰教的分化。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区出现以回归经训、纯洁信仰为目标的伊斯兰运动,如沙特的瓦哈比主义、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和阿尔及利亚的卡迪里耶教团纷纷打着伊斯兰教复兴的旗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质疑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宗教权威。苏丹最有影响力的苏菲教团是哈特米教团(Khatmiya),它是赛努西教团在苏丹的分支,19世纪由伊德里斯的弟子穆罕默德·奥斯曼·米尔盖尼(Mohammed Uthman al-Mirghani al-Khatim)创建。苏菲教团向苏丹渗透始于丰吉苏丹国时期,这种游走于帝国边缘的神秘主义教团的出现是对传统宗教秩序的反叛。苏菲教团的导师往往被宣传为具有某种神奇能力的圣徒,通过其传教行为,获得大批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将苏菲主义进一步扩散,在这个过程中,成功的苏菲教团会脱离已经存在的苏菲秩序而获得独立,这样就导致苏菲主义的传播本身构成了一个不断裂变的基因图谱,不同教团对伊斯兰教的不同解读如细胞分裂般解构着传统的社会秩序,使社会认同与权威的构建变得支离破碎。
埃及被征服以后,宗教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变得明朗化,以艾资哈尔大学为代表的逊尼派伊斯兰信仰被引入苏丹。作为征服者的官方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推行被赋予了对苏丹进行社会整合的政治目的,通过沙里亚法来建立政府的宗教和政治权威,但由于苏丹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部落社会结构,沙里亚法的推行并不顺利。在地方层面上,苏菲主义宗教学者根据个人对伊斯兰法的理解以及部落习惯法来调节社会争端。从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输入大量训练有素的乌里玛对苏丹传统权威构成了双重挑战:首先是沙利亚司法系统的引入意味着部落司法的终结;其次是艾资哈尔大学的乌里玛的到来破坏了传统的苏菲主义秩序。因此,苏菲主义与正统伊斯兰教的冲突使民众在宗教效忠对象上出现了分歧,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也直接影响到政治上的斗争,这种信仰上的危机最终演变成了政治上的危机。
二、马赫迪国家的治理体系
1881年8月,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称“马赫迪”,号召人民进行圣战,驱逐外来统治者。起义很快得到苏丹民众的支持,起义队伍也不断壮大。到1885年马赫迪军队攻占首府喀土穆,基本上解放了苏丹全境。6月马赫迪病逝,这场运动开始转向国家建设阶段。马赫迪国家的建立是苏丹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国家,各民族、部落和教派都处于马赫迪政权的管辖之下,为构建苏丹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第一,马赫迪国家的等级制度。马赫迪国家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马赫迪的弟子穆哈默德·阿卜杜拉援引先知时期的先例,将归附马赫迪的追随者称为安萨尔(Ansar),按照归附时间的先后将安萨尔分成不同的等级。第一等级由马赫迪的最早期弟子组成,他们在穆哈默德·艾哈迈德宣布称为马赫迪以前就已经追随他,因此也是马赫迪国家的功勋元老;第二个等级是在阿巴岛的安萨尔,也就是马赫迪揭竿而起时追随他的人;第三等级是在卡迪尔山根据地时期投奔马赫迪的人;第四等级是离开欧贝伊德以后投奔马赫迪的人。[4]这种安萨尔组织形式类似于哈里发欧麦尔时期从波斯借鉴而来的迪万制度(Diwan),它将每一场战争中归附先知的战士登记在册,并规定了每个人从新征服地区的税收中领取相应的补贴,通过这一制度创造出一批新的土地贵族,他们取代传统部落领袖,成为国家的支持者。马赫迪国家的安萨尔制度也收到了同样的效果,新的统治阶层取代了那些与土耳其人有关系的商人和部族。因此,较早跟随马赫迪的人成为新的统治阶层,此外,这个新的统治阶层还包括马赫迪与哈里发们的亲属。比如阿卜杜拉成为哈里发以后,其亲属和他所属的塔伊莎部落处于统治制度的最顶层,国库每个月相当大一部分开支用于哈里发家眷和马赫迪家族的支出。
第二,马赫迪国家的行政体系。国家最高统治机构分为三个组成部分:马赫迪国家最高指挥机构、财政体系和司法体系。马赫迪时期的最高指挥权属于马赫迪本人,他任命其重要弟子、得力助手、亲密战友穆哈默德·阿卜杜拉、穆哈默德·希卢、穆哈默德·沙里夫为哈里发,马赫迪和三个哈里发构成了起义的最高指挥机构。[5]马赫迪去世前,其亲属也参与起义指挥,但主要决策仍由马赫迪在与哈里发商议后决定。马赫迪是立法者与决策者,哈里发是执行者。阿卜杜拉成为马赫迪国家哈里发后,他既是行政最高权威,还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与其任命的助手磋商要事,偶尔会邀请马赫迪时期的元老参与咨询会议。在地方层面,马赫迪国家设置了20个省,省按其职能分为两种类型:军事省和都市省。军事省处于马赫迪国家边境地区,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领土和发动圣战。都市省则负责为国库征集税收,为边境省的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各省的统治者是埃米尔,在所在辖区拥有无限权力,埃米尔对哈里发负责,而省内的地区级埃米尔对省级的大埃米尔负责,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
第三,马赫迪国家的财政制度。马赫迪的财政系统也是按照先知时代麦地那的管理体系组织起来的,伊斯兰教早期扩张中的战利品分配方式成为马赫迪国家效仿的对象。战利品的五分之一、天课和什一税被作为公共财产归马赫迪分配,这形成了马赫迪国家的金库制度。最初的中央金库设在卡迪尔山,由马赫迪的挚友艾哈迈德·瓦德·苏莱曼管辖,其中的财物都是战利品。后来征服的区域逐渐扩大,欧贝伊德、沙伊坎、喀土穆和辛纳尔等地陆续纳入统治范围,在战争中收获的黄金、武器和奴隶等都被上缴国库。随着中央金库的日渐充盈,其功能出现分化,地方亦设置地方金库,用以处理地方财务。地方财务由各省埃米尔管辖,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一些为前政权效力的官员继续在金库任职,利用他们以前学得并使用的会计和簿记方法进行管理。[6]公共财政是马赫迪国家的行政中枢神经,因此,国家对财政系统给予充分的重视,每天的财务收入和支出都有专员向哈里发进行汇报,在财务方面,马赫迪国家并不反对更加现代的管理方式。
第四,马赫迪国家的司法制度。马赫迪在司法方面也仿效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榜样,强调国家合法性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创立沙里亚法和以法治国。苏丹社会部落习惯法根深蒂固,苏菲教团的活动使习惯法进一步巩固。英国学者霍尔特(P.M.Holt)认为,有必要对苏丹国内,特别是西部错综复杂的定居部落和游牧部落进行区分,马赫迪的官僚、财政和司法人员多来自于前者,而军队和哈里发阿卜杜拉的统治精英则来自后者。[7]马赫迪在部落社会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神权政治,它将沙里亚法限定在必要的范围内,以此来调和部落习惯法,而且还能够在神学上赋予马赫迪以克里斯马式领导人的地位,从而具有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合法性。由此,沙里亚法的来源被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古兰经》和圣训;另一种是创制。马赫迪和阿卜杜拉借鉴了伊斯兰司法体系,设立了大法官的职位,并辅以数名助理法官,法官会依据经训和马赫迪的训诫审理案件。显然,马赫迪国家的司法体系除了伊斯兰教法所具有的神启本质以外,又被添加了马赫迪的个人色彩,并成为重要的司法来源。马赫迪国家禁止吸烟、跳舞和男子留长发等行为,禁止前往麦加朝觐,否定正统四大教法学派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赫迪国家背离了伊斯兰原则,它实际上是通过在司法体系上的创新,与旧的统治秩序划分出清晰的界限。
三、马赫迪运动的特点
从1885年到1889年,马赫迪国家通过其系统的治理,使国家发展达到顶峰,但在1882年沦为埃及殖民地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的竞争开始加剧,英法两国在非洲的较量使苏丹成为争夺的焦点。法国派遣远征军在苏丹的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殖民活动,英国迫于压力,将消灭马赫迪国家的任务提上日程。1896年英埃军队司令赫伯特·基切纳帅军远征苏丹,马赫迪军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终究无力对抗现代化的英军。1899年哈里发阿卜杜拉牺牲,苏丹的马赫迪运动最终归于失败。然而,赫迪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消亡,通过马赫迪对宗教秩序的整顿,对苏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马赫迪的救世主观念。马赫迪意为被真主引上正道的人,[8]但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之中并未提及这样一种头衔。在什叶派信仰体系中,十二伊玛目派相信,“隐遁的伊玛目”终有一天要重新返世,以救世主(即马赫迪)的身份来重新建立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制度。[9]苏菲主义后来也使用马赫迪的观念,但马赫迪又从什叶派和苏菲主义传统中获得基本要素,从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民间传说。[10]苏丹马赫迪运动和马赫迪国家从政治动员和权威构建来看,是通过超验神学的方式赋予世俗政治以合法性,属于韦伯所言的“克里斯马”类型的政治权威。马赫迪权威的树立需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土耳其、埃及和英国对苏丹的失败治理引发社会失范,造成社会整体性危机的爆发,从而形成对当时的政治体系、信仰体系和价值认同的彻底否定,使大众动员成为可能;其二是克里斯马式领袖所具备的超凡魅力,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超凡魅力源于其作为萨马尼耶教团(Sammaniyya)导师期间的谦卑、虔诚和苦行所积累的良好声誉;其三是赋予马赫迪神圣光环的宗教启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称受命于先知穆哈默德,这意味着在原则上,按照最初穆斯林模板建立社会秩序;在实践上,要严格执行沙里亚法,驱除19世纪奥斯曼帝国和西方带来的一切创新。[11]
第二,以先知时代原初伊斯兰教为导向重建秩序。奥斯曼埃及统治下的苏丹,不仅出现政治碎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存在各种伊斯兰派别的竞争,这种竞争客观上对政治碎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马赫迪构建的新的政治秩序必须能够弥合宗教上的分裂,而能够实现对艾资哈尔大学正统逊尼派学说和各种苏菲主义的超越就必须回到伊斯兰教还未分裂的逻辑起点。马赫迪在神学上宣布直接继承先知的权威,在实践上以先知时代为榜样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通过这种统治的象征性来确认政权的合法性。马赫迪将其从阿巴岛迁往卡迪尔山的运动称为“希吉拉”(Hijrah),[12]以效仿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那的行为。在马赫迪去世后,哈里发阿卜杜拉仍然沿用马赫迪的思想,通过肯定马赫迪的价值,将这种统治的象征性特征继承下来。在马赫迪国家的构建中,哈里发政治和军事上模仿欧麦尔时期的迪万制度,建立了安萨尔制度;在经济上,仿效穆罕默德时期的战利品分配原则创立了金库制度;在司法上,主张回到伊斯兰教创立之初的立法原则,反对后世的一切创新,通过这些措施,马赫迪国家为分裂的部落社会提供一种替代组织模式和意识形态基础,形成了以马赫迪和哈里发为中心的效忠体系,从而为苏丹国家超越旧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指南。
第三,超越苏菲主义秩序的神权政治。穆哈默德·艾哈迈德自称是先知穆哈默德的后裔,早年学习《古兰经》知识。在奥斯曼和埃及治下,艾资哈尔大学出身的宗教学者往往能够获得好的晋升机会,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始终没有离开苏丹,后来他加入穆哈默德·谢里夫(Muhammad Sharif)创建的萨马尼耶教团,过着禁欲苦行的教徒生活。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后来与穆罕默德·谢里夫决裂,加入了谢赫古拉什领导的教团,并成为其领袖。苏菲主义的特点在于其神秘主义、等级制度和反正统伊斯兰信仰的传统等,这种特点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王朝体系中遭到边缘化,但它却能够与部落社会结合在一起。超验的神秘主义能够增强宗教领袖的超凡魅力,等级制度能够使宗教领袖成为信仰的最高权威,而反正统伊斯兰信仰则又使信徒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此,马赫迪的早期成功与苏菲主义教团在部落社会的信仰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马赫迪国家的合法性构建过程中,苏菲主义造成的权威的多元性会使统一的公共权威无法树立,因此,马赫迪信仰最终超越了苏菲主义和部落认同,对具体的苏丹人的日常习俗也予以禁止,[13]为统一的国家提供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马赫迪的思想转变成排他性的神权政体。
总之,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及其创建马赫迪国家的实践是这一时期伊斯兰运动从传统社会基础出发向经训回归尝试的一次努力。马赫迪国家失败后,苏丹面临的社会危机仍然存在,马赫迪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并没有消失,因此,马赫迪主义对苏丹人民的斗争仍然发挥重要的影响。[14]同时,马赫迪主义也对西苏丹地区的伊斯兰复兴政治起到了推动作用。推翻土耳其和埃及的统治,并于1885年处死了戈登,这场由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领导的救世主反叛运动,不仅仅是苏丹历史上的重要篇章,还是现代穆斯林大起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