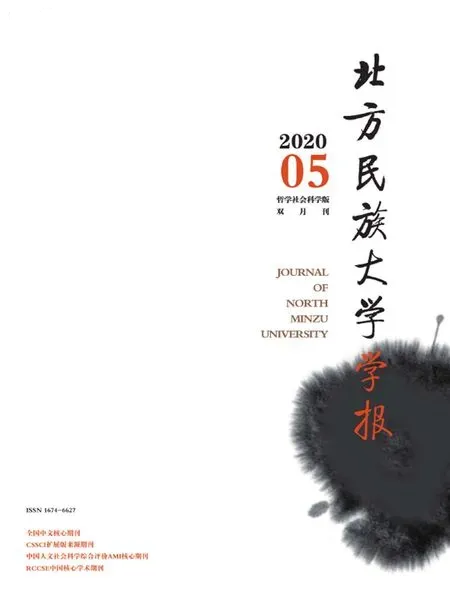马克思对斯密和黑格尔劳动观的批判与超越
张 鲲
(北方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活动。古往今来,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都对劳动的内涵和意义做了重要阐述。苏格拉底说:“如果你要土地给你带来丰盛的果实,你就必须耕耘这块土地。”[1](49)摩尔根认为:“对财产的欲望超乎一切其他一切欲望之上,这就是文明伊始的标志。”[2](213)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是创造财富的能动的要素。”[3](97)亚当·斯密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4](1)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5](209)。马克思在继承以往劳动学说合理内核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斯密经验主义劳动观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的批判和改造,揭示了劳动的真实内涵,实现了劳动观唯物主义向度的重大跃升。
一、亚当·斯密经验主义劳动观及其限度
自古以来劳动就备受重视,近代以前农业在社会中具有奠基性地位,劳动观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朴素的观念。古代中国,最高统治者将农耕作为重视民生、赢得民心、树立威望的重要政治手段,民间百姓也将耕作视为一种实践德性。周天子甚至率领百姓亲自耕作,“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古希腊时期劳动虽然被认为是下等人的事,但劳动的重要性和意义仍然是社会共识。色诺芬提出:“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6](16)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发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观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建立起来是近代社会的事。近代以来,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劳动产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在欧洲兴起并得以充分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主导的生产方式迫切需要合法性辩护。在马丁·路德为财富正名之后,劳动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洛克发现劳动是社会产品的本源性价值,他说:“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7](27)。卢梭认识到产权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提出产权是西方商业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并揭示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人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卢梭说:“我们不可能撇开劳动去设想新生的私有观念。……只有劳动才能给予耕种者对于他所耕种的土地的出产物的权利。”[8](123)后世将卢梭在财产权认识上“文明”与“不平等”两种对立观点共存的现象称为“卢梭悖论”。
亚当·斯密从交换、分工、价值、劳动区分等角度阐述了古典经济学劳动观,确立了劳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以劳动价值论回应了“卢梭悖论”。斯密将社会分工的原因归结于人类“互通有无”的本性,并认为“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4](13)。斯密还给劳动分工赋予了道德含义,在他看来天赋资质是不值得一提的,人与人的差别主要是“习惯、风俗与教育”引起的。斯密对天赋资质的淡化为劳动价值预留了空间。他赞同劳动所有权的合法性,并从人道主义立场肯定了劳动所有权的神圣性。斯密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和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4](115)在这里,斯密将劳动看作人的自然权利,并将道德合法性从“资质”过渡到人的“劳动”,其中蕴含着平等、公正、道义,这无疑是劳动观的重大转向。至此,劳动不再是低下的,而是普遍正义的事,而且劳动的普遍性也进而衍生出可度量性,于是劳动便具有了广泛的价值交换功能。斯密指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4](32)斯密还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认为只有投入到物的增值之中的劳动才能称之为“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的提出,进一步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亚当·斯密的劳动观较之于传统社会是进步的,而且具有很强的人文主义色彩,但是他对劳动的分析总体上是经验的,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看,这种经验主义劳动观只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表面正义,实质上掩盖了社会变迁、资本关系、劳动主体及其智慧,未能揭示出劳动的真实内涵。斯密同情工人阶级的处境,看到了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关系及不得不勉强同意的境遇,但他没有认识到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只是寄希望于资本家的良心发现和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够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马克思认为,产生这种依赖的先决条件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解体,农民和工人在法律上被剥夺了直接生产产品的权利,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得生活资料,看似公平的生产活动实则是以资本的剥削和奴役为前提的。斯密关于“两种劳动”的区分只是从资本家或货币所有者的立场出发的,看不到劳动者的地位和劳动的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之实质的性质,从而,劳动生产物之实质的性质,就其本身说,毫无关于生产劳动与不生产劳动的区别”[9](203)。从劳动者角度看,斯密的劳动观也是悲观的,他认为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单纯无变化,职业技能和就业机会的获得是以“智能”“交际能力”“尚武品德”的牺牲为代价的,劳动者最终将沦为“堕落”和“呆滞”的状态。斯密的劳动观中看不到劳动主体,也未能预示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
二、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及其实质
黑格尔是揭示劳动本质的第一人,他首先将劳动过程中的人看作对象化的人,对象化的人是相对于人的自我意识而言的,是人自身劳动产生的结果。黑格尔第一个发现了劳动主体,劳动第一次具有了主体建构意义。这较之于亚当·斯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劳动不再是制造产品的工具化活动,而是一种主体性的双向建构活动。劳动创造着产品又创造着人本身,人的能力提升又改进着劳动活动。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将人的本质界定为劳动,认为劳动是人对自己本质规定的自我证实。黑格尔还将劳动看作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中介,通过人对对象物的改造活动,人的需要不仅得以满足,自我意识也得以发展。黑格尔说:“生命在这种普遍的流动的媒介中静默地展开着形成着它的各个环节,它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成为这诸多环节或形态的运动,或者过渡到作为过程的生命。”[10](177)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是第一性的,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劳动是自我意识的自身异化又克服异化的过程,劳动对于意识保证了它自己本身的内在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通过扬弃和享受以独立事物的姿态出现的异己的存在而达到的”[10](205)。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掩盖了劳动的性质,他指出黑格尔劳动观的唯心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11](102)
劳动作为自我意识的扬弃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主奴关系的否定之否定,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的本质力量推向了唯心主义的新高度,主奴关系的对立在精神观念中得以化解。在黑格尔看来,主人不参加劳动,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奴隶直接通过对物的改造来对物发生否定关系。但是,“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把他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10](187)。奴隶用劳动取消自然的存在,扬弃了对自然存在的依赖性,摆脱了物的依赖性的“劳动”在黑格尔看来就具有了精神熏陶功能,而且在“陶冶”式的劳动活动之中,奴隶摧毁了异己的否定者,把自己建立成为一个自为存在的东西,“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了他(奴隶)自己固有的了”[10](189)。这样,奴隶通过自身劳动重新发现了自己,在劳动产品里面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并且在劳动之中意识到自己自在自为地存在着。至此,奴隶完成了主人对物的处置权和改造活动,成为自然对象的主人;与之相反,“主人是通过另一意识才被承认为主人的”[10](187)。主人由于依靠奴隶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对物的作用仅仅是动物式的简单消灭,这就使得自己不能达到绝对的否定性,从而丧失了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主人地位。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黑格尔将人的本质归结于劳动的这一重大发现,不过黑格尔的异化只是纯粹意识的异化,扬弃也只是变成虚无,人通过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以重新占有自我意识外化产物来扬弃异化,实则是把劳动看成了意识和精神的外化和收回。因此,即使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他对劳动的理解仍然徘徊在意识领域,严格地说,是将意识等同于人的主体。所以,黑格尔的劳动观终究是其庞大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绝对精神才是其本原。马克思说,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2](320)。马克思认为对象性存在物是相对于人的活动的对象,是客观存在于劳动过程之中的,而不是人的意识设定的产物;在对象性活动中,作为存在物的人也是受限制的,而不是绝对精神的支配物。黑格尔的劳动观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异化,而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的异化及其成因,他说:“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3](157)。
三、马克思劳动观的创新和超越
马克思首先论证了劳动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自身及其精神活动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整个自然界首先是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12](272)马克思对物质生产活动的规定,将劳动观从黑格尔的意识领域拉回到了社会存在,从而奠定了“现实的人”及其本质活动的合法性。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劳动活动的重新规定,进而提出人类历史的形成是以人的生活为前提的,以生活为基础的“新的需要”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3](531)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活动的先在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观念追根到底都是转换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即使是黑格尔式的抽象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从理论根基上摧毁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从而加深了对劳动历史性的认识和把握。他说:“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实用性。”[14](29)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剥削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已变成了“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受制于资本的奴役和摆布,而不再是工人劳动的实现形式。资本家正是依靠资本驱使工人为其劳动,在此情形下,“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15](8)。马克思认为劳动解放是摆脱“雇佣劳动”的途径,劳动解放不是囿于精神世界,对现实无视,而是劳动向“现实的人”的回归。马克思说:“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2](18)马克思认为劳动解放是以政治解放为前提的,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解放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而劳动解放最根本的前提是消灭“雇佣劳动”产生的根基,即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并没有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简单地消灭私有制,他区别了“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和“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16](876)的私有制,肯定了小块土地的私人占有的合理性,认为它是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由此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观实质是其唯物史观的反映。
马克思的自由劳动包括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和人的自由真正的实现。马克思认为扬弃异化劳动就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874)。只有消灭分工和私有制,才能消除异化,才能使劳动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实现自由的手段。马克思认为自由劳动的实现是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条件的,自由劳动不是外在的和强加的,而是人的需要使然。在自由劳动中,“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17](287)。马克思通过对机器大工业下的现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矛盾的审视,不再过分强调分工和物质生产活动的作用,他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5](926)。马克思对劳动的辩证分析也印证了他的唯物立场及其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在马克思看来,最高层次的自由劳动是以人的能力发展为目的的自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劳动观和唯心主义精神劳动观的批判,揭示了劳动的真实内涵,厘清了人的本质特征,也使得劳动观的内容更加深刻而丰富。劳动观在马克思人学思想和世界历史理论中具有奠基性作用,马克思的劳动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及其自身解放的重要内容,指明了人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理论铺设,对人们辩证地看待历史阶段及阶段性产物、坚定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的劳动观蕴含的哲理超越了它所产生的时代,对理解当今世界复杂多样的劳动现象,提高人们的理论认识能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