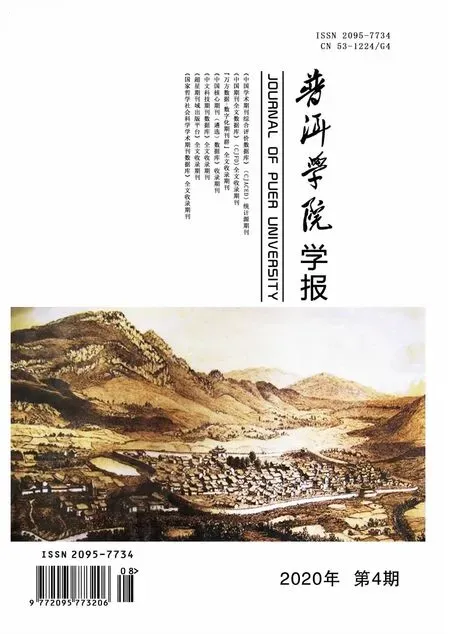明清儒家德性思想研究
宋 丽
玉溪师范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明清儒学家企图建构一套与正统儒学相异的学说,因此在德性问题上的思考展现出了迥异的风格。我们既可把他们的思想视为儒家德性思想的承继,也可当作儒家德性思想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始。对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德性形上学的消解
传统儒学的德性形上学基本都是从天道直贯下来的,如先秦儒学的道器论及宋明理学的理气论等。首先确立一个绝对先验的始基,然后以生与被生的关系把先验本体与经验世界联系起来,并指出以先验本体为代表的“天命”、“天则”是支撑世界的终极法则,也是人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这种德性形上学很容易为人提供一套具有绝对权威性的价值信念,对维护德性价值的普遍性和尊严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分超越性的表现,也使它极易脱离人性的实际需要,结果成为阻碍人性正常发展的“理障”,如戴震揭露的“以理杀人”现象。因此,明清“异端”思潮都积极地解构这种德性形上学。陈亮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链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有其于本质之外,挽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1]!这就明确反对从现实具体事物之外来构建普遍绝对的一般之理。明儒罗钦顺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2]。又说:“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2]。理在气先是宋明理学德性形上学的基本原则。但罗钦顺却认为,理不是一种单独存在物,而仅是表现在气化流行过程中的规律。基此,他重新诠释了一直为宋明理学家津津乐道的“理一分殊”命题。他说:“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3]。在宋明理学家那里,“理一分殊”落脚点主要在“理一”,所谓“分殊”只不过是同一个理在不同情境下的呈现。而罗钦顺却从个别与一般的辨证关系角度来理解“理一分殊”,落脚点放置在“分殊”,所谓“理一”则是蕴涵在具钵事物当中的抽象的普遍本质。这就充分肯定了具体事物独立的存在价值。如他说:“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之者也,若夫天地之万古如一”[4]。理因物而有,离物则无理,因此具体事物相对抽象的普遍之理具有本然的价值。
明代气论学派的代表王廷相则进一步取消了普遍之理的存在。他说:“儒者曰:‘太极散而为万物,万物各具意义太极。’斯言误矣。何也?元气化为万物,万物各受元气而生,有美恶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小,万万不齐,谓之各得太极一气则可,谓之各具一太极则不可。太极元气混全之称,万物不过各具一支耳”[5]。太极是气的总和,而万物只是分有气的一部分而成,因此不能说万物皆有太极,而应说万物因分有相互差异的气而具有不同的本质。退一步说,即便事物原初是相同的,但作为由不断生灭变化的气组成,事物彼此的性质也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产生差异:“或谓‘气有变,道一而不变’,是道自道,气自气,歧然二物,非一贯之妙也。道莫大于天地之化,……草木昆虫,有荣枯生化,群然变而不常矣,况人事之盛衰得丧,杳无定端,乃谓道一而不变得乎”[6]?道因气而有,而气又总是生灭变化的,因此作为气中之道必然也随之变化,不存有所谓绝对永恒的道。
王夫之据此提出“气化日新”的思想。他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视听同喻,触觉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类聚而化相符也”[7]。天地生灭变化是天地永恒的品质,因此由天地生灭变化而来的万事万物其实也是处于不断“日新”的状态;至于能够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是由于共同的社会生活所赋予的。人性作为人的根本品质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日新”的宿命。王夫之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但初生之顷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于一日,俾牢持终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劳劳于给与;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无可损益矣”[8]。就是说,性即气化之理,气不断地变化,理也随之变化,人的身心各方面也皆顺宇宙大化而日非其故,所以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日生日成。可见,王夫之反对将人性视为生而完具的看法,而将其气化日新的观念引入了人性论,认为人性是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创新之中。他的这种人性思想,不仅否定了自先秦儒学开始就一直提倡的形而上学人性论,也开始把人性问题逐渐引向社会历史领域。
二、从天理到人欲的转变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最核心的道德命题。它强调道德的至上性、纯粹性,但由于极端鄙视人的欲望,导致道德与人欲间形成难以跨越的鸿沟,使道德失去感性依据。早在南宋时期,儒学家陈亮就与朱熹进行过一场著名的“王霸义利”争论。陈亮说:“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不可违也”[9]。就是说,人的自然欲望也是人的天性,既然是天性就不可以完全违背。但陈亮并没有因肯定人的欲望,从而否定道德义理对欲望节制的必要性,只是主张“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10]。明代哲学家罗钦顺则说:“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节无节,非天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纵乎?君子必慎其独,为是故也”[11]。人性必然包括欲望,所以欲望不可能通过人力强行取消,至多只能对其进行必要节制。他又说:“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无节尔”[12],欲望不代表着恶,也可以为善,这取决于“有节”与“无节”。但罗钦顺依然主张以性制情,在价值序列上性依旧高于情。而明代气论学派思想家吴廷翰则提出了“性无内外”的观点。他说:“道无内外,故性无内外。言性者专内而遗外,皆不达一本者也。……以性本天理而无人欲,是性为有外矣。何也?以为人欲交于物而生于外也。然而内本无欲,物安从而交,又安从而生乎”[13]?他反对程朱理学家将天理、人欲二元对立的划分。认为人欲与人性浑然一体,根本无法简单区分,性即欲,欲即性。这就充分肯定了人欲本然的价值地位。
明代“异端”的思想家李贽最终提出“私者,人之心也”的命题。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14]。长期以来,“私心”都是宋明理学家批判的对象,而李贽却公开承认“私心”的合理性,甚至认为没有“私心”就没有人性。更可贵的是,李贽也取消了理学家对“至善”概念的设定,认为善恶必然互为一体:“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柔与刚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即有两矣,其势不得不立虚假之名以分别之,如张三、李四之类是也”[15]。万物都是相互对立并存的,而“至善”却绝对没有分别,所以也就不存在“至善”,或者说是纯粹的虚假概念。这就意味着任何善的行为必然包含恶的因素,或者说恶往往是成就善的必由途径。
清儒戴震则认为道德原则的完美体现,并不在于净化人欲:“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16]。道德离不开人欲,人欲本身没有邪恶,真正的道德就是实现自己欲望的同时,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欲望,最终实现共同欲望。
三、由“德性之知”走向“见闻之知”
从根本上说,“德性之知”代表着对人性的自觉自知,是传统儒家治学修身的终极目标。但从宋明理学发展理路来看,一般都把“德性之知”作为本然的宇宙精神放置在人性当中,而“见闻之知”往往只起启发诱导的作用。因此,“德性之知”是宋明理学家阐释认知论的基点,无论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致良知”,还是刘宗周“慎独”之学,都可清楚地反映这一点。但明清“异端”思想家却开始改变了这种具有先验色彩的认知论。王廷相说:“圣贤之所以为知者,不过思虑见闻之会而已。世之儒者,乃日思虑见闻为有知,不足为知之至,别出德性之知为无知,以为大知。嗟乎!其禅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与见闻,必由于吾心之神,此内外相须之自然也”[17]。这就把“见闻之知”视为人唯一的认知能力,而把被宋明理学家视作圭臬的“德性之知”斥为禅学“见心明性”之异种。但王廷相并没有完全否认道德理性的存在:“且夫仁义礼智,儒者之所谓性也。自今论之,如出于心之爱为仁,出于心之宜为义,出于心之敬为礼,出于心之知为智,皆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18]。可见,王廷相依然认可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的存在,只不过把它们建立在“人之知觉运动”基础上,或者说是人“见闻之知”逐步发展的一种产物。
方以智则把人的认知分为“质测”与“通几”两种:前者代表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后者则相当于哲学之知或“德性之知”。他说:“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19]。“考测天地之家”,即从事具体事物研究的学者,他们从事的工作是“质测”,而“质测”的对象是物理。“宰理”指社会人文之理,其实也从属于具体事物之理。“通几”即掌握“所以为物之至理”,即通晓具有普遍性质的哲学之理。关于“质测”与“通几”的关系,方以智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竞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20]。作为具体的“质测”之理先天地就内含了“通几”之理,因此,若想达到对“通几”之理的理解就必须研究和积累“质测”之理。“言义理,言经济,言文章,言律历,言性命,言物理,各各专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数端几格通之,即性命、生死、鬼神,只一大物理”[21]。可以看出,方以智把关涉“性命、生死、鬼神”等价值之理,当作实证的物理知识来研究。换言之,所谓价值之理只不过是各种具体物理的概括与总结,是作为普遍一般之理蕴涵在具体物理之中。这基本就取消了传统儒学所提倡的“德性之知”的独立地位,而使其同化为“见闻之知”。
王夫之也深入地探讨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内涵与关系。在他来看,“德性之知”就是指:“循理而及其原,廓然于天地万物大始之理,乃吾所得于天而即所得以自喻者也”[22]。这说明“德性之知”就是总结天地万物具体之理后的整体认知,根本离不开对具体事物的理解与认知。因此,就人的认识顺序来言,“见闻之知”一定在“德性之知”的前面:“既已为人,则感必因乎其类,目合于色,口合于食,勾非如二氏之愚,欲闭内而灭外,使不得合,则虽圣人不能舍此而生其知觉,但即此而得其理尔”[23]。但这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人从“见闻之知”上升到“德性之知”,而不局限于见闻。戴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心知有“蔽”未能达到“神明”。而“蔽”就是:“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也哉”[24]?“蔽”就在于以个人主观臆断代替普遍客观的真理。因此,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戴震认为必须不断去“蔽”。这就基本承认了人具有无限认知的能力。但清儒唐甄没有延续传统儒学强调的“见心明性”的反观思路去阐释这种“德性之知”,而以“才”这一观念来构建自己的德性观。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上与天周,下与地际,中与人物无数,天下莫有大于此者。服势位所不能服,率政令所不能率,获智谋所不能获,天下莫有强于此者。形不为隔,类不为异,险不为阻,天下莫有利于此者。道惟一性,岂有二名,人人言性,不见性功,故即性之无不能者别谓为才”[25]。所谓“才”即指人改造现实世界的能力,表现在认识上即为把握客观物理的“见闻之知”。在他来看,“性德”即为“性才”,因为,作为包容万物的性之德只有通过性之才的努力才能把客观世界转变成为“我”的价值世界,无“性才”妄谈“具天地万物”的“性德”毫无实际意义。唐甄又说:“言性必言才者,性居于虚,不见条理,而条理皆由以出。譬诸天道生物无数,即一微草,取其一叶审视之,肤理筋络亦复无数。物有条理,乃见天道”[26]。天德为虚,必有条理才能显现,如天道必现于物理一样。因此,欲知天德必知人伦物理,或者说,天德即为人伦物理的总结与综合,而这必须借助“性才”才能完成。“智之真体,流荡充盈,受之方则成方,受之圆则成圆,仁得之而贯通,义得之而变化,礼得之而和同,圣以此而能化,贤以此而能大。其误者,见智自为一德,不以和诸德,其德既成,仅能充身华色,不见发用。以智和德,其德乃神。是故三德之修,皆从智入”[27]。
从根本上说,德的意义在于能创造出现实功用,服务于人的现实生活,这就需要人用智去把握物理、分辨利害,因此,智是德之根本,无智即无德;而这种智,实际上就是把握具体物理的“见闻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