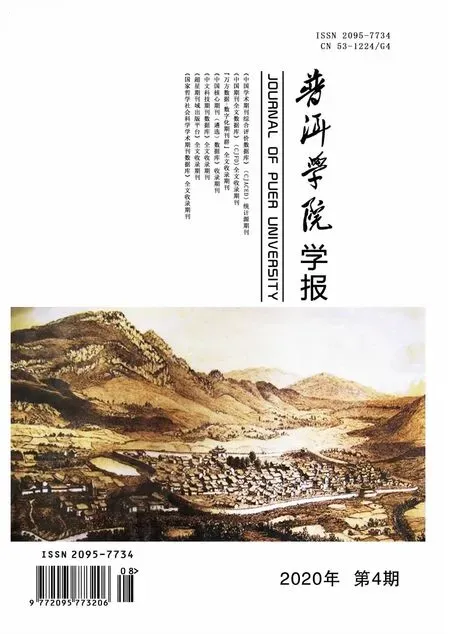从“冲突”到“一致”
——论马克思对机器形成过程的分析及其当代意义
姚 咏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3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在学界,工具主义、技术实体论、社会建构论都是该问题的热门观点。其中,工具主义受到了技术实体论的严厉批判。实体论认为,工具主义忽略了技术在社会中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忽视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尽管实体论指出了技术与社会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其在处理技术负面效应时,将原因归结于对技术的应用上,认为技术本身没有问题,这就遭到了社会建构论的批判。社会建构论认为,尽管实体论指明了工具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与工具主义一样,都将技术当成是中性的,而忽视了社会在技术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由此,究竟是技术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还是社会决定了技术的进步的问题就产生了。实际上,马克思早在分析机器替代劳动的过程时,通过区分机器与工具的差别和机器的来源时就已经表明了技术与社会是互动的有机整体,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明确界定。
一、技术决定与社会决定的冲突
技术中性论包含技术工具主义和技术实体论两种观点。社会建构论认为,它们都将技术当成是中性的,而忽视了社会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技术中性论的技术观
工具主义是技术中性论的观点之一。它最早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后经柏拉图的知识专家治国论、达·芬奇的技术理性,再到近代培根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和笛卡尔对工具理性的推崇,使工具的巨大力量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同时,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启蒙运动的影响,又证明了:技术不仅能打破宗教神学对人类的束缚,还能给物质世界带来极大的丰富。于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就诞生了:人类可以通过控制技术去改变上帝和自然,从而获得无尽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1]。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二战之后——核威胁给人类带来的震撼,技术的伟大梦想开始破碎了。
其实,从苏格拉底提出技术是否能征服自然开始,对技术的反思就拉开了序幕。严格来说,柏拉图并非是一个工具主义者,而是最早提出技术实体论的先哲,他强调技术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才能展现自己,所以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只是由于技术一方面满足了人类改造自然的需求,另一方面对打破宗教神学对人的禁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而对技术的反思被淡忘了。而卢梭认为,技术越发展,人对技术就越依赖,体能也会越退化,并且还会招致道德堕落等问题。这些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实体论对技术的批判也越来越突出。例如,芒福德认为,技术的开端和终点都应该是人,而当前的技术已经成为人类自己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了政治的合理性”[2]。
可见,技术实体论是对工具主义的反思,它指明社会与技术之间的桥梁。但是,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是中性,则中性的技术就可以是最为客观的和无法改变的。所以,社会建构论认为,这种技术中性论的观点,最终使技术变成了一种宿命,那么一切的现代性问题也许都将变成公平公正的了。
(二)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产生于上个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此前,R.K.默顿、J.D.贝尔纳都是社会建构论的先驱,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表示,“经济学与社会学教研室与研究所,比科学的哲学单位更有条件这首开始科学学的工作。”而1987 年出版的论文集《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技术社会学和历史学中的新方向》则成为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其中代表人物有比克、平齐、休斯、科万、芬伯格等。他们的理论主要表达了技术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3]。社会建构论的起点主要是批判技术的中性论,它的主旨是在于强调技术具有一定的价值负荷。人们如果抛开社会的因素去掌握技术,则只能从“外部”去理解技术,而不会明白技术出现的原因以及它的发展方向,所以,对技术的负面效应都只能走向宿命论的困境。而只有从技术“内部”去理解技术,才能真正的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故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由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性、规律性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利益、文化、价值等作用。
综上所述,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的焦点放到了技术形成的过程之中,可以说,他是实体论观点的延伸,他从技术“内部”说明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但是,这是不是表明可以忽视技术与社会的“外部”联系呢?显然,这也是不合理。其实,马克思在他的论述中早已阐明了技术与社会是互动的有机整体。所以,对马克思这种技术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走出以上两种观点的困境。
二、马克思的技术观:技术与社会的互动
马克思指出,机器的形成有赖于简单工具的聚合,但这并不足以形成真正的机器,并不能带来社会变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技术与社会应该是处于一个互动的有机整体之中,其并不能分开而论。
(一)机器产生于简单工具的聚合
马克思认为,发达的机器都是由三个不同本质的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发动机、传动机和工具机。发动机是整个机器的动力源,它将推动传动机,例如皮带、齿轮、转轴等联结装置的运动,并将这种运动传送到工具机身上,由工具机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马克思说:“机器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机器从一开始就出现这些工具的组合”。由于手工业时期,通常一个人只能推动一种工具运作,所以简单协作体现在劳动分工上,而工具与工具之间已经可以进行分工操作,所以简单协作体现到了机器之中。因此,马克思断言,在机器中所体现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4]。但无论是机器还是工具,它们都是为了改造自然或者进行生产而被人类所利用的一种手段,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机器与工具在本质上的差别就消失了。然而,马克思并不承认这一点,他认为:“说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这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
(二)机器产生于人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机器只是工具的聚合,只是对一般简单工具的改进,那么自动机早就诞生了,可是仅有机器就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影响吗?马克思通过对机器的追溯认为,即使最简单工具的创造也是由于人的需要而造成的。
马克思列举“磨”的发展进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为了把谷物碾碎,最早是用石头砸碎即可,但是这样不方便劳动成果的收集,于是,就将谷物放入容器中碾碎。后来,人们发现研碎比砸碎谷物更有效率,于是就在容器内发明了杵做旋转运动,并在杵上设置了一个把手,以方便力的操作。而为了大量的生产,人们把杵越做越大,当人们不能推动杵时,就尝试用牲畜来代替人力。后来,又发现牲畜的力量仍然有限,又发明水磨,这种利用自然力的工具……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机器产生的探索,与今天社会建构论的论述是如出一辙。如果我们将“磨”发展的过程放入所有机器的进程来考察,就会明白,机器的产生不仅仅依靠了简单工具这种客观的因素,同时也离不开人的需要这种社会因素。至此,我们通过马克思对机器发展进程的梳理发现,技术中性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之间的冲突,可以在马克思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技术观中走向一致。这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走向一致:马克思的技术观对当代的意义和启示
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形成过程时所表达的技术观,是一种全面的、辩证的和历史的技术观,这对只从技术去理解社会的发展或只从社会的因素去理解技术的发展这样片面的理论都是一种纠正。
(一)马克思的技术观是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片面理解的纠正
通常将技术与社会分开叙述,其实,是为了语言或者是思维抽象方便而已。也就是说,将技术与社会分开讨论只是为了认识的需要才这样做的。这就是说,技术与社会从来就不是分离的。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且相互作用的关系,使技术和社会构成了一个整体。在马克思看来,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任何一方皆是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历史状态。一方面,技术在当代社会中,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生态、社会等角度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每次技术创新都给社会各领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技术始终是人类的产物,其不存在于真空中,在推动社会发展时,技术又必定要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5]。可见,马克思的技术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技术中性论和社会建构论的片面性,从而形成了对技术与社会的辩证理解。
(二)马克思的技术观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马克思的技术观向人们表明了技术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相互协调发展的关系。所以,人们必须承认,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不仅仅是表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文化发展、生态建设都有着巨大的功能。首先,应当加大投资技术的发展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质量,以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其次,应该利用技术的发展推进政治文明的建设,例如当今社会的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可以收集公众对政治发展的意见,让广大公众参与到政治文明的建设之中。其三,也不能忽视,社会对技术的作用。技术的物质手段作为人工的自然物,是客观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从它产生之日起,它同时也是物质存在的社会形式。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应当从社会中人的需求出发,发展符合人的发展的技术。
四、结语
总之,只有在技术高速发展了,社会才能真正的发展,而也只有社会真正是发展的,技术才可以说是得到了真正的进步。要充分贯彻马克思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观念,使技术与社会的协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