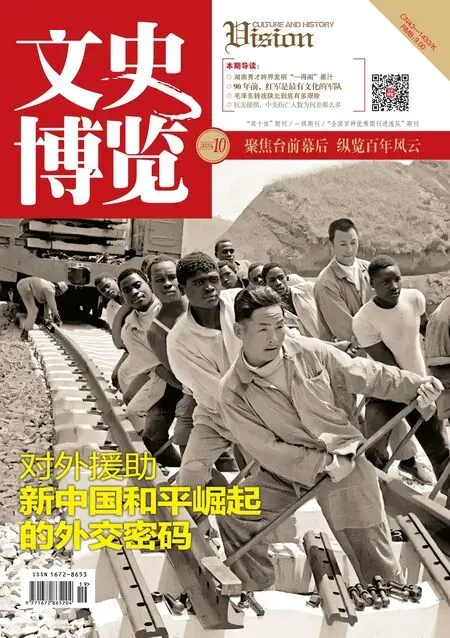文史精粹
“狼烟”真是狼粪烟吗?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狼烟”是这样解释的:“古代边防报警时烧狼粪升起的烟,借指战火。”看到这,你可能会想到历史上有名的“烽火戏诸侯”事件。注意:是烽火戏诸侯,而不叫狼烟戏诸侯,因为那时还没有狼烟一说。那么,狼烟真的是烧狼粪的烟吗?
首次提到烧狼粪用于烽烟的是唐代段成式,他在《酉阳杂俎》中写道:“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意思是,燃烧狼粪形成的烟很浓,且能直直上升,不像其他的烟那样遇风即散。宋人陆佃沿袭此说并加以发挥,其著《埤雅释兽狼》中记有:“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可见自唐以后,狼粪用于烽烟这一观点传承下来,就连明代的李时珍、戚继光都这样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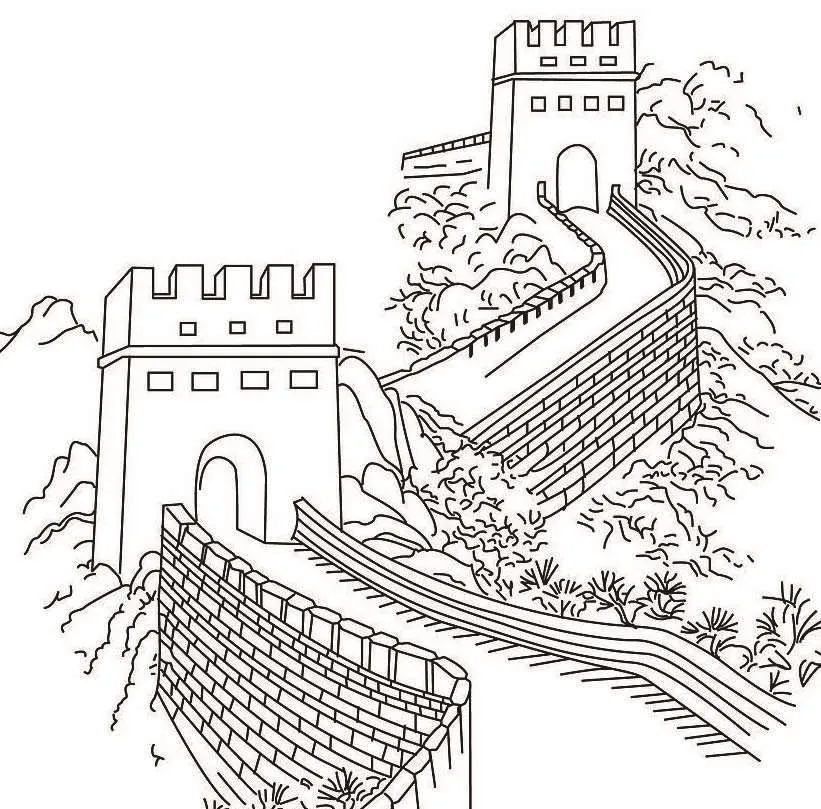
不过,敦煌学者李正宇对此做了研究,首先他发现狼粪燃烧形成的烟并不是直直上升,跟牛粪没多大差别。其次,《狼图腾》的作者吕嘉民也做过实验:“烧狼粪就像是烧羊毛毡,冒出的烟是浅棕色的,比干柴堆冒出的烟还要淡。”后来,李正宇在西北地区的许多烽火台遗址里发现燃烧芦苇、红柳等植物留下的残迹。据此,他认为烽火台燃烧的实际上是芦苇、红柳,甚至杂草。唐朝时兵部明文规定:每年秋天之前,要采集艾蒿、茎叶、苇条、草芥,“为放烟之薪”。这与李正宇的发现是吻合的。
唐朝前期的主要边患是突厥,而突厥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民族,经常在旗纛上绘一个狼头。唐朝后期的边患变成了回纥和吐蕃,回纥同样以狼为图腾。吐蕃虽然不以狼为图腾,但其地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属“狼星”的分野,所以唐人对其有“狼蕃”之称。历史上的中原人习惯称游牧民族首领为“狼主”,称其军队为“狼兵”。那么,“狼主”领“狼兵”来犯,边关点燃的烽烟称为“狼烟”,意为防狼或御狼之烟,是说得过去的。
当然,狼烟中或许还是有一些狼粪的。杜佑《通经总要》载有燃放烽烟之薪中,除蒿艾、苇条、茎叶、牛羊粪之外,还有狼粪夹杂其中。狼粪仅是其中之一,但以取狼粪所燃之烽烟作为“狼烟”之说,实属以偏概全。
(文/张 勇)
皇帝女婿为何又叫“粉侯”
晋朝之后,凡是皇帝之婿都被加封为驸马都尉,简称“驸马”。从此,驸马就正式成了皇帝之婿的专门称呼。不仅汉族如此,就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辽、金等王朝的皇帝之婿也称为“驸马都尉”。如《辽史·百官志》记载:“驸马都尉府掌公主帐宅之事。”不过,在明清之前,驸马的官阶并不高,金朝时,驸马都尉仅仅是正四品。到了清朝,驸马称为“额驸”,地位才逐渐显赫起来。咸丰年间,咸丰皇帝指派驸马富察·景寿为自己死后“赞襄政务”的顾命八大臣之一。
除了驸马这个称呼之外,皇帝之婿还有另一个知者甚少的称呼——粉侯。
清代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云萝公主》的小说。其中写道:“一婢以红巾拂尘,移诸案上曰:‘主日耽此,不知与粉侯孰胜?’”这里的“粉侯”指的就是皇帝之婿。把皇帝的女婿称为“粉侯”,是因为三国时期的何晏。
何晏是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的孙子,少年时以文才出众而闻名,而且长得仪表堂堂,尤其是他的脸,粉白粉白的。三国时期魏国的皇帝魏明帝见何晏虽然长得帅,却柔美有余而阳刚之气不足,怀疑他性格浮浅、尚美好装扮而整天在脸上敷粉,就想找个机会给何晏一点难看。一年夏天,魏明帝选了一个天气炎热的日子请何晏吃饭。魏明帝专门让人端上了热汤和热饼让何晏吃。何晏吃得大汗淋漓,魏明帝坐在一旁等着看好戏。但是,何晏擦了脸上的汗水之后,脸色依然嫩白如敷粉,而且白里透红。魏明帝这才知道何晏脸色的白嫩是天生的,于是在心里暗暗赞叹。不久,何晏娶了魏国的金乡公主为妻,被封为驸马,还被赐封为侯爵。因为何晏的脸色天生嫩白如敷粉,人们就称他为“粉侯”。从此,粉侯成了皇帝之婿的又一个称呼。(文/王吴军)
“福尔摩斯”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与其他文体相比,侦探小说其实是一种现代发明。
侦探小说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896年。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和习俗,在一年时间里刊载了4篇有关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当时,福尔摩斯的名字被翻译成“呵尔唔斯”。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非常流行。有学者统计,那个时候大概一共翻译了1000余部西方小说,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侦探小说。
为什么晚清读者喜欢读西方侦探小说呢?一些读者被小说中的新奇事物所吸引。比如,福尔摩斯外出取证,他有时候是坐地铁去的——当时的伦敦已经有地铁了。还有,福尔摩斯在探访证人的时候,有的证人在读《泰晤士报》,有的证人在看天文望远镜,这些都是当时比较新鲜的事物。法国的侦探小说里,还有对化装舞会的描写,晚清的读者自然觉得十分新奇。
由于西方侦探小说在当时十分流行,它影响或者说刺激了很多中国文人,使他们不自觉地将西方的侦探小说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小说,创作出了一些有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晚清有名的小说家刘鹗的《老残游记》就是其中之一。在书里,老残被称为“福尔摩斯”,这可能是“福尔摩斯”这个词第一次在中国小说里出现。老残按照西方侦探的推断方法抓获了凶手。还比如晚清有名的翻译家林纾,也曾经翻译过一些侦探小说,包括福尔摩斯的故事。
“九儒十丐”之说的真实来历
元朝时,我国就有“九儒十丐”一说,即把人分成等第。
那么,九儒十丐前面的八等人又是些什么人呢?据曾经身受元人不平等对待的两个最有名的宋末遗老谢枋得、郑所南的文集中记载,九儒十丐之说大概始自元朝。谢枋得在其所著《叠山集》中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朝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

元代士人服饰画像
谢枋得只告诉我们元代分人为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却没有说三、四、五、六等是哪一类人。郑所南著《铁函心史》,填补了这个空白。其《鞑法》曰:“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文中的三僧四道,五医六工,是无疑的,七猎八民,则不如《叠山集》七匠八娼说得明确,因为古代“民”的含义范围较广。
由此可知,元代分的十等人应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元朝将儒位列娼之下、丐之上的第九等,把读书人、知识分子贬低到如此地步,难怪毛泽东说他们“只识弯弓射大雕”。
其实把人分为十等,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即有之。《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里说的十等人,应是一王二公,三大夫四士(此四等属于贵族),五皂六舆,七隶八僚,九仆十台(此六等属于奴隶)。只不过当时的十等人与元朝的十等人不同罢了。(文/蔡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