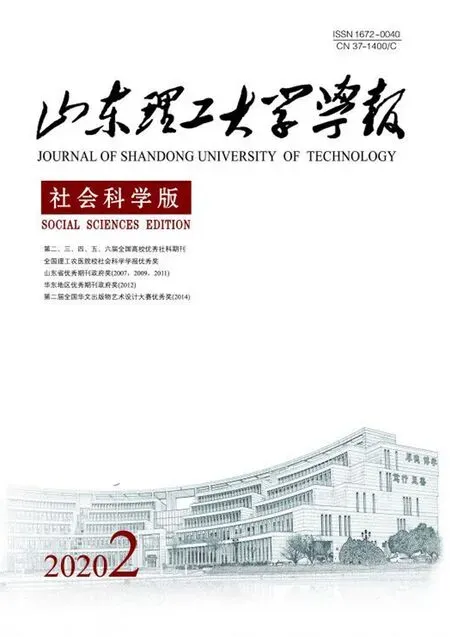深海底层渔业商业开发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分析
马风成,任秋娟,吕晓明
深海底层渔业商业开发与海洋能、海上风电、蓝色生物技术、海水淡化、海底采矿等海洋新兴产业正在成为目前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对底层渔业开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估是启动其开发的必要条件。目前国际海底区域渔业资源的商业开发还是主要集中于基因资源,区域渔业组织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渔业尤其是深海底层渔业的开发仍然带有附带性。虽然深海底层渔业实际上集中于深海海水水体,只是因为现有的深海捕捞方法主要使用拖网,而拖网必然会影响到底栖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及生物多样性。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规定,2020年所有鱼群和无脊椎动物种群及水生植物都以可持续和合法方式管理和捕捞,并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以避免过度捕捞,同时建立恢复所有枯竭物种的计划和措施,使渔捞对受威胁的鱼群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不产生有害影响,将渔捞对种群、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限制于安全的生态限度内;至少有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 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通过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相连性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基于保护区的有效保护措施得到保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土地景观和海洋景观。
当下,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则在深海底层渔业管理研究中备受关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有学者以深海海洋脆弱生态系统为切入点,单纯强调生态系统方法在深海底层渔业管理中的应用[3];有学者关注深海底层渔业的区域性特征,强化其国家管辖范围外特征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属性[4];有学者支持扩大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深海底层渔业商业开发中的示范作用,进而使渔业商业开发规范逐步具体化[5];有学者强调国家在深海底层渔业商业开发中国家责任落实的重要性,主张应该将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捕捞活动作为重点[6]。深海底层渔业商业开发中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则的履约方式的不断更新已经悄然地取代现有公约体系的更改。本文拟在现有公约体制梳理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当下各国履约方式的变化规律,以展望未来深海底层渔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践行方向。
一、深海底层渔业资源的生态环境
(一)深海底层渔业资源物种特点
典型的深海底层渔业的目标鱼种是海底和底栖物种,而大多数海底和底栖物种和传统水体渔业尤其是近海浅水捕捞的物种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海底和底栖物种生长缓慢,成熟周期长,生命周期跨度大,因此只能经受低度捕捞。
2.大部分海底和底栖物种含水量过高,肉质松软,单纯就人类食用角度来看经济价值较小;海底和底栖物种往往处于海洋生物链的中低端;就捕捞成活率而言,海底和底栖物种因其缺乏浅水鱼类发达的粘液表皮并且鳞片较大,因此在遭受拖网作业时,其鳞片和表皮往往易被刮而导致死亡。
3.海底和底栖物种的捕捞大多都在孤立的海洋地形结构上进行,如海底山脉、海脊系统,也有在大陆坡之上深水中。捕捞这些品种通常使用接触海床的渔具。传统底层渔业国主要集中在北半球的俄罗斯、美国和挪威。联合国粮农组织捕捞区域中,西北太平洋产量最高,该区域远洋和底栖物种资源最为丰富,其次是中东大西洋,其底层渔业资源大部分处于充分可持续捕捞状态。
(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
底层拖网捕鱼方式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基于联大61/105号决议,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在《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中指出:脆弱性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与特定人类活动相关,包括特别捕鱼形式和作业模式。底层渔业活动与其他海洋捕捞活动相比不仅具有质量差异,捕鱼强度也有所不同。当捕鱼强度上升,某一特定生态系统就很可能显示脆弱性,尽管两者关系不一定成线性和比例,但是临界线的突破会导致种关联发生突然变化。人类所认知的国家海底区域都可以被定义为特别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以海绵为主的群落,冷水珊瑚,以及冷泉和热液群落,这些通常与地形、水文或地质特点相关,如海底山峰和山脉,海底热液喷口和冷泉[7]。深海具有潜在的生态保护利益,海底生境的脆弱生态系统为生物资源的商业开发提供了种群评估的信息基础。即使目标物种为深海底层和底栖物种的深海捕鱼,也会对深海生态群落产生直接影响,包括在系统中营养和碳运动的变化,以及系统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控制系统平衡的变化。
二、深海底层渔业资源开发公约框架
(一)制定一系列全球性法律文件
深海生物资源和上覆水域生物资源密不可分,联合国粮农组织针对公海渔业制定了一系列全球性法律文件,主要包括《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公海渔船遵守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准则》和《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议》。其中《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公海渔船遵守协定》和《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议》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准则》仅仅起到指导的作用。联合国大会自2004年起至今每年通过一个可持续渔业的决议,即通过1995年《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和相关文书等途径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决议,主要内容是促请所有国家直接或者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在养护、管理和开发各种鱼类种群时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和生态系统方法。要求各国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深海上覆水域禁止使用底拖网作业,并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适用以保护海底脆弱生态系统[8]。联大61/105号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监管深海底层渔业的要求,作为基础性的文件,此后历次联大的可持续渔业决议反复强调执行61/105决议并以其为入门标准逐年加强对深海底层渔业的监管。联合国粮农组织主要从技术层面着手解决公海深海渔业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保护包括冷水珊瑚在内的成长缓慢且脆弱的深海生态生物系统,具体做法是要求各国及相关自然资源国际组织通过措施减少底层渔业对深海生物系统的不良影响。但是《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依赖各国自愿遵守。《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涉及海底山脉、深海热泉及冷水珊瑚等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公海底层渔业管理。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目标在于有效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相关条款,确保长期养护和可持续捕捞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在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建立了许多新的原则,强调船旗国对悬挂本国旗帜的渔船的责任和义务、强化区域渔业组织在辖区海域内的主管地位、进一步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生态系统管理、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倾向、捕鱼活动数据的收集及共享、监督监控的加强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3(2)条规定了涉及在专属经济区及公海水域进行的跨界捕捞。虽然深海种群不属于高度洄游种群,但是深海底层渔业的跨界性使得其受到《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的约束。不仅如此,联合国大会号召各国采纳《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中的规定来制定本国在公海渔业的相关保全及管理规定。《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7条规定,细化国家的义务,必要时对属于同一生态系统的物种或从属目标种群或与目标种群相关的物种制定养护和管理措施,以保持或恢复这些物种的数量,使其高于物种的繁殖处于不会受到严重威胁的水平[9]。201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针对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有关在专属经济区内外渔获分别报告问题的几点考虑》专门提及部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避免被定义为违规,一反以往对捕获量数据开发共享状态的做法,而拒绝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捕捞位置及地图、捕获量数据信息。联合国粮农组织要求船旗国在收集、报考渔业统计资料数据方面负有首要责任。生态系统方法是实施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基本手段,为在渔业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途径。在涉及海洋的方面,跨部门方法的实例包括由美国太平洋渔业管理理事会实施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渔业管理(EBFM)、由南极洲区域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承担的生态系统管理方法(EAM)、澳大利亚生态可持续发展(ESD)国家战略中包含的渔业生态系统管理框架以及大型海洋生态统(LME)管理措施等。
(二)协调现有渔业组织机制,建立统一的全球管理机制框架
当下国际海底区域渔业资源和深海渔业资源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连带性,主要基于人类对国际海底区域底栖生物的动物区系组成掌握信息极其有限而导致对单纯的底层渔业开发的不确定。国际海底区域生物资源勘探就国际海底区域渔业资源而言,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性及区域性的渔业组织海洋渔业资源的管理框架基本围绕着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规则和框架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之间的全球合作及区域合作,基本覆盖了所有公海海域;深海渔业可持续管理问题已在《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联大46/215号决议、联合国粮农组织《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等法律文件中做出安排。这些法律文件和管理机制所秉承的基本原则大体一致、采取的管理措施大致相同,具备统一协调的基础。充分协调现有渔业组织机制,建立统一的全球管理机制框架,这或许是国际海底区域生物资源商业开发统一的未来发展趋向。
一是进一步完善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标准体系。水规总院加快推进标准化工作,着力开展了涉及资源环境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公共安全、政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制定工作。《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设计规范》《防洪风险评价导则》等28项水利标准已经发布,《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规范》《水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导则》已通过水利部审定。
三、深海底层渔业资源商业勘探发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一)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引领作用是基础
渔业管理最终要依靠船旗国,通过修改或新建区域性海洋管理条约,或者对区域渔业管理内部管理机制进行改进,这在管理成本上要比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性的生物资源组织更加节省。除此之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与组织成员国有着更为密切的事物联系和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易于达成有建设性和更为实用的规则。当然,由于欠缺统一的全球机制,以及区域渔业组织成员国组成情况的差异,各区域渔业组织在生物资源的管理上也存在着局限性,比如深海底层渔业没有被完全覆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基本目的在于稳定高度洄游鱼类的产量,因此并未涉及深海非洄游鱼类及非目标鱼类。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虽然对深海鱼类设置了生态系统管理,但实践表明生态系统管理往往仅是作为临时措施而非付诸长期和系统的计划[10]。因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立足点在于,保证本区域组织当事国优先捕鱼权的实现。譬如关于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目标鱼类的监控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是在对误捕物种、食物链系统方面很少涉及,且各区域渔业组织区域之间既合作很少,也不愿意接受专业科学团体的建议。迄今为止,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和中西部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决策机构对专家意见的接受比例仅为39%和17%[11]。
在深海渔业中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是基于缺乏对海底脆弱生态系统的成熟认知及现有底层渔业对其影响的信息和数据资料收集的欠缺。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同时,首先需要加强对深海生态系统的认知,建立公海海底底层渔业科学观察员体系,加强生物数据收集。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提供国际培训计划帮助渔民和底层渔业科学观察员改进捕捞认证和生物数据收集,观察员通过使用粮农组织现有材料以确定商业开发种群并编制使用手册以确定底栖无脊椎动物等非商业品种。其次,《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和相关文书等途径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决议草案(A/60/L.38)决议以及渔业委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达成的协议,国家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应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适当的协助和支持,积极与相关组织合作以建立深海全球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数据库。具体做法是应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安排,各国应将船只登记或记录数据至少按年度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交,并报告具体采取何种措施对这些船只进行管制。同时区域渔管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应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部门将这些数据和信息对外开放。而对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没有覆盖的区域,各船旗国应绘制全面图像以显示现有渔业空间并和其它相关国家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进行合作以绘制相关区域的联合图像。各国对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联合国负责深海提供支持,向联合国粮农组织直接提交包括种群评估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影响评价在内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深海渔业数据。
根据联大61/105号决议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渔委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决定,联合国粮农组织要求各国家和区域渔管组织提供适当的协助和支持,以建立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的全球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数据库。作为确定脆弱海洋生态系的必要步骤,国家和区域渔管组织有义务收集和分析在这些区域渔管组织主管领域内的相关信息或由各国管辖的从事深海渔业或正考虑从事或扩大深海渔业的船只的相关信息[12]。区域渔业组织在渔业数据的统一收集整理和解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洄游物种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公海跨界种群评估及相关管理决策提供信息基础。不同区域渔业组织针对不同规模的渔业会有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以此要加强参与渔业数据和展开种群评估和渔业管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考虑建立一个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全球信息数据库,以协助各国评估底鱼捕捞活动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任何影响,并邀请各国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向数据库提交关于根据本决议第83段查明的所有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信息[13]。但是在底层渔业数据库建立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成员国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的问卷调查与区域渔业组织公布的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其原因一是公渔业活动经常与专属经济区渔业活动相互混淆,这对公海底层渔业统计十分不利;二是很多在不同区域渔业组织的作业船活动并没有区分开来[14]。
(二)跨部门生态系统管理的适用是依据
跨部门生态系统管理(cross-sector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是针对国际海底区域不同利用途径,衡量和评价多部门相互影响的工具。跨部门生态系统管理通过建立生态系统环境基线和比较生态系统服务前后的差别来评价多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的价值。尤其针对当下气候变化、自然生物多样性改变、海洋表面温度变化及酸化加重引发海洋物理化学的变化等情况,其重点在于辨别及协调各部门的相互影响。但目前主要障碍在于缺乏各部门间相互影响的信息,而效益成本方法的适用是把握跨部门生态系统管理的关键和灵魂。
效益成本分析法在衡量生态系统服务的不同价值方面对各种资源、各产业和利益相关者进成成本效益分析,通过比较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来决定不同选择的经济价值,是权衡不同部门相互影响的利器。在成本效益分析中,特定部门的活动所有的成本和效益会被估算,效益大于成本的部门有利于蓝色增长。成本效益分析中所有成本及效益来自于使用和非使用价值,从而揭示了目标活动的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在深海底层渔业资源商业开发中,底层渔业开发的效益体现在市场上的产品及专利,其经济成本体现在市场及非市场评估。使用市场评估来估算成本体现在包括勘探设备的成本,使用非市场评估来估算成本包括活动潜在的环境负面影响,以及对能够产生非市场价值的其他部门的负面影响,及对底层渔业生态系统存在价值的影响。
底层渔业的商业勘探会满足人类和社会的需求、期望和偏好,这些偏好是通过他们基于对生物资源和时间限制所做的选择和妥协表现出来的。尤其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方面这样的经济评价通常可以发挥有益作用,因为能够在不同区域内进行横向比较。但是现有情况下国际海底区域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有很多弊端。首先,估算非市场价值即环境的负面影响,因为人类目前认识的不足,只能是作大概的估算,实践中评估者往往将其评估为零。其次,如果商业勘探被估算为能带来纯经济效益,成本效益分析就会力推这一行动而不管其会对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和损害可持续发展。换言之,成本效益分析假设市场评估和非市场评估是可以交易的,优势明显的市场评估可以吞并非市场评估。再次,成本效益分析中当评估某一行动的未来收益及成本时一直具有争议,则其现存价值会在评估中被适当减损(appropriate discount rate)。在与环境变化引发成本效益变动的时候,过多的减损现存价值会引起现在和未来成本效益估算的不合理失衡。
(三)对IUU捕捞活动的监管是重点
对生物资源进行底层捕捞大多数属于非法、不报告及不管制捕鱼行为(IUU),构成对深海海洋生态系统的主要威胁。为了有效维护生态环境,加强政府监管至关重要[15],为此,于2016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制定了《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及未受规范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以下简称《港口国措施协定》)。截至2018年4月5日,《港口国措施协定》有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54个缔约方。目前各缔约方正在努力推动协定的有效实施,包括鼓励非缔约方遵守协定内容。《港口国措施协定》规定的违反国家、区域和国际法的捕捞和捕捞相关活动包括:不报或误报捕捞作业和渔获物信息(不报告);不明国籍(未登记)船只开展捕捞(不管制);非缔约方船只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公约水域开展捕捞(不管制);未经国家充分管制且无法轻易监测和记录的捕捞活动(不管制);针对未采取养护或管理措施的区域或渔业资源实施的捕捞活动(不管制)。《港口国措施协定》的核心内容是要求缔约方在本国港口内履行甄别处理渔船并收集渔船相关信息的义务,港口国有权通过对使用渔具、渔船证书、捕捞日志及其他文件及船上设施进行检查从而掌握对渔船捕获物的来源及实际捕捞情况,从而对非法捕捞的捕获物依法采取措施进行处置。协定强调港口国有权拒绝从事非法、未报告及未受规范捕捞的渔船入港,并要求缔约方之间实现渔船信息共享,互相提供任何涉嫌非法、未报告、及未受规范渔船的相关信息。
深海所处的传统大型渔业场所周边就近的港口国往往是包括小岛屿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财政基础及技术能力受限,这些国家在落实《港口国措施协定》关于港口国的甄别管控义务时存在困难。所以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各国开展合作交换渔船及其为落实《港口国措施协定》所开展活动相关信息,包括支持协助港口国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以及协助船旗国控制嫌疑渔船,支持沿海国保护渔业资源,确保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所得产品不得进入市场。区域渔业组织的有效协助和支持可提升全世界渔业可持续性。联合国粮农组织侧重帮助港口国完善港口措施,进一步提高对非法、未报告及未受规范渔船的甄别和管控能力。《港口国措施协定》实际上建立了最低限度的法律框架,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港口国国内法律法规的建设及港口硬件设备的加强,推动港口国对供应链关键点实施管理。
显而易见,对远洋作业渔船管控信息的全球合作是《港口国措施协定》的关键点,国家海底区域底层渔业作业中的重要信息透明化和信息共享将会促进深海生物资源商业勘探的健康有序发展,建立全球信息分享和发布机制势在必行。《港口国措施协定》与渔获登记制度准则和全球记录是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协同框架,着眼于在公海和深海等船旗国管辖区外进行渔业作业且寻求进入他国港口的渔船设立有效“合规检查点”。《港口国措施协定》为各国提供了合作和交换渔船及其活动信息的机会,也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提供了机会。 通过《港口国措施协定》信息交换机制汇总的船舶检查和合规记录可作为可靠资源纳入国家风险评估,并可协助各国在违反港口国、区域或国际法律法规(包括禁令)时采取适当行动或冻结相关的船旗国补贴。以中国为例,2016年中国远洋渔业报告渔获量约为200万吨,但仅就在中国销售的渔获量(约占远洋捕捞总渔获量的24%)提供了物种和捕捞区域详情。由于信息的缺乏,其余150万吨被列入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捕捞区域中西北太平洋“海洋渔业未纳入别处”项下,由此造成该区域渔获量可能被夸大。尽管部分未列入准确的捕捞域项下且未具体到物种,但中国大批远洋捕捞渔获量已列入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港口国措施协定》对于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因为中国既是重要的船旗国也是重要的港口国。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远洋渔船队,其中半数在公海作业,同时中国也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港口众多。但目前我国的渔业执法检查,尤其是海洋渔业执法主要依靠海上巡航检查,以港口为基础的渔业甄别监管能力有待加强。中国于2018年发布了《全国沿海渔港建设规划(2018-2025年)》,《渔港监督管理条例》也即将出台,两者相辅相成,可以为港口管理打下更好的基础。
中国作为重要的远洋渔业国家,目前在国际海底区域上覆水体中主要捕捞中上层的跨界或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并逐渐发展以深海鱼类种群为捕捞对象的渔业。但是中国在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捕捞全球风险程度及响应程度中评分较低。具体表现为:首先,中国作为船旗国,中国籍渔船的IUU捕捞活动脆弱性最强,发生率最高,这表明中国作为船旗国面临的监管压力巨大。从IUU列表中的船只数量、渔业观察员和监测、控制和监督从业人员的观点调查以及国际媒体中不断出现的负面新闻数量来看,中国的远洋渔船仍被视为IUU捕捞活动的重要推动者。尽管中国一直积极主动与国际社会合作履行监管职责,但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要求的船旗国义务仍存在较大差距。其次,中国作为港口国,主动采取的禁止IUU捕捞活动的应对措施十分有限,在对渔船的监督和检查方面手段较弱,被认为发生IUU捕捞相关交易的几率极大。况且中国至今未加入《港口国措施协定》,也未曾开辟限制外国渔船进入的港口,这也导致中国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中履约较差。消除IUU作为当下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已被单独列为一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对IUU捕捞的治理不力,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家管辖范围外水域渔业协定的参与度与效果。
四、结论
鉴于国际社会对深海底层渔业损害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强烈关注,中国应加强对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发展的跟踪研究,在决策层面上避免与公海渔业管理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同时,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区域及次区域国际渔业治理,负责任地开展渔业活动,认真负责地履行国家的国际责任,在可能发展的区域,也应提前评估可能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并遵循预防措施、渔获量监测、数据收集、观察员等管理要求。积极主动地提高执行国际渔业协定的履约能力,创新与完善渔业管理制度。最后,中国应积极采取步骤,提高我国参与国际渔业治理的话语权和治理能力,包括加强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能力和参与国际渔业执法的能力,例如我国渔业执法船舶应该具备参与公海渔业执法的能力,积极参与公海渔船登临检查的国际或区域性渔业执法,提升中国在国际渔业治理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