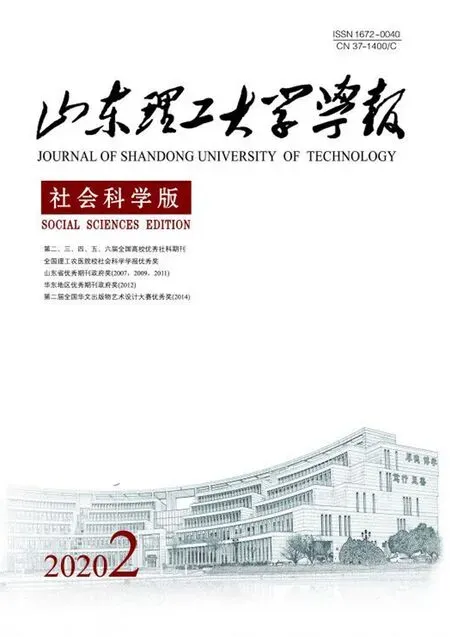拓展生态想象与跨入环境人文研究
——评《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
盖 光
如何通过文学与生态的关系探究一种发现及创造,不只是论及人的创造,更需认同自然的、物性的创造?如何以不止于文学想象的力量去探究自然及物性对个人和集体观念的影响?劳伦斯·布伊尔著《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山东理工大学岳友熙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布伊尔把“环境(的)”视为既是“自然的”和“人造的”可感知世界的两个方面,并称“人类关怀和价值根据一种更强大的关心非人类环境的伦理来调整,会使世界成为人类和非人类的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该书第7页)。“生态想象”是布伊尔所坚执的一个学理命题,他并非“停止在树林的边缘”,而是置入林中,于纵深之处去“想象”。布伊尔的研究视阈及批评路子是非常宽阔的,他曾指出:“我的批评方法体现了各种批评调查范例的融合,它是由生态历史、社会人类学、文化地理学、伦理学、现象学、宗教、文化理论和自然科学的历史以及文学与美学理论改编而来。”(1)见岳友熙、劳伦斯·布伊尔:《美国生态想像理论、方法及实践运用——访劳伦斯·布伊尔教授》,载《甘肃社会科学》,2012(5):54。该著不只关涉了多种学科及方法,并融括着西方多个国家、地区二百多年来的人文书写及其现象阐释。
一
人类活动创造了人工环境,时至今日,我们更多是在人工环境中挺进,如果环境也在颐养人们,文学或许更是如此。人工环境为人的生存会生成且创造许多物性及精神的存在,有正向的,也不乏负面的;既为人类带来幸福,也会造成危机,甚至是深度危机。当下,不管是生态想象、环境伦理及批评,还是生态伦理及批评,或许介入更多的是对这种“危机”的忧思。布伊尔的研究路数则不然,尽管在该著的开篇,布伊尔意在坚信 “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的危机、公共健康的危机,或者政治的僵局。”(该书第1页)但同时他又指出化解这些危机,“最终不是与‘一些高度发达的技术或某种神秘的新科学’相关,而是与‘精神状态’相关:态度、情感、意象、叙事”(该书第1页)。或许这就是布伊尔拓展“生态想象”的基本理路及概念支撑。尽管该著不是史论,但又具史的脉络,所观照及依据的是被他称为“主人公”“有创造力的作家”的创作,大都是18世纪后期到今天的美国作家。显然,这些文学书写的对象及际遇大都在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进向中,既带有历史性书写特点,也促人反思“危机”进程为何加快。应该说,布伊尔的著述有别于多年来关乎生态伦理及生态批评的研究,因学人们往往会堕进单面的“危机”或“主义”性缠绕,往往会缺失许多如怎样能够透过文学现象而全方位且透彻地对人类性基于历史性辨析。如布伊尔言:“那些崭新的文学作品和环境研究运动就渐渐被贴上了标签。”(该书第3页)在我看来,如果暂且搁置“危机”之论,或所谓“中心”“主义”的论争,而有理有据、有张有弛地借力于现象及文学作品的深度研究说事,或许更能够置入深层说明事理。
二
布伊尔的研究守持的依据和路径呈现出宏阔且透辟,对文学现象、思潮及作家身份、背景的辩证以及对多样性的文学文本解析细致,使其“生态想象”不只停留在个案性概念和命题上,尤其是理与据的充分,其论域至为宽广,把控甚为精到,辨析也颇为到位。如“导言”就先期讨论一个文化现象,因他“为看到超越‘环境’与‘自然’的必要性和微妙而寻找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该书第10页)。因为在美国及可以是“符合道义”的其他地区,被称为美国移民文化历史上最经典的生态文学,是一首流行的圣歌及多种表达,布伊尔以此为引线比较简·亚当斯和约翰·缪尔这“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双联画”。亚当斯是将“礼仪带给‘城市荒野’”,而缪尔则守持保护荒野的使命,两者似乎是不相容的,但布伊尔认为,他们的路径没有发生交叉,对生态支持的看法是互补的。在该著最后一章中,布伊尔从水的流域特性论说,河流由古老的象征性及生命对河流的依赖性,明确流域对人类文明的定义,甚至一条河流或能成为一个国家明显并可信的“自然象征”。基于寻古而今地分析现代流域意识,以玛丽·奥斯汀为范例展开而推至现在,并指出“当代流域意识经常并越来越多地包含有更明显的多元文化”(该书第299页),由此便宏观地托举出一个全新表达,即“流域美学”。由布伊尔著述可见,在对环境问题研究的世纪性推进中,仅仅由文学而释解环境现象分析问题,试图找寻疗治的良方并非是精准的,其融括也是弱化的。
三
在该书的研究进路中,文化是一个大视阈,也是可操作且力主全面概览的视阈,在新世纪的进路中,这或被称为“环境人文”研究。这种研究路线的对象、阐释依据及所关涉的“作家”们被布伊尔称为“纵横驰骋于‘文学’与‘非文学’的传统划界之间的人”(该书第3页)。由此看来,这种“批评”并不仅限于文学批评,或就广义而言可谓环境人文批评,因该书的标题就设定为“文学、文化和环境”。我们还可以脉络性梳理布伊尔的这种研究路径,由简·亚当斯和约翰·缪尔的对峙与互补为始端,阐明“生态想象”和“生态无意识”两大概念,确证“生态无意识”所引发的“这种环境会根据个人、文化、历史时期的不同给予巨大的可塑性”(该书第28页)。环绕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而关涉了18世纪末到现在的多样相关文本,并引出了有毒物剖析的话题,继而阐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前提、前因、影响及文化意义。对“住所的住所”的研究,布伊尔指出,“文学想象的传统特色之一是唤起并创造一种住所感”(见该书第66页)。他认同的住所并不只是一个实在居所,而是“飘忽不定”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结构,具有高度的且灵活的主观、社会和物质方面的含义,因而他说“住所想象是重要”的。布伊尔用“拯救不为人所爱的住所”的引题分析非裔美籍作家约翰·埃德加·怀德曼,因怀德曼从童年开始,其居住地或为住所就是不定的,飘移性显然制导其文学活动。从漫游到重新入驻城市,布伊尔研究了惠特曼、奥姆斯特德,基于极端现代主义下的现代城市理论,分析了作为物质地方主义者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以“决定论的话语”引出系列性的作家阐释,由狄更斯到莱特的都市小说,分析德莱塞和杰弗斯,贝里和布鲁克斯。这个话题涉及着一个“生态决定论”的视阈,因其关涉“那些在最低生活水平上的”人的存在,这些人或许是依靠自然、物质基本需要而生活,对之反思、论争不断,于此,布伊尔称美国女作家简·亚当斯的华丽文章《现代李尔王》是更好的反思生态决定论的文学范例。福克纳和利奥波德是被公认的关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倡导者,布伊尔在“现代化与自然界的诉求”的话题中称福克纳为生态历史学家,将猎人转变为生态环保主义者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称为现代生态伦理学之父。海洋在布伊尔这里是“作为资源和图标的全球生态系统”,在这种论题下书写海洋,忧思海洋遭际的著作多而又多,但蕾切尔·卡森关乎海洋的研究以及《寂静的春天》仍然是布伊尔首先引带出来的,而麦尔维尔的《白鲸》又必然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话题,以此展开的重要表述是“民族、文化和物种等级”。非人类生命是环境人文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必然会关涉多个关键性视点,人类与保护、苦难与杀戮、伦理与正义等,环绕这多重视点产生的文学文本同样多而又多,霍根的《灵力》是布伊尔的重点阐释文本,因其关涉一个美国土著女人杀害濒危物种佛罗里达豹而被审判的事件。在“流域美学”论域中布伊尔称“流域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生态偶像”,继而他以总结性话语表述:“在大都市化增加的时代,关于流域的景观想象进一步用来提醒人们,即使在密集的城市中心(其中许多城市是建立在海湾或河流开始的地方),‘人造’和‘自然’元素的共处;也提醒人们把乡村与城市隔离或者把城市与乡村隔离都是不可能的。”(该书第307页)
多角度延展、驰骋“生态想象”,继而深度剖解文学、文化与环境,且主要以美国视角展开,以其为“镜”“像”而对人类所为及人类进程把脉的这部著作,布伊尔在其开篇即引述《庄子·外篇·胠箧第十》所论:“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知者,皆知非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是以大乱……。”应该说,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导入该书,似在引领全书的研究,必然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可见布伊尔对中国文化及文脉的知晓,当其以此作为释解当代的“危机”警示及警语,也许他看到了中国智慧对解决当代环境问题,提升人类文明所应该起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文明的“自信”也必然认同,或肯定中国智慧的精义的确对人类贡献巨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人类未来行进路程中必定会起到越来越大,越来越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