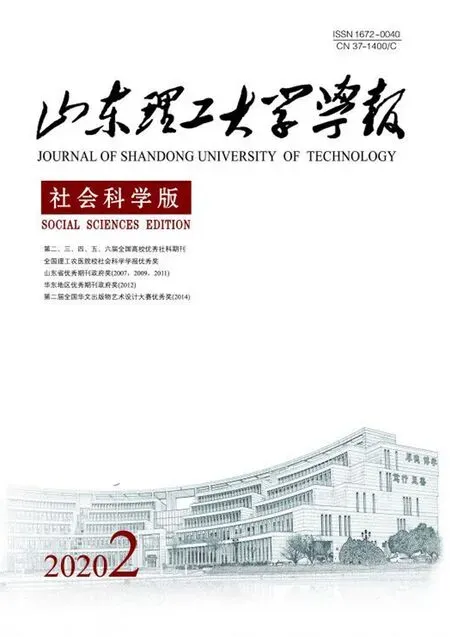家族文化视角下“神韵说”生成观照
丁 修 振
新城王氏家族是山东著名的仕宦家族,有“江北青箱”之誉,兴盛达三百年之久。其家族鲜明的文化传统以及优良的文化生态使得家族名人辈出,王士禛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家族文化传统对王士禛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王士禛及其家族文化的研究在学术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讲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探究(1)目前学术界对新城王氏家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新城王氏家风》《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文化研究》等少数专著,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王氏家训、家风、文学传统、婚姻等方面,这些研究相对于王士禛的诗歌研究来讲,显得比较薄弱,缺乏深层次、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所以王志民先生在“纪念王渔洋诞辰38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也指出:要大力加强王氏家族文化的研究,将其作为今后王渔洋研究的重中之重,要做强做好。。“神韵说”是王士禛诗歌文化的核心,贯穿于他人生的始终。而家族文化又对王士禛“神韵说”的生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试图将其家族文化放诸“神韵说”生成过程中,对“神韵说”进行深入的观照,试图找到“神韵说”与其家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
一、家族文化与王士禛“神韵说”初萌
顺治十四年(1657年),是王士禛人生重要的时期,有两件事对他日后的诗歌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八月与诸名士云集大明湖,作《秋柳四首》,诗传大江南北,和作数百人。其二:王士禛将一年前创作的诗,编为一集,名为《丙申诗集》,明确提出了“典、远、谐、则”四字诗歌创作原则。在前一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年)王士禛已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的储备,他在自撰年谱中称:
山人自乙未五月买舟归里,始弃帖括,专攻诗,聚汉、魏、六朝、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故诗断自丙申始。钱塘吴君宝崖云:“先生论诗要在神韵,画家选逸品居神品之上,惟诗亦然。”[1]5061
从以上我们可以明确,顺治丙申前后是王士禛神韵诗作的开端,也是“神韵说”诗歌理论的初创时期。在他晚年亲自校订的《渔洋精华录集注》中,作品即是从丙申年开始收录的,这与“诗断自丙申始”的说法相符。此时他的神韵理论的提出以及神韵诗作《秋柳四首》首创大成,虽令人惊异,但也绝非偶然,良好的家族诗歌文化有力地促进了“神韵说”的初萌。
首先我们看“典”这一理论的生成。“典”字着眼于诗歌的正统性与典雅性,表明了“神韵说”的古典主义性质。我们再看王氏家族的诗歌文化传统,“王麟(王士禛三世祖)以明经出身,是为滥觞”[2]。王麟十岁师从以《诗经》为长的学者毕义理,开启了家族诗歌文化的先河,此后家族诗人辈出。“时方伯公(王士禛祖父)以遗老居田间,自号明农隐士,闭户谢客。亲教诸孙,颇及声律之学。尝邀从弟洞庭(象咸)饮。洞庭工草书,有张颠遗风。酒阑,诸孙竞进乞书。方伯公把酒命对句曰:‘醉爱羲之迹。’山人在旁应声曰:‘狂吟白也诗。’二公皆大喜,赏以名人书画”[1]5055。被誉为“生于于麟之乡,承季家学”的伯兄王士禄“兄道兼师”,教授王士禛唐人诗法。浓厚的家族诗歌氛围,良好的诗歌教育,使王士禛等诸兄弟效仿前辈,以唐人诗歌为模仿对象,相互唱和。“尝岁暮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辋川集》,约共和之,每一诗成,辄互赏激弹射,诗成酒尽,而雪不止”[3]。
基于家族优异的诗歌氛围和良好的诗歌教育,王士禛的诗歌具有路子正,起点高的优势。王士禛在十五岁时便成诗一卷《落笺堂初稿》,其中“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等诗句已极富唐人山水诗的韵味,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神韵说”的生成奠定了基础。正如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说:“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泝之楚辞、汉魏乐府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可以说,“典”,具有“正”的属性,深植于传统文化,在其“四字”诗歌理论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其次“远”是在“典”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典”使得王士禛的诗歌具有雅正的意味,“远”使王士禛的诗歌更具山水意蕴。
家族先辈王重光、王之垣、王象节、王象艮、王与胤等皆有诗名,新城王氏在齐地是诗歌的代表和主导力量,其中最著名的诗人当数王象春。王象春与公鼐、冯琦号为“齐地三彦”,与明代诗坛领袖钱谦益为同榜进士,首倡“齐风”并在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王士禛没有被动地学习和借鉴前辈的诗歌,而是充分利用“典”这一思想原则来评点家族前辈诗歌名家,以此反哺自己,提升自己的诗歌理论水平。王士禛虽折服叔祖王象春的“天才排奡,目空一世”的豪气[4],但他对王象春诗歌的评价却颇严苛:“季木公诗与钟伯敬、文太青皆一魔也。然钟有慧心,去其魔十可得三,文与公惟以伧气叫嚣怒张,去其魔十才得一而已。”[5]此评价虽有过激之嫌,但指向问题实质,正如文坛领袖钱谦益对王象春的评价:“尤以诗才自负,才气奔逸,时有齐气,抑扬坠抗,未中声律……季木如西域婆罗门教邪诗外道,自有门庭,终难皈依正法。”[6]这个阶段王士禛是以“典”为严格的评鉴标准,他在评十八叔祖王象明《鹤隐》《雨萝》诸集时说:“才不逮考功(王象春),而欲驰骤从之,故时有衔蹶之患,未能成家,今刻板仅有存者。”[7]
从王士禛手批王象春《问山亭诗》来看,王士禛对叔祖的多篇诗评曰“俗”。对一些符合“典”“远”的诗句则以“田舍语好”“用意蕴藉侣唐人”等作为评价。王士禛在手批王象春《问山亭诗》中已开始运用“远”字作为评价,如在《宾王南还》中“还家诗酒推豪长,咫尺清江燕子矶”诗句旁,书写一“远”字。他虽然称叔祖王象明的诗有“衔蹶之患”,但对具有“远”的意味的诗,也是加以肯定和记录,认为:“亦有足传,如旧日轻雷送雨声,小窗历乱竹枝横。水痕时落还时涨,枕上看山秋欲生。”(《渔洋诗话》)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士禛已经将“远”作为重要的诗歌评价标准,他最中意具有“远”之意韵的山水诗歌。
“远”的思想在王士禛手批王象春《问山亭诗》中已现端倪,“远”的思想的生成也是受家族文化教育影响的结果。新城王氏喜好山水,他们在新城、济南等地建有别业,叔祖王象春罢官居里,在济南百花洲筑问山亭,常与齐鲁诗人在此雅集,并写就《齐音》,《齐音》被赞誉为:“况历旧无专志,今百咏所载,千秋之作备矣。”[8]家族传统的山水清音滋养着王士禛的性灵,他自少癖好山水,在《古欢录自序》中称“山人少无宦情,虽有周行,时有来景云栖之志。幼读书至《秦风·兼葭》,流连三复,掩卷旁皇久之。”
王士禛在欣赏山水,在歌咏山水,在山水中自觉地提升着对诗歌“远”的认识。少时在家乡新城及邹平留下了不少的山水之作。顺治丙申春,专心攻诗的王士禛与叔祖王象春的外孙徐夜“同游长白山(2)山东省邹平、章丘一带山脉,有泰山副岳之称,摩诃山为其主峰。,凡柳庵、上书堂、醴泉寺诸胜皆至焉”,其间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山水诗作。丙申四月,王士禛又到莱州看望莱州府学教授兄长王士禄,在莱州与明末山左诗坛中坚赵士哲兄弟相互酬唱,创作了大批初具山水神韵之作,王士禄将诸家作品集为《涛音集》。集中频繁的诗作活动,使王士禛原先的积淀得以升华,最终使“神韵说”得到了萌发。
总体来说,“神韵说”的初萌是家族文化熏染以及前辈诗人二十余年对王士禛培养的结果。在他的“四字”诗歌理论中,“典”是基础,“远”是在“典”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远”的意义在于诗歌要有意在言外、耐人寻味的特质,它使“神韵说”具有了鲜明的特色。王士祺这一时期的诗作《秋柳四首》《南园池上》等,其风格确如明末遗民作家冒襄在《阮亭诗选序》中所说:“其标旨也,微而远,其托物也,思而多风。”
二、家族文化与王士禛“神韵说”的深化
创《秋柳四首》逾三年,(顺治十七年)二十七岁的王士禛就任扬州推官,此时他的“四字”诗论受到诗坛领袖钱谦益的激赏。钱谦益在《王贻上诗序》中说:“季木殁三十余年,从孙贻上,复以诗名鹊起。闽人林古度铨次其集,推季木为先河,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新城之坛坫,大振于声销灰烬之余,而竟陵之光焰熸矣。”[9]
在扬州推官任上,王士禛务尽职守,清廉为官,他曾颇为自豪地称:
山人官扬州,不名一钱。急装时,惟图书数十箧。尝有诗云:“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1]5073
王士禛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主持红桥修禊,遍访扬州遗老,也因此获得了“绝代消魂王阮亭”之誉。“绝代消魂”正是基于对王士禛“秋柳四首”的再评价。
在明清时期齐地文人的雅集中,新城王氏一直居于领袖地位。家族多人是复社的成员,声望很高。“明季复社,声气徧天下,每会,至二、三千人……新城则三王倡首。西樵、礼吉主‘晓社’,渔洋举‘秋柳社’。此外,又有‘因社’”[10]。顺治十四年,王士禛在秋柳诗社上所作的《秋柳四首》振动齐鲁诗坛,传遍大江南北。“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于是《秋柳诗》为艺苑口实矣”[1]5062。继齐地“秋柳雅集”后,王士禛在扬州主持重要的文人雅集活动有三次。第一次是康熙元年(1662年)的红桥修禊,有名句“绿树城郭是扬州”传世,八人和作刊刻为《红桥唱和集》。第二次雅集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成《治春绝句》二十首。第三次雅集在冒襄的水绘园,成七言古诗十章。他在扬州倡导的文人雅集,实为其家族在齐地做法的承袭。文人雅集一方面起到了交流创作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王士禛在江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从“秋柳”的伤感迷茫,“微而远”般自我心理体验,转向了超乎功利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康熙二年,王士禛三十岁,写就了著名的《论诗绝句》四十首,这标志着“神韵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试看其中之一:挂席名山都未逢,浔阳喜见香炉峰。高情合受维摩诘,浣笔为图写孟公。
王士禛此时的诗作充盈着人与自然的审美之趣,具有强烈的诗画色彩。如《再过露筋词》《青山》《江上》等著名的神韵诗皆是如此。在扬州推官任上,“神韵说”深化扩展的实现,实由王士禛年轻的积淀为基。
首先王士禛“神韵说”的深化与他年轻时的书画教育密切相关。王士禛出生在一个诗、文、书、画俱优的家族,族人亦不乏书画名家。叔祖王象咸被明末之人誉为“墨王”,堂兄王士誉举人出身,能诗能文,是书画名家。有“南董北邢”之誉的邢侗与家族成员关系密切,王氏家族在忠勤祠刊刻宏大的碑林时,也得到邢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家族艺术的熏染下,多思善感的王士禛,对书画艺术有着不凡的造诣,他的书法被称为具“晋人之韵”。
“韵”是中国古典书画艺术的特征之一,重写意而非写实,重写神而非写形。正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云:“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这与王士禛的“神韵说”是一致的。王士禛将书画与诗歌的艺术精神打通了,极大地促进了他的“神韵说”的生成。此时王士禛的神韵诗作也达到了他所倡导的“登高极目,临水送归,蚤雁初莺,花开花落”自由、写意的艺术之境。也如吾师王小舒先生所言:“诗意和灵感乃是在人与自然间发生了一种审美关系之后才产生出来的,这是诗的真正源泉。”[11]扬州时期,王士禛的“神韵说”看重的是“意在笔墨之外”,重在体现人与自然间的审美关系。
其次随着“神韵说”的深化,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确定,诗歌的主、客体间的关系变得显明。诗人的人格境界,对诗的品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士禛在年轻时积淀的人格品性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曾制《太仆家训》,以“道义”“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来告诫子孙。曾祖王之垣严行家教、勤俭朴素,力戒奢侈,堪为表率。“之”字辈之下的“象”字辈中多清廉之士。祖父王象晋曾撰一联:“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耕惟读。”[12]新城王氏族人以耕读为宗,以儒家文化立身,力求保持人格独立。新城王氏家族这样的事例很多,王士禛在著作中也多次提及,引以自傲。受此影响他在扬州任上,清正廉洁,不名一钱;在处理“通海”大案、“扬州积欠案”中,不避险恶,保全贤正无辜者无数。也如王英志先生所说:“渔洋成为‘一代正宗’,一个十分实在、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他的处世型态和人生道路。他儒道双修,行儒言道,亦官亦言文,不热衷迫切但却不辞恩宠甚至以退促进,上下和睦,谨慎温厚,忠孝友悌、敬业修身。”[13]
家族的文化以及遭遇,使王士禛对为官有着比同僚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力求从官场的险恶、尘俗中脱离出来,与读书之人为朋,与江南遗老为友,他赏太湖,览真州,忘情畅游其中。顺治十八年正月,即王士禛到扬州第二年,他“晓起登诸阁望太湖,渔洋山一峰正当寺门,爱其秀峙无所附丽,取以自号”[14],渔洋山成了王士禛自身理想的化身。从自号“阮亭”到“渔洋”的转变,标志着王士禛从早年效仿魏晋风流文士逐渐向清远、独立的人格追求发生着转变,这一转变也使他的诗论得到了更大的深化和提升。
所以说王士禛在扬州时期,家族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他为官处事、诗歌创作。这也使他从世俗中解放出来,进一步将这些文化修为的因素“移情”于诗歌中,含而不露地改变着自己诗歌和诗论的风貌,由此有了“神韵”的深化,也为王士禛“神韵说”的真正成熟奠定了基础。
三、家族文化与王士禛“神韵说”的成熟
王士禛康熙五年至京师,因“诗文兼优”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在此期间他进行了诗歌取法宋诗,典试四川时雄壮诗风的尝试。王士禛试图寻求诗歌的发展与突破时,诗坛的“唐宋之争”,为他“神韵说”的成熟和嬗变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首先这个契机变成现实的生发基础是新城王氏不立门户,不参与党派之争的家族文化。
康熙二十七年,王士禛撰《唐贤三昧集》三卷。此时他的诗学思想正处于趋宋重归唐的一个新转变时期,他将唐代诗人符合神韵的诗编为一编。“门人彭太史直上来问余选《唐贤三昧集》之旨,因引洞山前语语之”[1]5090。可见王士禛编《唐贤三昧集》是有意而为之的,是针对于当时诗坛的状况而来的。当时的诗坛宋诗派,“依托遭际相同的亡宋遗事,抒发故国旧君之感……以至出现‘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的现象,宋诗蔚成大国”[15]。据《清诗史》载,唐诗坚定支持者“益都相师(冯溥)尝率同馆官集万柳堂,大言宋诗之弊”[16],可见当时的诗坛“唐宋之争”已呈尖锐之势。
典雅深厚的诗学修养,公道正派的主张,使得王士禛的“神韵说”得到了当时诗坛的广泛认可和拥护。“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语录史论,皆可成篇。于是士祯(禛)等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而矫之”[17]。
不立门户,不参与党派之争是新城王氏的文化传统,在明末党派纷争之际,适逢新城王氏鼎盛之时,而新城王氏秉持中庸思想,严禁族人参与党派之争。受家族文化的影响,王士禛处事中雅平和,雍容大度,这为他以诗的审美价值为标准,跳出“宗唐界宗”的束缚,矫正诗坛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其次境界高远的家族文化塑造了王士禛超凡脱俗的人生情怀,这也是让他跳出“唐宋之争”,促成“神韵说”成熟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七年成书的《唐贤三昧集》,是王士禛摆脱唐宋之争而有意为之的,但这只是王士禛“神韵说”成熟的序幕,他在康熙二十八年成书的《池北偶谈》则标志着“神韵说”的成熟。
汾阳孔文谷(天胤)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12]430。
“清远”是“神韵说”成熟的重要标志。“清远”是神韵诗歌的一种境界,既是品格,又为风神,诚如王士禛所言:“格谓品格,韵为风神。”[18]“清远”最终指向的是诗人超凡脱俗的人格品性。
王氏家族在明末遭受多次兵祸,其中以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兵祸尤为惨重。“十二月,清兵至济南,新城陷落。叔父与玫、与朋与朋子士熊、士雅遇难,从兄士和妻张氏经死。徐夜母及家族十馀人亦殉难”[14]11。新城王氏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在明清易代中多有殉节者,王士禛的母亲在兵乱中也曾自杀,幸而绳绝未死。这些事例成为一道心理的暗影,时时影响着王士禛。他虽称“少无宦情”,但在《鲁仲连陂》等诗中却表现出“功成不受赏,飘然归海垠”的高义之情,他的内心是矛盾的。日后,王士禛走上仕途,受到康熙帝的恩遇,但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与统治者“不黏不离”的心理距离,始终保持着清远的人格。
在《唐贤三昧集》成书的四年前,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王士禛奉命祭告南海时,曾记“雪阻东平,望小洞庭中有蚕尾山……自序梗概以志寄讬。一时海内风雅之士,咸谓山人处高位而有超世之志焉。”[1]5088七十一岁,他被免官归里,“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堵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王应奎曾说:“内大臣明珠之称寿也,昆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笺一幅请于先生,欲得一诗以侑觞。先生念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遂力辞之。先生殁后,门人私谥为文介。”[19]
王士禛为官清正廉洁,心态超然物外,生命安宁清远。这些做法或品性也与他的诗歌理论一脉相承。他特别推崇“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的艺术境界,这个艺术境界要求诗人与审美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淡泊自处,他终于为自己保留了一块宁静超然的审美天地实践了基本的人生原则,使得创作理论和主张都站在了基本踏实的基础上,没有悬空”[11]318。诗风与人格一致是王士禛“神韵说”的重要特点,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清远人格的话能做到超凡脱俗吗?清远的审美距离能实现吗?“神韵”还存在吗?
王士禛受家族文化熏染所成的“禅境”是“神韵说”最终的旨归。
“神韵说”到“清远”之境是谓成熟,但没有结束。王士禛以独到的审美判断,跳出了“唐宋之争”,但这并不是他“神韵说”的最终归宿,“神韵说所概括的诗歌之美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一种缥缈悠远的情调或境界”[20]。缥缈修远的情调或境界是生命状态的表达,它直切人生之本谛,直指“禅境”,正如王士禛所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21]。当代美学大家宗白华也说:“禅是动中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22]
王士禛的“神韵说”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王象春晚年也提出“神韵说”,也提倡过“禅诗”,两人都提出同样的论断绝非偶然。这与新城王氏家族浓厚的宗教文化有直接关系。新城王氏因多有善举而被誉为“大槐王氏”,家族发展的历史充满着传奇色彩。王之垣母亲刘太夫人在王氏家族中举足轻重,她笃信佛教,寿九十有余。王之垣、王象乾、王象晋等受此影响也不例外,他们在乡梓修建寺庙,供奉菩萨。王士禄因磨勘下狱后,王士禛到南京长干寺燃灯,以求伯兄的平安。王士禄平安回归故里后说:“昔人忍饥诵经,吾辈骨相穷薄,理固应尔,且时于此中得少佳趣耳。”受家族宗教传统的影响,王士禛与僧人关系密切,在京师时,他与盘山和尚释智朴过从甚密,他评点释智朴的《青沟偈语》,并为其作品作序,“已巳七夕,予赴京师,诸君饯于禅智寺……因刻《禅智录别》一卷,志一时穷交之谊”(《居易录》)。
他在编选《唐贤三昧集》时云:“《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三昧”即为佛经自在之义,他此时提出的“平淡之境”是“神韵说”走上禅境的先声。晚年王士稹在《古欢录》自序中曾云:“康熙已卯,山人官御史大夫,世号雄峻,山人居之淡然。其门萧寂如退院僧。”康熙四十六年被罢官回乡,他闭门谢客,专心写作,有《古夫于亭稿》《蚕尾续集》等得到厘定。此时的王士禛感悟人生,感悟禅语,感悟诗歌,由此他认为诗境与禅境的心理体验是相同的,所以他在《蚕尾续文》中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
王士禛随着对人生感悟的深化,家族宗教文化在他的心中生长,使他完成了“绝代消魂”到“清远淡泊”风神的蜕变,也使他的“神韵说”臻于炉火纯青,蔚为大观。
总之“神韵说”贯穿于王士禛人生的始终,新城王氏家族文化在王士禛“神韵说”的生成中伴随始终,起了诱因与基础性的作用。新城王氏的家族文化这棵大树,开出一朵以“神韵”名之的祥瑞之花,成就了王士禛诗化的人生,成就了中国的和谐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