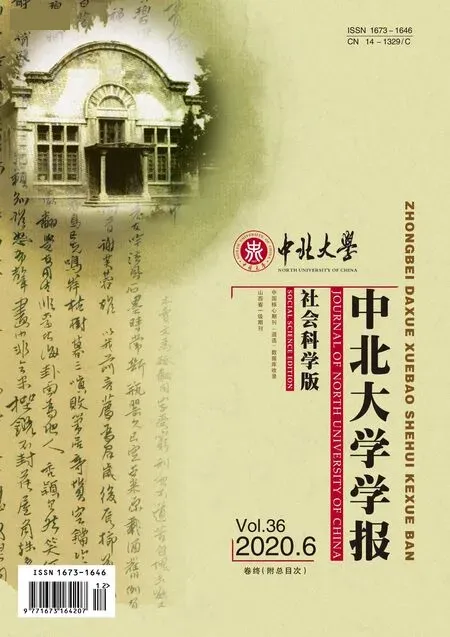《快乐影子之舞》: 音乐共同体之形塑、 幻灭与想象*
史红霞
(山西农业大学 基础部, 山西 晋中 030800)
《快乐影子之舞》是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同名短篇小说。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 叙事细腻精湛, 内蕴峻旷幽远而丰富。 小说伊始, 叙述者“我”便开门见山地告知读者, “马萨利斯小姐又在举行聚会”[1]211-224。 接着, 讲述了马萨利斯小姐以一成不变的方式举行一年一度的钢琴表演聚会, 而以“我母亲”为代表的马萨利斯小姐的学生, 毫无热情地看待和出席聚会。 最后出场的身有残疾的学生的钢琴表演, 某种程度上在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学生心中激起了一点涟漪, 但这点涟漪转瞬即逝, 钢琴演奏仍得不到认可。 最后, 学生们驱车而去, 马萨利斯小姐永远不可能再举行钢琴表演聚会了。
门罗的作品在国内引发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 就《快乐影子之舞》这篇短篇小说而言, 截止目前, 相关研究很少, 研究成果的水平也尚未达到一定高度。 王晓英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 解读小说中异化的母女关系。[2]薛琴的研究表明, 异化关系不只存在于母女之间, 同时也存在于音乐教师马萨利斯小姐和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学生之间, 究其原因在于马萨利斯小姐代表的现代主义精神和以“我”“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错位。[3]赵晶和侯君又指出, 门罗的作品充溢着加拿大后殖民、 后现代的文化特色。[4]本研究赞同以上观点, 同时认为该小说还蕴含了门罗的共同体思想, 因而试图从音乐共同体角度对《快乐影子之舞》加以阐释。
根据滕尼斯的观点, 共同体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其赖以生成的基本要素包括共同目标、 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共同目标强调“满足成员需求”, 是共同体生成的前提; 身份认同指个人把自己认作属于哪个群体或持有哪种文化价值观的人, 是共同体生成的基础; 归属感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 是共同体维系的纽带。[5] ⅲ科恩认为, 共同体的构建, 需要共同体成员之间就共同关心的价值观和文化符号内涵等问题, 不断进行对话、 商议和讨论, 定期更新彼此之间的精神默契和情感纽带, 方可避免共同体形式的教条化, 激发并维持共同体鲜活和旺盛的生命力。[6]40本文拟基于文本细读的方式, 从共同体社会文化语境、 共同体个体、 共同体想象三方面探析《快乐影子之舞》中音乐共同体的形塑、 幻灭与想象。
1 共同体之社会文化语境
在探讨小说中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审视一下其标题DanceoftheHappyShades(《快乐影子之舞》)。 “shades”有“阴魂、 幽灵”之义, 同时影射小说中的人物包括马萨利斯老师和她的学生都如同影子般虚幻地存在着。 而“happy”显然充满了质疑和反讽的意味, 反衬出作品中人物所处的阴郁“心态”, 因为影子是不可能具有情感的, 自然也不可能快乐。 门罗巧妙地借用最后出场的残疾学生弹奏的钢琴曲作为故事的标题, 意味深长, 诗意地影射了处于母国幽影之下的加拿大人“阴性”的精神状态。
众所周知, 加拿大是一个后殖民国家。 门罗笔下的音乐共同体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构建的。 由于加拿大祖先与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之间存在的联系, 所以一直保持着对母国的忠诚, 这种社会历史语境导致了加拿大民族的阴性身份——被统治者[4], 而被统治的阴性身份又会导致加拿大人孤独彷徨的文化焦虑, 从而引发摆脱这种身份的心理诉求。 这篇小说中, 在马萨利斯老师的房间里, 有一张苏格兰王后玛丽的照片。 这张照片在文化上象征着加拿大民族身份的阴性特征, 以及马萨利斯老师作为加拿大人对“母国的忠诚”。 而马萨利斯老师终其一生努力建构音乐共同体, 则体现了她对处于阴性状态的加拿大民族文化问题的忧虑。 同样, 她的学生也处于被统治的阴性状态, 也体现了对自我身份的孤独、 异化的焦虑。 这种自我身份焦虑、 缺乏归属感是共同体缺失的证据, 也是马萨利斯老师构建音乐共同体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 与其他国家一样, 加拿大也呈现出后现代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 深受资本和商品逻辑的支配, 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 怀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产生, 同时也导致了人的被异化、 被物化[7]15, 以及非中心、 不确定思想的彰显。 《快乐影子之舞》中, 马萨利斯老师的学生是典型的后现代文化的产物, 他们的精神信仰已经瘫痪, 各自为一个“孤岛”, 彼此之间缺乏沟通交流, 内心孤独异化, 已然虚化为滑稽荒诞、 平庸委琐的影子。 而马萨利斯老师从始至终得不到学生认同, 最终也沦为一个缺乏归属感的苍白“影子”。 她们的这种身份特征显然成为音乐共同体构建的一大障碍。
总之, 在加拿大后殖民、 后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人们处于一种没有主权、 没有归属感、 没有自我精神价值和身份认同的茫然若失的状态, 是共同体缺失的表现。 那么, 在《快乐影子之舞》中, 门罗是如何揭示处于后殖民、 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加拿大人在构建音乐共同体方面所呈现出来的问题, 又是如何对构建音乐共同体展开想象?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2 共同体之个体: 形塑与幻灭
音乐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审美、 认识和育人等社会功能, 是共同体构建不可或缺的因素。 然而, 20世纪中叶到来之际, 艺术音乐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不可避免地接近了“分崩离析”的后现代局面”[8]续论3。 在这篇小说中, 马萨利斯老师正是努力通过构建音乐共同体, 以一己之力来挽救音乐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
共同体由一个个个体组成, 音乐共同体也不例外。 判断音乐共同体是否具有深度, 需要深究一下共同体中的个体。[9]小说中, 马萨利斯老师这一中心人物是音乐共同体构建的组织者, 她的学生包括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学生”以及最后出场的身有残疾的学生们是参与者。 这一部分探讨的共同体参与者, 只涉及以“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学生”, 而最后出场的身有残疾的学生们, 在音乐共同体建构中扮演着不同于前者的角色, 因此被置于第三部分予以论述。
2.1 马萨利斯老师: 执着与固化
在后殖民、 后现代语境下, 加拿大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沉迷于自身, 自我成为拯救的先驱。[10]在《快乐影子之舞》中, 马萨利斯老师显得格格不入, 似乎过着一种“孤岛”生活。 但她“孤岛”不孤, 因为她内心有信仰, 有音乐作为其精神慰籍。 而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学生”则是后现代人。 根据利奥塔的阐述, 后现代是存在于“现代性”之中的某种正在颓废的事物, 包括异化、 麻痹、 委顿、 颓废、 平庸等, 唯有艺术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神圣的存在, 可以改变后现代社会的这种颓废的精神现状。[11]故事中, 门罗塑造的马萨利斯老师是传统文化的代表, 试图以一年一度的钢琴演奏聚会为纽带, 借助音乐来弘扬真善美, 救治“我”和“我母亲”为代表的后现代人的“孤岛状态”, 为彼此找寻精神归属感和寻求身份认同, 构建真善美的音乐共同体。 但是, 她是否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呢?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音乐。 所有孩子的内心深处都热爱音乐”[1], 这是马萨利斯老师一生恪守的信仰。 为了构建一个想象中的美好的音乐共同体, 她不顾个人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 一生坚持给孩子们上钢琴课。 “马萨利斯老师能不能付得起这些礼物的钱。 ……她的学费10年来只涨过一次(即便如此, 那次涨价还是让两三个母亲再也不来了。 )”[1]音乐对马萨利斯老师而言是一种神圣的存在。 一年一度的聚会上, 她总是精心打扮一番, 体现出对音乐仪式般的尊重和重视, “涂了口红, 还是古典的发型, 锦缎长裙”[1]“你知道她今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做三明治了……我猜她是担心自己到时准备不好。 怕她自己忘记什么事情。 他们讨厌忘记……”[1]从这些对马萨利斯老师细致入微的描写, 可以体会到其构建共同体的精神诉求和执着追求。 马萨利斯老师的共同体情怀, 还体现在她的共同体伦理理念。 作为共同体形塑者, 马萨利斯老师拥有一颗善良、 仁慈之心, 从不会批评孩子们, “除非用最为细腻抱歉的方式”[1]。 无论是对身体健全的学生, 还是对身有残疾的学生, 她都表现出对生命一视同仁的尊重、 认同与关怀。 尤其是当那些身有残疾的孩子进行钢琴表演时, “马萨利斯老师坐在钢琴边, 以她一贯的仪态冲每个人微笑。 她的笑容不得意洋洋, 也谈不上谦虚。 她并不是魔术师, 要看每个人的脸”[1]。 总而言之, 马萨利斯老师对音乐、 对真善美的崇尚, 使得她甘愿倾尽一生的努力去构建音乐共同体。
然而, 正如英国威尔克斯大学菲莉丝·韦利弗(Phyllis Weliver)所指出的, 在共同体文化空间的建构中, 把文雅和平静的掌控当作衡量音乐的标准, 循规蹈矩地寻求同质效应, 其实显露的是一种由规训和理性构建的公共领域, 而非有机生成的、 充满激情的公共领域。[12]马萨利斯老师执着于以自己的居所作为共同体空间来构建共同体, 然而, “马萨利斯老师从银行街的砖结构平房搬出来……搬到一个甚至更为小的地方——要是她的话还算准确的话——她搬到了巴拉街。 (巴拉街?在哪儿?)”[1]“一幢狭窄的房子……阴暗, 造作, 一幢表面诗意而其实不堪入目的家居房屋”[1], 这个共同体空间破旧而狭窄, 贴切地折射出马萨利斯老师极其狭窄的话语、 视野和思维方式。 而且, 在这个音乐共同体空间中, 组织者马萨利斯老师是“原生态的、 文雅的人”, 她以温文尔雅、 一成不变的方式在塑造共同体。 “那些日子, 这一切都是稳定可靠的、 有传统的, 有自己宁静过时的方式, 有它自己的风格。”[1]举行聚会的时间地点、 马萨利斯老师每年的穿着打扮、 聚会上准备的食物, 甚至包括马萨利斯老师送给学生的礼物、 安排学生每年弹奏的曲目、 迎接学生的方式和对学生的态度, 一切都是千篇一律。 音乐, 本应是活力、 生命激情的代名词, 但在马萨利斯老师的聚会上, 却显得毫无张力, 索然无趣。 “传统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阴气, 当他被传统占据的时候, 就失去了活力。”[1]马萨利斯老师构建共同体的初衷无可厚非, 但她“循规蹈矩地寻求同质效应”, 试图利用这种僵化单一的仪式模式之矛对付后现代颓废功利之盾的做法, 显然陷入了机械主义的误区。 她的话语和视野仅代表她自己, 没有考虑“学生的需求”, 营造了一种死气沉沉、 毫无活力的氛围, 导致她的学生对聚会的态度也是一成不变, 表面敷衍应付, 内心却充满反感和厌恶。
同时可见, 在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 马萨利斯老师由于自己作为音乐教师的身份一直得不到学生的认可, 潜意识里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 在我看来, 马萨利斯老师在吻我们的时候, 看的是远处, 她正往街上看, 在等哪个尚未到达的人。[1]“马萨尔斯老师也难以将目光投向表演者; 她一直望着门。 她是否期望即使现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缺席者也会出现?马萨尔斯老师也很难把目光聚焦在孩子们的身上, 她一直在看着门。 难道她到现在, 还在等哪位没有解释就没出现的客人?”[1]马萨尔斯老师意识到自己得不到学生的认可, 意识到自己无力填补共同体形塑与现实之间的裂痕, 力不从心, 所以注意力一直聚焦于“学生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显露了她无法实现自我身份认同、 缺乏归属感的状况。 马萨利斯老师建构音乐共同体的程式化的老套方式反复得无以复加, 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与她“诗意”地构建共同体的恒心之间无法架起桥梁, 其努力遭到了学生一如既往的“不抵抗的抵抗”[13], 最终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失序、 无机的绝境状态(aporia)。[14]1
2.2 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学生”: 敷衍与拒斥
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学生们, 与马萨利斯老师相比较, 对钢琴演奏会的态度迥然不同。 在马萨利斯老师打电话告知“母亲”要举办钢琴演奏会时, “她(我的母亲)放下电话转过脸的表情, 着实有点恼羞成怒——仿佛她看见东西乱七八糟, 但又不能收拾。 ……她答应参加,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她一直软弱地谋划不去的种种办法; 尽管她知道自己会参加”[1]。 不仅“我的母亲”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她对马萨利斯老师举行聚会的厌恶和反感, “以前学生的孩子, 似乎是马萨利斯老师新学生的唯一来源。 每年六月都有新的, 当然也会有大量辍学的情况。 玛丽兰·伯特的女儿不上了; 琼克·利伯的女儿也不来了”[1]。 一届届的马萨利斯老师的学生对钢琴演奏会丧失了兴趣, 而学生这种明显的缺席, 强烈地烘托出了共同体形塑的无望。 “这些搬到郊区的女人们, 有时会被自己已经落伍的感觉困扰, 所以她们想做正确的事情的本能便混乱不堪起来。 钢琴课如今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 大家心里都清楚。”[1]后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的思想左右着她们的价值观。 本来是来参加钢琴演奏会, 可“我母亲”却把注意力全放在了一些琐碎的物质上, “稍微弯曲的三明治边角”, “舒畅地爬过小碟子的嗡嗡打转的苍蝇”, “三明治都非常不错, 鸡肉、 芦笋卷, 都是健康的,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育儿食品”[1]。 可见置身于后殖民后现代社会中的“我的母亲”无视艺术之美, 视野和思维极其狭窄, 已然物化。 钢琴演奏不能激起母亲们一丝的热情, “每次不过拍两三下手”[1]。 之后, “她重新换上半梦半醒、 漠不关心的表情, 目光留在蟠趣酒上方的某个地方”[1]。 类似的描述在作品中俯拾皆是。 “我”和母亲们一样, 眼里也只是一些物质的东西, “有超过半打礼物, 用白色的纸包装, 扎着银色的缎带, 不过不是真正的缎带, 而是撕开的便宜带子”[1]。 包括“我”作为叙述者, 也努力将自己置于局外人的位置, 以讽刺的语气讲述着故事。 对于残疾学生, 言辞也有失尊重, “这个白头发的女孩, 有点笨拙地坐在钢琴前, 脑袋垂了下来”[1]。 “我”做为故事的叙述者, 亲眼目睹以“母亲”为代表的学生们的言行, 同时也是故事的体验者, 亲眼目睹并参与了马萨利斯老师构建音乐共同体的过程。
综上所述, 马萨利斯老师作为共同体塑造者和组织者, 试图以师生关系为纽带、 以钢琴演奏为媒介来构建音乐共同体, 可是在后殖民、 后现代语境下, 这个共同体缺失情感纽带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无法就音乐的价值和内涵展开对话或交流, 彼此都没有归属感。 相反, 马萨利斯老师始终是一位孤独、 无助、 焦虑的局外人, 被排挤在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学生”之外。 面对异化的学生, 马萨利斯老师幻化成了自己的影子, 而这正是她缺乏自我身份的体现。 另一方面, 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学生”, 陶醉于“分裂”和“异化”, 深处身份危机的困境却无动于衷, 如同影子一般出席聚会, 游离于认同、 共识、 合作和融合等共同体关系之外。 总之, 师生之间趣味不投, 无法达成理解、 共识和共约, 形成一种永恒的错位, 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同时, 钢琴演奏得不到学生认可, 与学生之间呈现出不可缝合的裂缝。 这个音乐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丝毫凝聚力的“伪共同体”。 马萨利斯老师终其一生构建音乐共同体的“严肃诉求”沦为一种小丑式的独角戏, 而她则沦为自己曾经梦想的苍白影子(shades), 其作为音乐教师却不被学生认同的身份危机几乎展延了一生。
最后, 学生们驱车离去, 以此表达了对音乐共同体的逃离和背叛。 “她(马萨利斯小姐)以后再也没可能聚会了, 几乎肯定地说, 永远不会了。”[1]共同体构建最终成为无所作为的徒劳。 在加拿大后殖民后现代语境下, 共同体也许是一种难以抵达的精神彼岸。
3 共同体之想象: 希望在别处
共同体的构建, 需要关注处于其中的每位成员, 尤其不可忽略生活在“漏洞”和“边角”里的人。[15]门罗选择残疾儿童, 这群生活在“漏洞”和“边角”里的人作为最后出场的对象, 恰是印证了殷企平教授的这一观点。 残疾儿童虽然生活在“漏洞”和“边角”里, 但却是共同体构建的希望所在。 在残疾学生出场之前, 马萨利斯老师的居所作为共同体空间, 一直笼罩在死气沉沉的阴霾之中。 当残疾女孩德洛丽丝·波义耳演奏完《快乐影子之舞》后, 情况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机:“音乐毫不费力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几乎不需要注意力, 我们也并不觉得意外。 她弹的曲子并不是耳熟能详的, 而是虚幻的、 典雅的, 欢乐的什么, 传达着一种自由, 充溢着不动声色的喜悦感。 而这个女孩所做的唯一的事儿, 却是你从来没想到能这么做的事儿, 她只是弹曲子, 于是这一切便能被感觉, 所有的一切都能被感觉到, 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荒谬的下午, 在马萨利斯老师位于巴拉街的房子的起居室里, 你也能感觉到。”[1]“音乐穿过敞开的门, 敞开的窗外, 飘到了灰蒙蒙的夏日马路上。”[1]与聚会沉闷的基调、 “灰蒙蒙”的马路形成鲜明对比, 此时的音乐呈现出浪漫灵动的色彩, 显现出向外散播的态势。 残疾学生的表演为师生之间的深度交流提供了最后的契机。 然而, “母亲们的脸上分明写的是反对, 比刚才更多了一层莫名的焦虑”[1], “我”则认为, “演奏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伎俩, 但也许——怎么能直接说出来呢?也许, 总而言之, 不得体”[1]。 “对于马萨利斯老师来说, 残疾儿童的表演是合意的, 但对于其他人, 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 这个学生的表演仍得不到认同”[1], 音乐的效力再度淹没于后现代人的漠视和拒斥之中。 残疾儿童在这些学生的漠视中, 也幻化成了毫无意义的影子。
“是《快乐影子之舞》阻止了我们; 快乐影子之舞, 是他的生活向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公告。”[1]这里的描述显然是一种冥思式的共同体想象, 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指出, “另一个世界”, 脱离后殖民、 后现代语境的“另一个世界”, 才是寻求身份认同、 寻求归属感、 构建共同体可依托的社会或艺术空间。 罗伊斯与杜威指出, 想象来源于有机体对环境的回应, 反过来又促使有机体更好地回应环境。[16]这种冥思式的想象实质上根植于后殖民、 后现代的历史之根、 文化之源, 是对后殖民、 后现代的文化语境的回应。 在后殖民、 后现代的阴性语境中, 共同体构建的愿望落空了。 但是, 这个“公告”诗意地昭示读者: 音乐是亘古不朽的; 只要音乐在, 共同体一定可以得到建构。 门罗以隐喻的手法传达出对弘扬人类音乐文化的诉求, 和对形塑深度共同体的憧憬和想象。
4 结 语
《快乐影子之舞》, 描述了如影子般存在的马萨利斯老师与她的学生的“阴性”之舞, 蕴含着音乐共同体构建无望的悲伤, 是加拿大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处于困境的一个隐喻。 在加拿大后殖民、 后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处于“阴性”状态的马萨利斯老师的学生处于一种异化、 物化、 茫然若失的自我流放状态, 加之马萨利斯老师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建构着共同体, 导致师生之间没有情感基础, 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无法就音乐的价值和内涵等展开对话或交流, 彼此缺乏归属感, 从而相背相离相错位。 本质上, 马萨利斯老师试图构建的音乐共同体是一个无机的多重体, 一个“伪共同体”。 最后出场的身有残疾的学生的表演, 在一瞬间曾为共同体构建带来了一丝希望, 但仍得不到学生们的认可, 希望也许在别处, 这体现了门罗对深度音乐共同体的想象与憧憬。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藻海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