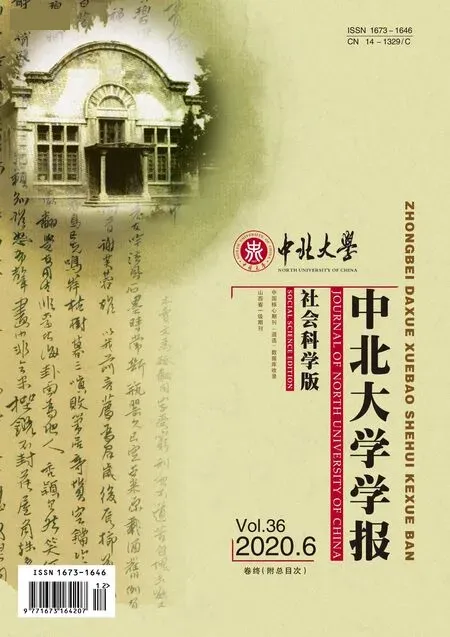抗战史要重视沦陷区研究
——太行山和吕梁山沦陷区研究的学术检讨
岳谦厚
(山西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山西 太原 030006)
太行山和吕梁山(以下简称“两山”)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及中共华北根据地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有关抗战时期“两山”沦陷区文献的收集、 整理与研究, 实际上早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或全国抗战时期业已开始, 1939年毛泽东在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解放社1939年 10月初版)作序时就强调了研究沦陷区的重要性, 而至今数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但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整体情形言之, 则显得十分薄弱; 或者说, 需要学界强力拓展和深入探讨的空间巨大。
1 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回顾
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性环节, 档案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历来受到史家所重视。 然而, 与大量出版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料乃至国民政府抗战史料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沦陷区”日伪资料相对十分“匮乏”。 尽管近些年来有一批以“沦陷区” “日伪”为主题的史料相继整理出版, 但大多集中于“伪满洲国”或汪伪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 华北等地相关史料则甚显薄弱且又多涉及于军事、 政治、 经济等方面。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李云汉主编的《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版)、 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和中共党史教研室合编的《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北京市档案馆编的《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邯郸市档案局(馆)编的《邯郸市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唐山市档案馆合编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的《华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5年版)和《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以及《华北“大扫荡”》( 中华书局1998年版)、 季啸风和沈友益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63-6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居之芬和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中央档案馆等编的《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2004年版)、 (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公报处编的《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等。
除以上专题性史料集之外, 有关华北“沦陷区”的史料还散见于一些史料类丛书中。 如彭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北京市档案馆和河北省档案馆合编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章伯锋和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龙向洋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影印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此外, 《民国档案》等期刊及日本、 中国台湾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及史料集中亦有部分涉及华北日伪政权各方面的资料。
史料的整理、 出版与研究的发展是相互因应的, 从20世纪90年代起, 曾业英、 居之芬、 (日)内田知行、 王士花、 岳谦厚等人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 以定量研究为主线,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经济政策与具体实践,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简单定性研究的局限, 同时发掘、 整理了一批史料。 在日伪政权组织构成上, 以张同乐、 郭贵儒、 刘敬忠等人为代表的燕赵学者出版了一批相关著作, 亦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相关史料的不足。
2 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检讨
“两山”周边“沦陷区”日伪政权史料收集、 整理与研究工作尽管取得了不小成绩, 但总体上仍有不少缺憾。
第一, 史料收集、 整理的广度与深度难以支撑全面性研究。 在先前出版的史料中大多集中于“两山”周边日伪统治时期的军事、 政治、 经济方面, 其他诸如社会结构、 生活日常、 文化教育、 身心体验等方面涉及不多或几乎无任何涉略, 这与历史研究要尽可能将史料“涸泽而渔”的方法或精神存在很大距离。
第二, 史料收集、 整理过于零散难以形成系统性观照。 资料辑录与历史研究一样, 需要有同样的历史态度, 即尽可能体谅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现实状况。 不仅如此, 史料之间本身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某种程度上讲, 史料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与命脉, 同时亦是一种方法与角度, 忽视任何史料均不可能客观真实地认识历史或还原历史。 “两山”沦陷区涵盖了日本占领时期整个华北, 日伪在各方面都有着较为完整而统一的政策与实践运作体系, 所以资料收集、 整理应不分地域不分内容地尽可能将之全部“归入囊中”(穷尽所有史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则是学者应取之态度)。
第三, 史料收集、 整理方面的诸多“缺憾”导致相关研究论证不足。 日伪史料的欠缺使得史事的论证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故在大多数相关研究成果中都会出现“中方资料解释‘日伪’史事”的现象, 进而导致只注重定性研究而忽视定量研究, 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沦陷区研究模式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全面推进和深度发展。
针对以上情况, 学界有必要尽快地构建完整的“沦陷区”日伪史料库。
第一, 要尽可能发掘各地日伪档案。 其实, 在各省市县(区)档案馆及图书馆存有大量日伪档案, 这批资料大部分未被辑录, 更遑论具体运用了。 仅山西省档案馆就存有日伪档案七八千卷; 其中(伪)山西省公署案卷313卷, (伪)山西高等法院案卷5 940卷, (伪)山西省河东道公署、 雁门道公署、 上党道公署案卷67卷, (伪)山西邮政管理局案卷440卷, (伪)山西高等检察署案卷1244卷, (伪)建设总署太原工程局案卷48卷, (伪)华北棉产改进会山西分会案卷49卷, (伪)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案卷9卷。 另外, 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党史馆”及日本防卫省、 外务省亦有大量资料, 大部分是可以通过网上查阅的, 这些资料可以相互补充、 相互印证。
第二, 抗战期间日本人在山东、 河北、 山西、 河南等省铁路沿线就主要城市和农村地区做过不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地调查, 除已出版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日本岩波书店1952-1958年版。 该调查资料整理时以《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为名, 出版时则更名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外, 尚未刊行者甚多, 这些调查所形成的资料现在日本各大图书馆甚或中国相关省份档案馆和图书馆均有收藏。 如在山西铁路沿线, 目前所能见到的实态调查资料就有《岚县地方社会经济状况与共产党工作概况调查报告》 《北支农村的实态——山西省晋泉县黄陵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山西省农村概况调查——以在平遥进行的生产分析为中心》 《潞泽地区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 《满铁北支农村实态调查临汾班报告》等。 充分发掘这批资料, 则可深化全国抗战时期“两山”沦陷区经济社会史的研究, 亦可弥补以往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区域或空间上的不平衡状态(参见岳谦厚、 梁金平: 《也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与华北乡村研究》,《福建论坛》2017年第8期)。
第三, 日本全面侵华期间, 在晋、 冀、 鲁、 豫等地发行了大量的报刊资料, 这亦应纳入收集、 整理的范围。 这部分内容包括日伪政权发布的“政府公报”、 宣扬和美化侵略的期刊及报纸等。 其中, 《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 《山西省公报》 《河北省公报》 《丰润县政公报》 《昌黎县政公报》等分别保存在北京市、 山西省、 河北省档案馆。 另外, 诸如《新民会报》 《华北合作》 《中联银行月刊》 《中和》 《大风》 《古今》 《天地》 《风雨谈》 《子曰》 《朔风》 《逸文》 《学文》 《艺文杂志》 《文史》 《雅言》等期刊散存在国家图书馆及各地档案馆和图书馆, 应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第四, 史料收集、 整理应是多维度多层次的, 有必要重视口述史料及日记、 书信、 回忆录的征集。 相对于档案等文献资料, 口述历史资料及时人日记、 书信、 回忆录更为“鲜活生动”。 由于时代久远, 当事人的故去、 资料的零散等主客观原因, 这部分资料收集起来异常困难, 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抢救”这方面资料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除加速口述史料的辑录外, 要加紧对散存在名人日记、 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相关资料的收集、 整理工作。 此外, 最近根据旧书市、 旧书摊收集并整理出版的董毅的《北平日记》(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颜滨的《1942-1945: 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日)髙仓正三的《苏州日记——揭开日本人的中国记忆(1939~1941)》(日本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版)等为学界提供了新思路新思维——要重视散落于民间的各种史料, 要关照“市井”中普通人的历史记忆。
3 结 语
“学术复兴, 文献先行”, 即文献资料的搜集、 整理在整个学术研究中具有基础性与前提性的作用。 文献资料的发现、 发掘与整理往往能够推动一个新学科走向繁荣发展。 如改革开放以来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山”地区社会历史变迁, 特别是“两山”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就与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与大量整理密切相关。 只有充分占有文献资料, 才能使该领域或该学科研究取得坚实的基础, 而新资料新文献发掘与整理往往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条件(参见岳谦厚: 《从太行山革命文献整理谈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取向》, 《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 《太行山和吕梁山中共抗日根据地文献整理与研究述评》,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8年第4期)。 综前所述, 学界关于全国抗战时期“两山”区域沦陷区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或今后须努力的方向具体叙说如次:
八年全国抗战期间被日军占领的“两山”地区是是日、 伪、 华三种政权交互渗透、 激烈争夺的主要场域, 更是日、 伪、 国、 共四种力量犬牙交错、 彼消此长的展演舞台, 这种复杂的政治生态能够很好地诠释当时的各种关系。
首先, 对日伪政权各个层面的研究是沦陷区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沦陷区”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 三种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具有“独立”的政治、 军事、 经济等形态的组织构成。 因此, 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研究不能因日本的殖民性、 伪政权的傀儡性而忽视其主体性, 只有充分认识到日伪政治、 军事、 经济等因素的客观存在, 才能更好地建构被国内外所认可的解释体系与话语体系。
其次, “两山”地区在日伪统治秩序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 随着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 这些区域不仅从前沿阵地变成日本南侵的战略后方, 而且成为其所谓“日满华合作共荣的基础”。 这样的定位使得日本对该地区的殖民政策有别于东北、 华中等地, 故对“两山”地区日伪统治的定向研究是进行区域间横向比较并最终建构较为完整的“沦陷区”历史研究的基础。
最后, 中国有关日伪或沦陷区研究的薄弱性直接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全面推进。 长期以来, 作为中日全面战争重要一方的日伪被国内学界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轻视, 即使有限的成果亦往往陷入某种程式化研究中——或大量引用中方资料来解读日伪统治, 或跳过基础性的定量研究而只作定性研究。 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有碍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整体发展, 而且“一面之词”或简单的立论非但无法取信于人反而导致了整体可信度的流失, 有时甚至沦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华历史的重要“佐证”。 进一步说, 中国对日伪政权或沦陷区研究的“忽视”不仅反映了当下学界的研究取向, 而且更由于相关史料的“稀缺”, 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