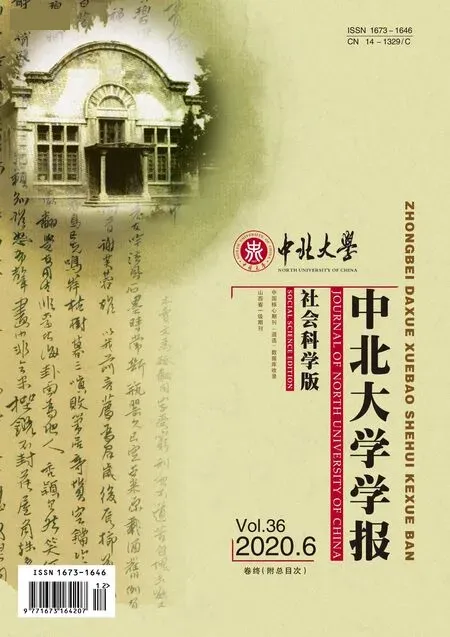论王保忠《甘家洼风景》的叙事策略*
彭栓红
(山西大同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山西知名作家王保忠热爱家乡, 熟悉农村, 其小说乡土气息浓郁。 王保忠的《甘家洼风景》是一部由20个彼此独立, 人物、 事件又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小说。 该小说“为我们多角度地呈现了当代农村城镇化、 工业化过程中过去乃至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之村与人的当代困境: 外出农民工的艰辛和农村留守者的困惑以及农村不可阻遏的空心化与精神变异”[1]。 《甘家洼风景》宏观上有两种风景, 一是故事风景, 二是叙事风景, 二者互为表里。 王保忠大致有三种叙事策略: 一是人与非人视角的任意切换; 二是拉开时空距离, 进行历史与现实、 传说与当代故事的交叉叙事; 三是同一事件在不同小说中的互补叙述。
1 人与“非人”的切换叙事
在人物视角的选择上, 作家注意到小说人物性别、 年龄、 身份、 城乡视角的差异, 尽可能地全面覆盖各类人。 作品中有老村长的孤独留守, 守庙老人老葵的执着正义, 空巢老人富仁娘在除夕夜大火中的亲情期盼, 中年留守女性的出轨恋情, 青年女性的未婚先孕, 小学生的异地求学, 中学生的外出寻梦, 农民工的性苦闷和家的责任, 小凤和磨粉的铤而走险犯法等, 都把城市化对农村的冲击与人性的复杂予以揭示。 另外, 《酒国》补记“王老师”又是作家自己的现身说法。
小说“人的视角”除了大量农村打工者和农村女性的成人视野外, 就是从学生、 儿童的视角观察成人的世界、 乡村乃至城市, 是王保忠小说的一大亮点。 《结婚》以小学生清华“我”的视角来叙述, 看到打工的天成过年回家与月桂亲嘴, 认为父母吃嘴很香有滋味, 担心和麦子亲嘴就会生娃娃; 认为老甘媳妇跟别人跑了, 是因为村长没钱, “男人没钱, 女人就不稀罕他, 就会找个野男人”。 从中我们看到, 农村打工家庭两地分居的情感饥渴和农村性教育的缺乏, 以及城镇化下金钱对婚姻、 家庭的腐蚀。
在乡土中国, 重视家族血缘、 地缘关系的文化中, “人的视角”必然要触及到家族村落。 小说在宏观层面的叙事, 延续了家庭、 家族叙事的文学传统。 从《红楼梦》到《家》《白鹿原》都是以家族的兴衰来折射社会的时代变迁, 《甘家洼风景》同样如此, 只不过不再以大家族的兴衰展开叙事, 而是以乡村平凡家庭的城市梦的追求和家的离散为切入点, 整体上又兼顾中国家族村落文化。 家、 家族、 古树、 山水、 鸡狗、 庙宇, 传统家族村落的标识贯穿小说始终。 这使得小说叙述小家庭、 大家族的裂变与城镇化下农村的解体与重构相一致。 段友文教授研究家族村落时指出:“单姓村, 是同一姓氏的居民共同居住的村落, 心理观念上认为他们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 在这样的村落里, 居民姓氏与村名吻合……同一姓氏的居民在村里占绝对优势, 很少有外姓人, 既或有个别外姓家族也……被村人视为小户, 形不成主体”“这类村庄里家族势力也比较明显, 同一姓氏的村民们往往分属于各个支族。”[2]259而小说展现的甘家洼, 是一个以甘姓为主的单姓村落, 小说人物故事以甘姓家族为主, 以老甘家族和甘天成家族为核心, 涉及的小说各7篇(见下文表格), 其他王铁成、 三铁匠、 二旺、 老葵、 富仁等家庭人物叙事穿插其中。 甘姓家族人物为核心的叙事, 与作品中老甘子承父业当村长巡村和甘家洼村落命名相结合, 透露出传统农村聚族而居, 家族势力影响村落权力构成, 大家族统治村落的现实。 杜赞奇经过调查中国华北农村政体时指出:“宗族势力越强, 其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活跃”[3]70“村长作为保护人的作用十分明显”[3]119, 甘姓家族在甘家洼的绝对地位决定了老甘父子相承担任村长的现实(见《夜活儿》)。 老甘巡村、 开会、 组织唱戏等都出于一种农村权力欲, 担负着农村保护人的角色。 事实上, 老甘父母进城陪读、 妻子的叛逆, 留守妇女的出轨, 村人的外出不归, 都一次次动摇着村长的权力威望, 瓦解着农村道德体制, 老甘甚至提出换村长。 通过村长老甘的权力呈现与村民的应对变化, 从政治层面看到了在城镇化下传统农村正发生质变, 传统农民对“官”的敬畏也在稀释, 原有乡村秩序和伦理规范正在颠覆, 重建乡村伦理和乡村秩序变得尤为迫切。
非人的视角, 主要表现为动物(狗)和鬼魂的视角。 《浮石》中青莲鬼魂的人鬼对话。 《鸳鸯枕》天成鬼魂的自述。 甚至还隐匿一个神的视角, 《香火》在神圣空间的老庙中磨粉被捕, 冥冥之中似有神意。 非人视角的选择, 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观和民间神灵信仰在当代农村仍存在, 改革、 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割断传统文化, 中国农村的城镇化道路必然伴随着现代与传统思维的交织、 冲突的巨大张力, 左右着民众的生活、 言行乃至命运。
非人的视角, 可以出奇制胜地带来喜剧效果, 有时这种喜剧是一种生活的冷幽默, 在可笑之余更增添几分悲戚。 《雪国》中小皮(狗)的视野写老甘的孤独、 唠叨, 他“老气横秋的, 跟着他这么过下去, 我肯定会比他还老几百岁。 ……我为啥要陪着他变老呢”。 红嘴鸦袭击进村观光的人, 老甘为救一个女子, 掐女子的人中穴位。 小皮(狗)的视野中是这样描写的:“老甘呀老甘, 你这是干啥呢?你总不会要吻人家的脸吧?”当女子尖叫并骂老甘流氓时, “我发现她的脸扭曲得厉害, 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丑陋极了”, 还看见大胡子边骂“老流氓”边追打老甘。 通过小皮(狗)的视野, 展现出老甘的孤独、 善良被误解后的无奈, 以及城市人与农村人的隔阂。 在叙事方面, 潜隐的作者、 故事中的老甘、 小皮相互交织, 王保忠接受《文艺报》采访时也指出, 《雪国》中“我”摹拟小皮(狗)的语调看待乡村自然和人文生态被破坏时受到一定的伤害, “我和老甘他们的界线彻底混淆了”, “我既是在‘代言’, 也是在表达我自己”[4]。
以上视角, 互相补充, 融为一体, 随意切换, 作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人、 物、 鬼、 神并存的多元而混沌的叙事世界, 折射了甘家洼人的立体世界和信仰。 全书这种布局构思, 本身又形成了一种乡土文化叙事。 整部小说在纷繁复杂的叙事背后又隐匿着一双眼睛: 老甘的守望以及潜在作者的视角, 村长老甘目睹了甘家洼的巨变, 而出身农村的作者又俯视着老甘及其甘家洼的命运, 由此构成了一个“看/被看”[5]40的模式, 但不同于鲁迅小说批判封建思想、 国民劣根性的启蒙阐释, 而是采取“当局者”与“旁观者”对农村城镇化、 现代化的“在场”审视、 反思模式, 作家有卞之琳《断章》看风景的构思特点。 对于作者的视角, 段崇轩指出, 王保忠小说讲故事的背后, 始终“隐含着一个土地的儿子、 赤诚的知识分子的身影”[6]。 这是中国五四乡土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质, 也是当代商品化、 市场化和当代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惟有责任、 理性、 担当, 乡土才能守住传统之美, 容纳现代之新, 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因此, 我们也就能理解2013年以来王保忠“行走百村”调研, 深化乡土文学的实践, 为何如此执着和坚定。
2 拉开时空距离的交叉叙事
王保忠还拉开时空距离, 进行历史与现实、 传说与当代故事的交叉叙事。 王保忠谈起《甘家洼风景》说:“我只写了它的现在时、 进行时, 但是我们知道, 叙述一个事物既不能与它的周围割裂, 更不能无视它的过去, 我特别想搞清它的过去, 它的来龙去脉, 也就是说我想写一部特别能够完整地呈现一个村庄的东西, 写一个村庄的心灵史。”[7]作家对山西农村、 对“甘家洼”过去、 历史的特殊情结, 使得他叙述“村”与“人”时总会在历史与现实中来回穿梭, 而对“历史”有一种溯源性, 时间上有“五六年前”“从前”等描述。
一方面, 作者对甘家洼的历史与现实交叉叙事, 常用触景生情的回忆手法。 《夜活儿》中老甘巡夜由女人头发联系到老甘老婆的头发, 又想起月桂、 甘大脚等女性, 望见夜空中的眉月, 想到“从前, 村子里的屠户甘四劁猪, 用的就是这种弯弯刀”。 《活着》中老甘回忆五六年前被人拐走的老婆爱唱“八月桂花”的歌, 写小皮(狗)的历史是“你根本就没听过你家女主人唱歌, 我把你抱回家时, 她就走了”。 没有女人的生活中, 小皮是他孤寂时的伴侣。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小皮代替了他老婆, 在喧嚣浮躁的社会, 狗比人忠实。
这类触景生情式叙事甚至不乏梦境、 幻境、 灵魂“穿越”叙事, 如《夜活儿》中老甘睡梦里浮现父亲给他讲述的村里传说、 故事。 《浮石》中现实的月桂与逝去的青莲两个出轨女性的灵魂对话, 讲述不同时期甘家洼女性共同的遭遇和难以抑制的本能情欲。 《鸳鸯枕》中天成之死也是通过鬼魂讲述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展现一个传统老实的男人由于长期的性饥渴本能而导致的肉体放纵, 但其精神上对妻子、 家庭仍有牵挂和坚守。
至于《雪国》《酒国》, 无论是狗的视角勾勒童话般的雪国世界, 还是沉浸在“酒国”老甘的自语, 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背后总是被甘家洼过去的历史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所牵扯, 在这种现实和超现实的混沌叙事中追求一种平衡。
另一方面, 神话、 传说, 某种程度上是更为久远的“历史”, 既有地方性, 又有民族性。 作者借用神话传说引出对当代人、 事的思考。 在当代重视非遗保护、 杰米·拜恩发起的“重述神话”背景下, 文学也再次重新审视“民间”, 赋予神话传说以新的意义。 作者对神圣的神话传说采取世俗化、 生活化的叙事策略, 这种策略与甘家洼世俗人生融为一体, 而无刻意雕饰之感, 激发了读者阅读之兴致。 如《夜活儿》:“天上有一弯女人的眉毛。 老甘抬头看了看, 觉得自己就坐在那弯眉毛下。 小皮也抬头看了看, 它知道那其实不是眉毛, 是月宫, 是天上一个冷冷清清的宫殿。 村子里有个叫嫦娥的女人跟男人拌了嘴, 觉得这穷日子过得也没甚意思, 就跟她养的鸡借了双翅膀飞到了上面。”小说对众所周知的嫦娥故事的演义, 虽无大的出入, 但升天原因、 故事细节(借鸡翅膀升天)发生了喜剧性变化。 此外, 在讲述任昉《述异记》中王质烂柯的故事时, 原本是下围棋, 王保忠笔下却成了当代农村常见的下象棋。 “小说在神话与现实之间有了一种平衡, 在传说的基础上, 加重了现实的成分, 蕴涵了各种复杂的理解和可能的隐喻。”[8]这种变化更贴近当下百姓的世俗生活。
王保忠叙述的神话传说故事, 并不是停留在久远的过去, 而是旨在引出当代故事, 思考当代的甘家洼的人与事。 这似乎继承了鲁迅、 郭沫若等现代作家借助神话传说以“社会学的新视角”[9]来思考现实问题的文学传统。 《夜活儿》用嫦娥故事引出文本故事的时间, 由夜梦遇仙乃至艳遇, 再引到老甘现实生活中的“夜活儿”。 对于甘家洼地方知识中的银狐“撞到谁身上, 谁家的日子可能就要翻身”交好运的地方传说, 作家不无忧郁地叙述“可是, 他会撞上啥好运呢?他这样的人也会撞上好运吗”, 对老甘当下的生活窘况进行了调侃。
如果说寻根文学中神话传说的叙述是一个隐喻, 是一种深植于民族灵魂深处的集体无意识, 无论《爸爸爸》还是《小鲍庄》, 神话传说都是一种象征, 神秘而神圣, 有一个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魅力。 《甘家洼风景》中神话传说的叙述, 没有“寻根”的神圣和对传统的反思, 而有的是当代文艺“重述神话”的图解戏说成分, 对现实世俗的折射和生存思考; 有时又是为了彰显一种地方知识、 文化权力, 是地域作家的身份标识, 是地域文学叙事的传统策略。 这一现象, 恰是作家顺应当代小说世俗化、 地域化发展趋势的一种尝试。
整部小说将甘家洼过去历史的辉煌、 热闹与今朝的萧瑟、 荒凉景象的片段呈现, 连缀在一起, 构成了整体的甘家洼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叙事。 神话传说的介入, 物我一体的叙事, 艺术的“甘家洼”和现实村落原型的“黄家洼”(《结婚》)同现, 作家王保忠和主人公“王老师”并出, 造成一种混沌的叙事效果。
3 互补叙事的迷宫效应
王保忠较为频繁地运用限知视角、 补叙、 插叙, 同一事件在不同小说中以不同的视角互补叙述, 详见表 1。

表 1 《甘家洼风景》叙事视角
王保忠的小说《甘家洼风景》对同一事件在不同短篇小说中互补叙述, 不同于老舍《茶馆》让每个人物述说自己的事情, 更接近于丰村《美丽》中同一事件在不同身份的人物口中以不同方式各有侧重地讲述, 从而共同还原事情经过。 但王保忠又与丰村不同, 不局限于一篇小说, 而是通过多篇小说、 多个人物来讲述、 还原同一个人物故事, 是片段式、 碎片化的叙事, 本质上是一种记忆的唤醒过程。 J·希利斯·米勒在《解读叙事》中指出:“叙述就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一串真实时间或者虚构出来的事件。”[10]44
关于文学与记忆的关系, 21世纪初诸如马原、 余华、 余秋雨、 王富仁、 张隆溪、 朱大可、 洪志纲等作家、 学者不断探讨。 2009年底暨南大学国家211重点工程“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举办了“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11], 国内著名作家、 学者、 编辑云集, 反响强烈, 至今不绝, 更有陈全黎提出“文学记忆史的建构”[12]。 《甘家洼风景》在此大背景下创作并于2011年底出版, 最早的《活物》发表于2009年。 王保忠尽管说创作“很少受潮流左右, 多是有触动才写……不大注意这些讨论”(1)笔者与作家于2016年4月2日下午微信上的一次对话。, 但事实是不管作者有意还是无意, 《甘家洼风景》一定程度上恰恰为“文学与记忆”的关系讨论做了一次创作实践回应。 王保忠接受《文艺报》访谈时说:“我小说里的‘甘家洼’, 其实有一个真实的地理模拟。”[4]小说中瘸腿的村长、 奔跑的黑狗、 火山、 浮石墙、 老窑洞、 老柳树、 狼窝山、 金山、 黑山、 水库……都是如此的真实。 小说是作者对艺术的甘家洼历史的回顾, 更是对真实农村, 尤其是大同市云州区巨乐乡黄家洼的记忆。 小说叙事的散乱, 其实是作者对农村的记忆以碎片化的方式被唤醒的过程。 读者阅读就成了对现实农村记忆和小说故事片段记忆条理化的过程。 作者写作就是“重现记忆和再造记忆”[13], 在记忆中显现意义, 表达思想。 小说主人公讲述事件也常采用回忆的方式。 记忆心理学认为, 场合、 环境影响记忆。[14]473-527人物塑造上, 老甘在孤寂环境下往往勾起对老婆、 父母乃至甘家洼过去的记忆, 在看到女性时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老婆, 此时小说叙述就会采用插叙、 补叙。
《夜活儿》《浮石》等小说讲述月桂的故事就是一种互补叙事。 《夜活儿》中老甘巡夜担心月桂出轨, 《浮石》中月桂反复提到天霞跟着丈夫进城打工, 月桂寂寞想随丈夫甘天成到城里, 丈夫不同意, 与青莲的对话折射出月桂内心的骚动和受人引诱被动出轨的经历。 《向日葵》讲述天霞夫妇提到嫂子月桂, 说“你想回去, 你嫂子可是想跟着你哥出来呢”。 《老瓜棚》有月桂自传式叙述出轨经历。 《回家》以天成的视角写对妻子月桂出轨的隐忧。 《鸳鸯枕》则是天成(鬼魂)视野下的妻子月桂出轨描述。 《结婚》以天成的儿子清华的视角看到打工刚回家的天成与月桂亲嘴的一幕。 《夜活儿》《浮石》《向日葵》《老瓜棚》《结婚》《回家》等小说都讲述了月桂的故事, 涉及既有天成夫妻及儿子、 天成的妹妹天霞夫妇的家庭内视野, 也有村长及其村民等他者的外视野; 既有人的视角, 也有鬼魂的视角。 作者往往采用限知视角, 让故事中不同人物讲述、 评价同一事件, 根据人物的身份讲述和反映同一事件的心理和知情权也不同。 通过重新梳理小说中所有这些有关月桂的叙述片段, 我们看到一个本是传统保守的中年妇女在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孤寂无助、 性与爱的缺失和另类的城市生活向往; 抛却道德的责问, 从人性、 人的本能的角度, 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并理解农村打工家庭的两地生活, 使得夫妻双方在现实家庭内外都将承受巨大的生活艰辛和情感孤寂的双重煎熬。
这种互补叙事, 不仅影响故事情节, 而且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影响较大。 不像一般小说对人物相貌言行的集中叙述, 王保忠小说要求读者必须整体阅读小说, 把散乱的细节、 线索串起来才能勾勒出人物轮廓。 如老甘女人形象在《活物》《夜活儿》《雪国》《酒国》中通过老甘、 小皮等不同视角的侧面描写, 大致还原了她过去生活的样子: 南方人, 曾当过四川女服务员, 因美貌遭流氓调戏, 老甘英雄救美相识; 梳着两根大辫子, 爱唱歌, 爱打扮, 细皮嫩肉, 瓜子脸, 柳叶眉, 大眼睛, 皮肤白皙, 腰细胸大。 这类描写侧重老甘老婆的美丽, 突出其女性特征。 在《弹力裤》中作者又让老甘老婆现身, 从正面描写一个由于打工而城市化了的女性: 干净整洁, 身穿白羽绒衣、 弹力裤, 脚蹬皮靴, 客气礼貌, 温柔羞涩, 朴素能干, 喝酒爽快, 有主见, 敢反抗, 是一个独立的、 具有社会经验、 城市化思想的女人。 波伏娃在《第二性》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5]309, 处境改变女性。 小说以城乡对比、 正侧面描写兼顾的手法, 塑造了一个老甘记忆中的昔日乡村老婆和现实中城市化了的女人形象。 这样的叙事安排和人物前后对比, 折射出城市文化可以改变传统农村女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 也揭示出女性的成长、 妇女解放首先来自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城市经济、 文化客观上又加快培育女性独立和思想解放的意识。
《甘家洼风景》中同一事件在不同短篇小说中的互补叙述, 表面上似乎给读者一种重复拖沓之感, 但实际上, 不同视角的互补叙事不是简单重复, 而是由浅入深、 层层推进的结果。 从记忆心理学角度理解, 这是短时记忆转变为长时记忆, 强化事件给人物造成的影响。 陆建德谈到记忆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记忆的过程也是我们怎样对记忆进行解释的过程。”[16]小说叙述老甘的老婆出走这件事, 《活物》侧重进村开沙厂的城里坏男人把他老婆拐走了, 老甘不明白为何老婆出走, 还相信她会回家。 《夜活儿》中老甘认为骑着摩托车做生意的河南人卖东西吆喝, 把女人们的心喊乱了,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老婆走的原因是“家里没钱”。 《雪国》补充老甘没钱给女人买白金手链, 又借助小皮(狗)的视野解释老甘老婆被拐走的原因:“女人要是动了跑的念头, 甭说一串手链了, 就是十八根绳子也拴不住她。”对于老甘老婆的离去原因更触及到思想层面。 《酒国》中老甘自述酒后骂走老婆, 《弹力裤》中老甘固执地坚守乡村, 遵循传统的家庭观念、 家长专制作风, 大男子主义, 对妻子的不理解和粗鲁, 这才是女人离开的直接原因。 在事物的矛盾发展中, 内因具有决定性作用。 乡村的贫穷、 城市人的诱惑, 这都是外因, 而老甘和妻子自身对城市的看法以及人生观、 价值观的差异才是他们分离的主因。 可见, 《活物》《夜活儿》《雪国》《酒国》《弹力裤》对于老甘的老婆出走原因的叙事, 由表及里, 由外因到内因, 由物质到精神, 层层推进解析, 揭示出事件是突然的, 但转变是渐进、 缓慢的。 农村妇女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和思想转变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而甘家洼的贫穷、 城市的诱惑、 拜金享乐思想对农村人思想产生冲击并改变着他们的观念和生活。 以上这几篇小说先后顺序的排列和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正好契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主人公老甘对此事的认识, 也有一个由无知到逐渐有所感悟、 觉醒的过程, 但这种感悟有几分被动和痛苦。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 外部世界、 城市化、 现代化影响着甘家洼的人们, 而外出或固守甘家洼人的每一次转变又从甘家洼内部进一步催化影响着甘家洼人的思想, 尽管这种影响、 转变伴着痛苦、 迷惑和不理解, 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是时代社会发展之使然。
整部小说中老甘的记忆与作家对农村的记忆相互交织, 又共同传递出作家对人、 事、 时代的阐释, 既有作家对甘家洼原型“黄家洼”的真实个人记忆, 也有对中国农村城镇化现实的时代集体记忆。 作家叙述乡村记忆的同时, 又融入时代记忆, 透过艺术的甘家洼乡村, 折射出整个中国农村时代和历史的变迁。 小说既有真实的人物、 地理标识, 也有艺术的虚构, 但大多都能找到乡村原型。 王保忠用自己的创作, 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回应了当代重大的“文学与记忆”之思考。 《甘家洼风景》运用“互补”叙事, “小说间、 故事间、 人物间若有若无联系的审美补白, 和讲述故事的欲言又止造成的阅读饥渴”[17], 也是其小说叙事一大魅力。 这种叙事的探索性, 某种程度是对传统小说叙事方法的一种变形, 也是对民族传统的一种续接。 重述神话、 当代农村三留守、 小沈阳、 李刚、 租女友、 火山旅游等, 这些视角和素材的选取, 无论是文学层面, 还是生活层面, 都与时代同步, 极具当代性, 创作甚至有“新闻”的及时性。 王保忠小说的互补叙事, 使得小说甘家洼故事前后呼应, 有一种“互文”的效果, 能产生回顾性的整体阅读美感。
甘家洼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历史发展中的一道风景, 是城市人眼中的风景, 更是甘家洼人自己营造的风景。 《甘家洼风景》叙事表面的散乱, 恰如甘家洼人心的浮躁, 思想的激荡, 恰如甘家洼人在城镇化、 现代化过程选择的艰难, 挣扎的苦痛无助。 王保忠《甘家洼风景》多样化的叙事探索与甘家洼农村的发展变化, 共同构成一道形式、 内容相表里的别样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