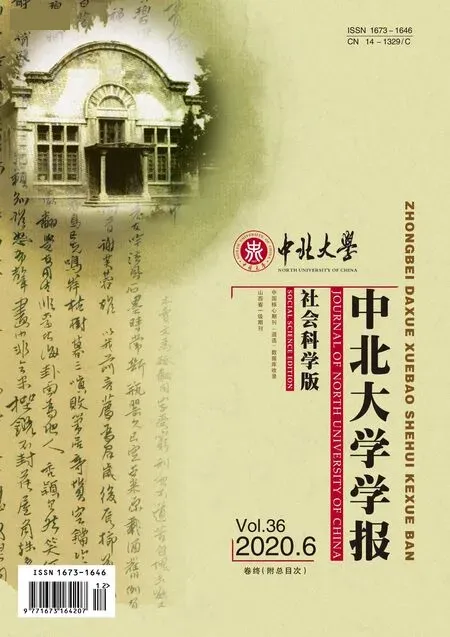女性导演爱情类型片中的女性形象重构*
李兰英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艺术与传媒学院, 上海 200083)
爱情类型片(romantic film), 就是以爱情为主题, 通过对爱情的艺术表达来吸引观众, 围绕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和爱情的阻碍之间产生的冲突为叙事的主要动力, 通过表达爱情的绝对超越性来探讨爱情的艺术主题。[1]75在当代的爱情类型片里, 爱情是可以超越一切的, 爱情很少承载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因素。 相比其他类型的当代电影而言, 爱情类型片更倾向于商业电影的创作模式, 突出个性化的故事内容。 影片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真挚的情感是故事叙述的主要内容。 在爱情类型片中, 什么都可以被束缚, 唯有爱情是自由的、 纯粹的。 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 来自生活的压力使得人类的情感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化, 人们真实的情感难以琢磨, 这就促成了观众对爱情类型片中纯粹爱情的追求与渴望。 早在20世纪30时代, 好莱坞爱情类型片模式已经确定, 爱情类型片无疑是最持久的电影类型之一。 在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发展进程中, 爱情类型片创造了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 这些经典的爱情类型片对全球的电影观众都保持着吸引力, 如: 《罗密欧与茱莉亚》《泰塔尼克号》《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
进入新世纪,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 国内爱情电影获得了巨大动力, 影片的整体质量和票房也都在稳步上升。 在目前中国商业电影市场中, 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有力, 优势显而易见: 由女性为主导的年轻观众群逐渐稳固, 以女性导演女性的独特视角将社会现实问题融入爱情类型片之中, 这使得影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据笔者初步的统计, 从2010年至2018年, 在她们拍摄的爱情类型电影中有6部作品, 如徐静蕾《亲密爱人》、 邹佡《一生一世》、 赵佳蓉《剩者为王》、 李晓雨《北京·纽约》、 刘雨霖《一句顶一万句》、 张歆艺《泡芙小姐》获得了千万元以上的票房, 其中《亲密敌人》和《一生一世》取得了亿元以上的票房纪录。 在这些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中, 虽然大多数的影片对于现实的感情问题很难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在影片中, 她们更加注重女性在爱情故事里的主体地位, 试图改变传统的爱情与婚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形象, 建立起更接地气、 本土化、 贴近现实生活的女性人物, 使观众能从人物身上观照自身, 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1 摆脱“他者”视阈
在新世纪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中, 女性成为电影的主体, 女性角色也不再只是作为被看的对象, 也不是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到的“他者”。 “她是附属的人, 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 他是主体(the Subject), 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2]作者序4-5而作为“他者”的“他者意识是一种依附意识”[2]60, 女性的他者意识是表现在依附于男性的。 但是在新世纪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中, 我们看到的却是女性爱情的独立宣言。
在这些电影中, 如《西藏往事》《亲密敌人》《一生一世》《剩者为王》等突出了女性在爱情上的独立与自主意识。 《西藏往事》里的雍措作为单身母亲毫无怨言地默默承担来自周围的舆论压力, 在与美国飞行员相爱之后依旧能保持爱情的独立与自主, 既不依附于对方亦不成为对方的羁绊; 《亲密敌人》的艾米在面对相恋七年的男友不能给自己足够的情感需求时毅然决定分手; 《剩者为王》中的盛如曦虽然是大龄剩女, 但是她却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大龄剩女而将就自己的感情生活, 依旧追求有爱情基础的感情生活; 《一生一世》中的安然与赵永远在一次误解后, 安然伤心地离开北京去了美国, 即便怀孕也依旧独立地在美国艰难地生活着, 她也保持着爱情的独立与自主。 这些电影中的女性将爱情视为自己个人的事情, 保持着独立性与自主性。 这一举动打破了以往男性为主体、 女性为他者的关系, 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认识。
在传统观念里, “父母培养女儿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结婚”[2]129, 认为女人的爱情是“通过承受她注定的依附性来克服它的最高企图; 即使依附性被接受了, 也只能在恐惧和奴性中存在”[3]528。 在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中, 我们看到了女性与男性的爱情不再是依附关系, 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是独立自主的, 女性从“男性视角”中的“他者”身份走出来, 成为“女性视角”中的主体, 与男性平等地存在, 而不再是依附关系。
2 人格的解放
鲁迅说:“妇女的解放, 在于人格的独立与经济的独立。 舍此, 女性说不上真正的解放。”[4]68作为当代的女性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多方面地融合, 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中, 女性主人公并没有完全沉浸在两性的情感纠葛中, 女性也拥有自强自立的事业心, 女性导演在爱情类型片中都会塑造有一定事业基础的女性, 或是在经济上能保持独立的女性。
在徐静蕾的《亲密敌人》(2011年)中, 女主人公艾米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在职场上和前男友一决高下, 用专业技能为难对方, 使得男方不得小觑; 马俪文《巨额交易》(2011)中周允离开公司之后开始经营一家礼品小店; 邹佡《一生一世》(2014年)中的安然出国留学没有拿走赵永远给她准备的钱, 而是自己在美国一边兼职一边读书; 落落《剩者为王》(2015年)的盛如曦及她的两个好友也都在职场拼搏已久, 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李晓雨《北京·纽约》(2015年)的茉莉为了梦想到了美国纽约, 为了自食其力同时做了几份工作来养活自己。 这些女性不仅具备一定的知识与文化素养, 还具有一定的事业基础, 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她们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男性而生活, 不再成为传统爱情中的“他者”。
西蒙娜·波伏瓦认为:“知识女性知道她是一个意识、 一个主体。”[3]548在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中, 即使女性总是强烈地表现出对婚姻、 爱情的向往与依赖, 但这些女性由于拥有自强自立的事业心, 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 于是她们在两性关系中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 凯特·米利特认为, 父权制统治最有效的方式是在经济上对女性进行控制。[5]因此, 女性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 就要有一定的事业基础, 做到经济独立, 这样的女性才能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意识。
3 “身体即战场”
西克苏认为, 妇女被迫与自己的身体分离, 被要求忽视身体的存在, 付之以性的谦和与节制。[5]在父权制社会中, 女性的欲望受到一定的压制与束缚, 她们被要求能控制住自己的性欲。 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妇女不应该压抑她们的天性。 她完全有权利为自己是女人而骄傲。 正如男人也同样可以为他的性别骄傲一样。 毕竟, 他有权利为之骄傲, 前提是他不剥夺别人也有同样为之骄傲的权利。 每个人都可以为他/她的身体而快乐。”[6]279由此看来, 女性身体是女性解放的关键。
在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中, 女性导演们毫不回避女性自身的欲望, 大胆地在影片中表现出女性欲望, 以此来彰显女性的主体意识。 徐静蕾《亲密敌人》、 马俪文《巨额交易》、 邹佡《一生一世》、 李晓雨《北京·纽约》等爱情类型片中, 女性导演们大胆地在影片中展示了女性的身体以及身体欲望, 如《亲密敌人》中的艾米可以身裹浴巾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巨额交易》中王云鹏的妻子用生孩子来要挟王云鹏多赚钱, 周允利用自己以前的情人来帮助丈夫实现赚大钱的梦想; 《一生一世》里的安然在赵永远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体欲望; 《北京·纽约》的茉莉也毫不回避自己的身体欲望, 她能在下大雨的夜晚出现在曾有一面之缘的外国男性家中, 她的感情一直在两个男性之间游移不定, 把控着她在爱情中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在爱情中不再掩饰自己的身体, 也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
芭芭拉·克鲁格宣称, 女性的身体就是战场。[7]96“身体, 包括性对身体的表现, ‘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政治竞技场之一’。”[7]96女性导演正是利用电影中对女性身体的掌控来呈现女性的主体意识。 苏姗·莱西说:“身体不光是一个场所, 还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根植于身体, 因此诸如暴力、 生育、 性和美学等问题成为常见题材。”[8]96身体变成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关键所在。 这些女性导演正是从女性的视角通过爱情类型片电影, 用影片中女性的身体符号去释义当代女性的主体意识。
4 新世纪以来女性导演主体意识的呈现
在这些女性导演的爱情类型片中, 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 而是与男性平等甚至能摆脱男性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 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 福柯曾指出: 司法权力体系产生主体, 然后又再现这些主体。[9]2“主体”是通过话语在话语实践中构建的, “话语”则通过不同方式塑造、 主宰个人, 使个人成为可以体现“话语”的“主体”[10]61。 这些爱情类型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世纪女性导演在电影女性形象角色塑造方面的重构, 它集中通过反映在摆脱“他者”视阈、 人格的“解放”、 “身体即战场”三个方面, 来呈现新世纪以来女性导演的主体意识。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妇女再现为女性主义‘主体’的语言与政治之间司法建构, 它本身就是话语建构的, 是某种特定形式的再现政治的结果。”[9]3女性成为一种话语的建构体系, 体现了一种主体性。
按照朱迪斯·巴特勒对女性主义主体的分析, 我们可以理解女性导演通过爱情类型片中女性形象的重构去构建自己的影片, 也是一种话语体系的建构, 亦或是一种女性意识的体现, 是女性作为主体的一种意识的呈现。 同时, 这一时期的女性导演以自身作为女性的视角拍摄的关于女性题材的影片, 也是女性电影的呈现。 “‘女性电影’的话语就可以被看作是权力运作的一种话语, 它在父权文化中产生, 并调节女性主体性。”[11]96李少红导演也曾说道: 女性导演会把影片中的女人当作一个“我”来塑造, 而男性导演则会把影片中的女人当做一个“她”来处理。[12]1李少红导演提到的“我”即体现了电影中女性导演的主体意识的呈现。 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导演在爱情类型片中逐渐淡化男性的权威性, 更多地彰显女性的主体地位, 用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思维去参悟当下的爱情。 这也符合琼·斯可特在《经验的见证》提到的:“主体性是通过情境及被赋予的地位创造出来的。”[13]20新世纪以来, 这些女性导演的主体意识正是通过电影情境的塑造以及电影中人物形象的重构, 呈现出这些女性导演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