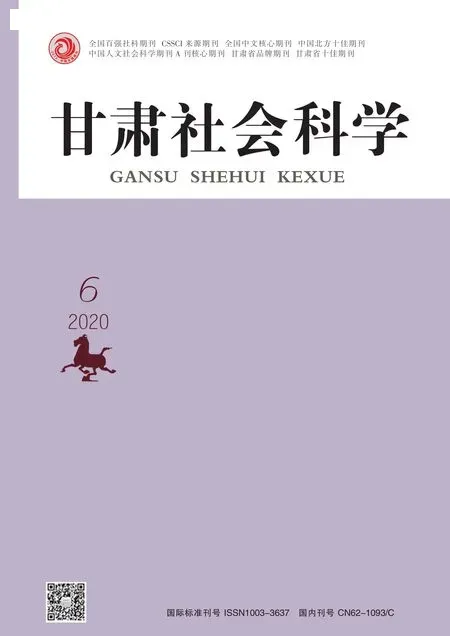法治概念的历史性诠释与整体性建构
——兼评“分离的法治概念”
周永坤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提要: 法治是文明社会的首要政治法律原则,法治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宪制性、整体性概念。因此,法治这一重要概念需要从三重历史视角来作整体性诠释与建构。在法治语义史上,法治的初始含义是法律的普遍效力与法的“德性”的统一;在法治实践史上,法治或表现为宪法统帅下的体现公共利益的法律的统治,或表现为权利法主治,或正义法主治;在法治原则发展史上,法治表现为一系列形式性原则与实质性原则的统一体。法治的这一概念史昭示人们,法治的形式要素具有手段意义,实质要素具有目的意义,两者不可分离。没有形式要素,实质要素便无以表达,无法运作;实质要素又是基础性要素,“形式”是“实质”的形式化,没有实质要素,形式就是无源之水,就失去意义,特权加暴力的形式化与法治无缘。法治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两者都从对方获得正当性证明,并从对方获取其意义,“法性/法德”正是法治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的交汇点。摒弃形式与实质“分离的法治概念”,确立整体性法治概念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rule of law)”作为理想政体的最高原则两千多年后,法治逐渐成为文明世界共同的最高政治法律原则。中国在清末宪政运动中接纳了这一文明世界的共识,迈上了古老文明历史性转型之旅。然而不幸的是,刚刚起步就对这一伟大历史运动的核心概念法治产生了“本土性误读”——望文生义地以申韩来解读rule of law。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执政者力图在治国原则上拨乱反正,积20年之功,法治终于1999年入宪,成为一个重要的宪法概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宪法概念却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形成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分离的法治概念”逐渐获得了广泛共识,接着,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双方又展开了论争。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之间除了在基本概念上(何谓形式法治、何谓实质法治)存在争论以外,其学术主张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坚持形式法治,坚持实质法治,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弱化的实质法治(法理型法治)。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上述诸论对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的基本分类却存在相当高的共识。以致法治入宪20多年后的今天,“分离的法治概念”仍然支配着治理理论研究与法治实践。鉴于法治概念不清所引发的法治思想的混乱及对法治实践的严重干扰,有必要对法治概念作一个历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性建构,廓清这个宪法核心概念,以利法治国家建设。
一、思辨中的法治
法治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法治概念的基础性概念是“法”,因此“法治之法”的概念是理解法治概念的钥匙。这里有一个知识性前提即区分两个“法概念”:通常意义上的“法概念”和“法治之法的概念”——法治论者在谈论法治这一概念时所秉持的法概念。让我们从法治的源头古希腊说起。
(一)古希腊法治与良法
与诸多承载政治文明的重要概念一样,法治的概念同样起源于古希腊。毕达库斯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法治”这一语词并与人治对称的思想家之一,他明确说“人治不如法治”①。大立法家梭伦也推崇法治,他的法治是与正义相关联的②,但是大体上,前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人对于什么是法治却未见明确的阐述。希腊早期的法治似乎只是指法律制度的存在,与它相对称的是丛林状态,这从史学巨制《修昔底德》卷一之章五章六中提及雅典的“法治”时的语境可以推知③。

如果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放到当年论辩的语境下来观察,则其语义就更加清晰。亚里士多德是在讨论“什么是好的城邦政体”问题时提出法治这一概念的。他将政体分为两大类:正宗的和变态的。“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1]132而他的“法治”是指一种正宗的政体。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政体”一语与宪法是同义的,政体(宪法)的好坏决定了法律的好坏,他说,“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这里,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宪法)制定的;既然如此,那么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而符合变态或乖戾的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了。”[1]148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的良法是宪政体制下合宪的法律。如果我们再把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特殊的混合政体理论结合起来观察[1]310,那么,就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本质上是在寻求一个保障法律处于至尊地位的分权的优良政体⑤。
(二)英美法治与权利法
英国宪法学家A.V.戴西在其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中使用了rule of law一语,现在通译为法治⑥,内中对英国法治的精髓有精当的叙述。戴西认为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格兰的政治制度呈露两件异彩”,两者之一便是“法律的至尊性,或称法律主治”,英格兰“有独与其他国家立异的一点:就是法律主治”[3]229。在这部享誉世界的著作中,他用了整整240页来阐述rule of law,可见在这位宪法学大师的心目中法治的分量。他指出法治包含三个“分明而又联立的”“意指”:第一,武断权力的不存在。指凡人民不能无故受罚,或被法律处分,以致身体或货财受累。有一于此,除非普通法院曾依普通法律手续,讯明此人实已破坏法律不可。用在如此指意时,法律主治与下文所陈一个政制刚相反。这个相反的政制是;在政府中有一人或数人能运用极武断、又极强夺的制限权力[3]232。第二,普通法律与普通法院居优势。即法律平等的意思,“不但无一人在法律之上;而且每一人,不论为贵为贱,为富为贫,须受命于国内所有普通法律,并须安居于普通法院的管辖权之治下”[3]237,宪法的通则形成于普通法院的判决。第三,戴雪称此项意指是英国制度的“专有德性”,即“宪法的通则形成于普通法院的判决”,“英宪是完全被法律精神的优势浸淫弥漫……英宪的通常原理(譬如即以人身自由的权利或公众集会的权利为例)的成立缘由起于司法判决,而司法判决又起于民间讼狱因牵涉私人权利而发生……”[3]239在回答英格兰的“宪典”(宪法习惯,并非制定法)的“责效力”(效力来源)时,戴雪的“唯一答案”是“法律的力量”,因为“凡有违宪行为……犯者在迟早间终要与国法及法院发生冲突”,“自然不免陷入法网”[3]442。戴雪法治的三项意指中的法,都是指普通法。众所周知,普通法在内容上是权利法,在形式上,它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法官在诉讼中发现与发展的具有普遍效力的一般性规则,它的目的是控制权力、保障权利。
当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法治概念也是以控制权力为核心意指的:“法治的基本点是很清楚的:即留给执掌强制权力的执行机构的行动自由应当减少到最低程度。”[4]74“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业务。”[4]73如何控制权力?哈耶克寄希望于“成文法或形式上的法律或公正”同“实体性质法规”之间的区别之上,即,“以形式上的法律或公正”限制权力⑦。因为“普遍性的规则,有别于具体命令的真正的法律,必须意在适用于不能预见其详情的情况,因而它对某一特定目标,某一特定个人的影响事前是无法知道的”[4]77。为预防法治沦为空谈,哈耶克特别强调法律效力的普遍性,他说:“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更为重要。只要同样的规则能够普遍实施,至于这个规则的内容如何倒是其次要的。”[4]80他认为“这种区别是法治和专制政府之间的更具普遍性的区别的一种具体表现”[4]74⑧。
上述哈耶克的法治定义有两个显著的形式主义特点:一是区分两种不同的“主治者”,即“形式的法律与公正”和“实质的法律或公正”,只有前者与法治相洽;二是强调规则普遍适用的重要性高于规则的内容。但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哈耶克是“形式法治论”者。理解哈耶克的法治概念还当关注其形式所表达的实质性内容:一是哈耶克法治的“主治者”是“法律或公正”,而不仅仅是法律,更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法,它是由去中心的职业法官群体在诉讼中世代沿袭发展形成的普通法;二是这个普通法是普遍性的规则而不是特权的命令;三是这个普遍性的规则又是普遍地适用的;四还不要忘记,哈耶克是个自由主义者,在他那里,法治的目的是自由。一句话,哈耶克阐发的是一个以形式包容实质的法治概念。
(三)法治国与正义法
大陆法系“法治国”理论的首创者是19世纪初期的德国法学家Pual Johann Anselm v.Feuerbach(1775—1833),其时德国学界自然法学说衰退,历史法学、实证法学独大,Pual Johann Anselm v.Feuerbach其人就是一位反康德主义的法实证论者。不过,他虽然否认自然法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却“承认人类权利是不可处置的,因为人类是由其道德自治而产生(基本权利或人权)。另一方面,其教示吾人,实证行为系所有法律重要的及不可放弃的要素,对于这些不公正法律的案件,他指出尚有法官反抗权”[2]28。这表明,法治国一语中的“法”是包含正义(实质要素)的,法治并非国家法之治。就法学方法论而言,当时流行的是萨维尼的“实证法学方法论”,此论主张法官在“法律和案件”两个客观的范围内,“将其包摄作相互的安排及相互配置,在此法官并不作价值判断”[2]30。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司法理论。上述法治国的特殊语境告诉我们,“法治国”这一概念本身及其主治的“法”是形式与实质兼具的。
另外,从德语“法治国”一语的语义来看,法治国也包容了良法内容。德语“法治国”这一短语用的是Rechtsstaat,而不是“法律(Gesetz)治国”,这里的“法”是正义导向的普适性的规则,而不是国家制定法。这表明,法治国是“正义法”之治,国家制定法要受正义原则——法的精神的评价,不仅如此,这里的正义还保留了“正义法律的仓库”作用,这与美国宪法理论中的“剩余权利理论”相仿⑨,所不同的只是,美国的“正义法律仓库”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德国的“正义法律仓库”是正义的理念,而理念在权力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不过两者相同的是,这个“正义法律仓库”的“管理人”是独立的职业法官,舍此则法治成泡影。
德国法治国之法的实质正义属性还可以从德国传统的法哲学中找到证据。且不说康德所言法律是“自由的普遍法则”这一法学箴言⑩,即使常常被认为是国家主义法哲学代表人物的黑格尔也将自由和人格作为法的要素,对国家法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态度。黑格尔特别强调区分“法律”(国家制定法)与“法”,强调“法律”必须是“法”的“客观化”、形式化,即国家制定法在“内容的客观性”(自由)与“形式的普遍性”两个方面受到制约。
虽然20世纪的德国法学界有过臣服纳粹的耻辱历史,但是有良知的法学家从来没有放弃抵抗。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德国法哲学大家拉德布鲁赫早在1924年就提出“法之不法”的理论,以保持对邪恶制定法的道德批判力。经受过纳粹统治的苦痛以后,拉德布鲁赫在1946年写就《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一文,文中他明确将“不法之法”逐出法概念:“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当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同时,他还指出当警惕另一种有害的倾向:“在12年弃绝法的安定性之后,更应该强化‘形式法学的’考量,来对抗这样一种诱惑:可以想见,这种诱惑在经历了12年危害和压迫的任何人身上都可能会轻易地产生的。我们必须追求正义,但同时也必须重视法的安定性,因为它本身就是正义的一部分,而要重建法治国,就必须尽可能考量这两种思想。民主的确是一种值得赞赏之善,而法治国则更像是每日之食、渴饮之水和呼吸之气,最好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因为只有民主才适合保证法治国。”[5]该文中,他提出了被后人称为“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克服“非法之法”弊端的三条原则。这三条原则是法官在法的形式效力与正义之间进行权衡的司法规则,它体现了法治国之法体系在形式与实质间的平衡。
强调宪法基本权利的规范属性以制约国家权力是二战后德国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另一种法治努力。这个“基本权利规范论”针对的是“基本权利价值秩序论”,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属性问题:它是法院必须遵守的规范,抑或仅仅是法院“衡量”的对象?哈贝马斯力主前者。他说“作为法律规范,基本权利像道德规则一样是以义务性的行动规范——而不是有吸引力的诸善——作为其模式的”[6]316。“一旦个人权利转变成善和价值,它们在单个案子中就必须在同一平面上为谁具有优先性而发生竞争……而规范则由于一种普遍化检验而取得合法性”。“宪法法院如果采纳价值秩序的学说,并且把自己的判决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非理性判决的危险就会相应增加”。“相反,一旦基本权利的义务论性质受到重视,这些权利就退出了这种收益—成本分析的范围”,作为规范来得到执行[6]320。很显然,这个法治努力本身诉诸形式,内容却是实质——基本权利——指向的。
重新定义同“法的主治”不相容的权力意志法概念,是思想界法治努力的又一举措,这是实证主义法学反思的成果,其最早的理论形态是凯尔森的规范等级理论。与实证主义创始人奥斯汀将法定义为“主权者的命令”不同,氏将法体系描述为一个效力自足的阶梯式规范体系。这个法体系的“分子”是规范,不是权力意志,它的效力不是来自主权者的命令(意志),而是自足的,所有规范的效力均来自上级规范,而法体系的终极效力之源则是“基本规范”。这样,法的权威和法效力就与权力(主权)相分离,使法律在“法性”的获得上取得规范权力的权威,为法治提供了逻辑前提。这一努力的后继者是哈特。哈特的“规则法学”在这一点上与凯尔森一脉相承,他的“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相结合”的法概念不仅以“规则”来定义法律,而且其法也是效力自足的,次要规则中的承认规则所起的作用与凯尔森的基本规范可谓异曲同工。比凯尔森法概念更接近实质内容的是,哈特的承认规则在赋予规则体系效力的同时,涵盖了道德原则和实质价值,它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一以对抗法官专横,二以导入正义。
综上所述,从古希腊到当代,无论是在普通法思想还是在大陆法思想脉络里,法律主治、法律至尊都是法治的最低要求,即没有人能在法律之上,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同时,法治之法是有价值偏好的,亚里士多德称为良法,普通法系中它是权利之法,大陆法系中它是正义之法,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以控制权力为特质的。法治之法是契约之法或客观之法,它与任何特权之法、意志之法不相容。法治与法治之法的内在逻辑关系决定了法治概念包含了形式与实质双重要素,单独的形式法治或实质法治皆有悖法治概念的本意。
二、实践中展现的法治概念
法治是一种实践,因此,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法治概念的另一个有效视角,让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观察。
(一)希腊实践中的法治——践行宪法与习惯
古希腊可称古代法治的“孤本”,让我们还是从它说起。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讨论的是“政制”——宪法问题,因此,他的法治其实是从希腊政制中归纳与抽象出来的理想政制的构成与运行规则,还是他的传世杰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雅典法治实践的窗口。“雅典的政治素重旧典和成规。公民大会以审议政事为主,如有变更成法的议案须另由司法委员会加以审订才能颁行,实际上公民大会制定新法律的事例是很少的。有些人利用公民大会通过有违旧典的‘政令’,常被指责为僭越。执政人员如有违背成法的措施,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违制罪’诉之于公审法庭。”[1]147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法律主治”的政体,法律——宪法与旧典、成规——处于至尊地位的政体。那么,这个法体系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伯里克利在他那篇震古烁今的演讲中说得简洁而清晰。他说:“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对国家有所贡献,决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7]不仅如此,这个法体系中还包含了广泛的控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诉权,例如,“阿勒俄琶菊斯议会是法律的保护人,它监督各长官,使之按法律执行职务,一个人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便可向阿勒俄琶菊斯议会提出申诉……”[8]如果稍事分析,就会发现这个“良法体系”包括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从形式上看,这个法包含了宪法,总体上是遵循多数决原则由公民制定的,或者是在世代的习惯中形成的普遍性规则,它的核心内容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公职向公民开放、公职人员通过公平的形式(选举或抽签)产生、放逐(权贵)法、公民的诉权、权力分享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极其权威的、高度程序化的独立司法,它具有违宪审查权——审查任何权贵包括法律本身的合宪性。很显然,它在法律普遍效力的形式下容纳了善的实质。
(二)普通法实践中的法治——权利法控制权力
英国是现代法治的先行者,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分析一下它的内涵是什么。英国法治的起点是1154年亨利二世发布的《克拉伦敦敕令》(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这个《敕令》是王国的大法,这个声称为了维护“正义与和平”而在国王与贵族们(人民)之间达成的契约,在内容上近乎程序法典。其要者有:(1)造就了高于王权的全英统一的普通法 ;(2)法官独立于王权;(3)国王的利益和郡长及一切政府官员的行为,包括职务行为都是诉讼对象,使王权从法上走到法下;(4)为了防止法官被地方权力或财主收买,对巡回法官的任命实行一次性的委任状制度,而这个委任状由专门的咨询会发出,这进一步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与权威。这些内容虽然不是一下子全部得到遵守,但是它以王权与人民契约的形式出现,无疑对后世法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开创性。这个《敕令》对法治的主要贡献有:它是契约法而不是“王的意志法”,是王与贵族们的共同“主治者”;所有人(自由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王既不造法也不司法,实现了“法性”同国王身份的分离,使“国王的法”转变成“王国的法”,在规范上实现了“王在法下”。特别需要指出以下两点:一是这里的法治之法在形式上除了宪法意义的《敕令》以外就是正在发展中的普通法,普通法是由法官群体发现与维护的规则体系,它的核心内容是权利。二是法官独立及其地位之丰隆,他们站在王权的对立面,是中立的裁判者。
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无疑是英国法治史上另一个重要节点。总共63条的《大宪章》对法治至关重要的有四条。首先是第39条和第40条,它开启后世人权神圣原则之先河。其次是第17条、第18条,将普通法及其法院同国王的人身进一步相分离。当然,这些只是开始,路还很长。又过了几百年,光荣革命后制定的《权利法案》(1689年)成为英国现代法治最终确立的标志,它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制约王权,其前三条限制的都是国王关于法律的权力。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增添了纠正普通法不足的衡平法(现已与普通法合一),衡平法以正义来弥补或纠正普通法刻板形式可能产生的不公。当代英国法学家宾汉姆列出世界法治进程中的12项重大事件,其中七项发生在英国,七项中除了第五项“法官伦理”和第七项后半部分之《1701年王位继承法》以外,皆为“权利宣言”,就说第五条,其目的也是为了保障权利,而《王位继承法》是将王位继承这一传统的“王室家事”纳入国家法治,王成为一个荣誉职位,王在法下原则得到进一步落实。
上述对英国法治史的简单描述告诉我们,英国实践中的法治是围绕着控制王权、保障权利、实现正义而展开的,所谓法治,其实是权利之治,正义之治,其实质内涵非常明显。但是我们万万不可忽略它的形式内涵。普通法法治是真正法律至尊的,而其法是通过“去中心”的法官群体发现与维持的,是抽象权利的形式化。其严格的诉讼程序、司法独立,权力分立的宪政体制等等,都是严格形式化的。特别令人艳羡的是,在前现代国家普遍存在的、生杀予夺的王权,在法治的英国竟然“羽化”为正义的维护者,这一切似可以称之为形式化的权利之治,令人叹为观止。
(三)德国魏玛宪法法治目标的变质
德国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标本,于认识法治同样弥足珍贵。虽然《魏玛宪法》贯彻的是法治国原则,德国法学家的法治观念和良法观念与英国学者也无分轩轾,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结果却大相径庭。原因何在?中国大陆学界对此持有两种正相反对的理论。有的学者将德国法治国家分为“形式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上的法治国家”,认为早期法治明显的形式化倾向,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9]。有人则相反,认为第三帝国占主导的法思想实际上是带有激进理性主义色彩的自然法思想,“它是运用自然法思想并通过转化为实在法的形式去实现纳粹党所认为、所秉承、所坚持、所追求的所谓‘民族正义’的浪漫主义理想”[10]。愚以为这两种看法都不甚贴切。
《魏玛宪法》所确立的法治体制的历史性蜕变,既不是“过于形式化”之过,更不是“过于实质化”之误,而是政治法学界的浊流与纳粹一定程度上的“合谋”所致。这股浊流屈从(或迎合)纳粹的需要,一方面将法治矮化为国家法之治,另一方面在价值方面又高扬国家主义,从而导致法治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的双重变异与脱节,使纳粹得以产生并最终走到了法上。首先,在法治的形式方面只注意了法的效力,忽略了法的形式德性。例如,法产生的正当程序、法的一般性特质、一般法律原则对实在法的规制、法不溯及既往、法的明确性与不矛盾性、法效力的普遍性、司法独立等等。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把元首的命令当作法甚至奉为最高法,使法治原则下的“主治法”堕落为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法”。在法治实质要素方面,一则忽略了法治所维护的实质价值的人类性、一般性或共识性特质,将它等同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再则忽略了价值的规范化、价值权衡时对实在法的尊重等等,使正义蜕变为价值专横,同样成为权力的刀锯。这一脱节使法治这一整体性的宪法概念变得四分五裂,法治原则在滥用的权力面前喑然失声甚至帮腔作势,失控的国家权力最终成长为可怖的、为所欲为的“利维坦”。对此,德国当代法学家考夫曼的灼见可谓一针见血:“法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都不该为那场历史性的法治失败埋单,而是权力主体恶意曲解、利用实证主义和自然法而带来的恶果。”[2]30德国的悲剧昭示人类,颁布并执行恶法、滥用自然法的名义僭越现行法,这两者不过是权力滥用的不同手段而已,在分裂的法治语境下,权力主体可在形式与实质这两端间翻云覆雨,或以恶的形式消解共识性的实质要素,或以伪善来对抗普遍性的形式要素,法治最终落为笑柄。
上述对三种代表性的法治实践的简单梳理告诉我们,古希腊法治实践是社会自然进化的产物,它的法治是宪法统帅下的法体系的统治,这个法体系在形式上是由民众直接宣告,或由民选机构通过的普遍性规则,或为原始民主的良俗,它的核心价值是基于城邦公共利益的平等、自由、民主,这些价值依托的是种种高度形式化的规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职向公民开放、公职人员通过选举或抽签产生等等。它的主要依托是民主,公民的直接参与、赋予公民广泛诉权的司法,这使滥用的权力难逃审判,当权力主体成为法的主人(例如僭主)的时候,法治也就死亡了。
与古希腊基于民主的法治不同,英国的法治是国王与贵族(人民)契约的产物,国王以走到法下换取贵族的忠诚,成功地由国家的所有者转变为正义的化身,国家则成功转型到rule of law。英国的法治是普通法(期间有几百年衡平法加入)的统治,这个普通法是高度形式化的(早期甚至有点僵硬),但是它的本质却是权利、自由、平等,形式与实质在普通法里是无法分离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法治的拱梁是独立的职业化的法官,法官的依托则是形式化的判例及同样形式化的诉讼程序与技术,因此,它比古希腊以民主为主要依托的法治形式化程度更高,因此生命力也更强。
与上述成功的范例不同,德国魏玛宪法体制提供了一个失败的范例,撇开社会政治原因不谈,它失败的重要学理原因是实践中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的分离。这从实践的角度启示人类,将法治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相割裂,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法治。
三、法治原则中的法治概念
在不同的学科中,法治有不同的意义指向,法学中的法治一语由其自身的学科性质——规范学——所决定,它关注的是法治的规范方面。简单来说,法学关注的法治是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法治概念的规范性表达就是法治原则,抛弃法治原则而空谈法治(如所谓申韩法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一部法治概念史,其实就是法治原则展现并日臻完善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从法治原则的历史中进一步深化对法治概念的认知。
具有开创意义的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包含了两大原则:法的普遍性原则和良法原则,这两大原则虽然过于简单,但却是切中肯綮的,涵盖了形式与实质这两大要素。现代法治思想的开创者之一戴雪将法治表述为三大原则:法律至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权利源自法院判决[3]244。初看三者只有形式,但是不可忘记这里的“法”本身涵盖了法治的实质要素。二战以后,鉴于纳粹独裁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世界法学界展开了关于法治原则的经久不息的大讨论,深化、丰富了法治概念。让我们以权威法学家的思想为蓝本作一个分析。
自然法方面率先作出贡献的或许是富勒。富勒将法律的形式要求纳入自然法,称之为程序自然法,或法律的道德性,或八大法治原则:法律的一般性、公开颁布、不溯及既往、清晰性、无矛盾、不规定不可能之事、稳定性,以及官方行动与公布规则之间的一致性[11]55-107。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八大法治原则就会发现,这里的“道德”一词与传统自然法学的“道德”一语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指法律所承载的价值,例如,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富勒的“道德”却是抽象的形式化规则,他称之为法之为法不可或缺的“属性”,或许也可以称为“法的德性”或“法德”“法性”。虽然在传统的道德概念里很难找到富勒“道德”的位置,但是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认识法治之门:法治之法不仅应有善的实质,而且当有善的形式,这个法的“属性”概念既坚守了自然法的传统立场——道德是“法律之为法律”的条件,同时又堵死了传统自然法被“价值暴政”绑架的通道。
具有跨学科影响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阐述的法治原则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这个法治原则体系是从两大正义原则中推论出来的,推演的起点是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罗尔斯认为无知之幕“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12]10。在此预设下他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正义原则,这两个正义原则可以说是形式与实质的完美结合。罗尔斯的“法治”是被作为满足上述两大正义原则的“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而予以讨论的[12]153,法治原则则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基本结构”所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在这里,罗尔斯将“形式的正义”直接表述为“作为规则的正义”——即有规则的、无偏见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公平的执法。罗尔斯认为“作为规则的正义”对于法治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要的。他说:“如果作为规则的正义偏离十分普遍,那么就可能产生一个严重问题:即一个法律体系是否是作为一系列旨在推进独裁者利益或仁慈君主的理想的特殊法则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即“仅仅保证对规则的公正的、正常的实施,而不管规则本身的内容,所以它们可以与不正义相容”[12]。为了解决执行规则与正义的“不相容”问题,罗尔斯进一步提出了法治之法的准则(法治原则):(1)“应当意味着能够”的准则;(2)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准则;(3)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准则;(4)有一些规定自然正义观的准则,它们是用来保护司法诉讼的廉政性的指南。最后,罗尔斯进一步强调了法治原则是建立在“自由优先性的规定”之上的[12]214。如果将罗尔斯的上述法治原则放回到他的正义论的总体框架中去解读,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法治原则咋一看是纯形式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与实质相互交融的规则集合:它的前提是形式的(无知之幕),它的内容是形式的,但是它又是“满足两大正义原则的正义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自由优先的。
第三届“唐奖法治奖”获得者、师从哈特的拉兹教授倡导的法治原则及其晚年对它的“扩容”,当是法治原则中形式与实质同在的又一例证。拉兹将现行的法治定义分为“法的统治”(广义)和“政府受法律的统治”(狭义)两种,他指出这种将法治单单理解为“形式”的概念是有失偏颇的。据此,他提出了形式与实质兼容的法治八大“重要原则”。这八大法治原则除了强调司法对于法治的意义以外,其他内容均与富勒的八大法治原则相仿,它是形式与实质兼具的。
值得一提的是,拉兹后来将他“定义法治的基础”及法治原则都进行了“扩容”,进一步突出法治概念的实质方面。作为“排他性实证主义者”的拉兹教授将法律的“品性(德性)”作为定义法治的基础,主张不具备“法性”的法不可以用来定义法治,可知他的法治概念是形式与实质兼备的。早年他将“能够引导受约束者的行为”作为法的唯一品性,近年他自我反思道,能够引导受约束者的行为“仅仅是效率意义上的品性(the virtue of efficiency),本身并不是道德品性(a moral virtue)”,进而将“法治的目的在于防止政府滥权”作为法治之法的道德品性,两者共同构成法治的观念基础。同时,拉兹将他的八项法治原则扩容为11项[13]。至此,以形式法治观面世的拉兹的法治原则,实质内容更加充实。
上述对法治原则体系的分析昭示我们,法治本质上是一种原则,法治原则清楚表达了法治概念的规范性内涵,法治原则体系由多项原则构成,这些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构成法治概念的内涵,而且,一些单项原则本身又是形式与实质兼具的,比如平等原则,此足见法治概念是形式要素和实质要素的综合体,两大要素是不可分割的。
四、结 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思辨中的法治、实践中的法治、法治原则中的法治——对法治概念的历史性诠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法治即法律主治,法治是一个包含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的制度性、整体性概念。理解法治概念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法治不是简单的国家实证法之治
法治(rule of law)即法律主治,或法的统治,不是“依/以法治理”(rule by law),它的首要原则是法律至尊或法律至上,即所有社会主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受法律约束,这在逻辑上涵盖了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受制于法律,即“国家实证法”本身要接受“法治”,这里的“法”包含了但不限于实在法,也包含法的精神——正义。
(二)法治与法的“法性/德性”不可分离
“法治”是良法之治,只有符合“法性/法德”要求的法,才是法治的适格“主治者”。亚里士多德对此表达为“良法”,英国的普通法法治之法是权利法,大陆法系“法治国”之法是正义法。法律的“德性”要求是不断扩展的。在早期,法的德性单单指法的实体价值:自由、平等、权利、公平正义等等,富勒加入了所谓“内在道德”内容,以区别于前者(外在目标的德性)。现在,法的德性有四个向度:一是外在目标向度,人性尊严及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权;二是效力向度,法律必须有效地规制人的行为,特别是规范权力行为,为人的行为提供预期;三是表达向度,法律必须以良好的形式表达出来,主要是普遍性、平等性、公开性、明确性、确定性、不矛盾性等;四是程序向度,法律必须是交往理性的产物,法的实施贯彻司法独立原则并遵守正当司法程序。
人们对“法性”之于法治的意义的认识也有了提升。早先人们认为“失德之法”不该或不具备“主治”的资格;现在,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失德之法”与法治犹如方枘圆凿,在逻辑上不可能,富勒的“雷克斯国王”的寓言很好地论证了这一命题[11]40。如果说“不该论”只具有应然意义,那么“不能论”则表达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判断:失德之法不会带来法治是必然的。失德之法表现形式很多,它们的共同点是意志法或工具法。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三)法治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不可分离
法治包含形式与实质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是不可分离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法治的形式要素具有手段意义,实质要素具有目的意义,但是没有形式要素,实质要素便无以表达,无法运作;实质要素又是基础性要素,“形式”是“实质”的形式化,没有实质,形式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特权、专横的形式化与法治南辕北辙。法治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还是相互诠释的,两者都从对方获得正当性证明,并从对方获取其意义,“法性/法德”正是此两者的交汇点。总之,世界上只有一个法治:形式与实质兼具的法治,两者的分离意味着法治的死亡。
(四)建构整体性法治概念,以利法治建设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当下流行的法治概念恰恰是“分离的法治概念”。许多形式法治论者将法治解释为单纯的国家法之治,此“法”不仅缺乏实质价值,更无法性要求,甚至连讲话、会议纪要、内部通知、团体规章等等悉数视为“法”。更有甚者将宪法中的法治概念与申韩之论混为一谈,主张中国法治只能走申韩之路,其害自不待言。其实,在亚里士多德笔下,不仅法治、就是人治也没有波斯式“治理”插足之处。割裂的实质法治论则容易为“善超越法”的价值专横与“结果司法”背书。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分裂、相互龃龉的法治语境中,权力就得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有鉴于此,法学之当务便是反思在“学术性”与“正确性”的张力中被撕裂的法治概念,对现行宪法第五条的法治概念作整体性诠释,以利法治建设。
注 释:
①修昔底德(希腊文Θουκυδiδηξ 、英文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狄奥多洛:《史丛》卷九27。(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2页脚注。)
②梭伦说:“法治让所有人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而且,经常给不义者带上脚镣。”(参见《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刘小枫编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③修昔底德说:“希腊古时各族都佩武器以自卫,无论海上或陆地都互相劫掠。雅典最先进入法治,禁止盗贼,因而民众在平日可以不携刀剑。”(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0页脚注。)
④苏格拉底提出建立国家的“总的原则是正义”,“审理案件无非为了一个目的,即,每一个人都不拿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占有自己的东西。”“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4页以下。)
⑤针对一人治理的主张,“这种制度的性质(比富户和贤良为政)实际上就更是寡头……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良好的政制。”(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2页。)
⑥1930年,雷宾南先生将rule of law中译为“法律主治”这是很传神的,避免了在“法治”语义上徒生争执。
⑦哈耶克将两者的区别比作“制定一个道路使用规则(像公路章程)与命令人民向何处去”两者之间的不同,“或者更明白一些说,和设置路标与命令人民走哪一条路之间的区别一样。”(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⑧但是拉兹反对哈耶克关于法治的“法律仅是普遍性的规则”的理论,主张“我们需要一般和特殊的法律来完成工作”。(参见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⑨德国联邦法院明确断定:“法律并不等于全部成文法的总和,在有些情况下,在国家权力机关颁布的法律之外,还可能存在着一种附加的法律成分,它来源于立宪的法律秩序的意义总体(Sinnganzem),并可以作为成文法的纠正物起作用,司法的任务是发现这种成分并将其实现于它的判决之中。”(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2页。)
⑩“法律,乃是‘使个人恣意与他人恣意,依据有关自由的普遍法则,得以互相共存一致的条件整体’,或者是:法律是‘防止自由的障碍’。”Kant,道德形而上学,学院版,第230页。(转引自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