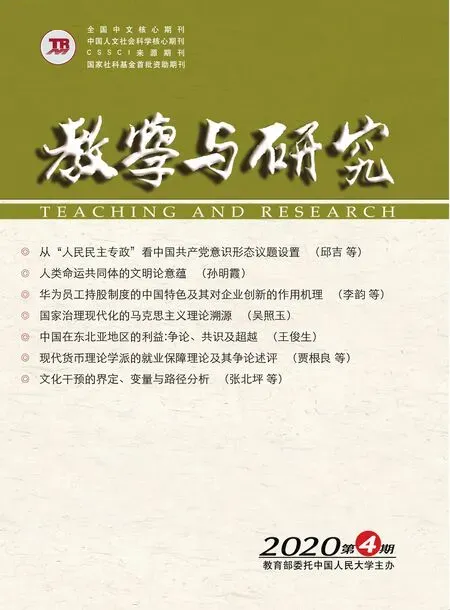巴迪欧事件哲学的理论特质
——基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性视角的考察
在当今西方哲学理论景观中,“事件”(event)无疑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生长点。可以看到,它是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比如早期维特根斯坦与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并见之于利奥塔、德里达与德勒兹等当代法国重要哲学家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马利翁(Jean-Luc Marion)的现象学思考中也蕴含着事件分析的独特视角。从巴迪欧在今天法国思想界的影响来看,事件哲学也是一个引发广泛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对他的引用抑或批判大都围绕“事件”概念所展开。目前学界对巴迪欧事件哲学的讨论大体呈现两种思路:一是从本体论层面上考察巴迪欧对海德格尔“诗歌本体论”的反叛,在其“数学本体论”的视域中澄清“存在与事件”“一与多”的内在关系,进而揭示“事件”对于开启真理的理论意义;一是通过考察保罗与基督教复活事件的关系分析革命主体与真理性事件的内在关系,以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主体性理论危机。反观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其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都忽视了巴迪欧事件哲学建构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批判的重要旨趣。事实上,事件问题之所以如此广泛地被关注,这与各种后现代激进思潮反叛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涤除其长久以来的主体中心主义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些核心观念,比如同一性、主体性、本质论与必然性等遭到质疑,而非一致性、开放性、偶然性与可能性等理论价值备受推崇。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现象学中一直以来隐而未显的诸种关于“事件”的前瞻性话语开始得到关注。毕竟,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直至马利翁,现象学都并非是一种关于存在和本质的静态思考,而是对偶然性和不可预期的开放性事物的动态思考。同时,在多数学者那里“事件”概念都被赋予了非一致性、偶然性与可能性的理论内涵。所以,尽管在巴迪欧集中讨论事件的著作中并未出现过多的现象学分析,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说现象学构成了其事件哲学建构的深层底蕴。对此,当代法国现象学研究者弗朗斯瓦斯·达斯杜尔(Françoise Dastur)的论断不无道理:“我们不应该将现象学和对事件的思考对立起来,而是应该把二者联系起来;对现象的开放性必须与对不可预测的开放性相一致。”(2)弗朗斯瓦斯·达斯杜尔:《事件现象学:等待与惊诧》,载《生产》第12辑,汪民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说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致力于揭示某种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普遍必然性,那么无论是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还是巴迪欧,其理论建构中之所以都包含了突显偶然性、非一致性、开放性与可能性等理论价值的事件性分析视角,无非是要给予传统形而上学以反叛。就此而言,关于现象的思考与关于事件的思考非但并不相悖,反而彼此交相呼应。
一、缘起:一种关于“事件”的现象学思考何以可能?
尽管关于“何为现象学”的问题至今仍诉讼纷纭,但毋庸置疑的是,“回到事情本身”是现象学普遍共识的一个基本原则。按照胡塞尔的理解,我们无需寻找任何所谓的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某种超越性“本质”或“实体”,现象本身就构成了哲学研究的对象。承继于此,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研究也严格坚持这一原则,他指出:“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41页。不过,“回到事情本身”并不意味着现象学只是对现象世界的一种静观描述。在《现象学的观念》一书中胡塞尔明确指出,现象学的任务并不是一件似乎只须直观,只须睁开眼睛即可办到的平凡小事。因为谈论那些简单地存在于此并且只需要被直观的事物实际上根本没有意义,所谓“简单的此在”都是在诸如知觉、想象与回忆的体验中构造自身的。(4)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6页。在胡塞尔看来,每个意识本质上都是意向性的,也即意识总是能够超越自身构造一个意义世界并使其相对于意识而显现,所以正是意识构成了现象自身显现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胡塞尔并不关心独立于意识所自在存在的客观对象,他更关注的是事物如何相对于意识而自身显现。因此,对意识的结构与功能的考察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内容,而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时间性维度逐渐显露。
根据胡塞尔的观点,意识的每一个“当下”时刻都延展地和滞留地向将来、过去两个方向涌现,这构成了意识的时间性结构。借用胡塞尔本人的一个比喻,意识如同一条无限体验的时间之流,我们对每一个“当下”时刻的体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从这一个“当下”中涌现出对与它随即相联之物的期待。尽管这个尚未到场之物并没有真实“到场”,但是在“当下”之中已经包含了它即将到场的潜能,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已经被当下化了。胡塞尔将意识的这种预期倾向称为“前摄”(pretension)。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刚刚离开“当下”的曾在之物,在“当下”中也仍然持存,这种先前消失之物的“仍然在场”称为“滞留”(retention)。不过,当胡塞尔谈及“时间意识的河流”时并不意在突显时间流变的一种连续性与必然性。一方面,“前摄”和“滞留”打乱了时间各部分之间的原初关联,在时间内部构成了一个裂缝。另一方面,从“过去”或“将来”的到场总是不可预料的,因而相对于每一个“当下”而言都是一种“过剩”。由此,我们便已能够洞察到胡塞尔意向性分析的非凡之处:意识不是一劳永逸被给予的,而是具有一种“视域”(horizon)结构,即任何显现的意义都暗含无限可能的意义。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一书中,胡塞尔指出:“现象学解释通过使想象中的潜在感知当下化(这可以使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澄清了在思维对象的意义上什么被包含了进来以及什么仅仅是非直观地被共同意指(比如立方体的另一面)。”(5)Edmund 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60, p.48.也就是说,在我们实际被感知到的事物中总会有一部分是当下无法被感知到的,不过这部分内容并非真正消失,而是在意识中沉淀下来随时都可能被激活。比如当一个立方体的正面显现时,尽管它的背面无法同时显现,因而相对于正在显现的正面而言是一种过剩,但是它仍具有显现的可能性,只不过是暂时地隐而未现。不难发现,“视域”本身是一种可见与不可见、现实与可能的交织,它说明了直观与意向之间并不充分符合,意向性始终对不确定保持开放。实际上,从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关于现象性的思考与关于事件思考的相似之处。众所周知,在巴迪欧、齐泽克等当今西方左翼激进理论中,事件被认为是产生于特定情势(situation)内部一个极为特殊的点位,即“事件点”(evental site)上。由于“事件点”位于情势中的空无边缘进而它并不属于情势的构成部分,这意味着在事件点上事件的发生总是难以捉摸,我们无法在情势之中对其进行预测或判定。所以相对于既定情势而言,一个事件的爆发就构成了其内部的一种断裂性力量,它代表着超出现成情势秩序的一种“例外”和“过剩”。正如齐泽克所言:“事件产生于无……它把自己归于每种情境的虚无、归于其内在的不连贯和过剩之中。”(6)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反观胡塞尔,意识的意向性构造从来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无限可能的生活经验对任何当下的生活经验而言也构成了一种意料之外的“过剩”。因此,正像达斯杜尔所敏锐洞察的,“过剩是这里的规则,因为在被经历过的事物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增添……当意向性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当无法实现的威胁永远无法完全避免,意向就会展开自身。”(7)弗朗斯瓦斯·达斯杜尔:《事件现象学:等待与惊诧》,载《生产》第12辑,汪民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2页。从这一点而言,一种关于事件的现象学思考便得以可能了。
如果说事件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中初露端倪,那么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中则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尽管同样宣称“回到事情本身”,但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分歧却是显而易见的。胡塞尔认为,原初的东西是纯粹意识,现象学就是对对象向纯粹意识显现的方式以及纯粹意识本身的结构予以反思性描述。海德格尔则认为更原初的不是纯粹意识而是生活经验,后者才是“事情本身”的真正含义。事实上,海德格尔一直以来都不满意胡塞尔的现象学奠基于纯粹先验自我的构造,他认为胡塞尔没有从根本上脱离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理论窠臼,因而最终遗忘了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回到事情本身”并不意味着返回到意识的意向性结构,而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8)但问题至此还没有那么简单。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首先与通常恰恰不显现,同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其情况是:它构成这些东西的意义和根据。”(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41、42页。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需要看到,虽然海德格尔也极力否认“现象”背后存在“物自体”,但是不同于胡塞尔将“现象”看作是明见性的,海德格尔认为“现象”首先不是自身显现而是被遮蔽的,“恰恰因为现象首先与通常是未给予的,所以才需要现象学”。(10)按照海德格尔做出的“存在论区分”,“存在”不是某种对象化的“存在者”而是一种纯粹的现象或者说自身显现,同时在海德格尔视域中“此在”(Dasein)是最为特殊和最为重要的“存在者”,所以“现象”究其根本指的是“此在”的自身显现。倘若说“现象”首先和通常处于被遮蔽状态,那么“此在”也总是遗忘自身的显现而沉沦于世,也即处于一种“非本真”状态。当然,“此在”并非对此毫无察觉。比如在“畏”的情绪中“此在”就会突然体悟到自己的茫然失所,以及周遭世界的无意义。所以,这种朝向“无”或者说向着死亡的生存构成了此在的本真存在,在“畏”之中它向此在显现自身。
问题的关键在于,海德格尔所提到的“死亡”不是流俗意义上的生命终结,而是一种“悬临”(Bevorstand),它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的可能性”。(1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42、288页。也就是说,此在只要存在着,“死亡”便如影随形,尽管不在场但却随时可能出人意料地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无疑是一个事件。不过海德格尔认为,与其说“死亡”是一个“事件”毋宁说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因为对“此在”的“现在”而言,朝向死亡而存在总是在先的,这种“终将有死”的紧迫逼促人们规划当下的存在;曾经消逝的东西也并非毫无意义,而是时刻会被“此在”激活作为共在的一部分。所以说“此在”总是先行向死而生(将来),同时仍然承担着自己的过去(被抛入世界),并且作为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做出决断(当前)。这种时间性的绽出统一性,就是此在的存在意义。不同于传统理解中的时间类似于一道均匀流逝的长河,它表现为从“过去”经由“当下”向“将来”延展,海德格尔讨论的“时间性”更像“喷泉”一样是动态的与发生性的,它不断从自身中涌现出来,而“此在”随着时间性到时一道自身显现。这样一来,海德格尔视域中的“终结”不意味着“停滞”而是一种“到时”,即“某事发生了,到了做……时间”。也就是说,对于“此在”而言有限性已经发生,关键在于其能否做出决断:是直面本已存在,还是继续沉沦于世?这是一个能否从常人状态中脱离的决断时刻,因而相对于常人状态,它代表一种断裂的发生与纯粹的可能性。由此,海德格尔与巴迪欧的惊人共识也初露端倪。
前文已述,在巴迪欧的视域中一个事件的发生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是难以从既定情势结构的内部加以判定的。因此事件的存在,不是客观知识领域的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主体性的实践问题。按照巴迪欧的观点,一个事件是主体宣称的结果,“事件已经发生,对于该事件,我们既不能评估也无法给予其论证,而是将只能对它保持忠诚……主体凭运气决断一个事件的存在。”(12)Alain Badiou, Infinite Thought, Continuum, 2005, p.47.显见的是,这种“宣称”带有赌注的意味,主体是“下赌注”以决定(decide)一个事件的存在,其基本逻辑是“一个事件发生了,到了决断的时刻”,也即主体“决定”是否在情势中探寻该事件的踪迹并给予其以命名和忠诚。不难发现,海德格尔与巴迪欧的讨论中都涉及了一种主体性决断,这种决断又都指向与既定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常人状态,在巴迪欧那里是某种“计数为一”的结构)的突然断裂,因而相对于既定状态而言“断裂”本身构成了一种“过剩”。正如达斯杜尔所指出的,“事件总是以惊诧的方式,确切地说,是从一个你没有预料到的地方来到我们身边。因此,现象学的艰巨任务就是思考事件所带来的这种期待的过剩”。(13)弗朗斯瓦斯·达斯杜尔:《事件现象学:等待与惊诧》,载《生产》第12辑,汪民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应该说,达斯杜尔的这一论断还是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问题的关键。一直以来,西方哲学都相对较少地对偶然性、机缘性、可能性与非一致性等理论特质投以关注,而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恰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包含对隐藏在意识现状之中的无限可能性的揭示。后来海德格尔在讨论现象时不忘谈及遮蔽,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思想转向后认为“未显现者”比“显现者”更原初,指认存在是既自身显现同时又自身隐退。这种自身显现与自身遮蔽之间的争执,被海德格尔称之为“事件”(Ereignis,或译为“本有”),它描述了人与存在之间难以预料的相遇与达赠。
二、近代西方主体形而上学的颠覆:马利翁与巴迪欧论“事件”
如果诚如研究者所指认的,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是近来法国思想界的重大事件之一,(14)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xxi.那么这也绝非偶然。一方面,尽管当代法国哲学表现出爆炸性的话语增殖和竞争,延异、他者和差异等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多数理论仍然围绕(后)结构主义这一中轴所集结。结构主义在法国由语言学的宁静走向哲学的喧嚣,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反叛以萨特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所以其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理论影响就是对主体的解构乃至消解。自此之后,法国哲学诸种新话语的生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主体问题相关涉。20世纪70年代,事件理论研究热潮在法国的兴起亦是如此。另一方面,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现象学在当代法国焕发新的生机,甚至一度扮演着法国理论先锋的角色。这其中,由马利翁所领导的“新现象学”运动尤为引人注目。马利翁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将事件概念引入对“饱和现象”(saturated phenomena)的考察之中,旨在取消胡塞尔“意向性”叙事逻辑中先验主体的奠基。虽然巴迪欧与马利翁的理论立场与研究思路不尽相同,但是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落脚于事件概念以期提供一种关于主体的新理解。
“事件”在马利翁的视域中并非一个专门的独立问题,而是同现象学建构密不可分的,其所直面的对象就是胡塞尔。前文已述,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是“回到事情本身”,他主张消除一切形而上学前提以便让事情自身显现。后来胡塞尔又借由该原则进一步提出了认识的“相合性”目标,即最高级的认识乃是意向与直观之间的充分符合,或者说事情自身的完全显现。当然,这种“相合性”最终只能是一种理想。因为意向对象从不会一次性被完全给予,意向性活动具有“过剩”的特征。马利翁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种“过剩”并将其作为自己现象学叙事的基点,在《过剩:论饱和现象》一书“序言”中他明确表示:“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过剩,直观对于概念的过剩,饱和现象及其在概念之外的给予……”。(15)Jean-Luc Marion, In Excess: Studies of Saturated Phenomena,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p.xxi.那么究竟为何马利翁会对“过剩”如此强调呢?如果说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形而上学表现为理性主体话语的霸权,比如康德就曾为了探求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而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强调直观内容如果离开思维便无法成为认识的对象,知性范畴是一切有关对象的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那么后来胡塞尔虽然也以获得普遍可靠的知识为目标,但是由其所开创的现象学却旨在实现一种彻底的“无前提性”。不过问题也正在于此,在马利翁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正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所最终达到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先验自我。这意味着现象学本质上没有摆脱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中心主义,因为现象仍然作为主体的对象而存在,主体统摄的优先性取代了现象的自身显现。在主体的注视下,事情本身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被遮蔽了。正是为了涤清胡塞尔现象学中先验主体的奠基性作用,马利翁提出了“饱和现象”。
“饱和现象”是针对“贫乏现象”(poor phenomena)和“普通现象”(common phenomena)所提出的。“贫乏现象”主要指那些由于缺乏直观内容而太过抽象与形式化的现象,比如数学公理或逻辑形式;这类现象在其自身中所显现的除了空洞概念之外一无所有,因而表现出了一种现象学上的匮乏。“普通现象”则包括物理等自然科学现象,原则上在这一现象中直观与意向基本相一致;这意味着有别于“贫乏现象”,“普通现象”具有了直观内容,但是其中概念仍然统摄直观。不同于以上两种现象,在“饱和现象”中直观超越概念的限定,“直观产生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是概念所无法把握,从而也是意向无法预测的。直观并不受意向所束缚,而是从中挣脱出来,将自身变成一种自由直观。由于不再追随概念以及遵循意向的路线(目标、预见、重复),直观颠覆并超越意向,并取消了意向的中心化。”(16)Jean-Luc Marion, Being Given: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Given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25、322、270-271.从马利翁的表述来看,这种直观相对于意向的“过剩”是出乎意料、不可预见的。为了进一步澄清问题,马利翁还参照康德的量、质、关系和模态四种知性范畴的划分,将饱和现象分为四种类型加以考察。从量上来看,饱和现象既无法预测又不可复制,它的发生既无法被追溯又不可逆转,马利翁称其为“事件”(event)。“事件”作为一种现象是绝对的自我显现与自我给予,这使得它严格区别于“对象”(object),因为对象总是被某种先验自我建构出来的。马利翁指出:“事件实际上也像其它现象一样显现,但它被区别于对象化现象就在于它本身不是一种生产的结果,这种生产将其作为一种明确的和可被预见的产物,将其看作是可以根据诸种原因被预见到并且在这些原因的重复下可被重复生产的结果。相反,通过突然发生,它证实了具有一种无法预见的起源(我们无法因此给予其以再生产,因为其构成没有任何意义),它从一些常常是没有被认识到的,甚至是不在场的,至少是从无法确定的原因中涌现。”(17)
那么,饱和现象作为一个事件显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马利翁曾以自己某次演讲所在的报告厅为例对此作出了更详细的说明。(18)Jean-Luc Marion, In Excess: Studies of Saturated Phenomena,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2,p.31、31-33.当一个“报告厅”以事件的模式显现,那么从过去的视角来看,它已经存在于此供人使用,至于其缘何于此并不为人所知。这个报告厅拥有一个不为我所控的过去,它的出现亦不在我的预期之中,它只是突然闯入我的视线;从当下的视角来看,这个报告厅只是在这一时刻,这一特殊场合面向特定观众敞开,这一切皆是当下的、独异的和无法重复的。从将来的视角来看,报告厅中演讲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已是既成事实,它是不可逆转、无法复制的,任何力图穷尽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或解释的可能性都没有。如果诚如马利翁所界定的,现象具有一种事件的起源,即一个事件总是突然朝向人而来,其发生完全是自身给予的,它既无法被预见又不可被重复,那么近代以来的一切主体性叙事逻辑便被颠倒了。因为由此,“在中心处矗立的不是主体,而是一个受馈赠者(a gifted),其功能是接受那源源不断向它给出自身者,其优先性被限定在了如下事实,即他从他所接受的东西中接受他自身。”(19)Jean-Luc Marion, Being Given: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Given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25、322、270-271.可以看到,在事件出乎意料地自我给予中,“主体”从建构者的中心位置陨落成为现象的接受者和受馈赠者。不是主体召唤现象显现,而是现象召唤主体生成,“召唤所带来的结果是受馈赠者的产生,这是一种完全服从于被给予性的主观性或主体性……”。(20)Jean-Luc Marion, Being Given: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Given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25、322、270-271.
应该说,马利翁从现象学出发对事件的考察与巴迪欧在结构视域中所展开的讨论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从直接的意义上,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所直面的对象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按照阿尔都塞“历史是无主体过程”的观点,历史变化关涉于社会整体结构,“历史时代概念只能建立在属于一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的起主导作用并具有不同联系的复杂结构的基础之上”,进而“人在理论中只是表现为结构所包含的关系的承担者”。(21)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1、309页。在阿尔都塞看来,传统形而上学中充当本原、基础和中心的“主体”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这种主体恰恰是需要被解构的。不过阿尔都塞这一“无主体”的理论操作在强调结构优先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原本不言自明的解放主体变得无从谈起了。所以,如何在结构主义之后重新讨论主体便成为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的重要问题。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就是在这一语境中出现的,其主要目的是在结构的基础上重新确证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巴迪欧曾在一次访谈中直言,在为解放而斗争、反对殖民或资本主义秩序时总会遇到哲学上的所谓“主体”。我们不可能设想在没有理性的和合理的主体理论时就可以谈政治激进主体问题。(22)巴迪欧、高歇:《关于共产主义的对话》,蓝江译,《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那么巴迪欧究竟是如何应对这一主体性理论难题的呢?其策略首先是对“结构”提出了新的理解。在传统语境中“结构”往往被看作是一致性的、连贯性的自运动体系,巴迪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指认情势的客观结构是非一致性的与不连贯的,其中充满着许多“事件点”。在这些事件点上可以产生能够使结构整体发生断裂,或者说颠覆结构的力量,即“事件”。由于“事件”的产生总是不确定的,出乎意料而且转瞬即逝。所以主体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后探寻事件踪迹、给予事件以命名并忠诚于该事件的一系列程序,即一个真理性事件诱发主体独异性生成的过程。
愈益明朗的是,马利翁从现象学角度与巴迪欧从结构视角出发对事件问题的讨论都包含对近代西方主体形而上学的反叛。在二者的视域中,事件的产生总是无法预见与不可重复的,而事件又都代表着与某种现成状态的非一致性。(23)在马利翁的现象学中,事件作为饱和现象,代表着直观超越意向的非一致性;在巴迪欧的结构视域中,事件代表着与既定情势相断裂的非一致性。通过与一个事件的不期而遇,主体不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建构成的。不过,虽然马利翁和巴迪欧的很多理解不谋而合,但实际上两个人的讨论还是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深度。毕竟,在马利翁的现象学图景中,神学始终是一抹最鲜明的理论底色。可以看到,他对饱和、事件与主体等问题的思考一直隐含着强烈的神学关怀,而其神学建构的终极目标是在后现代语境中确立一种崇尚“爱”的伦理价值。(24)Jean-Luc Marion,Being Given: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Givennes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24.如果说马利翁最终走向了一种神学的超验性,那么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则体现了关照现实并改造现实的历史性理论维度,而这一点恰恰是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马利翁的现象学叙事都无法企及的。
三、超越“事件现象学”:巴迪欧事件哲学历史性维度的彰显
前文已述,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对萨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批判是深刻影响当代法国哲学理论版图构型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批判的非凡意义在于当阿尔都塞以结构消解主体时,他实际上是对自笛卡尔以来奠基于主体性理论逻辑的整个形而上学叙事造成了冲击。如果说颠覆形而上学是今天多数左翼激进话语的共同诉求,那么相较于单纯否定同一性、本质论与必然性等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特质,摧毁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理论根基在反形而上学的效果上显然要更大。我们看到,传统形而上学始终以探寻存在为终极旨归,而开端于笛卡尔、中经康德和黑格尔直至尼采,“存在”纯然变成了意识的构造物,理性主体成为一切存在物的本原和根据。尽管后来从海德格尔到萨特都旨在超越这一主体形而上学叙事逻辑,但他们对形而上学的超越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了某种不彻底性。第一个将对形而上学的颠覆推进到对其所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生活本身的颠覆,并在历史理解的基础上给予主体性问题以重新讨论的是马克思。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但在资本逻辑场域中人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的主体性取代了人的主体性。承继于马克思,随后出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阐释路径:一条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通过历史的运动再度确证人的主体性;另一条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通过转向社会整体结构的研究最终彻底消解了主体。但问题是,这两条路径在面对资本场域中解放主体的生成问题时同时遭遇了解释能力透支的尴尬。卢卡奇最终没能有效说明无产阶级究竟如何才能突破资本主义物化意识以获得革命性的阶级意识,而阿尔都塞则因为过于强调结构的优先性而使革命主体的问题根本无从谈起。
如果说颠覆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能否打破其隐含的主体中心主义逻辑,那么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萨特都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倒是实现了,但他的问题是在“反主体”的道路上走得太过了。正如巴迪欧所指出的,剥离主体的唯心主义属性是可以的,但彻底消灭或者说取消主体在哲学话语秩序中的所有正当性则是矫枉过正。(25)巴迪欧、高歇:《关于共产主义的对话》,蓝江译,《郑州轻工业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后来伴随现象学在法国的复兴,马利翁的新现象学重新引入事件的讨论。他努力涤除胡塞尔现象学中残余的先验主体性叙事,同时又避免走向极端的反主体道路,从而揭示了主体相对于现象的被动性。从反主体中心主义的理论效果来看,马利翁的理论操作与巴迪欧坚持主体悬系于偶然发生事件的被建构性是异曲同工的。不过,由于巴迪欧深入到资本结构化运动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并提供了一种打破资本逻辑结构化操控的主体解放策略,这种历史性使得其事件哲学最终彰显出了超越事件现象学的理论深度。众所周知,现象学从其开端处就旨在“回到事情本身”,但是其反复重申的“回到”仍然只是限于理性思辨之内,丝毫没有触碰到现实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胡塞尔到马利翁,现象学关于意识的讨论始终奠基于一种抽象的理性认识论,意识所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和基础却被遮蔽了。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这意味着哲学的真正基础并不在于观念或意识本身,而是在于社会物质生活,抽象的理性认识论需要以关照现实生活的历史认识论为前提。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历史性理论深度,现象学才会虽然也表现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但始终未能彻底超越形而上学。在这一问题上真正实现变革的是马克思。对此,海德格尔也是看得十分清楚,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他指出:“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27)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全然缺乏历史性视角,问题在于他最终没能穿透理性思辨的迷雾,从“回到事情本身”走向“回到生活本身”,也即从理性规定的历史性走向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即使海德格尔后来落脚于“此在”的历史性,他所论及的“历史性”仍然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意味。针对海德格尔,巴迪欧就曾这样评论到:“哲学直到最近才懂得如何用与资本相称的术语来思考,因为它曾让这个领域最本质的方面去徒劳地怀念神圣的束缚,执迷于在场,服从于诗歌的模糊的统治,怀疑其自身的合法性。它不曾知道如何让思想理解下述事实:即人已经无可逆转地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而这里的问题既不是丧失也不是忘却,而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尽管仍然以计算时间愚蠢的含混性为特点。”(28)Alain Badiou,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58.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将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归结为对存在的遗忘,但关键是他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也是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海德格尔没有看到,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生产与交换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存在”就不再仅仅是哲学反思的抽象对象,而是也获得了具体的历史规定性。与之相对,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同样涉及“存在”,但他没有抽象地对其考察而是指认“存在”就“属于一个情势”。(29)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Continuum, 2005, p.372.其实反观现实不难发现,巴迪欧视域中的“情势”正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结构的一种表征。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分析,在商品交换中人们所关心的并非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能否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价值增殖,商品的价值量又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如果对商品予以追溯的话,它最终落脚于一种对时间量的计算,商品世界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以“数”为特征的一致性结构。正是基于此,巴迪欧后来指认海德格尔没有洞察问题的关键。因为根本就没有超历史的可被抽象言说的“存在”,而只有商品结构中的人与物,一切存在都不过是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
事实上,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不仅跳出纯粹理性思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予以揭示,更重要的是它还为超越资本逻辑的操控提供了主体解放策略。正如同其《存在与事件》的书名所表明的,“事件”是相对应于“存在”而言的,它代表着同客观存在领域的彻底断裂。所谓的“存在”领域指向的正是现实的资本逻辑,它将一切人与物都吞噬于其中,丝毫不允许任何例外发生。面对主体于资本逻辑中的“滑落”,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理论反叛的姿态从未消失,但解放议程的推进却是步履维艰,建构革命主体最后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未竟事业”。比如按照卢卡奇的思路,打破资本逻辑结构化限定的革命机遇被诉诸于普遍的无产阶级,当他们克服资产阶级物化意识获得一种普遍立场(即把握社会总体性),一场普遍性的革命就会爆发。这是一种带有强烈人本主义色彩的内在超越的解放策略,那么显然这一策略将无法面对如下问题: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条件进行着永恒的革命化(齐泽克语),它能够将一切矛盾消解于内部;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摄下,今天工人阶级的反抗性与斗争性不是增强而是日渐衰弱,这表明任何在资本体系内部发动超越资本的革命道路实际上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巴迪欧和齐泽克等激进左派学者必须面对并需要提供解放方案的问题。当巴迪欧赋予“事件”以断裂性内涵并强调一个事件的发生是在任何既定情势内都无法预测的,进而指认在一个事件发生后,个体如若能够忠诚于该事件,其主体身份也就被建构起来了。他所提供的就是一条外在超越的革命之路。这条革命道路奠基于偶然发生的事件,它代表着始终无法被资本结构所消融的“例外”,也即一种纯然的外在性与新奇性。一旦事件与我们发生联系,一种新的可能性便被开启了。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