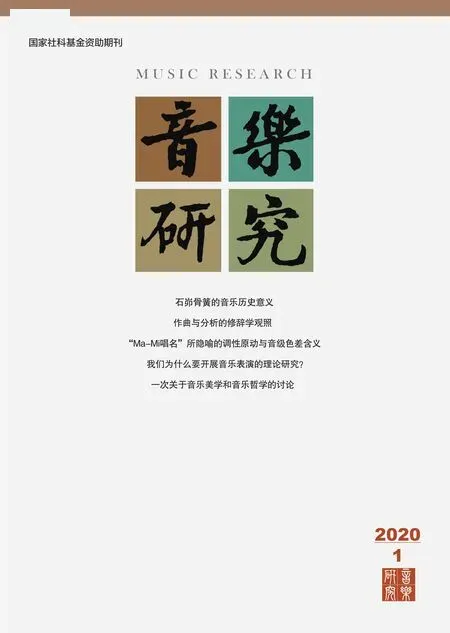论周代“房中之乐”的两种形态及钟磬问题—兼论其与乡乐、燕乐的关系
文 姚苏杰
一、周代“房中之乐”的“名”与“实”
周代“房中之乐”最早见载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的文献中,主要有三条:一是《仪礼·燕礼》“记”所载:“若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①(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457 页。按,《仪礼》诸篇之“记”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认为其产生时代晚于正文。二是《诗经·王风·君子阳阳》“右招我由房”句,《毛传》谓:“国君有房中之乐。”②(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351 页。三是《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时“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③(汉)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67—1468 页。《汉书》接着又全篇引录了当时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班固所说周有“房中乐”,与前引“房中之乐”应是指同一事物,为表述明确,本文统一称“房中之乐”。
有学者认为,上述三种材料“应该是各自独立的,并非递相转述”,即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而《仪礼》《毛传》都出于汉以前,这足以说明,在“周代乐制中确有‘房中乐’这样的名义”④钱志熙《周汉“房中乐”考论》,《文史》2007 年第2 辑,第45—61 页。。今按,《仪礼·燕礼》“记”与《诗经》“毛传”是否出于汉前,目前或难定论,但若说它们代表汉初学者的观点,应该是可以的。加之《汉书》依托官方资料记载汉初的情况,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可以初步推断,西周应该存在“房中之乐”这一音乐形式。
除了上述三条材料外,后世学者所能依据来研究房中之乐的,主要是汉末郑玄的经注。如其《周南召南谱》谓: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终以《麟趾》《驺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兴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获嘉瑞。风之始,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⑤同注②,第6—9 页。
这段话有多处值得注意,它除了陈述《周南》《召南》的古老来源、主体精神、礼乐功用外,还提到了“周公作乐”时对二南诗乐的改造。汉代学者普遍认为,二南经过“周公作乐”才被推广到“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在此过程中其音乐形式也应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此后的二南,已被纳入由周公建立的“宗周礼乐”系统中,成为维系周代社会制度的重要内容。
但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郑玄在此段末尾说“或谓之房中之乐”,即当时“有的人说”或“有一种观点”将二南称为“房中之乐”。这似说明,“房中之乐”在当时还不是一种正式的、主流的称谓。郑玄又在《仪礼·燕礼》“遂歌乡乐”一节注中说:“《周南》《召南》,《国风》篇也。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又在《燕礼》“记”的“有房中之乐”句注说:“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⑥同注①,第431 页。前条材料谓其“房中之乐歌”,这显然是一种描述性的话语,并非一个专名;⑦如同“室内之音乐”与“室内乐”的区别。后条材料又说“谓之房中”,把“房中”单独拿出来解释,也说明“房中之乐”尚未融合成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本文认为,“房中之乐”或“房中乐”应是秦汉以来用于指称周代某类诗乐的别称或俗称。也正因为如此,经典文献中才少见“房中之乐”的提法。⑧比如《诗经》“二南”部分毛序、毛传,虽然时时将其与后妃、夫人联系,但并未使用“房中之乐”这一名称。汉代可能因为高祖《房中祠乐》的影响,此称呼才逐渐流传开来,但似乎仍不被经学家完全接受。
二、周代“燕乐”与郑注的两个矛盾
上文初步判断了房中之乐“名”与“实”的情况,但相关研究尚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未能解决。本文试图对其中两个小问题提出一些更合理的解释:第一是房中之乐有无钟磬的问题;第二是房中之乐与乡乐、燕乐的关系问题。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是互相关联的,其缘起则要从郑玄注说起。《周礼·春官·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郑玄注:
杜子春读缦为怠慢之慢。玄谓缦读为缦锦之缦,谓杂声之和乐者也。《学记》曰:“不学操缦,不能安弦。”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⑨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881—1885 页。
在此段注文中,郑玄先解释何谓“缦乐”,他认为杜子春“怠慢”说不合理,应当理解为“杂声之和乐者”。但他的观点也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按,《说文解字》谓“缦”字本意为“缯无文”,则缦乐也应是指“无文”之乐,即曲调简单舒缓,不事雕琢。郑玄先将缦训为“缦锦”,又用“锦”(用各色丝织成)的意思来解释缦,有增字解经之嫌。而郑注所引《学记》“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是说初学弦乐,当由曲调舒缓的曲子入手练习,这是极合乎情理的。所以有学者认为缦乐并非郑玄所谓杂声合乐,而是指如《周颂》一般的慢乐。⑩王志《古礼考释三则》,《华夏文化论坛》2006 年第1 期,第29—33 页。此说似有理。此外,《学记》既然说“操缦”“安弦”,那么缦乐本来应该是弦乐,或以弦乐为主。而《周礼·磬师》说要教其“钟磬”,又说“凡祭祀,奏缦乐”,这显然是为配合祭祀而作的改变。正是基于这一点,前人便认为文中的“燕乐”也可能是在用于祭祀时发生了变化(此问题后文再详论)。
如果说关于缦乐问题,郑玄可能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他一家之言),那他对于燕乐的说明,则着实让后人费解。他说“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这好像是把燕乐等同于房中之乐了,但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一般所说周代的燕乐,是泛指宴享时所用的一切诗乐。如杨荫浏谓:“最早的‘燕乐’,是指宾客燕饮时所用的音乐而言,是因应用的场合得名的”,⑪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万叶书店1952 年版,第120 页。是“被统治阶级在宴会中间应用的一切音乐”。⑫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3 页。邱琼荪也认为:“这‘燕乐’二字,乃泛指宴享时所设之乐而言,不问它用的是什么乐,既为宴享而设,便称之燕乐。”⑬邱琼荪《燕乐探微》,载《燕乐三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64 页。这些结论基本符合目前所见秦汉文献所反映的情况。周代宴享的场合非常多,除了正常的君臣飨、燕外,在乡饮酒、乡射、大射甚至祭祀等场合,都有附带的宴享环节,其中所用音乐便都可以称为燕乐。《周礼》中记载燕乐被用于祭祀,可能就是指祭享环节使用了这些音乐。⑭也可能存在专门为祭祀而进行的移用或改造。总之,“燕乐”这一称谓的所指是非常宽泛的,它应该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音乐。
清代黄以周曾总结宴享用乐,他说:“乐有六节:一曰‘金奏’,二曰‘升歌’,三曰‘下管笙入’,四曰‘间歌’,五曰‘合乐’,六曰‘无算乐’。”⑮(清)黄以周《礼书通故》,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1795 页。也有学者归纳为正歌四节,如彭林《说乡乐、房中之乐与无筭乐—评〈周代乡乐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7 年03 期,第199—203 页。其中,“金奏”应是指主人迎宾、纳宾时所用的音乐。如《仪礼·燕 礼》“记”中载:“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宾拜酒,主人答拜,而乐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⑯同注①,第452 页。另外,《大射》也有“奏《肆夏》,宾升自西阶”“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东北面献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与《燕礼》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出现在正礼的最开始阶段。《周礼》“鼓人”“钟师”“镈师”也都提到金奏,是钟镈一类打击乐的泛称。燕享、大射中的金奏,应是以金属打击乐为主的器乐,主要目的是规范宾主的行礼动作,无人声歌唱。“升歌”是指宾主及众大夫都基本入席之后,乐工等由西阶进入堂上(“升”),⑰周代行礼之庙寝,前堂后室,堂有台阶,台阶之上为堂上,台阶之下为堂下。参见沈文倬《周代宫室考 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3 期,第37—44 页。在琴瑟的伴奏下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曲。这三曲都出自《诗经·小雅》,歌词主要表达主人对宾客的欢迎与尊敬之情,可谓切合情境。“下管笙入”是指接下来堂下的管乐表演。《燕礼》说“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燕礼》“记”中又说 “升歌《鹿鸣》,下管《新宫》”。⑱同注①,第429、453 页。古人将堂下钟磬陈设之处称“县中”,管乐表演者即位于此处。周代礼乐贵人声,所以升歌在堂上,笙管钟磬在堂下。“下管笙入”环节应是纯器乐表演。⑲按,《南陔》《白华》《华黍》三诗在《诗经》中只保留了题目而没有内容,传统观点认为是歌词亡佚,但现代学者多认为它们在周代就已经是纯器乐了,故没有歌词。《新宫》问题比较复杂,郑玄注说“《新宫》,《小雅》逸篇也”,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宋公享昭子,赋《新宫》”,说明春秋时尚未散逸。也有学者提出《新宫》就是今本《诗经·小雅》中的《斯干》篇,如传为汉代申培所著《诗说》谓《斯干》是“王者落其新宫,史佚美之,赋也”。但这些说法都无法确证,或者《新宫》可以有歌词,但在“笙入”阶段只取其器乐部分。接下来第四环节的“间歌”,就是堂上堂下交替(相间)进行表演。《燕礼》说:“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⑳同注①,第430 页。也就是先由堂上乐工以琴瑟伴奏演唱一曲,再由堂下笙管乐工演奏一曲,如此交替重复三次,故《燕礼》“记”又称为“笙入三成”。这里所歌的《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都是《诗经·小雅》中篇目,其内容多为颂美君子、祝酒祈福之语,很符合宴饮的情境。而《由庚》《崇丘》《由仪》是《诗经》中“有目无辞”(有标题而无歌词)的笙诗,一般认为是纯器乐演奏。第五环节的“合乐”是指多种音乐形式共同进行表演。在宴享场合,就是指堂上琴瑟乐工,堂下笙管钟磬的合奏与合唱(可能还有舞蹈)。《乡饮酒礼》《乡射礼》都说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 南:《鹊巢》《采蘩》《采》”,唯独《燕礼》说“遂歌乡乐(下同)”。这大概是因为乡饮酒礼、乡射礼本属“乡礼”,故其正乐即为乡乐,无需说明;而燕礼有不同等级,故要特别指出“乡乐”。合乐是宴享用乐的高潮阶段,在合乐结束后,“大师告于乐正曰:正歌备”,即标志着宴享的正式乐歌部分已经表演完毕。在宴会的最后阶段,为了达到尽兴的目的,宾主放弃一些过于繁琐的礼节,比较随意地酬酒、饮酒,称为“无算爵”。与此相配合,音乐也不再遵循严格的顺序和终数,宾主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点歌,称为“无算乐”。㉑㉑ 参见彭林《说乡乐、房中之乐与无筭乐—评〈周代乡乐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7 年第3 期,第199—203 页。㉒ 唯《有司彻》(属少牢馈食礼)有无算爵而没有无算乐,可能是因为祭飨场合比较特殊。㉓ 至于乐官未掌握的民间乐曲或私人乐曲能否临时参与表演,就目前材料看尚无法得出任何结论。㉔ 同注①,第358—359 页。《仪礼》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等篇都有无算爵、无算乐的记载。㉒㉑ 参见彭林《说乡乐、房中之乐与无筭乐—评〈周代乡乐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7 年第3 期,第199—203 页。㉒ 唯《有司彻》(属少牢馈食礼)有无算爵而没有无算乐,可能是因为祭飨场合比较特殊。㉓ 至于乐官未掌握的民间乐曲或私人乐曲能否临时参与表演,就目前材料看尚无法得出任何结论。㉔ 同注①,第358—359 页。显而易见,这种“无算乐”的曲目可选范围应该是非常广泛的,可能包含了当时乐官掌握的所有乐曲。㉓㉑ 参见彭林《说乡乐、房中之乐与无筭乐—评〈周代乡乐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7 年第3 期,第199—203 页。㉒ 唯《有司彻》(属少牢馈食礼)有无算爵而没有无算乐,可能是因为祭飨场合比较特殊。㉓ 至于乐官未掌握的民间乐曲或私人乐曲能否临时参与表演,就目前材料看尚无法得出任何结论。㉔ 同注①,第358—359 页。
以上即黄以周所说的六节。实际上,宴享最后还有一个乐节,是宾客告辞时要奏《陔夏》。《乡射礼》说“宾兴,乐正命奏《陔》。宾降及阶,《陔》作”(《乡饮酒礼》基本相同)。㉔㉑ 参见彭林《说乡乐、房中之乐与无筭乐—评〈周代乡乐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7 年第3 期,第199—203 页。㉒ 唯《有司彻》(属少牢馈食礼)有无算爵而没有无算乐,可能是因为祭飨场合比较特殊。㉓ 至于乐官未掌握的民间乐曲或私人乐曲能否临时参与表演,就目前材料看尚无法得出任何结论。㉔ 同注①,第358—359 页。《燕礼》《大射》还记载,宾要取一部分果脯,将之赐给“钟人”以为答谢。可见《陔夏》与宴享开始时的金奏应是同样性质,主要就是钟磬演奏。
综上可见,在周代宴享的不同阶段,其所用音乐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根本不能以一种艺术性质来予以概括。所以郑玄说“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这就显得与文献格格不入:因为《燕礼》说“与四方之宾燕”时“有房中之乐”,即房中之乐只是宴享用乐的一部分,不能等同于燕乐;另外,燕乐的性质也不是“阴声”。这是郑注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重大矛盾。
郑注的第二个矛盾,是关于燕乐与房中之乐是否使用钟磬的问题。《周礼》“磬师”注中郑玄说“二乐皆教其钟磬”,二乐是指缦乐和燕乐。郑玄既然说燕乐就是房中之乐,那么就能得出推论:房中之乐也是有钟磬的。但在《仪礼·燕礼》注中,郑玄却又说房中之乐是“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那么房中之乐到底有没有钟磬呢?㉕㉕ 郑玄《燕礼》注又说“房中之乐歌……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既然合乐,自然应有钟磬,似乎也是自相矛盾。㉖ 可参见注⑨;王福利《房中乐有无“金石”器使用问题新论》,《音乐艺术》2008 年第3 期;李婷婷《周代房中之乐考论—〈诗经〉与器乐研究之一》,《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3 期等文对此也略有梳理。㉗ 同注①,第457 页。㉘ 同注⑨,第1885 页。这一问题引起了后人不断的讨论。㉖㉕ 郑玄《燕礼》注又说“房中之乐歌……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既然合乐,自然应有钟磬,似乎也是自相矛盾。㉖ 可参见注⑨;王福利《房中乐有无“金石”器使用问题新论》,《音乐艺术》2008 年第3 期;李婷婷《周代房中之乐考论—〈诗经〉与器乐研究之一》,《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3 期等文对此也略有梳理。㉗ 同注①,第457 页。㉘ 同注⑨,第1885 页。
以上郑注的两个矛盾,看似根本不可调和,后世学者也因此对郑玄房中之乐说的真实性产生了整体性的质疑。但事实上,古代学者早已注意到郑注的矛盾论述,也尝试予以阐释或调和。如《仪礼注疏》贾公彦疏谓:
(郑)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者,此文承“四方之宾燕”下而云“有”,明四方之宾而有之。知“不用钟磬”者,以其此《二南》本后夫人侍御于君子,用乐师,是本无钟磬。今若改之而用钟磬,当云有房中之奏乐,今直云“有房中之乐”,明依本无钟磬也。若然,案《磬师》云:“教缦乐,燕乐之钟磬。”注云:“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房中乐得有钟磬者,彼据教房中乐,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钟磬也。房中及燕,则无钟磬也。㉗㉕ 郑玄《燕礼》注又说“房中之乐歌……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既然合乐,自然应有钟磬,似乎也是自相矛盾。㉖ 可参见注⑨;王福利《房中乐有无“金石”器使用问题新论》,《音乐艺术》2008 年第3 期;李婷婷《周代房中之乐考论—〈诗经〉与器乐研究之一》,《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3 期等文对此也略有梳理。㉗ 同注①,第457 页。㉘ 同注⑨,第1885 页。
贾疏即认为房中之乐本无钟磬,其用于“四方之宾燕”时也无钟磬,唯有当其用于祭祀时才配上钟磬。这一说法,如果单就这则材料来说是能通的,但如果联系其他材料,此观点也会面临矛盾。因为在《仪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正歌环节需“合乐”二南六曲,郑注也说这是“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而这二南六曲显然是带钟磬的。因为合乐的意思就是堂上堂下诸乐皆作,钟磬就陈设于堂下,不可能单单不用它们。如果我们说用于宴享的音乐就是燕乐,那么这二南六曲当然也属于燕乐了,贾疏怎么还能说“房中及燕,则无钟磬也”呢?
又如孙诒让《周礼正义》引黄以周说:
燕乐自有钟磬,有舞,教于磬师,掌于旄人,通行于祭祀飨食。房中之乐,弦歌二南,郑云“无钟磬之节”者,嫌与乡乐无别也。然既以磬师燕乐当之,不能谓无钟磬矣。但钟磬自在堂下,不在房中,房非设县之所也。《梁书》曰:“周备六代之乐,至秦,余《韶》《房中》而已”。《汉书》亦云“《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之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然则汉之《安世》,即《房中》之遗响也。史但曰“备其箫管”,而不及其他,此即郑“无钟磬”之说也。㉘㉕ 郑玄《燕礼》注又说“房中之乐歌……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既然合乐,自然应有钟磬,似乎也是自相矛盾。㉖ 可参见注⑨;王福利《房中乐有无“金石”器使用问题新论》,《音乐艺术》2008 年第3 期;李婷婷《周代房中之乐考论—〈诗经〉与器乐研究之一》,《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3 期等文对此也略有梳理。㉗ 同注①,第457 页。㉘ 同注⑨,第1885 页。
显然,黄以周不同意郑玄的观点,也不同意贾公彦的说法,他肯定燕乐是有钟磬的。他认为郑玄注《燕礼》时出现了错误,出错的原因是郑玄受了《汉书》的影响。《汉书》只说“备其箫管”,没有提到钟磬,所以郑玄便以为房中之乐应该没有钟磬,以此与“乡乐”进行区别。黄以周的指正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直接说郑注因《汉书》而误,就显得较为主观。
另外,孙诒让自己则认为:
郑《燕礼》注谓房中乐无钟磬,与此注(指《周礼》注)说异。贾氏曲为调停,亦无定说。窃谓房中乐有钟鼓,燕乐有钟磬及钟笙,《诗》《礼》有明文足证。后寝亦具宫县,但乐县自在堂下,黄说得之。《诗》著“由房”之文,亦止云“执簧”,明在房者唯琴瑟簧矣。《燕礼》注说实未晐备,当以此注为正。㉙㉙ 同注⑨,第1885 页。㉚ 王福利《房中乐有无“金石”器使用问题新论》,《音乐艺术》2008 年第3 期,第105—112 页。
孙诒让首先断言房中乐与燕乐都有钟鼓或钟磬,同时也赞同黄以周提出的“钟磬自在堂下,不在房中”之说。但他认为虽然房中不设钟磬,而燕乐奏于房中却也可以有钟磬伴奏,这是用堂下“乐县”(含钟磬)来与房中之乐进行配合。细考其意,孙诒让是区分了“房中乐整体”和“在房中演奏的部分”这两种情形。他认为在房中演奏时确实只有“琴瑟簧”等管弦乐器,郑玄《燕礼》注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故谓房中无钟磬;而《周礼》注是说明房中乐的整体情况,因堂下有“乐县”配合,故谓其有钟磬。所以他认为“《燕礼》注说实未晐 备,当以此注为正”。今按,孙诒让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他认为房中乐需要房中管弦与堂下钟磬相配合,又认为郑注只描述了房中部分,这些推论都没有文献依据。《燕礼》郑注说“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这明显是在说房中乐的整体情况,怎么会只是描述房中奏乐的局部情形呢?
关于房中乐的钟磬问题,今天的学者也提出过一些新的观点。比如王福利《房中乐有无“金石”器使用问题新论》认为:《燕礼》“记”说的是燕礼迎宾、飨宾、宾射之后的情况,即在前几种礼完成之后再“燕宾”的情况,前者在庙,后者在寝;“将《燕礼》及《燕礼记》中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当是‘房中乐’于飨食合乐时用之,有钟磬之节,飨食之后、宾射之后于‘寝’中燕时亦用之,但用弦歌,而‘无钟磬之节’。”㉚㉙ 同注⑨,第1885 页。㉚ 王福利《房中乐有无“金石”器使用问题新论》,《音乐艺术》2008 年第3 期,第105—112 页。今按,周代确有正礼结束之后再行副礼的情况,如《乡饮酒礼》有“明日,宾服乡服以拜赐……乡乐唯欲”的记载(《乡射》亦如此)。但《燕礼》中却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只是在最后一段交代了“公与客燕”的情况,也即国君宴请他国使臣的一些特殊言辞对答。因为这部分内容过于简略,所以《燕礼》“记”就着重补充了宴请他国使臣的主要仪节,其内容大致还按燕礼顺序进行叙述,包括迎宾、纳宾、燕宾、用乐、舞和宾射等各个环节,但它始终没有提到复燕于寝的情况。所以王文提出《燕礼》“有房中之乐”说是针对寝中复燕,这也是没有太多依据的。
总之,目前对上述矛盾的调和意见都不能算太合理,其关键就在于,学者们只注意到郑注关于钟磬问题的矛盾,而没有注意到郑注关于燕乐、房中之乐的矛盾。而后一矛盾或许才是解决钟磬问题的关键。
三、周代房中之乐的两种形态与矛盾的解决
如前文所述,学者普遍以为郑玄是将“燕乐”等同于“房中之乐”。如前引黄以周观点说郑玄“房中之乐……既以磬师燕乐当之,不能谓无钟磬矣”,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郑玄既然已经将房中之乐等同于燕乐,就不能说房中之乐无钟磬了,因为燕乐显然是可以有钟磬的。这里黄以周是将“郑玄认为房中之乐等于燕乐”这一点作为了默认的前提,后世许多学者同样也以此为基础来分析、解决郑玄的矛盾之处。但问题是,郑玄真的认为燕乐等同于房中之乐吗?
本文认为,郑玄说“燕乐,房中之乐”其实并非是将二者等同。实际上,任何稍有礼乐知识的学者都不可能将二者等同。正如前文所述,燕乐与房中之乐在内涵与外延上存在巨大的差别。简单来说就是:房中之乐是比燕乐小的概念。㉛㉛ 这是最简单化的说法,实际上二者所定义的层面不同,不能直接比较。㉜ 好比我们说西方古典音乐可用于学校,那么说“学校音乐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没问题的。但绝不能因为学校音乐中还有中国风音乐,我们就推论出西方古典音乐也应具备中国风。因此就算房中之乐不用钟磬,也不影响我们对燕乐“有钟磬”的判断,正如同西方古典音乐无中国风,不影响我们说学校音乐有中国风。㉝ “镈师”有“掌金奏之鼓”,有点相似,但掌与教不是一事。房中之乐可用于燕礼,所以房中之乐可以归入燕乐,房中之乐的性质也可以传递给燕乐。但这一点不能反过来说。比如燕乐有金奏、合乐等乐节,所以我们说燕乐“有钟磬”,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因此认为隶属于它的房中之乐也必定“有钟磬”,这一性质不能由大往小传递。㉜㉛ 这是最简单化的说法,实际上二者所定义的层面不同,不能直接比较。㉜ 好比我们说西方古典音乐可用于学校,那么说“学校音乐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没问题的。但绝不能因为学校音乐中还有中国风音乐,我们就推论出西方古典音乐也应具备中国风。因此就算房中之乐不用钟磬,也不影响我们对燕乐“有钟磬”的判断,正如同西方古典音乐无中国风,不影响我们说学校音乐有中国风。㉝ “镈师”有“掌金奏之鼓”,有点相似,但掌与教不是一事。
那么郑注说“燕乐,房中之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就需要辨析一下,在古代“甲,乙(也)”这种训诂形式中,甲和乙其实有三种可能的关系:(1)等同关系;(2)“被包含”关系;(3)“包含”关系。“包含关系”型注释在文献中确实不多见,但《诗经》注中却相对较多。
那么,郑玄“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这一句训释中,郑玄其实也是将一个泛指概念落实到了具体所指。如果把郑注翻译一下,应该为:“这里所说的燕乐,是特指我们(后来)所说的房中之乐,也就是所谓阴声。”这就是说,郑玄是特意强调《周礼》“燕乐之钟磬”不是指燕乐整体,而是特指房中之乐。
但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如前文所说,燕乐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且复杂,但《周礼》只单独提到教“燕乐之钟磬”。为什么不说要教“燕乐之琴瑟”或“燕乐之笙管”?又,《周礼·春官》乐师系统所载各职官,要么以乐器为类而各掌其教,如“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要么以乐类为区分而各掌其教的,如“笙师:……教祴乐”,“韎师:掌教韎乐”,“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等。这其中需要教某“乐类”中特定乐器的,就只有“磬师”所说“教缦乐、燕乐之钟磬”,这可以说是一个特例。㉝㉛ 这是最简单化的说法,实际上二者所定义的层面不同,不能直接比较。㉜ 好比我们说西方古典音乐可用于学校,那么说“学校音乐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没问题的。但绝不能因为学校音乐中还有中国风音乐,我们就推论出西方古典音乐也应具备中国风。因此就算房中之乐不用钟磬,也不影响我们对燕乐“有钟磬”的判断,正如同西方古典音乐无中国风,不影响我们说学校音乐有中国风。㉝ “镈师”有“掌金奏之鼓”,有点相似,但掌与教不是一事。郑玄大概因此得出结论:“磬师”教燕乐之钟磬应是一种特殊情形,是特指燕乐中的“房中之乐”。又因为“房中之乐”是女性房中之乐歌,所以又说它是“阴声也”,这也很合理,但郑玄显然并非将燕乐也等于阴声。
那么说到底,房中之乐究竟有没有钟磬呢?理解了上文对郑玄《周礼》注的分析,钟磬问题就有了一个解决思路。其实《仪礼注疏》中贾公彦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假设,他说:“《二南》本后夫人侍御于君子,用乐师,是本无钟磬。……房中乐得有钟磬者,彼据教房中乐,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钟磬也。房中及燕,则无钟磬也。”㉞㉞ 同注①,第457 页。㉟ 贾公彦关于房中之乐“本来形态”与“祭祀形态”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本来形态”包含了“房中及燕”,但燕乐显然有钟磬(金奏、合乐部分),不符合本来形态无钟磬的特点。贾公彦自己应该未能厘清此问题,故在《仪礼注疏·乡饮酒礼》中他说:“用钟鼓奏之者,诸侯、卿、大夫燕飨亦得用之,故用钟鼓。妇人用之,乃不用钟鼓,则谓之房中之乐也。”便与前言自相矛盾。见《仪礼注疏》第230 页。㊱ 同注⑨,第1885 页。㊲ 它们是乡乐的全部,还是乡乐的一部分,尚存 争议。㊳ 可参见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3 期。㊴ 二南、房中之乐、乡乐三者篇目是否完全一致也有争议。㊵ 二者是否为线性发展关系也可存疑,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暂时认为“房中之乐改造为乡乐”。他认为房中之乐“本来”是没有钟磬的,只是在用于祭祀时才有钟磬。这一观点可称为“两种形态假说”:它认为房中乐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本来形态”,另一种是“祭祀形态”。不过,前文曾分析贾公彦的观点有许多问题,㉟㉞ 同注①,第457 页。㉟ 贾公彦关于房中之乐“本来形态”与“祭祀形态”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本来形态”包含了“房中及燕”,但燕乐显然有钟磬(金奏、合乐部分),不符合本来形态无钟磬的特点。贾公彦自己应该未能厘清此问题,故在《仪礼注疏·乡饮酒礼》中他说:“用钟鼓奏之者,诸侯、卿、大夫燕飨亦得用之,故用钟鼓。妇人用之,乃不用钟鼓,则谓之房中之乐也。”便与前言自相矛盾。见《仪礼注疏》第230 页。㊱ 同注⑨,第1885 页。㊲ 它们是乡乐的全部,还是乡乐的一部分,尚存 争议。㊳ 可参见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3 期。㊴ 二南、房中之乐、乡乐三者篇目是否完全一致也有争议。㊵ 二者是否为线性发展关系也可存疑,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暂时认为“房中之乐改造为乡乐”。但他提出房中之乐可能存在多种变化形式,这一点很有启发性。
周代诗乐确实可能存在多种形式的变化。如汉代学者认为宗周礼乐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结果,当时很多诗乐在进入礼乐系统时都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造。前引郑玄《周南召南谱》就说:“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正因为这种变化,所以即使是同一类诗乐,在礼乐系统中也可以存在多种互有差异的形式。孙诒让说:“祭飨无无算乐,则唯合乐时奏之,虽与乡乐同用二南,而其音节当小异也。”㊱㉞ 同注①,第457 页。㉟ 贾公彦关于房中之乐“本来形态”与“祭祀形态”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本来形态”包含了“房中及燕”,但燕乐显然有钟磬(金奏、合乐部分),不符合本来形态无钟磬的特点。贾公彦自己应该未能厘清此问题,故在《仪礼注疏·乡饮酒礼》中他说:“用钟鼓奏之者,诸侯、卿、大夫燕飨亦得用之,故用钟鼓。妇人用之,乃不用钟鼓,则谓之房中之乐也。”便与前言自相矛盾。见《仪礼注疏》第230 页。㊱ 同注⑨,第1885 页。㊲ 它们是乡乐的全部,还是乡乐的一部分,尚存 争议。㊳ 可参见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3 期。㊴ 二南、房中之乐、乡乐三者篇目是否完全一致也有争议。㊵ 二者是否为线性发展关系也可存疑,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暂时认为“房中之乐改造为乡乐”。所谓音节之小异,就可以说是属于不同的形态。
因此本文提出,房中之乐在周代礼乐系统中(至少)存在这样两种主要形态的对立。今据文献常见称谓,将其命名为“本来形态”与“乡乐形态”。“乡乐”是指《仪礼》诸礼在宴享合乐阶段所歌的二南六曲,即《周南》之《关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鹊巢》《采蘩》《采》。㊲㉞ 同注①,第457 页。㉟ 贾公彦关于房中之乐“本来形态”与“祭祀形态”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本来形态”包含了“房中及燕”,但燕乐显然有钟磬(金奏、合乐部分),不符合本来形态无钟磬的特点。贾公彦自己应该未能厘清此问题,故在《仪礼注疏·乡饮酒礼》中他说:“用钟鼓奏之者,诸侯、卿、大夫燕飨亦得用之,故用钟鼓。妇人用之,乃不用钟鼓,则谓之房中之乐也。”便与前言自相矛盾。见《仪礼注疏》第230 页。㊱ 同注⑨,第1885 页。㊲ 它们是乡乐的全部,还是乡乐的一部分,尚存 争议。㊳ 可参见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3 期。㊴ 二南、房中之乐、乡乐三者篇目是否完全一致也有争议。㊵ 二者是否为线性发展关系也可存疑,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暂时认为“房中之乐改造为乡乐”。与“燕乐”这一概念之宽泛且含混不同,“乡乐”是当时已有的概念。《燕礼》有“遂歌乡乐”“遂合乡乐”,《乡饮酒礼》《乡射礼》也有“乡乐唯欲”,可见“乡乐”是一个相对明确的乐类,它在周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㊳㉞ 同注①,第457 页。㉟ 贾公彦关于房中之乐“本来形态”与“祭祀形态”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本来形态”包含了“房中及燕”,但燕乐显然有钟磬(金奏、合乐部分),不符合本来形态无钟磬的特点。贾公彦自己应该未能厘清此问题,故在《仪礼注疏·乡饮酒礼》中他说:“用钟鼓奏之者,诸侯、卿、大夫燕飨亦得用之,故用钟鼓。妇人用之,乃不用钟鼓,则谓之房中之乐也。”便与前言自相矛盾。见《仪礼注疏》第230 页。㊱ 同注⑨,第1885 页。㊲ 它们是乡乐的全部,还是乡乐的一部分,尚存 争议。㊳ 可参见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3 期。㊴ 二南、房中之乐、乡乐三者篇目是否完全一致也有争议。㊵ 二者是否为线性发展关系也可存疑,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暂时认为“房中之乐改造为乡乐”。但有学者认为乡乐就是房中之乐,这一说法似是而非。乡乐虽然与房中之乐一样采用二南诗乐,㊴㉞ 同注①,第457 页。㉟ 贾公彦关于房中之乐“本来形态”与“祭祀形态”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本来形态”包含了“房中及燕”,但燕乐显然有钟磬(金奏、合乐部分),不符合本来形态无钟磬的特点。贾公彦自己应该未能厘清此问题,故在《仪礼注疏·乡饮酒礼》中他说:“用钟鼓奏之者,诸侯、卿、大夫燕飨亦得用之,故用钟鼓。妇人用之,乃不用钟鼓,则谓之房中之乐也。”便与前言自相矛盾。见《仪礼注疏》第230 页。㊱ 同注⑨,第1885 页。㊲ 它们是乡乐的全部,还是乡乐的一部分,尚存 争议。㊳ 可参见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3 期。㊴ 二南、房中之乐、乡乐三者篇目是否完全一致也有争议。㊵ 二者是否为线性发展关系也可存疑,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暂时认为“房中之乐改造为乡乐”。但应该是它改造后的形态。㊵㉞ 同注①,第457 页。㉟ 贾公彦关于房中之乐“本来形态”与“祭祀形态”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所谓的“本来形态”包含了“房中及燕”,但燕乐显然有钟磬(金奏、合乐部分),不符合本来形态无钟磬的特点。贾公彦自己应该未能厘清此问题,故在《仪礼注疏·乡饮酒礼》中他说:“用钟鼓奏之者,诸侯、卿、大夫燕飨亦得用之,故用钟鼓。妇人用之,乃不用钟鼓,则谓之房中之乐也。”便与前言自相矛盾。见《仪礼注疏》第230 页。㊱ 同注⑨,第1885 页。㊲ 它们是乡乐的全部,还是乡乐的一部分,尚存 争议。㊳ 可参见傅道彬《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3 期。㊴ 二南、房中之乐、乡乐三者篇目是否完全一致也有争议。㊵ 二者是否为线性发展关系也可存疑,但为了简化问题,本文暂时认为“房中之乐改造为乡乐”。按汉儒的说法,这种改造应由“周公作乐”完成,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总之,简单说来,当房中之乐用于“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或“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等场景时,这属于它最原初的乐用环境,此时它的音乐形式应是琴瑟伴歌而无钟磬的“本来形态”。而当置于“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的宴享合乐环节时,它的音乐形式是人声、琴瑟、笙管和钟磬的合奏,这是房中之乐的“乡乐形态”。
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郑玄一定要指出《燕礼》“记”中记载的“房中之乐”是它无钟磬的“本来形态”呢?这应是郑玄将《燕礼》“记”的补充看作是“无算乐”阶段的用乐了。仔细分析文本可发现:首先,《燕礼》“记”在补充交代完所有“与四方之宾燕”的仪节之后,最末才说“有房中之乐”,从叙述顺序上就比较符合无算乐出场的顺序;其次,《燕礼》正文中已经使用了房中之乐的“乡乐形态”(所谓“遂合乡乐”),那么燕礼中有房中之乐本就毫无疑问,“记”部分的补充还有何意义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记”中所说的房中之乐与正文的乡乐有区别,它是特指采用房中之乐的“本来形态”,所以郑玄才要专门注明。用房中之乐的“本来形态”应是周代“与四方之宾燕”的特殊仪节,这也正是《燕礼》“记”所要补充的重点。
反过来说,既然《燕礼》“与四方之宾燕”的无算乐阶段可用“本来形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普通燕礼的无算乐阶段,便不用“本来形态”的呢?这是很有可能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的无算乐阶段就只说“乡乐唯欲”,似乎只能选择乡乐。而《燕礼》无算乐的一般情况文献虽未载,但如果说在“与四方之宾燕”时增加一些特殊音乐,用以表示对他国来宾的一种特别尊重或亲昵之情,这也是符合情理的。正如《燕礼》“记”还说到此时“有内羞”,内羞就是“房中之羞”,一般由地位高的主妇或宰夫来进献,而相对一般的“庶羞”则由司士进献。《仪礼·有司彻》即谓:“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妇,内羞在右,庶羞在左。”㊶㊶ 同注①,第1573—1574 页。㊷ 按,房中之乐的这一特性,实际与“缦乐”有点相似。《燕礼》注中郑玄反对杜子春以“怠慢”训缦乐,但杜子春可能是将缦乐理解为一种私昵而不庄重的音乐,这与房中之乐有点接近。贾谊《贾子新书·官人》篇说:“清晨听治,罢朝而论议,从容泽燕。夕时开北房,从薰服之乐。”(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884 页引)其中的“薰服之乐”就是一种专用于享受的私昵之乐,而学者亦多将其与房中乐对应。㊸ 对房中之乐的表演者、使用者、欣赏者的性别,汉人经注说得也不是很清楚,大概以女性为主。㊹ 古人认为“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隋书·音乐志》),此外还因为“古者堂后左房右室,钟磬簴难以移入房”(元敖继公《仪礼集说·房中之乐》),这或是它本无钟磬的客观原因。㊺ 其他声乐、器乐形式也都可能发生了转变,合乐的二南六曲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其“合乐”的表演方式,融合了弦乐(琴瑟)、管乐(笙箫)、金奏(钟磬)、人声等多重样式,可称周代礼乐之典范。其实在其他祭祀、燕享场合,由主妇于房中进献的祭品、食品,也往往具有一种特殊的尊贵性。这大概是因为房中之乐、房中之羞都是主人夫妇私昵之物,能把它们拿出来与宾客共享,则更显一种礼遇之情。而客观来说,主人夫妇私下享用的音乐,也肯定比正礼上使用的典雅庄重但略显刻板的音乐更加动听,更能娱乐宾客,也更适用于无算乐环节之“尽欢”需求。㊷㊶ 同注①,第1573—1574 页。㊷ 按,房中之乐的这一特性,实际与“缦乐”有点相似。《燕礼》注中郑玄反对杜子春以“怠慢”训缦乐,但杜子春可能是将缦乐理解为一种私昵而不庄重的音乐,这与房中之乐有点接近。贾谊《贾子新书·官人》篇说:“清晨听治,罢朝而论议,从容泽燕。夕时开北房,从薰服之乐。”(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884 页引)其中的“薰服之乐”就是一种专用于享受的私昵之乐,而学者亦多将其与房中乐对应。㊸ 对房中之乐的表演者、使用者、欣赏者的性别,汉人经注说得也不是很清楚,大概以女性为主。㊹ 古人认为“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隋书·音乐志》),此外还因为“古者堂后左房右室,钟磬簴难以移入房”(元敖继公《仪礼集说·房中之乐》),这或是它本无钟磬的客观原因。㊺ 其他声乐、器乐形式也都可能发生了转变,合乐的二南六曲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其“合乐”的表演方式,融合了弦乐(琴瑟)、管乐(笙箫)、金奏(钟磬)、人声等多重样式,可称周代礼乐之典范。
结 论
“房中之乐”的来源十分古老,在周代礼乐的演变中,它也经历了各种变化。但新形式的产生并不妨碍旧形式继续存在,或者新旧形式会各自发展,从而形成两种或多种形态的共存。
根据汉代经注,房中之乐本是与女性相关的诗乐,㊸㊶ 同注①,第1573—1574 页。㊷ 按,房中之乐的这一特性,实际与“缦乐”有点相似。《燕礼》注中郑玄反对杜子春以“怠慢”训缦乐,但杜子春可能是将缦乐理解为一种私昵而不庄重的音乐,这与房中之乐有点接近。贾谊《贾子新书·官人》篇说:“清晨听治,罢朝而论议,从容泽燕。夕时开北房,从薰服之乐。”(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884 页引)其中的“薰服之乐”就是一种专用于享受的私昵之乐,而学者亦多将其与房中乐对应。㊸ 对房中之乐的表演者、使用者、欣赏者的性别,汉人经注说得也不是很清楚,大概以女性为主。㊹ 古人认为“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隋书·音乐志》),此外还因为“古者堂后左房右室,钟磬簴难以移入房”(元敖继公《仪礼集说·房中之乐》),这或是它本无钟磬的客观原因。㊺ 其他声乐、器乐形式也都可能发生了转变,合乐的二南六曲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其“合乐”的表演方式,融合了弦乐(琴瑟)、管乐(笙箫)、金奏(钟磬)、人声等多重样式,可称周代礼乐之典范。以琴瑟伴奏配人声演唱,适合在房中表演。郑玄说是“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也好,说“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也好,虽然未必就是周代实情,但其与女性有关则是可信的。这是房中之乐无钟磬的“本来形态”。㊹㊶ 同注①,第1573—1574 页。㊷ 按,房中之乐的这一特性,实际与“缦乐”有点相似。《燕礼》注中郑玄反对杜子春以“怠慢”训缦乐,但杜子春可能是将缦乐理解为一种私昵而不庄重的音乐,这与房中之乐有点接近。贾谊《贾子新书·官人》篇说:“清晨听治,罢朝而论议,从容泽燕。夕时开北房,从薰服之乐。”(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884 页引)其中的“薰服之乐”就是一种专用于享受的私昵之乐,而学者亦多将其与房中乐对应。㊸ 对房中之乐的表演者、使用者、欣赏者的性别,汉人经注说得也不是很清楚,大概以女性为主。㊹ 古人认为“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隋书·音乐志》),此外还因为“古者堂后左房右室,钟磬簴难以移入房”(元敖继公《仪礼集说·房中之乐》),这或是它本无钟磬的客观原因。㊺ 其他声乐、器乐形式也都可能发生了转变,合乐的二南六曲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其“合乐”的表演方式,融合了弦乐(琴瑟)、管乐(笙箫)、金奏(钟磬)、人声等多重样式,可称周代礼乐之典范。当房中之乐被吸纳入周代礼乐体系时(“周公作乐”),它经过一定的改造,变成了“乡乐”(或其一部分),其中明显变化就是增加了钟磬。㊺㊶ 同注①,第1573—1574 页。㊷ 按,房中之乐的这一特性,实际与“缦乐”有点相似。《燕礼》注中郑玄反对杜子春以“怠慢”训缦乐,但杜子春可能是将缦乐理解为一种私昵而不庄重的音乐,这与房中之乐有点接近。贾谊《贾子新书·官人》篇说:“清晨听治,罢朝而论议,从容泽燕。夕时开北房,从薰服之乐。”(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884 页引)其中的“薰服之乐”就是一种专用于享受的私昵之乐,而学者亦多将其与房中乐对应。㊸ 对房中之乐的表演者、使用者、欣赏者的性别,汉人经注说得也不是很清楚,大概以女性为主。㊹ 古人认为“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隋书·音乐志》),此外还因为“古者堂后左房右室,钟磬簴难以移入房”(元敖继公《仪礼集说·房中之乐》),这或是它本无钟磬的客观原因。㊺ 其他声乐、器乐形式也都可能发生了转变,合乐的二南六曲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其“合乐”的表演方式,融合了弦乐(琴瑟)、管乐(笙箫)、金奏(钟磬)、人声等多重样式,可称周代礼乐之典范。这就是房中之乐变化之后的“乡乐形态”。周代“乡乐”既用于宴享正歌,也用于无算乐,其表演形式或略有差别,但有钟磬则是相同的。与此同时,在某些特殊场合,房中之乐的“本来形态”也可以出现,比如《燕礼》“记”所记载的情况:当“与四方之宾燕”时,在最后无算乐阶段,允许宾主要求房中之乐“本来形态”的表演,以此体现一种特殊的礼遇。
当然,房中之乐可能不止有“乡乐”这一种变形,但就目前文献来说,其他形式还缺少确凿的证据。所以本文仅以“本来形态”和“乡乐形态”两者的对立,来解释前述文献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最后做一简单总结如下:
(1)房中之乐“本来形态”:弦歌无钟磬,主要用于房中,㊻㊻ 如用于夫妇房中之日常休闲娱乐,或用于女性房中之行礼,相关问题拟撰文另述。㊼ 这种意义下的“燕乐”就比较狭义,应指专为燕享而创作或改造的、主要用于燕享各环节的音乐。㊽ “与四方之宾”的燕礼当然也有正歌合乐的环节,这时房中之乐以其乡乐形态出现,所以郑玄《燕礼》注才说“房中之乐歌……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这里就不是郑玄的自相矛盾。特殊情况下可用于燕礼无算乐阶段。郑玄注《燕礼》“有房中之乐”句谓“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说的就是这种“本来形态”。这种形态的房中之乐虽然用于燕礼(因此可归入广义的燕乐),但实际上是一种“借用”。
(2)房中之乐“乡乐形态”:有管弦钟磬的配合,广泛用于诸礼宴享正歌及无算乐阶段。郑玄注《周礼》“燕乐之钟磬”句谓“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说的是这种“乡乐形态”。这种形态的房中之乐,实际上就是为配合诸礼燕享而专门做的改造,因此也可称“燕乐形态”。㊼㊻ 如用于夫妇房中之日常休闲娱乐,或用于女性房中之行礼,相关问题拟撰文另述。㊼ 这种意义下的“燕乐”就比较狭义,应指专为燕享而创作或改造的、主要用于燕享各环节的音乐。㊽ “与四方之宾”的燕礼当然也有正歌合乐的环节,这时房中之乐以其乡乐形态出现,所以郑玄《燕礼》注才说“房中之乐歌……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这里就不是郑玄的自相矛盾。
由此我们就可以厘清文献中出现的房中之乐、乡乐、燕乐之间的复杂关系,图示如下:
至此,郑玄注中的两个矛盾都可以得到解释。《燕礼》记“有房中之乐”,这是指房中之乐以其“本来形态”用于“与四方之宾”燕礼的无算乐环节,㊽㊻ 如用于夫妇房中之日常休闲娱乐,或用于女性房中之行礼,相关问题拟撰文另述。㊼ 这种意义下的“燕乐”就比较狭义,应指专为燕享而创作或改造的、主要用于燕享各环节的音乐。㊽ “与四方之宾”的燕礼当然也有正歌合乐的环节,这时房中之乐以其乡乐形态出现,所以郑玄《燕礼》注才说“房中之乐歌……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这里就不是郑玄的自相矛盾。故而郑玄注说“不用钟磬之节也”。这实际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形,所以郑玄要特别指出。而《周礼·春官·磬师》“教……燕乐之钟磬”,郑玄注只说“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这是因为此处“燕乐”特指房中之乐以其“乡乐形态”用于宴享正歌环节,这是周代燕礼最常见的用乐方式,所以郑玄便不再注明。
由于“房中之乐”这一称谓并非正式名称,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笼统性,所以汉末郑玄也不一定能够明确将其与别的礼乐概念进行精确区分。但联系诸条材料,将房中之乐理解为两种形态“共存而同名”,似是解决目前矛盾的最佳假设,有其合理性。当然,房中之乐很可能还存在其他变化形态,比如当其用于祭祀或诗教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