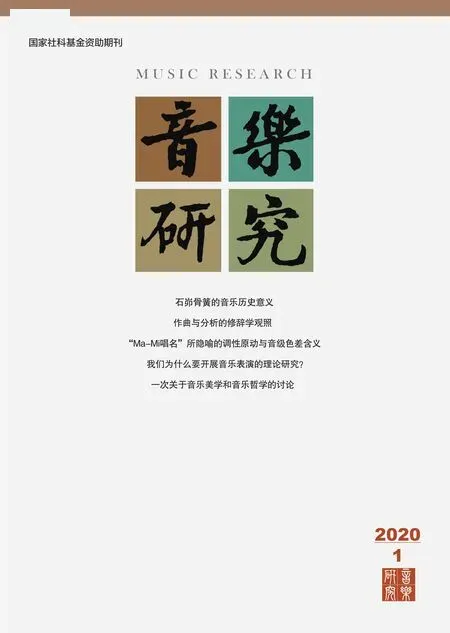纯音乐与标题音乐的历史论争
文 孙胜华
一
浪漫主义时期,标题音乐成为当之无愧的热潮,众多作曲家投身其中,寻求音乐与文学的共振,追求“具体内容”的音乐表达。作为一种“新鲜物”,它的出现一方面受到追捧,另一方面又引发巨大 争议。
“纯音乐”一词实际出自瓦格纳,其意在承继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末乐章中打破纯音乐界线,将器乐与声乐结合,而为自己的乐剧理论证言。纯音乐代表人物是汉斯立克,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著作《论音乐的美》中,其极端的形式主义,同样引来巨大争论。
由于标题音乐具有成熟的美学观念、显在的史学现象与相应的音乐创作,关于它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仅列举重要论著,尼克《近四个世纪的标题音乐:音乐意义的历史文稿》(1901)、奥雷《标题音乐概览:从16 世纪至今》(1973)、卡斯勒《标题交响音乐与它的文学来源》(2001),以及克雷格尔新近出版的《标题音乐》(2015)。应该说,纯音乐不像标题音乐那样“高光”,早期研究多以汉斯立克的美学思想为主。近年,关于纯音乐观念的学术研究才开始“发酵”。如达尔豪斯《纯音乐的观念》①Carl Dahlhaus, The Idea of Absolute Music, Eng. Trans. by Roger Lusti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将它作为浪漫主义音乐美学的统一基础,邦兹《纯音乐:一种观念史》②Mark Evan Bonds, Absolute Music: the History of an Ide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探讨了它在整个西方音乐美学史中的流变。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深入阐述了纯音乐与标题音乐的历史内涵、发展脉络。但是,一方面,上述研究各自为战,总体侧重某一方,没有在整个历史语境中探析二者对立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无论是标题音乐,还是纯音乐,都不是单向度的范畴,而是融美学观念、史学现象、音乐创作于一体。然而,这些研究,尤其是对纯音乐的研究,偏重于美学向度。
美学上,纯音乐与标题音乐以形式主义与内容美学尖锐对立;史学上,它是交响曲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发展分歧。因而,论争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 世纪30—40 年代,是论争的萌发期,论争主要围绕“交响曲危机”“柏辽兹的标题交响曲”进行。贝多芬去世后,传统交响曲陷入危机,这不仅体现在浪漫主义初期门德尔松、舒曼等作曲家的交响曲创作困境中,而且反映在当时的各类音乐评论中。柏辽兹于19 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两部标题交响曲《幻想交响曲》和《哈罗尔德在意大利》问世,引起音乐界的轩然大波。一方面,它们成为标题音乐的引领和理论基础。众多作曲家热情歌颂其创新,努力追随这一创作潮流。50 年代,李斯特正是以后者为论述对象,发表了《柏辽兹与他的〈哈罗尔德交响曲〉》,③〔匈〕弗朗茨·李斯特著,张洪岛、张洪模、张宁译《李斯特论柏辽兹与舒曼》,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阐发标题音乐论纲。另一方面,门德尔松、费蒂斯(Francois-Joseph Fétis)等予以批评,乃至抨击。舒曼虽赞扬其音乐创新,却视标题文字为“怪癖”。④参见〔德〕罗伯特·舒曼著,古·杨森编,陈登颐译《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 年版,第56—82 页。论争大幕由此拉开。
第二阶段,19 世纪50—70 年代,论争达到鼎盛时期。纯音乐与标题音乐各方阵营清晰、立场鲜明,前者以汉斯立克与勃拉姆斯为代表,后者以柏辽兹、李斯特和瓦格纳为主。他们以美学论述宣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创作观念,以评论维护自我立场、攻击对方要害,以音乐创作予以支持、佐证。50 年代,李斯特在魏玛建立起自诩的“新雅典”,意图再现古希腊音乐与文学的融合、繁荣。他指挥瓦格纳歌剧演出,写下《瓦格纳的〈罗恩格林〉与〈唐豪塞〉》(1851),为标题音乐理论与交响诗创作铺路。1855 年,他发表文章《柏辽兹和他的〈哈罗尔德交响曲〉》,明确阐述自己的标题音乐理论。19 世纪50 年代,李斯特创作了十二首交响诗,以践行标题音乐主张。瓦格纳于1850 年前后在著作《艺术与革命》(1849)、《未来的艺术品》(1849)和《歌剧与戏剧》(1851)中充分阐述了“综合艺术”理论。1857 年在论文《论弗朗兹·李斯特的交响诗》中竭力为李斯特的标题音乐辩护。60 年代,瓦格纳相继完成《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65)与《尼伯龙根的指环》(1869)等乐剧,开始点燃浪漫主义晚期“瓦格纳主义”的狂热。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纯音乐维护者大肆批评标题音乐,但是,传统交响曲的创作困境使他们缺乏牢固的实践基础。1853年,舒曼发表《新的道路》⑤此文英文版参见Jam Swafford,Johannes Brahms: A Biography,Vintage Books,1997,pp.85-86;中译文参见注④,第129—131 页。一文,指出勃拉姆斯将开拓出一条传统交响曲的新路,纯音乐开始改变其保守、弱势地位。1854 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首版发行(此后再版九次),纯音乐找到了自己的美学宣言。此后,汉斯立克的音乐评论从“形式”角度,热情赞扬勃拉姆斯,极力批评李斯特与瓦格纳等,纯音乐逐渐占据舆论制高点。⑥参见Eduard Hanslick, Vienna's Golden Years 1850-1900, trans. Henry Pleasants,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50.
1859 年,布伦德尔在《新音乐报》二十五周年庆典大会上,将柏辽兹、李斯特和瓦格纳等冠以“新德意志乐派”之名,使之比肩巴赫、贝多芬等“老德意志乐派”。勃拉姆斯等作曲家随即发表《宣言》,反对此提议。可以说,“宣言事件”标志着双方阵营的正式形成。70 年代,随着前两部交响曲瓜熟蒂落,勃拉姆斯“贝多芬继承人”的称号已实至名归。1877 年,彪罗将勃拉姆斯与巴赫、贝多芬并称为“3B”,双方对立达到顶点。
第三阶段,19 世纪70 年代以后,论争逐渐偃旗息鼓。勃拉姆斯后两部交响曲继续提升其“古典继承者”的声誉,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诗延伸着标题音乐的创作观念。各自创作路径仍在延续,但显然,随着时间流逝,历史已经铭记双方贡献,论争双方也开始相互赞许。更为重要的是,交响曲迎来了它的“第二黄金期”。布鲁克纳、马勒的交响曲受到双方的共同影响,柴科夫斯基、西贝柳斯和德沃夏克等汲取民族基质,他们与勃拉姆斯一道将交响曲再次推向辉煌。这既回应了浪漫主义初期的交响曲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纯音乐与标题音乐的论争。叶的德国古典哲学。前者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后者可从黑格尔“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中找到理论出处。无论是“形式论”还是“情感论”,其源流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⑦关于“形式论”与“情感论”的哲学渊源可参见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但是,就音乐本身而言,如何继承贝多芬的伟大艺术成就,尤其是交响曲遗产,是标题音乐与纯音乐论争的史学根源。克雷格尔论述道:“标题音乐发展于对待贝多芬遗产和音乐未来方向这一问题的迫切需要,尤其表现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诞生之后。交响康塔塔(门德尔松)、标题交响曲(柏辽兹)、交响诗(李斯特)相继出现,所有这些新体裁以贝多芬音乐为范式,又进一步挑战形式与内容的传统观念,从而凸显了一个舒曼提到的交响曲危机问题、一个价值评判问题”⑧Jonathan Kregor, Program Mus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p. 3.。也就是说,论争来自交响曲的发展分歧和对音乐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认知。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即贝多芬去世之后,交响曲发展陷入困境。贝多芬交响曲的伟大成就为浪漫主义作曲家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随着其影响愈大,听众对新交响曲的愈发期待,传统交响曲的危机或者说焦虑就益深。实际上,此时的新交响曲数量庞大,但少有优秀者,更毋宁说比肩贝多芬。一位评论者论述道:“自贝
二
浪漫主义时期,标题音乐的兴盛及其引发的论争具有多种背景。标题音乐的勃兴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密不可分。作曲家不仅借鉴文学叙事结构,表现文学思想内容,而且汲取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浪漫精神,推动音乐与文学的融合。标题音乐与纯音乐的美学论争集中于“形式论”与“情感论”的对立,二者皆直接渊源于18 世纪下半多芬以来,交响曲是否取得进步?这种体裁是否在形式上有所扩展?其内容是否像贝多芬之于莫扎特一样更加宏大、更具意义?所有这些—包括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的创作,他们主观上认为具有新意,且意义重大—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是没有。”⑨Walter Frisch, Brahms: The Four Symphonies, New York: Schirmer, 1996, p. 1.于是,舒曼评论柏辽兹《幻想交响曲》时指出,有理由相信,交响曲的活力已经不再;瓦格纳在《未来的艺术品》中直言,贝多芬写完了最后一部交响曲。
无论是门德尔松、舒曼,还是李斯特、瓦格纳,都曾对传统交响曲创作做出过努力。门德尔松的交响曲大体创作于19 世纪30 年代,但他自我怀疑、不断修改,甚至不愿出版。舒曼对于交响曲创作小心翼翼,迟迟不愿涉足。约1830 年,李斯特计划创作《“革命”交响曲》,但搁置二十年之久,最后变身为交响诗《英雄的葬礼》。1832年,瓦格纳创作了《C 大调交响曲》,但迅速放弃这一体裁,转向歌剧。前两位虽也投身标题音乐创作,如门德尔松的标题性序曲、舒曼的钢琴套曲,但他们在传统交响曲领域苦苦挣扎、坚持,最后把希望寄托于勃拉姆斯。后两位在贝多芬第六、第九交响曲及戏剧配乐中看到了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未来方向,并在柏辽兹的感召下,走向了标题音乐与“综合艺术”。这种分歧已经拉开了纯音乐与标题音乐世纪论争的大幕。
应该说,1830 年柏辽兹《幻想交响曲》的上演标志着论争的开端。作为法国人,柏辽兹没有继承德奥交响曲传统的巨大压力;作为医学出身的作曲家,他也没有超越贝多芬的强大动力。这部标题交响曲的诞生,源于“贝多芬运动”和“莎士比亚运动”的双重影响,源于他对音乐与文学的双重痴迷。历史资料表明,19 世纪20 年代末,阿伯内克(Francois Antoine Habeneck)将贝多芬交响曲引入巴黎,深刻影响着这位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而柏辽兹因为喜爱莎士比亚戏剧,进而疯狂追求饰演“莎剧”的女主角史密逊(Harriet Smithson),这已是音乐史中的著名事件。《幻想交响曲》引发的争论和深远影响,既令柏辽兹始料未及,也需学界研究者细细思量。乐曲、乐章标题与文字说明的创作方式,犹如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巨石,激起轩然大波。批评声不绝于耳,比如,门德尔松认为作品没有表达任何内容,除了彻底的贫乏和冷漠,还有无处不在的咕哝、咯吱、尖叫。⑩R. Larry Todd, Mendelssohn: A Life in Mus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9.赞叹声更为喧嚣,它被标题音乐者视为“圭臬”。他们坚信,柏辽兹开辟了一条交响曲发展的新路。
如果说柏辽兹的标题交响曲并非有意回应“交响曲危机”,那么,李斯特、瓦格纳清醒地以理论与实践宣示自己沿着贝多芬的道路前行。李斯特在《柏辽兹和他的〈哈罗尔德交响曲〉》中阐述自己的标题理论时,明确指出交响诗的前身是交响曲,尤其是贝多芬交响曲。瓦格纳在《未来的艺术品》中,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音乐与文学的结合视为“未来艺术的福音”“未来的完美艺术”。19 世纪50 年代,李斯特以十二部交响诗等作品意欲在魏玛建立一个19 世纪的“新雅典”;六七十年代,瓦格纳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乐剧开始在拜罗伊德构筑自己的朝圣之所。此时,标题音乐声名赫赫,从者如云。至少于标题音乐者而言,它已经成为交响曲发展的一种替代。1859 年,布伦德尔将之命名为“新德意志乐派”,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承继、替代关系。
与此同时,标题音乐的创作与观念遭到巨大非议。一方面,他们批评“新德意志乐派”的相关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对标题音乐者自诩为“贝多芬继承者”“未来音乐的方向”更为反感。正是这种批评与反对构成了纯音乐的历史土壤。由于门德尔松、舒曼等在传统交响曲创作上的“艰涩”,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纯音乐的声音几乎被标题音乐所淹没。除了零散评论外,纯音乐基本处于压抑、积蓄阶段。直至50 年代,随着汉斯立克的评论、美学思想与勃拉姆斯交响曲创作的相继出现,纯音乐才真正浮出历史水面,与标题音乐分庭抗礼。
汉斯立克的音乐评论紧紧抓住形式问题,猛烈抨击标题音乐的形式缺乏。在著作《论音乐的美》中,他将“情感内容”剔除,把“纯粹、自足的形式”本身抽象为音乐本质。美学层面,这是“形式论”与“情感论”的对决。不过,汉斯立克的美学仍然基于器乐创作。贝多芬的器乐作品是他批评标题音乐的历史尺度,勃拉姆斯则是他的现时范型。
勃拉姆斯可谓纯音乐与标题音乐对立的中心人物。早年逃离李斯特转向舒曼,“宣言事件”,他与约阿希姆、彪罗的关系,⑪约阿希姆原是李斯特的学生,但遇到勃拉姆斯后,他离开李斯特,与勃拉姆斯成为知己。彪罗原为李斯特女婿,妻子转嫁瓦格纳后,他转而支持勃拉姆斯。晚年“勃拉姆斯阵营”与“瓦格纳阵营”的形成,这些事件与创作一道真切地反映了世纪论争的起起落落,而贯穿此中的仍是交响曲发展问题。
1853 年,舒曼发表《新的道路》一文,把年轻的勃拉姆斯推向这场论争的风口浪尖。某种意义上,舒曼将三四十年代的交响曲危机转嫁给了勃拉姆斯。自此,勃拉姆斯背负起巨大的交响曲创作压力。他坦言,“我将不再写作交响曲!你不知道,当他总是听到一个巨人的脚步在背后响起,这是多么令人气馁啊!”在当时标题音乐盛行的情况下,这既表明贝多芬交响曲之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压力,也从侧面反映了勃拉姆斯将走一条不同于标题音乐的交响曲创作道路。从夭折的《d 小调交响曲》(后改为《第一钢琴协奏曲》)、《德意志安魂曲》到《第一弦乐四重奏》,勃拉姆斯艰苦探索二十余年,直到1876 年《第一交响曲》问世。汉斯立克评论道,“整个音乐界如此强烈地期待一个作曲家的《第一交响曲》,这是非常少见的。”⑫同注⑥,p. 134.显然,《第一交响曲》既是勃拉姆斯的个人成功,又是纯音乐的实践宣言。
此后二十余年,交响曲再次达到历史高峰。勃拉姆斯、布鲁克纳、马勒乃至民族乐派的作曲家们,又一次将交响曲推向辉煌,纯音乐与标题音乐的论争也在这种历史语境中逐渐退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双方开始相互认可。李斯特认为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拥有杰出艺术作品的创造性,勃拉姆斯期待着去聆听瓦格纳的《帕西法尔》。⑬参见Jam Swafford, Johammes Brahms: A Biography, Vintage Books, 1997, pp. 467-470.其二,浪漫主义晚期交响曲的繁盛受到纯音乐与标题音乐的双重影响。比如,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纯器乐形态、四乐章结构明显源自贝多芬,而它的模进、配器等又被视为瓦格纳翻版;马勒第一、四交响曲具有明显的交响诗痕迹,第二、八交响曲与《大地之歌》将声乐与器乐融合,而第五、六、七交响曲则倾向于传统交响曲。
由上可见,浪漫主义交响曲是纯音乐与标题音乐论争的历史基础,其困境、发展、繁盛,与论争的萌发、鼎盛、退却紧密相随。
三
纯音乐与标题音乐的论争主要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展开。内容层面,二者看似截然相反,实则有诸多趋同性。真正的论争焦点在形式,它既反映于哲学层面,也包含在音乐作品的结构逻辑之中。
美学上,它们分别借由“形式论”与“内容论”针锋相对。汉斯立克的“形式自律论”宣言—“音乐除了音符的运动,别无他物”,将内容从音乐中完全剔除,音乐本质囿于“形式”本身,并以纯粹、自足标识这种局限。李斯特的“诗意概括”,瓦格纳“音乐是戏剧之手段”,它们都彰显了“内容美学”追求。二者似乎各执一词、决然对立。然而,就内容而言,它们并非泾渭分明、判若鸿沟。甚至,当瓦格纳皈依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后,它们在音乐本质上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
无论是音乐评论,还是美学论述,汉斯立克都留下了“内容”印痕。汉斯立克的音乐评论总是聚焦于音乐形式结构,但他在评论李斯特交响诗时曾明确指出“没有人会狭隘到否定一个音乐外主题参照给予作曲家的诗意刺激”。即便勃拉姆斯交响曲,他也提及了音乐的表现内容,如《第一交响曲》的“道德”因素,《第二交响曲》的“田园”因素。⑭分别参见Eduard Hanslick, "Liszt's Symphonic Poems(1857)", "Brahms' Symphony No. 1(1876)","Brahms' Symphony No. 2(1878)", "Brahms' Symphony No. 3(1883)", "Brahms' Symphony No. 4(1885)", in Vienna's Golden Years 1850-1900.显然,汉斯立克并不否认音乐与诗意内容之间的关联。在著名美学著作《论音乐的美》中,汉斯立克说道,“一切音乐要素相互之间有着基于自然法则的秘密联系和亲和力”“艺术从自然界接受粗糙的物质材料,它利用这个材料进行创造”“思想情感在端正美好的音乐躯体中好像血管中的血一样流动”。⑮〔奥〕爱德华·汉斯立克著,杨业治译《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第52、97、115 页。汉斯立克不仅没有隔断音乐与外界的联系,而且谈到了音乐的思想情感。
最能凸显汉斯立克折中性的言论,莫过于《论音乐的美》第一版删除的末段:“在听众心中,这个精神内容将音乐的美与其他崇高和美的观念统一起来……当聆听人类的天才作品时,这种联系使我们同时领略到无限。就像音乐的声响、音符、节奏、强弱这些要素在整个宇宙中被发现,人类也在音乐中重新发现了整个宇宙。”⑯有关论述参见Mark Evan Bonds, "Aesthetic Amputation: Absolute Music and the Deleted Endings of Hanslick's Vom Musikalisch Schönen"', 19th-Century Music, Vol.36, No.1, 2012.音乐不仅具有“精神内容”,还能领略“无限”,发现“宇宙”。这不仅将汉斯立克的美学思想与浪漫主义初期的器乐美学—理念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进一步显露出它与瓦格纳音乐哲学的某些共 通性。
由此可见,汉斯立克没有否定音乐内容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汉斯立克认为,内容不是音乐本身所具有,而是欣赏者因音乐产生的主观反映,它因人而异、无法衡量。邦兹将这一对命题概括为本质与效果,形式为本质,内容为效果,“汉斯立克坚持,音乐效果与音乐本质毫无关系,反之亦然。”⑰同注②,p. 141.
标题音乐追求音乐内容的具体、准确,它借助标题、文字说明及文学蓝本指明音乐内容所在。在评论舒曼的文章中,李斯特说道:“艺术中的形式是放置无形内容的容器,是思想的外壳、灵魂的躯体”,“没有感情内容的形式只能满足我们的感觉,只不过是手艺匠的制品”。⑱同注③,第131 页。正是在这种“情感论”美学诉求下,标题音乐作曲家拓展了许多新的音乐表现手段,如“固定乐思”、“主题变形”、配器乃至由此产生的结构变化。
但是,音乐与文字两套符号系统的差异决定了标题音乐的某些特殊性。标题音乐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的具象?标题文字等同于音乐内容吗?李斯特阐述标题音乐时说道:“在标题音乐中,动机的重复、交替、变化和转调都取决于它们与诗意构思的关系……一切纯粹的乐思—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容忽视—都服从于所选题材的发 展。”⑲同注③,第19、65 页。另一方面,李斯特又指出,音乐是诗意内容的概括。他赞誉柏辽兹《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时论述道:“他的作品标题初看起来尽管过分详细,事实上却远不能概括他要通过器乐语言来表达的全部感情活动”。⑳同注③,第89 页。海波考斯基更是直言:“假如动机A、B、C 代表叙事形象X、Y、Z,但当听众一开始就不接受这个音乐隐喻,那么,整个音诗的前提就崩塌了”㉑㉑ 同注⑧,p. 2.㉒ 参见Michael Musgrave, "Brahms's First Symphony: Thematic Coherence and Its Secret Origin," in Music Analysis, Vol. 2, No. 2, 1983, pp. 117-133; Reinhold Brinkmann, Late Idyll: The Second Symphony of Johannes Brahms, trans. Peter Pal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显然,我们在肯定标题音乐追求明确意义表达的同时,不能忽视音乐表达之非语义的特殊 属性。
因此,内容层面,这两个看似尖锐对立的命题——纯音乐与标题音乐实际存在诸多趋同性。音乐作品中,这种趋同性更为明显。纯音乐代表作曲家勃拉姆斯的音乐无标题、抽象、内敛,但同样蕴含丰富的人文内涵。比如,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引用贝多芬“欢乐颂”主题,告知我们它继续表达着“从痛苦到欢乐”的音乐内容。近年,随着“新音乐”兴起,学者们从这部交响曲中解读出更多信息。比如,姆斯格雷夫将它诠释为“克拉拉”交响曲;布莱克曼指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末乐章中蕴含着“自然与宗教”意涵。㉒㉑ 同注⑧,p. 2.㉒ 参见Michael Musgrave, "Brahms's First Symphony: Thematic Coherence and Its Secret Origin," in Music Analysis, Vol. 2, No. 2, 1983, pp. 117-133; Reinhold Brinkmann, Late Idyll: The Second Symphony of Johannes Brahms, trans. Peter Pal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纯音乐不仅没有压缩音乐意义,反而为诠释提供了更大空间,释放出更为丰富的人文内容。反过来,标题音乐在追求具象表达时也须遵循音乐符号系统的特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比如,李斯特交响诗《前奏曲》实际源于早年创作的《四种元素》,事后才将它与拉马丁诗作《诗的冥想》相联系;交响诗《理想》中,李斯特改变了席勒原诗的诗意顺序,最后一段的胜利、升华也是原诗所没有的;《节日之声》《英雄的葬礼》则没有对应的文 学作品。
纯音乐与标题音乐论争的真正分歧在于“形式”。
哲学观念上,是否以形式或者说音乐本身作为音乐美的本质,是纯音乐与标题音乐对立的根本问题。它所形成的“形式论”与“情感论”论争,已是学界共识,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瓦格纳在音乐哲学上的转向,使其与纯音乐思想达到了极大的相似性。
瓦格纳于1846 年率先提出“纯音乐”一词,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乐剧理论铺路。此后几年,瓦格纳相继完成几部重要论著:《艺术与革命》(1849)、《未来的艺术品》(1849)和《歌剧与戏剧》(1851)。特别是后两部,充分阐述了瓦格纳“乐剧”理论与思想。他旗帜鲜明地宣称艺术的真正追求是包罗万象的,最高的共同艺术作品是戏剧,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诗歌等都是实现它的手段。㉓㉓ 〔德〕理查德·瓦格纳著,廖辅叔译《瓦格纳论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8 页。㉔ 同注①,p. 34. 或参见Richard Wagner,"Beethoven", "On the Name 'Musikdrama' ",in: Richard Wagner's Prose Works,vol.V,trans. William Ashton Ellis,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2009.㉕ 同注①,p. 33.㉖ “有机体”一词在当时被多个音乐家运用,如瓦格纳、布伦德尔等。显然,在追求音乐具象内容、音乐与戏剧的关系上,它是标题音乐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但是,读到叔本华哲学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后,瓦格纳折服于“音乐意志论”。叔本华认为,世界皆为表象,意志才是世界的内在本质。音乐是意志的直接体现,其他艺术只是意志的间接反映。由此,音乐不仅成为最高艺术样态,而且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瓦格纳深以为然,相继著文。1870 年,瓦格纳在《贝多芬》一文中写道:“音乐表达了动作的最内在本质”。1872 年《论“乐剧”》中,瓦格纳把乐剧称为“可视的音乐行为”。1878 年,面对“戏装与化妆的世界(指歌剧)”,瓦格纳的厌恶之情彻底爆发,他甚至谈及“要像不可见的管弦乐一样,应该发明不可见的戏剧”㉔㉓ 〔德〕理查德·瓦格纳著,廖辅叔译《瓦格纳论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8 页。㉔ 同注①,p. 34. 或参见Richard Wagner,"Beethoven", "On the Name 'Musikdrama' ",in: Richard Wagner's Prose Works,vol.V,trans. William Ashton Ellis,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2009.㉕ 同注①,p. 33.㉖ “有机体”一词在当时被多个音乐家运用,如瓦格纳、布伦德尔等。。音乐乃戏剧本质,其他皆为表象。瓦格纳完全逆转了此前论断。确实,音乐作品中,瓦格纳的创新主要来自交响思维。精彩绝伦的管弦乐配器、统领全剧的主导动机、极度扩张的调性体系,还有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这些都源自器乐化的交响语言。即使是“无终旋律”,也是将声乐旋律器乐化,使之成为管弦乐队的一个声部与器乐旋律水乳交融。尼采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视为交响曲,㉕㉓ 〔德〕理查德·瓦格纳著,廖辅叔译《瓦格纳论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8 页。㉔ 同注①,p. 34. 或参见Richard Wagner,"Beethoven", "On the Name 'Musikdrama' ",in: Richard Wagner's Prose Works,vol.V,trans. William Ashton Ellis,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2009.㉕ 同注①,p. 33.㉖ “有机体”一词在当时被多个音乐家运用,如瓦格纳、布伦德尔等。确为一针见血。瓦格纳也正是借此将控制西方音乐二百余年的功能和声体系推向极致,从而成为西方音乐历史转折里程碑式的人物。
不难发现,瓦格纳“音乐为本”的观念与汉斯立克“形式为本”的美学思想已无本质区别,二者论争消解于纯音乐观念之中。
在具体的音乐形式结构上,纯音乐与标题音乐之间的争论最为频繁、激烈,它是二者哲学分歧的基础,也深刻揭示了分歧的史学实质。
汉斯立克论证“美在形式”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术语“有机体”(organism)㉖㉓ 〔德〕理查德·瓦格纳著,廖辅叔译《瓦格纳论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8 页。㉔ 同注①,p. 34. 或参见Richard Wagner,"Beethoven", "On the Name 'Musikdrama' ",in: Richard Wagner's Prose Works,vol.V,trans. William Ashton Ellis,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2009.㉕ 同注①,p. 33.㉖ “有机体”一词在当时被多个音乐家运用,如瓦格纳、布伦德尔等。,意在说明音乐作品不是机械、松散的形式组合,而要像生命有机体一样达到完整统一。他说:“音乐带来变化无穷的优美的形式和色彩……并且自成为完整充实的一体”;㉗㉗ 同注⑮,第50 页。㉘ 同注⑮,第114 页。㉙ Nina Noeske, "Body and Soul, Content and Form: On Hanslick's Use of the Organism Metaphor", in: Nicole Grimes et al., Rethinking Hanslick: Music Formalism and Expression, Boydell& Brewer, Unin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p. 243-245.㉚ 同注⑮,第60 页。㉛ Alan Walker,Franz Liszt Vol.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7.㉜ 参见注⑧,p. 110.㉝ 关于“发展性变奏”的技术分析可参见Walter 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乐曲必须遵守形式的美感规律,因此,作曲的过程并不是任意的、无计划的即兴漫游,而是有机的、纵目全局的逐步开展,好像从一个花蕾中开展出来的繁多的花瓣一样。”㉘㉗ 同注⑮,第50 页。㉘ 同注⑮,第114 页。㉙ Nina Noeske, "Body and Soul, Content and Form: On Hanslick's Use of the Organism Metaphor", in: Nicole Grimes et al., Rethinking Hanslick: Music Formalism and Expression, Boydell& Brewer, Unin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p. 243-245.㉚ 同注⑮,第60 页。㉛ Alan Walker,Franz Liszt Vol.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7.㉜ 参见注⑧,p. 110.㉝ 关于“发展性变奏”的技术分析可参见Walter 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确实,汉斯立克批评标题音乐并不是对准其标题、文字,而是形式。他批评李斯特交响诗《玛捷帕》“音乐成分常常镶嵌在一起,就像一个马赛克图案”,他指责瓦格纳《唐豪塞》序曲是“动机的组合而不是有机发展而成”㉙㉗ 同注⑮,第50 页。㉘ 同注⑮,第114 页。㉙ Nina Noeske, "Body and Soul, Content and Form: On Hanslick's Use of the Organism Metaphor", in: Nicole Grimes et al., Rethinking Hanslick: Music Formalism and Expression, Boydell& Brewer, Unin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p. 243-245.㉚ 同注⑮,第60 页。㉛ Alan Walker,Franz Liszt Vol.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7.㉜ 参见注⑧,p. 110.㉝ 关于“发展性变奏”的技术分析可参见Walter 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对于贝多芬奏鸣曲,他却认为其有机结合是通过音乐本身的统一,而不是乐曲与作曲家设想的外在事物的某种关系而达到的。㉚㉗ 同注⑮,第50 页。㉘ 同注⑮,第114 页。㉙ Nina Noeske, "Body and Soul, Content and Form: On Hanslick's Use of the Organism Metaphor", in: Nicole Grimes et al., Rethinking Hanslick: Music Formalism and Expression, Boydell& Brewer, Unin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p. 243-245.㉚ 同注⑮,第60 页。㉛ Alan Walker,Franz Liszt Vol.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7.㉜ 参见注⑧,p. 110.㉝ 关于“发展性变奏”的技术分析可参见Walter 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可见,汉斯立克不是反对标题文字本身,而是反对妄图借助音乐外成分来企及音乐结构的统一。
这些形式结构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奏鸣曲式。瓦尔克指出“19 世纪50 年代搅动音乐世界的中心问题是奏鸣曲式的命运”㉛㉗ 同注⑮,第50 页。㉘ 同注⑮,第114 页。㉙ Nina Noeske, "Body and Soul, Content and Form: On Hanslick's Use of the Organism Metaphor", in: Nicole Grimes et al., Rethinking Hanslick: Music Formalism and Expression, Boydell& Brewer, Unin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p. 243-245.㉚ 同注⑮,第60 页。㉛ Alan Walker,Franz Liszt Vol.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7.㉜ 参见注⑧,p. 110.㉝ 关于“发展性变奏”的技术分析可参见Walter 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显然,他抓住了纯音乐与标题音乐之争的核心所在。标题音乐作曲家试图借助音乐外叙事逻辑改变音乐结构,以达到发展、创新贝多芬器乐传统尤其是交响曲传统的目的。比如李斯特的《前奏曲》可以视为单乐章交响曲、性格变奏曲、无展开部的双呈示部奏鸣曲式或带谐谑插部的奏鸣曲式。㉜㉗ 同注⑮,第50 页。㉘ 同注⑮,第114 页。㉙ Nina Noeske, "Body and Soul, Content and Form: On Hanslick's Use of the Organism Metaphor", in: Nicole Grimes et al., Rethinking Hanslick: Music Formalism and Expression, Boydell& Brewer, Unin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p. 243-245.㉚ 同注⑮,第60 页。㉛ Alan Walker,Franz Liszt Vol.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7.㉜ 参见注⑧,p. 110.㉝ 关于“发展性变奏”的技术分析可参见Walter 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对于这种变化,汉斯立克批评为“主题平凡、缺乏发展,插入新材料令人无法理解”。勃拉姆斯则基本遵循古典奏鸣曲式的结构框架,通过“发展性变奏”(developing variation)㉝㉗ 同注⑮,第50 页。㉘ 同注⑮,第114 页。㉙ Nina Noeske, "Body and Soul, Content and Form: On Hanslick's Use of the Organism Metaphor", in: Nicole Grimes et al., Rethinking Hanslick: Music Formalism and Expression, Boydell& Brewer, Unin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3, pp. 243-245.㉚ 同注⑮,第60 页。㉛ Alan Walker,Franz Liszt Vol.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7.㉜ 参见注⑧,p. 110.㉝ 关于“发展性变奏”的技术分析可参见Walter Frisch,Brahms and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Vari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等继续推进奏鸣曲式乃至交响逻辑的内在连续性和变化多样性,从而达到发展、创新的目的。
结 论
所谓历史是观念的基础,观念是历史的抽象。纯音乐和标题音乐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更是一个史学现象。美学上,它们各自渊源于悠久的西方哲学传统。但正是浪漫主义交响曲的发展,或者说,如何继承与创新贝多芬器乐尤其是交响曲传统,促成了二者的诞生、繁荣与衰退。
浪漫主义时期,纯音乐者以贝多芬为代表的器乐创作为历史前提,借助形式主义的美学阵地,努力捍卫古典交响曲传统;标题音乐者以贝多芬的戏剧配乐、《第六交响曲》《第九交响曲》等作品为实践基础,并在“情感论”美学中找到美学诉求,借此突破古典传统,获得新生。
美学上,纯音乐与标题音乐以“形式论”与“情感论”尖锐对立。不过,瓦格纳转向“音乐意志论”后,二者在音乐本质上取得一致。史学层面,它们共同根植于浪漫主义的交响曲发展。二者的真正分歧在于音乐本身的形式结构,即如何发展古典形式逻辑,尤其是奏鸣曲式。正是这种分歧,孕育了浪漫主义音乐的繁盛,也正是浪漫主义音乐的繁盛,弥合了这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