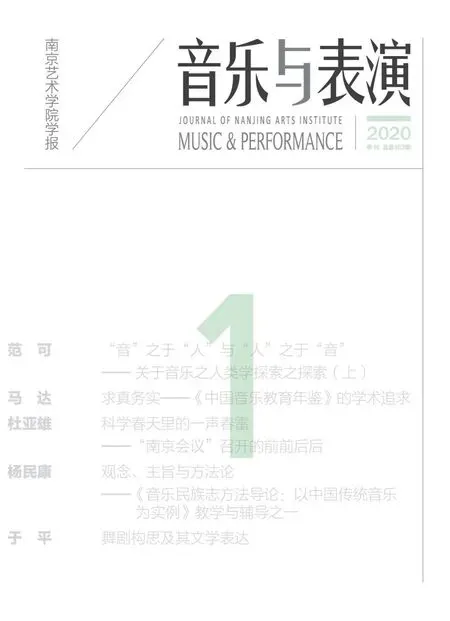试析《公羊传》对“万入去籥”的误读
马金水(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春秋·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1]316仲遂即公子遂,是鲁国的大夫。他于垂这个地方逝世的消息,在太庙祭祀这一天为鲁宣公得知,次日,大祭的仪式并未因此而废止,只是变通为“万入去籥”。关于“万入去籥”,《公羊传》解释道:“万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万入去籥何?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存其心焉尔。存其心焉尔者何?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犹者何?通可以已也。”[1]316《公羊传》对“万入去籥”的阐释是颇值得玩味的,它误解了春秋“万舞”的内涵,错释了周代彻乐的制度,引发了后世诸家绵延不绝的争论。结合《诗经》《周礼》等相关先秦文献的分析可知,对“万入去籥”的解读可以再行推进:在以干羽为舞的大型“万舞”中,鲁宣公撤去以“籥”为代表的乐器,进行单纯的文舞和武舞祭演。
一、关于“万舞”的对立阐释
《毛诗正义》云:“言干则有戚矣,《礼记》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则有羽矣,《籥师》曰:‘教国子舞羽吹籥’。”[2]308“干”与“戚”相伴,“籥”与“羽”相随,前者彰表武功,后者扬显文治。所以《公羊传》认为,“万”即“干舞”,应指一种舞者手执干戚的武舞,而“籥”则为“籥舞”,一种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柄翟”的文舞。然而,对比《左传·隐公五年》的记述,却不难发现二者抵牾之处:“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3]23为仲子神庙落成而进献“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执羽舞人之数,说明“万舞”表演也有执羽的文舞,即与《公羊传》将“万舞”直接视为“干舞”的见解相左。
此外,据《左传》所述,“万舞”亦不可以直接理解为手执羽籥的文舞。《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云:“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仇,我反忘之!’”[3]161楚国令尹子元希望以“万舞”来蛊惑文王夫人(息妫),夫人因此指责他,楚文王在世之时以此舞演习战事,如今令尹不思以之对付仇敌反将其用在自己身上。可见,在当时“万舞”确实具备武舞的性质,舞者是需要手执干戚进行操演的。总之,“万舞”既不能理解为“籥舞”,也不能仅视为《公羊传》所谓“干舞”。
关于“万舞”的矛盾认识不仅见于《公羊传》与《左传》,《诗·邶风·简兮》的笺注尤为集中地展现了诸家解释上的混乱状态,《诗》云: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第一章)
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第二章)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第三章)[2]308-309
《毛传》云:“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故言于四方。”[2]308《毛传》的认识实际上与《左传》较为一致,将万舞理解为“干舞”与“籥舞”的结合。孔颖达解释“毛说”云:“以万者,舞之总名,干戚与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为万舞’,以祭山川宗庙。”不过,他却更支持郑玄“万舞,干舞也”的笺注,复引孙毓语:“万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并断言:“传以干羽为万舞,失之矣”[2]308。迨至宋儒,朱熹推赏毛公的解释而不以郑、孔之说为然。朱熹尝言:“万舞,舞之总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4]吕祖谦亦云:“万舞,二舞之总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别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别名也。文舞又谓之羽舞。”[5]故而,郑玄、孔颖达对于“万舞”的理解是不曾背离《公羊传》的,而毛公,宋儒的阐发有明确地反对《公羊传》的意思。
二、《公羊传》对“万舞”的误读
王维堤说:“因为解释万舞的两种分歧意见中,《诗经》《左传》提供的材料比较古,也具体。《左传》叙事性的史料对万舞的解释行不言之教,比《公羊传》的‘下定义’更权威,更有说服力。”[6]178较之《左传》,在王维堤先生看来,《公羊传》的认识有两处不足:一方面是材料较新,另一方面是论断过于简单。
首先,对于“万舞”的理解出现分歧,至少说明战国时期,《春秋》所述的传统“万舞”几近失传,而这一现象或许不仅仅存在于公羊高所在的齐国。正如王先生所言,《公羊传》对于“万舞”缺乏叙事性描述,因而其言很难成为此时存在“万舞”的有力证据。
其次,《诗》《左传》《墨子》等关于“万舞”的叙述,说明春秋至战国初期,宋、卫、鲁、楚、齐等地尚保留了“万舞”的礼乐活动。《诗》明言:“万舞”的地方共有三处:《邶风·简兮》兼用实笔与虚笔,全面地展示了邶地也即卫国一带的“万舞”表演。此外,《鲁颂·闭宫》“万舞洋洋”描写了鲁国祭祀先祖时的盛大场面[2]615,《商颂·那》“庸鼓有斁,万舞有奕”[2]620很有可能描绘的也是宋国祭祖时的乐舞表演。《左传》主要交代了鲁、楚诸国的“万舞”使用情况。其中,关于鲁国的记录有隐公五年的“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3]23,以及昭公二十五年“将褅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3]1149。关于楚国的事件则是庄公二十八年的“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3]161。《墨子》对齐康公“兴乐万”的论述,亦可证明战国初期在齐国尚保存着“万舞”的形式。左丘明曾活跃于“万舞”尚未灭迹的时代,其所在的鲁国以及临近的宋、卫、齐等国也保留着“万舞”活动,故而他是十分有可能见过“万舞”表演的,他对“万舞”的相关记录亦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最后,结合前文所示,《左传》述及“万舞”时皆是具体的事件,《公羊传》则直接给出主观论断,当二者有所出入,自然是《公羊传》之言更难取信于人。
后世就“万舞”释义互相攻诘的经学家们多由《简兮》一章来阐发自己的观点。《简兮》首章云:“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2]308毛公率先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看法正与《左传》相合,与《公羊传》相悖:“简,大也。方,四方也。将,行也。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故言于四方。”[2]308不过,郑玄、孔颖达等人的认识与《公羊传》却是一致的,前者只作了“万舞,干舞也”的判断,后者则结合《诗》与毛、郑之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分析与结论。孔颖达先分析《毛传》云:
以万者,舞之总名,干戚与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为万舞”,以祭山川宗庙。宜干、羽并有,故云“用之宗庙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于四方”,解所以言四方之意也。《周礼》舞师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则山川与四方别。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礼》言“天子法四方为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谓四望也。”《大司乐》注云:“四望,谓五岳、四镇、四渎。”然则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与四方别舞。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内则祭之,非其地则不祭,无岳、渎之异,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对宗庙在内为四方也。此传干羽为万舞,宗庙、山川同用之,而《乐师》注云“宗庙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庙、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礼大,故可为之节文,别祀别舞。诸侯唯有时王之乐,礼数少,其舞可以同也。[2]308
根据《周礼》的说法,“籥舞”是用以祭祀四方,即“五岳、四镇、四渎”的,“干舞”是用以祭祀山川的,二者的用法是有区分的。然而,对诸侯而言,他只用祭祀自己封地内的山川,也就不存在“五岳、四镇、四渎”的“四方”之祭了。因此,在诸侯的祭礼当中,“山川在外”便如同“四方”,“宗庙在内”便如同“山川”,其祭祀宗庙、山川便等同于祭祀山川、四方,所以要兼用“籥舞”与“干舞”,也就是《毛传》所谓“以干羽为万舞”。不过,孔氏又补充《乐师》中“宗庙以人,山川以干”一言,指出,宗庙与山川之祭时常都不用“籥舞”,以明确诸侯与天子之礼的不同,他认为,“天子之礼大”因而并用“干羽”,但诸侯“礼数少”便可只用“干舞”。孔氏言下之意即卫君(翟相君《诗经新解》认为是卫庄公)、鲁宣公这样的诸侯所兴“万舞”应该只是“干舞”,而非“以干羽为万舞”。
此外,他还明确地为《公羊传》之见申述以支持郑笺:
知万舞为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万入去籥”别文。《公羊传》曰:“籥者何?籥舞。万者何?干舞。”言干则有戚矣,《礼记》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则有羽矣,《籥师》曰“教国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则羽为籥舞,不得为万也。以干戚武事,故以万言之;羽籥文事,故指体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注云:“干戈,万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异也。且此万舞并兼羽籥,则硕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论硕人之才艺,无为复言“左手执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说羽籥舞也。以此知万舞唯干,无羽也。孙毓亦云:“万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传》以干羽为万舞,失之矣。[2]308
孔颖达以为《公羊传》谓“万舞”为“干舞”是准确的,并以此来佐证郑玄“万舞,干舞也”的判断,然而他却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分析。《礼记》《籥师》的记录的确说明了干戚常常同时使用,籥羽常常一起出现,然而,二者的区别却无法说明“万舞”与“干舞”的对等关系。此外,孔氏以郑玄注解《文王世子》的定论复言“是干、羽之异也”,似是自说自话,也无法证明郑玄此处的判断。孔颖达解读《简兮》这首诗时说:“‘仕于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艺’,卒章言‘宜为王臣’。”[2]308他认为后二章是描述“硕人”的才艺,以称赞“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为王臣”[2]308的。故此孔氏将此诗一分为二,首章是一部分,只言“万舞”,后二章是一部分,论及“籥舞”,认为二者相互结合以写出他“文武道备”,“可以承事王者”的贤能。孔氏此见割裂了诗的整体结构,下文将详细论述。
孔颖达疏解“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2]308曰:
言硕人既有武力,比如虎,可以能御乱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马之执辔,使之有文章,如织组矣。以御者执辔于此,使马骋于彼;织组者总纰于此,而成文于彼,皆动于近,成于远。以兴硕人能治众施化,于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动于近,成于远矣。硕人既有御众、御乱之德,又有多才多艺之伎,能左手执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复能为文舞矣。且其颜色赫然而赤,如厚渍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于祭祀之末,公唯言赐一爵而已,是不用贤人也。[2]308
孔氏将“有力如虎,执辔如组”理解为“武力”“文德”,指“硕人”拥有“御乱”和“治众”的文才武略。而“左手执籥,右手秉翟”一语则是对其兼善“文舞”的描写,郑笺解释道:“硕人多才多艺,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备。”[2]308孔颖达认为此处写他“能为文舞”,正可以与首章武舞相结合,表现出“硕人”卓越的才能和德行。至于“赫如渥赭,公言锡爵”,郑、孔二人皆阐发出讽刺之意,郑笺云:“硕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赐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贤而进用之。散受五升。”[2]308孔亦认为其意在讥刺卫公不知任用贤人,也就是《简兮》一诗的主旨所在:“刺不能用贤也。”《简兮》卒章又云:“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2]309郑玄解释曰:“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硕人处非其位。”[2]309榛木和苓草尚能为用,而“硕人”却不能被选用,实在是令人惋惜。郑、孔皆以为后面说的“美人”指的是“硕人”,这样的“美人”应该身在王朝、成为王臣,然而,现实中却没人能够举荐这样的“硕人”。郑、孔二人对《简兮》的诠释,在整体上割裂了连贯的诗意,也误解了“万舞”的具体内涵。王维堤先生指出:“郑玄笺《诗》,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却因原诗第三章换韵而对章法做了割裂的理解,认为前二章写的是万舞,第三章写的是羽籥舞,因而郑笺云:‘万舞,干舞也。’孔颖达更详加论证,作出‘传以干羽为万舞,失之矣’的结论。”[6]176王先生将《简兮》分为四章,前二章为一个韵,后二章为一个韵,他以为郑、孔二人受换韵影响,将其内容也分裂为前后两个部分,并以此断定前二章所述“万舞”应是与后二章“籥舞”相对立的“干舞”。王先生的换韵说法或可商榷,但郑、孔的注疏诚如他所言,破坏了《简兮》一诗的整体表达,关于此,他亦说道:“若照郑玄、孔颖达那样读诗,那这首诗就谈不上丝毫艺术性了。试想上来就两次提到万舞,开场锣鼓打得可谓紧矣,接着却只有两句并不具体的描写,万舞就此戛然中止,宣告结束了,这不是太煞风景了吗?下面一换韵,据说已经是第二个节目羽籥舞了,而事先又一点招呼也不打,其没头没脑正与万舞的有头无尾同样拙劣。”[6]178王氏所谓“两句并不具体的描写”当指“有力如虎,执辔如组”,郑、孔皆以为这是在称赞“硕人”“文武道备”的,而王维堤认为,此处虚笔应写的是“万舞”的前半部分表演:“看来舞中有摹拟驾驭战车的动作。《郑风·大叔于田》写‘叔’田猎乘驷马之车,就是用‘执辔如组’来形容他的御术高超。”[6]189所以,在他看来,对《简兮》应做一气呵成的理解,先总言“万舞”,再分述其武舞和文舞两个部分的表演。王说以意逆志,多有值得商讨之处,而他指出的郑、孔理解上的问题,却未必没有道理。
根据《简兮》的描述,可知郑玄、孔颖达等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万舞”之解实不可信,我们应该以毛公等的传义为准。换言之,“万舞”不仅仅是“干舞”,还应该包括“籥舞”在内。不过,如宋代陈旸所云:“先干戚后羽毛。”[7]前人多以为“万舞”是依照先文舞后武舞的顺序来表演的,更有学者指出,“但若以干戚和羽籥同时舞起来,似乎又有相当的难度”[8],殊不知,除了《简兮》当中用于教授国子的“万舞”,大多数时候用于祭祀的“万舞”都是“万舞洋洋”,“万舞有奕”的盛大场面,也即《左传》所谓:“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因此,“万舞”完全有可能是“干舞”与“籥舞”同时进行的,一部分人手执干戚,另一部分人手执羽籥。不过,这与《公羊传》对万舞的误读已无直接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三、《公羊传》对彻乐的误释
彻乐仪制是周代礼乐制度当中的重要内容,即面临天灾人祸时,撤去用乐以表示忧戚。《春秋》载:“宣公八年,鲁国的大夫公子遂逝世于垂,鲁宣公得知此消息的第二天,将大祭的仪式改变为“万入去籥。”《公羊传》据此解释道:“万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万入去籥何?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存其心焉尔。存其心焉尔者何?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犹者何?通可以已也。”[1]316《公羊传》将“万舞”解释为“干舞”是不准确的,此外,“万入去籥”亦不应当理解为撤去籥舞,而应理解为撤去以“籥”为主的乐器,正如高亨先生所言:“鲁国因为绎祭太庙时,遭大夫仲遂的丧事,所以舞具去籥,只用羽,以表示哀悼。”[9]
首先,同形制严格的置乐之仪一样,彻乐的方式会根据用乐者的身份,变故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调整,具体而言,常有“去乐”与“弛县”之别。孙诒让说:“去乐者,敛凡乐器,一切尽藏之府库 ;弛县则直弛金石之县而已,不必尽藏去也。”[10]据此,付林鹏解释道:“‘去乐’之‘乐’,当是广义概念,不独乐器,歌、舞亦在其列。”[11]40事实上,就彻乐原因而言,“去乐”适用于较为严峻的事故,“弛县”则应用于出现较为轻缓的变故之时。《礼记·乐记》云:“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2]1527故而“去乐”的范围要包括“弛县”在内,指摒弃一切乐舞活动。付林鹏亦认为,《管子·霸形》“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里的“伐钟磬之县”与“弛县”相似,是针对乐器而言;“并歌舞之乐”则与“去乐”相似,除乐器外,还包括歌、舞。[11]40因此,《公羊传》谓:“万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将“万入去籥”理解为撤去“籥舞”,保留“干舞”,这既不属于“弛县”撤去器乐的范围,亦不符合“去乐”摒去一切乐舞的规定。
《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3],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乐舞使用的,所以对于鲁宣公“万入去籥”逾礼一事,他评论:“非礼也,卿卒不绎。”[12]1310在孔子看来,鲁国的大夫逝世,宣公是应该执行“去乐”之仪的,显然,“万入去籥”并未遵守“去乐”的周礼规定。《公羊传》云:“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存其心焉尔。”[1]316何休注:“废,置也。置者,不去也。”[14]仅就《公羊传》这一句来说,实际上也符合于撤去乐器之声的“弛县”制度,不过,结合前文可知,其意为撤下有声的籥舞,留下无声的干舞。因而,其整体传疏可能误释了“万入去籥”的“弛县”之意,而直接将指代乐器的“籥”表示为“籥舞”。
礼乐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一般情况下,鲁宣公变通用乐之仪,也只是放松“去乐”的要求,简化为“弛县”的仪式。不过,既然“万入去籥”本身就是违背了彻乐制度,自然也存在鲁宣公完全自由地使用乐舞的可能性,也即《公羊传》认为的撤去籥舞的说法。如果这种假定性成立,据《公羊传》“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存其心焉尔”之意,在“干舞”表演当中就应该没有乐器的使用了。《毛诗序》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270《春秋左传正义》亦云:“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则咏其辞而以声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15]2008先秦时期,诗、乐、舞立足于共同的情感、韵律而结合在一起,通常情况下,舞祭当中是离不开乐器之声的。据《周礼·春官·宗伯》,周代的正式祭祀乐舞包括大舞和小舞,大舞即“六代之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小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大舞的表演当中却无一不适用乐器,《春官·宗伯》曰: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
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
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
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
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
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16]789
这六种调式的乐舞,都要用五声、八音来相互配合,其目的是“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16]788。“万舞”之名,虽不在六大舞、六小舞之列,但据前所析,其运用于祭祀当中绝对是一种场面宏大的大型乐舞,所以其表演过程当中理应贯穿着器乐的演奏。《春官·宗伯》云:
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从声展之。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16]790-791
但凡进行礼乐活动,无论是用于祭祀、宴飨抑或献功,都有着一整套井然的用乐制度规范,更遑论鲁宣公进行“万舞”这样的大型活动,其中“干舞”这个环节没有器乐演奏是很难想象的。其次,六小舞当中直接提及“干舞”,《周礼》虽未介绍“干舞”用乐规范,却又载言:“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16]794即使是“国之小事”,尚要使用钟鼓之乐,亦说明了器乐使用的广泛。此外,关于六小舞,《周礼》补充道:“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16]793乐师教授“干舞”一类的小舞,是为了使国子的日常活动都依节奏行事,无论是慢走还是快走,无论是乘车还是拜见,都必须合乎相应的节奏。至于射礼,更会根据使用者身份的不同,提出不一样的音乐节奏规范。因而,“干舞”本身自然也要伴随着有节奏的器乐演奏,诚如后世孔颖达所云:“舞为乐主,音逐舞节,八音皆奏,而舞曲齐之”[15]1728,换言之,《公羊传》将“万入去籥”理解为撤去“籥舞”,保留“干舞”,又补充说“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公羊传》很有可能是明白周礼当中有禁乐器之声的“弛县”制度,但是其误以为“干舞”是无声的舞祭,所以将“万入去籥”简单地割裂讨论,直接释为摒去“籥舞”部分。
《周礼·春官·宗伯》云:“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大札、大凶、大灾、大臣死,凡国之大忧,令弛县。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大丧,莅廞乐器。及葬,藏乐器,亦如之。”[16]791天有异象,人逢灾异,诸侯之丧,是需要“去乐”的,瘟疫饥荒,水灾火灾,大臣之丧,是需要“弛县”的。国家遭遇大事,用乐不可不谨慎,或禁失度之声,或一律摒弃之,这是需要根据情况细细分辨的。《春秋》载鲁宣公“万入去籥”一事,实际上正是“弛县”的意思,指宣公未禁祭舞,仅仅撤去了器乐,《公羊传》未能准确理解其中彻乐的内容,简单地误释其为撤去了“籥舞”祭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