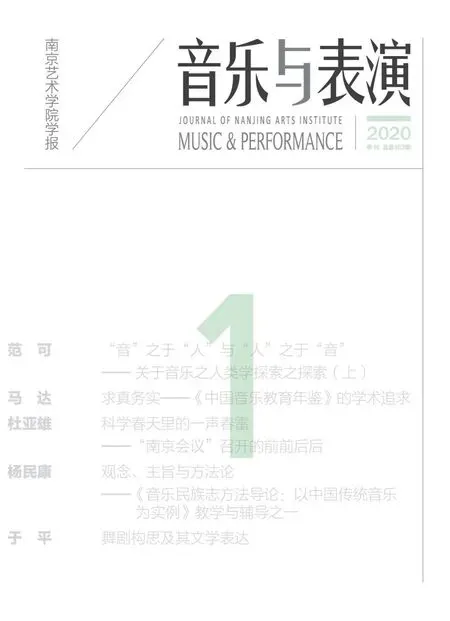元代歌行观念及其音乐性问题探赜①
唐 丽(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李昌集(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近半个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不断上扬的趋势,其长期不被重视的诗歌批评以及诗歌文体研究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元代歌行诗体的研究渐开堂庑,陆续有新的成果出现。这在一些有关歌行研究的重要学人,如葛晓音、钱志熙、赵敏俐、王辉斌等那里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统观既有的研究成果,发现此前诸公更多是在关注乐府概念考辨的过程中渐次逼近歌行诗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也就间接导致了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元代歌行研究起步较晚,一直未能形成规模。意识到这一点,笔者曾以此另撰文《元代歌行论略》《元诗“四大家”歌行的主题内容与文化意蕴》《元诗“四大家”歌行比较研究》,尝试对元代歌行进行截取式地分体断代研究,对其主题内容与叙事技巧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②请参见唐丽.元代歌行论略[J].中国韵文学刊,2018(2):21—26;唐丽.元诗“四大家”歌行的主题内容与文化意蕴[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3):1—7;唐丽.元诗“四大家”歌行比较研究[J].临沂大学学报,2020(1)(待刊)。。鉴于此,本文继续在原有基础上延伸开来,对元代歌行观念及其可歌性问题予以全面观照,冀为近古三代歌行与乐府内在互涵关系的探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思维材料,以略补当前歌行专体文学史研究之“未思”。这亦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一、歌行在元代以前的演进
“歌行”之名,本自乐府诗而来,此义古今人多有涉及。其中,尤以钱良择《唐音审体》中,“歌行本出于乐府”[1]一言最为直接简要。汉代乐府诗开始出现以“歌行”命名的“歌辞性”篇章。这一阶段歌行主要存在于乐府之中,故又被薛天纬称之为“乐府歌行的形成期”[2]。然此时诗题所云“歌行”二字,只是作为乐府诗体的一种题名方式,并未成为一般性的统称用语。
进入唐代之后,歌行与律诗大体同时发展起来。其创作已经从孕育它的母体乐府诗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唐人也从创作实践的角度,为歌行奠定了最基本的诗体模式。但较之歌行的创作实绩,唐人对其本质和艺术特征的体认则显得相对滞后。在文体观念上,唐代“歌行”一词仍是难以具体指陈的混杂概念,其创作模式主要是以七言古诗为参照对象,而在实体指称上却常以乐府冠之。胡应麟“唐人李、杜、高,岑名为乐府,实则歌行”一说,可为此做注脚①唐代“乐府”兼统众名。在具体的诗歌评论中,“乐府”一词多与“歌诗”“杂句”“长句”“杂言”指意相一致。例如白居易《编集拙诗城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书二十》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句后自注:“予乐府五十首”,以歌行指其《新乐府五十首》。理论的滞后必然会带来实践上的迷误,这种互注同时也表明,唐人判定歌行与乐府诗体性质时不免稍显朦胧,颇费踌躇。。
迄至宋代,歌行一体独立的诗体学概念逐渐明晰起来。《文苑英华》特辟“歌行”这一诗歌门类,才首次出现歌行与乐府的指代差异。通常而言,命名本身即是分类的开始,然而宋代将“歌行”一目编入诗集且单独分卷的自觉意识并不突出。据笔者目力所及,只寻见三处,分别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七中《金丹诗诀》曰:“下卷歌行尤鄙俚”[3]1958;卷一四九记载宋人王钦臣校定的《韦苏州集》曰:“……次游览,次杂兴,次歌行。凡为类十四,为篇五百七十一”[3]2002;卷一六三《方壶存稿》曰:“是编第一卷为书、辨、序、说、颂,第二为赋、歌行”[3]2166。由此,歌行一体于宋代仍处于有名无分的尴尬状况。
要之,唐代以前歌行体诗歌的基本样式一直处在整合演变的过程中,人们对其诗体学的了解仍停留在初步认识阶段。后经过唐代人的创作实践与宋代人的总结整理,歌行才获得独立的诗体学地位。只是遗憾的是,唐宋期歌行一体的批评理论与创作步伐基本不相一致。诗人虽然存有大量的歌行作品,但这些诗篇“所属之类”指意不明,大多没有理论上的支撑,歌行创作所依据的是一种模糊的写作原则。至于歌行有何特征,唐宋两代尚未形成理论化的表达。这也给元代歌行一体的探考留出了审思空间。
二、元代歌行理论的多种阐述维度
较之唐宋,元诗尤妙于歌行的文献记载渐次增多,歌行理论也随之进入到一个较高层次的探索,可从不同角度进行提炼。
第一,元人好从唐代歌行作品的评述中寻绎创作门径,并借以提出歌行创作的基本形制规范。据笔者统计,今存25 部诗法类著作中,《诗法家数》《诗学禁脔》《木天禁语》例举杜甫歌行诗篇达75 次,而《诗学禁脔》《木天禁语》征引李白歌行也有7 次之多。激赏之情,可见一斑。这股“祧唐”之风同时也关联到了歌行诗体的理论批评。范梈《木天禁语》“送尾”一条,对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加以祖述,指出杜诗歌行“不迫促,甚有从容意思”[4]160。而“歌行转换处,类聊聊有之,观其用虚字处可见也”“歌行之奇绝者”[4]443,也是范氏将个人对歌行创作的理论感悟与杜甫诗篇予以贯通研究,颇有认识的价值。
出于给当代诗人歌行创作提供“处方”与艺术借鉴之目的,元人还经常将唐代歌行作为文本典范加以参观互勘。这样的案例较多,暂且引述范梈《总论》一例为证。
后世之诗,奠高于杜子美,然观《饮中八仙歌》,一篇之意,层见叠出,凡用韵二“船”字,二“眠”字、“天”字,三“前”字。且“皎如玉树临风前”,与“苏晋长齐绣佛前”,同在一处,说者谓当分为四章,或分为八章,如《周诗》分章之意,然终是一歌。[4]201
一般而言,古人歌行之作多以分节或转韵标示段落层次的递进与衔接。按照范梈的认识,四章、八章之结撰体式呈现在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文本上,是其展现歌行诗型音乐结构的方式之一。分为四章,亦即四个节奏单元的意思。而以往“说者”大多不明此理,遂陷入皮毛之讥。事实上,范梈这一观点与元人“以诗为歌”的艺术实践是互为关联的,像杨翮《金谿县孝女庙乐歌三章》并序:“上元杨翮撰为乐歌三章,俾金谿之民岁时歌之,以祀孝女。”[5]46册167 顾瑛《安别驾杀贼纪实歌》“谨歌长歌一章,以纪其事”[5]49册45 等实例,都反映出元人在歌行创作中对“章”这一音乐体式因素的尝试。所谓“古之人未有不歌也,歌非他,有所谓辞也,诗是已”[6]20册152,就是将歌行视为分解、分章的演唱歌辞,亦即范梈最后所提出的指标性结论:“终是一歌。”
第二,对谋篇造辞等细节要素在歌行创作中的构成作用多有论列。例如,“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此二句是起,语极平直,似鄙俗而实非鄙俗也;‘握发呼儿延入户,手提新画青松障’,此二句是承,语便舂容;‘障子松林静窈冥’以下是转;‘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是再转,语意桓极变化之妙;‘松下丈人巾屦同’以下是合,乃借松障中实景与当时人事感慨结之,意兼比兴,可谓渊永之至矣。”[4]246即是以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起承转合”的结体方式为切入点,分析了歌行诗体统筹布局的创作技巧,认为处理好“文脉贯通,意无断续,整然可观”的内在结构关系,是规范歌行诗体的基础工作。类似地,元人对歌行遣词造句的运用法则也有真切的认识,“长篇之法,亦有宜实在字多方好者,如岑参《马》诗:‘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红缨紫鞚珊瑚鞭,玉鞍锦鞯黄金勒。’多是实字,故易入眼……可见实字之健也。”[4]223谓歌行依句用字之法,重在突出实字的镶嵌,字实则自然响亮,而句法健。某种意义上,元人对练字锻语技法予以介入和规定,既是为后学解析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提供了模仿取则的空间,也表明了当时对歌行诗体认识的深化程度。
第三,除上述诗论著作外,元人的诗文序跋也是表述歌行观念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对歌行之“体”的缘起与艺术体性等内容有一定深度的揭橥。
(一)识诗体于原委正变之余。迨及元代,中国古代各种诗歌体式已然发展完备。因此,元人要想在歌行一体上另辟新境,不可避免地会从诗歌流变的延衍过程中探寻理论依据。元代的这类序跋数量众多,如“《诗》三百篇外,汉、魏,六朝、唐、宋诸作毋虑千余家,殆不可一一论。五七言、古今律、乐府、歌行,意虽人殊而各有至处,非用心精诣,未知其所得也。”[6]44册540 刘诜《夏道存诗序》亦云:“诗之为体,三百篇之后,自李陵、苏武送别河梁,至无名氏十九首,曹魏六朝,唐韦柳为一家,称为古体。自汉《柏梁》《秋风词》,驯至唐李杜为一家,称为歌行”[6]22册65。从论述方式上看,两段文字均是以《诗经》为起点,纵向究厥歌行诗体的渊源与动态承衍态势,指出唐代以前就存有歌行一脉,而《诗经》中的七言古歌已初步显露出歌行诗体的诸多特点,对歌行梯度演进路脉具有一定的导源作用。
(二)养性以立歌行之本。元代文人在此义上多有论述,以虞集《易南甫诗序》最为言简意赅,该序曰:“豪于才者,放为歌行之肆。”[6]26册109 在他看来,言为心声,天稟旷达之人出辞吐气易于“放情”,这对发挥歌行体面宏阔、跌宕超轶的美学潜力尤为重要。对此,戴良《玉笥集序》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歌行’等篇,则又逸于思而豪于才者”[7]4册2522。他如“古体非笔力道劲高峭不能,歌行非才情浩荡雄杰不能”[6]22册65,亦主张才气是诗人创作歌行的基本艺术品质。因此之故,多数元人认为:“饮如长鲸吸百川”,“笔阵独扫千人军”①此作应为杜甫歌行体诗歌《醉歌行》,见《全唐诗》卷二一六,张书引文中为王义之,有误。,“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志欲河带吞”这类佳句得以横被千载之要诀,“皆因豪气所发而然”[4]438。
(三)艺术风格的评析也是元代歌行观念的一个重要考察维度。对此,戴良《鹤年吟藁序》一文称:“古体歌行诸作,要皆雄浑清丽可喜”[7]4册2523,指出,雄伟清健即为歌行当行本色。刘诜接受了此观点,其《桂隐文集》卷二《张子静诗词》中评价张子静:“七言长篇,浩荡不羁”[7]3册1953,以为歌行风格贵在雄俊铿锵、健爽跌宕。王礼《黄允济樵唱稿序》也提出歌行须以“格高气畅”居要,“沉郁雄浑,开阖曲折”乃是其区判“高古朴茂”五古与“折旋婉媚”[6]60册596绝句的关捩之处。更可注意者,对雄伟清健诗风的追求,本质上是元人缘饰盛世思想形态在歌行创作方面的推衍和渗透。关于这点,可以在杨载《诗法家数》中获得直观的了解:“作诗要正大雄壮,纯为国事。夸富耀贵、伤亡悼屈一身者,诗人下品”[4]37,即是把诗歌创作与“纯为国事”加以对应性解释,用意在阐明“正大雄壮”这一诗歌风貌是“以鸣太平之盛治”的最终效果,它折射出的是一种时代情绪。而苏天爵《滋溪文稿》“沐国家承平之泽,正当觞酒乐歌”,“时有汙隆,而文随之”[8],亦是此意。
以上所述,仅仅是元人把歌行作品与诗法著作勾连所得。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元代在文体辨析方面已经有了展现歌行特性的自觉意识,具有较为明显的“研究”气质。这恰恰是其不同于唐宋时期歌行理性认识相对滞后的主要标识。就这一意义而言,元代无疑是拓展了歌行文体的表达空间。
三、音乐性挖掘:元代歌行的选编实践
较之唐宋时期,元人更看重对“歌行”诗体的记录。就笔者统计,元代将“歌行”单独立卷并标目的诗歌(文)别集共有16 部,分别是:虞集《道园遗稿》、范梈《范德机诗集》、陈宜甫《秋岩诗集》、张宪《玉笥集》、丁鹤年《鹤年诗集》、郭钰《静思集》、邓雅《玉笥集》、郝经《陵川集》、袁桷《清容居士集》、黄玠《弁山小隐吟录》、马祖常《石田文集》、欧阳玄《圭斋文集》、许有壬撰,许有孚编《圭塘小稿》、鲁贞《桐山老农集》、杨维桢《东维子集》、梁寅《石门集》。现将有关结论条述如下。
其一,重在别其异。所谓:“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7]1册1087,从诗集对歌行文本的分类标准来看,上述所列诗集均明确将歌行与绝句、律诗等诗体同等分类并置,从诗体类属上强调歌行的独立性价值。与此同时,这些诗集是一种介于理论和创作之间的中间形态,比上文单纯以诗法理论为基础的探讨形式更具有导向性与针对性,是我们直观把握元人歌行观念的关键所在。
其二,重在合其同:歌行诗体由并行关系到统属关系的转移。具体而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数端。
(一)门同而类殊之关系,即七言古体诗中的一部分“歌辞性诗题”者与歌行迹近形似,可概称为歌行。傅若金《傅与砺诗集》就是这层关系的典型代表,是集卷三“七言长短句古诗”中,先是将所有随事定题的七言古诗置于卷中前部,再分别录入有特定歌辞类标题的“行”诗与“歌”诗。可见,歌辞性诗题是编者“由类中以思其不类”的直接参照点。众所周知,以“行” “歌”名篇的这类诗题在其形成之初是具有“播于乐章歌曲”音乐属性的,只是在演变过程中失掉了曲调,日渐和曲辞脱离了关系,但在诗歌形式上仍内蕴着声乐韵律的因子,大略又与徒诗有所区别。而这些“有辞无声”的歌辞类标题后来也都是歌行诗体常见的命题特征。傅若金正是基于“歌行之名,本之乐章”的历史经验,强调七言古诗在歌辞性诗题层面上是一种与歌行密切相关的诗歌形式,这一认识也潜在反映了元人在七言古诗文体上分流意识的萌芽。关于这一点,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可以作为相仿案例列举出来。该集有意将“七言古诗”分作四、五两卷来编辑,稍加注意便会发现,那些诗题后缀以篇、曲、引、谣等音乐性较强的七言古诗都被统括在卷四之中。这种编排方式,当是刘因有意识地认同:辨别歌行与七言古诗的有效界域应首于歌辞性诗题上进行求证。在他看来,两卷诗歌虽同时被冠以“七言古诗”的指称,但已然“貌合而神离”,因而题名中存留“乐府风味”的作品自然不宜直接视为七言古诗,须单独立卷保存。由此,刘因将歌行诗体从七言古诗中直接分流出来单立一体的区分意识甚是明显。而张雨所编的《贞居先生诗集》,更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分类范式转移的过渡性质。是集“七言古诗、歌行”卷中,单列歌行专类置于七古之后,以示区别对待。其中歌行所录全为依傍“引”“吟”“谣”这类乐府旧题者。可知,张雨这里明确是以“辞章”为本位作为二体“以标区界”的最根本依据。
以今天的眼光看,元人以歌辞性标题作为歌行诗体的识别要素虽然不尽适切,但他们至少找到了一个方面的判定标准,潜在地反映了歌行与七古文体间彼此借重又分流裂变的一个面向,这也就一定程度上扩容了唐宋时期以古律区分诗体的传统提法。因而,从集中全力突破一点的意义上说,这种处理自有其价值所在。
(二)至于一卷之中同类诗歌体裁的作品,元人则多是着眼于传统的开发,兼用分类或分体的编排办法。如袁桷《清容居士集》强调,诗各自为体,集中诗歌选取亦皆以体标目。而为了突出歌行诗体与音乐之间的疏密关系,袁桷又将“行体”诗(9 首)、“词体”诗(1 题2 首)、“歌体”诗(13 首)细分,依次归于卷八“歌行”子目之中,层级分明。与此类似,郝经《陵川集》则以诗乐离合为落脚点,将“歌诗”卷下的词体、曲体、叹体、吟体按顺序单独列出,在文体特征上明确展现出强化诗体音乐性的意图。按照元代《王构诗话》的说法,“纡徐抑扬,永言谓之歌;非鼓非钟,徒歌谓之谣;步骤驰骋,斐然成章,谓之行……声音杂比,高下长短,谓之曲;吁嗟慨歌,悲尤深思,谓之吟”[9],郝经这里意即指此。在他看来,词体、曲体、叹体在音乐文学性质上虽然同属“歌诗”一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却是较为严格的,以“吟”为题者歌唱效果显然要低于行体与曲体,故要保持一定距离,别立一类。这种“以乐为次”的别类意识足以看出:元人在歌行文体观念上“品录颇严”,较之唐宋宽泛的立类标准,它更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
(三)与上述一点互为因果的是,乐府与歌行相依一体。即歌行和乐府以关联方式在音乐“歌辞”层面上获得了某种相通性,这主要表现在“乐府歌行”这一概念中。比如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乐府歌行”类共收录20 位作家33 首作品,验之卷中诗篇的创作实况可知,像王恽《义侠行》、鲜于枢《水荒子歌》、宋本《舶上谣》、揭傒斯《李宫人琵琶引》诸篇,或保留复词叠语以“骀荡其音节”[10],或长短句错落并杂以求回环映射的音乐节奏,表现出歌行一体对音乐文学本初属性的回归与亲近。除此之外,马祖常《石田文集》、陈宜甫《秋岩诗集》中的“乐府歌行”卷次也均同此法,“往往多可诵之句”[6]34册447。
整体上看,“乐府歌行”这一语称习惯尽管在元代使用的频次并不高,但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推考出这样的事实:从“辞”的角度名之,歌行与乐府所以虽异而近的同类关系,是因为二者乃当时之歌词。也就是说,歌辞性基质的保留才是二者“兼通”的性质所在。前引吴澄“歌非他,有所谓辞也,诗是已”的论点亦即着眼于此。究其根本,此时之“乐府歌行”已不是某种单纯诗学体式层次上的概念,而是在曲体音乐文学影响下元人为歌行寻求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派生行为,用来泛指一切入乐的歌诗。可以说,这既是元代歌行观念中最为深刻的内涵部分,也是元人对歌行体诗歌本质认识的又一大进步之处。
结 语
通过前文的探讨分析,或可得出如下几点看法:
相较于唐宋歌行理论的匮乏与滞后,元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体现了对歌行一体总结的要求。其歌行观念的表达形式大致含有两种基本认知理路:第一种是诗法著作及序跋文献中所覆涵的歌行观,趋向于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断面对歌行篇章体制的结构之法、遣词造句、形制规范和艺术体性等进行审鉴与归纳,属于歌行之“体”的知识体系范畴;第二种是诗集选编实践中的歌行观念,更多的是指向歌行这一体裁的诗体分类与编排方式,歌行与乐府、七古三者之间文体归属及其边界指认等方面,是前者诗学理论探讨的直接外化形式,最能体现出元人歌行考究的“当代”意识。这两个认知理路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生发,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唐宋以来歌行诗体批评的形式领域,为歌行理论层次的提升做出了一定贡献。
藉由析类和归类两种逆向活动的双向建构,元人歌行观念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变特色——重拾“歌辞”指意以激发歌行潜隐的“弦歌”质素,为歌行本体在元代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契机;“以乐为次”的编次方法,既有整体的统一性,又有局部的差异性,彰显了歌行这一体裁张力的艺术优越性。据此可推,在元人秉持的观念中,歌行的实际状态是一个亦歌亦诗,更具有流动性质的诗歌体式。而吴相洲先生提出歌行“带有音乐性质,但又偏重体裁而言”[11]的观点亦可与此相印证。歌行诗体的开放性也鲜明地反映出,曲体音乐文学背景下元人与时共进的诗学意识。笔者以为,这在其他朝代是不多见的,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和强调。
历史地看,有元一代歌行“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12],是古代歌行发展史上的一个中间环节,也是我们当下深入研究乐府专体文学史必须关注的一个学术参照。因而,在乐府学研究愈来愈精细化的今天,漠视元代歌行接续与引介作用显然是不合适的。元代歌行应当有更系统化的研究空间。仅就音乐文学这一研究视角而言,元人对于歌行诗体仍然有强烈的入乐期待,像“作《烈妇行》以歌之”(《烈妇行》),“作诗以歌之”(《星聚凤池砚歌》),“赋海隄曲一章俾之歌之”(《咏余姚海隄》),“系之以歌”(《天屏歌》)等诗篇,均透露出一个重要事实:音乐文学在元代歌行诗体上有一定范围的显现。故此,对歌行的理解和研究都不能离开音乐这个维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呼声之下,研究者应当改变以往从文学单一视角出发研究歌行体诗歌的惯性行为,自觉地运用音乐界的研究成果,发挥歌行一体对音乐文学研究的能动作用,以辅助完成诗体音乐文学研究从表面现象的描述到内在所蕴藏规律的深层透析。且从深层的论证逻辑看,从音乐文学角度认识元代歌行,是继续揭示歌行与乐府内部动态依存关系的有效方式,也有益于乐府学课题向更具有深度与广泛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