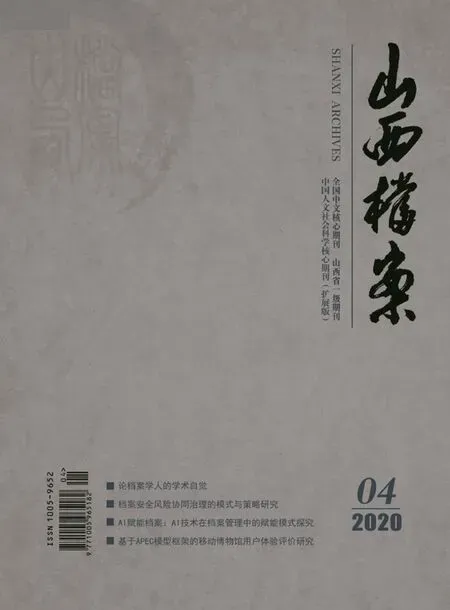档案起源:过程说与根本作用说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南宁 530006)
1 过程说与层次论
1.1 “过程说”缘起
档案起源问题,是我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最早的研究内容。之所以较早地研究档案起源问题,一方面它是档案学学习者与研究者们最早接触到的问题、最早思考的问题;同时,就我个人而言,历史学是除档案学外跟我个人关系最近的学科。我所在的辽宁大学档案专业,隶属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后来称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院),历史学的学术氛围浓厚,无论是读书的时候,还是教书的时候,历史学科都是和我们关系很近的学科。当时的辽宁大学历史系大家硕儒比比皆是,吾等晚辈耳濡目染,受益良多,今天回想起来,亦心向往之。
这种档案学与历史学的亲密关系曾经是中国档案学科共同的传统,但后来多数档案学科都脱离了历史学院,只有辽宁大学、山东大学等为数不多的档案学科仍然保持着这种传统。就事物的多样性而言,这种保留是有益的。
辽宁大学档案学科,一直保持着历史学的传统。在档案起源问题上,辽宁大学档案学科有多名学者参与了相关研究,包括关静芬、吕明军、陈辉和笔者等。分别发表了:《文书的起源──河图、洛书为我国文书之首》[1]《试论档案的起源》[2]《从考古新发现看我国档案的起源》[3]等。几十年来,辽宁大学成为中国档案史学重镇。
辽宁大学历史学为我打下了档案史研究的学术基础,而我的档案起源研究最初的触发者则是吴宝康先生的文章《档案起源与产生问题的再思考》[4]。吴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档案起源过程说,他写道:“我认为档案的起源与产生应该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它有一个从起源到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要有一个从萌芽、不成熟状态到成熟产生以至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一起前进的。不是我们过去那样(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明确把这问题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而是简单地认为档案产生于什么时候,起源于什么时候,或者起源与产生混淆不分,有的只讲起源,也有的只讲产生,没有把起源与产生作为一个过程联系起来阐述 。”这种观点的提出,在档案起源问题上是革命性的,表现出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解决档案起源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在吴先生文章的启发下,笔者写作并发表了《档案起源新论——兼与吴宝康教授商榷》一文[5],对档案起源过程说的观点给予了支持和补充。我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很赞同吴教授关于档案的起源和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看法。这种观点对研究档案的起源和产生是有指导意义的。”并“遵循这一观点,我将档案起源与产生分为三个阶段:一、原始萌芽时期的档案;二、发生、发展时期的档案; 三、档案之产生与形成。”文章肯定了档案起源“过程说”,并从上述三个阶段的角度对档案起源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明确的论述。从此,档案学术界将吴宝康先生和笔者列为档案起源过程说的代表[6]。
吴宝康先生的《档案起源与产生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不但表现出很高的学术素养,更表现出值得我们学习的学术品格。他在文章中勇于承认自己此前研究的不足,他说道“我自己在《初探》[7]中标题虽写明起源与产生, 但实际上并没有阐述清楚。”先生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勇于自我纠正,是我们这些后学的榜样。笔者继承先生的精神,在学术亦是不断突破自我。在起源论、价值论等多个研究领域,都通过不断突破自我而提升了研究水平。
这篇文章(《档案起源新论——兼与吴宝康教授商榷》)在当时还属于较高水平,是我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学界前辈陈贤华先生还在文章中给予推介[8]。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兼与吴宝康教授商榷”,是我后来后悔不已的事情。吴先生是新中国档案学的主要开拓者,我作为后辈不应该指名道姓地进行所谓的“商榷”。内容上争鸣是可以的,但对前辈的尊重也是必须的。当时我还年轻,有少不更事之嫌,事后想来颇为后悔,但吴先生胸怀宽广,毫无怪罪之意,我们之间学术上鸿雁往来,得到了吴老的诸多指点与鼓励,受益匪浅。我们成为了学术上的忘年交。极为可惜的是,吴老的书信我没有保存下来,成为终身遗憾。
1.2 “过程说”之深化
关于档案起源问题,笔者本身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过程。《档案起源新论——兼与吴宝康教授商榷》一文虽然已经明确了“过程说”的观点,并做了在当时还算较为完备起源过程的阐述,但在逻辑论证上还有所不足。所以,近十年后,笔者又发表了《档案学三题小议——档案定义、起源与档案学科属性》一文[9],对档案起源过程说的逻辑论证做了补充。这是一篇非常特殊的文章,不拘泥于普通的论文形式,对档案学中的三个重要问题——档案定义、起源与档案学科属性问题做了单纯的逻辑论证,全文的引文也很少,主要是笔者对这三个问题做出的逻辑解释,旨在阐述一种简单明了的看问题的逻辑。
档案学界有一些学术争议颇有些无谓,它们之间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而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判断的标准不同而已,只是争论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在档案起源问题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因此,笔者在《档案学三题小议——档案定义、起源与档案学科属性》中指出:
“研究和分析所有关于档案起源的观点时——尽管人们有不同的罗列这些观点的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观点无非包括记录手段 ( 结绳、图画、刻契、文字) 、社会需要( 生产发展、社会管理发展、知识发展、阶级产生、国家产生等) 两大要素。目前, 关于档案起源, 多数学者持“点”说, 即以某个特定时间( 如文字的发明) 作为档案的起源。这些说法都各有道理, 也各有缺陷。因此而争论不休, 无法相互说服。它们这种‘是与不是之间的绝对对立, 都没有为中间立场和思想的细微差异( nuances) ——里南提醒说, 真理通常在这里找到——留下空间。’ ( [美] 查尔斯) 那么, 这种可以找到真理的空间在哪里呢? 一种非“绝对对立”的立场是什么呢? 如果把大家所提出的“点”串起来, 就成为一条线, 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人们在这条线上确定不同的“点”实质上是人们采取了不同的判断标准。那么, 这些不同的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吗? 考察起来, 我们发现, 这些判断标准只是不同, 而非对立。它们实际上可以在档案起源问题上并存, 共同组成一条线(过程),来完整地说明档案起源的问题。”
文章还以人为例,说明“人正式成为“人”的时间是各不相同的,他( 她)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具有一个唯一的时间点。从各种不同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确定不同的起源时间。”并从过程说出发阐述了档案起源的过程与标志。指出:“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我们可以在事物产生的过程——线上,找出不同的点。所有的点连起来,我们才能对事物的起源,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在探讨档案的起源时,我们也应以这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和需要出发,把档案的起源看作是一个过程。并按照各个角度,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档案的起源点。这样我们对档案起源问题的认识才比较完整、全面、准确。”
笔者关于档案起源过程说的两篇文章已经发表很久了。笔者至今仍认为档案起源过程说的观点是正确的,档案学界不要再把功夫过多地花在判断标准方面的争论了,要把精力多放在把起源过程描述准确、清晰、完整等方面,不要弄得让人们看起来我们档案学界总是没有一致性,总是争论不休,没有站得住的理论。
1.3 层次论
档案的种类繁多,依据其对应的人类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次序,档案的起源亦有时间上的层次与先后。一般而言,与人类生存关系较密切的实践活动类型,其相应的档案产生得较早一些,如地理、天文气象、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档案。而在档案起源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各种档案起源的这种层次性关注的有所不足,我们所看到的文章绝大多数以“档案起源”即“文书档案起源”为题,此题之外的文章寥寥无几。如科技档案作为一种重要且起源较早的档案种类,探讨其起源问题的文章极少,目前所见主要是笔者的《科技档案起源论》[10]《我国天文气象档案的起源》[11]等文章。
笔者的《科技档案起源论》是国内专门探讨“科技档案起源”问题的唯一的一篇文章,文章已经发表20年了,但学术界仍然没有出现第二篇专门研究科技档案起源的文章,说明学界对这个问题关注度不高,也说明学界在研究档案起源问题时视野有些狭窄,只集中在文书档案起源方面。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一种遗憾,说明我们的档案起源研究缺乏多样性和层次性。
除了以上科技档案起源方面的文章外,笔者在《档案学概论》中对层次说做了明确的说明:
“我们一般所说之档案起源,指的是文书档案的起源。但事实上,档案起源存在着层次性,即各个种类的档案并不是同时起源的,有时间前后之分和种类、内容渐趋丰富之别。这种层次性的决定因素是社会需要,并与记录方式相关。
最早的一些档案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如天文、地理档案。它们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以原始图形方式记录,记录方法也比较简单。
较早的还有与经济生活有关的档案,如账本。它们在人类开始有财物积累时就产生了,西方较早产生的档案中就有寺庙的账本。其后产生的便是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档案。”[12]
2 人类进化的内在需要与事物存在的根据
2.1 档案起源的社会需要与内在根据
我在档案起源问题上的核心观点是“过程说”与“层次论”,以上所述文章和著作阐述了档案起源“过程说”与“层次论”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过程,并说明了档案起源的两个基本条件:社会需要及相关的技术条件(制作文档的信息符号工具与物质载体工具)。但这些论述的哲学高度仍然有所不足,它没有涉及档案产生与存在的根据问题,即档案的根本作用问题。讨论档案起源的社会需要与内在根据是不同的。此前包括笔者在内的档案界同仁在讨论档案起源时,多谈到其社会需要问题,诸如社会管理、知识积累、经济活动、宗教活动等方面的需要,这些社会需要对档案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们尚未触及事物的本质需求,即档案的产生对人类进化的根本意义。
档案具有凭证、参考、情感、美感等作用,但这些还不是档案的根本作用。那么,什么是档案的根本作用呢?这关系到档案起源与存在的根据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关于档案起源的第5篇文章《论档案的根本作用是人类群体思维的重要经验基础——兼论档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13]给予了回答。这篇文章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提出了档案起源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作为一种记录性经验具有的人类第二经验基础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人类第二经验基础是档案的根本作用。档案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作用,才会被人们发明和使用。“思维的记录性经验基础”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但解释了档案起源问题,也把“实践本体论”“事实性经验价值”等一系列理论彻底贯通,是我完成自己的档案哲学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笔者完成自己的档案起源论理论链条的最后一环。
2.2 档案起源与人类文明:档案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基础的基础
笔者在这里还要谈谈档案起源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关于档案与文明产生的关系问题,档案学术界早有论述,如王金玉先生指出:“文字,特别是文书, 是人类文明因素中最抽象、最理智的代表。”[14]“档案的起源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 ;档案的产生是文明形成和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15]
档案与人类文明产生的关系是什么?笔者在这里希望给予更深入的说明。简言之,档案作为人类符号记录性经验的最初代表,是文明产生的基础的基础。档案作为最早的文字记录物,它本身不但是最直接的文明载体,更重要的是,它是文明基础的基础。即思维是文明的基础,只有人类思维进化到了群体思维的阶段,人类才有可能进入文明阶段,群体思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主要有:国家的出现;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工具的出现; 文字的发明等。而这些的背后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群体性思维的产生。人类如果没有群体性思维,很难想象他们会进行国家政治活动和金属冶炼活动,而文字的发明本质上是一种较高级别符号的统一使用,更是群体性思维的表现和工具。总之,群体性思维是文明产生的基础条件。
群体性思维是文明产生的基础条件,而群体思维的经验基础是人类的符号记录性经验——最早的符号记录性经验是档案。思维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大脑的生物性功能与作为思维材料的经验基础。人类思维最早的经验基础是记忆性经验,但它主要是个体思维的经验基础,它在群体思维方面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样,人们就发明了体外符号记录性经验,这种人类性的经验形态,克服了记忆性经验的一些缺陷,成为人类群体思维的主要经验基础。档案是人类最早的原始的符号记录性经验,它就这样成为了文明产生的基础的基础。
2.3 关于记忆与记录
在人类经验的大家族中,记忆与记录[16]是最重要的成员,它们是人类经验积累的两种主要方式。需要明确说明的是,两者是相互管理又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从产生时间看,记忆在前,记录在后;从功能属性看,记忆是人脑的一种特殊功能,主要为个体思维服务,记录是人类发明的一种信息工具,具有良好的共享性,主要为群体思维服务;从存在特点看,记忆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易逝的,记录是固化的、可以长期保存的。总之,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分工是明确的。
档案是不同于记忆的人类活动的原始符号记录。但近些年来,“记忆”这个词,以“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城市记忆”等方式,与档案关系密切起来,甚至档案就等同于“记忆”了。档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记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无需言说的。那么,档案等同于“社会记忆”“ 集体记忆”“城市记忆” “文化记忆”吗?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这里简单地说说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社会记忆”“ 集体记忆”“城市记忆”“文化记忆”等方面的理论,在西方有不同的流派,中国学术界实际上是各取所需的,并没有反映理论的全貌。
第二,即使是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下,将档案直接说成是“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城市记忆”的说法也未必是适当的。因为这些“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城市记忆”都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而绝大多数档案在社会性和现实性方面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哈布瓦赫对记忆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在哈布瓦赫看来,记忆是在现实的社会文化的框架下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他认为,社会框架是一个符号系统,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都在这个系统中进行,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在交往活动中同质化,进而影响他们作为个体的感知和由此发出的回忆行为,这就塑造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记忆。[17]哈布瓦赫所描述的社会框架、符号系统、交往活动,都是现实的社会的,而档案有多少存在于这个现实的社会系统中呢?显然,大部分档案并没有现实地存在于社会活动中,它们或者静静地躺在库房里,或者被少部分人所用,只有极少的档案进入到现实的社会框架、符号系统和社会交往活动中。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档案与“社会记忆”“ 集体记忆”“城市记忆”“文化记忆”的关系。
3 丰富与深化我们的研究
3.1 提升档案起源研究的深度和宽度
对于档案起源问题的研究,应该远没有结束,要继续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宽度。在深度上,要更清晰地说明档案起源的历史过程,要跟踪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不断深化我们的研究;在宽度上,要对各种类档案的起源给予说明,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对应档案的多样化。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研究的质量。从以往的档案起源研究文章看,有些文章的质量不高,主要是缺乏新意,缺乏原创性。这样的文章应该少一点。少一点重复性工作,多一点建设性原创性工作。笔者近几年还看到探讨档案起源的文章中仍在大篇幅地描述“结绳记事”“刻契记事”“贝壳珠串记事”等事物,仍在重复前人说的话(有的做了引用注释,有的甚至没有做引用注释),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学术要不断进步,而不是不断重复。
3.2 中西比较与借鉴
在档案起源研究方面,西方档案学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但我们对他们进行关注和相互借鉴是有意义的,我们对这方面的关注也比较少。笔者仅见过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丛超的一篇小文——《中外比较研究概述档案起源问题》[18]。
在档案起源问题研究方面,西方档案学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思路是有所不同的。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是档案应该在什么时候起源?而西方档案学研究的是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档案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当然,两者都是值得重视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对丰富档案起源问题的研究很有意义。
——《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