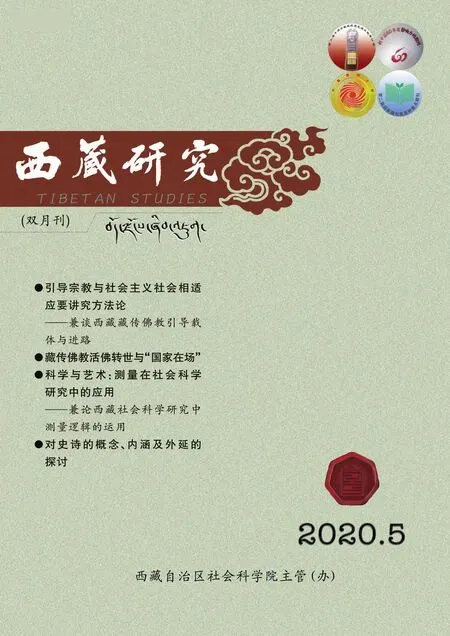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与“国家在场”
秦永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与“国家在场”理论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传承制度,属于宗教事务,但它也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3世纪下半叶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以来,它不仅成为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构成“国家在场”的特殊政治场域。翻开西藏历史可以知道,从元代开始的历代中央政府深知藏传佛教在西藏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和特殊地位,都把处理藏传佛教事务作为治藏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同时又把活佛转世管理作为主要抓手和重中之重,中央政府通过批准寻访、看视灵童、主持掣签仪式和坐床典礼、册封名号等措施的实施,牢牢地掌握着对达赖喇嘛等大活佛转世的决定权。这不仅成为活佛转世制度演变过程中“国家在场”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且成为活佛转世制度的历史定制和核心内容。因此,活佛转世成为“国家在场”的特殊政治场域,国家权力介入活佛转世成为一种政治原则和历史定制,历经元、明、清、民国时期,传承至今。
然而,近年来境外“藏独”及西方反华势力不顾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极力否定我国中央政府在达赖转世问题上的权威和主导权,美国国会众议院还于2020年1月通过了一项赤裸裸地干涉我国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的“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因此,对历史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进行多视角的学术研究,澄清事实,批驳谬误,成为学术界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活佛转世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以“国家在场”的视角探讨藏传佛教及活佛转世制度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以人类学的“国家在场”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国家权力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历史定制形成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作一个简要地梳理。
“国家在场”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最早出自美国著名学者米格代尔(Joel S.Migdal)《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1]一书,可直译为“国家在社会中的视角”,它主要探讨国家权力在社会领域中的存在与体现,即国家通过政策、法律、运动、行为、仪式、场景等方式对民间社会产生影响,民间社会采取一定的方式和策略对“国家在场”进行回应。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概念被引入中国学术界,有学者把米格代尔“a state in society perspective”直接译为“国家在场”[2],此后这一术语被学术界广泛运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学等学科纷纷借鉴这一研究思路,并将它运用到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解释模式。同样,在“国家在场”理论视域下,阐述自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管理,揭示国家权力与活佛转世制度的互动,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研究视角。
二、历史上的活佛转世与“国家在场”
(一)元代(1271—1368年)
“活佛”藏语称作“朱古”,本意为“化身”。活佛转世出自佛教灵魂不灭、生死轮回、佛以种种化身普度众生的观念。活佛转世制度始于13世纪末期,至元二十年(1283年)藏传佛教噶举派大师噶玛拔希圆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一位出生于后藏贡塘的男童被迎请到噶举派主寺楚布寺,被认定为噶玛拔希的转世,这是藏传佛教首位转世活佛,即第三世噶玛巴·攘迥多吉(1284—1339年)。后来噶举派的活佛转世方式逐渐被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吸收和发展。
13世纪由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行政管理之下,从此也正式开启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管理。早在元王朝建立之前的13世纪上半叶,蒙古势力就已开始经营西藏地区。太宗十一年(1239年),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蒙古皇子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兵到达西藏。当时的西藏在政治上处于互不统属的分裂状态,但民众笃信宗教,藏传佛教在西藏地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势力较大的有萨迦派、噶举派。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蒙古统治者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策略,建立帝师制度,优渥喇嘛,册封宗教领袖;设立宣政院,专门掌管佛教及西藏事务。
真后三年(1244年),阔端致信西藏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贡噶坚赞要求他速来凉州商谈[3]81,63岁高龄的萨班遂不顾年老携侄八思巴(1235—1280年)等人从西藏出发,于定宗二年(1247年)初与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达成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的协议,萨班发表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3]91-94,西藏地方正式纳入元王朝直接管辖。元中央政府为了维系和巩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利用传统的宗教势力行使统治权,对西藏各教派首领封赐名号、授予印信进行笼络,其中不少教派领袖也是转世活佛。当时萨迦派的教主由昆氏家族内部世袭传承。宪宗元年(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其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宪宗三年(1253年),八思巴应召赴六盘山觐见忽必烈,给忽必烈和皇后传授了萨迦派喜金刚灌顶,被忽必烈尊为精神导师,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4],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这使八思巴身兼西藏地方宗教领袖和朝廷命官两种身份。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又赐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化身如来,宣文辅治,大圣大德,普觉其智,佐国如意,造字圣人,大元帝师”[5],并赐玉印,帝师制度自此成为定制。从八思巴受封帝师直至元末,帝师之职一直由萨迦昆氏家族或其门徒担任。帝师是元朝皇帝管理西藏的代理人,位高权重,皇帝的旨意可通过帝师昭示于西藏,帝师法旨的效力仅次于皇帝的圣旨,史载“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6]。在忽必烈对宗教、政治方面的大力扶持下,萨迦派在西藏境内建立起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
元朝不仅对萨迦派领袖尊崇有加,对噶举派宗教上层也非常重视,对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噶举派支系较多,历史上其活佛多系师徒传承。宪宗六年(1256年),元宪宗蒙哥汗召请正在甘肃一带传教的噶举派领袖人物噶玛拔希(1204—1283年)赴漠北觐见,赐金印、金边黑帽,从此,这顶黑帽成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系统传承的标志。至元二十年(1283年),噶玛拔希在西藏楚布寺圆寂,攘迥多吉成为其转世活佛,即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至顺二年(1331年),笃信佛教的元文宗图帖睦尔遣使召请攘迥多吉进京,为皇室说法。次年攘迥多吉抵达大都,适逢元文宗薨逝,攘迥多吉于元统二年(1334年)五月从大都起身返回西藏楚布寺。行前,继任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赐国师玉印、金字圆符[7]。此间,元顺帝还封攘迥多吉的弟子扎巴僧格(1283—1349年)为灌顶国师,并赏赐红帽,从此开启了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的转世世系。至元三年(1337年)三月,攘迥多吉再次应元顺帝之召抵京。至元五年(1339年)六月,攘迥多吉在上都病逝,舍利运回西藏楚布寺造像供奉[8]。在攘迥多吉两次进京及其在元朝宫廷活动的过程中,其政教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与元廷尊崇的萨迦派帝师、国师相近。至正二十年(1360年)底,黑帽系第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1340—1383年)奉元顺帝之命抵京,受封为“持律兴教大元国师”,受赐水晶印。若必多吉在元宫廷中活动了4年,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启程返藏。他返回西藏后,从明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每年派使给新生的明王朝进贡。从此,西藏地方政权、宗教上层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敕封、进贡的双向互动关系一直延续下来。
由上可见,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开始形成起,元王朝通过封赐名号、召其入觐、朝贡等形式,将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纳入其直接管理之中,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存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朝优崇佛教领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策略,既稳定了西藏地方的发展,又加强了元朝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理,这也为其后明清两代统治者治理西藏提供了一个范式。
(二)明代(1368—1644年)
洪武元年(1368年),明王朝代元而起后,在吸收元制的基础上,采取“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一是广行诏谕,广泛册封各教派领袖,二是实施朝贡政策。
明廷对当时影响较大的藏传佛教三个教派上层封授“法王”称号。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皇帝册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1384—1415年,汉文史籍中称“哈立麻”)为“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9],颁赐诏书、金印,从此“大宝法王”成为历世噶玛巴活佛的专有尊称。得银协巴圆寂后,宣德皇帝派员“审察”转世灵童,是为中央政府首次派人进藏直接介入活佛转世事务。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皇帝册封萨迦派首领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颁赐诏书金印。宣德九年(1434年),宣德皇帝册封格鲁派首领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
除以上三大法王外,明朝永乐年间还在西藏及朵甘都司辖境内相继册封了五大教王:永乐四年(1406年),封西藏帕竹政权首领扎巴坚赞为“阐化王”;永乐五年(1407年),封西藏僧人宗巴干(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封灵藏(今四川甘孜一带)僧着思巴监藏为“赞善王”;永乐十一年(1413年),封噶玛噶举止贡寺座主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封后藏萨迦派僧人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10]。明廷给五大教王册封的同时,都要赐予金印、诰命。上述“五王”系领有封地的政教首领,互不统属,五王的承嗣须报告朝廷认定,听候中央遣使册封。
明廷这种充分依据藏地各教派实力大小和各地区代表性而进行的分封,改变了元朝将西藏的宗教和政治权力集于一人、一家、一派的局面,使明中央王朝与西藏之间建立起了更广泛的政治领属关系。明朝实行“广行招谕、多封众建”的政策,除册封藏传佛教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外,对归顺明朝的其他宗教领袖封授品秩不一的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号,致使各种封号泛滥,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明朝规定受封的西藏各地僧俗官员,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履行向明朝朝贡的义务。加之明朝对朝贡的回赐相当丰厚,使藏地各派僧人纷纷遣使来贡,朝贡者络绎不绝。于是,明朝具体的朝贡政策,其形式分为请袭朝贡、谢恩朝贡和例贡,等等。如请袭朝贡,明朝规定除三大法王的名号可由师徒或转世者继承,其余五教王和灌顶国师等王位的承袭都必须上报明朝中央,听候中央的批准册封。朝贡是一种政治行为,这是明朝对西藏地方确立隶属关系,行使政治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领袖们通过这种定期的进贡,不仅获得了丰厚的赏赐,还加强了他们在本地区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也使其真正成为中央政府在地方统治的代言人。
(三)清代(1644—1911年)
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在承继元、明治藏策略的基础上,采取了通过扶持格鲁派来加强对西藏统治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除利用传统的册封等形式外,还大胆创新,通过制定法律等手段极大地加强了对活佛及其转世事务的管理,使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日臻完善。清代的活佛转世事务由理藩院和驻藏大臣负责。该阶段,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更是体现了国家在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继续册封宗教领袖;二是实行金瓶掣签制度;三是对违法犯罪的活佛实行废黜制度。
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召到达北京朝觐清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特派钦差至扎什伦布寺“照封五世达赖之例”,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自此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活佛系统和班禅活佛系统的名号及其在西藏的宗教地位,从此以后,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后须经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成为定制。清朝除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外,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皇帝正式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并让其管辖蒙古国喀尔喀等部之宗教事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皇帝又封章嘉呼图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掌管漠南蒙古的佛教事务,从而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执掌蒙藏地区藏传佛教事务的局面。
由于中央政府的支持,格鲁派大活佛拥有西藏政教大权,因此,特权阶层争夺其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大权的斗争不断发生,贿赂、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等现象愈演愈烈,一度造成大活佛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的结果,这不仅危及佛法,也严重影响到蒙藏地区的社会稳定。乾隆皇帝为了整饬格鲁派活佛转世中存在的弊端,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明确了清朝驻藏大臣在掣签中的地位,以及中央政府在灵童转世问题上的批准权,从此以金瓶掣签的方式确定各大转世活佛,成为历史定制。清代,经理藩院注册的呼图克图以上的大活佛及各教派领袖人物的转世都必须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来进行。清朝中央特制的两个金瓶,一个奉于拉萨大昭寺,供西藏地区遴选达赖、班禅等大活佛时掣签之用;另一个奉于北京雍和宫,供遴选蒙古、青海等地区大活佛时掣签使用。如果寻访到的转世灵童只有1个,确实没有任何异议的话,经过中央政府特许批准可免于掣签。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在清朝理藩部注册受管的大的转世活佛共有39位。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皇帝创立金瓶掣签制度直到清末的100多年,西藏地区39个活佛系统中,共认定转世灵童91位,其中用金瓶掣签认定的有76位,由于种种原因经清朝中央政府批准免予掣签的有15位(1)李德成:《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发展》,载《光明日报》,2011年11月7日第11版。美国学者欧麦高(Dr.Max Gordon Oidtmann)指出,“金瓶掣签”是清廷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双赢方案,从1793—1825年间,大约一半重要“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使用了“金瓶掣签”,对52个不同的重要转世活佛世系一共使用了79次,更特别的是,其中的40多例竟是由西藏地方主动要求清廷进行金瓶掣签选任“转世灵童”。相关内容参见Max Oidtmann:Forging the Golden Urn: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欧麦高:《金瓶铸就:大清帝国与西藏活佛转世政治》,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由此可见,绝大多数转世灵童的确认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
清朝虽然对藏传佛教宗教领袖继续采取册封措施,但改变了明代滥封活佛名号的弊端,严格封授,对个别违法犯罪的活佛直接废黜其所授名号,甚至直接废除其活佛系统,禁止转世。康熙帝曾以寻访与认定未经中央政府批准为由,准奏废黜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下令将其押送北京,并派遣军队护送新认定的达赖转世灵童格桑嘉措至拉萨坐床,赐金册金印,是为第七世达赖喇嘛。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皇帝曾以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夏玛巴活佛确珠嘉措勾结廓尔喀人扰藏之罪,勒令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禁止转世,并强令其所属百余名红帽系喇嘛改宗格鲁派,十世夏玛巴活佛确珠嘉措畏罪自杀,从此,噶玛噶举派红帽系不复存在。清末,受外国势力的威逼利诱,十三世达赖喇嘛分别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宣统二年(1910年)出走蒙古地区和印度,清政府遂以勾结国外势力为由,两次褫夺达赖喇嘛名号,后查明其出走“非出本心”,便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和“民国”元年(1912年)又恢复了达赖喇嘛名号,使得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得以继续传承。
(四)民国时期(1911—1949年)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边疆危机加深,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控制力减弱,但继续对西藏实施主权管辖,并高度重视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民国时期的活佛转世事务由蒙藏委员会负责。该阶段活佛转世中的国家在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按照历史惯例,中央政府主持完成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第九世班禅的转世事宜。1925年,九世班禅大师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来到内地。1931年6月,鉴于由藏来京的九世班禅拥护国民政府、执行中央决策的爱国之心,国民政府下令:“班禅额尔德尼志行精诚,翊赞和平统一,此次远道来京,眷念勋劳,良深嘉慰,著加给‘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以示优异”[11],并颁授玉册、玉印。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圆寂,国民政府追赠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封号,特派致祭专使戴传贤前往甘孜致祭[12]。1949年6月,在青海寻访到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后,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签署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3]8月10日,由中央特派专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赴西宁,在青海塔尔寺主持完成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坐床典礼。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十分重视,特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入藏致祭。次年9月,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黄慕松代表中央颁给玉册、玉印[14]。1935年10月,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致电西藏地方政府,指出达赖喇嘛转世应遵守清乾隆时期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慎重寻访,并要求将寻访进展随时报告中央。1938年寻访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国民政府依照历史惯例,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吴忠信抵藏察验灵童情况后向国民政府呈报,1940年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14]290-2912月22日,吴忠信代表中央在布达拉宫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与达赖喇嘛座位平行。吴忠信进藏察验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和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充分彰显了国民政府对西藏所拥有的主权。
二是颁布了《喇嘛转世办法》,活佛转世管理进一步走向法制化轨道。民国政府在吸收前朝政府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加强了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依法管理,相继出台了针对藏传佛教及活佛转世的诸多法规,于1934年颁布了《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1935年颁布了《管理喇嘛寺庙条例》,1936年又颁布了《喇嘛登记办法》《喇嘛任用办法》《喇嘛转世办法》《喇嘛奖惩办法》等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20多项法规条例。其中《喇嘛转世办法》是中央政府颁布的第一个专门规范活佛转世管理方面的法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明确了活佛转世范围、活佛圆寂和转世灵童寻访须呈报中央、转世灵童掣签地点与程序、活佛认定方式、活佛印信管理、活佛前辈物品的使用、免除金瓶掣签的最高决定权等[15]。这使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起到了活佛转世有法可依的历史作用。民国政府以此为据,依法办理和完成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的认定、坐床等事宜,牢牢掌握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的控制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三、结语
综上所述,自元代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以来,至清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大致而言,其核心内容为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和坐床三大环节及其相关仪制,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掣签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已成为历史定制。自元朝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通过采取封授名号、批准寻访、主持掣签仪式和坐床典礼等措施,掌握着达赖喇嘛等大活佛转世的决定权,并通过立法等措施,使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中央政府对有影响的大活佛封授名号等措施,将藏传佛教上层纳入到了国家的边疆治理体系中,这既体现了国家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在大活佛转世认定上的权威,同时也强化活佛等藏传佛教上层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从而实现了对西藏地方有效治理的目的。就历史上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旧西藏的佛教僧团而言,他们对国家的在场管理既有依赖性也有妥协性,各教派为取得统治西藏地方的政教权力都力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籍此不仅获得了进入国家体系的合法性及自身发展的机会,并且也强化了对信教民众的政教控制力。
可以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形成、发展并延续至今的历史过程,是藏传佛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是藏传佛教中国化逐渐加深的过程,也是历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国家在场”成为一种原则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发展,活佛转世这一历史现象,将会在较长的历史时空中延续下去,并影响着涉藏相关地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相信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力量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这一特殊宗教制度的存续过程中将一直“在场”,这也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