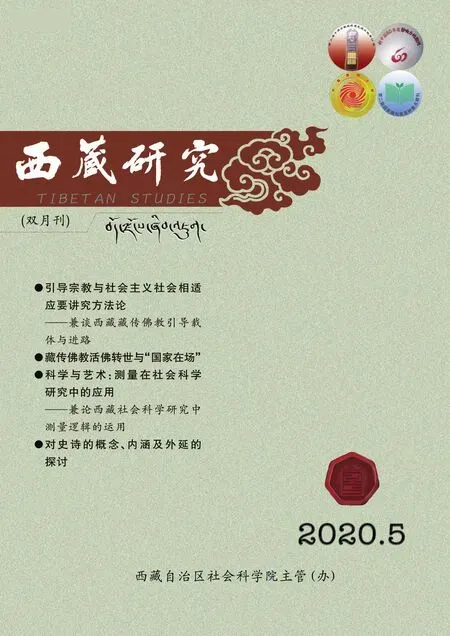论象征符号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神圣性建构
廖云路
(西藏日报社,西藏 拉萨 850000)
作为藏传佛教在社会中的载体,寺院是藏传佛教实现其社会功能的重要载体。在寺院的时空环境下,藏传佛教体现为一套象征符号体系。象征符号在人与神之间充当传递信息的媒介,不仅是寺院神圣性的所在,使藏传佛教的实践可观察、可理解,还将宗教内化为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从象征符号分析藏传佛教寺院神圣性的建构,为理解藏传佛教之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
一、象征符号视野下的藏传佛教寺院
宗教之所以能从人们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中分离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神圣世界,其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人与神之间的对话,为变化不羁的世俗世界提供终极意义。宗教“用其神圣的帷幕遮盖住制度秩序的一切人造的特征”[1]11,宗教的神圣性是一种观念的、抽象的存在,为使这种超现实的力量能够介入到现实环境中并发挥其功能,神圣性又需要附着于实在的象征符号,于是便有了神灵、宗教场所、专职宗教人员等的出现。
符号分类有三个基本角度:一是从符号载体的属性进行考察,二是从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进行考察,三是从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进行考察[2]。符号有类似语言的组织能力,从而拓展其使用的广度和深度。象征符号是社会文化的可感知的表达机制,通过类比联想的方式赋予事物规范、意义、价值,从而在社会关系模式中反映出社会集体情感意识、心理状态、价值规范体系和文化现象。藏传佛教寺院借助象征符号,指向一个神圣的领域。
从象征符号的分类上看,以符号自身与建构对象二分对立方式的符号象征体系可以划分为语言符号、工具符号。语言符号是以具体的文字、声音、图像等为载体的符号体系。语言符号建立在参与者共同的认知图式上,包含着解释与理解的目的。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宗教器物从世俗之物转换为神圣之物,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禁忌等语言符号的共同经验积累;而宗教仪式通过弹奏、唱诵、蹦跳、涂抹甚至哭泣等方式,表达宗教教义的同时,起到了人与神之间情感的沟通作用。此时的语言符号是一种策略性行为,旨在强化神圣的主题。
工具符号是除了语言符号之外的意义表征符号体系。它不仅是表示一种事物的标识,还具有支配性的工具效力,能够作用于发生关联的个体或群体,使之呈现有关社会秩序的象征表述。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工具符号的介入使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方式更为丰富,让不能直接被感知到的观念、价值、情感等神圣世界变得可观察、可理解。宗教活动参与者通过工具符号强化了宗教的社会价值,传递一种集体规范力量。
象征符号展现了藏传佛教的宗教教义、宗教活动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体系。作为认知图景的基本构成元素,象征符号必须通过宗教实践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按照杨庆堃对宗教的分类,藏传佛教属于制度性宗教,是有系统的教义、仪式和组织体系的信仰形式[3]。藏传佛教自身无法表达,需要借助寺院这一载体。本文从藏传佛教寺院中常见的神灵、供品和仪式等构成要素角度,揭示语言、工具符号是如何相辅相成建构起寺院的神圣性的,这套意义体系又是如何推动宗教的社会功能与现代社会环境相结合的?
二、神像的象征符号
神灵是寺院最为重要的资源,是寺院得以成为寺院的基础。部分寺院甚至可以“有寺无僧”,但必须要有神灵这一象征符号,独特的神灵往往是寺院神圣性地位的关键。“人类在宗教生活中,往往通过将一些特定物品人格化的方式,赋予这些物品以特殊的宗教意义。”[4]护法神是藏传佛教寺院最重要的神灵之一,诞生之初原为保护该寺僧人能专心学经、寺宅平安,但由于其世间神灵的特征(1)藏传佛教护法神分为出世间护法神和世间护法神。出世间护法神表示已经脱离轮回之苦,不再管理世间事物,属于高等级神灵,如大威德金刚、吉祥天母等;与之相对的世间护法神则是还没有脱离人世,需要不断建立功德的护法神,如孜玛护法、扎基拉姆等。在藏族信众眼中,世间护法神往往比出世间护法神更为灵验,有很多关于世间护法神附体到人身上的说法,被附身的人于是便有了神迹。,吸引了大量信众的朝拜。几乎每座藏传佛教寺院都有护法神,护法神及其相关的象征符号构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独特场域,给信众以区别世俗社会的神圣感。
奥地利学者勒内·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曾对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进行过细致描述。在容貌上,护法神的嘴因愤怒而龇牙咧嘴,嘴角突出长牙,往往上齿咬住下唇;双眼凸出而血红,透露出凶猛的神情,一些神灵在额头上还有天眼;护法神的头发蓬乱,上面结满了污垢,有的将头发扎成一种发髻,用珍珠、绿松石、龟壳等作装饰。在着装上,除少数护法神赤身裸体外,大部分都穿着兽皮或粗毛材料制成的衣物。例如,一些护法神的围腰是用牦牛或秃鹜等的毛制作而成;许多护法神身着的披风是从马等牲畜身上剥下的皮、内脏等材料制成,这些衣装还会搭配丝带、珍珠带、金带或绿松石带子当腰带。此外,护法神身上的饰品也十分多样,胸前的项链由人骨或海螺、宝石等打磨而成,许多护法神带有手镯、脚镯,通常是金、银打制的。
以拉萨扎基寺的护法神扎基拉姆为例,该护法神头戴人头骷髅头冠,吐着火红舌头,面目狰狞,还长着一双鸡脚,其外形的独特性衍生了许多流传于僧众口中的语言符号。学者西尼崔臣在《拉萨扎其护法女神及其扎其寺》一文中引用过民间关于扎基拉姆由来的传说:扎基拉姆原为清朝乾隆皇帝的妃子,年轻漂亮且富怜悯之心,但也引起了其他妃子的嫉妒,被打上莫须有的罪名关入监牢,并遭毒害。由于含冤而死,这位妃子化作厉鬼,时常在皇宫附近吓人。乾隆皇帝不得不邀请色拉寺吉扎仓堪布强巴敏朗大师到北京举行酬补仪轨,以平息她心中的怨恨。最终女鬼被降服,并跟着大师回到西藏,成为捍卫佛法的护法神[5]。
还有学者认为,强巴敏朗向皇帝迎请事毕后返藏途中,一位中原内地女神紧随而来,并停留在了现在的札什寺(指扎基寺)地方,这位女神就是后来的扎基拉姆,“神灵的形象逐渐被藏地化后发生了改变,鸡脚可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6]。由于扎基拉姆的身份由来指向内地,因而又被视为藏汉文化交流的产物,并逐渐代替原来关帝庙的地位,留下了求财非常灵验的名声,“每天向她敬酒向她朝拜的人群一直络绎不断”[7]。
扎基拉姆来历的一种版本流传开后,不同人又根据自己的理解逐渐演化出多个版本,但每一种版本都基本能构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因而也广泛被僧俗所接受。对于宗教神话、传说而言,大都难有确实的文字记载,或者说一种确实记载的意义并不大。语言符号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反而增加了神灵的神秘感,成为依附于神灵这一实体之上的文化资源,更能吸引信众对于神灵的兴趣与向往。
寺院既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场所,又是诸神的居所。神之所以为神,在于神圣与世俗间的区隔,“神圣之物是世俗之物不应该也不可能接触之物,否则必遭惩罚。”[8]寺院通常将神灵置于位置较高的橱窗中,神灵的目光要高于人的目光。橱窗是封闭的,一是可以与信众拉开距离,树立神灵的神圣性;二是避免神灵被风烛蚕食,保持神灵清洁的同时,便于寺院管理;三是可以在橱窗里摆放花束等供品,进一步美化神灵。
扎基寺对扎基拉姆作为工具符号的展示却有所不同。扎基拉姆被单独供奉在一个开放式的橱窗里,橱窗一次可以容纳一位信众进入。扎基拉姆被供奉在桌子上,底座与人的肩部平行,整个佛身则稍高于人的身高。信众朝拜方式通常是掀起神灵衣服一角,用额头轻贴神灵的底座,触摸她的鸡脚,同时双手合十,嘴里念经或许愿。部分信众还自带手表、项链等小物件在扎基拉姆的躯干部位摩擦,以获得开光的象征意义。
直观的宗教体验是增强信众宗教委身和信心的重要方式。与扎基拉姆相似,拉萨丹杰林寺的护法神红面狱卒被供奉在半开放式的橱窗里,以更加直观地向信众展示。红面狱卒的橱窗里接出来一根类似于辫子般粗细的绳子,是信众与神灵交流的工具符号。信众通常将额头轻触在绳子上,开始念经并祈祷;在信众较少时,还会用绳子在全身“涂抹”一遍,这种更加彻底和深层次的加持方式被认为可以消除人体身上的痛楚。
扎基拉姆、红面狱卒都是藏传佛教中著名的世间护法神。从宗教神圣性本身包含的人性异化角度看,世间护法神自然要更多地承担起人与神之间的交流,神灵作为工具符号的角色凸显。信众不会认为触摸护法神是一种不尊重,甚至降低其神圣性,反而将这种朝拜礼仪视为神对人的加持与关怀,一旦追求的回报实现,会更加归因于“灵验”。允许触摸但不表示没有禁忌,如触摸神灵脸部肯定是不可以的,也不允许信众对僧人、神灵拍照。当然,这些禁忌不可能完全落于纸上,只能依靠工具符号使用中的成规加以约束。
三、朵玛供品的象征符号
藏传佛教供品是用来讨好神灵的。寺院中最常见的供品是朵玛——一种用糌粑、酥油和水捏起来的面团,上面贴着酥油花制成的法轮、花瓣样式的装饰。根据仪式和供奉神灵的不同,朵玛的形状、颜色、大小规格也有所差异。“西藏有很多的文献记载有关朵玛供品的情况,有的文献详细地记载了朵玛的制作过程,说朵玛至少有一百零八个品种。有的朵玛,仅有几英寸高,有的则高达十英尺。例如一种叫做护地神朵玛的朵玛就是巨型供糕。”[9]419朵玛也可用作替换物品或伏魔术中使用的物品,在仪式结束之后就要抛弃或者供牲畜食用。
“仪式与暴力、毁灭和寻找替罪羊,密切相关。特别是,它们富有戏剧性。”[10]供品通常不会单独供奉,与朵玛同时供奉的还有清水、干花、藏香、大米、青稞和饼干等。当几种朵玛供品组合在一起时,供奉时有何讲究、有怎样的情节和故事、背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则基于语言符号对其神圣性的建构。
在一种名为“百供驱魔”的供品中,僧人首先制作了小型锥形朵玛,一部分朵玛分别涂上绿色和蓝色的矿物颜料,另一部分未染色的朵玛则是他们的食物。这些朵玛被围成四方形,僧人再在中间的地方用糌粑制作了人偶和魔鬼,人偶前面还有一盏糌粑捏成的酥油灯。这个供品的寓意是驱魔,僧人念经之后,将糌粑做成的酥油灯点燃,魔鬼就把信众替身的人偶吃掉,保佑信众平安。
西藏有很多的驱鬼仪式也用人的模拟像。“假如有某个妖魔威胁某人、某家族或某部落的安全,人们便有举行特殊的打鬼仪式,制成模拟像。这样,所有威胁个人和家族的鬼怪和瘟病都附在人们制作的模拟像身体上,人们便可以安然无恙。”[9]433朵玛的制作精细而耗时,僧人有时制作一个模拟人偶需要捏出眼睛、头发和嘴巴,细节的地方还用刻刀,用小木片固定住人物的身体和头部,并用矿物颜料对细节之处染色。
除了人偶外,僧人们还制作须弥山,须弥山是糌粑垒起来的四方形基座,通常是四层,代表世界;有时制作大象、马等动物,大象在藏族看来是吉祥的动物,常见于壁画中,而马则代表人的牲畜,并有保卫和作战的意思。一些难以用糌粑捏制寓意,则可以用画在纸上的语言符号来表达。例如,“姜普”是一种插在糌粑上的扁平木条,木条前面贴着一张纸,上面绘有男人、女人的素描,用来代替某个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成员。一种十字网格的供品名叫“垛”,基本形式是用两根细木棍绑扎成十字架,从十字的中心向外缠绕彩色毛线,制作完成后的样子像一张蜘蛛网。“垛”代表着神灵的栖息地,通常插在须弥山上,有时还要加上一把幡盖,在整个供品营造的故事中,是驱邪降魔的关键法器。
“五官供品”的制作比普通的朵玛更为复杂。五官供品与人的五大器官相对应:一个撕裂的心脏代表觉识或触觉,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代表视觉,伸长的舌头代表味觉,隆起的一对鼻孔代表嗅觉,一对宽大的耳朵代表听觉。五官供品比一般的朵玛体积更大,制作更加精美,同一类型的五官供品可能有几种相近的造型。为了凸显五官的特征,上面还涂着矿物颜料调制而成的几种色彩。五官供品代表人们寻求来世的意识,“五官及其相应的五觉是‘门’,通过这道‘门’,寻求再生的意识最终感受到了这个世界。”[11]
朵玛供品具有通灵的媒介、献祭的礼品、驱魔的道具等功能,没有这些供品在场,僧人念经的作用和意义就无法实现。朵玛制作与展示的过程,也是供品作为工具符号介入人与神关系的过程,符号的意指功能与宗教参与主体发生了关联。
在前一天念经仪式结束后,寺院僧人会根据第二天要念诵的经文,制作相应的朵玛供品。制作过程通常就在佛殿之中,并不避讳信众在场,因而又具备了仪式的表演性。当信众见到供品的制作时,通常会低头念经,并对僧人和寺院布施。这既是出于对僧人劳动的敬畏,又是对因供品建立起的藏传佛教与信众身份关系的确认与强化。
制作完成的朵玛供品被供奉在寺院神灵之前,通常用一张单独的藏桌陈放。供品的陈列与僧人的念经,共同指向供品背后的宗教功能,供品也因此作为工具符号联系着信众与宗教所营造的神圣世界。在念经仪式结束后,僧人将部分供品切成小块放在一个托盘里,信众会像吃饼干似的捏一块品尝,年龄稍大的信众还会拿一块带回家中,认为会带来好运,由此又延伸了宗教对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的影响。
藏传佛教寺院中的朵玛供品大都讲述着神灵、魔鬼与信众之间的关系,故事神秘而又难以用语言表达。按照仪轨,这些供品中还要用到替魔人的一些指甲或毛发等,最好用那人洗过身体的水来和制糌粑,以此治疗人们因祟于妖魔而得的疾病[9]433。在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背景下,这些仪轨都被较大程度地简化和省略了。然而,在寺院供品制作和供品展示的过程中,依然保留了大量有别于世俗之物的一面,这既是神圣性确立的过程,又是帮助信众认识宗教和加深信仰的方式之一。
四、宗教仪式中的象征符号
彼得·贝格尔从功能角度揭示宗教的本质时认为,宗教活动就是建立一种神圣的秩序,而一切的秩序化都具有某种神圣的特征。“它的神圣性要通过种种仪式,才能象征性地得到重新肯定。一旦失去了这种特性,它就成为世俗的了。”[1]6宗教与仪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仪式构成了宗教的基本特征,宗教以仪式的方式得以实践。在藏传佛教寺院中,语言、工具象征符号共同支撑了宗教仪式展演进程。
藏传佛教寺院通常依据藏历安排日常性仪式,仪式的时间与内容是固定的,由本寺僧人完成。念诵的经文有多个音调和语速,时而语速轻快、时而浑厚有力。根据经文内容的需要,僧人们各自分工负责击鼓、吹法号、敲铙钹、摇碰铃等乐器。当诵经声与乐器声齐鸣时,寺院的气氛庄严而震撼。
宗教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并非以僧人念经的语言符号为开始,仪式准备过程就包含了工具符号的介入。念经之前,每位僧人都要来到寺院正殿中央,面向供奉的神灵磕三个头。藏传佛教教义认为,磕头的目的是洗清世俗世界中的贪、嗔、痴、慢、妒“五毒”,以求接近于佛的功德。僧人念经时身穿红色袈裟、头戴千佛冠帽。僧人磕头后,起身整理好僧服,坐到固定的位置上,靠近主供佛位置由年龄最大的僧人和领经师就座,年轻的僧人坐在最外面。这些工具符号都是从世俗世界向神圣世界转换的准备。
当语言、工具符号有机结合为一体时,宗教仪式被推向高潮。空行母是荟供法事的一种,每位僧人的眉心涂上红橙色朱砂,念经的形式从快速朗读变成诵唱,称为荟供歌。几名僧人从卡垫上起身来到正殿中央,面向佛像和其他就座的僧人领唱荟供歌,其他僧人们跟着音调附和。仪式过程中,站在正殿中央的僧人手持供品和用木碗盛着的经过加持的圣水,依次走到就座的僧人面前,每位僧人从碗中蘸取圣水,再洒向空中。这一仪轨完成后,僧人们再顺时针绕着佛殿转,最后将供品和器物供奉在寺院主供佛前。
在藏传佛教重大节日和寺院传统的重要时间节点时,寺院还会举行展佛、讲经、火供等宗教仪式。寺院的开放性通常吸引信众的参与,由此形成僧俗共享的仪式。宗教仪式规模的扩大与仪轨的复杂性,促使象征符号使用的丰富性。
以这类仪式中常见的讲经为例,讲经原本由德高望重的经师向僧人传授为僧之道,而广大信众也把讲经视为面见高僧和提高自身修行的机会。仪式的第一个环节通常为僧众集体念经,仪轨中由僧人带头领诵和吹奏乐器,以信众熟悉的经文进入主题的方式容易引起广泛的参与。寺院的氛围由于念经而变得庄严肃穆,调动起经师讲经与信众听经的积极性,当念经声停下时,僧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师身上。
讲经仪式以阐释《入菩萨行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典籍为主,经师根据经文的内容,引用著名高僧大德的名言,再结合僧众日常生活中的案例加以说明。这类语言符号包含着一种理解的目的,而该目的的基础在于仪式参与者共享的认知图式。由于大部分僧众对经文的理解多停留在记忆与背诵,讲经将深奥的宗教教义转换为僧众可理解的语言符号,有利于引导僧众思考,在发心起念上遵循教义,唤起僧众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讲经仪式中,宗教需要借助工具符号加以固定和强化。工具符号的参与不仅引出情感表达或刺激了欲望,还在参与者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宗教价值规范的遵循、完善以及再生产。讲经仪式通常持续数日,寺院需要提前装饰场地、准备茶水和调适音响设施等,这些工作由僧人和信众共同完成,日常宗教禁忌在劳动过程中被打破。寺院布置上的变化又营造了一个有别于日常性宗教仪式的神圣时空环境,再加上日常性宗教仪式中很少使用的宝座、乐器、僧服等,集中凸显了讲经仪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工具符号的介入增加了宗教仪式的表演色彩,其形成的感染力加深了信众对宗教的信任与委身。“他们坚信通过寺院里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可以洗涤他们身上沾污的前世或现世中的各种罪孽,培育宗教伦理道德种子,为来世有个好报打下行善积德的基础。”[12]在讲经仪式中,工具符号的使用频率、使用范围、使用方式的多样性等,与信众的虔诚表现呈正相关关系。当僧人身着宗教礼服、奏响宗教乐器、向信众供茶时,信众的宗教体验被激起,更自然地做出磕长头、双手合十、向寺院布施等行为。这些行为会在僧人与信众、信众与信众之间相互传染,由此内化为宗教之于社会的行为规范。
无论是讲经中的语言符号,还是作为工具符号的供品、法器和参与者的行动,象征符号让宗教仪式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并成为神圣意义和宗教经验产生的催化剂。虽然象征符号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断重复的,但重复不等于无效,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仪式化的手段加强神圣性,还能促进信众形成集体记忆,增强对宗教解释的信心。
五、结语
藏传佛教之所以成为制度性宗教,离不开一套完整的象征符号体系。藏传佛教自身无法表达神圣性,必须要借助象征符号在寺院的实践。象征符号在人与神之间充当传递信息的媒介,使藏传佛教可观察、可理解,也使得寺院空间明显有别于世俗空间。
从对神像、朵玛供品和宗教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分析来看,语言符号大都讲述着神灵、魔鬼,以及宗教教义与信众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这些叙事神秘而又难以理解,但恰好是区别于一般世俗语言的神圣性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符号经过社会再生产,关于神像、朵玛供品、宗教仪式等载体叙事变得多样与丰富,成为附着在寺院之中的文化资源,更加吸引信众对于宗教的兴趣与向往。工具符号以宗教载体在寺院中的“自我呈现”,介入到人与神关系的过程,这种更为直观的宗教体验是增强信众宗教委身和信心的重要方式。从朵玛供品的制作中可以看出,在藏传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寺院中的部分仪轨已较大程度地简化,工具符号的呈现方式也随之简略,但符号强大的意指功能依然可以传达神对人的神圣性影响。在宗教仪式中,语言符号充实了工具符号的内涵,工具符号加深了语言符号的表达效果,两者的有机结合将宗教仪式推向高潮,宗教的神圣意义和信众的宗教情感共同达到顶点。
人与神关系不是单向建构的,信众通过神像、朵玛供品和宗教仪式中的象征符号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宗教价值的遵循、完善以及再生产。象征符号还具有很强的效仿性,通过在僧人与信众、信众与信众之间相互传递,内化为宗教之于社会的行为规范,而寺院也会根据象征符号的传播效果,适时调整宗教载体的神圣性表达。
总之,藏传佛教建立在神圣性与世俗性二分关系的基础上,而象征符号使神圣性处于既敞开又遮蔽的状态中。作为藏传佛教实体的寺院,过于敞开神圣性会使其与世俗的界限模糊,丧失宗教的社会功能;过于遮蔽神圣性也容易造成宗教理性化的缺失,与现代社会发展不适应。从象征符号分析藏传佛教寺院神圣性的建构,为理解藏传佛教之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从“以言行事”的角度而言,象征符号又是一种行为,通过象征符号的调适与变迁,亦是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