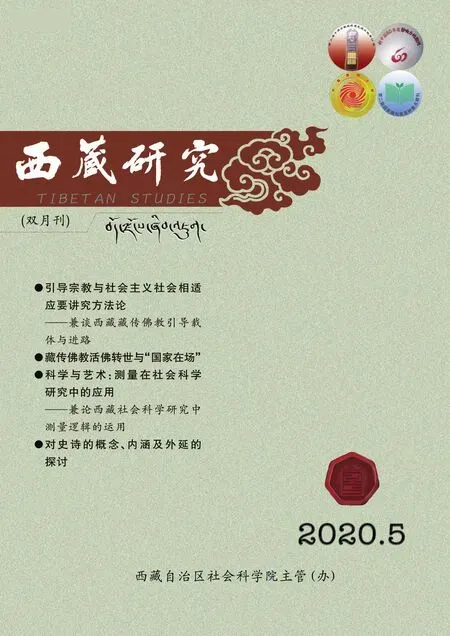洋人入藏与清廷、西藏地方的因应及其对西藏局势的影响(1876—1886年)
高龙 高亚西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2.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17、18世纪以来,经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崛起的西方列强逐渐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英帝对我国西藏更是生出侵略野心,并派人与西藏地方接触,遣人非法潜入西藏、获取情报,遭到西藏地方的拒绝和抵制。其后英国不断蚕食鲸吞中国西藏西南边境处的哲孟雄(今锡金)、布鲁克巴(今不丹)等藩属地,渐次逼近西藏。1875年2月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戕(史称“滇案”),英国以之为契机大做文章并提出了入藏的申请。清政府为了迅速了结“滇案”,只得同意其进藏要求,并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与英帝签订了《烟台条约》“另议专条”:
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1]350
英帝因之获得了蓄谋已久的入藏“权利”。按照“一体均沾”的原则,各列强也随之分享此项“权利”。洋人入藏是清代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2-4],但获得清政府同意、经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准予入藏的洋人与私下入藏的洋人有很大不同。因为前者行使的是其“条约权利”(从1876年《烟台条约》起,至1886年《中英会议缅甸条款》止),清政府非但不能拒绝,还需发放护照、“妥为照料”。而且对这类洋人进行许可和护送的官方行为极有可能引起西藏地方的误解,使其以为清王朝袒护洋人、轻视西藏(详见下文)。这一区别似乎并未被研究者所注意。既往研究或因主题限制、或因侧重不同,在述及这10年间的入藏洋人时,或失之简略,或语焉不详,为这一题目的研究留下了再探讨的余地(1)参见曾友豪编《中国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84—85页,该著中对洋人入藏仅述及条约条款,后来诸多以“中国外交史”为主题的著作也多是如此,不再一一赘述。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60—67页;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6页;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等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7—661页,上述3部著作均有专节论及洋人入藏问题,对该问题有一定的梳理,但稍显简略。张云:《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6页,其中提及洋人入藏对西藏地方局势埋下诸多隐患,但未展开论述。另外,边疆史、近代洋人在华活动史研究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论及,傅德元:《论丁宝桢对巩固西藏边防的贡献》,载《西藏研究》1992年第4期;张秋雯:《丁宝桢川督任内对藏局的因应》,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25期;唐密峰:《晚清时期外人来华游历管理政策初探》,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这些成果是本文的重要参考。:洋人入藏一事的始末需要进一步理清,其对西藏局势的影响也有尚待发覆之处。
一、入藏洋人的构成及分析
仅就笔者所见,入藏“专条”签订后10年间,经总理衙门发给护照载于史料的入藏洋人如下(见表1):
表1:

1876—1886年入藏洋人名单
从上表来看:(一)入藏洋人涉及多国,其中以英、俄人次最多。规格以奥匈帝国摄政义一行、俄国尼润赖一行、英国马科蕾一行为高,均是由政府派出官员并正式知照清政府。奥匈帝国、法国意图不明,英、俄两国则有较明显的侵略意图。
(二)光绪五年之后的几年似乎为洋人入藏的低潮期,而英国似乎从光绪三年之后对入藏就不太积极。但揆诸史实,俄国尼润赖一行于光绪五年被“以礼阻回”后也并未放弃,其后几年一直在青海、新疆等处盘桓,刺探情报、打探其他入藏路径、等待时机。光绪十一年俄人撇武撮伏等人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进入藏北。英国实际上对由中国内陆省份侵入西藏期望不高,其主要侵略路线是以英属印度为跳板侵略西藏西南边境处的哲孟雄等地区,再由该处进逼西藏。影响较大的马科蕾一行便是企图从境外的哲孟雄强行入藏。
(三)西藏地方对洋人入藏基本持抵制态度,大多数洋人都被阻回或改道。俄人得以入藏的两次则是各有因由。光绪五年俄国尼润赖一行入藏时正值摄政义入藏一事在川藏等处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该事件吸引了西藏地方的主要精力,使其疏于防范藏东北处盘踞的俄人。尼润赖虽利用此时机得以入藏,但也很快被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注意并阻回。光绪十一年俄人撇武撮伏一行得以入藏的原因在于俄国私下联系并迷惑西藏地方当局,以财物和枪支讨好西藏地方以图“结盟”。
二、清廷各方的认知和应对
在中英《烟台条约》谈判时,身为钦差大臣的李
鸿章虽虑及“西藏探路一节,将来恐有棘手”,但为了迅速了结“滇案”,只得应准。在细节上,李鸿章稍做变通,“于原议内添‘由总理衙门、驻藏大臣查度情形’字样。并与言明如有阻滞,切勿勉强”,英使同意。李鸿章对之似乎也还满意,认为“届时应由总理衙门妥慎筹酌,纵难阻其弗往,但属沿途加意护送,自无他虞”[5]914。此外,检诸李鸿章同期的奏稿和信函,并未发现其对洋人入藏一节有过多注意。即将赴英了结“滇案”并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召对中论及“滇案”时,也认为应先了结“正案”,使英国无所“要挟”[6]。熟稔洋务的两位大臣如是说,清廷便也未再置议。
相较于《烟台条约》中颇为紧要棘手的“昭雪滇案”“优待驻京大臣”“整顿通商事宜”等项,洋人入藏一节作为附加条款确实构不成谈判中的问题。或许对清廷而言,中英、中法签定《天津条约》后洋人便已经获得了在华游历、传教的权利,洋人入藏一条只是洋人在华特权的一部分或补充。议定之后,清廷在谕旨中重申了地方官员应加强对在华洋人的保护,并未对新签订的入藏“专条”有过多的说明或留意。
随着入藏洋人的陆续前来,地方大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四川是内地进入西藏的门户,“自英人有西藏探路之约以后,来川游历者日见其多”。光绪三年英人吉为哩、贝德录等赴川、滇、藏游历,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光绪二年至十二年在任)依约派人接待护送,但不料英人“或则欲会凉山伙夷,或则欲由藏赴国,沿途详绘地图,其几已见”[7]1619-1620。至光绪五年,“洋人来川游历者十倍于前;其欲入藏者,十居三四”[8],形势日益复杂。丁宝桢认为英人名义上为游历通商、实则对内陆西南各省包藏祸心:“欲以向之致力于海疆者,转而用之于西南各省……此时用意在蜀。蜀得而滇黔归其囊括矣。”[7]1620他敏感地察觉到,英人游历入藏是“蓄意开通西路……此次先由附近边隅以次渐进,将来道里既熟,必多不情之请”[7]1684。
其时,清廷的边境、藩属国频繁告警,丁宝桢不得不对洋人入川游历及入藏一事高度警惕,并把洋人入藏与川、藏等西南疆界的安全问题相联系。他希望清廷能意识到洋人入藏“实为中国陆路一大关键,未可视为末务”[5]1622。总理衙门也认为英人用意诡谲,不可大意。清廷遂于光绪五年下令丁宝桢与驻藏帮办大臣色楞额“会筹藏中应办事宜”。二人不敢大意,“设防闲不豫,致洋人冒昧前进,则藏番必一意胶执,设有他事,其酿祸将有甚于马加哩(即马嘉理,笔者注)者”[7]1893。马嘉理事件殷鉴不远,洋人入藏极有可能再度酿成重大的外交纠纷。当年“滇案”谈判时附带“另议”的入藏条款俨然成为川、藏疆臣眼中的“藏中第一要务”[7]1972。
丁宝桢、色楞额认为,对洋人赴川藏等地游历一事应未雨绸缪、多方筹划,以免意外。如果有赴川游历的洋人意图西进,则由丁宝桢“预饬该厅同知及各塘委员随时查探。如有入藏洋人,必先婉言阻止,决不令其轻入”。如果有洋人“由外洋及新疆别路入藏”,则由驻藏大臣在“交界之处派员探迎,或婉为阻止,或加意防护,庶免失事”[7]1892-1894。此外,丁宝桢、色楞额倡议“于藏中与各路交界之处,择要增设文报委员二人”专门负责稽查护送洋人事宜(2)参见罗文彬编《丁文诚公(宝桢)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892—1894页。需要补充的是,增设委员一事并未依议执行,而是有所变通。西藏有些地方可从四川拣派委员,而“江孜等处距哲孟雄尚远,未便增设委员”。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页。。这些想法获得了清廷的认可。至此,清政府对于洋人入藏一事才算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应对办法。但这些办法在具体实施时仍不免一波三折。
光绪五年,奥匈帝国摄政义一行意图入藏,经总理衙门发给护照并于六月抵达甘肃、青海等地。西宁办事大臣喜昌和陕甘总督左宗棠致函丁宝桢,请四川方面加以防护。由于摄政义入藏路线过于含混,丁宝桢为免别有歧误,只得查对图籍,将所有可能的西宁至西藏的路线和道里程站情况开单抄送驻藏大臣松溎,请他迅速派出官兵照单查探,并“飞饬各台站文武、转饬土司,各按单开道里探明行径,随处接替保护”。前后牵涉到的地区有四川德尔格特土司属境、松潘土司曲那木镇、懋功厅、西藏三十九族地区等。川西北、藏东北都为之惊动。丁宝桢还下令“所有派出各员弁兵役经费口粮,均准其作正开销,以资实力迎护”[7]1969-1972。这些举措可谓是如履薄冰,慎之又慎。但摄政义一行对之或许并不知情、也不领情,其在青海前进时“见该处难以行走,因知四川至藏系台站大道”,随即改道由大路入川、拟由川入藏;到川后也是我行我素,不听四川各级官员的劝阻,坚决要求入藏[7]1999-2001,引起西藏地方的轩然大波。
从此事中不难看出洋人在入藏一事上所具有的主动权和随意性。洋人一旦获得护照,则取得了绝对的主动权,行走的路线、日程及入藏与否,似乎都要视其心情和意志而定。而清政府和地方官员则较为被动,不仅要尊重洋人的意愿,还要随时接待防护。即便如此,清廷还能勉强应付,更为棘手的是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和抵制态度。
三、入藏纠纷与西藏地方的抵制
西藏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与四川等内陆省份有着极大的不同,清王朝也只是在藏设置驻藏大臣进行“羁縻”统治,西藏当地的僧俗权贵对藏务有着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作为平息“滇案”的被牺牲者和洋人入藏、侵藏的直接受害者,西藏地方对洋人入藏一事始终抱有不满。往前追溯,更可以发现,西藏所遭受的不仅有列强的觊觎和侵略,还有法国传教士的宗教挑战。咸丰年间,法国传教士罗勒拿、肖法日等在川藏边界处活动,意图进入西藏传播基督教[9]328。洋人入藏、传教对西藏而言都是切肤之痛,其对之的忌讳和敌意自是日渐加深。
清廷无视列强对西藏日渐严重的侵略,忽视西藏的特殊情况及其仇洋仇外的情形,直接批准洋人入藏,显然伤害了西藏僧俗的感情。入藏“专条”签订的消息传到西藏后,西藏僧俗“人心颇觉涣散”,产生了不满和不安情绪[9]547,“阖藏各寺不愿外人到境游历,吁请阻止”。但条约刚签,岂容轻易更改?清廷不予同意,命令驻藏大臣“设法开导,勿令生事”[9]493。申请阻止不成,西藏地方便自行阻拦。光绪三年英人吉为哩行抵巴塘、江卡,引起该处藏兵的“惊疑”并在远处“连放数枪”[9]489。江卡位于川藏交界,向为川藏交通要冲,西藏地方政府在此“设一台吉番官扼守,于此稽查来藏之人,附近藏属各番部皆受其节制”[10]。吉为哩虽幸无事,但江卡地方敢于放枪,暗示着西藏地方可能以武力抵制洋人入藏。
光绪五年摄政义一行将要入藏的消息传到西藏,更是引起西藏僧俗的公开反对。七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开出具甘结、共立誓辞:“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9]463。掌办商上事务(官名)通善济咙呼图克图将此甘结经驻藏大臣松溎上达清廷。清廷下令松溎“责成该呼图克图等开导僧俗人众,告以该洋人入藏人数无多,前往游历,不至有欺压之事,毋庸妄自警疑,致生事端”。
这一旨意的效果可以想见。清廷转而寄希望于四川,希望四川官员能于洋人抵川时“将藏众情形详细告知,设法劝阻”[11]4430-4431。但摄政义颇为固执,四川官员多番劝说都收效甚微。十月,摄政义等人抵达巴塘,意图西进至江卡。该处藏族僧俗头目集结阻拦并扬言:“我等在此防阻,万不能使伊等前来”[9]554。“暂从宽免”的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非但没有奉旨开导藏族僧俗,反而派藏官颇琫(官名)香噶带兵前往江卡,以武力阻止摄政义入藏,致禀声称:“必须巴塘文武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勒令土司出具永无洋人进藏切结,方可罢兵。否则直到巴塘,焚毁教堂及土司房屋”;同时责令川藏、滇藏交界处各土司、僧俗:“以后一体不许洋人过境,亦不准各处迎护接送”[9]500。态度强硬,剑拔弩张,矛头直指西藏及其他涉藏省的所有洋人。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巴塘地方文武只得再行劝说,并请该地的传教士从中斡旋。摄政义最终“赏准”改道入滇回国。但颇琫香噶却不愿罢休,“意在必得永无洋人游历入藏结据,并允以后驱逐法国教堂”,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肯退兵。丁宝桢认为藏官此举实属蛮横无理,随即派兵前往巴塘弹压,并责令该地文武保护教堂,不准教堂和土司私自出具甘结,以免留下后患。驻藏大臣也特派专员驰往巴塘进行开导。在多方压力下,颇琫香噶带兵折回[9]501。
这一事件颇为典型,涉及清廷中枢、四川官员、驻藏官员、西藏地方政府、藏兵及僧俗领袖、边地土司、洋人洋教等多种势力,显示出洋人与藏务交织时所带来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然而西藏地方也并非铁板一块,西藏地方当局对藏境各处的控制和管辖也多有疏漏。颇琫香噶带领藏兵前往江卡时,曾在阿足山沟地界遭到三岩“野番”抢劫,并伤及人马[9]500。阿足山沟地属藏境,藏兵在此却遭到抢劫,足见藏境内形势的复杂混乱以及藏兵的软弱无力。俄人尼润赖一行在前往西藏时,也被“崖热娃在途抢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尼润赖一行非但没有损失一物,反而击毙崖热娃数人,上演了马嘉理事件的“反面”剧本[9]553-554。
西藏地域广袤、地形复杂,部落、民众错综杂处,西藏外围尤其是川藏、青藏交界处更是灰色地带,仇杀、抢劫盛行。如三岩各部“并无头目,以人强财富为能。若徒有资财,无强狠亲族,亦必被邻里夺取谋杀。盖豺虎之乡也,素以抢劫大道为事”[10]22。民风如此,汉、藏地方官员也无可奈何,很多时候只能听之任之:“其藏中应办各事……俱系彼地之田土买卖、命、盗各件居多,其实在费手者,则惟有彼此撤卡争斗之事。然亦系蛮触相争,决无大患”[7]1972。
而今这些状况却因洋人入藏而变得难以回避且不易处理:“盖其未入藏境以前也,既虑野番之劫掠,其既入藏境以后也,又虑藏番之阻拦”[7]1972。“野番”抢劫藏兵得手、抢劫俄人失败似乎也昭示着以西藏地方的实力,对列强恐怕“只有阻遏之心,并无坚拒之力”[11]4472。一旦列强获得借口、恃强逞凶,西藏地方难以抵御,必然遗患无穷。
四、入藏、通商与“专条”的废止
光绪十一年,俄官(撇武撮伏)改道由新疆赴和阗,并与法国人庚和礼勾结,以“缠头回民”作引导,行抵藏北达木八旗。俄人此行迷惑并贿赂西藏地方当局,意图共同结盟以抵制英人,西藏地方政府似乎颇为所动[10]8、14、15。一时间“洋人进藏之隐忧,俄国更有甚于他国者”[7]559。而英国听闻此消息,自然不甘其后。同年九月,英国带着新的侵藏计划卷土重来,派出使臣马科蕾赴北京与清廷会商入藏及西藏通商事宜。“西藏一隅,而两大并争,其间办理洵属不易”[7]532,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马科蕾此行所奉英国政府的指令,是争取使团进入西藏的拉萨或扎什伦布;如不能进入,则争取在藏印贸易上获得更多的“权益”[12]。或许是鉴于早先洋人由内地入藏的失败,马科蕾此次意图由英属印度出发经哲孟雄入藏。由界外入藏是一步杀招,因为清廷不便、也不能在国界外派人对之进行保护或阻拦。入藏与否,只能以英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以西藏地方的抵制态度,强行入藏势必引发冲突。清廷居中调停、事处两难,正好给了英国讨价还价的契机。
驻英公使曾纪泽因马科蕾一事告知清廷:法国侵略越南最初也是以“无名之私商、无赖之教士暗中经营”,英国谋求入藏游历通商也是此意;但现今英国承认大清对西藏的主权,就西藏通商、遣使等事商量于我,似乎应回应英国的请求并签订一“公允之约”[13]1067。清廷也知道英人入藏游历“即为通商地步”,但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洋人入藏这一棘手问题[10]4472-4473。清廷将此旨意和曾纪泽的意见传达给丁宝桢、色楞额等人,责令他们会商办法。
丁宝桢以为马科蕾此举与之前洋人进入川、藏游历是同一路数,“阳借通商之美名,实阴以肆侵夺之秘计……设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9]528-530。中法战争事在眼前,英国潜身其后、趁火打劫,“幸而不发则已,不幸妄动,其害更甚于法夷”[7]2855。丁宝桢因而建议整肃军备,以防不测。色楞额对藏方多次开导,成效不佳,以为“准其游历,亦必俟开导有成”,贸然遣使,必将酿成边患[11]4473。
马科蕾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年初持照行至大吉岭,拟三月中旬起程入藏,并声称:“如藏番仍前阻拦,彼即带兵三千,自行保护前进”[9]477-478,图穷匕见。而驻华英使为了迷惑清廷,放出了“永不入藏”的烟幕弹:“当时定议入藏探路,本为通商而设,并无他意。现在印藏交界之大吉岭地方,早有与英人互相贸易之事,如果准令在印藏边界通商,即可永不入藏”[11]4478-4479。清廷以为通商虽然可信,但入藏一事载在条约,必须改订才行。这一意向刚好与英国新的侵略诉求歪打正着。
中法战争后,法国在印度半岛的实力被消耗,英国加紧了对缅甸、云南的侵略、企图取得更大的侵略利益,如勘定滇缅边界、设关通商等。英使于是以修订入藏“专条”、电告马科蕾从缓入藏为条件,换取清政府对滇、缅问题让步[13]1084。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1886年7月24日),双方签订《中英会议缅甸条款》,其中对入藏一事重新规定:
《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查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1]485
至此,入藏一条得以废除,藏务的焦点变为通商一节,清廷的“紧要关键”转以“开导番众于边界通商为主”[11]4481。英国不断以通商为幌子在西藏西南边境地带施压,西藏地方则在边界设卡进行严厉抵制。英国的侵藏野心难以满足,急不可耐,遂于1888年悍然发动隆吐山战役(第一次侵藏战争),公开侵略西藏。
五、洋人入藏与西藏局势的变迁
从《烟台条约》到《中英会议缅甸条款》,洋人入藏一条载在条约仅有10年,被清政府注意并留下记载的入藏洋人也仅有几拨,确实只是近代外交史上一段很小的篇章。但洋人入藏一事的10年迁延更则成为清廷和西藏地方关系恶化的一大诱因,对西藏局势及清王朝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影响匪浅。
康雍乾之后,清王朝国势渐衰,道光以降,藏务废弛。驻藏大臣体制遭到侵蚀[9]495,历任驻藏官员中的贪渎无能之辈也给当时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如后来英国谋求入藏通商的说辞中所声称的西藏私下早有商贸往来一节,其始作俑者便是“内地贪吏豪奴在官人役”。被西藏当局查知后,驻藏大臣对涉事内地官民进行包庇、不了了之,走私贸易也禁之不绝[9]549。这致使驻藏官员的权威下降,也给后来英国图谋通商提供了借口。此外,清王朝驻藏官兵仅有1000多人,力量本就弱小,且是由四川派驻,满3年换班。但“名为年满换班,其实多半顶补。顶补之人,率皆换防兵丁贸易客民私与番妇奸生之子,姓仍从父,性与番同”[9]550。这些人利用职务之便在军营中打听公事、勾结官员、播弄是非、参与走私贸易,影响极差。驻藏官兵的腐朽没落,必然使清王朝对西藏的统治力量衰弱、清王朝的权威受损。
咸同年间,清廷又忙于应对太平天国起义,对藏务重视度下降且有力不从心之势。四川忙于对抗太平军,本应按年解送到西藏各台站的饷银难以接济,使得西藏地方更加轻视驻藏官兵[10]6。此时川藏交界地带也不太平,川属土司瞻对发生重大叛乱且愈演愈烈。瞻对在打箭炉西北处,当地百姓多是藏族,宗教和风俗都深受西藏影响(川藏、滇藏交界土司地带均是如此)。清王朝本该迅速平叛,以避免西藏地方势力“见缝插针”。但当时清廷和四川因为连年应对太平军和匪患,兵疲财匮,难以平叛,转而请西藏地方派出藏兵协同平叛。同治四年(1865年),叛乱平息,有功的藏兵向清王朝索要军饷。清廷无力拨给,遂把瞻对赐予达赖以作奖励,达赖在此设置藏官进行统治。瞻对划归藏属事件直接反映出清王朝对川、藏地区统治力量的极大衰弱。此消彼长,西藏地方势力则以此为契机、以瞻对为跳板在川属(滇属)土司地界施加影响(3)“然不察其事者,以为所与者只一瞻对,尚无妨于大局。而不知藏番利用瞻对,遂殃及于关外全部各蛮族”。见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2页。具体研究可参见陈一石:《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二)(三)》,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1、2、3期;石硕:《瞻对:小地方、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期。,直至清王朝灭亡。颇琫香噶在江卡阻拦摄政义入藏时敢于放话让川藏、滇藏交界处各土司、僧俗抵制洋人洋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影响的持续和扩大。
这些局势的变迁因为洋人入藏一事而变得更加复杂棘手。清廷或屈从于列强、或怕洋人在华再生意外,就洋人入藏一事(及后来的通商事宜)不断向西藏地方施压;西藏则不听清廷的多次“开导”(其实“开导”一词也很微妙)、公开出具甘结,甚而悍然出兵对峙。两相凿枘,自然加速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光绪十一年丁宝桢在筹划马科蕾一事的对策时便注意到:若再派人前往西藏开导,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是未与英人通商,已先与藏中喇嘛构祸,似觉不合”[9]530。色楞额也认为:如果操之过急,“势必驱数百年归顺之赤子从而携贰于吾”[9]477。洋人谋求入藏(通商)一事已不只是一棘手的外交事件,更成了清王朝和西藏地方之间的一大隔膜。
西藏地方开始还只是阻止洋人入藏,之后竟开始阻止内地官员入藏。光绪四年(1878年)黄懋材欲入藏赴印游历被阻;光绪六年(1880年)由四川调往西藏专门处理洋务的委员被阻(后经开导后放入);光绪十年(1884年)丁士彬奉旨前往西藏调停藏、廓冲突被阻。可以说一旦涉及洋务洋人,不管想要入藏的是何人、是何缘由,西藏地方必有一番阻拦且“已成惯技”,“藉有洋人为词”变相抵制清廷对藏务的干涉[7]2763。下一任驻藏大臣文硕在北京更是听闻:因洋人入藏通商一事,西藏僧俗“不惟不听驻藏大臣约束,转致驻藏大臣办公掣肘。甚者公文折报,须先关白,然后乃得遄行”[9]547。西藏僧俗甚至怀疑清政府“左袒洋人”“且有英人不见汉官断无进藏之事,英人一见汉官,藏事终无不坏之理之语”[9]549。再考虑到上述驻藏官兵的弊病,文硕不无担忧地指出:“即无洋人力请游历通商之事,而后此控驭之方,恐亦须大费一番筹画也”[9]546。
六、结论
清廷为快速了结“滇案”,在《烟台条约》谈判时就洋人入藏一节未多加考量便予以应准,为晚清藏务埋下了巨大隐患。清廷未曾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更未料到后来西藏僧俗对洋人的抵制会如此强烈。在后续的实际应对上,清廷也一直处于被动,既不能有效地在北京通过各国外交使臣阻止洋人的入藏申请,也不能令行禁止地责令西藏当局对入藏一事进行配合。
洋人一旦要求入藏,身为中枢的清廷便会进入“禁之不能,听之不可”的两难地步[9]492,除了命令大臣“设法阻止,傥不能阻,则加意防护”[11]4462及“开导”西藏当局外,在外交和内政上没能率先形成具体可行的应对策略,反倒极为依赖于四川总督和驻藏大臣的建言献策。川督丁宝桢在对洋人入藏事宜的应对上起了重要作用,实施了一系列牵制洋人、拱卫藏疆的有效措施,并形成了“筹川援藏”的边防思想[14]。
清廷后来虽然通过谈判废止了入藏专条,但却以缅甸利益的割让为代价,且在西藏通商一事上留下了隐患。通商问题承接入藏问题成为中英两国和西藏地方三方新的问题焦点,并为之后英国发动侵藏战争埋下了导火索。入藏一节的签订是英国谈判《烟台条约》时的顺手牵羊,其废止也是英国以芝麻换西瓜。清政府前前后后的软弱、短视以及暴露出的对西藏控制的无力无疑助长了英人的侵略气焰。
洋人入藏带来了诸多纠纷,引起了西藏地方当局的严厉抵制,加剧了西藏局势的不稳定性,对清王朝和西藏地方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清王朝在两次英国侵藏战争中的处置失当固然是其与西藏关系恶化的重要节点,但此“山崩”之前已有多年“风化”,洋人入藏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节。因为之后的西藏局势都是循着这一轨迹愈走愈险。考察《中英会议缅甸条款》遗留下的西藏通商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与洋人入藏一案的如出一辙:西藏依然抵制,英国依然强势,“是通商先既不敢取必于西藏,不通商又将开衅于洋人”[7]2952。而清政府依然软弱无能,只得轻视西藏僧俗的不满情绪、牺牲西藏地方利益以求苟安。在西藏僧俗看来,这些举措更是其“左袒洋人”的有力“注脚”,以致西藏地方对清中央的离心力更是越来越强,造成清末民初西藏局势的动荡,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