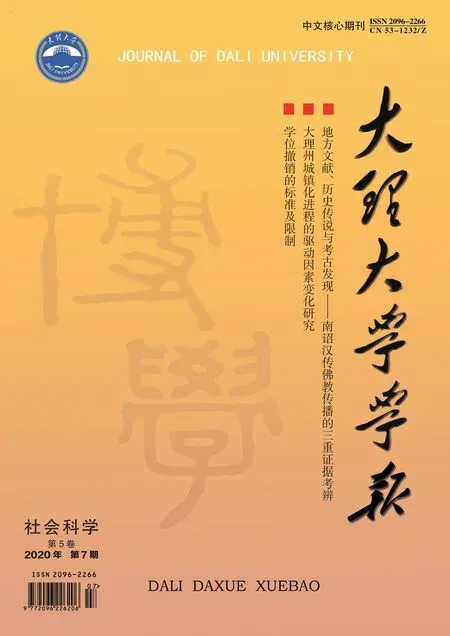主题、类型与前文本:评影片《绿皮书》
苗 瑞
(大理大学文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美国电影《绿皮书》自2018年9月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以来可谓叫好又叫座。影片在获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的同时,还收获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人民选择奖第一名、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音乐类最佳影片、美国国家评论委员会最佳电影、年度和平电影最有价值电影提名等荣誉。截至2019年4月,制作成本为2 300万美元的《绿皮书》在北美获得了8 476万美元的票房收入,成为自《国王的演讲》(2010年)以来北美票房最高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影片在海外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尤其是在中国,票房超过7 070万美元,在奥斯卡最佳电影中仅次于《泰坦尼克号》。其全球票房收入超过3.06亿美元。
《绿皮书》的成功得益于它成功地游弋于因袭与创新之间,在继承“类型范式”和“前文本”的基础上实践艺术创新,很好地平衡了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在影片的创作生产过程中,编剧和导演面临着如何处理影片与同题材、同类型影片,以及自身与经典“前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互文性理论认为“一个文本只有通过与那些在其之前产生并通过变化对其发生影响、产生作用的文本加以比较才能读懂”〔1〕。与《绿皮书》形成互文性的影片主要有《为黛西小姐开车》(Driving Miss Daisy,1989年,以下简称《黛西》)、法国影片《无法触碰》(Intouchables,2011年),及好莱坞翻拍片《触不可及》(The Upside,2017年)等。它们都讲述了“一名白人与一名黑人以雇佣关系为契机建立起跨越种族的友谊”的故事。其中《黛西》获得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化妆四项大奖,以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表演团队和金熊奖提名等;《无法触碰》则打破了法国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同时收获了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和法国凯撒奖最佳影片提名。由于该片的巨大成功,印度、阿根廷也先后翻拍了它。基于《绿皮书》的成功与非议,本文从主题、类型与前文本等方面对《绿皮书》游弋在因袭与创新之间的平衡艺术进行讨论分析。
一、政治主题:白人救世主与黑人的身份追问
当分析解读一部影片时,我们会首先尝试概括它的主题,因为掌握了一部影片的主题就掌握了它的核心内容。影片的主题相当于“情节动作的概要、情节动作的中心立意或组构原则”,是“作品的意识形态的或事件的中枢”,它能够“确保作品结构严密”,是“限定着对作品的任何解释的一个常数”〔2〕。影片的主题必须反映人们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影片会空洞无实,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在主题上,《绿皮书》回应了长期困扰美国的种族问题,这是影片“政治正确”的保证。美国是世界三大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之一,“百衲衣”的比喻准确生动地表明了美利坚民族的多样性。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仅贯穿于美国历史,也是当今美国社会的重要课题。在美利坚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以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最为尖锐。美国南北战争后,1863年颁布的《解放奴隶宣言》理论上使黑人获得了自由与平等权利,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与压迫却长期存在,终于在19世纪中叶爆发了长达十余年、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绿皮书》的故事设定在民权运动高潮前夕的1962年,讲述了在纽约夜总会“当差”的意裔美国人托尼·瓦莱隆加(Tony Vallelonga)在夜总会歇业期间被优秀爵士钢琴家、黑人唐·谢利(Don Shirley)聘用为钢琴巡演的司机兼保镖,在旅途中建立起跨越种族和阶级的友谊的故事。影片以交易性的雇佣和服务关系为契机,通过两位主人公的路上遭遇和心灵转化,想象性地弥合了美国种族之间的矛盾隔阂并达成和解,从而整合了当代美国种族问题上的个体认知与民族身份问题。
影片的尾声通过三个颇具意味的标志性段落达成了这种弥合与和解。第一个段落是在种族隔离最严重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因为主办方不允许自己在餐厅就餐,谢利拒绝了演出,标志着谢利一改以往的软弱态度,开始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说“不”。第二个段落是“橘鸟酒吧的合奏”。西装革履的谢利在酒吧与黑人朋友们欢快地合奏,找到了久违的轻松快乐,象征性地完成了谢利向黑人这一“自然身份”的认同与回归。第三个段落是“平安夜的欢聚”。影片的最后,在结束旅程回家后,孤单寂寞的谢利走进了托尼家,与他的家人欢度平安夜,标志着谢利突破黑人的身份认定,象征性地完成了谢利对家庭港湾的回归。作为《绿皮书》片名来源、最早出版于1938年的真实出版物《黑人司机绿皮书》正是美国30年间种族歧视与隔离制度的真实写照。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维克多·雨果·格林的邮递员。它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指南,介绍了在吉姆克劳南部欢迎黑人旅行者的饮食场所和住所,并警告他们哪些城镇对黑人来说是危险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有媒体批评《黛西》《绿皮书》等影片“对歧视背后的制度和系统问题视而不见,息事宁人地把种族议题处理成个体之间增进了解达成伟大的友谊”〔3〕。“从消除种族隔离到融合、到平等、到真正的友谊,种族进步中所有的乐观主义都是由服务条款规定的”,它们“把工作场所浪漫化,把黑人角色当作封闭的白人思想和与世隔绝的生活的理想撬棍”。同时,《绿皮书》还延续了“白人救世主”的刻板印象,结合了“白人救世主的比喻与偏执”。的确,影片以黑人与白人个体之间跨越种族和阶级的友谊来弥合“血雨腥风”的种族冲突与斗争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这一方面映照了当时美国政治上解决黑人种族平等问题的乏力,也是现实生活中经济和就业的平等在解决黑人种族问题上的基础地位的反映。实际上,此种花钱买玩伴的现代消遣,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一体化后的美国,民权运动或多或少地平息下来,资本主义和开玩笑的白人家长式作风肆虐之后才有可能。
《绿皮书》的主题创新,体现在它揭示了非裔美国人的阶层分化以及谢利对自我身份的追问。在前往北卡罗莱纳州的旅途中,汽车出现了故障,谢利和托尼都下了车,他们看到了田地里劳作的作为“他者”的黑人,同时劳作的黑人们也在凝视着作为“他者”的谢利和托尼。这种互为“他者”的凝视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引发了观众对美国种族内部阶级分化问题的思考。在结束密西西比州图珀洛(Tupelo)的演出后,因托尼殴打辱骂自己的警察而被拘禁的二人被释放后争吵了起来,在雨中谢利情绪激愤,向托尼痛陈自己的身份困境:
是的,托尼,我住在城堡里,孤身一人,有钱的白人付钱让我为他们演奏钢琴,因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文化,但当我一走下舞台,在他们的眼里我立马变成一个黑人,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文化。我独自忍受轻视,因为我不被自己人所接受,因为我和他们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不够黑,也不够白,我甚至不够男人,告诉我托尼,我是谁?
谢利是美国社会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但他同时也是一名黑人、同性恋,他属于美国社会中真正的少数群体——白人群体视他为“玩物”异类,黑人群体也不接纳他,他既是白人眼中的“他者”,也是黑人眼中的“他者”。于是发出了“我是谁”的追问,把影片的主题引向对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的“身份认同”的思考。
二、类型范式与前文本:艺术与商业的平衡路径
除了“政治正确”外,“艺术与商业的平衡”是奥斯卡最佳影片获奖的标准之一。自1929年奥斯卡金像奖诞生以来,尽管奥斯卡的评审规则做了多次改革,但这一原则却始终未变。最为显著的例子是被奉为影史经典的《公民凯恩》虽然获得资深影评人九项提名,但因平庸的票房成绩和冷淡的公众反应,最终只获得了一项最佳编剧奖。“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其尺度很难拿捏,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无疑是一条成功的实践捷径。《绿皮书》正是这样一个成功案例。
“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在具体影片中并非无迹可寻。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考量最终投射在文本中,为我们分析导演的创作动机提供证据。当导演以“追求影片的艺术品味”为创作动机时,意味着文本要打破通俗的商业电影的叙事成规和惯例,强调人物性格和视觉风格,抑制动作性和关注内在的戏剧冲突;当导演以“票房和商业利润”为创作动机时,意味着文本主题要契合社会热点和公众关切,遵循类型片的叙事规则,拥有明星阵容,并以院线放映为主;而当导演以“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为创作动机时,则意味着在尊重观众的审美经验基础上的艺术创新,既尊重观众的观影经验,又适当挑战观众的审美能力,在创作中采用继承“类型范式”和“前文本”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的艺术创新策略。在好莱坞的电影生产体制下,《绿皮书》以“艺术与商业的平衡”为创作动机,在“治愈式旅途片”的基本叙事范式和“前文本”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实践艺术创新,是影片取得成功的关键。
从类型上看,《绿皮书》遵循了公路片中“治愈式旅途片”的叙事范式。公路片是美国对世界电影的类型贡献,到今天发展成了“以旅程和道路为叙事载体,以主人公在路上的遭遇和人物内心的转变来推动剧情发展,表现人们疏离、孤独、寻找、沟通、反叛等内容”〔4〕的电影类型。作为公路片的子类别,治愈式旅途片着意于“对现代人的心灵拯救,解决其精神焦虑,并最终投奔‘家庭’,曾经被‘公路片’的主人公所摒弃的‘家’的意象重新回归为‘爱的港湾’”〔5〕。《绿皮书》沿袭了治愈式旅途片的类型叙事结构:影片的开端把谢利设定为身处19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孤单压抑的非裔美国人,通过深入南方腹地的钢琴巡演旅途,解决了其精神焦虑,从心理和行为上达成了种族和解。《绿皮书》的创新在于,率先在同类题材中开创了“治愈式旅途片”的叙事范式,这是它与《黛西》《无法触碰》等“前文本”不同的地方。《绿皮书》中“汽车的移动性带来了希望,暗示着种族隔离制度终将结束,以谢利博士为代表的黑人也将拥有更多的社会移动性及自由”〔6〕。
与“前文本”比较,《绿皮书》的创新还体现在人物设计上,并通过细节塑造了立体的人物性格。同样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黛西》,雇主犹太老太太富有高贵、固执吝啬,黑人霍克乐观仁厚、身份卑微;《绿皮书》则做了相反的人物设计:黑人雇主谢利来自上流社会、文化水平高、举止高雅,白人托尼则是底层平民、生活窘迫、文化水平低、举止粗俗。影片不但塑造了两位性格迥异的主角,以增强影片的戏剧冲突和喜剧效果,而且还颠倒了白人优越论或白人至上的传统观念和固定人设。《绿皮书》在黑人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故事开始于1948年的《黛西》中出现的黑人都从事家仆工作,社会地位低下。黑人司机霍克虽乐观善良,但目不识丁、身份低贱。而《绿皮书》中的黑人谢利则是高贵优雅的上层精英。固然,这样的人物设计来自故事原型,但它增强了影片的幻想特征,反而凸显了当时的黑人社会地位普遍低下的社会现实。
为了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除了因袭“治愈式旅途片”的类型范式外,《绿皮书》还增加了不少商业元素。如影片把谢利设置成“离群索居、孤僻压抑”者。影片上映后,谢利的后人因此产生质疑与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谢利不仅有三个兄弟,与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参与了民权运动,在其他非裔美国艺术家和领袖中也有许多朋友。谢利的朋友作家大卫·哈伊杜说:“我认识的这个人与阿里在《绿皮书》中描绘的一丝不苟的优雅形象大相径庭。(谢利)理智,但是朴实得令人不安,机智,自我保护,不能容忍一切事物的不完美,尤其是音乐,他就像他那独特的音乐一样复杂,无法分类。”影片之所以违背现实把谢利塑造成这样的形象正是为了满足商业类型片“先抑后扬”、形成“角色弧线”的戏剧化要求。另外,影片的喜剧成分也为影片增色不少。在世界电影的范围内,“笑”与“性”“暴力”一起被称为最受欢迎的类型元素。由于题材的限制,在缺乏“暴力”元素的情况下,“笑”与“性”成了《绿皮书》重点开掘的类型元素,而这正是擅长低俗喜剧的彼得·法拉利导演的优势。
总之,《绿皮书》在主题上回应了社会热点和民族关切,通过一名白人与一名黑人在旅途中建立起跨越种族与阶级的友谊的故事,想象性地弥合了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隔阂并达成和解,从而整合了当代美国种族问题上的个体认知与民族身份问题;同时,影片在因袭“类型范式”和“前文本”成功经验基础上的适应性创新,使其艺术性和商业性得到了很好的平衡。任何一部影片的创作与生产,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类型范式、前文本、市场因素等的影响,这些因素如隐藏的暗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最终投射在电影文本中。在影片的叙事框架内,寻找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状态,成了考验影片编剧、导演等电影创作者艺术水准的试金石。
——论《绿皮书》中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