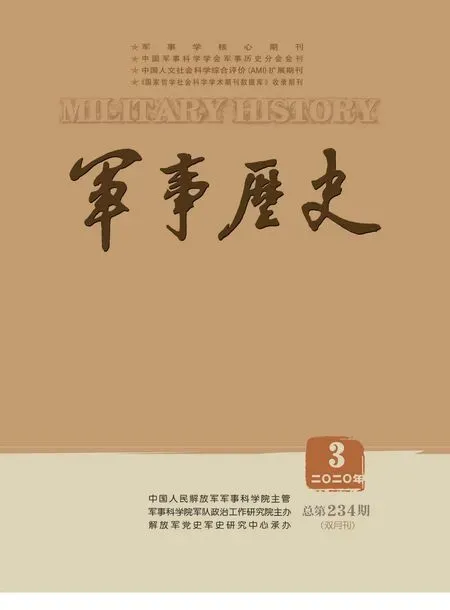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役动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根据军事战略、作战方式以及所处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兵役动员的策略和方式,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解放战争时期,在对前两个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兵役动员方式和策略更趋成熟,更加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激励,极大激发了翻身农民的参军热情。
一、土改——参军志愿的利益动因
进入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巨变。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构成了这场历史巨变的重要一环。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条关于土地问题的原则,即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公共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提出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大农民群众已不能满足于减租减息,到处伸手要求土地,他们从反奸反恶霸、清算、减租退租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方法取得了土地”①《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全军参加乡村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训令》(1946年7月1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8 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305 页。。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及时地调整了土地政策,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不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其目的除了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之外,还承担着为战争汲取必需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的任务。关于土地制度对于兵役工作的重要性,无论是当时战争的领导者还是后来的历史研究者,都给予极大关注。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中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中国一切人们、一切政党的两个‘关’。”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人民日报》1950年6月24日,第1 版。因此,在内战爆发三个月后,他总结道:“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③即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它正式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耕者有其田”,标志着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面展开。,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事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①《三个月总结》(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8 页。有学者指出,人民解放军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改革巩固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②[美]周锡瑞(JosephW.Esherick):《“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冯崇义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民众的支持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获取公粮、兵员、劳役的合法性基础,而国共两党对于这种合法性逻辑的理解则截然相反。国民党历来以“正统”地位自居,以其武力为后盾,打着战争的旗号,用强制的手段来完成上述任务。强征或者“拉壮丁”的手段造成的结果是役政的腐败和军队士气的低落。国外学者也认为:“政府所做的事情中,没有什么比征兵更能给农民带来痛苦。这一制度的腐败、不公正和残酷令人生畏。……整个征兵制度削弱了士气,伤害了农民的生计,它也就造成了这样的新兵,他们不仅无意与共产党作战,而且对他们所在的军队为之效劳的政府颇有愤怨。”③[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王建朗、王贤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 页。直到1948年,在国民党力量优势即将丧失殆尽之时,国民党才意识到忽视农村和农民的严重后果。当年9月,国民政府的86 名立法委员提出了一份进行“土地改革”的议案,主张废除租佃制,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但由于行政阻力太大难以推行而最终流产。
反观中国共产党,先是从地主手中获取土地和资源,将其无偿分配给占据乡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同时以“巩固胜利果实”“保卫翻身果实”等口号进行宣传,从而“将党的军事需求和政治需求转变为农民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安全需求”④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 期,第73 页。。利益的满足和安全的保障构成了民众参军入伍的直接动因。晋绥军区一份关于土改运动的指示生动地描绘了土地制度变革造成的参军热潮:
战士的家庭翻了身,有土地、有窑洞、有饭吃、有衣穿,地有人种,“窑洞政治形势”好了,战士的觉悟就有了物质基础,他的家庭也会鼓励他上前线,开小差的就会很少,部队才能巩固住。宁武二马营一个雇工参加我军说:“我当十年长工,还买不下十亩地,现在一次就分得了十多亩地,我当十年八路军都划得来。”兴县寨上村抗属白润娥写信给她丈夫,叫他好好努力打仗,把反动派努力打垮以后,夫妻再团圆。宁武郭毛毛翻身后,参加游击队,他女人告他说:“你去吧!家中有我,咱分的那地,可不能再叫顽固抢去。”五分区三团,原来是一个武工队,反攻后扩大成一个团,打仗很好,因为三团战士们的家,都是分过土地的。⑤《晋绥军区关于恢复三大任务军队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9月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8 册,第367 页。
对于长期受封建压迫的具有朴素情感的农民来说,土地、窑洞、衣食无疑是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在获得这些之后,他们也非常清楚,要保留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好处”,必须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的军事、政治优势,一旦丧失这种优势,从前的“顽固”就会立刻回来“算旧账”。由此,在共产党军队和翻身农民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同舟共济的关系。
诚然,土改运动的目的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在土地分配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平均分配,而是要通过土改运动的开展,团结尽量多的力量“争取和平,准备战争”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7年8月20日。。为了准备战争,吸引更多的人参军,在土地改革执行过程中,经常强调对军属、烈属的适当倾斜,使他们分得超过平均数的土地和浮财,有的则按照烈属、荣军、远征军、地方军、工属、贫民的顺序来分配果实。①《中共冀中区党委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基本总结(节录)》(1947年4月1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810 页。土地和浮财分配的数量和质量也按照上述顺序略有差别,“正规军一般以五亩为标准,土质好;地方军四亩,地质次之;工属三亩地,地质又次之。”②《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参军经验介绍》(1946年9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8 册,第378 页。下表是关于冀中区安平张敖村分配土地和浮财的情况:

冀中安平张敖村土地浮财分配统计表③根据《中共冀中区党委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基本总结(节录)》(1947年4月1日)绘制,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810 页。
在土改运动中,除了用土地和浮财作为对参军者进行经济补偿外,政治权利和政治待遇的再分配也是参军动员的一个重要因素,参军往往作为入党的条件,通过参军,即使是剥削阶层的地主、富农也可以入党。如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军人入党办法中有如下规定,“凡剥削者本人加入我军者,入伍两年后始可取得革命军人身份”,经过战争考验之后,“已有候补期作用,一般可按党章第四条甲项规定”方能转为正式党员。④《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军人入党办法的规定》(1948年5月1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9 册,第484 页。提拔军属担任干部,是政治补偿的另一种形式。例如河北安国县将积极支持儿子参军者评为“模范爹娘”,优先提拔为村干,该县三区北楼村郭文兴送子参军,被提拔为村治安员;二区米家庄一妇女送子参军,被提拔为村妇女主任。⑤冀中九地委:《土地改革中整理组织的工作总结》,转引自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 期,第73 页。
总之,解放区土地制度的变革,将农民们数千年以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变为现实,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人民解放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掀起了解放区的参军热潮。“华北区三年多内有近百万农民参军,其中太行区参军者已达全人口的4%,少数高的地方达8%。1949年初,太行区在10天内即有24501人参军,鲁中南在一个月中即有38000人参军。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三年(1947—1949)来,共有160 万人参军。”⑥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80 页。经过土改之后的兵员征补,不仅在数量上有显著提高,而且兵员质量的提高也很明显,山东渤海区新兵中,党员干部占14%,华东区新兵中,中、贫农占90%,太行区新兵中,18 至25 岁的青年占75%以上。⑦中共中央统战部编:《土地农民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1949年8月。贺龙在一次总结中对于土改后的兵员状况有如下评述:
老区经过土改以后,在去年秋季也有计划的征收了一次新兵,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就动员了一万五六千人补充到野战军,质量比过去任何一次要好。据临县新兵团统计:行政村以上干部四百一十九名,占该团总人数百分之七点六八。党员六百七十一名,占该团百分之十点九八。自动报名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翻身户虽无精确统计,估计也不会少。因为有了党员、干部做骨干,新兵补充到部队之后,也比过去的兵好巩固。由于他们经过土改,得到了胜利果实,阶级觉悟比较高,进步也很快,许多战士很快变成了部队中的骨干。①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446 页。
二、“诉苦”——参军志愿的情感动因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在党与农民之间构建了一个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从而确立了从民众中汲取人力(包括兵役和劳役)的合法性以及农民参军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只是为兵员征集提供了可能,要使其转变为现实还需要更多的条件。众所周知,兵役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成员从普通百姓到军人身份的转换,但这种身份转换的同时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从业风险。任何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在参军入伍前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都会计算和思考,如果让其他人参军出夫而自己得利不出力,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岂不更加划算?事实上,作为社会经济改革措施的土地改革运动,很难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经过抗日战争后,“社会劳动力确已缺乏;群众觉悟尚未能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半老区更差);被刺伤的人有离心思想;翻身满意了的单纯闹生产,对参军支前不积极”②《关于十月接头会议给华北局的报告》(1948年11月18日),转引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269 页。等现象时有发生。解放战争初期,有些根据地已开始出现了“回家种地”的思想苗头,特别是1946年2月国共两党签署了《整军方案》③《整军方案》是国共两党对各自军队进行整编的一个依据。整军分两期进行:第1 期为12 个月,第2 期为6 个月。在第1 期终了时,国军缩编为90 个师,中共部队缩编为18 个师;在第2 期终了时,国军进一步缩编为50 个师,中共部队进一步缩编为10 个师。之后,国共双方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复员工作,致使其后“新兵的征集工作相当困难”④有的根据地扩军,不得不采取“抓球(阄)”的办法,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谁抓到谁去。参见《任河正×支部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和群众路线》,载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群众路线研究》(党内),1947年,第30 页。。因此,如何克服民众的“搭便车”⑤关于“搭便车”理论,参见[美]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心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支援人民军队的积极性,成为摆在共产党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不断深入,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对此,中共中央认为,支持农民渴望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既能变革封建农村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进一步巩固解放区,这对于支持长期战争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在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将地主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土改运动的动员效果,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动员必须跟进,因为“在果实分配以前,农民尚未得到实际好处,对参军很难发生兴趣;而分得果实所激起的农民的认同和热情,也可能很快就会消退。”⑥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 期,第75 页。因此,在给予农民“胜利果实”的同时,还要从思想上加以感化和唤醒。
“诉苦”⑦此处的“诉苦”是作为一种动员策略开展的。由于在同时期军队也开展了旨在改造“解放战士”的“诉苦运动”,二者在行为方式上有共同之处,但目标主体是不一样的,在此仅以“诉苦”命名。是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一种方式。它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⑧陈北鸥:《人民学习辞典》,上海:上海广益书局,1952年,第331 页。。诉苦的目的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启发阶级觉悟。在实践中,各解放区发明了“访贫问苦”“倒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斗争大会”等方式,从而激起反对“大蒋及小蒋”的怒火,再转到翻身,追富根,从而掀起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以及入党参军的热潮。至于如何将“诉苦”与参军动员结合起来,冀鲁豫党委的经验极具代表性:
在方式上,以区为单位,选择好的村干、积极分子,召开村干积极分子会议(四五百人),先进行小组酝酿,找出苦最深最痛的典型诉起,求得突开局面。小组酝酿成熟,即在大会诉苦,当群众诉苦到痛处,全场大哭,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气愤……这时候要抓紧火候,进一步追穷根,追到地主身上,追到老根蒋介石身上,群众咬牙切齿,顿足捶胸,激起高度的阶级仇恨。接着即抓紧火候,转到追富根,从共产党领导翻身后有了土地,生活好起来,大家认识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给的……,这时要抓紧,把大蒋与小蒋联系起来,说明大蒋组织与领导小蒋要想回来夺我们的三亩地,不让咱们翻身,不打退大蒋的进攻,三亩地即保不住。这样把反蒋内战与个人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群众即自愿自觉参军。在郸巨六区,……一百三(十)多人自动报名参军。①《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参军经验介绍》(1946年9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8 册,第379 页。
由此可见,“诉苦”作为兵役工作中的一种情感动员方式,必须与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精心挑选“好的村干、积极分子”以及“苦大仇深”的“典型”,这是“诉苦”的关键。同时要有序开展,严密组织。从实践上看,干部的带头作用极其重要,能够“自动报名参军,起带头作用”②《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参军经验介绍》(1946年9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8 册,第379 页。。只要农民的仇恨情绪被点燃,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和积极是让人震撼的,冀鲁豫解放区的一则通讯为我们描述了一幅诉苦参军的生动场景:
六区的群众诉到枣河杨庄被冯太恒一起杀死了廿八人,想起冯太恒如今还在东阿城里时,大家痛恨的说:“咱们要给枣河杨庄的父老报仇,非活捉蒋介石、活捉冯太恒不可!”三里庄刘长义也激奋的说:“我要参军,我要活捉蒋介石、活捉李岐山、冯太恒,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热烈报名的激奋声中,老年人也感动的说:“我给你们打水、泥屋、扫院子,保险不荒一亩地。”妇女们说:“俺给你做衣裳、织布,管叫你家不作难。你们放心去捉老蒋吧!”灭蒋复仇的热火,燃烧在每个到会人的心里,经过一天的酝酿,即有二十余名青年跑到英雄台上报名参军。最后,到会的积极分子们,均订出了自己回村后的工作计划,例如怎样把灭蒋复仇的任务交给群众讨论,领导群众展开小组酝酿、家庭会议等,并且展开村与村竞赛,看谁自愿、谁成份好,年龄合格,看谁拥军拥的好。③《茌平从诉苦入手 群众自愿参军复仇》,《人民日报》1947年12月12日。
生活在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农民,或多或少都有各自不同的“苦”,单独的“苦”很难汇聚成阶级情感和阶级意识,可一旦给他们一个平台,在公开场合将各自的“苦楚”集体表达出来,同病相怜的情感会使诉苦参与者产生共鸣。一旦追查到苦难根源之后,一个人的仇苦变成了群体仇苦,群体仇苦变成了整个阶级的同仇共恨,从而奠定了兵役动员的情感基础。
三、参军运动——参军志愿的集体表达
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的土地改革运动,给予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而完成了“革命共意”的构建;通过“诉苦”,实现了农民从“翻身”到“翻心”的情感转变,在物质和情感的双重刺激下,农民与共产党已经是“一家人”。共产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通过精心的组织,将这种有利局面演变成农民踊跃参军的现实。
解放战争时期的参军运动是伴随着战争的进程展开的。1946年8月20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参军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全心全意,拿出一切力量,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在参军动员中,要“造成群众性的参军运动,也只有造成群众性的参军运动,才能完成任务”①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8 册,第346 页。。1948年底,中共华东中央局也发出了《关于动员参军的指示》,强调征兵要以“自愿参加”为原则,并指出,“参军问题必须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充分的政治动员与细致的组织工作”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数据选编》第21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6 ~467 页。。根据这些文件精神,解放区确立了征兵的基本路线和方法。在路线方面,主要是抛开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以走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完成任务。③行政强制性的征兵在某些地区确实出现过,其结果是造成党群关系恶化,部队逃亡现象增多。比如在晋绥区的山阴五区曾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各村抽好,工作组一到就集合带走;还有的参军对象跑了,干部就捆打其家属,封他的门;还有个别雇佣的现象,比如崞县有一次扩大之445 名新战士中有40 名是雇的。参见《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春季扩兵工作决定》(1947年2月1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8 册,第554 页。在实施方法上,解放战争时期的征兵工作,一般先由中央军委和各大区领导机构,根据战场上的实际需求确定征兵人数,然后参照各地具体情形(如人口数量、经济状况、党的控制程度、土改完成情况等)进行分配。随即,征兵任务通过行政渠道层层下达,从各地区到各县、各分区,最后各个村庄都会分配到一定的参军指标。任务下到村庄以后,即成为该村的“中心工作”,村中各种组织,包括党支部、村政权、贫农团、农会和在村指导土改的工作队,都要围绕动员参军展开工作。④参见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福建论坛》(社科版)2007年第11 期,第75 页。当参军发展为一项运动时,必然要求运动的组织者采取一些措施来推动运动的稳步开展。
首先是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与国民党基层行政系统的保甲长们相比,共产党基层干部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他们处于政权体系的最末端,但作用却至关重要:一方面,各种征发均始于村;另一方面,各项政策均由村干部具体执行。就参军动员而言,村干部不仅要按规定的合法程序组织动员农民参军,而且为了完成任务,必要时带领农民参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平很低,因此“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不能成功的”,“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作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⑤辛玮、尹平符:《山东解放区大事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7 页。因此,在各解放区关于参军运动的文件指示中,都强调党员干部必须以带头示范的方式,由党内带动党外,由干部带动群众,将工作中“存在的内部意见或不满化除或保留”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动员参军的指示》(1946年8月2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8 册,第349 页。,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合力。晋察冀中央局规定“至少20%的党员参加到前线作战的野战纵队中去,成为广大人民参军的模范”⑦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321 页。。在此鼓舞下,“冀中最优秀的青年,大批共产党员涌上前线,河间、饶阳、武强参军青年中,共产党员占二分之一;无极一区九十一人入伍,其中共产党员有五十四名”⑧《冀中人民的优秀子弟共产党员争先参军》,《晋察冀日报》1946年9月11日。。淮海战役期间,胶东高密县5 个分区就有126 名村干部带头参军⑨张劲夫:《兵民是胜利之本:回忆山东人民对淮海战役的支援》,《军史资料》1986年第6 期,第39 页。;鲁中莱芜地区的一些村干认为“这次动参是自己提出来的,完不成可不行”⑩《鲁中参军运动之冠,莱芜六千八百人参军》,参见《莱芜战役中的莱芜人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 页。。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解放区,党员干部带头参军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其次是发挥模范典型的感染作用。在党史文件和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随处可以见到“送子参军”“送郎参军”“兄弟争相参军”之类的动人事迹,对于这些事迹的宣传利用成为参军运动中行之有效的动员措施之一。荣成县青年孙传在一次诉苦大会上,听到青年妇女唐希坤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害得她家破人亡时,咬破手指,用鲜血在学习本上写下了“为国为民”四个字,怀揣血书上了前线。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全村又有10 名青年报名参了军。①高玉峰:《中共威海地方史》第1 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94 页。日照县傅叮村范大娘有3 个儿子,长子、次子先后于1945年、1946年牺牲,1947年她又将幼子送去参军,滨海支前司令部授予她一面绣有“人民的母亲”字样的锦旗,以示表彰。②高克亭:《支持前线,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山东人民支持解放战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2 页。在1947年的大参军运动中,文登全县妇女劝夫参军1922 人,劝未婚夫参军的855 人,送子参军的2512 人。③高玉峰:《中共威海地方史》第1 卷,第294 页。如山东解放区莒南县动员哥哥参军的典型模范刘继再在接受王友明访谈时说:
上边号召参军,要求党员带头,翻身参军,我哥是党员,我在十字路开干部会,我哥登台报名,……参军成了,山东试验话剧团天天找我,一块生活、一块工作,写出又排演,在鲁东南地区、军人当中大演特演,起了一定的轰动作用,俺村成了参军模范村。④王友明:《论老解放区的参军动员:以山东解放区莒南县为个案的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4 期,第75 页。
除了用典型模范从正面鼓舞带动群众参军之外,还从侧面对落后村庄进行刺激,比如让模范村庄举行隆重的欢送新兵活动,欢送队伍从落后村通过,同时高喊口号:“只有哪个村还没有参军的?”“申家碥山!”从而使该村干部群众受到很大刺激,紧接着由县府一位科长动员自卫队长带动了7 人参军。⑤王友明:《论老解放区的参军动员:以山东解放区莒南县为个案的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4 期,第79 页。对于那些特别顽固落后的村庄,言语的刺激往往效果较差,就需要施加一些压力。1948年8月,赤西县扩军,“检查各村的出兵多少及本位思想,对出兵特别少的顽固村,在大会上开展了思想斗争,代表们向这样村提出了警告,在五区村干代表会上向下官地展开了思想斗争:为什么你们村没有当兵的,为什么青年小伙子们都参加了红枪会,红枪会能不能打倒蒋介石……下官地代表被查问的脸红脖子粗,没有任何回答,向来不出兵的下官地村这次参军者二十多名”⑥赤西县委:《扩军工作总结再写》(1948年8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520-1-314-5。。
四、结语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经验的基础上,在解放区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土地财产的再分配,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持。在给予农民物质利益的同时,还注意从思想上进行感化和唤醒。与土改运动相结合的“诉苦”,它将农民个人的苦难汇集成整个阶级的共同仇恨,最终爆发出难以估量的战斗力量。在“土改”与“诉苦”的双重作用下,民众的革命热情被点燃,通过宣传教育,很好地将参军动员转化为农民保田保家的切身利益。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对社会资源的汲取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汲取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的同时,也成功地将乡村社会成员进一步整合到政治体系中来,在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团结和秩序,顺利实现了兵役动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