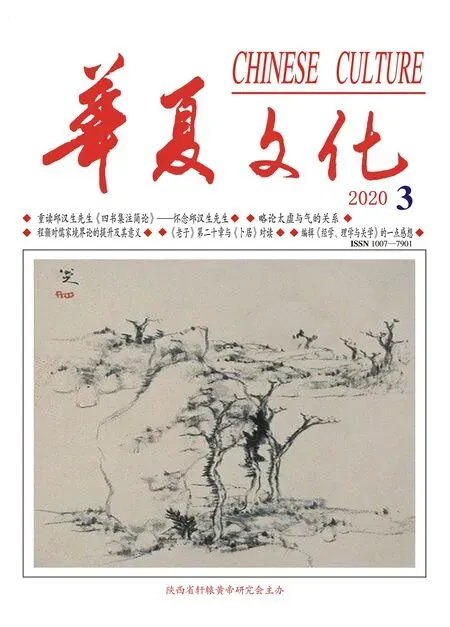程颢对儒家境界论的提升及其意义
□魏 涛
孔孟之后,程颢、程颐创立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以明道为目标、以成德成圣为目的的理学体系,基于对二程兄弟思想近似性的判定,往往将其统纳为一体进行定位和传播。自牟宗三、冯友兰始逐渐重视二程思想差异性的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界日益形成了对二程进行分化式研究的局面,然从总体上来看,对程颢的专门研究尚嫌不足。大程对传统儒学的推进和对后世理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环节,从境界的意义上把握程颢哲学对于深入理解其哲学总体特征和明确其问题指向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个儒学史来看,他对传统儒学境界论的理论建构与践行展现出鲜明的新特点。
活泼而有生气
明道心态活泼,为学教书不主强背。他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解释经典之时,也颇有独特之处。谢良佐说“明道先生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又说:“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不只谈诗时如此,讲论《论语》《孟子》《易传》《中庸》亦然。如在解释《中庸》时言:“‘纯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三月不违仁’之气象也。又其次,‘则日月至焉’者矣。”以天德解说“纯亦不已”,以“三月不违仁”之气象说“造次必如是,颠沛必于是”。这些都文字简约,语气活泼。一天看见火边烧汤瓶,便指之曰:“此便是阴阳消长之义”。他眉目清峻,语声铿然,讲话活波无呆气。文字简洁明了,很有启发性。伊川曰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两人比较起来,伊川的语言显得较为呆滞。但是朱熹并不欣赏明道这种讲话的方式,他曾批评说“明道言语浑沦。”又说:“说话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甚至批评明道这种语言教学方式:“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睥见上一截,少下面着实工夫,故流弊至此。”其实从另一侧面来看,朱熹所说的“浑沦”、“高”都是指明道说话时文字简略、义理圆融的现象。朱熹喜欢伊川的分解表达,就如此批评明道,这当是心态的差异所致。
自得而有生意
《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下记载张横浦之言曰:“明道书窗前有茂草履砌,或劝之 。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唯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语?”当一个人私意净尽,天理昭融时,心中自然无一毫系累,此时真得解放与自由,自然满腔子都是生意。但一个仁者的情怀不只是希望自己得自由,亦希望众生都自由,不止希望自己满腔子都是生意,也希望众生生意盎然。当这种自由、生意向外推展时自然与他人、与他物合为一体,并在“一体”意义中消除人、我,人、物之限隔,而体会他人之自由即自家之自由;他人之生意即自家之生意。明道已亲体此境,故而草之生意即自家之生意;鱼之自得即自家之自得,这是“常见造物生意”,“观万物自得意”。这也是明道所言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意思,这些现象不是偶然的行为,而是对圣人之境体悟的自然流露。故朱光庭见明道于汝州后,回去即告诉人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这是说他在仁心之浸润的潜移默化中经历了一个月。吕子约也说:“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人气象。”如其在《秋日偶成》中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更是简洁明了地道出了明道晶莹澄澈的生命境界。
温和而敦厚
明道性情温和令人容易接近。一次和伊川随侍太中知汉州。晚宿一僧寺中。明道从右门入,“从者皆随之”,伊川从左门入,“独行”。至法堂上相会时,伊川叹曰:“此是某不及家兄处。”明道偶尔会有戏谑之语,而伊川则无。刘绚说他“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然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 ,这也不只是他性情和易使然。这是他真正体悟圣学并于行为中实践出来的表现。《河南程氏外书》卷七中云:“安国尝见邹至完,论近世人物。因问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万物各得其所。’” 与伊川相较,程颢温润而敦厚。史载:“明道先生每与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讨论时,学生若对答得体,程颢会说:“更须勉力”。其敦厚之风溢于言表,故谢上蔡说“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 程颢作为王安石变法反对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对程颢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11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想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见是程颢,“为之愧屈”。
廓然而大公
儒门圣学在传统上不重学统的建立,而比较重视人格的完成,重视道德实践。个人的有限生命通过道德实践得到有限的归趋。从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对孔子而言最高造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孟子那里则是曾子式的“不动心”。用理学家们的话来说叫做“天理流行”,在程颢这里则被表达为“廓然而大公,顺来而顺应”。廓然大公是“不自私”,“物来顺应”是“不用智”。在《定性书》中认为,人之情各有所蔽,大抵病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此义实同于《论语》所说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必、固者,用智也;我者,自私也。所以不自私、不用智即是“四无”之工夫。当私意净尽,天理昭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自私,不用智时,此时之境界就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定性书》作为回答张横渠的答书,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定心”(定性)的问题。张载认为:“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上,而明道则认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茍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是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之所以“非是”,因为其先有内外分化之对待。以内应外,就是牵己而从之。既是牵己以从外,则外也累内。只有去除内外之分,“心通于道”,方可成就定性之工夫。当“心通于道”时,则一切行为不假思虑,用《定性书》的话说即“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可见能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的最真实工夫在“观理之是非”,能观理之是非即心通于道,这样方能言“定”。方能“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澄然无事”是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心通于道,一循于理,所以澄然无事。“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的澄然无事,是不着一分意思,不自私用智的澄然无事。圣心处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切执着、私我都去除荡尽,此是“廓然”。这就是程颢所说的时贯之以仁,即所谓“太公”也。理当如何则表现如何,这是“义之与比”。孔子被赞美为“圣之时者”,因他当清则清,当仕则仕,当和则和,一切都能适时合宜而中节合度。与其他人的执着一端明显不同。
从”定性”到“识仁”,程颢思想渐趋完善,其天地本一的思想借由“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得以系统地落实。从理与仁的同一、理与义、理与性、理与命、理与气的一体化理论特质,充分彰显了传统哲学中直觉思维重于生命践履的鲜明特色,对于中国传统儒学境界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程颢的境界论在很大程度上开显了传统儒家发展的新境界,其所提领的“物来而顺应,廓然而大公”的精神气象,与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一起,共同担当起建构中华人文精神的神圣使命,对后世士大夫理想人格的锻造与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程颢之后,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经其弟子谢良佐传入湖北湖南,由胡安国、胡宏父子弘扬,张栻发展而成的湖湘学派。二是经王频传入江苏而形成的吴学。以上两学派对陆王心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程颢的境界论,将儒学本有的自然主义进一步激发,并集纳了道家境界论上的高明玄远,既延续了孔子那里“吾与点也”的洒脱气象,也将魏晋玄学那里圣人有情无情、动静的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浑然通透而富有生意的境界论,展现出与周敦颐“窗前草不剪”相类的现实超越感,加上明显与程颐、朱子的重分别,严分形上形下,区隔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的路径不同。作为自然主义的典型代表,程颢致力于将自然与道德统一起来,试图从生生不息的自然中推导出仁德。尽管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考量,其推导过程并不是很充分,善恶并存的自然与至善无恶的道德似乎难以统一,但程颢所开显的“物来而顺应”“廓然而大公”的道德理想目标却着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儒家境界论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谱系中,程颢因其在境界论上的鲜明特色使得汉唐以来神学化、谶纬化、经学化、政治化的儒学严肃形象有所改变。在儒家道、学、政的不同理论面向上强化了自韩愈以来人们对大道流行地向往与追求,尤其是在关于道德体悟和道德践履的合一上实现了情性、内外、知行、动静、圣凡等的切实贯通,也无怪乎牟宗三对其评价甚高,将其视为儒学发展的“正宗”,而将其弟程颐与朱子一系视为“别子为宗”。作为儒释道合流的理论典范,程颢既通过自家体贴出的“天理”让在“学绝道丧”背景下的儒学有了立足之本,又通过身体力行将鲜活的生命气息注入儒学之中,让人们在思想深层增加了“如沐春风”般而非“道貌岸然”般的对儒学的价值认同。
说明: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正蒙》的古典诠释与现代张载哲学研究范式的生成”(项目号:2018BZX014);宝鸡文理学院科研项目“张载政治哲学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项目号:YKH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