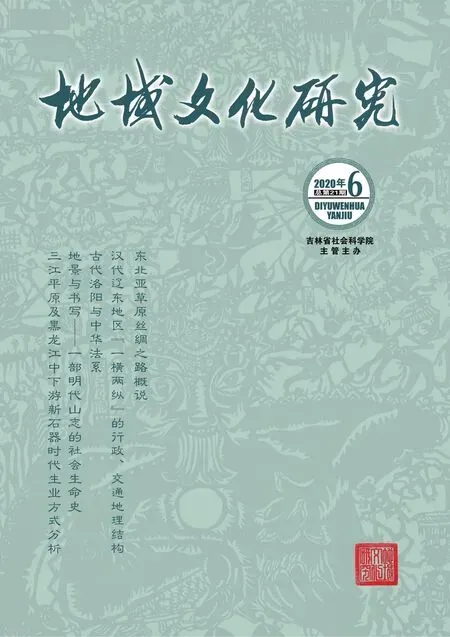古代洛阳与中华法系
邓长春
洛阳古称“天下之中”①《逸周书·作雒解》称洛邑为“天下之大凑”。见《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4页。《史记·货殖列传》亦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3263页。。作为西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北宋等重要王朝的都城或陪都,古代洛阳不仅是中原王朝法制推行的首选区、司法运转的示范区、法文化的塑形区以及法界精英荟萃的学术创新区,而且也是中华法系融合发展的创新之地、法制发达的至高之地、法文化辐射四方邻国的向心之地。概而言之,洛阳是中华法系最为核心和先进的区域之一。
一、古代洛阳与中华法制
中国法律的制度规范以礼法精神为魂魄,以律令法制为躯体,以渐次加入的民族法俗为不断更新的新鲜血液,构成一个完整的制度文明运作系统。中国法律的这三大法制要素,都曾在古代洛阳发生过节点性事件。
(一)礼法制度酝酿萌发于西周洛邑
中华法系之所以能与其他几大法系②1884年,穗积陈重首次提出五大法族(印度法族、中国法族、回回法族、英国法族、罗马法族)之说,是为法系学说之始。其后关于法系划分又出现的多种学说,中华法系都是其中之一。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法为中心、涵盖古代东亚、东南亚众多国家法律的一个庞大的法律群组。并立而称,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精神特质与价值内核,即礼法传统。①俞荣根教授指出:“‘礼法’不是‘礼’和‘法’、‘礼’加‘法’,或礼中有法、纳法于礼。‘礼法’是一个双音节词汇,一个名词,一个法律学上的法概念,一个法哲学上的范畴。是古代‘礼乐政刑’治国方式的统称。”见俞荣根《礼法传统与中华法系》,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江山亦谓:“从某种意义上讲,礼制是中国法律形态或中国法律文化的主体……研究‘礼法’,不仅于理解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国文化有直接的意义,而且对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转型,或创化地利用‘本土资源’支持中国进入‘法治’社会,亦是不可或缺的。”见江山《历史文化中的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7页。礼法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与商礼重祭祀、轻道德不同,②侯外庐先生说:“卜辞里没有道德一类的字样。除了对于祖先帝王的崇祀,并没有道德规范,这是和周代不同的。”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周礼紧密围绕“德”这一中心概念,推出敬天保民③《尚书·洛诰》中载成王对周公说:“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见《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11页。《康诰》中又载“用康保民”。见《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7页。、明德慎罚④《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见《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6页。《多方》又曰:“罔不明德恤祀。”见《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5页。、任人以德⑤《尚书·多士》曰:“予一人惟听用德。”见《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8页。等一系列主张,形成一套全新的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与法律制度,此即周礼——周代礼法。作为周代礼法的肇始之地与礼法之治率先垂范之地,洛邑便在此背景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就开始谋划在伊洛盆地营建都邑,⑥《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临终对周公言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见《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22-523页。《尚书·召诰》孔传亦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故成王居焉。”《史记·周本纪》载周公之言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页。“宅兹中国,自兹乂民”⑦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武王死后,周公、召公在洛水北岸选址,迁殷遗民营建洛邑。《尚书·康诰》描述了开工时的盛大场面。⑧《尚书·康诰》载:“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见《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5页。周公摄政七年,新邑建成。周公至镐京请成王移居洛邑。召公受命到洛水“相宅”⑨《尚书·召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11页。,营造王宫。⑩西周洛邑究为一城、二城还是包摄,目前学界尚有分歧。笔者认同一城说。详细参见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随后成王正式入住。洛邑自此又称成周,⑪《尚书大传》卷12:“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见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5,光绪二十二年师伏堂刊本,第18页。成为周王室控制殷商故地和东方国土并进而构建天下秩序的总基地。⑫杜勇:《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可见,营建洛邑作为统治中心是周室经过深谋远虑之后集体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堪称千年大计,影响深远。
成周洛邑的建成与使用,从三个层面上丰富了周代礼法的内涵:
其一,洛邑的规划、设计与定位,树立起礼法制度下中国传统都城的经典范式。例如,洛邑坐北朝南、背山面水,①《逸周书·作雒解》:“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见《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1-564页。洛邑王城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建筑格局,②《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见《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65页。都对后世影响深远。又如,洛邑城中有丘兆、社壝、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京宫、康宫等实施礼仪法制的重要建筑,成为展示礼法的舞台。③《逸周书·作雒解》,《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8-573页。出土金文显示,成周有京宫、康宫两大宗庙祭祀系统,前者祭康王以前各王,后者祭康王以下各王。有日本学者曾指出,中国古代都城既是生活的空间,也是统治者展示礼制的舞台。参见[日]妹尾达彦著,陈耀文译《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载[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5-483页。它们作为周代礼法的有形载体,承担着特定的政治文化功能,是周王室与天下诸侯保持联系的重要政治文化纽带。洛邑借此在天下体系中确立起政治中心、祭祀圣地、礼法宗源三位一体的尊隆地位。
其二,洛邑建成之后的礼法创设活动,不仅丰富了礼法制度的精神内涵,而且彰显出礼法对华夏多元文明的聚合力,反映出周代礼法颇具历史纵深的宏大构建进程。
在周代礼法的创建过程中,洛邑发挥着中心、示范的作用。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与军政,④《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见《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61页。洛邑自周初开始便发挥着最高层级的礼法职能。例如,成王刚到洛邑便在此地率领诸侯举行包括文武之祭在内的定宅典礼;⑤邹家兴:《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作为周朝核心军事力量的成周八师亦同样驻扎在洛邑。⑥作为西周畿内军事防御核心力量,宗周镐京附近设置六师,成周洛邑则设置八师。由于洛邑位居夏商故都附近,向东联结众多新拓殖的诸侯国和与殷商关系密切的东夷方国,因而驻屯重兵在此不仅可以震慑殷商后裔,而且可以巩固周王室的东方势力范围。由此可见洛邑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礼仪实践和制度安排,周代礼法在洛邑得到充实,并逐步扩大影响范围。而洛邑则成为中华法系打造、输出礼法制度的策源地之一。
其三,洛邑的礼法设施与礼法活动经过历史的沉淀,逐步演变为令后世景仰的礼法文物。这些礼法文物,一方面增加了洛阳礼法圣城的神秘光环,另一方面又引发出若干重要的法文化事件。
西周初,武王和周公将“九鼎”⑦《汉书·郊祀志上》:“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见《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25页。《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见《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9页、第671页。“九鼎”之意,一说实为一鼎,采九州贡金铸成;(《左传·宣公三年》载王孙满语)一说确为九鼎,每一鼎由九万人铸就,合计九九八十一万人铸成。(《战国策·东周策》载颜斶语)尽管考古研究表明,西周中晚期才开始出现成熟的列鼎礼制。参见刘颖惠、曹峻《周代中原用鼎制度变迁及相关问题探讨》,《殷都学刊》2016年第3期,但那主要指的是食鼎制度,与此处的“九鼎”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能据此而否认洛邑九鼎的存在。迁至洛邑,作为定鼎中原、天下一统的象征。东周时王室衰微,诸侯霸主凌越天子,藏于洛邑的九鼎招致诸侯觊觎。于是发生楚庄王亲赴洛邑问鼎之轻重⑧《左传·宣公三年》,见《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69页;《史记·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00页。、秦武王到洛邑举鼎⑨《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9页。等历史事件。春秋末期,孔子曾以私人身份到洛邑参观礼器,寻阅典籍,问礼于守藏室之史老子。尽管“孔老之会”自古以来便有质疑之声,但是以孔子重礼的思想主张,即便不曾见过老子,其至洛邑问学礼法也在情理之中。孔子及儒家学派以周代礼法作为治理天下的理想模板,必定从洛邑所存礼法文物中获得不少灵感。
(二)律令法典体系初成颁行于魏晋洛阳
律令法制兴于东周,起自关中、河东一代,是中华法系继礼法体制之后又推出的一种法律表现形态。自秦代以后,历代王朝都继承发展律令法制并形成一个系统,称作“律系”①程树德:《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页。或“律统”②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页。。
秦汉推行律法治国策略,然而律令法制混乱繁杂的困局亦随之而来。其突出表现有三:一是律令篇目及其分类标准的不系统。二是律令与其他法律形式关系混乱,难于理清。三是律令条文与司法解释规模膨胀,③《后汉书·陈宠传》:“宪令稍增,科条无限。”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54页。积重难返。④汉初奉行黄老无为之术,删约秦法而为汉律九章。汉武帝以后,律令规模迅速膨胀。《汉书·刑法志》:“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见《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1页。此困局经过秦汉四百年的缓慢积累而成,至魏晋时方才迎来转机。一个律令法典体系化运动在魏晋都城洛阳勃然而起,深刻影响了中华法系的发展趋向。
汉末董卓之乱令国都洛阳一时沦为丘墟,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并以之为都。曹丕接受献帝禅让之后,还都洛阳以示承继东汉正统。其子魏明帝“留意法理”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页。,重视法律。正是在洛阳,他命臣下对秦汉以来的律令法制文本进行系统整合。接到诏命的陈群、刘卲、韩逊、庾嶷、黄休、荀诜等人“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⑥《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3页。。这些精通法律的居京高官,调取收藏于洛阳秘府、兰台、东观的前代法律文献档案,对其篇章条文进行系统梳理,“都总事类”⑦《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4页。,重订体例。最终完成《新律》《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等法律文本180余篇,成为秦汉以来律令法制体系化的一件大事。
曹魏律令法典编纂的成就主要有三:一是律、令的纯化,即“律成为专门以定罪正刑为务的法典之专称”⑧刘笃才:《汉科考略》,《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令则成为基本国家制度的效力渊源。⑨梁健:《曹魏法制综考》,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0-81页。二是律令法制的体系化。曹魏《新律》各篇目和条文之间逻辑清晰,刑罚系统实现完整统一。⑩参见[日]冨谷至《通往晋泰始律令之路(I):秦汉的律与令》《通往晋泰始律令之路(Ⅱ):秦汉的律与令》二文,朱腾译,徐世虹校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编《日本学者中国法论著选译》(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三是律令法制的名理化,反映出自东汉以来律学理论发展的综合水准,是名理法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然而,曹魏律令法制体系仍有显著不足。魏末晋初的法律家贾充、杜预、羊祜等人在其基础上继续进行法律文本的整合工作。历时三年余,在西晋泰始四年(268)正式推出体系完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律令法制体系,由《律》《令》《故事》三部法典组成。①《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7页。,自此开始,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律令法典。在这个法律体系中,律典与令典的内容功能被严格区分,令典从正面规定一般制度,律典从负面规定违反国家制度的刑事处罚,从而达到二者分工合作、彼此辅助的效果。②“违令有罪则入律。”见《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7页。西晋泰始律令的出现,是“中古时代法典大备的开始”③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17页。。这个影响中国法制史的重大变革,正是在西晋都城洛阳酝酿完成并颁行天下。
西晋泰始四年(268)正月丙戌,晋武帝在都城洛阳发布诏书将其颁行天下。定科郎裴楷在律典初成之后,受命在洛阳皇宫太极殿的御前朝会上,手持律书当众高声诵读律文,称为“执读”④《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8页。。他每念完一条,便由在场君臣进行讨论,最终形成定议。裴楷仪表非凡,善于朗读。他那清爽、顿挫的诵读,配上简易、雅致的律文,堪称金声玉振,令“左右瞩目,听者忘倦”⑤《晋书·裴秀传附裴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3页。,堪称视听享受、精神盛宴。
《泰始律》颁行后,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上表请求:“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⑥《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47页。可以想见,当时抄有律典死刑罪名条目的法律文书,正是从洛阳十二个城门附近的都亭开始悬挂昭示,一直挂到王化所及的天下亭传。在文书行政的时代,中华法系的文本与精神正是以这种方式传递、实施,恰如由心肺发送的律动传递到奇经八脉,又如头脑发号的施令遥控手脚四肢。而洛阳正是这律动传递的初发点、施令传导的信息源。
西晋泰始律令的颁布在中华法系的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西晋灭亡以后,泰始律令一直在东晋南朝长期沿用。而在十六国、北朝,泰始律令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⑦楼劲:“天兴以来‘律’、‘令’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逐渐向魏晋以来定型的《律》、《令》体制靠拢的过程。”参见楼劲《北齐初年立法与〈麟趾格〉》,《文史》第61辑。泰始律令的影响直到隋唐,⑧例如,高明士教授称:“《开皇令》的源头,宜曰晋令。”见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页。而唐代令典又大体上是对隋《开皇令》的继承发展。并且与唐代律令法典体系一起流播海外,成为中华法系法律空间定型的标志。(详见下文)而其酝酿外传的始发站正是西晋都城洛阳。
(三)民主法制融合创新于北魏洛阳
历经八王、五胡之乱后,魏晋洛阳城沦为丘墟。直至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洛阳才开始慢慢恢复往日荣光,并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又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北魏法律广泛吸收中原、河西、江左的汉族三大法律传统,兼采汉、晋两代法制的优秀因子,与鲜卑民族法律传统融合在一起,炉而冶之,取精用宏,成为当时中国最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实现中华法系的重生再造。⑨关于北魏法律渊源,以陈寅恪先生“三源说”最为经典。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12-119页。曾代伟教授指出,探讨北魏法律渊源不应忽略拓跋鲜卑传统之民族习惯法。参见曾代伟《北魏律渊源辨》,《法律史论丛》第7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269-287页。在此过程中,洛阳再次发挥出关键节点的作用。
首先,迁都洛阳成为北魏确立政权合法性,竞争华夏正统地位的重大战略举措。
拓跋鲜卑凭借武力入主中原,如何获得中原汉人的认同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北魏前期统治中心在平城,就已开始从形式上模仿汉晋法制。孝文帝时,北魏法制改革突然加速,由以武立国转向以文治国。而迁都洛阳则成为当时系列改革的高潮和收官。
从表面上看,孝文帝看中的是洛阳的地理文化意义,即所谓“崤函帝宅,河洛王里”①《魏书·任城王元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页。,更合乎地域的正统性。但实际上,孝文帝汉化的用意远不止此。他要在洛阳“托周改制”,在政治文化制度层面确立真正的正统,“齐美于殷周”,比肩于汉晋。②《魏书·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迁都后诏曰:“卿等欲令魏朝齐美于殷周,为令汉晋独擅于上代?”见《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5页。只不过,他认为洛阳为周之东都,在洛阳隆修周制于华夏正统更为有据罢了。③陈金凤:《北魏正统化运动论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经过孝文、宣武两代皇帝的持续努力,定鼎嵩洛的拓跋鲜卑最终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其正统形象也逐渐得到南北朝士人的普遍认可。④《洛阳伽蓝记》“景宁寺”条记“中原士族”杨元慎斥责南朝梁将领陈庆之称梁为正统时说:“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而陈庆之后来回到建康后对北人钦重异常:“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见《洛阳伽蓝记》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180页。
孝文帝仿效周公营建成周的故事重建洛阳城,兼具胡汉两方面的文化特色。一方面,北魏洛阳城按照周制设计“左祖右社”的布局,遵循宫、城、廓三层环套的配置形制以及城、廓分工的传统规划。由于规模空前浩大,孝文帝在工程尚未完成时便迫不及待地于太和十八年(494)正式迁都至此。另一方面,由于参与洛阳新都建设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参与过孝文帝改建平城的工程,因此洛阳的建制规模还深受北魏故都平城的影响。尤其是反映出从草原文化到农耕文化过渡痕迹的“里坊制度”更是直接源自于平城,并且对后来隋唐的长安、洛阳形成了深远的影响。⑤[韩]朴汉济著,朱亮译:《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又参见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0-180页。
其次,北魏政权在洛阳完成律令法典的定本,展开中原汉人礼法与鲜卑部族习惯法的碰撞融合。
孝文帝之子宣武帝继承父志,进一步从法制角度巩固汉化政策成果,制定出北魏律的定本《正始律》。正始修律是北魏第七部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议律活动,不仅弥补了前面法律的各种缺陷,删增调整了不少条文内容,而且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贯彻儒家的礼教法律观,使儒学经义彻底占据法律领域。当时参与议律的人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刘芳、常景和元勰。刘芳长于儒家经学,在议律过程中担任议主,将大量礼法理论援引进入律典。常景则是律学名家,在议律过程中主要从专业角度把控律典的技术性内容。元勰作为深受儒家仁政观念影响的宗王,对议律有决断之权,保证了议律的总体方向。⑥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2-95页。北魏在洛阳的法制创新还不止于此。在《正始律》之前,宣武帝就已下诏“藏窜者悉远流”①《魏书·源贺传附源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3页。,正式开创流刑之名;《正始律》之后,又对官当制度的一些细则进行了补充修订。②《魏书·刑罚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9页。所有这些法律成就。都是在拓跋鲜卑部族习惯法与中原儒家法传统逐步融合的成果,“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所致也”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26页。。而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洛阳完成的。
二、古代洛阳与中华法学
洛阳长期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人文荟萃、思想激荡、学术碰撞的交流平台。同时,洛阳也常是天下法律文书档案最丰富的宝库。两种要素彼此交织,便催生出中华法学在洛阳的繁荣局面。若论洛阳法学之繁盛,尤推东汉、魏晋、北宋三个时期。
(一)东汉洛阳律章句之学
定都洛阳的东汉王朝,法学研究较之西汉更为繁盛。尤其是作为当时法学主流的律章句之学④章句本为汉代经学家研究儒家经典的注释形式,被法律家借用来解释律令就成为律章句,进而兴起了作为古代法学独特形态的律章句之学(简称律学)。,更是学派林立,名家辈出。《晋书·刑法志》载:“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可谓极盛!
据龙大轩教授考证,东汉律家有杜林、郭躬、陈宠、许慎、马融、钟皓、吴雄、郑玄、何休、服虔、文颖、应劭等十二人。⑤龙大轩:《汉代律家与律章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6页。这些律家,尽管来自不同地方,学术渊源各异,却大都以各种身份活跃于京师洛阳,与洛阳存在各种各样的学缘关系。他们有的求学于此,有的任职施展抱负于此,共同撑起盛极一时的东汉洛阳律学。
东汉律学有家学的传统,律学世家是东汉洛阳律学的主力。⑥崔祖思曰:“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洁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冤,庆昌枝裔,槐衮相袭,蝉紫传辉。”见《南齐书·崔祖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19页。当时著名的律学世家有颍川郭氏、沛国陈氏、河南吴氏等。他们的子弟自幼在家中受到法学的熏陶与训练,长大后又凭此进入洛阳担任法律要职,发挥专长贡献于国家法制建设。郭氏律学始于郭弘。郭氏子弟长期在洛阳任职中央法律要职。史载:“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⑦《后汉书·郭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6页。此外,沈家本先生亦曾提及,《晋书·刑法志》中的“郭令卿”、“或为颖川之裔,令卿其字也”。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750页。其中尤为著名的是郭弘之子郭躬。他自幼传习父亲的法律之学,长大后又招徒讲学,徒众常有数百人。后来他入洛阳官拜廷尉,断案宽平,推动法律改革的建议也都得到施行。⑧《后汉书·郭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4页。陈氏律学始于陈咸。陈咸之子陈钦在东汉初年任职廷尉左监。陈钦之子陈宠在洛阳担任中央最高司法官员廷尉,掌管天下狱讼;又撰写律学著作《辞讼比》七卷,被官方确认为具有法律效力;还提出“荡涤烦苛”“应经合义”“失礼则入刑”等礼法主张,对于振兴礼法传统,推动律令儒家化和体系化,均可谓影响重大。①《后汉书·陈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8-1554页。陈宠之子陈忠继承父志,进一步推动汉律朝轻缓化、体系化方向改革。②《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9页。河南吴氏律学始于吴雄。吴雄在顺帝时为廷尉。他的儿子訢、孙子恭也都出任过廷尉之职。吴氏一家三世廷尉,是当时响当当的法学名家。③《后汉书·郭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6页。
除上述律学世家子弟之外,活跃在东汉洛阳的律家还有杜林、马融、郑玄、许慎、应劭等人。
杜林和马融都是扶风茂陵人,来自西北。杜林早年投奔光武帝,在洛阳历任高官。太中大夫梁统主张重典治国,提出恢复肉刑。时任光禄勋的杜林对此动议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最终获得光武帝的支持。而马融则两次被拜为校书郎,到位于洛阳南宫的东观,④《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引《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5页。典校官藏书籍,包括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可知,马融律章句必定深受洛阳学术资源的滋养。
郑玄是北海高密人,来自东方。他年轻时曾赴洛阳太学求学,后入关中求教于马融。其律学先受自精通法律的廷尉陈球。后受自律章句大家马融,成为兼容实务、学理的通识之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郑氏律章句在兼采前贤的基础上又加创新,最终成为官方正式认可作为唯一权威的法律注释学说,成为汉代律学百家争鸣局面的终结者。⑤《晋书·刑法志》:“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见《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3页。
许慎生于汝南召陵,应劭是汝南南顿人,他们都来自南方。许慎后入洛阳拜师于经学家贾逵,并在洛阳完成《说文解字》的初稿。他利用《说文解字》研究汉代法律,“以汉律解字”⑥程树德:《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是东汉以经学训诂方法注律的一块丰碑”⑦龙大轩:《汉代律家与律章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6页。。应劭于献帝建安元年(196)上奏删定律令、点评古今而得的《汉议》《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春秋断狱》等律学著作。⑧《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0-921页。当时,洛阳经过董卓之乱,已经破败不堪,汉献帝及东汉中央机构迁至许昌。应劭的这些律学著作,是以洛阳所存东汉律令文书档案作为底本的劫余之作,堪称对东汉洛阳法学的终章总结。
(二)魏晋洛阳名理法学
汉末魏晋时期,中国学术思潮剧烈变革,而尤以洛阳为学术新风尚的策源地。⑨王国维说:“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4《汉魏博士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1页。汤用彤亦曰:“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76页。作为东汉二百年政治中心、文化圣地,洛阳成为天下学人精英荟萃、思想碰撞的文化高地。来自不同区域、秉承不同文化风格的学人、学派与学说,在交锋碰撞中迸发出惊艳的火花,产生新的学术思潮。尤其是,王弼、何晏等人在洛阳倡导的玄学清谈之风,对各种学问的研究思维、视角、技巧都产生了根本性的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魏晋名理法学勃然兴起,为魏晋时期全新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实用的思维工具,做足充分的理论准备。
魏晋名理法学对汉代律章句之学的突破之处在于,它并不停留在注释律令的微观层面,而是进一步思考律令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问题,从篇章体例、逻辑构造、法典编纂,到立法技巧、法律形式界分、法律内容归类,再到法律主旨、立法意图、语言表达,但凡此类较为中观、抽象、规律性、方法性的法学命题都在其研讨范围之内。总而言之,由专注于注释法律转而思考创制法律、寻求其背后的学理依据,法学理论取得突破性发展,由“法外之理”变为“法内之理”①喻中对这一对概念加以界定,笔者采之以配拟古代法学,实亦可通。见喻中《从“法外之理”到“法内之理”——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博览群书》2004年第7期。,是为汉魏之际法学的重大变革。而这一切正是发端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国都洛阳,并由此地对外推广形成全国影响。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法学家,诸如刘卲、杜预、张斐、刘颂,其主要学术创作与实践活动也都集中在洛阳。
刘卲是曹魏律令改革的主要负责人。在魏明帝期间,身为陈留太守的刘卲被征召入洛,参与整理前代法律文本,编纂撰修律令法典。在洛阳,他不仅参与编修出《新律》《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等系统的法律文本,而且还撰著一篇《律序》,概要阐发《新律》的精神主旨、学理依据,表达出强烈的名理化倾向,是魏晋名理法学的第一次全面展示。在《律序》篇末,刘卲得意宣称:“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②《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5页。这种自信正源于名理法学在思维工具、理论视角方面对律章句之学的超越。
杜预和张斐是西晋初年的著名律家、名理法学的时代闯将。杜预祖籍京兆,但他在魏晋时曾在洛阳为官,晋初时更担任守河南尹。张斐在洛阳主要担任的是中央司法机关廷尉下属的明法掾。西晋制定律令法典体系,既有高官主持评议,也有小吏辅助秉笔,因此杜预、张斐曾在洛阳共同参与这一重大的立法活动。律令颁布以后,他们又曾分别著有《律序》③《隋书·经籍志二》:“《汉晋律序注》一卷,晋僮长张斐撰。”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72页。“杜预律序云:律者八正罪名,令八序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也。”见《北堂书钞》卷45《刑法部下》,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128页。,力图对律典的主旨大义进行学理阐释,揭示其内在的法理逻辑。后世将他们二位对泰始律的注释成果合称为“张杜律”,影响极大。④《南齐书·孔稚珪传》:“江左相承用晋世张杜律二十卷。”见《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35页。南梁任昉《为王金紫谢齐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启》一文。而该《律序》究为张、杜谁家,则不得而知。见《艺文类聚》卷54《刑法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79页。尽管他们的具体法律主张有较大差异,一个提倡文约例直,一个主张穷究法理,然而总体来说,张、杜律学都是受到中原尤其是洛阳一带玄学新风影响的产物。⑤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0页。
刘颂亦为西晋的知名律家。他早年为司马昭征辟进入洛阳,在西晋朝廷中历任廷尉、三公尚书等高级法律官员。他曾“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⑥《晋书·刘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8页。,尤其是提出“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的法理构想。这种罪刑法定与非法定和合的理论最终在唐律及以后的法律中得到体现,成为中华法系罪刑关系原则的经典范式。⑦参见俞荣根《罪刑法定与非法定的和合——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中西法律传统》第3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三)北宋洛阳的哲理法学
理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登峰造极的产物、中国文化最有哲学意味的高度抽象与宏大具现。作为唐末五代以来以儒为本、融合儒释道三教精华的全新理论体系,理学话语蕴含着丰富的法哲学旨趣。按照《宋史·道学传》的说法,宋代理学主流可以分为濂、洛、关、闽四派,分别以周、程、张、朱为领军人物。其中,程颢、程颐兄弟籍贯在洛阳,中年之后又长期在洛阳生活,讲学问道,终于创立洛学,位居宋代理学正统。
唐末战乱之后,洛阳再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返。但到北宋时,洛阳虽然不再负有政治中心的职能,却仍是官方认定的西京陪都,承担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由于其地近都城开封,同时政治氛围又较为宽和平静,因而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交流中心。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邵雍等文化名人都在此居住。二程与他们进行学术交流,同时收徒讲学,著书立说。
在宋明理学中,“天理”的最高地位是二程确立的,是他们“自家体贴出来”①《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传闻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二程秉持理学“天即是理”“理一分殊”的基本主张,在讨论法律问题时强调“天理”的支配作用。“天理作为宇宙的最高实体和道德规范的源泉,自然也是封建社会礼与法的本原,维护等级特权的封建法律制度归根结底是天理的体现。”②陈金全:《理学法律思想评析》,《现代法学》1994年第6期。例如,他们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时与?”③《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二先生语二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将刑罚与法律说成是纯粹天理的产物,是天理之当然,这正是北宋理学法哲学家旗帜最为鲜明的立场。
在二程看来,司法的根据是立法,而立法的根据就是天理。如果立法可以不遵守天理的纲常原则,那么司法也就可以跳出具体法条程序,那么法律的效力与权威也就荡然无存了。④《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论政篇》中记载了张载和程颐的一段对话:有少监逮系于越狱。子曰:“卿监以上无逮系,为其近于君也。君有一时之命,有司必执常法,而不敢从焉。君无是命,而有司请加之桎梏,下则叛法,上则无君,非之大也。”子厚曰:“狱情不得,则如之何?”子曰:“宁狱情之不得,而朝廷之大义不可亏。”见《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4页。因此立法必须遵循天理,立法的效力应该受制于天理。正如程颐所说:“盖先王之制也,八议设而后重轻得其宜,义岂有屈乎?法主于义,义当而谓之屈法,不知法也。”⑤《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论汉文杀薄昭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4页。
程氏兄弟也曾进入京师开封,将其洛学主张也一并带入开封的政治当局,并在这里遭遇正值变法高潮时期的王安石。尽管在总体上,二程都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反对王氏的激进变法主张。但是,他们的主张仍然是基于自身独立的理性判断,而非政治派系之间的意气之争。尤其是程颐,他的态度和立场尤其显示出学者的理性、客观与冷静。他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表示反对。他不主张激进变法,而是主张渐变。即便是在司马光主政时废除变法主张的阶段,程颐仍在疾声呼吁保留变法中的合理内容,对完全翻盘的做法并不认同。
二程的学说不仅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在后世朱熹的推动下最终确立理学正宗的地位,受到官方的认可与推崇。程朱理学的法哲学主张,既是对以往中国法文化的总结,也是对中华法文化的再塑造。尤其是其“天理”说,更对后来历朝的法律实践活动带来深远影响。例如,河南省内乡县衙内至今仍可以看到当年悬挂的“天理、国法、人情”匾额。这匾额既是在揭示中国法文化的隽永内涵,也是在表彰以北宋二程洛学为代表的洛阳法哲学曾有的辉煌。
三、古代洛阳与中华司法
(一)都城司法体制的体系化构建首次完成于东汉洛阳
都城作为政治中心,自古至今都是朝廷法度最先推行而且贯彻最为彻底、实施最为规范的区域,也是全国范围内司法机制最为繁复、司法局面最为复杂的区域。因为都城既是君主和中央官僚机构的驻地,同时又是一级地方区划,导致其司法处于中央与地方两套机制的双重覆盖之下。两相交织,往往会造成都城司法体制的复杂混乱乃至叠床架屋,彼此干扰。例如,西汉时都城长安,既有作为地方监狱的长安狱,也有包括廷尉狱在内的中央列卿机构所属本部监狱即“中都官狱”,总计有26 个之多。①《后汉书·百官志二》“廷尉”条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世祖中兴皆省,唯廷尉及洛阳有诏狱。”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82页。同时,西汉在京师之外又设魏郡诏狱、钜鹿诏狱、洛阳诏狱。令出多门的刑狱体制,造成司法体制的系统性混乱。②在中国古代,“狱”是侦查、司法机关为羁押未决犯而设置的机构,不同于今日羁押判决自由刑罪犯的执行机关“监狱”。参见王忠灿《中国法律史叙事中的“监狱”》,《中西法律传统》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至东汉时,伴随着都城东移至洛阳,都城司法体制亦逐渐趋于体系化与合理化。
首先,捋顺了洛阳中央司法体制与地方司法体制的关系。洛阳狱设置在洛阳县官署即洛阳寺之内,由司隶校尉、河南尹与洛阳令逐级共同管辖。司隶校尉拥有京师洛阳及周围七郡的治安、监察、司法权。河南郡即为七郡之一。洛阳城则位于河南郡辖区之内。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分别行使京师洛阳的三级司法权。与之相对应的,廷尉只统属廷尉狱,其管辖地域可以广及全国。而作为更高司法权力行使者,皇帝、三公、御史中丞则可以广泛参与到廷尉狱和洛阳狱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之中。
其次,位居京师各种监狱被大幅裁减,只留下廷尉狱和洛阳狱两个监狱。尽管东汉中期以后,又出现黄门北寺狱、若卢狱、掖庭狱等,但较之西汉仍可称清简。而洛阳狱既是地方监狱,又是诏狱,关押特殊身份的罪犯与待审之人,凸显出其作为京师所在地监狱的独特司法职能。③宋杰:“洛阳狱规模巨大,机构庞杂,兼有中央政府‘诏狱’和地方郡县监狱的职能,囚禁的对象包括各级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对京师安全和朝廷政局影响甚重。”见宋杰《东汉的洛阳狱》,《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而且廷尉狱和洛阳狱又彼此分工。例如,廷尉府官员犯法,只能被关押于洛阳狱,以避嫌疑。④例如,廷尉赵世因为不敬被举奏,便被关押在洛阳狱,由河南尹审理。事见《后汉书·百官志二》李贤注引蔡质《汉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83页。由于洛阳居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优势,使得京师以外的诏狱失去存在价值,如同西汉魏郡那样的诏狱便被废止。因而形成诏狱仅止于京师、州郡县只有地方监狱的格局。司法监狱系统自下而上逐级负责,不再掺入其他权力机制。
东汉时期确立的都城司法体制模式被后世王朝大体沿袭。在以洛阳为都城的曹魏、西晋、北魏、武周时期,洛阳仍然保持着其兼具都城功能和地方机构功能的司法运行体制。洛阳地方的官员如洛阳令、河南尹等常能参与审理中央大案,与廷尉、御史大夫及诸狱官并称,受到特殊重视。当然,洛阳京畿官员体制也随着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而有一些变化。例如,西晋时取消司隶校尉,改为司州,而将其监察功能转移到河南尹。北魏初建时改司州为洛州,迁都洛阳后又改为司州。隋唐时期的大多数时候,洛阳都是作为陪都存在,其政治影响力自然逊色于长安。反映在司法体制方面,河南尹和洛阳令都不再具有多少特殊性。但是,在武则天在位的武周时代,洛阳升格为神都,恢复名副其实的京畿地位,因而当时朝廷的最高司法机构如大理寺、刑部(当时称为秋官)又都移到了洛阳。河南尹和洛阳令再度短暂成为重要的京畿司法官。宋代以后,洛阳政治中心的地位迅速下降,不再享有京畿地位的洛阳最终沦落为一个相对较为普通的地方行政区划,承担一般的地方司法职能。其司法机制也就不再有什么特殊的了。
作为京畿司法体制的贯彻执行群体,自汉至唐的历代洛阳令、河南尹中,也涌现出许多为政强直、不避豪贵、精通法律的地方司法官员,塑造出许多典范司法和执法官员的形象。例如,东汉洛阳令董宣因不畏惧权贵而被誉为“强项令”。其后,虞延、周纡、祝良相继出任洛阳令,同样由于严格执法而威震京师。①董宣、虞延、周纡事迹,见《后汉书·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87-2496 页。祝良事迹见《后汉书·庞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1页。以及《太平御览》卷500引《东观汉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86页。东汉末年,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严察权贵的事迹,更是让他借此一战成名。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页。曹魏时期,司马芝担任河南尹,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皇亲国戚也不得通融;③《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86-387页。河南尹李胜参与讨论恢复肉刑问题。西晋初年,担任河南尹的则是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家杜预。杜预不仅参与晋初律令法典的编纂工作,而且精通律学,勤于著述。他为《泰始律》撰写的注释被皇帝下诏与律并行,获得了正式的法律效力。北魏时,洛阳令高绰、元志、高崇、薛琡等人,也都因为政清断、不避强御而青史留名。④事迹先后见于《魏书·高允传附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91页。《北史·魏诸宗室·河间公齐传附元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58页。《魏书·高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7页。《北史·薛彪子传附薛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2页。到唐代,武周时代的洛阳令魏元忠同样是刚正不阿的一代名臣。
(二)洛阳树立天下司法文化的标杆
洛阳司法系统在运行中形成一系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司法文化,分别表现为法律职业自我认同、法律职业专业化、司法仁德化。
首先,司法人员供奉皋陶为职业神,强化自我职业认同,自东汉洛阳始。
宋人曰:“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祠之。盖自汉已然。”⑤(宋)方勺:《泊宅编》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东汉时担任汝南功曹的范滂因受人诬告参与士人结党。他刚被收押到黄门北寺狱时,就被狱吏告知要祭拜皋陶。⑥《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05页。这说明东汉洛阳监狱中已有专供祭祀皋陶之所,即狱神庙。皋陶已被请上狱神的神位,接受后世人的供奉。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人对皋陶十分尊崇,对其法官权威的十分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谶纬造神运动的风气影响。此外,又据《论衡·是应》记载,当时官府都有皋陶、觟䚦形象的壁画,以狱神皋陶执神兽断狱的神迹警示奸人。
皋陶自汉代始成为狱神,祭祀活动一直未断。至西晋时,皋陶祭祀进一步上升为国家礼法,于每年孟秋在洛阳铜驼街旁的廷尉寺举行。狱吏视皋陶为司法行业鼻祖。而在北朝,人们认为壬辰日是皋陶的忌日,司法机关在这一天有不审讯犯人的惯例或者规定,以此来作为对狱神皋陶的纪念。这说明,狱神皋陶的形象已经从中原洛阳扩展到地方边郡。①《敦煌文书》:“皋陶以壬辰日死,不得此日劾罪人。”参见李德范《敦煌西域文献旧照片合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狱神皋陶的形象一旦确定下来,就在中国法律史上扎根生长,狱神庙在天下州县监狱遍地开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其法文化意义深远复杂。从中国传统法律职业尤其是司法职业的角度来说,皋陶祭祀是其从业人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集中体现,也反映出某种民间法律信仰,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历史价值。②邓长春:《狱神皋陶崇拜考论》,《中华法系》第12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而推根其源,狱神皋陶文化最早起于东汉洛阳。
其次,官方推动的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专业化运动,自曹魏洛阳始。
法律专业素养的培养、专业知识的传播,是法律得以良好执行、司法得以良好运转的先决条件。有鉴于此,法律职业专业化运动便具有非凡的意义,而为国家所逐渐重视。秦汉时代,律令知识传播主要靠私人传授与家族传承,马融、郑玄之学属于前者,陈、郭世家属于后者。至曹魏时,社会风气转变,法律之学渐而失去往日风光,而为社会所轻贱。有鉴于此,有识之士便上书朝廷,扭转这种反常的事态。
曹魏尚书卫觊上书魏明帝说:“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③《三国志·魏书·卫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11页。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曹魏王朝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律博士的官职,隶属于最高司法机关廷尉,主要负责向相关官员传授法律知识。此举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曾对此给出高度评价。他认为,自从曹魏始创之后,律博士不仅对律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对于历代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改革完善影响十分巨大。④(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59-2060页。而律博士的最早设置,是在曹魏中期的都城洛阳。
西晋时期继承曹魏的制度,在廷尉设置律博士。其传统经由东晋一直延续到南朝,但都只在廷尉下设置一人。南朝梁陈时期则在国学下增设胄子律博士一人。在东晋南朝推崇清流、不屑浊吏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廷尉律博士被认为是刀笔小吏而为世议所轻。⑤《南齐书·孔稚珪传》:“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见《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37页。而在北朝,由于胡族政权积极学习汉魏法律制度的意愿十分强烈,所以律博士作为掌握实用专业知识的职位,也就为北方各政权统治者所重视。北魏洛阳时期,廷尉下仍设置律博士官,其职能不仅局限于传授法律知识,进行法律教育,而且还广泛参与国家议律的立法活动和重大疑难案件的司法活动之中。在推动北魏法制走向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所提到的常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再次,司法仁德化传统绵延于周、汉、魏、晋之洛阳。
司法仁德化在中华法系形成发展史中绵延久远,始终是中华法系颇具特色的优秀传统之一。而这一传统尤其在洛阳展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
西周初年,周公在成周洛邑提出“明德慎罚”的法律原则,主张刑法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周穆王也在这里改革刑制,颁布《吕刑》,提出“敬德于刑,以刑教德”“明于刑之中”“有德惟刑”“惟良折狱”“哀敬折狱”等一系列司法原则,成为后世长期推崇、效法的经典法哲学宗旨。①《尚书·吕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2页、第313页。
东汉时,正式出现皇帝亲自参与“录囚”的司法案件复核活动。录囚制度始自西汉,是改善狱政、监督司法的重要手段。然而当时录囚主要是由刺史在地方郡县进行。而到了东汉,明帝亲临洛阳狱查核案情,释放无辜者千余人。②《后汉书·寒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17页。可见,皇帝录囚的事例自东汉洛阳狱始。这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司法均起到正面的示范效应。
曹魏末年,毌丘俭谋反。其孙女毌丘芝尽管已经出嫁,且已身怀有孕,但按律亦当抄斩。这个大案波及广泛,很快就在京师洛阳的朝堂之上引起热烈讨论。主簿程咸上书指出,出嫁之女被本家族连累的规定,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应该进行改革,应该本着“哀矜女弱”的精神,规定“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③《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6页。,建议被官方采纳。这成为魏晋时期以个案推动律法改革、贯彻司法仁德化精神的典型事例。可见,妇女不再受族诛连累的法律规定,最早创立于魏晋之际的洛阳。
此外,在多民族法制融合的大时代背景下,洛阳同样充当着中华司法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舞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儒家法文化不仅在立法层面日益彰显,而且还渗透到司法领域,形成春秋决狱的潮流。例如,费羊皮卖女葬母因孝诚可嘉而得以免刑,儒家倡导的孝道纲常、宗法伦理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持。④《魏书·刑罚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80-2882页。同时也在洛阳发生过反向的案例。尤其是当父系宗法遇到鲜卑皇权的时候,对立就显得尤为突出。发生在洛阳的“殴主伤胎案”中,强调皇权权威的政治意见和强调儒家父系伦理的司法意见,形成尖锐的对立。⑤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洛阳这个皇权法与儒家法、鲜卑部族法与中原礼法的中心角力场,从一个历史侧面折射出掺杂着民族融合因素的中古法律儒家化过程的曲折与反复。
四、古代洛阳与中华法系的空间结构
一如前文所述,在中华法系的纵向演进过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思想和文化,都曾在洛阳发生过节点性事件。另一方面,洛阳对于中华法系空间结构的意义同样十分重大。中华法系既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也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既是精神文化概念,也是物质实体概念。它浓缩着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历史理想与民族精神,支撑起中华法文化的治理规模与空间格局。在中华法系地理空间不断充实和扩展的过程中,洛阳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古代洛阳对中国法律空间整合的意义
中华法系的源头是中国法律。最初的中国法律酝酿于一些早期文明据点。它们基于各自的文明环境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渊源和表现形态。伴随着文明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上层的远距离交流”①李新伟:《“最初的中国”:考古学证据和推想》,《读书》2016年第7期。逐渐培育出具有某种共通性的法律文化及其空间范围。又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由于政治融合、文化交流等历史大背景的展开,各地的法律传统通过多重线路在一个中心区域进行碰撞、交融,初步塑造出一些共通的法律规则,具有较强法律涵摄和辐射能力的核心区域逐步成型。这个最早的核心区域就是以上古洛阳盆地、河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这里熔炉锻造出来的法律规则再通过征服、渗透等方式,由核心区域反馈到周边的据点并进行法律空间的深度拓殖。在这个过程中,以“禹迹”“九州”为理想范围的中国法律空间逐渐由观念落到实践。
洛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多重文化碰撞交融的区位优势,当地考古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商城遗址都是“文化杂交”的硕果。②考古发掘显示,在中国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洛阳地区由于多重过渡性的地理特征而成为多种文化交融的优质平台。参见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1-62页。西周初年,地处洛阳盆地的洛邑城拔地而起,成为新时代中国法律创新最主要的政治文化平台和“普天之下”法律空间最核心的制度引领区域。传世文献记载,周公的制礼活动伴随着洛邑城的整个营造过程。③《礼记·明堂位》载:“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中庸》又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正义》,见《礼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4页、第740页、第1454页。虽然这些记载难免有些理想化的想象,④依照传世文献所载,周公“制礼作乐”为周室确立下一套庞大的礼法制度。然而此说近几百年来亦逐渐遭到学者质疑。例如,清代崔述认为“周公制礼”即便存在,也一定较为粗疏。见崔述《崔东壁遗书》卷5《考信录·丰镐考信录》。顾颉刚也认为“周公制礼”的内容与意义不宜过分夸大。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近年又有美国学者罗泰提出,周的礼法变革主要发生在西周晚期而非周初,“周公制礼”很可能并不存在。见罗泰著,吴长青、张莉、彭鹏等译《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引论”与第一章。总之,周初制作礼法的活动是否如文献记载那样集中、系统、完满仍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这并不能改变洛邑周代礼法的宗源性地位。因为西周礼法是在遥宗周原、监于夏商、吸纳周边各部族法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复合型规范体系。这个过程或许是缓慢复杂的,地点或许是分散多元的,参与者肯定也不止周公一人,但是洛邑凭借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而作为周人控御天下的基地,理所当然成为统合多重礼制传统、聚合各地习惯法最主要的历史舞台。周天下法秩序最重要的制度基石——“宗法制和分封制”中体现着周人的法律渊源和智慧,但在周公东征平叛之后进行的第二次诸侯分封才是化解殷民危机、奠定周室天下格局最关键的一步。⑤《左传·定公四年》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32页。相比于武王的分封,周公的分封规模更大,地理空间布局的战略进取意义更强。而营建洛邑正是周代分封到各地的诸侯,把周公以后确定下来的宗法分封制度积极进行实践操作,把在中原逐渐形成的混溶的礼法程序原则带到各地的政治据点,与当地土著的地方法俗和谐并行,缓慢交融。⑥王沛:《刑书与道术——大变局下的早期中国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3-45页。经过数百年的缓慢整合,春秋时的诸侯列国不仅实际控制区域大幅拓展,而且在上层贵族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礼法为主体的天下法律体系,从而奠定下中国法律具有丰富内涵要素、广泛地域影响的空间范围。尽管当时已经出现诸侯霸主,也有礼坏乐崩的评价,但是作为天下共主所居的洛邑,仍旧是这个法律空间范围在名义(亦即法律)上的中心。而且,由于周天子渐成虚位,洛邑的天下地位甚至出现了超越有形政治中心实体、脱凡而化为礼法圣城的态势。
经过战国、秦汉持续的法律空间整合运动,原本散布在各地的法律据点日益增多、扩大,据点间的连线日益增密、加宽,中原法律在更广大的汉人区域内施加更细密的影响,把更多的“山高皇帝远”的法律缝隙覆盖填满,吸纳包容进入一个以中原汉人政权为总号令、以农耕宗法伦理文化为总背景的法律统治空间之内。这个广大的区域主要包括今天中国的中部、东部、南部和中国西北地区,其核心区则先在关中,后转河洛。魏晋南北朝虽然进入大分裂的历史周期,但是当时中原法律的适用范围仍旧不减于此前的规模,并且在南方的深山密林实现更进一步的法律覆盖。在此期间,洛阳不仅始终洋溢着法制创新的活力,引领着中国法律的发展方向,而且更进一步升级为华夏法制正统的地理标志。总体而言,在1—6世纪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长期都是中国法律空间最核心的区域。①鲁西奇认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作为国家发展重心、借以掌控全局的核心区。这个核心区应该同时满足兵甲所出之区、财赋所聚之都、人才所萃之地、正统所寄之望等四项标准。这个核心区,秦汉时是关中和三河,北朝隋唐时是关陇、河东、河洛,六朝、南唐、南宋时是宁镇、江淮,中晚唐、五代、北宋时是汴洛、河北,辽、金、元时是草原、燕地,明清时是南北直隶和畿辅。参见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3-229 页。从中不难看出,洛阳所在区域在中国古代史长期都处于核心区域之中。这还不算两周乃至更早的二里头时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中国核心区的地位而担当中国法律核心区的职能,洛阳当之无愧。
作为中国法律的核心区域,洛阳担当着法制创设、法学引领、司法统合的独特历史职能。这主要表现在:通行全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颁行于洛阳,代表历史方向的法学新潮流兴起于洛阳,以实践贯彻法律精神、协调法律准绳的司法体制发端于洛阳。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文化差异性、多样性显著,整齐划一的法律从来不曾真正掌控整个国家。出发于法律核心区的法律制度、思想与实践,在进入“外在的边陲”和“内在的边陲”等所谓化外之地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打折扣的现象。②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见许倬云《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因此,洛阳在中国法律空间结构中的核心区作用,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强大。③事实上,自上古三代以来直到今天,中国法律空间的对内充实和对外扩展一直都是渐进的过程、历史的趋势,而始终没有走到终点。所谓法律核心区的对外辐射功能,也如强弩一样终究会有不能穿鲁缟的末途。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体属性所决定的。例如,西晋泰始四年(268)颁行于洛阳的律令法典体系在律令发展史上成就突出。但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全国统一标准的一刀切,而是兼顾多种区域治理模式的差别。当时主要规定民户租调制度的《户调式》,在课田与否、户调征收数额标准方面,分郡、国、夷三类,一般郡、边郡、边郡之远者、诸侯封地、夷人、夷人之远者、夷人之极远者七个等级,依据朝廷对民户所在区域掌控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变通,做出了不同的具体规定。④《晋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0页。
另一方面,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法律与四面八方部族习惯法的交融碰撞同样不曾间断,并且伴随着汉人与胡人之间政治、文化上互为主客的融合过程而日益活跃起来。在公元6世纪前后,中国第一次民族法制碰撞融合高峰期的中心舞台,仍旧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周边部族习惯法的许多因素以各种方式加入中原法律之中,中原法律也有变通地适用于周边部族生活的区域。公元10世纪以后,这一过程进一步升级,最终形成兼容西北游牧法律和东南农耕法律于一体的宏大国家框架和法律空间。中国法律的地理空间空前扩大,其核心区域也由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向东向北移到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二)古代洛阳对域外法律空间的辐射效应
中华法系是一个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法律文明现象,除中国之外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法律。凭借其由内到外的独特文明气质而能够超越国家和民族,在古代亚洲东部的广大区域内形成具有广泛法律效力、良好治理效果的规则系统,并与世界其他区域的规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公元4世纪开始,日渐成熟的中国法律的域外影响力逐渐凸显,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琉球群岛等许多国家,先后出现学习中国法律的浪潮。中华法系的空间格局逐渐成形。①详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法律在完成内部充实、自我整合之后,向后世空域广大的中华法系地理空间投射出的第一道法律之光,正是来自于西晋洛阳。以晋、唐律为蓝本的成文法典是中华法系的重大特征之一。②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11-314页。中华法系在地理空间上的初步成型就在4—6世纪之间。当时沟通各国法律最重要的纽带就是诞生于西晋洛阳的泰始律令法典文本。泰始律令法典体系,以其术语精准、体例严谨、逻辑周密、结构协调等优点,带动东北亚各国形成颁行律令法典的潮流。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和新罗,先后仿效西晋和南梁颁行律令法典,成为中国法律最早的域外追随者。《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三年(373)颁行律令。当时中国北方正处于十六国时期。前燕(346—370)、前秦(350—394)已先后参照西晋制定律令法宪,形成较为齐备的法律制度。高句丽制定律令显然是通过它们而受西晋影响的结果。③高明士:“就其时代而言,当仿自西晋泰始律令。”见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其后,新罗法兴王七年(520)春正月,亦颁示律令。④(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4《新罗本纪·法兴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7页。以当时朝鲜半岛诸国普遍尊奉南朝汉人政权为正统并行遣使朝贡的情况推之,⑤《梁书·诸夷传·东夷》:“普通元年,诏(高句丽)安纂袭封爵,持节、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宁东将军。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贡献,诏以延袭爵……太清二年,延卒,诏以其子袭延爵位……(普通二年)高祖诏曰:……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五年,隆死,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普通二年,(新罗)王募名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见《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03-804页。其律令法制极有可能系由模仿南梁天监律令法典体系(503)而来。而南梁法律则又大体沿袭西晋。可见,诞生于洛阳的西晋律令法典体系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朝鲜半岛,对东北亚法律形成重要影响。
而在更晚的后世,最初酝酿萌发于西周洛邑的礼法传统,则通过唐宋、明清法制的传承与发扬而流播域外,对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国家完成更深层次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精神的洗礼。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借由颁布《政戒》《诚百寮书》强调礼法大义,训示上下名分,构建以礼法为核心的法统秩序。高丽朝第六代王成宗以周、孔自期,效法中国构建系统化的儒礼祀典,建立起社稷、宗庙、五服等一系列重要的礼法制度,史称“成宗制礼”。在中南半岛,安南自宋以后脱华自立,然而仍是中国藩属,沿用中国官制,遵行中国礼法,礼仪章服,律令法制,未改中国礼法文化的底色。明清时期的琉球国法制,也是以中国法律作为母法,不仅移植律例,而且尊奉礼法。其人伦纲常、典章制度都和中国颇为相似。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法之所以成为古代日本、朝鲜、越南及琉球等东亚国家法律的母法,之所以一度支配东方亚细亚,不仅因为它本身具有的法律共同性的一般规律、原理、原则的实践与理论根据,而且在于中华法系包含了许多跨越时空、历史常新的价值和合理性因素。”①李青:《中华法系为何成为东亚各国的母法》,载张中秋主编《中华法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种以礼法传统为主的核心价值要素,正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国中原地区贡献给世界最可宝贵的法律文明成果。
而以洛阳城礼法地位与内涵的独特魅力而言,其对域外国家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以日本为例。早在东汉初期,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就曾遣使来洛阳,被光武帝洛阳南宫召见,并赐以“汉委奴国王”金印。此后来自日本的使节多次入洛,历经曹魏、西晋、隋唐。8世纪的日本平城京亦兼采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而在后来的平安京城市布局中,唐洛阳城的影响更超越长安城。②王仲殊:《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考古》2000年第7期。尤其是平安京(今日本京都)以朱雀大路为中轴线,分为左京洛阳和右京长安,而后右京地萧条,左京繁荣,以致“洛阳”二字遂成为平安京全体的代名词。③[日]村井康彦:《洛阳和长安》,《日本的宫都》,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第159-163页。当时日本名义上君主天皇留居平安京,但已失去实权。平安京又被称为“京洛”“洛都”“洛中”,各地赴京都则称“上洛”或“人洛”。其形势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东周时代。除日本以外,东南亚诸国也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遣使来华。他们在洛阳接受皇帝召见,并被赐以带有汉官体制意味的封爵和印绶。④许永璋:《东汉时期东南亚国家使者访洛阳》,《中州古今》1995年第2期。当时诸国虽然还未主动学习中国法律,但却在开始逐渐向中华制度靠拢,为日后加入中华法系进行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