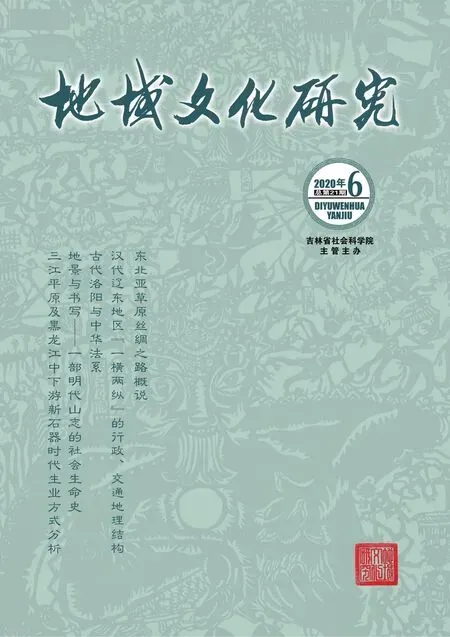辞赋视野下饮食书写的南方地域性
刘俞廷
今天的中华饮食分为八大菜系,根据不同地域和饮食形态,饮食也划分为多个文化圈。而饮食的地域差异,从人类文明的一开始便存在。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关于南北饮食的差异,从屈原的楚辞和记录中原地区重要饮食的《礼记》以及后来的《齐民要术》等书中均可发现南北饮食的明显差异。通过历代辞赋中关于饮食的书写便会发现,对饮食的文学书写、诗意化等都主要集中在南方饮食上。
需要明确的是,“南方”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相对“北方”而言。但由于中国的文化发展主要是从西北向东南发展,历经几次重大南迁,南方才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今天南北的地理分界是以秦岭淮河为界限,在历史上,也主要以天险长江作为分界线,南北饮食差异也与这条地理线相关。南北饮食差异简要从饮食系统可以概括为南方饭稻羹鱼,北方食粟餐肉。这也体现了水稻和小麦的种植范围。北方的代表性饮食是面食,南方饮食相较更丰富,水稻为主,多有水产、水果等。不过更南边的岭南地区,在唐代时,仍属于大多数文人想象中的神秘之地,较为普遍的认知是,岭南地区文化落后,布满瘴气,盛产水果,饮食怪异。虽然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岭南地区逐渐失去了神秘的面纱,但对南越地区的饮食文化,更多是好奇的观察。所以南方的具体范畴大约为:长江以南、五岭以北。这个范围内的东西向又以东边为主,这与历史上几次重要南迁所在的位置有关。总体而言,所谓南方,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从文化影响上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差异性,如罗宗强先生所言“战国时期曾鲜明地表现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特色。汉代这种不同的特色得到了融合,地域色彩进入汉文化中。永嘉南渡之后,政权的南北割据为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发展提供了条件,地域的色彩又从统一的文化进程中分离出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①罗宗强:《因缘居存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6页。。南方文化的高速发展与人口大量南迁有直接关系,在三次人口南下的大潮中,晋室南迁和南宋建立的文化影响力超过“安史之乱”的人口迁移,因为在晋和宋,政治中心带动文化中心全面迁徙,而唐代的文化中心虽历经浩劫,但终究得以保持在北方并最终重建。但依靠东晋南朝和宋代的文学书写,饮食文化所具有的南方地域性已经彰明较著。
一、东晋南朝辞赋中的尚雅饮食
南方地域的物产和风俗习尚的书写,一方面是北方中央政权对各地域情况的梳理和了解,而更重要的一方面,仍然是由南方人来书写南方。根据历史往南渐渐迁移的历史,生长于南方的文人渐多,对南方的书写也愈加丰富。
东晋的饮食书写群体依然是北方南下的权贵阶层及其后代,权贵生活在北方时期多是遵循礼制的“钟鸣鼎食”描写,西晋时期尚奢崇酒的迷狂状态除了嗜酒与酒肉书写之外,并没有过多的展露在文学书写中,辞赋中仍不缺乏雍容徐徐的富贵之气,但新士风的追求将生活的审美化也纳入了日常,饮食又是题中之意,从现实到思想本身是形而上的尝试,而饮食书写由于是最基于日常生活的项目,在文学书写上,反而是在思想浸染到生活各方面时,才会体现在饮食书写上。谈玄说理的玄学以及道家思想和逐渐壮大的佛教思想一步步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时人饮食中食材的选取便清晰地展露了这一点。所以在东晋南朝,权贵生活和南方地域可以提供的精致清新相联系,加之宗教中对欲望的克制使得当时的生活风尚一变而为对高雅的追求,在饮食书写中,被注重的不再是恢宏的场面和盛大的气势,或是权贵宴飨活动中酒肉满桌的场景,从魏晋时期,饮食从礼制转向日常之后,更注重的是符合个人情志和审美追求的饮食活动。而作为运用文字的优秀文人,通常都具有敏锐的情思和偏重感性的心理特质,虽然在铺采摛文的大赋创作中难以呈现,但在书写个人生活和情志时便会展露无遗,汉末抒情小赋便是如此。也是到了此时,地域的饮食文化塑造正式兴起。也是由于“衣冠南渡”,南北政权的分立才让南北分野意识趋于明确,南北饮食的区别也才成为关注点之一,如从南方迁到北方的王肃,从不食羊肉奶酪到最后被称作“酪奴”。
从辞赋书写来看,这一时期的文人不同于西晋的纵逸,对于饮食及其他欲望选择主动克制自我,转而向山水和自然投放心志,如谢灵运“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②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北魏的裴伯茂也会因多饮酒而自我批判:“伯茂末年剧饮不已,乃至伤性,多有愆失”③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90页。。所以对自我修养的有意识关注以及克制让酒肉满桌的描写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追求。生活于南方的文人陶醉山林清水之间,让南方的食材大量进入了书写中,这与食物和其他事物诸如音乐、美景等一起构成了文人高雅的生活景象,庾信的《春赋》仍是其中典型:
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吹箫弄玉之台,呜佩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入新丰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酸醅,鞭蓉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①庾信:《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6页。
随着对文学美感的追求,除了在遣词造句上的讲究,这一时期还有更深层次的追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总结道:“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37页。。“形文”追求的是由文字所书写形成的画面感要富有美感,在《春赋》中,颜色相当丰富,从青苔、小麦的青绿,石榴的红色,玉碗的青白色,杯子的金色,以及没有用颜色描写但富有色彩感的竹笋、杨梅,这些事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了颜色明媚的春景,也即刘勰所谓“五色杂而成黼黻”,同时明媚春景中也不尽富贵风流之气,新丰名酒,玉碗金杯,吹箫抚琴,庾信只稍作点染便将自然景致和士大夫的物质生活水准以及高雅的生活情趣展露无遗。而“声文”和“情文”在书写饮食中相对不那么突出和必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阶级的争论在较长时期里都是时代争论的重点内容,庶族与士族之间的争论让阶层的区分越辩越明,谱学也大为流行,所以此时进行的文学创作对于身份和阶层明晰度是有意识的追求,而留下的辞赋作品中,对饮食进行书写的基本是士族,因此东晋南朝饮食书写的贵气与高雅相辅相成,主要展现的便是士族作为精英阶层的饮食好尚和审美追求。除了像庾信这种书写十分典型的作品,通过其他食材也可得以一窥。这一时期书写较多的食材是水产、水果、蔬菜。水产类的书写与南方的地理位置相关,这一点无须多加讨论,至于水果书写,在汉赋中就多有出现,一般都以名贵品种作为书写对象,此时较多被关注的是:橘、梅、石榴、葡萄等,与此前乃至以后被关注的水果差异不大,总之多是贵族阶层食用的品类。较为引人注目的是蔬菜的书写,蔬菜在华夏民族的饮食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不同味道、色泽、生产季节、产量多寡决定了不同的蔬菜有不同的食用人群,与其他饮食一样,蔬菜之间的差异也展现了身份和阶层的差异。根据过往生活而造就的饮食相关的意象可知,藜藿、葵藿等蔬菜具有贫寒的意味,常用以指代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这在先秦以及西汉时期的辞赋书写中便已经定型。随着书写群体身份的改变,到宋代文学创作中心开始下移,之前都以精英阶层为主要创作对象,由于士族庶族之争,东晋南朝时期的饮食书写中,很少看到书写贫寒类生活的作品,从最明显的蔬菜差异来看,辞赋中几乎没有提及过上述三种植物,在诗歌中倒是偶有提及,除去“葵藿”因具有向阳不改的意味从而用以指代不变的衷心含义外,一般也是作为贫寒与富贵两种生活对立的姿态出现,如江淹《杂体诗三十首 其五 陈思王曹植赠友》“处富不忘贫,有道在葵藿。”③江淹著,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页。陆机《君子有所思行》“无以肉食资,取笑葵与藿。”④陆机著,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58页。相反,此时多写葵等作物的是陶渊明,“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⑤陶渊明:《陶渊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2页。,“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⑥陶渊明:《陶渊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页。,“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①陶渊明:《陶渊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5页。,将葵作为一种普通味美的蔬菜加以肯定本无可厚非,但时人对身份的看重让这类书写并不受欢迎,与束皙在《饼赋》等作品中极力书写多由贫寒人家食用的面饼如何美味、让人垂涎一样,难免被时人目为鄙俗。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书写的蔬菜为:“水草则萍藻蕰菼,雚蒲芹荪,蒹菰苹蘩,蕝荇菱莲。虽备物之偕美,独扶渠之华鲜。播绿叶之郁茂,含红敷之缤翻。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②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这些水草中,有很多便是水生蔬菜,当时世族的蔬菜种植按照曹植在《籍田赋》中的总结为:“大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辛者植乎蓼”③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70页。。所以谢灵运在山居中有这些蔬菜,有南方本身物产的关系,同时可能也是个人喜好,另一方面,谢灵运的蔬菜书写也和庾信笔下一样充满了画面感,只是相比庾信的色彩明媚,谢灵运笔下则主要是清新的绿意和红色的荷花。可见此时,辞赋中南方蔬菜所具有的清新画面尤为醒目,辞赋在这一点上的塑造相较诗歌更具优势,罗列的各项南方蔬菜所展现的清新幽雅与士族阶层所崇尚的精致互相契合。
除此以外,茶的饮用也显现了南北方的差异。最早关于茶的诗赋作品为西晋末杜育所做的《荈赋》,其中提及:“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④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61页。,也就是说,当时所饮的茶是初秋开始采摘的,这与春种秋收的其他作物并无差异,但陆羽与杜育相隔几百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⑤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61页。,表明当时已经以春茶为主。从杜育“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的记载来看,如果不是杜育亲眼所见,而是出于比况或听闻后的想象,那么当时所饮之茶可能来自西南地区,饮茶习俗受到巴蜀的影响,最早的饮茶记录也出现在辞赋作品《僮约》之中,这在魏晋时代其他诗歌中可以得到佐证,“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0页。。“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⑦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0页。。如果这两句是出于实写,那么杜育可能到过岷江一带,并看到了当地采茶的风貌(当然根据杜育生平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如若不然,则表明杜育生活的北方地区也种茶采茶,而“岷江清流”只是作为活水的指代而已。总体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魏晋时期,北方士阶层所饮的茶为秋茶,茶叶极可能来源于西南巴蜀地区,同时也可能在北方种植。
杜育于洛阳陷落时遇害。此后便是东晋南迁,到几百年后唐代陆羽总结茶文化,所以《茶经》体现了东晋南朝时期以及到唐的茶文化发展。《茶经》中说茶是“南方之嘉木也”。众所周知,后世名茶几乎都产自南方地区。《后魏录》:“琅琊王肃仕南朝,好茗饮莼羹。及还北地,又好羊肉酪浆,人或问之:茗何如酪?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⑧陆羽著,沈冬梅评注:《茶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0页。从王肃的事迹也可以看出,饮茶已经成为南朝的标志性饮食活动之一。生活于南方的文人士大夫将茶文化进一步发展,饮茶与文化和主观精神追求相结合,《荈赋》中茶道已初见雏形,茶在此时“清俭”意味已非常明晰。如陆羽所说“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①陆羽著,沈冬梅评注:《茶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4页。
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②陆羽著,沈冬梅评注:《茶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6页。
南方文化的发展,挖掘了南方的名茶。从陆羽记载的好茶产地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陆羽讨论的地区包括:山南、淮南、浙西、浙东、剑南,最后附加说明“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③陆羽著,沈冬梅评注:《茶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89-193页。也就是说,到唐代时,除了传统的西南产茶区,名茶主要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与对南方的开发是一致的。虽然南方多名茶以科学眼光来看待是土壤酸碱度、气候、雨量、光照等客观因素综合的结果,但在东晋南朝时期,是在开拓和开发南方的过程中,茶文化也得以士人精神追求相结合,从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茶与南方在此时相辅相成,共同营造了“清俭”的新形象,而这与东晋南朝时期士人的理想人格以及释道二教的追求都相为表里。从茶文化的发展来看,在茶书的著录上也体现出南北差异来,唐五代时期的茶书都是北方籍士人或者出仕东南时所写,而“到了宋元时期,茶书的作者群中再也没有北方籍作家了”④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序言。。在“饮”中具有重要文化意味的茶,除了气候生长的影响,在文学书写和文人的相关著述上也有明确的地域性。
所以东晋南朝时期,辞赋中的饮食除了有明显的南方地域特性,更重要的是将士人的理想人格和精神追求与南方的事物相融合。除了山水怡情之外,在饮食活动中,也显现出尚清新蔬果的特质。故此,水果、蔬菜的书写带有清雅宁静之气,而酒肉满桌的饮食与南方的清幽雅静相对立,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和格调,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文人士大夫剔除出诗文饮食书写,并影响到后世辞赋中的饮食书写。全新的南方成了士人新形象生长的土壤,而南方饮食的丰富与可选择性也反映了士族阶层为新的理想人格塑造所做出的努力。
二、宋代辞赋中的清简饮食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饮食书写不止于南方风物,对于南北饮食具有较清晰的划分,颂赞南方饮食的同时,还将北方饮食划归到粗陋的行列,且宋代的北方地区也是相对概念,真正更北方的辽金等地中的异族饮食形态在宋人看来更加粗陋。南方的饮食精细,欧阳修提及“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⑤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页。“于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⑥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诗文中呈现较多的是具有南方地域风味的果蔬与水产,以及作为主食的稻,如最受宋代文人青睐的饮食题材是蟹与笋。整个社会上层的好尚也是如此,京城中“贵人厌粱肉”,京城的人吃惯了美味佳肴,讲求“百物贵新鲜”。同时由于南方的经济发展和对南方饮食文化的认同,京城的南方人,因为“客居京城厌粗粝”,常常“买鱼斫脍邀朋徒”,表明了在时人心目中,食新鲜蔬菜和水产品,相较于北方饮食系统的吃法是一种更高级的饮食文明形态。即使是受欢迎的羊肉,“虽然,从笔记等相关记载中可看出羊肉在宋朝其实颇受欢迎,但其北馔的属性与历史记忆,却使它在宋人的书写中被贴上了虏馔肥膻的标签。正因如此,从前未分高下的羊酪与莼羹,在宋人笔下却代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生存状态。宋人经常偏重于后者,从中可见他们对理想人生的选择。”①曹逸梅:《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与士人心态》,《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水产鱼类和蔬笋成了时代共同趋向的“新鲜”,而“新鲜”作为形容词,在修饰的食物一般形容刚出产,没有变色、变味、变质,也没有经过腌制、干制等加工的食材,在宋人的诗文中用“新鲜”来形容的食材包括:缩鱼、瓜果、鳝鱼等等,所以也是针对果蔬和水产类南方式食材的书写,而羊肉等则与腥膻联系更紧密。“贵新鲜”既是对时令新鲜食材的喜爱,同时也是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尝试。《梦粱录》中记载了当时对新鲜的好尚,“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②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甚至“增价酬之,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③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如韩维《又赋京师初食车螯》中写道“京都贵人粱肉厌,远致异物无微纤”④韩维:《南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47页。,所以对于外地运来的水产“肯复重顾蛏与蚶”,欧阳修《初食鸡头有感》对于京城人争食芡实,“都城百物贵新鲜,厥价难酬与珠比。”⑤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王安石《后元丰行》感叹“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⑥王安石著,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页。所以在饮食上,不仅审美和精神追求是南方化的,连口味偏好也已经以南方为尚,素食果蔬与水产之类都更符合时代的追求。
如果说东晋南朝时期的南方相对而言仍是一个笼统的地理范畴,那么到了宋代,随着疆界意识的增强,宋人对于地域的关注度大为提高,对地方进行书写的作品变多,当然,仍然是对南方的进一步书写,其区域细致化甚至具体到县市。“随着理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发展,地方士绅阶层自觉恪守和发扬儒家人文化成天下的使命,崇尚耕读生活,注重地方治理”⑦刘培:《人文化成: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中地方意识的凸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辞赋中多有表现地方风俗的作品,南宋时期编撰地方志等地域文化活动也大为增多,古代方志体例的定型也完成于这一时期,以至于“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纪录焉”⑧赵与泌:《仙溪志》,见黄岩孙纂《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33页。。
此时以某一区域为名的赋作增多,赋中有明显的实录意识,相较于诗歌,赋作的题材特点可以进行大量实录,如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中所言,“余赋会稽,虽文采不足以拟相如之万一,然事皆实录”,《蓬莱阁赋》言因“越中自古号嘉山水”,而对没有被赋书写的蓬莱阁,作者便有意为文,同时长文抒情填补了“诗不足以尽意”的缺憾。《闽岭赋》《南都赋》《宁海县赋》《钱塘赋》等一系列的作品,以及孙因专门作了一组书写越地的作品:《鱼盐》《越醸》《越茶》等等,从地域上看,辞赋中的地域仍是集中在东南区域。这种写法在以往的大赋中也有,但是重点已然变化,如此时赋中的水产丰富,重点不是彰显帝国的德泽广布和实力雄厚,而是向下移到民众生活的安适富足以及该区域的物产丰富,作者对生长或生活之地洋溢着自豪感。辞赋中的饮食题材书写相较诗歌,写作对象更为具体,诗歌从数量上展现了文人选取题材的方向,辞赋中的饮食主题则更细致地体现出某一食材的特性以及其吸引文人的原因。北宋辞赋中的思归之作(思归南方)以及南宋辞赋都书写和记载了较为典型的南方特色,多以新鲜的素食类食物为主题,如梅尧臣的《思归赋》《针口鱼赋》,洪适《银条鱼赋》,苏轼《洞庭春色赋》《后杞菊赋》《服胡麻赋》,黄庭坚《苦笋赋》,范浚《蠏赋》,杨万里《糟蟹赋》《后蟹赋》,释居简《香鱼赋》等。此外宋代还有数量丰富的水果赋,但由于水果赋在历代都有大量写作,如在吴淑的《事类赋》中,水果在“果部”,茶酒等则在“饮食部”,故此处对水果书写不再单独作分析。从以上举例的赋作也可看出南方食材仍然集中在水产品和果蔬上,此处具体举褚国秀的《宁海县赋》为例,褚国秀本身为宁海县人,已有五世人居住于宁海县,所以“其山川里舍之所隶,人物土产之所钟,有亲见非剽闻,有念知非臆度也”,又因“前赋所未云及”,熟稔家乡的褚国秀担心宁海县会像孙兴公作的《天台赋》那样亡佚在历史中,最后宁海县“事或湮没而弗著,独一丹丘存旧名”,所以这本就是为保存当时的风物而以赋的形式作名录,以实录家乡以传后世为出发点,各类物产如蔬菜瓜果和水产都悉数罗列,其中蔬果粮食部分为:
姜畦富于松坛黄社,蔬圃利于后洋溪南,苔脯擅奇于古洞,茶笋毓瑞于宝岩……九顷莲芡得水泽之富,三洋椒漆宜土性之咸。……其卉则萱蕉葵蒲,艾蓼芦蒹,而洒然秀出者,惟荪珥兰簪。其果则李柰榴栗、桃杏梅枬,而磊然饤座者,惟香橙乳柑。其田谷则籼秫总总,而利获于海涂者相倍蓰;其陆种则麻菽穟穟,而岁收于山货者常二三。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水产部分为:
以至惟错之珍,所产者多,鲈脆鳘肥,螺珍䖴柱,蛎牡虾魁,望潮章巨;蟳含膏而团脐,䱥凝油而塞肚;鮻通黄而粲金相,魚孱柔白而悬银缕;新妇臂婉而凝脂,老妪帔长而曳组。旧总谓之鱻鲜,贱不论于分数。若夫涝涨而河豚生,汐退而弹涂聚;䖳沫浮鲗黑煦,鼇车攒蠔山竖。修带如篦,斑鹿赪虎。鳒目之比如瞪,妙觜之铦於锯。䱋梅之輭如束,鮨苗之多於黍。鲳枫叶之僄轻,鳢竹夹之癯露。加之麒鳗鲚鱽之党类,蚌蛤蛏䗯之俦侣。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还说“名不周知,品不殚举”,通过这些物产几乎可以看出当时这一区域的所有食材,这与其他辞赋以及前文中诗歌书写的饮食内容相吻合。随着南方经济发展而来的文化发展,文学创作中便也体现出时代的地域特色,东南地区物产和饮食好尚在书写中越加显著。以水产和果蔬为主的饮食系统,与清雅的时代追求相辅相成。
除了展现审美趣味和口味好尚,宋代辞赋中饮食书写还将南方式饮食活动与宋人所看重的自我修养的品行相联系,是在审美格调上进一步向品性操守发展,对于家国的担当与责任也展现在了饮食生活中,因此除了要写出饮食的美感,还需要显现不追求物质富贵的操守。在这样的时代追求下,宋人在饮食上提倡“粗茶淡饭”,“葵藿”的含义发生变化,尤袤“难与松筠争岁晚,也同葵藿趁时新”便将其贫寒穷苦意味抛开,只以新鲜食材来论。
对蔬菜的继续塑造,“白菜之王”随着生产培植技术的发展,也有葑(白菜)所替代,而文人的雅俗贯通便体现在这里,宋人推崇的“笋”并不是最日常的食物,但同时又想东晋南朝的贵族意味。
这两个时期对士大夫精神风貌的追求有极为明显的影响,尤其宋代士大夫几乎成为一种标杆。宋代饮食的文学书写,从权贵政要下移到中间阶层,宋代作为登峰造极的所在,再后来的明清基本沿袭了宋代的精神追求,虽然有所发展,不过在明清时期,更加走向了世俗和日常化,随着市民文化的大肆兴起,精英阶层维护文化纯洁性的努力已然不具备客观基础,因此在辞赋的饮食书写中,相较东晋的高雅和宋代的简雅发生了变化,主要倾向于日常。东晋的南方主要是清新蔬果,与南方地区的典型饮食“饭稻羹鱼”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宋代的南方地域性中水产书写明显变多,所饮所食,也是普通的食材和食物,从身份而言,展现了精英阶层及往下更多群体的生活面貌。饮食书写虽然同样反映个人审美和情志,但是宋代不是东晋的远离尘俗,而是以俗为雅,雅俗贯通。这是一种更容易沿袭的路径,因此在后世如明清的辞赋饮食书写中,继续发展了宋代的情志以及审美追求。
在经过东晋南朝、宋代等时期众多文人的书写和塑造,南方的饮食总体上呈现出诗意与富贵与闲适的倾向。明清辞赋中多有对此前饮食典故的发散,如建安文人的南皮之游,唐代进士的樱桃宴,以及苏轼曾提及的“盘游饭”“试院煎茶”“二红饭”等等。这些宴饮、游乐以及较为日常化的饮食,都是塑造南方饮食文化意蕴的重要因素。曹雪芹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是对南方富贵诗意的总结。清人江昌龄在《莼羹鲈脍赋》也言“南国豪华,吴门显贵”①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2006页。,鲈鱼脍又名“金齑玉鲙”,菜名中镶以金、玉,分别表现了菰菜嫩黄如金,而鲈鱼鲜白如玉,从色泽上将这道菜的夺目亮眼展露无遗,这道菜名充满富贵气息却又显得不俗气。除了这道典型的金齑玉鲙充满了诗意和富贵,在对南方食材的书写中,也几乎难以展现穷苦和贫寒,南方代表性的蔬菜菌笋以及藕、菱角等水生蔬菜,如果不代表富贵精致的生活,便就是体现南方生活的诗意化。即使展现生活闲适的小吃书写,几乎也是南方地区尤其江南地区的小吃为主,如鸭馄饨、饧箫之类。在留存辞赋作品的最多的清人笔下,深刻地体现了历代文化累积起来的南方饮食意蕴,南方的饮食充满了富贵、诗意以及细致的讲究。这与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地域在文学中被塑造的形象一致。而与此相对,将肉类作为重要食材的北方饮食系统中,既缺乏书写的文人群体,又不符合被南方文化精英把控的时代审美追求。在这一社会时代背景之下,南方地区物产和食物在辞赋中大放异彩。
三、何以选择南方
首先是南方本身的优势,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南方物产丰富。南方的产物进贡到权力中心,由此生活在北地的文人通过文献、与他人的交流以及南方进贡的实物增加对南方的了解和想象。这如同很多诗人没有去过边塞,但并不影响他们写边塞诗。“《东观汉记》曰: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橘、龙眼、荔枝”②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85页。,可见南方的水果对于北方来说,早就是珍品,所以北方的贵族并不缺乏对南方珍贵食物的食用和渴望,在交通条件和储存条件能支撑的情况下,南方的物产运送到北方的权贵手中,所以北地的文人对于书写南方的食物也充满了热情,到北方为官的南方文人在文学书写中也充满了对故土的思念,所以对南方食物的书写从文人角度而言,从主观情绪上,也是占优势的。而北方的食物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年代,通常不会运送到南方,这让北方的士人对南方的饮食总有一点好奇和念想。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久负盛名的雕胡饭,在宋玉的《讽赋》中,“为臣炊雕胡之饭,烹露葵之羹,来劝臣食”①严可均:《全秦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2页。。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也提及楚地物产“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②龚克昌等评注:《全汉赋评注》前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72页。,所以楚地的食雕胡饭较为常见。到了唐代,雕胡饭在文学书写中更是受到各类诗人的热烈欢迎,种曾经典型的南方风物在唐诗中大放光彩。只不过此后如盛极必衰,宋人笔下,便渐渐陌生了,苏颂《图经本草》上说菰根:“至秋结实,乃雕胡米也。古人以为美馔,今饥岁,人犹采以当粮……然则雕胡诸米,今皆不贵。”③唐慎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11,四部丛刊重修景上海涵芬楼藏金刊本。雕胡饭对于此时的宋人已经作为荒年补充类的食物了,并且已经觉得较为陌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宋代茭白培养技术的发展,菰黑粉菌的感染越来越普遍,菰米感染后成了茭白,粮食从此成了蔬菜。
其次这是历史的选择,从饮食书写的发展历史来看,文人的饮食书写经历过几次重要变迁,魏晋时期觉醒思潮之下,加之礼崩乐坏,礼制开始和日常生活剥离,汉赋中书写游猎宫苑变为日常或酒肉高歌或清雅的生活,第二个重要时期便是随着晋室南渡,时代风气变迁中,士大夫对精致生活的塑造,从食材、食器、食物等诸多方面都往精致高雅的方向上努力;第三次书写转向是在宋代,随着庶族阶层的兴起致使文学中心下移,转向了更通俗的日常化,最平常的饮食进入了文人的书写,并在后世的书写中基本延续了这种模式。加之用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书写饮食,势必在“文的觉醒”以后,如作为汉代代表性文体的赋,赋中有关饮食的书写,并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在写到富饶物产的部分一般会涉及粮食、蔬果等产物。等到“人的觉醒”时期,文的书写才相应成为一种“自觉”,在魏晋时期,诗文中关于酒肉的书写并不鲜见,这与北方的饮食习惯是相似的,但这一时期社会的非理性追求成了下一阶段的摒弃对象。因此在士风追求、生活习惯在永嘉南渡之后都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此时文人来到了南方,依托南方的风物开始重新塑造理想形象。北方在此时,脱离了文人的创造背景。所以很明显,这三次转向中后面两次都是在南方完成的。所以从客观上看,北方食材、食物以及饮食相关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书写土壤。加之随着几次南迁之后,经济中心转到南方,南方的文化影响力大为上升,生长于南方的文人又反过来促进南方文化的发展。
再次是文人的塑造。这从唐代和元代的饮食书写差异便可以看出,唐代前有南朝后为宋代,元代是紧承宋代而来,但在饮食书写上,唐和元由于兼容并包的形势和多民族的交融,文人在饮食书写上,便没有明显地展现南方地域性的意识,相反唐代大放异彩、广受欢迎的是以胡食为代表的融合饮食,连酒都以酒家胡为文人所喜;而蒙元时期的饮食书写可以看到各处的食材和饮食,从地域来看北方的上京、南方的广州的饮食活动都是文人笔下的重要书写对象,南方地域的书写自然并不缺少,但就呈现出的作品来看,南方的饮食和其他地域的饮食都只是作为地域的一部分而已,并不具备特殊的文化意蕴。所以即使在南方已经开发和发展的时期,当文人的观念不拘于地域而进行饮食的文学书写时,便不具有明晰的地域性,所以缺少文人的塑造也难以成型。历史机遇、南方的物产作为客观条件,加之以文人的塑造,让文学书写具有浓郁的南方地域性。
通过具体的食物书写比较,也可以窥探饮食书写中南方地域性的胜出。南方饮食与北方主食比较来看,北方的小麦和南方的水稻在文学书写中,当作为祥瑞时,如赋中的各类“瑞麦”“瑞禾”,此时水稻和小麦具有同样的政治意味。而水稻书写中,清人还有数篇《红莲稻赋》《稻蟹赋》,仅从南方丰富物产的角度出发进行书写。在文学性的描写中,水稻的文学书写明显多于小麦,这便是南北主食差异在文学上的反应,从客观环境来说,宋代时占城稻等良种传入,使得水稻的种植和收获大增,江南意象相关的意象除了“杏花春雨”式的清幽美丽,另一“鱼米之乡”式的富庶安乐也开始出现,明清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长、远超北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肉与鱼来看,南方的鱼类书写从第一次南渡之后便具明显的优势,在宋代水产类书写更加明显,各类赋作中以水产为名的作品非常多。从蔬菜来看,此前作为百菜之王的葵菜到宋代也渐渐让位于南方的笋。所以南方饮食在宋代饮食书写的地域性已经相当明显。这一饮食生活和书写模式在明清依然被沿袭,在某些客观情况的推动下,南方饮食在现实中也闻名于世,如明代张居正执政期间,由于他的褒扬,江南饮食在京城也炙手可热。
总而言之,饮食的文学书写所具有的南方地域性,与政权变迁、地域经济发展、文人的审美倾向等多方面都密不可分。早期的辞赋中的地域在于展现物质丰饶,并无文学性的追求。对南方的秀美和物产丰富的欣赏,要到东晋时期。被迫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世家大族,从与北方的荒芜和广袤对比中感受到了南方的温润和精致,环境的高雅清幽与士大夫想要塑造的士人风节相为表里。到宋代时,随着整个南方地区的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上升,南方人的饮食生活风尚,随着南方文人的推广辐射到整个社会,文人诗文书写中对南方秀气精致的崇尚十分明显。这对饮食文化和审美倾向的塑造在今天依然有所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