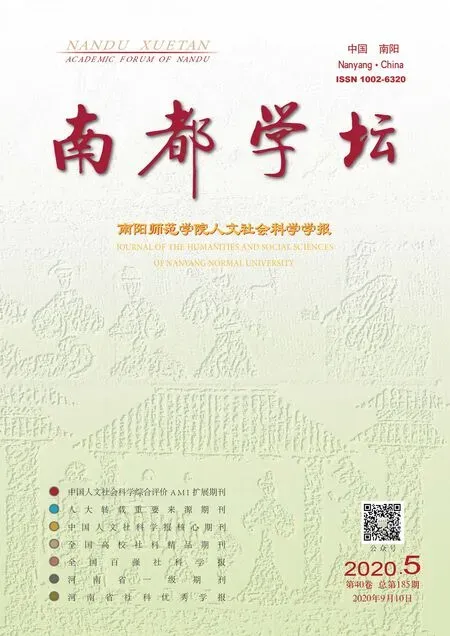从兰台、东观看汉代档案管理的发展演变
王 春 阳
(南阳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在中国档案史上,兰台和东观是两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1]后代学者多沿其说。但对于修史、著述之所由兰台移入东观的原因,学界则少有论述。本文拟从档案发展史的角度对兰台、东观作为汉代早期的档案馆的关系及其在职能、性质上的变化进行考察,从而探究东汉修史、著述之所从兰台移入东观的原因及其汉代档案管理的发展演变。
一、兰台与东观作为官方藏书机构的性质与职能
(一)兰台“图籍秘书”的职责
东汉立国后,文书的运行成为行政运转之枢机。故王充在《论衡》中指出“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汉代遂“以文书御天下”[2]。而文书运行的机构,在西汉主要是由御史大夫负责的,史载:“御史,员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绛,给事殿中为侍御史,宿庐在石渠门外。二人尚玺,四人持书给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领。余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也。”[3]又“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4]725。根据以上文献所述,御史大夫的职能主要有三:副丞相,与丞相共掌政务;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人,负责监察;皇帝的秘书长,在皇帝和百官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而御史大夫的属员一分为二,其中15人从御史大夫衙署中独立出来,由御史中丞带领进驻禁内,在殿中兰台办公,作为秘书机构,服侍皇帝左右。这时候,兰台是隶属于御史大夫的,而根据以上所引述材料,则可归纳出御史中丞职掌的文书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诏,负责皇帝诏令的拟定和印制;二是负责章奏转呈,奏请文书要经由御史核查,所言不善者、内容虚浮者屏去不报,余者上呈等待批复;三是档案的保存,皇帝的诏令、朝臣和地方官员的章奏及皇帝的批复等文书材料,都必须由御史登记并保存起来。除此
之外,朝廷颁布的法律条令、制作的舆图、地方报送的上计材料等,也交由御史保存。兰台作为御史大夫属官御史中丞的治事之所,是皇帝秘书机构的所在地,因此不仅承载着大量文书档案的收集转呈,而且自身亦是大量文书档案的产生地。又因为要拟定文书,以备皇帝咨询顾问,所以大量文书档案也就留存于此了。故兰台又成为文书档案的保存之所。同时又由于其处禁内,地位相当重要,以至于“兰台金马,递宿迭居”,日夜都有官员轮班值守,所以“典册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5]。这也反映了兰台的重要性。
随着职官制度的变迁,西汉末成哀之际,御史大夫转为司空,负责水土营造事务,完全成为政事官,其作为皇帝秘书长以及监察百官的职能为御史中丞所取代,其治事之所兰台被称为御史台。东汉初年,光武帝循旧制由御史中丞领监察和秘书事,并提高了御史中丞的地位,“执宪中司,朝会独坐,内掌兰台,督诸州刺史,纠察百寮”[6]3600。作为皇帝秘书机构的负责人,御史中丞仍然留在禁内办公,其属员有治书御史、侍御史和兰台令史。其中治书御史2人负责法律解释,侍御史15人负责查举非法并接受群臣奏事,兰台令史无定员,主要“掌奏及印工文书”。根据分工的不同可以看出,御史中丞所承担的监察职能主要由御史负责,而秘书职责主要由兰台令史掌管。因此一直由御史中丞掌管的“图籍秘书”也自然由兰台令史直接负责管理了,则兰台就成为御史台部门档案馆的代称。
(二)东观收藏档案典籍和校勘著述的职能
东观是东汉都城洛阳一处建筑物的名称,属于南宫建筑群的一部分。作为东汉时期档案存贮最为集中的地方,东观也成为东汉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心。由最高统治者颁布诏令,中央政府组织了一批批著名文人学士在东观进行大规模的校书修史活动,而东观也因承载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而留名史册。一是东观的系列修史活动。汉明帝时期,诏命班固修著《汉书》,但是未完成,班固就去世了。汉和帝把续修《汉书》的任务交给了其妹班昭,“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6]2784,班昭在东观完成了《汉书》八表和《天文志》的续修工作。东汉末年,掌管档案的秘书监荀悦按照献帝诏命,以班固《汉书》为依据,经过剪裁删润,去繁就简,在东观历时数年,完成了编年体史书《汉纪》的修撰工作。从明帝开始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朝廷支持下,经班固、刘珍、李尤、伏无忌、蔡邕等著名学者的前赴后继,历经100多年,完成了《东观汉记》的修撰工作。之所以命名为《东观汉记》,就是由于这部史书主要是在东观完成的。由此可见,《汉书》《汉纪》和《东观汉记》主要是在东观完成的。二是东观的系列校书活动。安帝永初四年(110),由于“惑于经书谬误”,邓太后诏令刘珍等50余人校书于东观,并令蔡伦监典其事。顺帝永和元年(136),诏命侍中屯骑校尉伏无忌、议郎黄景等人于东观校定中书、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灵帝建宁三年(170),召拜蔡邕为郎中,校书东观。三是最高统治者在东观开展的系列读书、学习活动。汉和帝多次亲临东观参观学习,如:“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6]188;“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6]2546。元和元年(84)汉章帝诏命“天下无双,江夏黄童”黄香到东观“读所未尝见书”[6]2614。安帝永初三年“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的和熹邓太后诏令“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6]424。东观之所以成为东汉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心,与东观作为国家档案馆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东观作为东汉“图籍秘书”的组成部分,也归属于兰台令史,由其负责管理。
(三)兰台和东观在性质、职能上的差别
东汉时期,虽然兰台与东观都是档案馆,但是二者还是存在差异的。一是兰台与东观的性质不同。兰台是皇帝秘书机构治事之所,兰台之所以成为档案馆是由兰台所驻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兰台不是独立的档案机构,而是附属于御史台的部门档案馆,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它随着皇帝办公地点的转移而转移,随着机构职能的变化而变化。而东观是专门用以存贮档案的场所,不依附于任何机构,只存在归谁管理的问题,具有明显的独立性,是独立的档案馆。二是兰台与东观的职能不同。作为御史台的部门档案馆,兰台存贮的档案与御史台职能密切相关,主要收藏与其职能相对应的档案以及作为秘书机构所产生的文书档案。由于秘书机构的运转不断产生新档案,兰台档案累积到一定体量的时候,就必须对部分档案进行移存,以便有足够空间来贮存新产生的档案。因此兰台馆藏档案具有时效性、临时性、部门性的特点。而东观作为独立的国家档案馆,其收藏档案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存贮前代档案,而且存贮国家搜求以及学者进献的图书档案,还接收其他部门移交过来的各种专门档案。东观所藏档案具有综合性、稳定性和永久性的特点。由于性质和职能不同,作为档案馆,兰台无论是场馆的空间还是收藏档案的规模、类别都是无法和东观相提并论的。
二、兰台、东观作为汉代档案管理机构职能的演变
对于兰台与东观二者之间的关系,历代学者普遍认为东汉时期档案馆藏有一个从兰台到东观在空间上的转移过程,甚至有“班固先在兰台修史,刘珍等移至东观”[7]的判断。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判断,主要是论者只注意到东汉前期从事校书修史活动的班固、贾逵皆有兰台令史的任职经历,而忽略了兰台机构职能以及兰台令史职责的变化。
(一)尚书台秘书职能的增强
汉武帝时,为加强皇权,开始重用尚书,并通过内廷尚书署来亲自处理政务。汉成帝时,将尚书署改为尚书台。东汉光武帝进一步提高了尚书台的地位,“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6]927。随着尚书地位的提高,尚书台的组织也日益扩大。从秦到汉初,尚书的名额都不过4人。汉武帝时增加到5人,成帝时增加到6人。东汉光武帝时期,尚书台设尚书令1人、尚书仆射1人,尚书6人,尚书丞12人,侍郎36人。其中尚书令负责“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尚书“掌录文书期会”,侍郎“主作文书起草”。
尚书最初的职责不过是“在殿中主法书”或“掌通章奏”而已,也就是收发章奏或者向各机关传达章奏。汉武帝以后,尚书的职权由“通章奏”而“读章奏”,由“读章奏”而“裁决章奏”,由“裁决章奏”而直接“下章”[8]。到了东汉时期,尚书台更是成为诏书起草、制作、下发的唯一机构,也是上行文书的汇集之所[9]。尚书作为皇帝的喉舌,出入帝命,不仅诏令由尚书宣达,而且群臣的奏章也必须经由尚书呈递。很显然,东汉时尚书台演变为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尚书令成为皇帝的秘书长,掌管章奏文书,负责起草诏令,在皇帝和百官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当时的大臣只有带“录尚书事”“领尚书事”才能真正握有实权,逐渐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
(二)兰台秘书职能的丧失
与尚书台秘书职权不断增强相对应的则是御史台秘书权的逐渐丧失。东汉光武帝时,御史中丞带领侍御史、治书御史和兰台令史,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仍驻殿中兰台,掌握监察和秘书大权。但是随着尚书台秘书职能的进一步增强,御史台的秘书职能逐渐丧失,其工作重心日益集中于监察职能,成为职能单一的中央监察机关。随着御史台机构职能的变化,其治事之所也有了变化。光武帝“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6]25,南宫遂成为东汉初的政治中心和朝贺议政之地。明帝时期开始修建北宫并移到北宫居住,此后历代皇帝多居于此,北宫逐渐成为帝国心脏。因为御史台机构职能的变化,御史台未能随皇帝迁到北宫,而是留在了南宫。御史中丞及其属员失去了在禁省办公的权力,由皇帝身边近臣而逐渐变为外臣,兰台令史作为皇帝机要秘书的身份随之丧失。明帝时期,兰台令史“掌奏及印工文书”的秘书职责已逐渐淡化。和帝永元三年(91),增尚书令史员,“皆选兰台、符节上称简精炼有吏能为之”[6]3596,尚书台完全取代御史台成为沟通内外的唯一机构。兰台令史开始分流,一部分选入尚书台,继续作为皇帝机要秘书。“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10]兰台令史凭借自己的业务素质,可以通过转任尚书令史进入禁内,再次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成员,并沿着兰台令史、尚书令史、尚书郎、尚书一路升迁发展。另一部分进入东观成为专职修史校书人员。“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11]由于兰台令史具体负责图书档案的管理,其职责开始向修史校书转变,并沿着兰台令史、校书郎、校书郎中一路升迁发展。
兰台作为档案馆是依附于御史台的,随着御史台作为皇帝秘书机构职能的丧失,其存贮机要文书等档案的功能也随之消失,作为部门档案馆亦不复存在。兰台令史掌管兰台档案的职责也已名存实亡。因此,在东汉和帝以后,“不要说‘兰台令史’校书事,连‘兰台令史’这一名称似乎也不再见于史书了”[12]。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的兰台和东观作为档案馆是共时性关系,在客观上并不存在档案馆藏中心从兰台到东观的转移。章、和以后东观取代兰台成为学术中心,是由于兰台机构职能变化而使兰台作为部门档案馆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而兰台令史也被调配至东观去校书修史所致。随着专职管理机构和档案管理者的出现,兰台与档案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联系。
三、汉代档案管理思想的变化
(一)统治者档案利用意识的形成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4]1701汉代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档案对王朝兴衰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特别重视对档案的利用。一是将档案整理作为统一思想的手段。汉武帝时期,通过儒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但是儒学内部却纷争不断,特别是今古文经学之争旷日持久,虽经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统一思想,仍未能解决思想界的混乱状态。汉代统治者主导的校书和修史活动,就是要利用档案的特殊价值,通过档案整理达到思想统一和文化认同的目的。例如蔡邕将整理校定的七部儒家经典刻石公布,为天下读书人取资,本身就有着统一思想的功用。二是利用档案制定礼仪以规范现实。礼制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手段,也是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因循。“为国以礼”“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儒家的一贯主张。但是时代变换,朝代轮序,礼制必须因时而变,“大汉当自制礼”[6]1201。东观典藏的典章、故事就成为制定汉家礼仪制度的重要依据,如“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6]1940。三是将档案作为教化的重要载体。东汉统治者认为“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因此下令“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6]424。灵帝时,褒奖典范,当曾经校书东观的高彪升迁后,在东观为其画像以劝学者。统治者将档案作为教化的载体,从而达到“美教化、易风俗”的目的。
(二)档案管理由分散到集中
西汉时期,御史中丞、太史、太常、博士、太仆、理官等衙署,既是档案的产生机构,又是档案存贮机构。这些衙署都会根据其职掌收藏皇帝诏命、地图户册、人口赋税、祭祀礼仪、天文历法、法律条令、典章制度等各种档案,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具有依附性的部门档案馆,其中以兰台最为著名。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专门用以存贮档案的独立档案馆,其中以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等最为出名。但是众多部门档案馆与独立档案馆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处于分散管理状态。东汉时期,虽仍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册文章”,但是除兰台之外,已经没有西汉时众多部门档案馆并存的情况。而专门的大型独立性档案馆,也仅有东观一处。可见,在东汉时期政府已经实现了对诸多档案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沈约《宋书》卷四十记载:“汉西京图籍所藏有天府、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东京图书在东观。”杜佑《通典》卷二十六也说:“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后汉图书在东观。”[13]由此可以看出西汉与东汉时期档案管理上存在的不同之处。作为独立的中央综合档案馆,东观的档案种类宏富,不但藏有各类图书,而且还藏有历朝注记、尚书所掌档案以及功臣功状和前朝旧典等档案。正是由于东汉档案集中藏于东观,张衡才上书皇帝“愿得专于东观,毕力于纪记”,而蔡邕亦上书皇帝请求参阅东观所藏档案,“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由张衡与蔡邕二人事例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档案与西汉时期档案管理相比较,已经实现了集中管理。与这种管理相适应,则出现了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和档案管理机构,“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14]。东汉桓帝时期,更是设立秘书监统一掌管所有档案,“自后汉置秘书监,而典司图籍设有专官,历代相同,未尝改作”[15]。
(三)官方组织档案整理常态化
与重视档案征求与收集相应,汉代王朝对档案的整理十分重视。西汉立国不久,汉高祖就命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对前代档案进行整理。武帝时期,又诏命杨仆整理兵书文献。成帝命著名学者、光禄大夫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秘书,数十年间,对汉代馆藏档案进行大规模整理,在整理过程中编制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七略》。东汉光武帝肇基,百废待举,即诏命尹敏和薛汉二人领衔整理馆藏谶纬档案。从明帝、章帝时期,政府档案整理便成为日常工作,由校书郎中、校书郎专职负责。安帝时,著名学者刘珍等50余人整理东观全部档案,7年后,刘珍等人再次整理东观收藏的档案。顺帝、灵帝时,亦承续有档案整理。汉代政府组织档案整理的常态化、日常化,使东汉的档案管理取得了显著成绩,《汉书》《东观汉记》《汉纪》三部史书在一定意义上均是东汉档案整理的成果。
东汉档案馆藏中心从兰台到东观的转移,不仅是兰台机构职能的变化,更是档案管理制度的创新。政府开始对档案收藏进行统一规划并实现了集中管理,开创了政府系统整理档案、利用档案的先例。这不仅拓展了档案功能,使档案具有了干预社会、服务社会的作用,同时还引起档案功能观的巨大转变,对古代档案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兰台人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