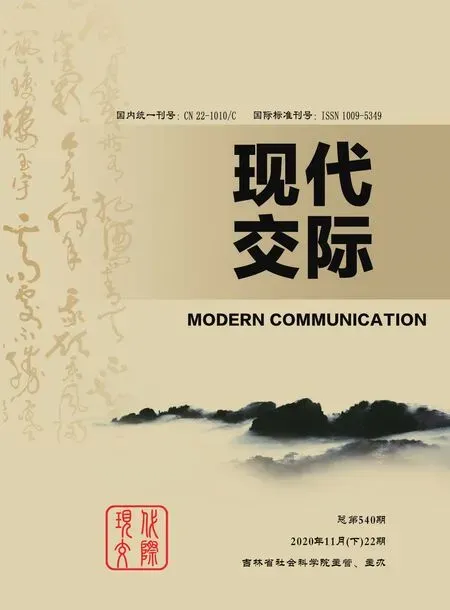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俞樾笔记创作研究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晚清中国面临的内外交困,被时人视为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文人目睹时风转移,形诸笔墨,造就了晚清笔记不同于前代的瑰丽盛况,包括作者增多,创作数量超越前代,笔记传播方式发生改变等多种变化。俞樾是晚清经学大家,在晚清世变当中,俞樾潜心著述,久为人师,为时局变换中的文化传承贡献巨大。然而,生逢晚清,俞樾不可能不受时代风气影响,他在经学研究之余,致力于笔记创作,成为晚清士大夫笔记的重要代表作家。俞樾的“学术与教育思想影响了同治、光绪年间的许多学者。他既是晚清汉学的最后绝响,又是清末民初学术重新勃起的前奏”[1]。俞樾的笔记创作兼有袁枚才子型风格与乾嘉以来学者型笔记的特色,可以说是清代笔记创作的集大成者。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他对笔记小说高度重视,其作品对近代小说观念有着开创意义。
一、俞樾的笔记创作
俞樾自言:“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2]俞樾的笔记观念,受其父亲俞鸿渐的影响。俞鸿渐曾评论蒲松龄《聊斋志异》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说:“《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五种》。”
实际上,《阅微草堂笔记》一直备受晚清士人推崇,但是部分名臣士大夫并不愿意谈奇说怪,加之乾嘉学风所及,清中叶以后笔记作品,志怪类笔记并未形成风尚。如袁枚的《子不语》就更不为正统士大夫所推崇了。作为经学大家的俞樾,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活动是在通经致用、干预现实的经学统摄下的文学活动,其经学家身份主导下的这种笔记观念并不奇怪。他自言:“余今岁行年六十矣,学问之道日就荒芜,著述之事行将废辍,书生结习未能尽忘,姑记旧闻以销暇日。”从中可见其笔记创作的动机是“消闲娱老”。在观念上,俞樾未曾脱离教化与补史这样的传统,因而他的创作中包含众多以小说为传记的作品和表彰节义的作品。
在创作观上,作为经学家的俞樾表现出鲜明的学者化态度,这也正是乾嘉以来笔记创作的主流倾向。俞樾的笔记作品主要包括《春在堂随笔》《小浮梅闲话》《荟蕞编》《耳邮》《右台仙馆笔记》等,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晚年,确有明显的“消闲娱老”意味。
1.《春在堂随笔》
俞樾因“花落春仍在”为曾国藩赏识,因而名其所居为“春在堂”。这一部《春在堂随笔》被认为“虽不是俞樾的主要学术成就”,但由于其深厚的学术根基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堪称晚清杂著类笔记之典范”[3]。《春在堂随笔》共10卷,涵盖内容广博,大略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记录科场经历、生平遭遇、讲学课士及著述情况;二是记录为他人所作的题赠及序跋诗文;三是记录经眼之名人遗墨及金石碑刻,间有考证;四是记录仕宦逸闻、学人著述,以及日本人、西方人的学行著述;五是转引摘录前人笔记条目,并予以点评考证;六是记录了局刻经史情况;七是记录异闻异说。[4]
《春在堂随笔》中轶闻掌故是整部书的主要部分,但在这些掌故中,甚少涉及时事。这与这一时期俞樾的身份有关系。作为被革职弃用的官僚,俞樾对于时政并非不关心,但不敢在著述中有过多的议论;因而,除了这些琐闻纪事,其中多有如小学考释、文学评定、史学辨析、金石考释,乃至内典、天文、历法,等等,均有涉及。所记如西学、西史、西方典籍等显示出俞樾的视野并不隔绝于时代之外,在晚清新学风潮中,体现出传统学者和学术的生命活力。
2.《小浮梅闲话》
《小浮梅闲话》不分卷,附录于《春在堂随笔》之后。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俞樾与夫人谈论古今小说,出入诗史之间,所论主要是演义小说,因而可称为演义小说研究的专书。俞樾对演义小说的考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者的考证。如对《红楼梦》作者的分析。俞樾既举出了“世传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说法,也指出了书中所署名曹雪芹,在袁枚《随园诗话》中已有记载的说法。又如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之说,俞樾也以《船山诗草》和乡会试制度内外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论说。二是小说人物与小说版本的考证。三是对小说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评价。
3.《耳邮》
《耳邮》四卷,署名羊朱翁,羊朱者即俞之切韵。《笔记小说大观·耳邮提要》中说:“是书为近人俞曲园所著。羊朱翁者,俞字之切音也。”书成之后,交由《申报馆丛书》出版。署名羊朱翁,来新夏先生以为或以此为小道,故隐其名,实则依照俞樾的笔记观念来看,似无此必要。在当时,《申报》作者中署笔名者为绝大多数,《申报馆丛书》作者亦多署笔名。《耳邮》内容上多为表彰节义、宣扬因果之作,谈鬼说怪者较少。俞樾在写作中有明显的史家意识,在大多数条目中,对于涉及的人事,多详细交代人物的名号里籍,事件的时间地点,等等,追求故事的真实性。在这样一部作品中,俞樾也时常显露出学术化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故事考据上,以引用典故、寻找佐证的方式对时事进行点评;另一方面,在议论当中也以学究态度关注世俗生活、常做学术议论。[5]
4.《右台仙馆笔记》
俞樾笔记作品中《荟蕞编》等均为辑录,而《右台仙馆笔记》的前四卷基本囊括了《耳邮》的内容,被众多研究者认为是俞樾笔记作品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
俞樾建右台仙馆是为纪念夫人,所记仍是在精力日衰、著述不能之际的消遣岁月之笔。其内容则是追摹《搜神》《述异》之类,在消遣岁月之外仍是劝世化俗为主。在《右台仙馆笔记》中,俞樾亦将学者化的思维贯注其中。不仅在笔记中引经据典、考镜源流,同时还有强烈的补史意识,表现出文人笔记的学者本色。
要而言之,俞樾的笔记创作与他的经学成就相类,可称得上是晚清笔记的殿军。在俞樾笔记当中,清代笔记学者化的倾向突出,但同时兼有才情;题材丰富,但谈怪说异尤为其所钟情。这都是清代笔记鸿硕的文化遗产在晚清积淀的产物。
二、西学文化背景下的守旧
《春在堂随笔》轶闻掌故中有数则关涉西学与西方历史,如所述宝山蒋敦复一例。蒋敦复为晚清名士,晚年寓居上海,与王韬等交往,在上海报界颇有影响,他曾协助传教士慕威廉编译《大英国志》一书,这部书是继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后,较早介绍英国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著作,军民共主、议院等概念和名词都来自这部书。但是,熟悉了英国历史和政体的蒋敦复,其知识体系和价值理念仍旧局域在儒家礼教观念当中,因而他对英国政体大加挞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英之议会,如使行于中国,大乱之道也……我历观英史,至查尔斯弟一为格朗瓦所杀,举朝宴然,无所谓戴天之仇与讨贼之义,不觉发指……英巴力门知有法不知有礼。法谁出乎?必百姓与一人共为之,民志嚣然悖且乱矣。何法之有?惜乎未有以为国,以礼之说告之也。”以中国传统礼法来理解英国,今日看来确实不适合;而在中西文化初次发生剧烈碰撞之时,传统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的解释能力的完全丧失,于此也可见一斑。俞樾对于英国“传国之法,传子亦传女,传兄弟亦传兄弟之子,若女,传女子之子,亦传女子之女”的做法,感到难以理解,认为是“殊俗”,这无疑也来自蒋敦复。蒋敦复认为,“天位神器不可妄干,明正统重嫡嗣,礼也。英之世系自中国言之,牡朝乱政,异姓乱宗,春秋之法在所必诛。统是三者观之,英之为政亦异乎中国矣。”蒋敦复本是因太平天国之乱而避居上海,目睹了洋枪队的厉害,又接触到了墨海书馆里先进的文化,较同时代人算是知洋派人物,他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俞樾在多年以后再读《大英国志》,竟然仍是类似观点,可见旧思想束缚之顽固。唯有王韬曾经指出:“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敢玉食万方也。所居宫室概从朴素,不尚纷华,从未有别馆离宫,迤逦数千里也。”“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6]可惜的是,在当时,如王韬这样的见解,非但不是主流,甚至被人视作异端,根本不可能在思想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的这一段记录,恰体现出当时至19世纪末,鸦片战争已过去数十年后,中国知识阶层对世界的认知。
三、东渐传播背景下的开创
俞樾在笔记作品中的小说考证与小说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小浮梅闲话》《茶香室丛钞》中,也散见于其他笔记中。清人所谓考据,多集中于经义,杂及史地等。俞樾生当晚清西学东渐之中,受到近代学术观念的较多影响,如在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上,俞樾认为通俗文学中的教化功用并不亚于诗教,从这个角度,俞樾对很多作品进行了考证、评点。俞樾对小说的评点和研究既是小说评点传统的延续,又蕴含现代小说研究的意义。俞樾等人对于小说教化意义的评价,在其后“小说界革命”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此后,小说竟取代诗文成为文学之大宗,小说研究也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宗与显学,晚清学人如俞樾等的研究可谓已肇其端。“俞樾是近代最早有意识地把传统治经史学问的态度和方法,用之于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大学者,他的小说研究的意义不仅仅体现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证和评论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小说观念和学术趋向的变化,而这些对于清末民初的小说研究乃至古代小说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7]至于其后人俞平伯、再传弟子鲁迅等皆以研究小说、著述小说而成家,恐怕也是渊源有自。
除此之外,俞樾对文学作品必须写真性情、表现个性的主张,在晚清时代风潮中无疑也具有其进步价值。俞樾对作品语言通俗晓畅的追求,虽然受到其弟子章太炎的批评,且章太炎一味古奥的文辞无疑是对俞樾的反动,但俞樾诗文的明白晓畅,却正是其可贵之处。
四、结语
俞樾没能像他的前辈“龚自珍、魏源那样成为启蒙主义思想家,后来也不曾直接去参加维新改良的活动,然而其思想不但与之同步,甚至有不少还是超前的。这样一位正统[8]的经学家,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恐怕是不能低估的”。俞樾既有其保守一面,又有其开创贡献的表现,这正是晚清时代中正统学者的典型,他们浸淫旧学,经过完备的传统学术训练,形成了系统的传统学术体系,苛求他们趋新求变,实在是勉为其难,然而他们却寄望于子孙后代,期待子孙能够习西人语言文字,通声光化电之学,[9]比如与俞樾同里的俞明震,也是如此教育子弟、课授学堂的,这便是这一代知识精英的高明之处。也正是他们如此的见识,超越于一般士人之上,才能够形成在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史上代有传人的文化家族,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