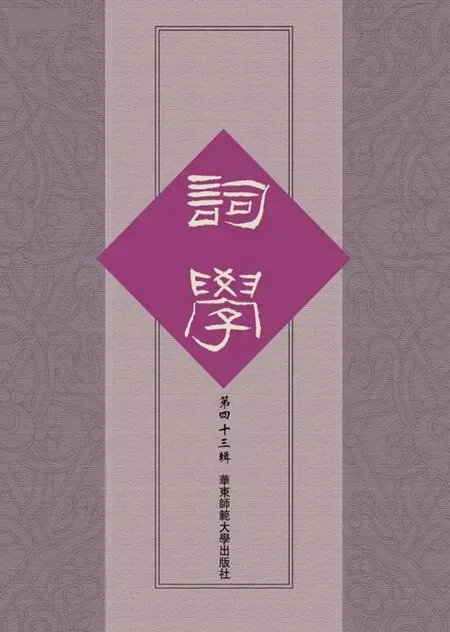王國維何以言蘇軾「皮相」:秦觀《踏莎行》接受史審思
韓立平
内容提要 寄托解詞的話語場由古人閑談賞鑒、紀事評點,一變爲現代學術體制下以探尋客觀規律爲旨歸的科研撰述,其存在的弊端明顯暴露出來。惠洪《冷齋夜話》關於秦觀《踏莎行》「郴江」句的評説,屬於「多及野逸賢哲异事佳言」以「資閑談」的性質。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於《踏莎行》調下注「東坡絶愛尾兩句」,遂制約了後世讀者的解讀路徑。王國維「皮相」之譏,主要緣於「郴江」句的「隔」,「隔」導致後世寄托讀詞的歧出。詞學研究與撰述,要警惕將宋人詞話筆記中的「叙事」與真正的「事實」之間劃上等號,在寬容「以史釋詞」之可靠性的同時,也應對其他解讀方式持一種寬容。
關鍵詞 王國維 踏莎行 秦觀 叙事 以史釋詞
以比興寄托解詞,將怨夫思婦之情、山河物類之景,導向賢人君子之思、孽子孤臣之恨,雖昉始於兩宋,然至清人常州張惠言始鬯宣之,遂張皇幽眇,爲世所重。其後,晚清譚獻更以「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一]給予了寄托解詞充分的「合法性」。二十世紀以來,當倚聲填詞之學由傳統社會的文人餘事,一變爲高等院校人文學科古代文學的教學内容;當寄托解詞的話語場由古人的閑談賞鑒、紀事評點,一變爲現代學術體制下以探尋客觀規律爲旨歸的科研論著,則寄托解詞原先尚存的一汪「烟水迷離」頓時雲銷雨霽,其存在的局限與弊端也明顯暴露出來。問題之關鍵在於,當話語場發生變異後,今人如何再次面對有限的文獻材料以求得審慎的結論?作爲中國詞史上的一闋名篇,北宋詞人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在後世的接受中産生了尚待辨正的諸多疑惑,本文即以此首作品爲例對寄托解詞及詞學文獻的利用方法略作審思。
一 《踏莎行》與蘇軾
《踏莎行》(霧失樓臺)是秦觀傳世詞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詞甫一問世,即引起蘇軾、黄庭堅、范温、惠洪等人的關注,且被當時人書寫刻石以廣流播,相傳蘇軾書其尾句於扇,米芾書寫全詞並蘇軾評語[二],南宋乾道間周必大爲米書秦詞作跋曰:「藉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詞此字所以傳世。」[三]淮海詞、東坡語、元章筆,在南宋號「三絶碑」,寶祐[四]、咸淳[五]年間,皆有人親見此石刻。此外,對歷代詞選、詞評的考察,也可印證《踏莎行》受後世讀者青睞之程度。據統計,秦觀有九十五首作品被後世選本收入,其中《踏莎行》被《花庵詞選》、《草堂詩餘》、《詞綜》、《宋四家詞選》等共計十三種詞選收入,數量排名第一[六]。同時,據徐培均《淮海居士長短句箋注》所輯匯評,《踏莎行》附有歷代評論二十八家[七],在秦觀所有作品中也排名第一。
歷代關於《踏莎行》的解讀與評論,主要聚焦點有兩處,一處爲上闋歇拍:「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另一處爲下闋歇拍:「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其中,關於「杜鵑聲裏斜陽暮」之「斜陽」與「暮」是否重出的論辯,從宋代以來聚訟紛紜,是《踏莎行》引發評論的主要原因。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范温《詩眼》首發黄庭堅對「暮」字重出的指瑕,張端義《貴耳集》、張侃《拙軒詞話》、何士信《草堂詩餘》、王楙《野客叢書》等宋人筆記、詞話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見解。此後,元代黄晋《日損齋筆記》,明代楊慎《詞品》、俞仲茅《爰園詞話》,清代沈雄《古今詞話》、宋翔鳳《樂府餘論》等皆有辯證,基本上「暮」字與「斜陽」是否重出的問題已得到解决。
其次,關於「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以下簡稱「郴江」句)的評論,宋人現存材料基本闕如,基本對「郴江」句不予關注。黄庭堅「顧有所屬而作」的闡釋(《山谷題跋》)、范温「模寫牢落之狀」的判斷(《日損齋筆記》引《詩眼》)與周輝「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的賞鑒(《清波雜志》),都是就《踏莎行》整首作品而發,未直接對「郴江」句發表意見。宋代關於「郴江」句的評論僅見一例,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引惠洪《冷齋夜話》:
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東坡絶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八]
惠洪此條被今人視爲關鍵性解讀「密碼」的材料,在宋代的影響却是微弱的,僅爲魏慶之《詩人玉屑》與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抄録而已,宋人並未受其影響而産生對「郴江」句的寄托解讀。直到四百餘年後,明代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始有關於「郴江」的鑒賞性文字:
「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又「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九]
其後,明代張綖鄂州刻《淮海居士長短句》詞末附注,引釋天隱注《三體唐詩》考證「郴江」句在修辭上自戴叔倫「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脱胎而來,並進一步指出更早的源頭:「毖彼泉水,亦流於淇」(《詩經·邶風·泉水》)。清代王士禛對「郴江」句的評賞,進一步發展了《冷齋夜話》的説法:
「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向瀟湘去」,千古絶唱。秦殁後,坡公嘗書此於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高山流水之悲,千載而下,令人腹痛![一〇]
王士禛「高山流水之悲」的解讀,已然在《踏莎行》的接受史中將蘇軾的書扇行爲「經典化」了。清人鄧廷楨《雙硯齋詞話》則更演繹爲毫無根據的「東坡讀之歎曰:『吾負斯人。』」[一一]
南宋黄昇編《唐宋諸賢絶妙詞選》於《踏莎行》調下注:「東坡絶愛尾兩句」[一二],此一行爲對明代以後的解讀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明代以後淮海詞的諸多刻本中,《冷齋夜話》的信息被附注於《踏莎行》(月迷津渡)之後,如嘉靖己亥張綖鄂州刻本、萬曆戊午李之藻高郵刻本、明末段斐君武林刻本、明末毛晋刻本等[一三]。這些刻本的附注,制約了後世讀者對《踏莎行》的解讀路徑,蘇軾已不可能「置身事外」了。
反觀蘇軾本人,他並未對《踏莎行》有任何直接評論。秦觀卒後,蘇軾有多處文字表達了傷悼之痛,不勝枚舉,如《與范元長十三首》之十一、十二:「哀哉少游,哀哉少游,遂喪此杰耶」,「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真爲异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答李端叔十首》之三:「少游遂死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與錢濟明十六首》之十:「途中聞少游奄忽,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答蘇伯固四首》之一:「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太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與歐陽元老一首》:「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複得?」[一四]這些傷悼之語,是否可以被「打包」入「東坡絶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呢,是否可以充當《冷齋夜話》那條筆記的疏證?還是需要審慎對待的。
就《冷齋夜話》此條文字的意脉來看,蘇軾「雖萬人何贖」的傷痛表達與「自書於扇」這一行爲之間,似乎有某種關聯。我們自不能排除此一可能,即蘇軾通過抄寫秦觀詞這一靜默無聲的行爲,來咀嚼回味對門生的傷逝之情。然而,也存有其他可能,「自書於扇」也許是蘇軾因相似的貶謫經驗而産生對「郴江」句的感同身受,抑或僅是贊賞「郴江」句在文學表達上的藝術魅力。進而言之,我們不能僅因《冷齋夜話》的這條筆記,就判定蘇軾對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具有「認領」的資格,仿佛秦觀這首詞是爲蘇軾而作,仿佛「郴江」句是秦觀對蘇軾的傾訴,這些推論皆無切實可靠的證據。
總之,惠洪《冷齋夜話》關於「郴江」句的評説,尚屬古代詩話「多及野逸賢哲异事佳言」(《郡齋讀書志》)以「資閑談」(《六一詩話》序)的性質,有宋一代未有直接針對「郴江」句的鑒賞性、解讀性的評論。《冷齋夜話》這條筆記的意義,僅在於佐證《踏莎行》(霧失樓臺)一詞或寄托了秦觀的遷謫之感,所謂將身世之感打並入艶情。至於此闋詞的創作動機、創作本事、預設讀者、寄贈對象等,今人皆不宜作過多言之鑿鑿的論斷。
二 王國維「皮相」之譏
在進一步審視「郴江」句之前,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破除這兩句詞上的「光環」。也許只有將其拉下「神壇」,才能減少後世讀者對「郴江」句層累叠加的寄托解讀的衝動。要破除「光環」,我們自然想到了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皮相」之譏:
少游詞境,最爲淒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爲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爲皮相。[一五]
在王國維之前,清代徐釚在《詞苑叢談》已表達了相近的觀點:「東坡絶愛尾兩句,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堪斷腸。」[一六]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有多條襲自前人的説法(此原是詩話著述的常見現象),「皮相」之説也可能如此。此外,稍早於王國維的陳廷焯也在《白雨齋詞話》中將秦觀「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與「郴江」句比較,認爲就「深厚、沉著」而言後者是稍遜色的[一七]。
理解王國維的「皮相」之譏,若聯繫其「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隔」與「不隔」的相關論述,自非十分困難之事。《人間詞話》云: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泪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一八]
問「隔」與「不隔」之别。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遊》咏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一九]對於王國維的「皮相之譏」,唐圭璋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爲王國維「過執境界之説,遂並情韵而忽視之矣」[二〇]。劉逸生也説王國維「未真正領會秦少游心中的慘痛」[二一]。相較而言,朱光潜的解釋是較有説服力的。他認爲秦觀「郴江」句屬修辭學上的顯喻(simile),特點是尖新,没有另一種隱喻(mitaphor)來得渾厚,「郴江」句屬「顯而淺」的「同物之境」,而非「隱而深」的「超物之境」,品格略低,故「雖亦具深情,究不免有露才之玷」,「詩最忌『炫』,『炫』就是露才而不能『隱』」。[二二]
「皮相」之譏作爲王國維對蘇軾的「隔空」批評,並不需要後人作站隊式的非此即彼的論辯。重要的不是追問王國維的本意,而是藉助王國維給予我們的「底氣」,來對「郴江」句的賞鑒持一種理性的反思——蘇軾的書扇行爲,並不能宣告「郴江」句就是無懈可擊的好句子。相較「可堪」句,筆者認爲「郴州」句的確比較「隔」。葉嘉瑩解釋道:「只有『可堪孤館閉春寒』兩句,是從現實之景物,正面叙寫其貶謫之情景,而其他諸句,則多爲象喻或用典之語。這與王氏平時所主張的『以自然之眼觀物』的欣賞標準,當然不甚相合。」[二三]彭玉平認爲「並非王國維不能欣賞」這兩句,「而是在表現情感的深度上,或者説在體現『有我之境』上」,「可堪」句比「郴州」句「顯得集中而有震撼力」。[二四]
錢鍾書《論不隔》對王國維的意見有了進一步深入,他提醒我們不應僅局限於「語語都在目前」而討論「不隔」,否則這樣一個「很圓滿的理論便弄得狹小、偏僻了」。錢鍾書認爲「不隔」是一種「透明洞徹的狀態」——「作者所寫的事物和境界得以無遮隱地暴露在讀者的眼前」,因此,「比喻、暗示、象徵、甚而至於典故,都不妨用」。[二五]「不隔」並非完全排除比喻、擬人等發生移情作用的修辭手法。若運用得當,比喻、比擬也可以具有「不隔」的藝術效果,例如蘇軾「欲把西湖比西子」、秦觀「飛紅萬點愁如海」之類。就「不隔」的標準而言,詩詞寫景中的比擬,一方面不能太「過分」,「不能與科學上的真,也就是事物所含的本性距離太遠」[二六],超出限度會不真切甚而難於理解。另一方面更爲重要的是,詩詞中的比擬對象,不宜採用遠離日常語境的陌生事物,否則就需要更多「知識性」的信息來彌縫其「隔」。
回到「郴江」句,郴州在北宋是遠離中原禮樂之邦的蠻荒之地,「哀歌巫女隔叢祠,饑鼠相逐壞壁中」(秦觀《題郴陽道中一古壁》),但對於「削秩徙郴州」的秦觀及宋代文士讀者群而言,尚屬日常語境中的認知對象,而對後世讀者却未必盡然。郴州這一地區在中國古代的落後發展會給予「郴江」這一符號以陌生化的效果。中國詩詞史上的「郴州書寫」是相對寂寥的[二七],其影響力自然遠不如揚州、杭州等發達地區的詩詞書寫。今日若非《踏莎行》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而擁有被教學的待遇,普通讀者對於它的接受仍可能存在一定困難。如「郴」字讀音chēn易被誤讀成bīn,以及張相《詩詞曲語辭彙釋》所指出的「幸自」應解作「本自」,「爲誰」應解作「爲甚」[二八],都讓「郴江」句基本告别了宋人所推崇的「天生好言語」(晁補之《評本朝樂章》)。此外,對於秦觀這兩句中「繞」與「流下」的欣賞理解,更需闌入額外的地理「知識」。
據《讀史方輿紀要》,郴水在「州東一里,一名郴江。源發黄岑山,北流經此,水清駛,下流會耒水及白豹水入湘江」[二九]。郴江向北流向瀟湘,這一信息對於後世讀者而言,可能是需要額外補充的。前此,雖已有杜審言「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與戴叔倫「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的詩句,但「郴江」遠較「湘江」爲隱蔽。郴江地理方面的「知識」參與,無疑對文學鑒賞接受造成了一定阻隔(下文將會呈現由「郴江」句的「隔」而導致的解讀分歧)。「郴江」句中的「幸自」與「爲誰」,顯示秦觀主觀情緒的「植入」太强烈,太過個人化,缺少直觀性,相對缺少那種超越時空的普遍的興發感動力量。毋庸諱言,與「杜鵑聲裏斜陽暮」的那種直觀、通透感相比,「郴江」句實在「隔」得厲害,二者之别不啻天壤。
總體而言,被譽爲「詞家正音」(胡薇元《歲寒居詞話》)的秦觀在北宋詞人中是「辭情相稱」的(孫競《竹坡老人詞序》引蔡伯世語),相較蘇、黄等人也更爲本色,不愧「初日芙蓉,曉風楊柳」之喻(況周頤《蕙風詞話》)。秦觀也寫下很多以「不隔」著稱的名句,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被晁補之視爲「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受到「少故實」的評價(李清照《詞論》)。然而,客觀上由於郴州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邊緣化,由於「郴江」意象在中國詩詞中的非經典化,主觀上由於秦觀移情、擬人太過個人化,從而導致「郴江」句的鑒賞接受難以阻擋「知識性」對於「文學性」的壓抑。作爲一種審美經驗,詞的欣賞接受本身應具有感性的完滿自足,無須過多倚賴知性的轉化和提升;當「知識」在讀詞的審美經驗中扮演主角時,必然會産生「隔」的效果。
三 寄託讀詞的歧出
正由於「郴江」句的「隔」,造成了後世比興寄托解讀的歧出。
明代以後的「郴江」解讀史,總體上分爲「艶情」與「政治」兩種路徑,而以「政治」解讀爲主流,「艶情」解讀爲支流。南宋洪邁《夷堅己志》載長沙義倡善謳尤喜少游樂府,願托以終身,會秦觀以王命不可久留,許以他日北歸幸一過之,孰料秦觀竟死於藤州貶所。洪邁後來又在《容齋隨筆》中對自己的叙述後悔不已:「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三〇]但洪邁的艶情叙事並没有提及《踏莎行》,清代趙翼《陔餘叢考》將《踏莎行》納入艶情叙事:「少游贈詞,所謂『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者也。」[三一]清人王士禛《香祖筆記》、吴衡照《蓮子居詞話》亦持此説。劉永翔在《清波雜志校注》中指出清人之説或有所本,可能出自元人鮑吉甫雜劇《王妙妙死哭秦少游》[三一],然全劇已佚,無法詳考。《踏莎行》的「艶情」解讀因蘇軾書扇這一附著信息而被「壓抑」,但並未在後世絶跡。今人論著雖未必如清人那樣膠著於艶情本事,但仍强調《踏莎行》主要是一首寫男女情愛的作品,如錢鴻瑛就從「桃源望斷」入手,論證「桃源」爲情人所在,而非君門九重或避世之所,認爲這首詞雖也滲透了貶謫的委屈與痛苦,但主要是寫男女愛情離别[三二]。
「政治」解讀是《踏莎行》接受史中的主流。「東坡書扇」仿佛給予了此種解讀以合法性。梳理「郴江」句的接受史,我們會發現正是對「郴江」流向問題、「郴山」比喻含義以及「幸自」意義的「隔」,導致了寄托解讀的分歧與矛盾。
第一種視角,秦觀將自己與郴江對比,以郴江之流入瀟湘爲幸,而以自己不得自由爲不幸。
如清人黄蘇《蓼園詞選》:「自己同郴水自繞郴山,不能下瀟湘以向北流也。語意淒切,亦自藴藉,玩味不盡。」[三三]陳匪石《宋詞舉》先言:「幸其回繞,惜其流去」,則是以「繞郴山」爲幸,以「流下瀟湘」爲可惜,但接著又説:「夫『郴江』之入『瀟湘』,以水言之是爲就下,以遷客言之仍是歸途」[三四],則仍是以人、水對比讀之,以遷客之不能如郴江入瀟湘而爲恨,前後不一致。胡雲翼《宋詞選》:「郴江也耐不住山城的寂寥,流到遠方去了,可是自己還得呆在這裏,得不到自由。」[三五]俞平伯《唐宋詞選釋》:「寫出望遠思鄉的真情。」[三六]在此一種解讀中,郴江之流入瀟湘,喻人之北歸。
第二種視角,秦觀將自己與郴江類比,以郴江之流入瀟湘爲不幸,而以郴江之繞郴山爲幸。
如沈際飛《草堂詩餘》:「少游坐黨籍,安置郴州,謂郴江與山相守而不能不流,自喻最淒切。」[三七]楊世明《淮海詞箋注》:「謂郴江本沿郴山,爲何流去瀟湘之遠處?」[三八]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唐宋詞選》:「郴江爲什麽要離開郴山,向瀟湘流去呢?這裏作者以發問的口氣,比喻人的離别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被迫的。」[三九]劉逸生:「自己好端端的一個讀書人,即便出仕做官,也不過要替朝廷做點本分的事罷了;正如郴江原本只是繞著郴山轉的那樣。不料却捲進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之中,落得這樣的不幸結局」,「把眼前的郴江比喻做自己」[四〇]。葉嘉瑩:「自己好端端一個讀書人,本想出來爲朝廷做一番事業,正如郴江原本是繞著郴山而轉的呀,誰會想到如今竟被捲入一場政治鬥爭漩渦裏去呢?」[四一],「郴江本來是幸福的,是美好的,它就流在郴山的脚下」,但又「一逝無還,流向瀟湘這樣遠的地方去了」。[四二]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南宋文學史》説這首詞表達了「誤入仕途、捲進政治風波的無窮悔恨」,蘇軾書於扇「既有深切理解秦觀内心巨痛的『高山流水』之悲,也有牽累秦觀、使遭致遠貶和卒於道中的深沉疚恨」。[四三]在這一種解讀中,郴江之流入瀟湘,喻人之不由自已、捲入紛爭。
兩種視角的分歧,恰是由於「郴江」句的「隔」所致。「流下瀟湘去」的寄托解讀是否需要加入「北流」這一地理知識?「流下」是高處流向低處,還是近處流向遠處?是由政治中心流向蠻荒之地,還是由蠻荒之地流向故國家園?此種悖論歧出的寄托解讀,並不能體現《踏莎行》的豐富意藴,相反,正顯示了「知識」對於文學鑒賞的壓抑。
採用第二種視角,引入蘇軾書扇以佐證政治解讀,在當代學術論著中普遍存在,其中程怡的論文無疑是一次「以史釋詞」的嘗試。程怡依《續資治通鑒長編》材料,詳細梳理元祐六年賈易彈劾蘇軾,秦觀找人疏通導致蘇、秦二人關係變化的史料,論證《踏莎行》是「令蘇軾心痛的真誠的表白」,是秦觀在「流放歲月中,通過同爲蘇門友人的黄庭堅,向蘇軾所作的曲折表白」[四四]。陳祖美也將蘇軾視爲《踏莎行》的預設讀者,斷言今日「無人再悉信所謂藝伎之事」,認爲「郴江」句的比喻意義是:「學生本自在汴京恩師周圍爲朝廷效力,如今爲什麽獨自來到這邊遠之地?正因爲蘇軾讀出了其中的深意,故而『絶愛』之。」[四五]
四 「敘事」與「事實」
以蘇軾爲《踏莎行》的預設讀者,在鑒賞談藝中自可以有發揮空間,但在學術論著中還是審慎爲好。以史料論證文學解讀,固然可以追求傅斯年所謂「據可知者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然而「若以或然爲必然,則自陷矣。」[四六]
惠洪《冷齋夜話》中多有道聽途説的材料,同時代的晁公武批評《冷齋夜話》「多誇誕,人莫之信」[四七]。也有論者懷疑《冷齋夜話》的記載非一手材料,而是本自米芾所書摩崖石刻[四八]。筆者雖不贊同此一觀點,但退一步説,即便《冷齋夜話》所記爲真,也不能推導出秦觀《踏莎行》是向蘇軾傾訴、爲蘇軾而寫,這中間是有一個「跳躍」的。二十世紀以來,歷史哲學領域發生了被稱作「叙事轉向」(n a r r a t i v e t u r n)的重大理論轉型,海登·懷特(H a y d e nW h i t e)是促成此轉型的關鍵人物。其主要觀點認爲叙事的功能在於賦予意義,叙事就是「通過對某些因素的選擇性强調和賦予特殊性地位」,「而將事件序列轉化成某種意義模式」。[四九]吕思勉也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認爲:「真正客觀的事實,是世界上没有的」,「所謂事實,總是合許多小情節而成」,「其能成爲事實,總是我們用主觀的意見,把它們聯屬起來的」。[五〇]
惠洪《冷齋夜話》的叙事,已然無意中將秦觀創作《踏莎行》與蘇軾書扇行爲這兩件事件轉化爲「意義模式」了,尤其當《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將「東坡絶愛」附於《踏莎行》調下「賦予特殊性地位」後,「政治」解讀對「艶情」解讀即産生了壓倒性勝利,也滿足了後世學者爲抬尊詞體而建構北宋詞史的預期。同樣,詞的比興寄托解讀以及詞史的研究撰述,作爲後世接受者對文學經典的一種歷史叙事,自不能不含任何主觀臆見來呈現客觀事實。中國雖向有「詩無達詁」、「六經注我」的闡釋學傳統,然今日詞學研究與學術撰述,若以探尋詞旨、作者本意爲目的標榜,則寄托解讀與史料運用的分寸拿捏,闡釋空間如何確立合理的邊界,仍是需要我們審慎視之的。寄托解詞的過程中,我們要警惕將「東坡書扇」之類宋人詞話筆記中的「叙事」與真正的「事實」之間簡單劃上等號。
現代詞學的確立過程中,隨著幾代學者的努力,以歷史學家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等著作爲典範,史學幾乎全面「侵入」詞的解讀。在此一過程中,也誕生了一些並無確鑿證據而僅憑推斷的詞之繫年、考釋等學術成果,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理論闡釋與詞史建構。誠然,詞的繫年遠較詩歌爲困難(詞有時幾乎不可繫年),但史學的「侵入」並非徒勞無功,創作時間、背景的信息爲詞的解讀與詞史建構提供了一種「脚手架」,詞學界的學術共同體能够默契在此脚手架上「相安無事」,以便於繼續進一步加邃密、轉深沉。但重要的前提是,我們要對「脚手架」保持一種清醒,在寬容「以史釋詞」研究成果之可靠性的同時,也應對詞的其他解讀方式持一種寬容,不宜將政治化的比興寄托解讀方式定於一尊。回到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這闋詞,我們其實不一定非要作政治化的闡釋而將蘇軾「拖下水」,男女艷情這一方向的鑒賞路徑,仍是可以存在的。
[一]譚獻《復堂詞録·序》,《復堂詞録》,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第二頁。
[二]王楙《野客叢書》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二九〇頁。
[三]周必大《文忠集》卷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别集類第八六册,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五六頁。
[四]黄溍《日損齋筆記·雜辯》,《叢書集成初編》據《金華叢書》本排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二頁。
[五]李瀚章、裕禄等《(光緒)湖南通志》第八册,岳麓書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五五二二頁。
[六]錢錫生《從歷代詞選、詞評和唱和看秦觀詞的地位及其傳播》,《中國韵文學刊》二〇一四年第二期。
[七]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居士長短句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八六—九三頁。
[八]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三三八頁。
[九]王世貞《藝苑卮言》,引自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八八頁。
[一〇]王士禛《花草蒙拾》,引自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六七九頁。
[一一]鄧廷楨《雙硯齋詞話》,引自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二五三〇頁。
[一二]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收入《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六二三頁。
[一三]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居士長短句箋注》卷中《踏莎行》「校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版,第九三頁。
[一四]張志烈等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七册,第五四五九頁;第八册,第五七七五頁、第五八二四頁、第六三六二頁、第六四〇一頁。
[一五]王國維《人間詞話》,《國粹學報》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〇八年十二月,第七十頁。
[一六]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詞苑叢談》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四九頁。
[一七]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十四頁。
[一八]王國維《人間詞話》,《國粹學報》第四卷第十期,一九〇八年十月,第四七頁。
[一九]王國維《人間詞話》,《國粹學報》第五卷第一期,一九〇九年一月,第六八頁。
[二〇]唐圭璋《評〈人間詞話>》,《斯文》第一卷第二一期,一九四一年八月,第十二頁。
[二一]劉逸生《郴江誤下瀟湘去——秦觀〈踏莎行>賞析》,《名作欣賞》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二二]朱光潜《詩的隱與顯——關於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五五—三六五頁。
[二三]葉嘉瑩《唐宋名家詞論稿·論秦觀詞》,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一四一頁。
[二四]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版,第二九四頁。
[二五]錢鍾書《論不隔》,原載《學問月刊》第第一卷第三期,收入《人生邊上的邊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一一年版,第四七—五十頁。
[二六]丁雨《論詩詞中的隔與不隔》,原載《民主評論》第十卷第十二期,轉引自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一頁。
[二七]就宋代而言,除阮閲《郴江百咏》之外,《全宋詞》、《全宋詩》所録關於郴江、郴州作品僅存數首。
[二八]張相《詩詞曲語辭彙釋》卷二,中華書局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六八頁。
[二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八二,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版,第八册,第三四八〇頁。
[三〇]洪邁《容齋隨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七一九頁。
[三一]趙翼《陔餘叢考》卷四一,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版,第九一一頁。
[三一]周煇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卷九,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版,第三九七頁。
[三二]錢鴻瑛《「桃源」望斷是何處——秦觀〈踏莎行>新解》,《名作欣賞》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三三]黄蘇《蓼園詞評》,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〇四八頁。
[三四]陳匪石《宋詞舉》,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一一八頁。
[三五]胡雲翼《宋詞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一〇三頁。
[三六]俞平伯《唐宋詞選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一頁。
[三七]沈際飛《草堂詩餘》卷一,轉引自《淮海居士長短句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九七頁。
[三八]楊世明《淮海詞箋注》,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六八頁
[三九]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唐宋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一七四頁。
[四〇]劉逸生《郴江誤下瀟湘去——秦觀〈踏莎行>賞析》,《名作欣賞》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四一]葉嘉瑩《唐宋名家詞論稿·論秦觀詞》,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一四一頁。
[四二]葉嘉瑩《説阮籍咏懷詩》,中華書局二〇一八年版,第六四頁。
[四三]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南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三一四頁。
[四四]程怡《元祐六年後的蘇、秦關係及其他——試論秦觀〈踏莎行>的曲折寄托》,《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〇三年第六期。
[四五]陳祖美《評李清照〈詞論>對秦觀詞的批評》,《詞學》第十五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十八頁。
[四六]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全集》第二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公司一九八〇年版,第三〇〇頁。
[四七]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一〇三四頁。
[四八]杜昭《殘陽樹還是斜陽暮——從摩崖石刻看秦觀〈踏莎行>的版本真僞》,《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〇一八年第四期。
[四九]彭剛《叙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第二二頁。
[五〇]吕思勉《歷史研究法》第六章,永祥印書館一九四五年版,第五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