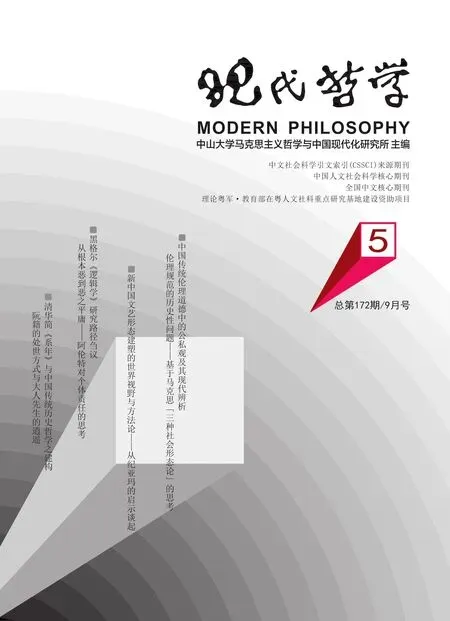中西修身之学的相遇与调和
——以高一志《修身西学》为例
沈 锐
“修身”虽非儒家所专有,但对“修身”问题给予最大重视及详细阐述的非儒家莫属。如孔子的“为己之学”,强调人要通过“修己”来成为君子(1)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中庸》以“修身”作为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2)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作为《大学》“八目”之一的“修身”更是被提到显耀位置;而在宋明理学,“修身”更是从北宋五子到朱子,乃至王阳明、刘蕺山关注的重点。相较儒家,天主教也强调教化世人,在宗教救赎之外,也十分重视道德修炼完善。特别是继承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阿奎那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培养和实践美德成为天主教思想的主流。
在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大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理解已不可忽视,东西方儒耶两大传统的对话更值得关注。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及皈依士大夫的西学东渐著作为考察相关问题提供了可能。其中,就耶儒伦理、修身问题最早展开讨论的,正是晚明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6-1640)的《修身西学》。近年来,此书已获得国内学界的关注(3)笔者是国内最早关注高一志《修身西学》的研究者之一,在《高一志〈修身西学〉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中就曾对此书相关内容做了较详尽的分析。后梅谦立、金文兵等对相关史料给予更详尽的考证。由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的《修身西学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业已出版。该注释本最大的特色是较全面地挖掘《修身西学》核心概念与神哲学思想表述的西学源流。。但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站在西学视角将其作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译本来考察,而不是在晚明思想环境下完成的合汇儒耶的专著;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文本翻译的准确性,而非调和两大思想传统的创造性。本文将紧扣“修身”问题,就中西方关注的重点,考察高一志如何理解儒家道德哲学并诠释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学,实现两大传统的融合的两学修身、齐家任务。
一、面向晚明的西学“修身”问题
高一志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其作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后继者在传教工作上的成功,并被列为“南京教案”中的“要犯”而被驱逐出境。二次入华期间,他使天主教在山西迅速发展,被尊为“山西开教宗徒”(4)[意]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92页。。与此相对,他在著书传道方面也不逊色。费赖之曾盛赞他:“精研中国语言文字,欧罗巴鲜有能及之(高一志)者,因是撰著甚多,颇为中国文士所叹赏。”(5)同上,第88页。高一志在华完成的19本中文著述,第一次在把西方教育学、伦理学等相关思想引入中国,在扩展在华西学外延的同时,也在内涵方面促进了中西进一步融合。这些著作多为偏安绛州时所完成,适逢明末战乱,其思想、著作在当时并未产生过大的影响。
出版于1637年前后的《修身西学》是高一志晚年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此书基于耶稣会传教团体的通用教材,即在葡萄牙耶稣会学校(6)可因布拉(Coimbra)学院创建于1290年,是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学。埃武拉(Evora)大学建立于 1559 年,是由当时即将继位葡萄牙国王的Henrique创办的耶稣教会学校。使用的一系列《讲义》(CommmentariiCollegiiConimbricensisSocietatisIesu)中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相关内容,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学。如果仅将它当作一份译本来研究,容易低估其价值。传教士并不是思想的首创者,多是“述而不作”,但这一“述”与现今的“翻译”有很大不同。与译本忠于原著的初衷相比,传教士的著作有更强烈地面向现实的目的性。晚明传教士传播或士大夫吸纳西学都有较强的目的性。徐光启就曾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7)[明]徐光启著、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历书总目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页。,士大夫的目的是为了借西学解决晚明社会的实际问题而实现“超胜”。因此,标榜“实学”的传教士自然不是单纯的翻译,其带来的西学必然要解决晚明思想和社会存在的问题,如此才能与士大夫的需求对接,进而促进传教事业。在具体操作层面,传教士并非逐句翻译,多是将其所理解的西学用晚明的论述方式进行重新整合表述。值得关注的是,在这“述”的过程中,中西思想实现了动态互释,不断革新其原有的含义。具备上述特点的《修身西学》的创造性更为明显,除作者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外,书中对中西概念的译介及论述的整合十分成熟。它与《齐家西学》《治平西学》共同构成“义理之学”,指导韩霖等皈依士大夫在山西地区开展的“两学修身”“两学齐家”“两学治平”的道德实践。基于上述特点,可将《修身西学》看作是一本基于西学思想源泉、立足晚明思想实际、探讨晚明核心问题、并极具实践指导意义的西学著作。
二、从Ethics到“义礼之学”“修身之学”
高一志在《修身西学》中延续了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进一步调和耶儒思想,将耶儒对话推向新高度,具体表现为关切晚明士大夫道德实践的具体问题、直面当时学术主流的宋明儒学等方面。与之前传教士更多讨论形而上的本体论、宇宙论问题和相对简洁的介绍西学伦理思想相比,高一志在耶儒融合的深度和细度方面都有较大提升。
如何为失序的晚明社会重建秩序,是阳明后学、理学正统及佛道各家面对社会动荡失序时都必须关注的问题。外来的天主教自然无法置身事外,道德实践方案比本体论和宇宙论对天主的证明更能吸引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多是认为天主教是解救晚明危局的良方才选择皈依。入华伊始,传教士就重视对西方伦理思想的传播。基于伦理道德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传教士希望借由伦理问题的中西融合来推动耶儒对话,即便他们的论述只是简洁的介绍。例如,罗明坚的《天主实录》着重介绍基督教伦理道德标准,利玛窦的《交友论》则最早对西方伦理思想的专门问题展开论述,《天主实义》则开始涉及古希腊和中世纪伦理学的部分思想。据统计(8)此结论根据《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提供的数据得出。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1584-1790年间在传教士的437本译著中,伦理(包含教义方面)相关著作就达270种,可见传教士对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高一志的《修身西学》正是迎合了士大夫在道德实践方面的要求。它在系统地介绍西方伦理学思想过程中,更关注的是具体的道德实践之法,是传统儒家政教和佛教所不及的修习切己的“必治之术”工夫(9)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155页。;在很多方面也借鉴了晚明劝善书特点,极具晚明时代特色。
《修身西学》所带来的道德实践思想正是西方的伦理学。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并没有伦理学概念,今天的伦理学来自日本学者对“Ethics”的翻译(10)最早是严复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道德哲学时》译作《进化论与伦理学》。方朝晖:《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实际上,“Ethics”进入中国要早的多,首次将它引入中国的就是高一志。在《西学》(11)此文收录于高一志的《童幼教育》(1632)中。参见[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编注、谭杰校勘:《童幼教育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年,第216—221页。一文中,高一志介绍西方“Philosophy”(音译“费罗所非亚”,意译“格物穷理”)概念时,将“Ethics”(音译“厄第加”,意译“义礼之学”)作为前者的一部分。他采用的“音译”和“意译”两种译法,是晚明传教士翻译西方概念时的常用方法。但在展开论述时,传教士多使用“意译”,以降低中西学之间的陌生感。例如,在《修身西学》,高一志就只使用“义礼之学”,丝毫未提“厄第加”这一译名;在《西学凡》中,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也曾用“义理之学”来指西方伦理学。但在宋明理学语境中,“理学”既可以指“义理之学”,也可指“性理之学”,还可以两者兼指,而“义理之学”与“性理之学”又可以互通。艾儒略的“义理之学”涵盖的外延已超越了伦理学所指,高一志“义礼之学”的翻译更为精准。“义”“礼”都是儒学的重要概念,但“义礼之学”在各类文献中未曾出现,以此来翻译伦理学,读者即知道其与中学之同,也明白其和理学有异。
《修身西学》之前的西学伦理著作,多是通过修辞学介绍蕴含西方伦理思想的格言,或集中介绍西方伦理思想的某些方面,却没有系统全面地介绍西方伦理思想体系。更多展示出西学的“所然”,而没有揭示出其“所以然”,自然无法实现其在“所以然”层面给儒学以补充的愿望,其结果只能是“以耶补儒”,而无法实现“耶儒互补”意义上的“合儒”。高一志面对更宽松的西学传播环境和以传教士为中心的话语团体,思考的是如何在晚明儒学思想背景下构建出完整的西方思想体系。而且,他对儒学的理解也较前辈更深入,已从对儒学笼统的认识,转向对宋明儒学论辩问题予以适当回应。当然,他对宋明儒学的理解仍停留在表面,难以全面进入理学话语体系辩难的核心问题。但对儒学认识上的转向,让传教士合汇中西、构建极具自身特色的思想体系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着手理解儒学内部分野源自利玛窦,强调“古儒”“今儒”之辨。为树立天主教思想合法性依据,他援引了“古儒”关于宇宙论方面的论述,对“今儒”的心性论讨论则不屑一顾。他对“今儒”宋明理学的问题鲜有正面回应,更多是站在“古胜于今”的角度进行批驳。其继任者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59-1654)开始直面晚明理学传统,对《性理大全》有较全面的研读,但他认为耶儒在根本上不可调和,其后续对中学整体上激进的反击几乎将耶稣会在华的传教事业逼上绝境。亲历了“南京教案”的高一志与前辈不同,他真切体会到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在社会中的影响,晚明的社会价值崩塌后带来传统权威的撼动也绝非利玛窦等人判断的那般严重。利玛窦构建“儒家一神教”虽以恢复古儒为说辞,但其强调的本体宇宙论问题已非晚明儒学发展所关切的问题,对彼时儒生而言,如何纠正阳明后学空谈心性的流弊才是更重要的。利氏看似成功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主流士大夫多对天主教思想不置可否、漠不关心,少数也只是对西方科学产生兴趣。高一志已认识到无论是在南京都城还是在绛州县城,都必须更谨慎地处理耶儒对话,进行“耶儒互补”,仔细处理耶儒各个思想概念的解释工作,进而通过切实指导士大夫修身工作来逐步巩固传教成果。
三、《修身西学》亲儒特色
高一志最终希望通过著作调和耶儒思想,实现中西融合、中西互补。西学更重逻辑性和系统性,为减轻晚明读者的陌生感,高一志等传教士在概念译介上选择更贴近中国经典语词。《修身西学》处理大量“西学”概念时,首先袭用中国思想的固有概念,将概念的辨析工作推到最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搁置“辨异”,以此主动造成中西概念的“混同”。其中,高一志使用了大量儒学概念来解释西学思想,如“格物穷理”(12)[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143页。“良善习善”(13)同上,第193—194页。“气禀”(14)同上,第208页。等儒家术语,偶尔也采用“心光现”(15)同上,第181页。等佛教用语。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他意图呈现出西学所要讨论的概念在本质上与中学并无差异,但实际上他使用的很多儒家概念,在讨论中都赋予其全新含义。例如,他使用的“仁德”“仁者爱人”“亲亲之爱”等儒家话语,但要讲的“仁德”实际上局限于类似儒家“孝德”的“Pietas”(16)同上,第275页。。对于这些概念,高一志采用的是一种“存同取异”的翻译方式,即在使用概念时不拘一格地“袭用”,在讨论概念时则细致入微地恢复其本身含义(17)对“求同存异”的翻译方式的分析,参见沈锐:《高一志〈修身西学〉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此外,高一志接引用的儒家经典也成为其论证的依据。例如,《修身西学》第1卷“义礼之序”(18)[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145页。及“意为身修之本第一章”(19)同上,第146页。就是对《大学》“三纲八目”一段的转述;第7卷“智之属德第五章”中的“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20)同上,第222页。引自《孟子·离娄下》;第3卷“司爱总督众司如何第三章”中的“又曰:志之所至,气必至焉”(21)同上,第170页。,源自朱熹《论语集注》的“盖为仁在己,欲之则是,而志之所至,气必至焉”(22)[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0页。。
借用儒家概念来解释西学思想绝非高一志首创,从罗明坚的《天主实录》开始,传教士就热衷于这种表述方式。在袭用儒家术语时,某些情况下传教士认为在这些概念的表述上耶儒并无二致,但更多时候传教士并非完全认为术语的真正含义与其所要表述的西学思想完全吻合,往往是期望通过实现耶儒概念上的混同来回避一些难以阐释清楚的问题。因而,选取概念的考量底线是这些术语的本身含义是否与西学思想存在明显分歧,往往只要不矛盾便可使用。袭用的最直接功用是让儒家术语充当西学概念的翻译,使讨论可以迈出第一步,至于“袭用”带来的误会则留给后续讨论逐步解决。即便无法解决,对于根本目的在于传播信仰的高一志等传教士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也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但“援古儒”“斥新儒”的利玛窦多用《尚书》《诗经》为思想依据,偶而引《论语》,鲜有《孟子》,对朱子、阳明的思想内容讳莫如深。高一志对“新儒”则持开放态度,经常直接引用朱子的观点作为论证依据,“理”“气”“血气”“心性”等理学概念也贯穿其中,借宋明儒学论辩讲解西学思想的内容也多有呈现。这些理学概念显然比“上帝”“天”等更接近晚明士大夫的话语。高一志不仅对待理学较之前的传教士更宽容,从其著作中较少直接批判佛教,也可看出其对待佛教的态度也是较宽容(23)相较而言,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庞迪我的《七克》等著作都有大量直接批评佛教的内容。。高一志这种较其他传教士更为缓和的态度,应该与其对“南京教案”的反思有直接关系。纵观整个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过程,不难发现西学对理学和佛教的批驳很难撼动二者的根基,而理学和佛教对于西学的反攻往往给其带来致命打击。高一志采取这种态度无疑是经历惨痛教训后的明智选择。
四、作为中西方道德实践核心的“修身”问题
基于对儒学整体认同,高一志合汇中西的工作得以展开,其切入点正是双方关切的“修身”问题。“修身”在儒学特别是宋明儒学中的重要性无需赘言。高一志的《修身西学》希望告诉晚明士大夫,修身在西方道德哲学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所贵义礼之学者三:曰身、曰家、曰国。人生非止为己生也,兼为家国,然必为已而后可以为家国也。则身之先修焉必也。盖诸实学,由内及外,由近及远,修身者剖诸义礼,诸德之源也……而修身为本矣,是学之序也。”(24)此内容与《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致知在格物”采取了相同的进路,后文提及的诚意也是如此。由于高一志已经区分了性理之学和义礼之学,修身之学以“诚意”为始,而“格物”属于性理之学的讨论范围。这也是高一志在山西提倡的两学“修身、齐家、治国”传教策略的体现。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六篇中,也重点论述了有关“诚意”的问题。参见[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145—146页。“义礼之学”大旨不外乎是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等问题,也就是宋明理学所关注的工夫。基于相同的工夫,“义礼之学”的目的是使人成圣、成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在儒家伦理体系中有着深厚的基础。高一志显然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士大夫,西方“义礼之学”和儒家教化都以修身为本,修齐治平为进路,实现人的完善(成为君子),因此二者在大方向、基本进路上并无区别,而细节上的不同恰恰可以实现二者的互补。经高一志的表述,“义礼之学”和儒家要解决的是同样的问题,所谓西学更多是从“实学”的角度给儒家道德实践以更多补充,而非要变革其根本。
在“修身”大纲下的具体表述可见高一志对中西思想问题考量的细致,“诚意”的论述就是一例。确定修身为本后,高一志提出“东西圣贤,胥先诚意”的判断。此处“诚意”为先,“格物致知”在后。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强调《修身西学》一书重在关注以“诚意”为代表的“义礼之学”(practical studies),而以“格物致知”为代表的“性理之学”(theoretical studies)则为辅助(25)[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143—144页。。他对“诚意”“格致”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亦与宋明理学的部分观点相契合。例如,《传习录》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26)[明]王阳明著、[美]陈荣捷编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54页。“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27)同上,第111页。在朱子那里,诚意工夫固然是关键,但必与格物致知结合才能成为一体完整的工夫,无格物致知之功则义理无由明。
单看“修身为本”“诚意为先”只能算是亲儒,远谈不上合汇耶儒,合汇耶儒的关键在于以儒家切入及其后的西学解读。在“诚意”上,相较朱子、阳明重“诚”,高一志则重“意”,展出“意之所向”,来讲其所要谈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重要的“目的”论:
凡物性皆有定则,造化运动有所向、所安焉。环中四行、交力运造:火向上,不获所不止;土向下,得其位始定;水浮土上;气乘土水负火。非至所向之域,虽强之不安也。生觉之品,凡饮啄之宜、阴阳之匹、孕字之时,畏矰缴薄青冥、驚网罟、若匿山薮无谬妄,无所向者,岂超万类之灵民反不然乎?观农之春苦秋劳,志稼穑也;圃之手植手种,志蔬羹也;商之牵车牛服贾四方,赢馀也;工之相陈以事,相示以巧,志既禀也;士之昼夜剧神,春秋匪懈,志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孰谓人意无所向者哉。(28)[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147—148页。
对于“人意有所向”(29)《修身西学》第一卷第二章中,高一志已将修身之本归于“诚意”,因此此处讨论的“人意所向”问题,实际上就是“人所向”的问题。的证明,高一志采取了经验的方式:通过总结物质界(四行的运动(30)高一志在《空际格致》(1633)一书中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四行说”(火、土、水、气),希望借此取代中国传统的“五行说”。)、动物界(鸟兽的自然本性)和人类社会(农商工士各行业的目的),得出世间万物都有目的这一原则,进而证明“人意必有所向”这一结论。虽然这种从经验出发的证明并不严谨,但这种论证无疑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在确定了人有所向之后,接下来则是“所向者何”的问题。高一志的回答是“所向者为好美”。而“好美者何,宜于性之谓也”的解释,无疑概括了亚里士多德“agathon-the good”在此问题上的准确含义。在《修身西学》中,高一志对good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好美”和“善”。通过这两个概念在《修身西学》首次出现的语境来看,“好美”从整体指本性完善之“善”,而“善”更多强调伦理道德之“善”,与“止于至善”类似。不过在后文讨论具体问题时,高一志多用“善”泛指这两方面的含义。高一志虽然未将两种译名的区分贯彻使用,但他以中释西的方式转述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还是比较注重概念的准确性,对语词的使用也十分谨慎。万物都以“好美”为目的,那么人的“好美”是什么?这是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这里,高一志要将问题引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重要概念“eudaimonia”(31)“eudaimonia”今多译为“幸福”,《修身西学》译为“安福”。的讨论。对于人的最终目的“安福”,高一志并未做太多论述,因为中国传统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尚书·洪范》就提出“所好者德福之道”“言人君所好者,道德为福”。虽然可能对于“德福”关系和终极真福的具体含义存在不同理解,但对人的最终目的是“福”这个问题,中西思想并无本质差异。
至此,高一志对于“意”的理解虽说阐明了亚里士多德的部分伦理思想,但按儒学思想脉络也并未有过多新意。他的解读最重要的是在此处首次引出西方哲学的“自由意识”说:“性有固有之善,有为恶之权……木石禽兽无灵才,不能自主,无善恶功过者也。灵民自有专有权,累功聚慝由己焉。”(32)[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194页。这种以自由意志为道德责任依据的说法,在当时的中国有着独到的新异性,而这恰恰对晚明士大夫天主教徒产生巨大的吸引力。(33)韩霖在《铎书》中曾介绍高一志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参见[明]韩霖著,孙尚扬、肖清和校注:《铎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善恶完全由人自己做主,相应的道德责任也完全由自己负责。高一志更是借用了利玛窦的“三司”(34)[意]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6页。概念来深入分析自由意志的问题。他指出,人由神、形组成,其中神是主导,形从之。“神”又具备三种主要功能:司记(主记忆)、司明(尚真实)、司爱(尚美善)。明爱二司共同作用,成为“生人万动万行之源”(35)[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167页。。但明爱二司的地位不是并列的,“司爱者管握人之诸权,司明者惟斟酌较量而已”(36)同上,第169页。,也就是说人最终的择善择恶由司爱决定,司明仅仅起到辅助作用,司爱发挥的作用正是人的自主性的体现。但为什么会有善恶的不同选择?高一志的回答是司爱有兽心、人心两部分。兽心又称血气司爱,跟从“觉司”,以“私好美”为对象;人心又称志气司爱,跟从“灵才”,以“公好美”为对象。“兽心”是人和动物共有的,“人心”是人所特有的。对于“一时一事”,只能由二心之一决定,要么跟随兽心,则“逆礼义”,要么跟从人心,则“重礼义”,最终为善为恶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强调恶非实体,而是善的缺乏(37)“是恶者,非物之实,善之无耳,犹死非实物,乃生之无也。人不能操此具之心以成善,则善无而恶有矣。”参见[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194页。,是天主教对善恶的问题的一贯看法,这一观点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著作中都有所涉及,高一志介绍西方正统伦理思想体系自然也需强调此点。基于此,“兽心”并非是恶的,也是人本性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人心”没有发挥其作用,才让“兽心”越权统领整个“爱司”,体现出一种相对于“至善”本体反向的违理从恶。虽然这一思想在西方有其渊源,但结合对儒家术语和表述方式的袭用,高一志关于人心和兽心的讨论,有较明显的借鉴宋明理学阐述“人心道心”关系讨论的痕迹。同样,在谈到如何使二司各守其分时,高一志给出的也是“以理服欲”的理学式答案。
不难发现,高一志完全是用儒家的论述方式、袭用儒家的术语,来论证一个在儒家传统中并未被揭示清楚的问题。其实,朱子对于“慎独”主体之“独”的阐释,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主体的责任问题。高一志在“意”的问题上引出的“自由意志”,并非是完全在儒家思想体系之外引入的,而是通过以西释中让儒家思想体系中一些被忽略的问题凸显出来。韩霖等士大夫之所以热衷于介绍自由意志理论,也是因为这一问题在儒家中并未予以明确的表述,因此儒家道德体系并非像一些儒生相信的那样圆满自足、毫无亏欠,也需要一定的补充(38)[明]韩霖著,孙尚扬、肖清和校注:《铎书》,第32页。,而中西互释正是在这些论述过程中得以体现。
除了“修身”观点的论述,在概念的翻译上,《修身西学》也展现独到之处。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中最重要的概念“mean”,正是借由《修身西学》首次进入士大夫的视野,也是高一志用儒家重要概念“中庸”来对“mean”进行解释(39)在《卷六》“德之中庸第三章”中高一志重点讨论此问题。参见[意]高一志著,[法]梅谦立、谭杰、田书峰编著:《修身西学今注》,第206—208页。。这体现了《修身西学》“求同存异”的翻译方式:《修身西学》整体上还是从儒家“执两用中”的角度来讲强调其无过之、无不及的特点,也肯定了“中庸”作为一种至德的面向,在这些层面上耶儒并无太大差异。但儒家的中庸除了具体德性方面的意义外,也具有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对此,高一志采取的策略是避而不谈。高一志的创造性在于抓住了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体系中“mean”这一重要概念和儒家经典中“中庸”这一至德的相同点。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说极大拉近了耶儒的距离,为更深层次的交流奠定了基础。而且,高一志挖掘出的共同点决非粗略的混同,而是经过深入分析后的契同。同时,在保存“中庸”和 “mean”之“同”后,高一志也揭示了亚里士多德论述的“中庸”作为各种恶的对立面这一层意义,而这层意义在儒家传统中一直都没有明确的阐发。
《修身西学》“存同取异”的翻译方式:介绍西方思想概念时采用的都是与儒家相同或相近的术语,然后通过进一步的论述为这些术语赋予西学新的内涵。“存同”是传教士介绍西学思想时普遍采用的办法,主要区别于我们今天对于西学的翻译,类似于佛教传入时的“格义”。传教士在介绍西学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儒学的认同,因此更多的是从传统中寻找类似的思想概念来表述西学内容。“取异”主要是考察在以中学概念表述西方思想后,是否再进一步揭示西学的特有含义。例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借用儒学既有的认知结构的适当概念来解释西学的新概念,不过在完成这项工作后,利玛窦就立足于在儒家经典中寻求对既有概念的支持论断,从而淡化了对这些概念再解释的工作。像“天主”这一概念,利玛窦就是借用先秦“上帝”的概念来“存同”,而之后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在先秦典籍中寻找“上帝”的有关论述。实际上,采取“取异”与否主要由传教士的处境决定。到了高一志二次入华时期,情况发生转变,通过早期传教士的努力,传教活动获得官方的认可,并形成自己的话语团体。因此,高一志等人可以进一步推进西学思想的传播,同时入教、亲教士大夫也需要传教士揭示西学不同于中学的特质。这时,如果不进行“存同”之后的“取异”,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如果西学和中学无异就无法实现对中学的补充,西学也就没有了传播价值。
《修身西学》首次将西方伦理学系统地介绍给晚明士人,并围绕“修身”这一中西共同问题,通过概念上的中西互释、论述上的互相借鉴将耶儒互补推向新高度。特别是书中对宋明儒学的回应,对儒学核心概念的辨析,进一步提升了中西双方对话的深度。由于客观原因,该书并未像《交友论》《七克》一样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但韩霖等晚明士大夫以《铎书》等著作的方式,从思想层面对《修身西学》进行回应,足可以体现高一志思想的价值。同时,该书介绍的西方伦理思想被用于官方的道德教化活动,证明高一志在书中的中西互释和彰显西方伦理学“实学”特点方面的工作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