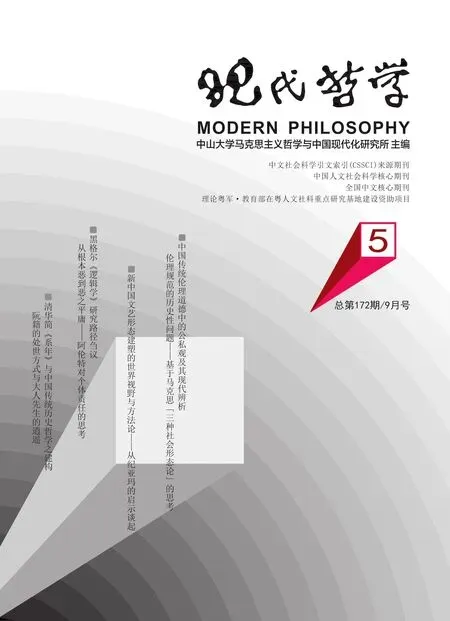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
——阿伦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
刘文瑾
1948年,阿伦特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描述了纳粹运动的“绝对恶”或“根本恶”,其分析契合人们对纳粹主义的震惊感受,使“绝对恶”或“根本恶”成为经典命题。阿伦特借用了康德的“radical evil”表述,但其含义已与康德有很大不同。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使用“radical evil”来讨论那种既不听从义务的要求、也不遵循道德法则的倾向。他用radical来限定evil,使用的是radical的词源学含义“根部的”,试图表明恶根植于人性,特别是根植于人自发选择的“任意性”(Willkür)的败坏。但在阿伦特那里,radical evil主要指那种消除人的自发性、把人变为“多余”的现象,并未直接涉及对行为主体的道德评价,在相当程度上偏移了康德的概念(1)Ha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p.459;参见[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3、33、254页。。
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发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下文简称《艾希曼》)一书,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视为丑闻。阿伦特对艾希曼的看法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她看到的不是一个残酷、冷血、自觉的反犹主义者,而是一个“正常”“普通”的行政性屠杀代理人、“恶之平庸”的典范。“恶之平庸”揭示人类处于一种新的道德伦理困境,阿伦特认为过去的神学、哲学和社会学解释不足以回应它。这一困境体现为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使人成为多余的“根本恶”现象;另一方面,是施害者(甚至包括受害者)的“无思”与道德自欺,以及阿伦特后来在与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通信中看似矛盾的说明——“恶没有深度”(2)Hannah Arendt, “‘A Daughter of Our People’: A Response to Gershom Scholem”,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ed. and intro. by Peter Baehr, Penguin Books, 2000, p.396.。在此,阿伦特说:
你十分正确:我改变了看法并且不再谈论“根本恶”……现在我的确认为,恶不再是“根本”,而只是极端(extreme)。它既没有深度,也没有任何恶魔般的维度。它能过度生长并污染整个世界,只因为它如同霉菌一般在表面蔓延。如我所说的,它“抵制思考(thought-defying)”,因为思考试图到达某种深度,进入根部。而思考面对恶,就会受挫,因为那儿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并能是根本的。(3)Hannah Arendt, “‘A Daughter of Our People’: A Response to Gershom Scholem”,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p.396.
如何理解阿伦特关于恶的这两种貌似截然相反的论述?这两种看法之间是否具有相容性?她是彻底还是部分改变了看法?此种改变说明什么?学界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讨论,主要观点可分为相容说与改变说,前者的代表是一位阿伦特思想的重要研究者理查德 J. 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后者的代表则是阿伦特的学生及其最重要的传记(4)[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作者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但他们都没有简化这个令人费解的改变。本文在基本认同相容说的基础上,尝试分析阿伦特改变的原因,认为她的改变主要涉及对恶的动机的理解。基于对个体责任的考量,她既拒绝黑格尔式神义论的诱惑,也放弃根本恶中隐含的神学维度,而试图仅从世俗主义角度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可能性进行探求。
一、变中的不变:恶的现象与后果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描述了大量极权主义制度中的恶的现象,称之为“根本恶”。12年后,在《艾希曼》中,虽然阿伦特用“恶之平庸”描述艾希曼,不再使用“根本恶”,但她从未在该书中否认根本恶的存在。正是由于根本恶的存在,她才能在书中对艾希曼的“反人类罪”进行裁决。“反人类罪”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特性即人类多样性的攻击。从法律角度定义的罪的实质,正是根本恶现象。在阿伦特那里,根本恶主要指那种使人变成多余的现象和制度,而非对主体道德罪责的评价(5)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t)也认同此观点。参见[英]卡诺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陈高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注1。。因此,关于阿伦特对肖勒姆的回复,我们似乎不必照单全收。基于当时激烈的论战气氛,她的措辞显然包含了某种夸张(6)理查德 J. 伯恩斯坦也认同此观点,参见[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根本恶》,第266页; R. Bernstein, “Did Hannah Arendt Change Her Mind?”, Hannah Arendt: Twenty Years Later, ed. by Larry May and Jerome Kohn, Boston: The MIT Press, 1996.。
事实上,“根本恶”和“恶之平庸”的彼此相容不仅体现在《艾希曼》,甚至早就出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当阿伦特描述极权社会“群众”的性格时,她已深描了群众的“市侩”(philistine)(7)Ha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p.337-338.与“拔根”(uprootedness)(8)Ibid., p.475.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别用过rootlessness(无根)与uprootedness(拔根)两个词。前者多用于描述种族主义与部落种族主义的精神状态与形成原因,即由于失去传统共同体社群的责任感而导致的以当下狭隘的土地或血缘意识为抱团理由的状况。(See ibid., pp.196, 197, 232, 236, 239, 417.)特性。这种“市侩”与“拔根”与艾希曼在阿伦特笔下体现出的平庸与人格肤浅、不能从别人的角度进行思考是一致的。“市侩”指那种一切考虑仅以私人利益为中心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拔根”是极权社会群众的生存处境,他们失去作为居间世界的公共领域,而处于孤独(lonliness)的原子式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意味着缺乏来自他人的承认和保障,首先就是缺少我与他人的共通感(common sense)。恰是那些由于孤独、“拔根”而无“家”可归之人,最容易在虚无主义驱动下成为将一己私利视为一切的“市侩”。如此,“市侩”与“拔根”两种特性便彼此强化,具有共生性。“共通感规范并控制其他一切感觉,若无共通感,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的感觉中,而这种感觉是不可靠并带有欺骗性的。”(9)Ibid., pp.475-476.因缺乏共通感而无法从别人的角度进行思考,是阿伦特笔下艾希曼无思的原因和表现。在此意义上,恶之平庸亦是恶的无根,这一点确如阿伦特在对肖勒姆的回复中所言。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将群众有组织的孤独状态比喻为一场对荒漠的动员、结果是那吞噬一切的沙尘暴的掩埋(10)Ha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478.。如果将此比喻与上述意象进行比较,便不难理解阿伦特在此形容的恶之平庸的状态:无根而迅猛扩散,如霉菌般在事物的表面繁衍弥漫,窒息并破坏整个生态环境。
作为相容说的著名代言人,理查德 J. 伯恩斯坦为说明阿伦特从未将“根本恶”等同于动机上的恶魔性,而后在写作《艾希曼》时发生实质性转变,特别强调阿伦特与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在1946年10月《极权主义的起源》写作期间的一次通信(11)[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根本恶》,第261—262页。。在此,雅斯贝尔斯提及对“恶之平庸”的看法,阿伦特大致赞同且在《艾希曼》及对肖勒姆的回复中采用了某些类似表述。关于纳粹罪行能否从法律上的“犯罪”范畴进行理解,阿伦特认为纳粹罪责逾越和粉碎了一切现行法律体系(12)实际上,阿伦特的这一观点贯穿始终,也体现在《艾希曼》结语部分,不过此处她强调艾希曼之流是“新型罪犯”。,雅斯贝尔斯则认为这种评价不太合适,会使纳粹罪责带上“伟大的”恶魔色彩。雅斯贝尔斯说:
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事情的完全平庸的性质,看到它们庸常的琐碎性,因为这是它们真正的特点。细菌可以造成它们席卷各国的流行病,但它们不过仍旧是细菌。我认为丝毫有关神话与传奇的暗示都是可怕的,而所有不确定性都是这样一种暗示……你的表述方式几乎已经走在诗歌的道上了。而一个莎士比亚式的人永远也无法为这些材料提供充分形式(他的本能的审美感将会歪曲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会试图做出这种努力。(13)[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根本恶》,第262页。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1926-1969, ed. by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 from Germany by Robert and Rita Rimb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2, p. 62.
阿伦特给肖勒姆的回信中也将恶比喻为在表面蔓延的霉菌、能过度生长并污染整个世界,在《艾希曼》中也曾将艾希曼与莎士比亚描写的著名恶人进行对照并否认其相似(14)[美]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安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306页。,于此不难看出雅斯贝尔斯意见的痕迹。而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的回复也表明,虽然她未必完全改变自己的看法,如在《艾希曼》中仍坚持纳粹罪行作为“反人类罪”而相对于“反犹主义”的“超越性”,但已部分接受了雅斯贝尔斯对纳粹恶行之庸常性的看法。阿伦特说:
你说我思考的纳粹行为具有“超越罪或无罪”的性质,这番话大体令人信服;也就是说,我完全意识到,我迄今为止所用的表达方式危险地接近于“恶魔般的伟大”,而这是你我都彻底拒绝的。尽管如此,一个动手杀死老姑妈的人和一群建造生产尸体的工厂而根本不考虑其行为的经济利益(放逐对战争后果有破坏性影响)的人毕竟有区别。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我们必须抵制将恐怖神话化的冲动,而考虑到我本人也不免倾向于如此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我尚未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或许在这一切背后发生的正是:个体的人并未出于人的理由而杀死其他人,而是一次有组织的企图,企图根除“人”的概念。(15)[美]理查德·J. 伯恩斯坦:《根本恶》,第262页。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1926-1969, p. 62.
不过,阿伦特的回复有种含混和不确定性。她承认自己“迄今为止所用的表达方式危险地接近于‘恶魔般的伟大’”,并同意这是应当改变和放弃的,但又强调的确有种无法理解的恶发生了(第二句话)。她对理智上知道“必须抵制将恐怖神话化的冲动”和事实上“我本人也不免倾向于如此表述”之间存在一种无奈,犹如一个无可避免的错位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尚未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引文最后一句话表明,她只能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和一种不直接回答问题的描述来回复雅思贝尔斯的批评。这个描述正是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根本恶”的根据。
理查德 J. 伯恩斯坦认为阿伦特的回复表明,“与雅思贝尔斯一样,阿伦特拒绝任何‘恶魔般伟大’的说法,也拒绝以神话或审美的方式描述犯下根本恶者的意图”(16)同上,第262—263页。。如果仔细推敲她的话会发现,其实未必如理查德 J. 伯恩斯坦考虑的那么简单。或许更完整的理解是,阿伦特在承认纳粹恶具有动机上的某种庸常性之时,亦认为这种庸常性仍有某种非同寻常之处。此种非同寻常不仅在于其后果的前所未有、闻所未闻,亦在于其道德上盲目自欺的独特方式,这在阿伦特看来迥异于传统对恶的理解。这种道德上的盲目自欺借助某种意识形态展开,如同她在后来增补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3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中所进行的分析。“恶之平庸”便是对这种非同寻常的“平庸”的表达。在此意义上,如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正确指出的那样,“恶之平庸”与“根本恶”是相容的,而且正是经由“恶之平庸”而铺设了“根本恶”这种使人变为多余的现象,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得到深刻揭示,只是阿伦特对二者间的关系没有十分清晰的理解与表述。
二、对神学传统的持续拒绝
1951年,雅斯贝尔斯读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序和最后几章后,在给阿伦特的回复中写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雅威(Jahwe)难道不是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很远了吗?”对此,阿伦特在同年3月4日回复说:
几个星期以来,你的问题“雅威难道不是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很远了吗?”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想不出答案。对于我自己在最后一章提出的要求,我同样也没有答案……事实证明,恶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本得多。客观地说,“十诫”并没有写到现代罪行;或者说:西方传统一直有这种先入之见:人所能做的罪大恶极之事出自“自私”之恶。但是,我们知道,最大恶或根本恶与这种人性可理解的作恶动机不再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根本恶究竟是什么,但在我看来它与下述现象有关:把人变成多余的人。(17)[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根本恶》,第253页。
这次通信更清楚地表明:阿伦特不仅拒绝以“自私”这种惯常视角来解读根本恶,亦拒绝基督教神学。几年后,她给《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修订版(1958)增添了一段话,否定恶作为人的反常意志或魔鬼的堕落属性,再次表明她认为哲学与神学传统完全无法思考根本恶现象的主观动机。
就我们整个哲学传统自身而言,我们无法想象“根本恶”。这对基督教神学和康德也是一样。神学甚至承认魔鬼本人有一个天使出身。至于康德,就其造出“根本恶”一词而言,他是唯一至少考虑过根本恶的存在的哲学家,然而他很快便用“反常的病态意志(perverted ill will)”这一具有可理解性动机的概念来理性化根本恶。所以,实际上我们无法指望任何资源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它以超强的现实力量直面我们,并打破了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标准。只有一点似乎是可辨认的:根本恶与一个制度相关,在那里所有人都同样是多余的。(18)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459.
以上两段话可将“根本恶”的内涵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涉及对根本恶的内在动机与精神品质的定性,阿伦特对此除了强调恶的前所未有和不可理解,坦承“我不知道根本恶究竟是什么”之外,逐渐明确拒绝了恶的传统根源与深度,为她后来转向“恶之平庸”做了准备;另一方面,是她对根本恶的现象和后果进行的描绘,如与某种特定制度相关、把人变成多余的,这是在《艾希曼》中同“恶之平庸”并行不悖的事件背景。如果我们同意理查德 J. 伯恩斯坦的意见(19)[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根本恶》,第252、266页。,不把她关于恶的思考简单归类为“根本恶”和“恶之平庸”这两个标签,并以其中一个来截然否定另一个,那么阿伦特的改变就只是在对恶的内在动机和精神品质的考量方面,从“不知究竟是什么”并否定传统说法的含混悬搁状态,转向对“恶之平庸”的确定。“恶之平庸”主要针对个体内在动机和精神品质方面的平庸与盲目,并未取消“根本恶”在现象和制度方面的所指。
三、以恶之平庸化解恶魔神话
那么,阿伦特为什么以“恶之平庸”取代自己过去对恶的内在动机和精神品质问题上的踌躇?她的改变既出于与当时一些德国知识分子,如雅斯贝尔斯、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以及她的丈夫布吕赫(Heinrich Blücher))等类似的对“不可战胜的恶魔神话”及“无人应当承担罪责”的忧虑,更源于其思想深处对恶的神义论诱惑的拒绝以及对政治道德的新探求。这种政治道德要求从彻底世俗的个体责任和判断力角度来面对恶的问题。
关于阿伦特最初从谁那里受到“恶之平庸”想法的影响,扬-布鲁尔的看法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不同,她认为阿伦特是通过布吕赫而受到布莱希特的影响(20)[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360页。伯恩斯坦后来也补充说,除雅斯贝尔斯外,布吕赫很有可能是使阿伦特采用这一观念的主要来源。(参见[美]伯恩斯坦:《根本恶》,第322页注26。)。为解释自己的戏剧《阿图罗·乌依的可抵抗崛起》(21)布莱希特发表于1941年的戏剧《阿图罗·乌依的可抵抗崛起》是一部嘲讽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作品。它虚构了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的一个黑帮如何通过无情铲除对手而获得统治权,其中的黑帮大佬们全都有其明显对应的现实指涉人物如戈林、戈培尔等,主角阿图罗·乌依则是希特勒的漫画版。它和卓别林创作于1940年的电影《大独裁者》一起成为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反法西斯文艺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布莱希特有意以讽刺手法刻画希特勒,其意图并非表现现实,而是如同他在前述引文所表达的那样,想要清理人们心中对巨大杀人罪魁常会抱有的某种危险的“敬意”。的创作意图,布莱希特在短论《关于希特勒“无法抵抗的”崛起的讽刺》中写道:
大政治犯们必须被揭露,尤其要在嘲笑者面前被揭露。他们其实还不是大政治犯,只是允许重大罪行产生的人,这两者完全不同。希特勒事业的失败不表示希特勒是个白痴,他事业的规模也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伟人。如果统治阶级允许一个小流氓成为一个大流氓,那在我们的历史观里面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位置。他成为一个大流氓的事实,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产生了重大后果,并不给他的地位添加什么……人们会说,悲剧与喜剧相比,是在以一种不那么严肃的方式处理人类的灾难。(22)Bertolt Brecht, “Notes”, The Resistible Rise of Arturo Ui, trans. by Ralph Manheim, ed. and intro. by John Willet and Ralph Manheim, New York: Bloomsbury, 1981, (Format Kindle 2015). 此处引文亦部分出现于阿伦特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一文中,参见[美]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6—237页。
布莱希特意图通过嘲讽方式,破除彼时风行一时的希特勒不可战胜的神话,从心理上消解人们对这位神一般的“领袖”的恐惧感。阿伦特曾在发表于1978年的《纽约书评》采访中引用他的观点,表示在评价希特勒那样的人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无论他做了什么,即使是他杀了无数的人,他仍然只是一个庸人(23)[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360页。在上文提到的雅斯贝尔斯1946年写给阿伦特的信中,他不仅提出有关纳粹恶之平庸的观点,也说到不应将希特勒视为恶魔。See Hannah Arendt / 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p.62.。可见在阿伦特那里,根本恶与恶之平庸彼此兼容,是从不同方面对纳粹之恶的描述。
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所引发的争议相似,布莱希特对希特勒的描写即把恶当作表象的嘲讽也引起争议。有学者批评说,希特勒的真实面目被琐碎和模糊化了(24)Stern, J. P, Hitler: The Führer and the Peopl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2.。但阿伦特非常认同布莱希特的做法。在一篇批评布莱希特关于斯大林主义错误政治立场的文章中(25)[美]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236—237页。扬-布鲁尔后来指出这篇文章的原题为《为善的诱惑是可怕的》,参见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 p.376.,她仍不忘引用布莱希特关于希特勒的这几句评论并称赞道:“这比1941年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要深得多,而这种智力的精确性如同闪电一样,在对陈词滥调的普遍怨言中穿透而出。”(26)[美]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237页。或许她亦如此认同自己对艾希曼的解读。
早在1946年的《噩梦与飞翔》一文中(27)Hannah Arendt, “Nightmare and Fligh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 and intro.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4.,阿伦特就已表达了对恶魔神话的忧虑。她在提出“恶的问题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之时,亦指出“诺斯替式辩证法”是一种当下存在的最危险的陷阱。她批评战后人们对恶的恶魔化想象是出于一种从现实抽身逃离的诱惑。现实其实是“纳粹同我们一样”,“我们离纳粹没那么遥远”,但人们忍不住产生某种“文学化”、戏剧性的想入非非,将纳粹描述为某种恶魔,而这正是人们试图回避现实、不反思自身行为与责任的“不成熟”表现。更糟糕的是,这种对现实的妖魔化恰好暗合某种诺斯替式辩证法,诱惑人们想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正邪之争,而人们似乎只需站在绝对正义那边,就可以忽视对当下现实的判断与责任,等待明天注定会到来的胜利。这种对现代人极具诱惑力态度正是异端邪说以未来之善为名大行其道的沃土。在阿伦特看来,对恶魔神话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便是恶之平庸。实际上,这也是她对纳粹道德责任问题的反思上最具贡献的方面:在一个充斥意识形态谎言的世界,唯有来自个体心灵深处的洞察与责任才最真实和重要。
四、不变中的变:恶的动机与责任的世俗化
扬-布鲁尔认为,通过写作《艾希曼》,阿伦特对恶的理解的确发生改变,她“不再认为是怪物和魔鬼策划了对数百万人的大屠杀”(28)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p.367.。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不同,扬-布鲁尔倾向于将阿伦特对根本恶的内在动机和精神品质方面的理解视为恶魔性的(29)Ibid., pp.367-369.:如果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还认为根本恶是出于植根人性的某种可怕魔性或罪性,那么在《艾希曼》中,阿伦特则认为恶是个体自我决定的选择,取决于每个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与人性或原罪无关;如果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恶的动机如此之深以致无法理解,那么在《艾希曼》中,动机则是多余的或者肤浅的。
我们认为,扬-布鲁尔对阿伦特的判断亦有其合理性。根据上文引用的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的讨论,我们倾向于认为,阿伦特对恶的动机问题的理解原本是含混不定、悬而未决的。她既承认应当避免将恶恶魔化,也承认自己对恶所用的表达危险地接近于“恶魔般的伟大”以及“不免倾向于如此表述”;她既否认神学传统的有效性,又无法避免表述“根本恶”时的神学色彩。这种神学色彩既体现在她大量使用诸如“炼狱”(Purgatory)、“地狱”(Hell)等富于神学意味的词汇来描述集中营的状况(30)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p.445-447.,以“一切都是可能的”等通常用于上帝的词汇来描述纳粹的“信念”(31)Ibid., p.459.,也体现在她对极权社会领袖通常来自的暴民阶层的虚无主义精神病症做出的判断。
暴民既是转型时代的“多余人”,又拥有未来的“天才”品质。作为转型时代的“多余人”,他们仇恨习俗、不甘平庸,渴望投身某个宏大未来,施展自己怀才不遇的抱负。在阿伦特的分析中,这种虚无主义的时代氛围和精神病症不仅构成暴民,而且构成文化精英的精神特征,并促成暴民与文化精英们的短暂同盟,形成虚无主义的时代命运。尽管阿伦特一再申明根本恶不同于传统神学范畴,实际上她对暴民内在动机的描述和分析在无意中进入了圣经框架。只有在圣经框架中,虚无主义的精神病症才能显现出来。在圣经叙事中,恶是人对上帝的创造和恩典的背离即“堕落”(fall)的后果。“堕落”只有就人对上帝之敬畏的偏离而言才有意义,虚无主义就是这种偏离和堕落之后的状态,纳粹运动则是人在虚无主义病症中的造神冲动。
因此,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根本恶实际上隐含着某种诺斯替主义的神学色彩。这也是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一篇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文章中所暗示的(32)Eric Voegeli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3)”,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ume 11, Published Essays:1953-1965,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显然,正如阿伦特拒绝从神学传统的角度来理解根本恶,她也不愿将根本恶视为某种诺斯替主义。这既由于她对恶之神义论的拒绝,也出于她思想的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倾向。有学者认为,“恶之平庸”可以从奥古斯丁为批判摩尼教而提出的“恶是善的匮乏”说来得到理解,实际上二者只有表面的相似性。阿伦特对恶之平庸的思考不仅是非神学性的,甚至是要去神学性的。如扬-布鲁尔所言,她只是“用一种世俗语言解释恶的私人性质”(33)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p.369.。也有学者指出,阿伦特不仅强调自己所说的恶与神学传统不同,而且还批评恶的匮乏说,认为这会使人无法看清恶的阴险面目(34)John Kiess, Hannah Arendt and Theology, Bloomsbury T&T Clark, 2016, pp.52-53.。
阿伦特之所以转向“恶之平庸”,是由于她感觉到潜伏于时代的神义论政治道德的诱惑,试图思考一种与之针锋相对的新政治道德(35)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p.374.。与那种相信“善从恶中产生”的神义论政治道德相比,这种新政治道德将格外强调个体道德判断力的重要。它要求人们不仅从个人主观动机,更要从与他人具有共通感的责任角度来思考恶,以避免主观意图与客观后果的悲剧性反差。那么,什么是阿伦特想要拒绝的神义论政治道德?她曾对神义论有过说明:一种始于17世纪的哲学家对上帝或大写存在的辩护,为了让人们的心灵与他们生活的世界妥协(36)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wo/Willing, New York: Harcourt, 1978, p.21.。笼统而言,神义论是指面对义人受苦的现实而为上帝存在进行的两难辩护:如果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存在,为何世上会有无辜受难的事发生?对此,通常存在两种辩护策略:一是柏拉图式的,强调恶的非本质性,将恶贬低为表象,例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让人把灾难视为时间因果链中的一环,而时间是非实在的,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实在,奥古斯丁的匮乏说接近于这种;二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典范,是前一种神义论的现代变形。黑格尔式神义论将恶视为事物发展的必要的部分和过程,认为作为整体的善产生于作为部分的恶,从而合理化了恶与无辜受难。黑格尔式历史哲学辩证法是近代思想与实践中的强大暗流,也是阿伦特一直与之较量的对手。这体现在她对现代问题的诸多思考中: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对“历史必然性的虚假辉煌”的批评,到《人的境况》对将政治行动误解为“制作”某物的现代世界的批判;从《艾希曼》开始对(无思的)意图之可靠性的怀疑,到与《艾希曼》几乎写于同一时期的《论革命》(37)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Viking Press, 1963; Introduction by Jonathan Schell, Penguin Classics, 2006.对神义论政治道德的反感——在她笔下,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有关神义论政治道德的悲剧舞台;最后,在写于生命晚期的《心智生命》第二部《意志》中,她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和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
阿伦特为什么严厉拒绝神义论政治道德?在她看来,神义论政治道德是那种诱惑“好人”以好意图为由,做出最坏事情的隐形机制中的润滑剂。正是这种“好人”的盲目与道德自欺,使得犹太人委员会、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纳粹分子、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包括诗人布莱希特等,都丧失了行动的正确判断力,因此她对人们在政治事务中的道德理想和同情心(好意图)抱有深深疑虑。恶之平庸总是与神义论政治道德相反相成,而道德上的盲目与自欺也正是恶之平庸的非同寻常之处。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指出:道德理想和同情心对于政治家和诗人更像是暴力的精神鸦片,而非清明恰切的判断。这在《艾希曼》中的反映便是,她试图通过对以服从善之命令为借口的“恶之平庸”的揭示,呼吁一种让人面对个人良知的思与判断力,一种不以权威、习俗和意识形态为由,回避个人责任的新政治道德。因而,阿伦特在给肖勒姆的回信中提到,她对“同情心”在政治中的使用抱有深深疑虑,并建议肖勒姆读读她《论革命》一书的第4章(38)Hannah Arendt, “‘A Daughter of Our People’: A Response to Gershom Scholem”, p.393.。
此外,恶之平庸也反映了经过对恶的问题的长久思考后,阿伦特最终选择一种彻底世俗主义的方案来面对恶的问题。当她说恶没有深度时,她不仅改变了自己过去对恶的理解,也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对极权主义制度之终极意味的理解:在“根本恶”的视野下,极权主义指涉了一种现代性内在的虚无主义潮流,这种潮流以一种总体化的统治,破坏了人类尊严,将复数的人变成多余的,应当被消灭;而在“恶之平庸”中,极权主义失去了这种终极性意味。沃格林曾批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由于未能从内在灵性角度诊断极权主义问题,产生了“理论脱轨”,致其叙事最终在理论上的无结论性(39)Eric Voegeli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3)”.。阿伦特的回应则表明了她康德式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立场:将属于私人领域的信仰与属于公共领域的政治区分开来,拒绝在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中介入信仰问题(40)Hannah Arendt, “A Reply to Eric Voegelin”,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ed. and intro. by Peter Baehr, San Diego,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3.。因此,对于虚无主义这一与上帝之死有关的后遗症,她不置可否;对于历史方向,她在反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时,主张将其留给未知与空白——新生性(natality);她在拒绝恶的神义论诱惑时,也拒绝理解恶的神学框架和救赎道路,而主张将救赎完全留给人和世界。
五、替补神义论的现代方案
阿伦特关于恶之思考的转变,于她本人而言既是一场“延时治疗”(41)这个说法来自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中专门谈论《艾希曼》一书的第八章标题“Cura Posterior: Eichmann in Jerusalem”。,即不再把恶视为有着不可理解的动机,也是一个新开端,甚至如有的学者所言是属于她自己的“神义论”,即她由此得以重新与世界这一(上帝的)造物和好并发现人有这种能力(42)Susan Neiman, “Theodicy in Jerusalem”, Hannah Arendt in Jerusalem, ed. by Steven E. Aschheim,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用阿伦特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发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43)[美]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3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阿伦特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案,提供了对神义论的替补。
“治疗”首先体现在阿伦特在《艾希曼》中试图直面和理解恶的原因。这是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表示无法理解的,但现在她相信这种理解能更好地服务于政治秩序的清明(44)[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403—409页。,并由此开始思考一种与判断力有关的新政治道德。这体现在她收于《过去与未来》一书中的《文化的危机》《真理与政治》两篇文章,也体现在她1970年的备课稿《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囿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判断力问题展开论述,仅指出:这种同判断力有关的道德考量,是她认为唯一有可能在黑暗时代中启明、抵抗极权主义的道德,也是她在晚年未竟的巨著《心智生命》中致力于阐明的新的思想方向。这种作为道德判断力的启明,如同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所言,“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些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45)[美]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3页。。对阿伦特而言,那本当源于人们的居间世界——公共领域——的启明,也需内化为个人直觉、想象力、共通感以及对存在意义的求索,成为在历史危机时刻、公共领域式微的黑暗年代里帮助个人思考判断,从而突围环境和“沉默大多数”的同化并保持独立而燃烧的支点。
阿伦特希望借助这种微弱又不确定的光亮来破除恶之神义论的诱惑,面对恶的问题。恶之平庸与其说是对恶的本质为何的解答,不如说是关于人如何能抵制恶、承担道德责任的思考。在《艾希曼》中,施密特中士的故事引发法庭上人们自觉的2分钟肃静。在这2分钟里,仿佛忽然一道耀眼的亮光刺透了深不见底、不可穿越的黑暗(46)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the Viking Press, 1963); Penguin Books, 2006, p.231.。这光亮同围绕艾希曼及其周围环境与人群的漫长黑暗形成强烈反差。阿伦特评论道,施密特中士故事的出现没有伴随任何宏大叙事,却是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戏剧性时刻”。应该说,对此片段的评述也是全书压抑沉闷、并偶或夹杂尖锐嘲讽的笔调下罕见的高潮时分(47)Ibid., p.230.。正如施密特中士的善无需任何金钱与后果的计算,抑或与善的宏大叙事有关的理由,恶的神话似乎也可以同样得到破解——艾希曼并没有任何深不可测的动机,他只是无思或者说道德判断力较差。这使得人们无法再以任何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自欺,仅需直面个人判断力和责任问题。这对于自欺艺术高度发达、谎言的完整与终极性前所未有、对事实的宣传与操控能力极度强大的现代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此,当阿伦特透过恶之平庸来理解极权主义的道德崩溃时,她便开始能放下面对“根本恶”的手足无措,在一定程度上面对与承担“根本恶”的重负。这是她认为思想者应担当的使命:理解不是以知性犁平难以面对的现实,更非用自以为是的教条来掩盖对现实的判断力和责任的欠缺,而是同现实和他者对话,给予亮光和方向。
1964年6月9日,玛丽·麦卡锡(Mary Therese McCarthy)在给好友阿伦特的信中提到自己阅读《艾希曼》时的感受:“读你的《艾希曼》确实让我精神振奋,这种感觉和我听那两部音乐作品时的感觉非常相近,而它们都和救赎有关。”(48)[美]阿伦特、麦卡锡:《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265页。这里提及的两部音乐作品,麦卡锡曾在一篇此前为辩护《艾希曼》而公开发表的文章《众声责难》中言及。在此,她写到:“我很坦白地说,这本书让我感到快乐,我在里面听到了赞美歌——不是表达对极权主义的仇恨,而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颂歌,一种天籁之音,就像《费加罗的婚礼》或《弥赛亚》最后的合唱……读者‘超越’了那个可怕的审判,仿佛得到了升华,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审视这一切。”(49)同上,第266页注6。对此,阿伦特在同年6月23日回复道:“你是唯一读懂我心思的人,我从来也没承认过,我是在一种奇怪的快感中完成那本书的。自从我写了那本书,我觉得——20年以来——我第一次对这段历史释然了。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不是证明我没有‘灵魂’了?”(50)同上,第268页。
这段朋友间心心相契的对话,见证了阿伦特写作《艾希曼》时与恶的问题展开的一场精神搏斗。于她而言,对“恶之平庸”的抵达不啻为某种程度的“救赎”:从此她可以告别恶的神义论诱惑,并以自己的“神义论”进行替补。或许也可以由此理解她在1969年的一份材料中写下的这句话:“在所有这些貌似学术性的问题背后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一种全然的世俗性处境中接近恶的问题。”(51)Susan Neiman, “Theodicy in Jerusalem”, Hannah Arendt in Jerusalem, pp.75-76.在此,她对世俗性的理解显然首先针对神义论陷阱的伪神学色彩而言。有学者指出,阿伦特的诉求与其说是“世俗性”,不如说是要获得偶然性、复数性与独特性的自由(52)Ibid., p.76.。黑格尔式的神义论已具有彻底的世俗性,却可能沦为一个人造神的程序性网罗,窒息人类思考和想象的自由。阿伦特的关怀则是如何摆脱这种人造神的网罗,而她从康德为理性划界的哲学,尤其是《判断力批判》中获得关于思考和判断力的灵感,因而在完成《艾希曼》之后,她便在晚年着手开展与康德的政治哲学和判断力问题有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