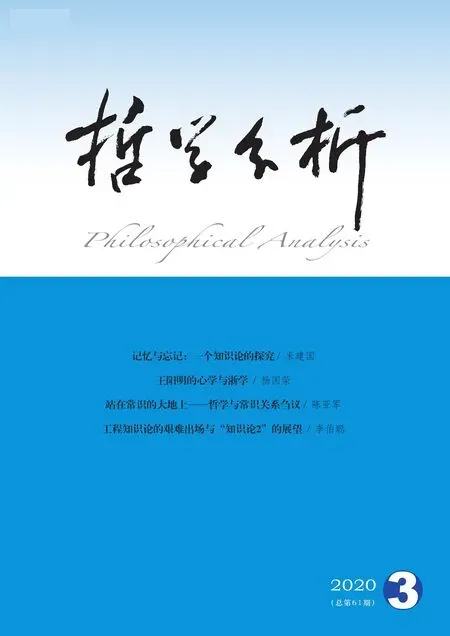论思辨实在论对生态哲学的补充
卢 风
20世纪在英语世界处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无疑是分析哲学,直至今天,分析哲学在英语世界仍然处于主导地位。①Stephen P. Schwartz,A Brief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From Russell to Rawls,New York:Wiley-Blackwell,2012,p.xi.20世纪直至今天,在欧洲大陆处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是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当然,分析哲学在欧洲大陆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现象学在英语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都继承了康德哥白尼革命”的传统,从而使哲学困于人类语言或意识的界限之内,而不再思及人类语言或意识的“外部”,不再思及比人类更高者,或不再思及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神圣者”的“自然”①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5—76页。。最近悄然兴起的一个哲学运动抑或哲学流派——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试图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这两大占据学院派哲学主导地位的哲学“范式”进行系统的批判,从而重新审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这项工作与20世纪六七年代逐渐兴起的生态哲学有共同的志趣。生态哲学可由思辨实在论获得重要的思想援助或补充。
一、思辨实在论的兴起
分析哲学家都认为“语言学转向”是现代英语世界“哲学的革命”。著名分析哲学家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的著作《分析哲学的起源》一书第二章的标题就是“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这一章一开始就写道:“分析哲学固然有多种表述,但[它坚持的]区别于其他哲学学派的基本信念是:第一,对思想的哲学解释(a philosophical account)必须通过对语言的哲学解释而实现;第二,对思想的综合解释(a comprehensive account)也只能通过语言解释而实现。宽泛地说,分析哲学家们是彼此不同的,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的整个学术生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美国以蒯因和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卡尔纳普哲学(post-Carnapian philosophy),都坚持了这两条公理。”②Michael Dummett,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London:Bloomsbury,2014,p.5.坚持这两条公理就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哲学的根本特征。思辨实在论运动包含了对“语言学转向”的严重不满,于是这场运动的干将们提出了“思辨转向” (The Speculative Turn)的口号。他们说:“我们之所以提出‘思辨转向’,就是有意和如今已令人厌烦的‘语言学转向’对着干。”③Levi Bryant,Nick Srnicek and Graham Harman,The Speculative Turn: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Melbourne:re.press,2011,p.1.。布赖恩特(Levi Bryant)、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和哈曼(Graham Harman)合编的《思辨转向:欧陆唯物主义和实在论》一书概述了思辨实在论(亦称“思辨唯物主义”)兴起的背景、思辨实在论的先驱与当今的干将、思辨实在论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思辨实在论的基本立场以及未来发展,也汇集了这个学派的重要文献。
《思辨转向:欧陆唯物主义和实在论》一书有如下一段对思辨实在论哲学运动的记述:
“德勒兹、德里达都可被视为思辨实在论的先驱。自从2014年10月德里达去世以后,齐泽克(Slavoj Žižek)成了他们阵营中最出名的人物,这多与他的英文版著作有关,也与他可爱的公众形象有关。齐泽克在公共思想(the public mind)方面与其同盟巴迪欧(Alain Badiou)越来越联系紧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巴迪欧的主要著作已陆续译为英文。在他们阵营中活着的哲学家中,齐泽克和巴迪欧或许是被英语国家哲学界阅读得最多的两位思想家。拉图尔(Bruno Latour)已是人类学、社会学和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领域的巨擘,于是也被博格斯特(Ian Bogost)、布赖恩特和哈曼以‘客体导向本体论’ (object-oriented ontology)名义‘走私进’ (was smuggled into)他们的阵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图尔的长期学术好友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以一种相当不同的路径进入了英语世界的争论,她以对德勒兹、怀特海和世界政治(Cosmopolitiques)的研究而为较年轻的德勒兹派所重视。拉吕厄尔(François Laruelle)的‘非哲学’ (the non-philosophy)也激发了许多年轻读者的想象力,尽管他的著作迄今只有很少一部分译成了英语。正在兴起的拉吕厄尔派业已表现了对认知科学和‘神经哲学’ (neurophilosophy)的强烈兴趣。对于思辨实在论,200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德兰达(Manuel DeLanda)在其《密集科学和虚拟哲学》,哈曼在其《工具—存在》中,公开宣扬了他们的实在论,这在最近的欧陆传统中或许是第一次公开亮相。五年以后,这种对实在论的明确呼唤被下一代迄今为止组织得最好的运动所加强。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的《有限性之后》于2006年初出版。受此激发,第一次思辨实在论会议于2007年4月在伦敦的金斯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举办。起初的群体包括布拉西耶(Ray Brassier)、格兰特(Iain Hamilton Grant)、哈曼、梅亚苏。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是2007年会议的主持人,到2009年接着在布里斯托尔举行会议,梅亚苏取代托斯卡诺做了主持人。如今,这个群体业已分裂,但其感召研究生中新生一代的关键点尚存。多亏最近博客空间的方便和‘零度丛书’ (zero Books)一类出版商的进取性收购政策,这些研究生中的许多人已令人惊讶地出名了。”①Levi Bryant,Nick Srnicek and Graham Harman,The Speculative Turn: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p.2.
由这段记述可知,德里达、德勒兹、齐泽克、巴迪欧、拉图尔、斯唐热都是思辨实在论的先驱,德兰达、哈曼、梅亚苏则是该学派的核心人物,2007年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和2009年在布里斯托尔举行的会议则标志着该学派产生了较大影响,构成了一种哲学运动,并形成了一个群体。如今,这个群体虽已分裂,但思辨实在论在研究生中已产生了较大影响,可谓后继有人。
思辨实在论者认为,长期以来欧陆哲学聚焦于话语、文本、文化、意识、权力或观念,认为实在(reality)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尽管认同这些思潮的思想家中的许多人自诩为反人道主义,但在他们提供的批判中,对人性(humanity)在世界中地位的省思少于对笛卡尔式自我封闭的主体的笼统批判。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性仍稳居中心地位,而实在只作为人类思想的相关物出现在哲学中。就此而言,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欧陆哲学中反实在论思潮(antirealist trend)的典型。当然不应轻视这些哲学的重要贡献,但它们显然缺失某种重要的东西。面对生态灾难的凸显以及技术对日常生活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日益渗透,反实在论是否足以应对这样的发展,实堪担忧。危险的是欧陆哲学反实在论仍未呈现衰退之势,如今这已严重限制了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精神力量。①Levi Bryant,Nick Srnicek and Graham Harman,The Speculative Turn: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p.3.
梅亚苏认为,被困于语言、意识或文化之内而无视独立于人类的实在,并非仅是欧陆哲学的特征,也是在英语世界居于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特征。梅亚苏称这种在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中稳居主导地位的反实在论为“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相关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只有思想和存在之相互关系(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这个通道,而绝不可能进入思想和存在相分离的任何一方。相关主义断言,我们不可把主体性和客体性看作彼此独立的两个领域。它不仅断言,我们不可能脱离与主体的关系而把握客体自身,同时也断言,我们不可能脱离与客体的关系而把握主体。②Quentin Meillassoux,After Finitude: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Ray Brassier(trans.),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8,p.13.在整个20世纪,相关性的两大主要媒介是意识和语言,前者孕育了现象学,后者孕育了形形色色的分析哲学。③Ibid.,p.15.
拒斥反实在论而试图重新思考独立于人类的实在或某种“绝对”是思辨实在论者的基本立场。经过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和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思辨哲学似乎已声名狼藉。他们为什么要逆分析哲学之大潮而扬言发起“思辨转向”呢?他们声称,在他们所说的“思辨转向”中有某种新的启示。与不厌其烦地聚焦于文本、话语、社会实践和人类有限性的欧陆哲学截然不同,新一代思想家再一次转向实在本身。尽管很难辨识这个阵营中不同思想家的明确的共同立场,但他们全都拒斥聚焦于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que)的惯常做法。他们中有的提出了本体对象(noumenal objects)概念,有的提出了自在因果性(causality-in-itself)概念,有的则转向了神经科学。有几位已经建构了数学绝对(mathematical absolutes),有些人则试图揭示心理分析和科学合理性的神秘内涵。他们都开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沉思独立于思想或人类的实在的本质。这样的思辨活动或许能引起某些读者的兴趣,因为这意味着回归前批判哲学(pre-critical philosophy)及其对纯粹理性力量的教条式信念。然而,“思辨转向”不是对批判哲学之进步的全部摒弃,却出自对批判哲学之固有局限的明确意识。就此而言,思辨意味着对批判哲学和语言学转向的某种“超越”(something“beyond”)。因此,在关心绝对(the Absolute)的意义上,它复活了“思辨”的前批判含义,同时它承认批判哲学(指康德开启的现代哲学)有其不可否认的进步。面对生态危机、神经科学的进展、基础物理学的分歧日增的解释、正展现的人与机器之间界限的模糊,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感受——目前的各种哲学无法面对这些事件。①Levi Bryant,Nick Srnicek and Graham Harman,The Speculative Turn: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p.3.
澳大利亚哲学家阿伦·盖尔声称其哲学为思辨自然主义,显然属于思辨实在论阵营。盖尔对蒯因及其门徒们所牢牢把持的英语世界学院派哲学极为不满,并诉诸思辨的方法对英美主流分析哲学进行了元哲学和方法论方面的批判。在盖尔看来,思辨性是哲学的根本特征,只有思辨哲学才能总揽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对之进行反思,并力图提出一个全体的实在观(a view of Reality as a whole),这样的实在能公正地对待万物。在基本方法上,思辨哲学必须兼用分析、通观(synopsis)和综合(synthesis)的方法,而不能像分析哲学那样只用分析方法。思辨哲学之最重要、最独特的工作是综合,它力图用一整套概念和原则整合受到通观的不同领域的事实。②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p.33—34.
实在论的基本信念是:存在超越于人类意识、语言、文化、力量之上的客观实在(Reality)。“思辨转向”的实在论则试图避免分析哲学对分析方法的单一使用,而兼用分析、通观和综合的方法,同时摒弃欧陆哲学沉迷于文本、话语、权力、意识等的相关主义,让哲学重新思及超越于人类意识、语言、文化、力量之上的客观实在或绝对,以反思人类文明在21世纪所面临的根本挑战。
二、思辨实在论的根本关切
从20世纪初直至今天,西方哲学的反实在论都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直接相关。所谓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就是放弃让直觉(intuition)符合客体结构(the constitution of the objects)的认知努力,却反过来让客体符合我们直觉能力的结构。③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p.110—111.经过“哥白尼革命”,人的主体性得以挺立,人类豪迈地宣称:人为自然立法,每个人都可以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成为自主的个体。到了20世纪,“建构”一词在哲学、社会学中逐渐流行,好像不仅“人化物”是人类建构的,世界的一切都是人类建构 的。
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较多地辨析了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普特南说:我们见证了一个持续了两千余年的理论的寿终正寝。尽管这个理论自相矛盾且模糊不清,却持续了很久,且有多种表述形式,从一开始这就表明了获得上帝视角(a God’s eye view)的欲望的天然性naturalness)和力量。康德第一个告诉我们这个欲望是无法实现的,但康德认为这个欲望已嵌入我们的理性本质,并建议我们把这种“总体化”冲动(totalizing)升华为在这个世界实现“最高善” (the highest good)的努力,通过在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和个人关系中协调道德秩序和经验秩序即可实现这种最高善。这种天然而不可实现的冲动之持续存在可能正是西方文化中虚假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不断增多的深层原因。尽管如此,没有上帝视角,我们仍可以安然无恙①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74.。
普特南认为,康德是最早提出内在论或内在实在论真理观的哲学家。②Ibid.,p.60.在20世纪80年代普特南以内在实在论者自许,后来立场有很大的改变。③成素梅:《普特南的实在论思想》,载《哲学动态》2019年第8期,第109—117页。普特南承认,与形而上学实在论对比,内在实在论实际上是一种反实在论。内在论或内在实在论的真理观认为真理只能是特定话语体系或理论体系内部的真理,而不可能是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观念、理论体系或符号体系。经过康德的批判哲学,我们必须承认,洛克所说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因为“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是一样的,或说,客体的所有性质都是“第二性质”。这便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关于客体的任何事情都只是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事情。我们所谈论的关于任何客体的东西都根本不描述独立于客体对我们之影响的客体本身,而我们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之理性本质和生物构成的存在。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假定在我们关于客体的观念与无论何种独立于心灵的实在之间存在任何相似性,不能假定这种独立于心灵的实在是我们关于客体的经验的最终根源。我们关于客体的观念并非独立于心灵的事物的复本(copy)④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p.61.。这也就是内在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可简约地概括为三点:(1)我们无法认知独立于人类心灵的客观实在(自在之物);(2)没有什么第一性质,事物的性质都是第二性质,即都是与人类觉知内在相关的性质;(3)真理符合论是不能成立的。显然,内在实在论就是梅亚苏所说的相关主义的一种,属于思辨实在论的批判对象。
经过康德的批判哲学直至今天,人们相信,世界是人类建构的世界,人类只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万物皆在人类语言或意识的内部,因为无论思考什么都必须先意识到它,或必须先说到它,于是我们被锁在语言或意识的内部而无法逃出。①Quentin Meillassoux,After Finitude: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p.15.在梅亚苏看来,现代哲学关于意识和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理解是悖论式的。一方面,相关主义无法否认,意识和语言一样,在根本上切不断与外部(exteriority)的原初联系,另一方面,相关主义又似乎总是在掩饰一种被囚禁或封闭于外部(“透明的笼子”)的奇怪情感。我们确实是被囚禁于对语言和意识而言是外部世界的内部,我们注定总是已在其内(“总是已在”是相关主义讲“相关”的另一种说法),我们注定没有什么能够观察那些“对象世界”的有利观点,而那些对象世界是从外部向我们提供信息的不可超越的提供者。这个外部是与我们隔绝的外部,是可以被合理地感觉到它是囚禁我们的,就因为这个外部实际上完全是相对的,因为它——这恰是关键点——是相对于我们的。意识及其语言当然是超越自身而指向世界的,但就意识超越自身而指向的对象而言只存在一个世界。于是,这个外部空间就只是我们面对的空间,它仅作为我们自身生存的相关物而存在。被抛入这样的世界,我们实际上没有怎么超越我们自身,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探测停留于面对面的两面,就像只知道其对面的一枚硬币。如果当代哲学家还顽固地坚持认为思想是指向外部的,那可能因为他们还不甘心这样一种丧失——在否弃教条主义的同时伴随着的一种损失。当代哲学家已失去了伟大的外部(the great outdoors),失去了前批判思想家的绝对外部(the absolute outside):那种外部不是相对于我们的,它对自身之被给予性和自身之所是也是中立的,不管我们是否思及它,它都自己存在着。思想可以作为外域的存在而带着正当的感情去探讨那种外部。②Ibid.,p.17.
如果说分析哲学还在执着地追求与自然科学的协作,那么欧陆哲学则一边批判自然科学,扬言要建立“最严格的科学”③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页。,一边日益与自然科学相剥离。中国哲学界的西方哲学追随者们则只能固守体制留给他们的狭小地盘,洋洋自得地做着模仿性的从文本到文本的“语言游戏”,既不关心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又不关注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当代技术无孔不入的现实影响。哲学不能不伴随时代脉搏的跳动而不断推陈出新地阐释世界观,进而阐释与之相协调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发展观,并由此审视当代社会制度、各行各业精英们引领的生活时尚和大众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自胡塞尔扬言要建立超越自然主义的“最严格的科学”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但我们未见现象学家们建构起真能胜过自然科学的“最严格的科学”。抛开自然科学而固守于意识和语言的内部,是不可能建构什么严格科学的。梅亚苏也是这么看的。在如今的科普读物中,我们经常会读到:宇宙起源于135亿年前;地球形成于45亿6000万年前;地球上的生物起源于35亿年前;人类起源于200万年前。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告诉我们:早在人类出现很多年前,非人生物、地球、宇宙就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梅亚苏称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存在的事实为“前先祖的” (ancestral)①Quentin Meillassoux,After Finitude: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p.21.事实。
护士分层级培训与考核紧密结合,以临床工作需要进行培训,考核要求与培训内容相结合,根据分层培训进行分层考核,技能训练与质控考核相结合,运用理论考试纸质或信息化平台,定期进行考核,并与绩效挂钩。护理部应该定期组织临床护理护生探讨会,广泛征求护生意见,了解护生在实践当中对于教学方法和方式的意见,然后进行改进,提高带教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质量。二是,要定期进行考核,对临床护理护生进行出科考试,要坚持理论课和实践课成绩相结合,对学生专业知识进行评测,同时要辅之以医德医风和劳动纪律内容由带教教师给出专业性意见,实施综合评定表,从临床护理需求出发,做好临床护士个人能力测评,给出专业鉴定表体现护生个人实际能力。
梅亚苏正确地指出,现代反实在论者或相关主义者不能合乎逻辑地承认“前先祖事实”的存在。按照他们的逻辑,物理宇宙不能先于人类而存在,因为仅当给定了一种生命或能思考的存在者时世界才是有意义的。②Ibid.,p.30.他们不会直接否定自然科学家所得出的关于早在人类出现很多年前非人生物、地球、宇宙等就早已存在的结论。他们只会说,只是对人类而言,早在人类出现很多年前地球、宇宙等就早已存在了,即前先祖事实也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这种说法是现代性的,现代哲学家通过这种说法抑制了对科学内容的介入,同时保住了一个在科学之外且更为本源的意义领域。每当面临前先祖陈述时,相关主义者会假定,这类陈述至少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其直接的意义,即实在论的意义,另一层则是相关主义者们所揭示的更为本源的意义。③Ibid.,p.27.
梅亚苏认为,相关主义者关于前先祖陈述的判断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他们会说,在一种意义上,科学陈述的这类事情是客观的,即可在主体间证实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不是客观的,因为这些陈述的所指不可能以那么天真描述的方式早已存在,即以与意识无关的方式早已存在。这样,我们最终就会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前先祖陈述是真陈述,但是其所指不可能以这个真陈述描述的方式真实地存在。它是个真陈述,但被它描述为真实的事件是个不可能的事件;它是个“客观的”陈述,但它描述的对象是个不可想象的东西。简言之,它就是胡说八道。如果前先祖陈述只具有其当下证实之普遍性的价值,那么科学家就不会劳神费力地去验证它们。对一种测量的验证如果只对所有科学家有效,那么科学家就不会去验证,科学家去验证就是为了确定测量的事实。是放射性同位素告诉了我们过去事件的年龄,把这种年龄转变为某种不可想象的东西,把测量的客观性变成毫无意义和丝毫不超越测量活动本身的事情是不对的。科学没有做过验证其实验之普遍性的实验;它设定外部所指就是实验的意义,从而进行可重复的实验。④Ibid.,p.32.
可见,如果我们严格坚持相关主义的立场,就不可能确立一种与自然科学协调一致的世界观。思辨实在论的根本关切就是突破意识和语言的壁垒,去重新体认一个“伟大的外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被许多现代哲学家所坚决摒弃的“形而上学实在论”,承认存在不依赖于人类意识或心灵的客观实在。梅亚苏要求我们承认“前先祖陈述”的客观性,也就是要求我们承认,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客观世界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复兴实在论也就是拒斥唯心主义。如哈曼所言,对思想的真正危险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唯心主义,因此,能救治我们的最好治疗不是真理/知识这一对概念,而是实在。实在才是我们的各种舰只所撞上的坚硬岩石,才是我们必须承认并对之心存敬畏的,不管它是多么捉摸不定。正如军事将领说没有什么战斗计划能在与敌人第一次遭遇时还能幸存一样,哲学家该说没有什么理论能在与现实遭遇时还能幸存。①Granham Harman,Object-Oriented Ontology: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New York:Penguin Random House,2017,pp.6—7.
三、反思可知论
“进步”是现代性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人一直对进步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确实有理由把进步或发展视为文明的根本特征。进步和发展可以是多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但现代性的进步往往被归结为科技的进步,现代性的发展往往被归结为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末,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现代经济增长依赖于科技进步,未来的经济或者是“信息经济”,或者是“知识经济”。至此,人们更加相信,归根结底,进步就是科技进步或知识进步。这种对“进步”的理解与现代性哲学的可知论有内在的关联。在“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看来,世界和人类思维(或自我)都是透明的、可知的,而且世界可以根据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而得以再造。②Ibid.,p.48.康德是现代性哲学的集大成者,但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往往对他关于人类知性无法触及“自在之物”的观点心怀不满,在某些哲学家看来“不可知论”似乎是康德哲学的最大错误。于是,康德之后,一边有相关主义的盛行,一边洋溢着可知论的乐观。在20世纪乃至今天,这种乐观信念曾表现为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关于物理学终结的信念③Stephen W. Hawking,The Theory of Everything,CA:Phoenix Books,2005,p.122.,也表现为爱因斯坦关于物理学统一的思想,更直接表现在温伯格关于“终极理论”④Steven Weinberg,Dreams of a Final Theory: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Laws of Nature,New York:Vintage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93,p.242.以及霍金等人关于“万有理论”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⑤Stephen W. Hawking,The Theory of Everything,p.122.的思想中⑥笔者认为,在阐述自然观和世界观时,著名科学家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任何哲学家,事实上,像爱因斯坦、普里戈金、温伯格、霍金那样的科学家的影响远大于任何当代的学院派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也怀有可知论的坚定信念。哈曼(思辨实在论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对这种源远流长的可知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哈曼也称自己的哲学为“客体导向本体论” (Object-Oriented Ontology),英文缩写为OOO,或“3O”①Granham Harman,Object-Oriented Ontology: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p.6.。哈曼同时宣称,“客体导向本体论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实在论哲学。这意味着客体导向本体论认为外部世界是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于其他诸物之中的。”②Ibid.,p.10.。顺便指出,同在思辨实在论阵营的不同哲学家的思想总是有差异的,并非所有的思辨实在论者都接受客体导向本体论,我们或许可把它看作思辨实在论的一 种。
哈曼说:“从客体导向本体论的视角看,没有什么真理,并非因为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而是因为实在(reality)是那么真实,以至于任何想把它转译成文字(literal erms)的企图都注定会落空。”③Ibid.,p.192.在哈曼看来,康德关于人类知性无法认知物自体的观点没有错。哈曼不赞同把宇宙万物都归结为“关系”或“事件”的观点,而认为客体”这个概念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并认为,“单个实体,无论其大小,都是宇宙的终极物质”④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黄芙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10页。。
我们在对某个事物进行观察或思考时,会停留在其表面,或者还原为特征勾勒。一把椅子、一剂化学药品或一幢建筑的本质要远比我们对其感知和认识更深:对象比我们所见、所言要深得多。但与感知或理论一样,我们对诸物的实践并未能让我们与它们有更深的接触。我们在使用锤子或椅子时并未能穷尽其全部实在,海德格尔真正的意图不仅仅是告诉人们理论和实践的严重对立,而是让我们知道理论和实践都不能让我们充分认识诸物,而只是停留在了对其表面的认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若我们的实践过程能够充分认识诸物,那它们就不会损坏。损坏证明在人类与之接触之外有存余。这样,海德格尔的对象沿袭了伊曼纽尔·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的传统,即对象存在于人的接触之外,人类可以对其进行思考,却无法理解和认识。⑥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第xii—xiii页。
哈曼也指出:“尽管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的确带我们追溯到关于物自体的论断,但这并非他的本意。”①格拉汉姆·哈曼:《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第xiii页。哈曼自己则借用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一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不仅人类认识和理论不可能充分认识诸物,人类实践同样不可能彻底把握诸物。他 说:
火燃烧棉花时,轻而易举就能将其化为灰烬,然而,棉花的很多特性与火不相关,火只是接触了棉花的可燃性,对棉花的其他特性却是一无所知。这样看来,宇宙中的每一种关系,无论人类参与与否,总是受到存在于关系之外、不涉身其中的物自体的影响。火与棉花之间的因果互动并不是火本身和棉花本身之间的互动,而是两个对象的感官特征勾勒之间的互动,因而,关系性必须总是对象间非直接形式的接触,而不是直接的。②同上。
显然,哈曼认为,把“火与棉花”换成“人与物”,以上结论仍然成立。人们常说,人类认知能力的神奇之处在于能够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本质”是哲学家们(包括现象学哲学家)常用的概念。在哈曼看来,“‘本质’仅仅指任何对象都具有的实在性质,不可被当前的思维表象穷尽,也不可在一般的意义上被对其他实体的当下影响所穷尽。”哈曼说:“这并不是说本质必须是永久的。至于可知性,此处被辩护的本质是绝对不可知的”③同上书,第37—38页。。这是迄今为止笔者读到的最为明确地否定可知论的论断。在哈曼看来,“对象从所有的理论和实践接触中隐没。地质科学并不能完全认识岩石的存在,因为岩石总是有实在的存余,比我们拥有的关于岩石最全面的知识都要深”④同上书,第43—44页。。
既然特定对象都是人类认知和实践所不可穷尽的,那么整个世界或宇宙就更是这样了。如前所述,爱因斯坦、温伯格、霍金等物理学家都相信物理学可以发现“终极理论”或“万有理论”,但哈曼认为,物理学乃至一般的自然科学不可能发现什么万有理论。迄今为止,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弦理论(string theory)最有希望成为万有理论,但哈曼认为这一理论的四大思想预设是错误的,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万有理论。哈曼所指出的四大预设是:第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物理的;第二,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基本的或简单的,指万物都是由基本的或简单的弦构成的;第三,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第四,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书面命题语言所精确叙述。哈曼对这四大预设逐一进行了批驳⑤Granham Harman,Object-Oriented Ontology: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pp.25—41.,受篇幅限制,本文对此不再详加介绍。
总之,在哈曼看来,不仅人类的认识不可能穷尽任何一个对象,实践同样也不可能穷尽任何一个对象。这便意味着人类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人类实践的后果永远都不是可以准确预测的。这种关于人类知识不完备的哲学观点也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支持。例如,著名物理学家罗伟利(Carlo Rovelli)就认为:科学不可能终结,人类永远都将行进在求知的道路上。他说:“我们正在探究的领域是有前沿的,我们求知的热望在燃烧。它们(指人类知识)已触及空间的结构、宇宙的起源、时间的本质、黑洞现象,以及我们自己思维过程的机能。就在这里,就在我们之所知的边界[我们]触及了未知的海洋(the ocean of the unknown),[这个海洋]闪耀着世界的神秘和美丽。会让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①Carlo Rovelli,Seven Brief Lessons on Physics,Simon Carnell and Erica Segre(trans.),London:Allen Lane,2015,pp.100—101.如果我们难以理解梅亚苏所说的人类意识的“伟大的外部”,那么罗伟利站在当代科学的前沿而体悟到的“未知的海洋”或许就是人类意识的“伟大的外 部”。
四、援思辨实在论入生态哲学
当代生态哲学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凸显整体论、系统论的思维方法,从而对对象的重视远不及对关系的重视。就此而言,生态哲学似乎与哈曼的客体导向本体论相左,但我们不难参照整个思辨实在论,而反观生态哲学的薄弱之处,并进而用思辨实在论的积极成果去补充生态哲学的不足。
生态哲学是直面现实并努力去凝练新时代之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它着力探究的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着力纠正的错误是现代哲学乃至现代科学所预设的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方面的错误,也力主改变现代人征服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大致有二:一是源自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的生态哲学,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和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是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一是深生态学(deep ecology),阿伦·奈斯(Arne Naess)既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也是其杰出代表。中国生态哲学的杰出代表是余谋昌先生。迄今为止,生态哲学都着重从伦理的角度去论证:在人与非人事物之间没有笛卡尔、康德哲学所凸显的那种根本区别。在康德等著名哲学家看来,人是有理性、自由意志、尊严、内在价值和权利的主体,而非人事物(既包括非人自然物,也包括人造物,如机器等)是没有理性、自由意志、尊严、内在价值和权利的客体。生态哲学家们都着力论证,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从而也具有道德权利,因此,人类也应该尊重非人自然物的权利,把非人自然物也纳入道德共同体。在笔者看来,这种伦理或泛伦理的努力是重要的,但其思想震撼力不够,从哲学思辨上看其思想深度也有待于提升,其广度也有待于扩展。局限于伦理学视域难以说清为什么有必要把伦理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包括人与非人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没有本体论、知识论、科学观、科学方法论的相应转变,无法说明人与非人自然物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利奥波德最早提出人与非人自然物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观点)。迄今为止的生态哲学论述都较多地集中于伦理学和价值论论域,而在本体论和知识论方面比较薄弱。思辨实在论正力图在根本上改变现代哲学的本体论和知识论等,这正好可补充生态哲学的不足。顺便指出,思辨实在论有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主张哲学直面现实,而不是只做从文本到文本的“语言游戏”,这与生态哲学不谋而合。双方取长补短,可促进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文明危机的更加深入的反 思。
失去敬畏之心,否认存在超越于人类集体力量之上的力量,从而力图征服自然,是现代人类陷入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迄今为止的生态哲学不太重视去追究这一原因,而过分纠结于伦理学和价值论方面的论辩。现代人之失去敬畏之心与后康德哲学反实在论的盛行不无关联。正因为人们否认或漠视了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客观实在而妄言“人为自然立法”,他们才认为文明的进步就意味着对自然的征服。思辨实在论指引我们重新体认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力量的客观存在,从而指引我们放弃征服自然的妄念。恰恰在这一意义上看,思辨实在论可为生态哲学提供最重要的补 充。
现代哲学过分夸大了人的道德自主性,这与它试图弱化或干脆删除比人类更高者的作用有关。事实上,个人仅凭理性很难做到对道德律的绝对敬重。个人总是生活在不同层级的共同体中的,其道德实践始终处于自律和他律的张力之中。一辈子从未做过任何违背道德的事的人大约可算是圣人了,但这样的人极为罕见。颜回不贰过就已大受夫子的称赞。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实践都既有赖于个人自觉又有赖于外部监督。一个人犯了小错,受到亲朋好友的批评,就可能改过,犯了触犯法律的严重错误,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舆论监督和法律制裁对个人的道德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外部警戒机制。一个组织犯了大错或罪行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一个国家公然违背国际法而犯下罪行,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制裁和惩罚。
如果全人类都犯了错误甚至罪过,那么人类如何纠错或改过呢?“哥白尼革命”之后的现代哲学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甚至也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康德后的哲学已封闭于人类意识或语言的内部,已失去了“伟大的外部”。这种哲学倾向于认为,“人为自然立法”,同时人凭其理性而为自己立法,于是,人类的生活世界似乎完全是人类自我建构的。人类共同体内部的特定个人、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可能犯错或犯罪,但人类全体不可能犯错或犯罪。当然,不可能有全人类所有成员意志一致的行动和共同采取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在全球化的今天,确实有在人类文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多数国家的统治阶级乃至大众大致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而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指引着一种主导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现代性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力主征服自然,工业社会的“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就是现代性指引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可以说现代性是现代全人类的基本共识,“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就是由这种基本共识指引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在失去了“伟大的外部”的同时,也失去了像中世纪欧洲人心中的“上帝”或像古代中国人心中的“天”那样的外部警示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无法纠正其共识中的错误。现在我们知道,科学家的共识就是科学知识,甚至就是真理。如今全人类的共识也奠基于科学知识,现代性受现代科学的直接支持。我们可以指望有良知的科学家去指责某些失去良知的科学家捏造实验数据、伪造科研成果等错误。但我们无法纠正全体科学家乃至全人类的共识中的错误①当然,可以通过科学之历史性的进步而纠正特定历史时期科学知识的错误,但那只能是长时间跨度的后见之明,往往需要好几个世纪,甚至十几个世纪。,人们甚至会认为,“全人类共识中的错误”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基督教中有人类集体堕落而受到上帝惩罚的故事,中国古代民间有“人在做,天在看”的说法。但康德之后的哲学会把这类思想斥为违背理性的胡言乱语,于是,在后康德哲学的思维框架内,人们无法证明,现代性力主征服自然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正确 的。
我们也可从人类学习的方面去省思失去了“伟大的外部”的后果。一个人必须虚心学习才能不断成长。周敦颐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可见在中国古人那里,人类中的最杰出者必须向比人类更高者学习,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向比人类更高者学习。在后康德哲学中,没有比人类更高者了,一切客体都只是人类可按其先天范畴去加以整理、建构的东西,人类只需要彼此之间互相学习,不需要向比人类更高者学习,这既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也是一种致命的狂妄,也正是这种狂妄激励着人们征服自然。迄今为止的生态哲学,对现代哲学这一错误的批判较少。思辨实在论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反思这一错误的理据。
思辨实在论呼吁我们回到一个简单的前现代的直觉:客观实在是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的。梅亚苏要求我们重新体认人类意识或语言的“伟大的外部”,让思想思及“绝对”,哈曼等人则着力指出,任何一个客体对于人类认知和实践都有不可穷尽的“存余”。由此可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仅从语言学、知识论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言说的一切都是在语言和意识之内的,当然也必定是与人类语言和意识相关的;同时我们也该赞同哈曼的观点: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说法并非全错。就此而言,我们该放弃发现“终极理论”一类的梦想(不排斥坚持这一梦想者能获得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或放弃普特南所批判的“上帝的视角”。在本体论上,我们应该响应思辨实在论者的呼吁,相信客观实在是独立于人类意识或语言而存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确立起一个纠正人类共识中的错误的客观参照系,才能向比人类更高者学习。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召回“上帝”或任何形式的人格神。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和非线性科学)而把大自然尊为比人类更高者。今天,我们说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里的“自然”主要指地球生物圈或自然生态系统。如果我们沿着思辨实在论的思路而思及独立于人类意识的“绝对”,那么我们就能确信:大自然就是这样的“绝对”。大自然是包容万物(包括人类)、化生万物的“大全”,是比人类更高者,人类不仅应该尊重它、顺应它,而且应该敬畏它。人类其实没有能力和资格去保护大自然,但人类能够且应该保护地球,而地球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客体(哈曼意义上的)。大自然本身不是一个可被科学所研究的对象,而是只能通过思辨哲学的沉思才能确信其存在的超验的绝对。①卢风:《超验自然主义》,载《哲学分析》2016年第5期。由哈曼关于人类认识和实践永远都不可能穷尽任何一个客体的论证,我们可得出结论:大自然永远都隐藏着无穷的奥秘,大自然是不可征服的,大自然永远都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无上权力。
简言之,思辨实在论支持我们去体认作为超验绝对的大自然的存在,从而支持我们敬畏大自然。一个人心存对高于人类者的敬畏,才能较好地敬重道德法则;全人类(当然首先是统治阶级或领导阶级)都心存敬畏时,才可能纠正其集体错误。当人们心存对大自然的敬畏时,他们才会敬重生态哲学所颁布的新道德律令,才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即尊重、顺应生态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彻底改变征服自然的狂 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