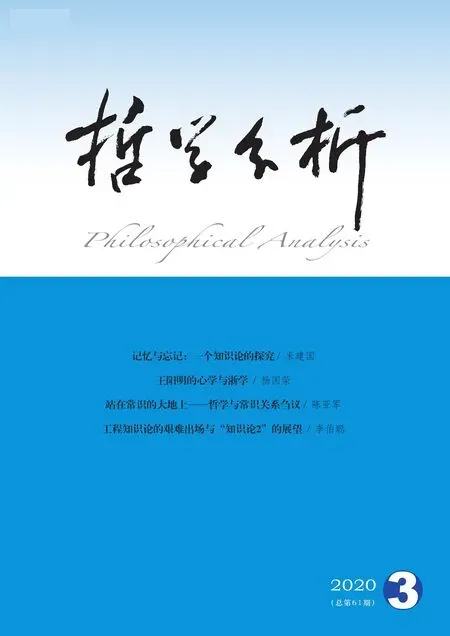“别子为宗”:本我论还是唯我论?
——论卡西尔对海德格尔真理观的“唯我论责难”
王庆节
我们曾经强调,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持的哲学立场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人类学”①参见王庆节:《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是“哲学人类学”吗?——论达沃斯论辩中卡西尔对海德格尔“康德解释”的一个责难》,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而且,它作为亲在(Dasein)生存论分析的基础存在论的基本意图恰恰就是要和以康德哲学,尤其是和以新康德主义的康德解释为代表的各种哲学人类学区别开来。这一区别的关键有两处:第一,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用亲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生存论分析(die existenziale Analytik)取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批判和推进了康德以及新康德主义后学的知识人的“认知活动”的先验论分析(die transzendentale Analytik)。我们知道,后者原本是康德先验哲学围绕“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论”的思考而展开的核心。第二,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是其最后的代表)以“知识人”为起点的发问,阻碍和遮蔽了康德及其后学清楚地看到“人的问题”背后的“存在问题”或“存在疑难”。相形之下,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以“存在人”为起点的发问,则直接引向了“存在疑难”的发问和开显。在海德格尔的眼中,正是这一发问和开显,不仅将自己同哲学唯我论区别开来,同时也在根基上彻底“动摇”和“瓦解”了传统哲学以“判断”和“知识”为核心来思考真理问题的思路。它触发和激发人们去思考和发问“真理”“普遍”“客观”“永恒”这些“价值”得以成立的源头,从而通过对亲在的生存论分析工作,进入或者深入到对“形而上学疑难”的奠基工作,而这后一项工作,正是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要进行和推进的事业。
在著名的“达沃斯论辩”中,卡西尔明显地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他即使看到,也不认同海德格尔的这一立场。相反,卡西尔责难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以“有限存在人”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基础存在论立场,不仅让自己陷入“哲学人类学”的窘境,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恰恰会在真理问题上把自己逼入在哲学史上一直被责难的主观唯我论和主观相对主义的绝路,这和康德哲学旨在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来达到和保证科学知识,即“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和必然真理性的目标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也是卡西尔在论辩中指责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对康德的核心思想不仅“误解”,甚至有“入侵” (卡西尔语)或者“篡窃” (牟宗三语)嫌疑的一个原因。实际上,这一有关“真理性”问题的指责十分严重,后来也广为流传,以讹传讹,给后人普遍造成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实质上是“反客为主”或“别子为宗”的印象。
毋庸多言,卡西尔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的责难实质是对在“达沃斯论辩”前不久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的主旨立场的批判。所以,“唯我论”和主观真理观问题是当时尚且年轻的海德格尔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达沃斯论辩”的前半段,海德格尔的基本姿态是防守,尽管他不时也小露锋芒,回怼资深的卡西尔的发问。但从真理观问题的回应开始,海德格尔可以说是反守为攻。他借回答问题之机,不仅反驳卡西尔以及重视传统的新康德主义的康德解释的失误之处,也不仅简单地去揭示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而且同时,他更从正面出击,公开辩护和展开自己的哲学立场,将其对形而上学疑难的发问和思考推向深入。①本文的讨论主要依据卡西尔—海德格尔达沃斯论辩的记录稿。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载《海德格尔文集》 (第3卷),附录IV,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01—316页。
一、“唯我论”还是“本我论”?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首先采取的策略并不是为自己的以亲在存在为核心的基础存在论立场进行被动的辩护,而是从其“存在真理观”出发,对卡西尔坚持的“普遍有效”的永恒真理观提出批评。海德格尔并不讳言,他的存在真理观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真理一般通过亲在(Dasein)的亲临存在和存在之亲临而展开出来。换句话说,这种作为亲在之生存活动的“亲临存在”与“存在之亲临”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源初意义上的“生存论—存在论真理”。“唯有亲在在,才‘有’真理。唯当亲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唯当亲在存在,牛顿定律、矛盾律才在,无论什么真理才在。”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载《海德格尔文集》 (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14页。这句著名的断言出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它说的就是亲在生存与存在之一般的关系,但往往被批评为“唯我论的”真理观。所以,当一般人谈到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时,往往都会引述海德格尔上述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这个说法,批评他露骨的唯我论立场。卡西尔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引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立场对之进行批评,但他这里关于海德格尔对康德想象力及图式化学说之理解的批评,恰恰说明他并无例外,即他也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真理观误读,并归入心理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甚至极端的唯我论的立场。
但是,情况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细究起来,我以为卡西尔以及通常传统的理解和批评在这里混淆了“本我”与“唯我”这两个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的概念或立场。从哲学上讲,“唯我”或“独我”与“本我”应该说均属于哲学形上学中主(基)体主义的立场。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唯我论” (solipsism) 在哲学上强调宇宙皆备于“我”或者“我心”。“我”或者“主观精神”是万事万物所以存在、所以被认识理解、所以有意义的全部根据和最后目的。相形之下,“本我论”的立场则走得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极端。“本我论”或者“基体主义”虽然也强调“我”在周遭世界意义建构和真理性认知中的不可或缺的奠基性作用,但这只是一个“初始的基础”,或者说,这是任何严肃哲学发问与思考所必经的“通道”或“枢纽”。但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我”并非是整个世界之存在的全部根据乃至渊源之所在。而西方近代哲学从康德开始,一直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再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基本上都沿循着这样一条“本我论”的传统进行着思考和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这就是为什么学界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究竟康德哲学中“物自身”性质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究竟应当被归为“唯心论”还是“实在论”的主要原因。当然,海德格尔的“本我论”与前两者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与主流的康德解释,尤其是与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解释不同,海德格尔的“本我”或“主体”主要不是“认知的主体”,即以现代理性和逻辑思维为根本特征并通过“知识划界”而确立自身权威地位的知识主体。海德格尔甚至也不像胡塞尔那样,通过将笛卡尔康德式的认知主体“还原”为所有意识行为,甚至包括前意识行为在内的作为源头的“纯粹意识”,“先验论主体”或者“超越论主体”。海德格尔的作为Dasein活动的“主体”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基体”,它不仅超出人类的认识活动,而且超出一切形式的意识活动,它是包括一切认知活动和意识活动在内的、涵盖一切人类生存在世活动的亲在活动(Dasein)。换句话说,在海德格尔看来,唯有将“主体”理解为Dasein,从Dasein的生存在世的存在论分析而非认知主体或意识主体的先验论分析入手,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存在本身的发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将此“亲在”命名为“在—世界之中—与他人—共在”并赋予其在“存在论暨存在者层面上”的双重优先地位。这样的一种关于“亲在之存在”的哲学研究,海德格尔称之为“基础存在论”或“亲在的解释学”。它“作为(亲在)生存的分析论,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向之回的地方上了”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54、587页。。
也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以亲在在世活动为核心的生存论分析工作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近现代西方主体性或本我论哲学传统的一个延续,但这个延续不能被理解为简单的重复。它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它将自笛卡尔以来一直占据近代哲学主流地位的“知识”“精神”“意志”“意识”的“主体论”或“本我论”推向了极限,从而使得突破这一“主体性”或“本我论”哲学的可能性得以第一次真正地显露出来。
另外,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强调,亲在生存活动的“基础存在论”之分析尽管构成了海德格尔成名作《存在与时间》已出版部分的主体,但并不是海德格尔原拟写作计划的全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最主要的部分。海德格尔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也不止一次地宣称,这部分的工作仅仅是“准备性的”或“先行的”工作而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更倾向于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在论”理解为“基始存在论”,因为Dasein的生存论分析对于存在本身的疑难发问来说,既是“基础性的”,又是“初始性的”,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了第一点而忘记了第二点。
二、究竟谁是“康德解释”中的“别子为宗”?
如果我们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作为底本来比较,海德格尔已发表的《存在与时间》的主体部分作为亲在在世的生存论分析论,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语言上,都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一部第二部分第一编“先验分析论”有着难以割断的思想渊源和延承关系。正是在这里,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关于康德解释之争辩的历史性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倘若我们将新康德主义的“知识理论”以及后来逻辑经验主义的所谓“摒弃形而上学”的“理性划界”视为理解和解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乃至全部康德“先验哲学”的要害和核心,那么,“先验分析论”以及其中的“先验演绎”部分无疑就会成为康德哲学的重中之重和核心中的核心。其他问题,诸如先验感性论、先验想象力、先验图式化、先验幻相、“物自身”以及“三大批判”之间的关系等重要的在存在论和形而上学层面上的问题,都会被边缘化,或者根据“知识理论”的需要而被轻视、漠视、裁撤,甚至遭到“肢解”和曲解。同样的道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最后一位掌门人的卡西尔,正是站在这样一种康德解释的主流立场上,从知识论的符合(判断)真理观的立场出发,质疑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道路无法解决人类知识的“永恒”和“普通客观”真理的问题以及必然陷入“主体主义”的“主观相对主义”泥潭而不能自拔。
上面我们谈到了为什么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康德解释的主流会将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误解为相对主义和主观唯我论的真理观的理论原因。不过,如果想在哲学上真正展开海德格尔在达沃斯论辩中对此诘难所进行的回应,我们需要先来看看正宗的康德解释如何从“知识理论”的立场和角度来回应和“解决”这个“普遍真理”的疑难问题,以及在海德格尔的眼中,为什么这一新康德主义的解决方案或发问途径实质上是问错了方 向。
我们知道,按照传统的康德解释思路,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疑难,而是来自笛卡尔以来的“知识论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论问题”,即人类知识的“真理性”和人类行为“价值性”如何可能的问题。换用著名的康德式语言就是,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如何可能?作为先天道德价值判断的“绝对命令”如何可能?这一切都通过对人类理性的批判来达成,前者通过对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的批判,后者则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来达成。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接着问,理论理性的批判如何进行?实践理性的批判如何进行?正宗的康德解释的回答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通过“划界”或“限界”来进行,通过这一批判,我们判定知识和非知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换句话说,在科学的限界之内,我们保证知识判断的永恒真理性和普通客观性,在限界之外,那是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地带,我们一无所知,应当保持沉默。至于在限界之内如何保证,康德有一系列的理论和说法,例如“物自身”的设定、感性杂多与先天直观时空形式、现象与本体、先验范畴、先验演绎、先验想象力与图式化,等等。但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庞大理论体系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划界”能够成立。而“划界”的标准是什么?这样说来,“划界”如何可能的问题要比“界内”知识(科学、经验)如何可能的问题来得更为基础和本源。康德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通过对著名“二律背反”命题以及这些命题所导致的“先验幻相”的分析来达成。而康德有关“二律背反”和“先验幻相”分析则诉诸理性逻辑的“矛盾律”得以成立。不仅如此,构成我们人类实践理性之基础的“定言律令”或者“绝对命令”也是以“矛盾律”作为基石。如果这样,那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无论是纯粹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的哲学形上学基础又在何方?用什么来保证逻辑理性本身的基础?
“限界”是现代知识真理性的保障。在这里,真理的本质被理解为“价值”问题和“有效性”问题,亦即“正确性”问题。而我们知道,“限界”所以成立在于“划界”,“划界”所以成立在于“逻辑理性”,“逻辑理性”的核心对康德来说是“矛盾律”,或者说,人类思维要严格遵循排除矛盾的定律。海德格尔继续追问,那么作为现代知识全部基石的“矛盾律”,其核心要害是什么呢?这里有两点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其一,矛盾律实际讲的是非矛盾律,它在知识论上的功能和作用范围是判断任何知识性命题以及命题系统的合法性。所以,矛盾律在根本上是任何判断理论的基础,即倘若可以从同一命题A中引出~A命题,则此判断不可能为真。或者更精确地说,它将命题Q和它的否定命题~Q二者同时在“同一方面”为真的任何命题P断定为假。其二,为什么矛盾律能够成立呢?这是因为A=A。我们知道,A=A是同一律。所以,矛盾律的根基在于同一律。相形之下,同一律更根本。这也就是康德在“先验论分析”“原理分析论”中讲完分析判断的至上原理之后立即转向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的原因。这里处理的问题就是主谓词判断之间的同一关系问题,但同一律的核心仅仅是判断问题吗?抑或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发问,即在存在层面上发问?这也是我们不能仅仅将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简单化约为语句命题判断中的系词“是”的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样,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海德格尔的思考就从康德的知识合法性和真理性问题,追到了西方哲学史上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到莱布尼茨被一再纠缠的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存在疑难。所以,当卡西尔诘问海德格尔关于“真理”的永恒、客观性以及主观相对主义的立场,他完全是站在了以矛盾律为基础的知识论判断真理观的立场上,而这一立场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它是否真正是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成长出来的康德哲学的正宗,这一切都是值得存疑的。如果借用牟宗三先生批评宋明理学长期以朱熹的《四书》解释为儒家正统去评判各家学说的做法,将之贬斥为“别子为宗”,海德格尔在此对卡西尔的康德解释的回应,也完全可以说持有相似的立场。所以,究竟谁的解释才是真正的“别子为宗”,“知识论的康德解释”还是“存在论的康德解释”?海德格尔的答案清楚明白。
三、“永恒真理”问题与时间性问题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海德格尔在这里提到“有效性”与“价值理论”,并以此来回应卡西尔关于海德格尔缺乏“普遍有效的永恒真理”的批评。海德格尔辩解道,当他说“真理相对于亲在而言”,他所持的立场并非是一个存在者层面上的唯我论立场,即将“真”视为某种“始终只是个别人所思所想的东西”,这实质上也是传统哲学所谓的或“知识论”、或“实践论”、或“美学”的立场。相反,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命题是个形而上学的命题”①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305页。,即这首先是个存在论层面上的本我论”的命题,而这才是康德哲学最核心的立场。这也就是海德格尔一再强调康德晚年对自己全部学说的核心问题的定位,即这个核心问题既非“我能够知道什么?” (第一批判),也非“我应当做什么?” (第二批判),更非“我可以希望什么?”第三批判),而是这个“我”,这个“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据此,康德全部的“三大批判”,归根结底就是作为去探索“人是什么”的第四批判。
这样就回到了卡西尔对海德格尔关于康德解释的“起点”与“终点”的责难。卡西尔批评海德格尔只看到了康德“主体论”的起点,而没有看到康德“永恒客观”的终点。海德格尔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责难只是回到了存在者层面上的“有效性”和“价值”的问题,而将“存在问题”遗忘或者干脆视而不见。在海德格尔看来,倘若我们只是从知识论的认识主体或实践论的自由主体出发,无论是通过理论理性的“主观演绎”或者“客观演绎”,还是通过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都不可能真正帮助我们从“此岸”的“主观相对性”达至“彼岸”的“客观永恒性”,因为这个此”和“彼”及其之间的绝对分离从一开始就被设为了前提。而这并不具备存在论上的“合法性”。所以,海德格尔才会说,人类理性的“丑闻”或“耻辱”不在于我们不能从“此岸”达至“彼岸”,从而用“彼岸”的“终点”来保障“此岸”的“起点”,而在于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想从“此岸”一跃而达至“彼岸”。换句话说,倘若从一开始就没有近代知识论中“起点/终点、主观/客观、相对/永恒、此岸/彼岸”之绝对分离,何来“一跃”之问?真可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 埃?”
我们为什么会在存在论上有上述种种“二元对立”的分离和对立?为什么会提出立基于“有效性”基础上的“永恒真理”的问题?海德格尔给出的“诊断”是由于我们关于“永恒时间”的观念。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有人说,在流动着的生命历程对面,有一持存不动的东西,就是那永恒者、就是意义和概念时,那他就对他的这个奇特的有效性给出了一个坏的解释。海德格尔发问,“在这里,真正的永恒究竟意味什么?我们究竟是从何处得知这一永恒性的?这种永恒性难道只是在时间的‘永远’之意义上的持存吗?”①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306页。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这种相对于流动生命对面的持存不动的永恒时间称为一个个“现在”的持续,即过去被视为已经逝去的“现在”,而未来则是尚未到来的“现在”。这样的时间观加上笛卡尔式的量的广延空间观,作为人类感性的先天内在直观形式(康德),才使得我们的感性直观知识,即最初的对象性知识成为可能。很明显,这种均匀持续流淌的永恒时间观属于牛顿以来经典自然科学尊奉的绝对时空观,它构成了“永恒真理观”的基 础。
因此,要真正回答卡西尔“客观”和“永恒真理”的责难,需要对“时间的本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时间的本质中就存有一种内在的超越性,时间不仅是那使得这一超越成为可能的东西,而且时间自身在本身中就具有某种境域化的特征。”②同上书,第307页。所以,我们在哲学存在论上不应当用持续现在的实体去说明时间的流逝以及与此相应的真实和真理,相反,我们应该用具有内在超越性本质的境域化源初性时间来说明实体的持存性以及与之相应的永恒时间观和真理观。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特别强调说,“在将要到来的、在正在回忆着的行为中,我总是同时就具有一个涵括了现在、将来与曾在之一般的境域,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超越存在论的时间规定性,而正是在这一时间规定性中,诸如实体的持存性那样的东西才被构建出来。”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