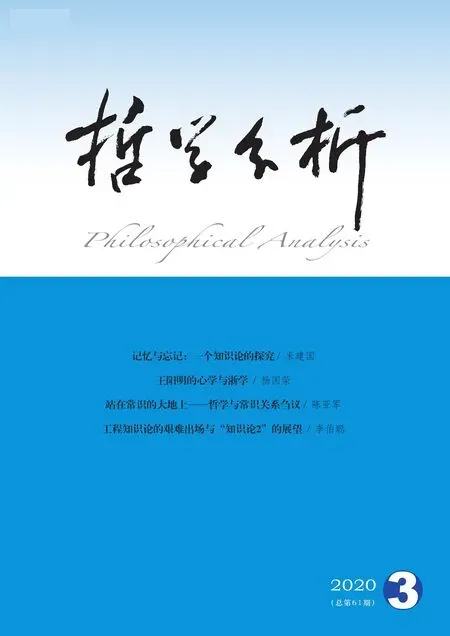从实践走向哲学观念的更新
俞宣孟
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7页。(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一篇宏文,至今已经有170多年了,它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传统哲学、实现哲学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我这里谈一下从马克思的实践观中可以引申出来的一种思想方法,即哲学就是对根据的追寻。进而从追寻根据的角度解说中国哲学之为哲学。
先来扼要谈一下我对这个提纲的核心思想的理解。虽然全部提纲篇幅不长,但也有11条之多,每一条都很重要,我把最后一条,即第11条,看作是整个纲领的总结,因而是纲领中的纲领。这一条是这样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同上书,第57页。这里复数的“哲学家们”,当指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由此来看,提纲从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为开始,最后的落脚点则是全部哲学本身。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进程,我认为,在批判旧唯物论的时候不涉及整个传统哲学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只有把整个传统哲学的特征拎出来,才能让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那种唯物论的弱点暴露无遗。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句话精辟地抓住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形态特征,对此不必怀疑。一部西方哲学史,看上去什么问题都谈,核心的问题有所谓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等,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从柏拉图确立的一个宗旨出发的,即要认知关于世界的真知识,这就开始了解释世界的历程。一踏上这条道路,所有的哲学家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一个前提,即有一个作为认知对象的世界,还有一个作为认知者的人,在哲学中,人是作为主客分离中的认知主体出场的。又因为知识前面加了一个“真”字,柏拉图把感觉中的知识看作不可靠的知识,只有理念、后来是思想概念,才能表达关于世界的真知识。所谓真知识,后来就逐渐明确为关于事物的本质、世界的最终原理。其最高形式就是所谓“是论”。由于用作表述事物本质和世界最高原理的概念必须是绝对普遍的概念,于是这种哲学始终伴随着质疑和反对:绝对普遍的概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绝对普遍的概念所表达的东西是否实有其事呢?既然概念表达的本质和原理对于可感的现象界事物具有优先的地位,那么,物质和精神究竟何者才是第一性的呢?这最后一个问题正是近代突出出来的,经过恩格斯的概括,成为我们熟知的贯穿在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条路线。然而,在马克思的《提纲》中,不管是唯心论还是(旧)唯物论,都是在解释世界,他们的差别只是使用的方式不同。
抓住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尤其重要。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主要是以西方传统哲学为样本整理出来的,它既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哲学精神,又不能符合西方哲学观念的要求,没有西方哲学那种形式的问题,因而中西之间很难进行哲学的对话。其结果是,依样画葫芦整理出来的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也遭到了怀疑。相反,如果我们明白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局限,感受到哲学本身需要变革的迫切性,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的束缚,如实表述中国哲学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中国哲学,还可以为形成新观念、新形态的哲学提供参考。反过来说,只有形成了新形态、新观念的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的“合法性”才能得到最后的确认。问题在于形成新的哲学观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只是”二字点出了传统哲学的局限,为哲学创新敞开了空间。哲学不该只是解释世界,那么,还可以是什么呢?马克思接着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改变世界”是不是哲学呢?对此马克思没有明说,我想字面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改变世界”是哲学之外的事情,但其重要性却在哲学之上。这样的理解并不违背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身份,他更关心的是改变社会制度的实际革命运动本身。但是,还有一种理解,如果马克思使用“只是”一词是批判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那么,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是不对的,是应当突破的;哲学还有其他许多事情,“改变世界”则是许多事情之一,且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这样的理解既传承了二千多年来这门古老学说的观念,即哲学应当涵盖所有学问,是各种学问的起点和根据;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性的要求:改变世界既是现实的要求,也应当有理论的支撑,而根本性的理论一定是哲学。我倾向于后一种理 解。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凸显了在“解释世界”之外,哲学还应当有的一件重要事情,即“改变世界”。但这并不表示“解释世界”之外的事情就终止于“改变世界”。起码,我们立即会想到“改造自己”,这也是哲学问题。马克思的话凸显了打破传统哲学的藩篱。然而,仅就这一点来说就很了不起,也很难。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来,直到康德、黑格尔,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大哲学家,都有自己的重大创建,我们还在不断地学习、理解、研究他们。然而,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创见,都还是停留在传统哲学范围内,是“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马克思想到的是一种崭新的哲学。所以恩格斯说:“……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788页,注51。“新世界观”当指一种对传统哲学实行了革命性变革的新的哲学,“萌芽”说明这还只是开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后人去探索、去展开。今天我们就来理解和探索一下。
二、实践观念的含义
前辈和时贤对《提纲》做过许多深入的研究,许多人都指出,《提纲》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实践”的观念。这是对的。这个全部才11条的提纲中,有8条、总共13次提到“实践”这个词。
人们重视“实践”的观念。但是,要真正理解“实践”并不容易。我们一向把哲学当作理论,甚至当作理论的理论,而实践毕竟是与理论有别的东西,甚至是站在理论对面的。于是有如下提问:今后的哲学还是理论吗?哲学是只“做”不“说”吗?或者哲学有“说”的话,说些什么?怎样说?实践与理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只是用来检验理论的吗?实践除了是认知理论的基础,还是什么东西的基础?它们是什么?这些都是由“实践”观念引发的问题,每个问题都会对传统哲学造成巨大的震动。
为了理解“实践”的观念,我先举《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卷》“实践”条为例:该条说,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的客观物质活动”。这个句子简约地说就是,实践是活动。但是这种“活动”有两部分修饰词,贴近的修饰词表明,实践是“客观物质活动”,然而,前面还有较长的修饰词“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世界的一切社会的”,简约地说就是,“人的社会的”活动。也就是说,实践活动既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又是客观物质的活动。一般理解,主观和客观是对立的双方,这里却混在一起了。这是不是搞错了?且慢,这个条目落款注明作者是前辈学者肖前,他行文、演讲一向以严谨著称。他这样写,一定是有根据的,根据就在马克思的《提纲》中。
《提纲》第一条开头就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人能够感觉到的东西(对象、现实、感性)看作是纯粹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客观的东西(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那是不对的。正确的理解方法是,应当把那些所谓客观的东西理解为也是对人而言的东西,即,“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东西。譬如拿起一块石头用作工具或武器,工具和武器就是人赋予这块石头的主观意义,哪怕路边随便一块石头,它的大小、颜色、重量,这些都是人与它打交道即实践的结果,因而都具有主观的性质。
马克思还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gegenstandliche)活动。”①参见《提纲》第1条,其中“对象性”一词特别标明德文原文,查德汉词典,这个词的意思是“物质性、物体”。思想客体,这是康德、黑格尔的观点,他们认为,真正客观的东西是用普遍必然的概念所表达的东西,因为达到了普遍必然性的思想,就不能有例外,也不是任何个人的想法可以改变的。譬如数学公式、物理定律,直至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因而他们称这样的思想是客体,是真正客观性的东西。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感觉中的东西倒是没有客观性的。②黑格尔说:“因此康德把符合思想规律的东西(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东西)叫作客观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完全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感官所直觉的事物无疑地是主观的,因为它们本身没有固定性,只是漂浮的和转瞬即逝的,而思想则具有永久性和内在持存性。”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9页)费尔巴哈显然不同意把思想的内容或对象说成是客观性的东西。然而,正如《提纲》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在感性的人和可感事物之间划分主客,这个划分是无效的。因为,人不是被动地知觉事物,而是在与事物打交道的实践活动中了解事物的,这个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也可以理解为“物质的”“物体”的活动。我想,肖前先生给实践下的定义,应该就是马克思《提纲》中这些文字的综合。虽然读起来有点困难,然而,其中透露出来的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观念的突 破。
首先,马克思打破了传统哲学对主客的僵硬划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显然把人和人能感觉的东西作为划分主客的标准,其中人是主观的,事物是客观的。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对的。外在的东西既然被我们感知了,就打上了人对它的感知方式的烙印,它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具有主观性的;同时,人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起码人所寄居的躯体就是物质性的。从前的唯物主义产生错误的原因在于,它不把人看作是处在与事物打交道关系中的人,即人是有目的地活动着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把感觉到的东西作为客观性的东西的标准,那么,思想的东西就不可能具有客观性。马克思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否认思维可能具有客观性,只是具体来说怎样的思维具有客观性,那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的哲学是一元论的哲学。主客分离是二元论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解释不清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意识和物质的关系,而且还导致传统哲学唯物论(从前的一切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实践则在主客未分之前,分出于未分,未分是分之前的原始状态,是可以分的根据,即在一元未分状态内在的分裂和矛盾中可以发现分的来历。用这个观点去看,可以获得对问题的深入理解。《提纲》第4条①《提纲》第4条全文是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关于宗教世界起源的观点:“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中被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55页。就是马克思运用这个方法的一个例证。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世界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马克思认为对宗教起源的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是不足以说明宗教世界起源的。说“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产生宗教,等于说是从宗教产生宗教。那么,说从世俗世界产生宗教对不对呢?也不对。因为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是同时产生的,正像胚胎发育中的左右手不是一者产生于另一者,它们都是从还没有分化的胚胎中产生出来的。宗教产生之前的世界不叫世俗世界,而是既非宗教世界、也非世俗世界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即“世俗基础”。“世俗基础”这个词在费尔巴哈这里是否就有了?我没有查。也许有了,因为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站在“世俗基础”上去解释,因为马克思接着的行文是:“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恩格斯于1888年将这个提纲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正式发表时去掉了“但是”一词,改写为:“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矛盾来说明”①《马克思论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59页。。恩格斯明确了马克思在“但是”后面的话是指费尔巴哈应当做而没有做的工作。我认为,马克思想法的关键是,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产生前的世界是一个与前两者不在同一层次上的世界,关于这另一层次的世界,马克思抛弃了“世界”而代之以“基础”。他的这种思想方法在这条提纲最后几句话中又一次得到体现,他说:“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②同上书,第55页。。世俗家庭是相对于神圣家族而言的,在神圣家族产生之前,家庭还是家庭,但它不是与神圣家族相对意义上的世俗家庭,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庭,因而,世俗家庭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恩格斯将原文修改为:“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③同上书,第59页。看来恩格斯在此未能理解马克思的想法。马克思透露出来的想法是,产生成对社会现象的基础,是与成对现象成立于其中的社会不同性质的社会。就好像分子是在原子基础上组成的,但是分子一旦组成,就与原子形成两个不同层次的物质存在形式。这个思想方式很重要。人们容易把它忽略,那是因为当我们只注意现成事物的时候,把现成事物表述为“是” (什么),那个作为基础或根据的东西就成了“不是” (什 么)。
第三,实践是“非本体性”的观念。本体或曰实体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全部哲学几乎都围绕着它进行,它代表事物的本质,各种特征都依附于它,而它本身则是独立存在的。对实体本身的界定,即它究竟是物质性的还是思想性的,遂产生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跳开一步看,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追问世界究竟是什么,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哲学是关于那个一般的“是者之为是者”的学问。而实践观念则是非本体性,它深入到各种观念产生的根源中,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行动的本质”④海德格尔《关于论人道主义的书信》:“行动的本质是完成。完成就是:把一种东西展开出它的丰富的内容来,把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带出来,producre(完成)。” [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 (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9页]中把事情带出来,即让各种东西是其所是。事实上,进入近代以后,许多哲学家都力图摆脱本体的纠缠,他们或者从追问“是什么” (what)转向“何以” (how),或者提出过程、关系,还有“间性”,把这些都看作是在本体之前的东西。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观念比较早就启动了这个方向,如我们所见,表现在对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神圣家族和世俗家庭起源问题的论述上。实践是先于本体的,现在人们用“实践一元论”来称呼它,这正是表达了实践是哲学的起点的观点。从实践中分离出物质和意识的区分,实践在物质和意识分离之前。但是要真正把握这个观念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哲学就是以本体为中心的,即使没有出现本体这个词,其思想方法还是拘泥于思考本体的方法。具体说,不把实践看作意识和物质的历史性的出处,而是结构性地把实践看作是物质和意识的综合,即,把物质和意识看作是在实践之前就确定的东西。这就有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实践条目的表述:需要借助于物质和意识来表述实践。
马克思实践观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重要的一点是打破了唯物和唯心的对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宣称自己是一元论,是唯一的出发点。但是,它们互相不能克服对方,它们的共存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特征,从整体上说,西方传统哲学是二元论的。马克思的实践超越这种二元论。这种超越,不是进一步的向上抽象、概括,而是向下,去发现它们共同的根基。这种超越,不是引向纯粹概念的思辨,而是把哲学重新安置到实际生活的方面,从而将要冲破传统哲学只是一门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的学问的局限,让哲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哲学成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伴随着哲学观念的变更,原来的学问分类也将在同一根基上重新组合,所谓认识论、价值论、美学、伦理学不再各自分离。不过,包含在“萌芽”里的那些可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沿着实践观启示的方向,有许多艰巨而富有成果的工作要做。
三、实践观对于哲学发展的两种意义
马克思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萌芽之为萌芽,是初步的,其中包含着种种尚未知的、可能的发育生长。马克思立足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已经把自己的哲学观直接运用于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推动社会革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就哲学这门学科本身而言,马克思的这个“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还有许许多多的方面有待后人去探索、去丰富、去发展。当我们去考虑这个发展的时候,先要将其可能的方向梳理出来。
有两个意义可以考虑。第一,沿着实践开辟的道路去展开各种论述,就像马克思当年做过的。在这个短短的提纲里,马克思以实践作为根据,解释了许多问题。他用实践、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主体和客体、人的活动和对象性的活动;用实践解释人的思维的客观实在性问题;用实践的观念解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的改变的一致性,解释教育者和受教育的关系;解释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神圣家族和世俗家庭的起源,等等。尤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提纲第6条阐释了人的本质问题,这是一个在哲学中时时要遇到的大问题。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从作为普遍性的“类”的方面去理解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则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56页。。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实践这个词,然而,“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说法就是实践的进一步落实或具体化,是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结成的关系,它区别于人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实践观为根据,传统哲学的许多问题就获得了新的解释。例如,在传统哲学中,普遍性的“类”不仅是用来解释人的本质的,而且是解释一切事物的本质的方法;个别的事物被认为是有变化、有生灭的,而个别事物归属的那个普遍概念则是不变的、永恒的,因此一切事物的本质都要用普遍的概念来表达。也是根据实践,传统哲学所不及的“改变世界”的问题进入了哲学,哲学的眼界大大开阔了。以实践为根据,还有许多问题,不管传统哲学涉及过还是没有涉及过,都可以进入哲学的视野,甚至那些在传统哲学中有过解释的,也可以获得更深入、更合乎真理的解释。在马克思已经开辟的这个领域或方向里,有待完成的工作做不完。
但是,我们还有第二种意义。关于这个意义我们可以从思考马克思为什么能从实践观的确立中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功入手。我觉得,马克思之所以在哲学领域有重大的斩获,根本原因是他改变了哲学的出发点或前提。传统哲学的出发点是寻找关于世界的真理,其前提是有一个既定的世界和一个对世界做观察的人。这样,人就被定位为一个认识的主体。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人不仅是一个对世界的认识者,照马克思的理解,人更是一个对世界的改造者。这后一个规定性进一步可以被理解为,人就是一个生存 者。
应该看到,这第二个意义上的发展是造成第一个意义上的各种成就的原因。实践观念的提出,将传统哲学的前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蕴含着的意思是:哲学不再从主客分离的立场出发,而是要在实践中追溯主客分离之前的状态。
前提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带来学问的变革。关于这个道理在科学哲学领域,库恩作过专门阐述,在《科学革命的结构》②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库恩所谓“范式”的变化,就是一门学问的对象和方法的变化,这个道理是容易理解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关研究方法的改变当然会产生一门新的学问,例如,同样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学与化学,从力学到量子力学,都是革命性的变革。即使在同一门学问内,例如在几何学内,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即从对平坦的平面到曲面的研究,就有了从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的变化。结合物理和化学就产生了一门物理化学。这些都是从前提的变化造成的学问革新。前提作为一门学问的出发点,也是这门学问的根据。所以前提的变化就是根据的变化。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谈哲学,实践就是他的理论的根据。相对于传统哲学来说,他找到了一个比传统哲学更深的根据。正因为这个根据比传统哲学深,他不仅可以据此对传统哲学的问题提出更正确、深刻的解释(如关于人的本质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被传统哲学遗漏的问题(如改造世界问题)。可见,哲学革新的关键在于前提的革新、根据的革新,而且这个新提出的根据要比原来的根据更深,而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前提的变更,如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那样。以实践观念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比传统哲学深刻,是因为传统哲学是从主客分离的立场出发的,而实践观念则让人触及主客未分的领域。在这里,主客如何分离将成为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进入视野,另一个问题马上就伴随着产生了,即主客有几种形式的分离?马克思已经提示,人不仅可以作为认知世界的主体,他同时也是改造世界的主体。此外,人作为审美的主体、伦理的主体、情绪的主体等,也并不是完全能够纳入认识论就能够解释清楚的。①这里我想起我国学界曾热烈讨论过的美的本质问题,出现两种观点,或者把美当作纯粹主观性质的东西,或者当作纯粹客观性质的东西,双方都不足以说服对方,陷入这种争论胶着的原因是,双方都站在包含着两个对立立场的、属于同一层次的前提,即参照着认识论的立场,把问题分成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这场讨论中还出现第三种立场,即李泽厚先生的主张,他认为美的本质当在主客结合中去解说。那么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客结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应当是反思当下的美的感受,其中有我的感受和为之而感到美的对象。用现象学的话来说,美是包含着意向和意向对象的纯粹现象。只是在反思中,人们才把它分为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对象,当下的感受是基础性的、在先的,没有那种感受,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分析。
实践之所以能够作为根据,因为它存在于主客区分之前,让哲学从思辨活动倒回到生活中。这不是要根本取消哲学的思辨性,而是要揭示思辨活动的起源。我们日常从事各种活动的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区分主客,人越是全神贯注于事情,就越是将自己融入到事情中,在这里,事情本身就是自己,自己也是事情的组成部分。譬如一辆飞驰在道路上的车,车子向前是人的意志,人是在车里前进的,甚至道路环境也是向前运动这个现象的构成部分。只是当出现车辆故障或道路障碍时,前进停止了,人才会从刚才的状态中抽身出来对车子、道路采取检视的态度,这时人和环境才进入了主客状态。思辨活动发生在主客区分之后的进一步反思中。
马克思在第二个意义上的发展就是为哲学寻求更深的根据。我们一般容易看到上述第一个意义的发展,在这个方向中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而看不到寻求更深的根据是更本质性的发展。实际上,第二个意义所揭示的才是真正的哲学精神。哲学就是向着根据不断地追问,刨根究底,直至不能追问。
那么,已经找到了实践这个根据,我们今天还有必要进一步去寻求更深的根据吗?怎样去推进这种深入过程呢?进一步挖下去我们将会遇到什么呢?
四、从实践观念到根据的观念
马克思导致哲学革命的根本方法是为哲学寻找更深的根据。他是从克服传统哲学主客分离、对立中提出实践观念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中西哲学的分离或对立。站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立场上,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身份受到了质疑。为中国哲学作辩护,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名分之争,而是关系到哲学本身的发展。中西哲学的相遇,正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契机。而这种发展不是将中国哲学依傍着西方哲学做阐述,也不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去解说西方哲学,更不是像有人曾提出的将二者向更普遍的层次的提升。因为这后一种途径正是落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并且已经显出了它的局限。唯一可能的途径是像马克思那样向下挖掘,去寻求哲学本身的最终根据。如果这样去想,一系列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例如,马克思是针对主客分离的情况深入挖掘的,那么,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或对立的症结究竟是什么?哲学是否真的存在着一个最终的根据?对这个最终根据的挖掘将把我们带向哪 里?
马克思是从传统哲学主客分离、对立这一情况深挖它们的根据,那么中西哲学二者间也找得到这种明显对立的特征以便我们能寻找到它们共同的根据吗?通过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学界对中西哲学各自的特征作了多方面的概括,一种流行的见解是,把西方哲学说成是世界观,而中国哲学则是伦理的,是人本哲学。或者有人会说,西方哲学虽然以追问世界的普遍知识为主要宗旨,但它也有伦理学,有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是的,然而仔细体会的话可以发现,西方哲学是以观察世界的方法用于观察人,在考察人的时候是把人当作客体的,那不仅反映在人的本质要从普遍性的类的方面去定义,而且还出现了人是机器这样的说法。中国哲学对于自然的单独研究比较少,这点是比较公认的。所以,我认为,上述关于中西哲学各自特征的区别的界定从表面上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之所以说只是从表面上看可以成立,因为这里对中国哲学的特征的表述还是对照着西方哲学来看的,这样看的时候已经对中国哲学作了拦腰截取,关于这点,稍后再谈。
即使明确了上面这一点,要找出它们共同的根据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里先要说明,寻找根据的方法也不止一种,主要有逻辑的和历史的两种。逻辑根据的运用是在一个既定的体系内从上到下、以普遍对具体的统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否能纳入一种体系,所以这个方法还不能用。历史的方法解释的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冯友兰先生论中国哲学特征时讲过,中国哲学纠缠在一个“生”字上,这就指出了历史的方法的特征。用这种思路去追寻中西哲学共同的根据,就是要问,中西两种不同形态、不同宗旨的哲学的区分是从怎样的一种未加区分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追问中西哲学的共同根据,这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因为提到了历史的方法,有人立刻想到的是哲学产生的历史。在西方,有人把神话当作哲学的先驱,在中国,有人把哲学看作起源于巫术(李泽厚)。他们讲的是中西哲学各自的历史,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哲学根 据。
对哲学的根据的追问是从对哲学既有的前提或根据的进一步追问。从西方哲学来说,洋洋洒洒,其开端就是寻求关于世界的知识,这就是它的前提,它的根据。然而,对于哲学为什么要从认识世界开始,尤其是,哲学何以能够从认识世界开始,即天地间为什么会出现认识世界的活动,以至于展现出我们认识中的那幅世界的面貌,对这些问题传统哲学本身并不予以回答。或者以为,人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必定要去认识自然世界,自然世界的存在还需要证明吗?胡塞尔则不然,他说,把世界看成客观存在是自然主义的态度,他想从(意识)现象一元论出发,解说对世界的各种看法形成的过程,自然的看法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起步时的出发点倒是要解释数的本质,进而解释一切普遍性观念的本质。胡塞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①泰奥多·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序言”第9页。,“他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纪的思想史地图”②同上书,“中文版前言”第1页。。这里且不全面评论胡塞尔哲学的得失,我只是指出,他所做的就是把传统哲学据为开端的前提向前移了,移到了一切从中得到显示的意识中。他的这种思想不久就被海德格尔修正了。照胡塞尔的观点,主客双方都是从意识中开显出来的,难道意识可以没有寄存处?它是孤零零地飘荡着的先验意识?海德格尔为它找出了一个寄存处,给了它一个名称叫作“此是” (Dasein),在这里,“是”保存了意识的特征,但这种意识不是纯粹的意识,而是伴随着人的生存活动的意识。这样,海德格尔同样开掘到了超越传统哲学的根据的深处,把哲学的开端前移到一个意识和环境世界尚未开显、而其本身保留着各种开显可能性的承载者。海德格尔的哲学和胡塞尔的一样,都对当今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它们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是向下挖掘既定哲学的根据,即将哲学的前提向前掘进。
前面提到,把中国哲学的特征概括为以伦理问题为主的人本哲学,这个说法已经将中国哲学作了拦腰截取,这只是对照着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寻找相近内容的结果。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哲学,“是论” (ontology)才是其核心部分,是纯粹哲学,伦理学只是作为实践哲学而成为哲学的一部分,因此,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即使中国哲学有关于伦理的丰富论述,也不能保证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合法性。那么不去对照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呢?中国哲学的特征就其自身来讲,是一个做什么样人的问题。在儒要成圣,在道要成仙,至于在佛,则要成佛。这还是一个结果,深入下去就进入了对根据的思考。且将佛家放在一边,就儒道二家而言,他们要成圣、成仙的根据是相同的,即所谓天人合一。因为天人合一,所以就儒家而言,人的行为要符合大道,做人要做到孔子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而对道家来说,他们相信人能够羽化进天地,达到长生不老。到了这里,还不是最后的根据,因为还可以问,天人合一之前呢?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这样问过,并且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赫然写在《周易·系辞》里的话:“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是什么东西?从字面上说,就是在幽深遥远处的一个端点。所谓两仪、四象、八卦,是解说卦的形成,说太极中产生出阴、阳两爻,两爻有四种位置的排列:阳阳、阴阴、阳阴和阴阳,将阴阳爻填入三个位置,就产生八个排列,即所谓八经卦。每个经卦与其余七个经卦置入上下位置的组合,加上自身的上下重叠的一卦,共得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象征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事变,其中有吉有凶。人类的事业无非是在避凶趋吉中展开出来的。在系辞的其他段落,更是形象地解说天地万物和人类自身及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从太极中衍生出来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周易·系辞》将各种事物、各种现象都归结为从太极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结果,包括思想观念,有些解释至今仍素朴可通。例如关于“类”的观念,这在西方哲学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连逻辑也是在有了“类”观念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但是产生“类”观念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照胡塞尔的说法,以此为基础的所有科学都是“不完善”①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的。《周易·系辞》解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这就是说,对各种事物的辨识、分类,是与它们对人类造成吉凶不同结果密切相关的。无论什么现象,都要追究它们的根据,这个根据不是逻辑的前提,而是与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相随的历史的起始。包括可以用作逻辑的“类”观念,以及建立在类观念基础上的一般、普遍观念也可以,而且应该这样去考察。
康德揭示了运用形式逻辑的形而上学的矛盾后仍然说,“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这个意思是说,人类的思想总是要不断的追问。这种说法有真理的成分,但是,他为追问规定的方向是片面的,因为他遵循的方向是为构成普遍必然知识的理念的先天存在和理念本身的合理运作作论证。《周易》则深入到人的原始生存状态中挖掘“类”观念的产生。形象地说,前者引导思想向上,后者则向下,其所追问的问题直入“类”观念产生的根据。
五、哲学:对最终根据的追索
自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我们看到了它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启的方向上的丰富发展,尤其是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于是一阵目眩,几乎把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活动及其成就遮蔽掉了。只有揭示了哲学原来是不断的追问,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方向上的追问,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哲学也是对一切根据的彻底追问。我想,进一步的工作不仅可以解释西方那种哲学方向的原因,还可以说明中国哲学为什么没有采取西方哲学方向的原因。这些都是今后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这篇短文里,我想先简单说明一下,在中国哲学采取的方向里,围绕着最终根据,其深入的内容同样是丰富多彩、值得借鉴的。
关于对最终根据的探寻。中国古人是明确意识到要对最终根据做出探索的。庄子《齐物论》一篇反映了这个探索过程的一些思考。“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乎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乎未始有无也者。”显然,庄子思考过,关于最初的开端,是可以一直追溯上去的。先想到一个“始”,但可以有连这个“始”也没有想到的时候,还可以有连这个“没有想到”也没有想到的时候。同样,如果把“无”看作是“有”的起点,那么,这个无”也有更早的“未始有无”的时候,进一步还有“未始有无”之前的情况。这里揭示的是,对“有”之前的开端的思考可以是无穷尽的。然而庄子又写道:“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又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这是说,古代的人知道应该有个确定的起点。从这个起点演化出物,物从无差别到有差别(封)。最终的根据也是一切过程的起点。从起点出发以后,起点往往被遗忘,表达为道之亏损。
关于最终根据的性质。前面提到,中国哲学把最终的根据归结到太极。到了宋代的时候,周敦颐又提出“无极而太极”,引起朱熹和陆九渊一阵不着边际的争论。我觉得,最终根据应当是不能进一步追问的东西,它应该是一;它又应该不是任何已知、生成的东西。但是,《周易》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同时,又用乾坤、刚柔等两种对立的力量或现象来描述它。这容易造成太极是两种东西的组合。“无极而太极”这个说法就明确了太极在各种因素之前,一切是太极生出来的。同时,无极也阻止了思想无穷尽的追问。如果无穷尽的追问是可能,那么,一切追问都是无意义的。
道和太极的关系。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是把道看作开端的,“无”是道的性质。然而《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阴阳是太极内相互作用的一种因素。从开端方面讲,太极与道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表达;但二者也有区别:太极是从开端方面讲的,道主要是从太极展开的过程方面讲的。
怎样把握最终的根据。最终的根据肯定是有的,但是把握起来不容易。庄子齐物论》表达了这个想法:“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这就是说,如果开端是一,一切都还没有分化,如果人去把这个一说出来,哪怕只是作这样的想法,在说和想的时候,人就在一之外了。这个批评也适用于谈论道。道既然有无的性质,绝对的无是不能生出任何东西的,能够说出无就已经不是无了。儒家对这个瓶颈的突破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关键一步。这写在《中庸》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切都是从开端发生出来的,把发生出来的东西收敛起来就可以回到开端的状态,喜怒哀乐是自身当下常在的简单状态,倒溯上去,就体会到了未发时的原始状 态。
把握了最终根据又怎样?《中庸》接着上面这句话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原来我们自己是参与在从开端处生发出来的过程中的,这就要求行动得当,要中节。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达到了“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了。这才见出成圣的根据。
理在事中,事在理中。回溯到最终的根据,从根据出发展开人生活动,一进一出,二者的综合就是从事中国哲学的道路,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学》把这条道路概括为修、齐、治、平。这是一个完整的表述,有开端,有落脚处。接下来的事情还有什么呢?道理已经讲透了,以后就是不断在变化的事中去体会,这大概就是中国哲学著作不需产生一个一个体系,而只是通过注经的形式不断更新自己的体会,同时将道理落实到事中。开端看来是遥远的、不可及的,但是,如果事事都从无的境界而“发”,那么,当下就是开端。这样说来,人生就是哲学一番,人生常新,哲学也是常新的。这就是我以包含在实践观中的哲学方法思考中国哲学的简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