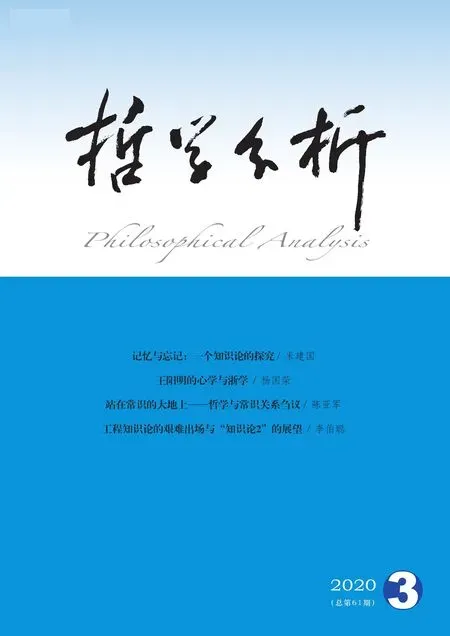记忆与忘记:一个知识论的探究
米建国
一、前 言
人类获取知识的认知机制或形成知识的主要来源,大致是来自我们的五官知觉(sense perceptions)、记忆、推理、直觉、内观(introspection)和证词(testimony)。这些认知机制或知识来源,对于在追求知识过程中所形成的“真信念”而言,都是重要的“证成” (justification)来源所在,而对于(以能力为基础的)德性知识论主张者来说,这些认知机制更是所谓构成知识的“智德” (intellectual virtues),或者是良好可靠的认知能力。一直以来,对于这些认知机制或能力的研究(不论是科学中的研究,还是哲学上的探讨),大多聚焦于五官知觉,而由五官知觉所形成的知觉信念,更是许多研究(不论是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心灵哲学,还是知识论)的标准范例。相较之下,“记忆”这个议题,则被科学家与哲学家普遍地忽略;同样的情形,当然也可以被印证在直觉与证词这些议题之上。
然而,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几乎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被“储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不论是个人的记忆还是群体的记忆,不论是历史图书的记载抑或是巨量数位的记忆。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我们利用五官所形成的许多知觉信念,也大都需要依赖我们的记忆支持,才能用来加以辨识与分别。如果我们也同意人类的行动、表现、决策与判断都预设了许多的“背景知识”,这其实就是在强调“记忆”足以成为人类行动的必要条件。更何况作为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人的“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也和“记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记忆扮演如此根本而重要的角色,我们对于这个认知机制或能力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我们对于“记忆”这个概念,在哲学上又有多少的掌握呢?
二、问题与困难
什么是“记忆”?一个日常最普通的想法,或者一个传统哲学中最主流的看法是:记忆就是我们把过去的经验予以储存起来(keep our past experiences in he“storehouse”)。当然,过去的经验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对象与内容,它们可以是某个事件、某个人的脸、某本书所出现的某个句子、某种感觉,甚至某个艺术作品。基于记忆之中的不同对象与内容,我们当然有必要为不同的记忆加以分类,不论是在科学上的分类、心理学上的分类,还是哲学上的分类。这些分类的结果,不得不让我们加以深省,究竟“记忆”这个概念能不能作为一种“自然类” (a natural kind)?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记忆是把我们过去的经验“储存”起来,我们把它储存在哪里?洛克的用词“storehouse”当然只是个隐喻(虽然这个隐喻符合大多数人对于记忆的直觉),即使这个隐喻是正确的,我们还是得追问,这个记忆的storehouse”位于人类的哪个部分?“心灵”“头部”或“大脑的某个区块”?我们又是如何“储存”我们的经验的?“随意放置”“加以分类”,还是“个别编码”?我们又该如何“提取”我们记忆中的经验?“任意抽取”“随机选用”,还是“系统译码”?这些问题,似乎都不是一般的想法或者传统哲学的隐喻所能够轻易解决的。
什么是“忘记”?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忘记”只是“记忆”的相反(就像“假”只是“真”的相反),那么只要我们了解什么是“记忆”之后,我们不就可以清楚知道什么是“忘记”吗?(就像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定义,我们不就也能清楚掌握什么是“假”了吗?)基于这个想法(“记忆”与“忘记”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我们日常最一般的想法是:忘记就是失去了记忆,或者记忆的丧失。传统西方哲学家(相对少数)尽管对“记忆”有些零星的看法,但对“忘记”却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争论与见解(特别是传统经验主义与当代英美哲学)。在一般传统心理学中,“忘记”也被视为无法回忆过去的信息,或者是失去记忆的能力(inability to recall information)。但是这个失去记忆能力的现象,却有着程度上的差异:最一般的忘记可能只是无法唤起或回想起对一般的琐事或长久以前的经验所形成的记忆;进一步还有所谓“健忘” (forgetfulness)的现象,也就是经常性地出现忘记的情形;最严重的可以达到所谓“失智症” (Dementia)的状态,或是近年来在医学上最常见的“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不论忘记的程度高低(从一般偶尔忘记,到经常性的健忘,甚至出现严重的失忆症状),“忘记”似乎都被用来和“记忆”这个认知机制加以对照,忘记似乎都只是记忆功能的退化或丧失:忘记程度的严重与否,都可以被记忆功能运作程度的高低或好坏加以解释。
但是,“忘记”真的只是“记忆”的丧失而已吗?忘记和记忆真的只是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而已吗?首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柏拉图对于记忆与忘记的看法。对柏拉图而言,通过“回忆”是我们恢复或重拾知识的唯一方法(因为真正的知识本来就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只是我们的灵魂在来到这个物质世界时忘记了我们原本所拥有的知识)。所以,忘记似乎是对回忆的一种威胁。然而,当代有一些对于柏拉图有关“forgetting”的诠释,倾向于区别柏拉图哲学中“forgetting [έπιλήθομαι]”与“oblivion [λελη]”两者之间的不同,前者是指“删除” (也即忘记是一种记忆的删除),而后者则是指“遗忘”或“隐藏” (也即“遗忘”是把记忆中的知识暂时加以隐藏,有待未来加以彰显)。在这个区别之下,“忘” (forgetting)可以是一种“忘记”(把记忆中的经验加以删除),也可以是一种“遗忘” (把记忆中的经验暂时隐藏起来或抛诸脑后),前者是对记忆的一种威胁,因为它代表记忆的丧失,而后者则未必和记忆完全对立,它只是暂时把记忆隐藏起来,并没有将之“丢弃”。有时候把记忆隐藏起来反而是对记忆的帮助,而不是威胁。
其次,依据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份对于“记忆问题”的健康报道,偶尔忘记一些东西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且随着人的年纪增长,许多人对于某些事情更会产生逐渐健忘的现象。健康的人经常会体验到记忆的丧失与记忆的扭曲,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些记忆的缺陷会逐渐明显,但是依据他们的研究与统计,只要不至于出现像阿兹海默症或其他类似的严重失忆疾病的症状,这些失忆的现象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常状态。而依据记忆毛病(memory problems)的轻重,可以出现下列七种型态的记忆问题:(1)稍纵即逝的记忆(Transcience);(2)心不在焉的记忆(Absentmindedness);(3)一时阻塞的记忆(Blocking);(4)随时间流逝而产生错误的记忆(Misattribution);(5)由误导所产生不真实的记忆(Suggestibility);(6)由偏见所形成扭曲的记忆(Bias);(7)挥之不去的记忆(Persistence)。但是这七种记忆问题的类型并不见得都是记忆的缺陷问题,也不见得对人类的认知与行动会产生任何威胁或不良的影响,有些忘记的情况反而会为人类的认知或情绪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例如(1)稍纵即逝的记忆(short-term memory)本来就是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人类的记忆有进有出,有的会长久保留,有的会很快消失,这对人类不断学习与经验的一生,反而是个良好的自然消长之记忆资源回收、汰换、再生长的循环过程(recycling process)。有关(2)心不在焉的记忆,反而有一点类似柏拉图对于“oblivion [λελη]”的看法,对于有些事我们并不特别在意,甚至加以遗忘,从健康的角度,这对人类身心都有实质的帮助。至于(7)则不是一般所谓记忆的丧失问题,反而是对于有些事物无法忘怀,导致心理上许多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会产生记忆强迫症”的严重心理疾病。这个记忆的问题与毛病很自然地将我们引导进入下一个心理学中重要而有趣的例子。
在认知科学的领域中,不能正常记忆也许是个缺失或障碍,但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不能忘记(或者不能遗忘)反而有时会是个心理上的缺陷,或者有时候会给当事人带来学习与生活上的许多困扰与阻碍。在一个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个案中,案例的主角吉尔·普赖斯(Jill Price)是位具有几乎完美记忆的女士(“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她可以对过去30年来所发生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记得一清二楚,而过去这30年的历史记忆也不断地缠绕着她。这个超强的记忆对吉尔当然会产生一些高于常人的好处,但是这个不断回放、斩之不断的记忆也不断地阻碍吉尔学习更多新的知识,甚至让她有了某种情绪障碍与人格失序的问题。如果记忆是人类认知的重要功能之一,在吉尔这个例子当中,是否显示出“忘记”可能也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或心理功能?虽然“忘记”可能还是和“记忆”互相对立的概念,但这并不表示忘记就一定是记忆功能的丧失所产生的结果,过度记忆也有可能是忘记(或遗忘)这个(调节)功能丧失所产生的结果。“忘记”可能是个平衡各种心理状态的一种重要功能,更有可能也是人类认知机制中的一个重要能力,不能忘记或遗忘的人,有时候是对人类认知的一种障碍,对人类身心正常发展也是一种威胁。在西方主流传统的思想中,把“忘记”当作一种心理功能或者认知机制下的一种能力,很有可能无法被认同,也很难找到支持的理论,但是在中国哲学传统的思想中(特别是先秦以来道家思想的传统),“忘”反而是个重要的心理功能或修养功夫。
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讨论中,有很多文献专注于讨论庄子的“忘”的功夫或“忘”的哲学,特别是“坐忘”这个重要的概念。然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大部分中国哲学的讨论中,多半把“忘”的哲学讨论聚焦于功夫论、人生哲学、实践哲学、伦理学,甚至形上学的讨论上,而忽略了“忘”与“记忆”之间的密切关联,也不多论“忘”在认知科学、心理学(或道德心理学)与知识论中的重要角色。无论如何,在近两三年来有关西方哲学对于“记忆”的许多文献当中,有一本由尼库林(Dmitri Nikulin)所主编的有关记忆的论文集①Dmitri Nikulin,Memory:A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它收录了一篇由华人学者陈霞(Xia Chen)所撰写的文章,标题为《道家中的记忆与遗忘 》 (“Memory and Forgetfulness in Daoism”),它是在十几篇回顾与谈论西方哲学发展过程对于“记忆”的诸多讨论中,唯一一篇有关中国哲学的讨论。然而比较讽刺的是,此篇论文虽然标题定为道家的记忆与遗忘,但整篇文章几乎都是在谈庄子对于“忘”的想法,完全没有讨论到记忆的相关问题;除此之外,作者在一开始对比儒家与道家时,宣称儒家强调记忆,但是道家却强调“忘”。大多熟知中国哲学的人都会同意道家对于“忘”的重视程度,但我不确定有多少人会同意儒家特别强调“记忆”这个概念。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证据与论述,才能下此定论。无论如何,作者指出在庄子的文献中,一共出现了超过80次以上的“忘”,这确实是个惊人的数字,也可以想见庄子思想中,“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至少我们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一个与西方哲学的有趣对比:也就是,当西方传统哲学特别着重对于“记忆”的探讨时,中国哲学却偏重对于“忘”的论述,虽然这个“忘”的概念可能同时包含了(相较于柏拉图)“忘记”与“遗忘”的意义,也很有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功夫修养的内涵(除了在心理学与认知或认识意义下的“忘记”之外)。至少,我们在中国哲学的启发之下,又可以论证“忘记”与“记忆”并不见得是绝对对立的一对概念。更重要的是,“记忆”并不总是具有积极正面的功能,“忘记”也不见得只能躲藏在记忆的背后,永远只是个消极负面的角色。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庄子的哲学中,“忘”才是真正的主角。
最近几年,当“记忆”哲学在英美,甚至德国、法国、意大利、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正如火如荼地积极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开始看到“记忆”的知识论(Epistemology of Memory)也逐渐占据舞台的中心位置,开始和心理学、认知科学与大脑神经科学有许多密切的互动与合作,把传统哲学中有关记忆的形上学、心灵哲学与伦理学的讨论,继续往前推进。在这个最新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推进其进展的两位领军哲学家:博内克(Sven Bernecker)与米克艾力安(Kourken Michaelian)。在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记忆”哲学的同时,也不忘强调“忘记”在整个理论系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米克艾力安在2011年所发表的《忘记的知识论》 (“The Epistemology of Forgetting”) 这篇文章,最能代表这个议题的创新性与重要性。米克艾力安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要论证:一个有限的认知主体,如果他的记忆功能要能够良好正常运作,必须有某种型态的“忘记”扮演着必要条件的角色;其次,“消除”我们记忆中许多不必要的障碍,反而可以使主体在整体的信念系统中保持一个最佳的认知状态;最后,通过心理学的研究与报告,正常人的日常“忘记”现象不仅不是一种缺陷或病态,反而是一种“德性”的特征表现。另外,博内克也在2016年10月一次访问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的讲座中,以及在2017年发表的《来自忘记的知识》 (“Knowledge from Forgetting”)文章中,试图提出“忘记”在盖蒂尔(Gettier)知识论的传统中,也可以在定义“什么是知识”时,是提供证据与证成的一个重要元素。也就是说,“基于忘记所形成的真信念”有时候也可以为主体带来“知识”。这两位哲学家对于“忘记”所提出的知识论主张,同时会对后盖蒂尔的内在论者与外在论者带来困难与麻烦,其实也会给最新发展出来的德性知识论者带来一个立即与直接的挑战。这个困难与挑战可以被叙述如下。
(一) 对于内在论所产生的难题
(1) 知识是加以证成的真信念(再加上可以避开盖蒂尔反例的其他必要条件)。内在论者的主张)
(2)“记忆”是我们形成真信念的重要证成来源条件之一。
(3)“忘记”是“记忆”的丧失,忘记不仅不能构成证成的条件,反而是个破坏者(defeater)的角色。(传统知识论之内在论者对于“忘记”的看法)
(4)“忘记”可以在主体形成真信念时,提供一个证成的基础。[索萨(Ernest Sosa)与米建国的论 证]
(5)(3)与(4)是互相矛盾的。
(6) 所以,内在论者出现了“记忆”证成的难题。
(二) 对于外在论者所产生的难题
(1) 知识是通过一种可靠的认知过程所形成的真信念。(外在论者的主张)
(2)“记忆”是我们形成真信念过程中一种可靠的认知过程。
(3)“忘记”是“记忆”这个认知机制出现了毛病,“忘记”本身使得记忆变得不可靠。(传统知识论之外在论者对于“忘记”的看法)
(4)“忘记”可以在主体形成真信念时,提供一个可靠的认知过程。(博内克的论
证)
(5)(3)与(4)是互相矛盾的。
(6) 所以,外在论者出现了“记忆”这个可靠认知过程的难 题。
(三) 对于德性知识论所产生的难题
(1) 知识是主体在形成真信念时展现它的智德的一种认知表现。(德性知识论者的主张)
(2)“记忆”是我们形成真信念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种智德。
(3)“忘记”是“记忆”的丧失,“忘记”本身是一种智恶(intellectual vice)。(德性知识论者的看法)
(4)“忘记”可以在主体形成真信念时,也表现出一种智德。(米克艾力安与庄子的论证)
(5)(3)与(4)是互相矛盾的。
(6) 所以,德性知识论者出现了“记忆”这个智德展现认知过程的难题。
以上人们针对内在论、外在论与德性知识论所分别提出的有关“记忆”的困难,可以被视为是由“忘记的难题” (the problem of forgetting)所引出的困难。①详细的难题与论证,请参见 Chienkuo Mi & Man To Tang,“The Problem of Forgetting”,forthcoming。在推理叙述的过程中,(3)所代表的观点,指的是一般传统看法对于“记忆”与“忘记”的日常观点。(4)则是当代认知科学、心理学、知识论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对于“忘记”的积极正面的主张与看法。
首先,在针对内在论的讨论脉络中,“忘记”如何能在主体形成真信念时,提供一个证成的基础?让我们用“密码”②这个“密码”的例子,是笔者与索萨在一次私下的讨论中共同提出来的想法,特别是针对内在论的一个挑战。这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尔尼已经是一位八十岁的长者。他在金融机构设置了一个综合账户,并把所有的积蓄、不动产与退休金都放置在这个账户中。为了安全起见,银行给了他一个长达12位数字的账号密码(其中含了一些数字、字母与特殊符号)。由于这个密码对于尔尼十分重要,他也知道自己并没有办法把它记在脑子里,所以他就把这组密码记在一个金属片上,每当需要用到这组密码时,尔尼就会拿出这个金属片,提供正确的密码。在这个例子中,尔尼知道凭他的记忆能力已经无法记下这组重要的密码,这个情形下最好的做法就是“把它忘了” (“forget it”)。只有把它(这组密码)忘了,并把它放置于某个容易被取得的地方,每当要“呼唤”这组密码时,“真信念” (这组密码的正确号码)才能及时出现。在这个例子中,尔尼每次要形成这组密码的真信念时,都是属于一个能被证成的真信念,其证成的基础就在于忘记这组密码(加上把它记在金属片上),而不再记忆这组密码。当尔尼每次形成这组密码的信念时,我们也可以确认他其实是知道这组密码的。
其次,在针对外在论的讨论脉络中,“忘记”如何在主体形成真信念时,提供一个可靠的认知过程?在这里让我们使用博内克自己的例子,也就是“数座位”③Sven Bernecker & Thomas Grundmann,“Knowledge from Forgetting”,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98,No.3,2017,pp.525—540.的例子来说明问题。仕问正在影院中等待播放电影。因为等待很无聊,他决定算算看到底这个影院拥有可以容纳多少人的座位。他先数了最前排的横排座位数目,然后再数直排共有多少排。然而由于影院内光线较为昏暗,仕问不大能确定他数的数目是否完全准确。然后他把横排的数目乘以直排的数目,最后得出660个位置,而且事实上,这个数目是准确的。几个星期之后,仕问已经忘记准确的数目,但仍然记得影院有超过500个以上的座位。在这个记忆的基础之上,仕问相信该影院有多于500以上的座位。
在“数座位”这个例子当中,仕问虽然忘记了影院内准确的座位数目,但是这个忘记并不影响他记得影院中有超过500个以上的位置。这里的忘记是一个省略或忽视细节的过程(levelling or omitting),也正因为这个省略的忘记,才可以使仕问得以可靠地记忆了“该戏院有多于500以上的座位”的真信念,也因此我们可以说仕问知道“该影院有多于500以上的座位”。
最后,在针对德性知识论的讨论脉络中,“忘记”如何可以在主体形成真信念时,也表现为一种德性或智德呢?米克艾力安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与实验,试图论证一个正常的认知机制的运作,既不能有过多的记忆,也不能有过多的忘记,记忆与忘记必须获得一种恰当的互补与合作,才能达到一个健康正常的认知与心理状态。米克艾力安也进一步指出,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这包括人的记忆的空间、学习的速度与认知的能力,在一个有限认知容量与能量的范围之内,如何有效地运用“忘记”的功能或能力,也会是一种重要的智德。①Kourken Michaelian,“The Epistemology of Forgetting”,Erkenntnis,Vol.74,No.3,2011,pp.399—424.上述心理学的实际案例“完美的记忆者”中吉尔正是因为无法有效地运用“忘记”的功能,才导致她在认知上与心理上都蒙受了巨大的障碍与阴影,这正好说明忘记作为一种智德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庄子也曾在他的《养生主》中提及:“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忘”如何能作为一种智德,但是以庄子对于坐忘的重视与态度,不难联想到对于一个人的有限生命来说,特别在面对知之无涯”时,“坐忘”应该是展现一种智德的最好作法与修养。当代心理学的研究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智慧,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帮助我们掌握与理解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忘”如何能成就一种智德。
以上我们通过“忘记的难题”,同时针对内在论、外在论与德性知识论提出了困难与挑战,特别是在推理过程中的第(4)个步骤,我们分别举出了“密码”“数座位”与“完美记忆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与支持。如果这些论证都可以被接受,当代知识论学者(甚至哲学家)应该如何面对与解决这个难题呢?
三、问题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由“忘记难题”为(记忆)知识论所带来的困难,而且是全面地为内在论、外在论,甚至德性知识论所带来的挑战,我们首先必须对“记忆”这个原本所谓的智德、可靠的认知机制与能力或对为我们提供追求知识过程中的证成条件(或形成信念的证据)进行深入的探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在科学的领域中(包括心理学、认知科学与大脑神经科学)人们已经有很好的理解与进展,并进行了许多科学的实验与实例的探索。哲学家(或知识论学者)应该要好好重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结果,重新思索与反省传统哲学对于“记忆”议题的纯粹思辨性讨论,特别是从洛克、休谟、托玛斯·里德,一直到罗素这个经验主义的传统中,对于记忆哲学(特别是记忆的形而上学议题)的一些主流观点的讨论。这个主流观点,主要是针对“记忆”进行形而上学的概念分析,试图从“记忆”的对象,定义记忆的本质内涵,解释“记忆” (或“回忆过去”)如何可能。这个主流的争议,主要是由洛克、 休谟与罗素(第一阶段的理论)所主张的表征理论(或间接实在论),对抗由里德与罗素(第二阶段理论)所主张的直接实在论。表征理论认为记忆的对象是通过我们的某种心灵表征(表征过去的经验),用来回忆过去所发生或学习的一切事件或经验,但是直接实在论则认为,我们回忆的对象是(内在地)直接面对过去的事件与经验,而不需通过心灵表征的媒介来进行。这个由形而上学的概念分析所形成的哲学上之争议,连带产生出其他的一些相关争议,这些争议包括:记忆的因果关系理论、链接主义(connectionism)、保留主义(preservationism)与生成理论(generativism)之间的论辩。对这些不同理论的内涵与争辩的重点,都需要重新进行仔细的整理与探究之工作,处理这些理论与问题的发展,是日后进一步研究“记忆”与“忘记”的哲学议题(特别是知识论方面的议题)之基础所在。
其次,“忘记”这个概念,当然也是个核心关键所在,毕竟上述提到记忆知识论所面临的难题,主要就是源自“忘记”所带来的挑战。西方目前的科学研究与理论,大都聚焦于“记忆”这个认知机制,并探索这个机制在健康医学、生理、心理和大脑神经所具备的积极功能,但是科学家对于“忘记”这个现象与征状,大都从一个比较消极与负面的态度来面对。相对来说,哲学家在“忘记”这个议题上,反而有比较开放与多元的想法。虽然西方哲学家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这方面的议题,但是中国哲学的文献中反而有许多丰富的素材与元素,可以提供给我们对于“忘”这个概念的一个比较正面与积极的看法。但是,相反地,中国哲学似乎对于“记忆”这个概念并不是十分重视,以孔子的《论语》为例,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关“记”或“忆”的文字。与记忆最相关的文字,大概只有“识” (出现了八次)与“念” (出现了两次),而“识”这个概念在《论语》中是次要的,是“知之次也”,“念”则通常和“忘”有密切的关联(“不念旧恶”)。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记忆”与“忘记”并列,仔细研究两者之间的紧密与互补的关联,对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对记忆哲学(或“忘”的哲学)的发展,都可以有比较实质性的帮助。
最后,我们可以继续从一个知识论的视野来探索“记忆”与“忘记”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特别是从一个德性知识论的观点来看。简单来说,“忘记”为德性知识论所带来的挑战在于,如果“记忆”是一种“智德” (intellectual virtue),那么忘记” (依据传统上对于记忆与忘记之间的对立关系来看)就会成为一种“智恶”intellectual vice)。但是,“忘记”有时候可以具有一些心理学上的疗效,有时候也可以具有伦理学上的善意,有时候甚至可以具有成为知识论上证成条件的可能,而在中国哲学的理论当中,“忘”甚至是一种重要的修养工夫与实践智慧。在这些情境之中,“忘记”都不算是一种“恶”,反而是某种“德”。德性知识论(甚至德性伦理学)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个难题与挑战呢?
德性知识论在当代所谓“德性的转向” (the virtue turn)这个趋势之下生发出两个不同的主要派别或分支①有关德性知识论在这个德性的转向中的发展与内涵,请参见米建国于《华语哲学百科》 (2019)中撰写的词条“德性知识论”。:一个是以索萨为首的“建立在卓越能力基础上之德性知识论” (competence-based epistemology),另一个则是以札格泽博斯基Linda Zagzebski)为首的“建立在人格特性基础上之德性知识论” (character-based epistemology)。前者有时也可被称为“德性可靠论”,是一个强调以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为发展基调的知识论;后者则亦可被称为“德性责任论”,是一种着重以智性伦理学(intellectual ethics)为讨论焦点的知识论。
索萨的德性知识论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后盖蒂尔的知识论传统中所发展出来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出发点还是要对“知识”这个概念进行分析,并强调解决知识本质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利用知态的规范性解决盖蒂尔难题的同时,索萨的“适切性信念” (apt belief)也同时解决了知识的价值难题。索萨解决知识的本质问题与价值问题的方式,主要在于避开了以“真信念”作为我们追求知识的唯一基本目标,而强调适切信念才是我们追求知识的主要目标,在追求适切信念的这个目标之下,我们不仅追求真信念(精准性的要求),我们还要求具有知态的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s)来形成我们的真信念(熟练性的要求),最后更要求我们所获得的真信念是因为借由我们的智德所获致的结果(适切性的要求)。为了能够适切地获得真信念,索萨认为我们必须具备相当可靠的信念形成的认知机制,也就是要有相当熟练与相当卓越能力的智能德性,这些德性包括第一序的智德(例如,我们的五官、记忆、推理能力、证词、直觉等)与第二序的省思机制(例如,我们的反省能力与风险评估能力)。不论第一序还是第二序的认知机制与智德,都是为了要能够可靠地协助我们获取真信念,进而达成适切的信念这个最终的目标。所以,索萨的德性知识论也被称为“德性可靠论”,因为“知识” (对索萨而言也就是“适切信念”)的获得,才是索萨最主要的关怀所 在。
札格泽博斯基虽然也重视真信念的基本知态要求,同时也重视获得知识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最终着眼点并不在“知识”本身(虽然他也同意我们可以为了追求知识而追求知识),而在于如何获得一个“美好的人生”。如果我们真的在乎并关怀过一种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必须更重视一种“良知的信念”,这种信念(的形成)是以追求真信念(甚至知识)为依归,而其目的是为了要确保我们能够获得我们真正关怀在乎的事物,确保我们(作为一个认知主体或行动的主体)在与世界接触的过程之中,不至于产生错误的联结(由于错误的信念)或失去联结(由于不相信)。所以知识的价值(而不是知识的本质)是札格泽博斯基的关怀重点,因为在追求美好人生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可以获得我们所关怀的对象与目标,才是我们寻求知识、形成信念的依归所在。不同于索萨宣称我们第一序与第二序的认知机制是可靠的,札格泽博斯基认为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认知官能(不论第一序还是第二序)是可靠的,札格泽博斯基所要宣称的是,为了生活在一个正常一般的生活世界之中,也为了要实现一个我们所关心的美好生活,我们必须具备知态的自我信赖(epistemic self-trust),不仅信赖我们的感官知觉与认知官能,也必须信赖我们(作为一个认知主体和行动主体)和这个世界(被认知的对象与行动的对象)互相联结的其他机制(包括情绪、选择、与行动),也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得信赖其他人(包括他们的认知官能、情绪与选择)。但是自我信赖与信赖他人并不是一种盲目的举动,一个具有良知的认知者与行动者都会有一些内在的证据证明自己曾经犯过错误,所以如何从这些错误的经验中,一方面学习如何规范自己,一方面又要信赖自己,使自己在信念形成的过程之中,避免不可靠的情形发生,这就需要积极养成(或培养)许多知态上所需具备的智德,用以避免自己过度信赖自己不当的认知行为,同时又能强化自己信赖自己可靠的认知机制。对札格泽博斯基来说,这些智能德性包括我们是否能适度地关注、智性上的付出关怀、思虑缜密全面、勇敢追求真理、坚持、稳固、谦卑、慷慨与开放心灵。(很明显的是,札格泽博斯基心目中理想的智德,几乎和索萨所列出的智德完全不同。)具有以上这些知态上智德特征的人,就是一个能够具有良知地自我信赖的人,而在以获得真理与知识为依归的认知过程中,拥有这种知态良知(并自我信赖)的人,才是一个知态上负责的人,也是一个能为自己关怀的对象与追求自己想过的美好人生真正负责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札格泽博斯基的德性知识论会被称为“德性责任论”的主要原因,也可以看出在追求一种实践智慧与美好人生中,认知者(生活在一个智性的伦理学环境之中)在形成信念与完成关怀的行动时所需担负的知态责任。
从以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知识论来看,“记忆”可以算是第一种德性知识主张中的智德,但是相对来说,“忘记”却会成为一种智恶。而第二种德性知识论中,记忆”并不能算是一种智德,相较之下,“忘记”并不会立即成为一种智恶,但是在札格泽博斯基的理论当中,我们也看不到“忘记”如何成为一种智德的可能性,甚至也不清楚如何成为伦理学上一种美德的可能。我们该如何在这两种德性知识论之上,同时认可“记忆”与“忘记”都可以成为智德的可能,或者最少可以成为某种意义下的美德?我初步的想法是:在一种两层的德性知识论(Bi-level Virtue Epistemology)中,运用第二层次的省思机制与注意力,我们也许可以同时调节平衡“记忆”与“忘记”作为第一序或第一层次认知机制)的功能,使两者得以并存互补,进而同时能享有较高、较好的知态地位。这里所谓“两层”的德性知识论指的是:人的认知机制与功能其实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类似于认知科学与心理学中常见的两层(认知或心理)过程的理论(dual-process theory),也就是区分认知或心理过程中的系统一与系统二(system 1 and system 2)的不同表现。在索萨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德性知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也就是“动物之知”与“省思之知”的区别。这个区别基本上是建立在由第一序认知机制所形成的信念与由第二序(引导第一序)的认知机制所形成之信念间的差别。而所谓的第一序认知机制包含了感官知觉、直觉、推理、内观、证词与记忆(和忘记),第二序的认知机制则可以涵盖省思、注意力、理解与意识能力。我们先从记忆与忘记作为一种第一序的认知机制或能力来看。一般心理学会将记忆视为一个历程(而不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个历程可以完整地包含由输入为起点,历经储存的过程(这个储存的时间可长可短),到最后这个记忆的拥有者提取这段记忆为止(记忆的主体当然可以在提取这段记忆之后继续再储存该片段之记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这段记忆的历程称为“输入—储存—提取”的历程(the process of imprinting-storing-retriving);不同的记忆理论也会把这个历程称为“编码—储存—译码”的历程(the process of encoding-storing-decoding)。而心理学家也更进一步利用这个记忆的历程模型,加以说明忘记是如何产生的。有些心理学家指出:蕴含着“忘记”的事件可以在这个实际记忆历程之前或之后发生。也就是忘记可以代表一种“不能编码” (或输入)、“无法储存”或者是“不能译码” (或提取)的表现。这里对于“忘记”的解读如果还是把它看作是记忆功能的丧失或退化,或者是不具备应有的正常记忆功能或能力,那么“忘记”基本上还是只具有消极负面的功能(它是“记忆”这个积极正面功能的反面或丧失),如此一来,我们还是无法解决“忘记的难题”:忘记可以是一种智德,因而是德性知识论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个一般的刻板印象,并且能够扭转“忘记”在记忆历程中的负面角色,进而凸显它在人类认知与心理过程中的正面功能,而且也能展现它所具备的智德(甚至道德)的角色呢?这里我们除了运用所谓的记忆与忘记作为一种第一序的认知机制或能力之外,还要同时加上并运用第二序的省思与注意力的认知机制。记忆历程作为第一序的认知过程,我们似乎只聚焦于记忆与忘记两者之间在这个历程中所具有的正面或负面的功能(正常运作或功能与能力丧失或退化)。我们除了应该要注意到“忘记”可以表现为一种“永久丧失记忆的忘记”之外,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暂时抛诸脑后的遗忘” (如柏拉图区分“忘记”与“遗忘”一般)。更重要的是,在记忆的历程之中,不论记忆或忘记都有可能以一种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被动地(或无意识地)进行记忆的认知活动,也可以主动地(或有意识地、特别加以专注地)进行记忆活动。这个被动与主动的区分,同样也可以应用在记忆历程中“忘记” (或遗忘)的活动或表现。我们通常在第一序无意识地进行记忆活动,和我们有意识地、同时特别专注或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记忆活动,这两个层次的记忆表现是在认知上不同的认知过程,前者大部分表现为一种被动式的(第一序)记忆,而后者则经常表现出认知者主动的(第二序)记忆。也因此,我们可以只是在第一序无意识地与被动地忘记某些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积极主动地忘记或遗忘某些事情。当我们被动地忘记一些事,也是因为记忆功能或能力的丧失或退化,使我们因此产生忘记或健忘的现象,这是一般把“忘记”视为负面的认知或心理功能缺失的基础所在。但是,如果一个认知者或行动者主动积极地想要遗忘或抛开一些不愉快的往事,或者排除一些琐碎无用的信息,这时候“(主动的)忘记”似乎有了正面积极的功能与角色,也因此“忘记”成为一种实践智慧,或具有了实现一种“智德”的可能性,似乎有了很好的支撑力与正当性。
当我们把记忆历程视为“编码(输入)—储存—译码(提取)”的历程时,忘记在第一序的认知表现通常只被视为一种“不能编码” (或输入)、“无法储存”或者是“不能译码” (或提取)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加入了第二序的认知机制用来引导第一序的认知机制时,就多了一个认知主体之“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区分。建立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之上,对于记忆历程就会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解方式,因为不论这个历程中的“记忆”或“忘记”的表现,都可以同时具有主动性或被动性,也因此可以有以下各种不同的面貌:被动记忆的历程(输入—储存—提取)、主动记忆的历程(编码—储存—译码)、被动的忘记历程(无意识地没注意到—永久的丧失—提取能力丧失或退化)与主动的忘记历程(有意地忽略—有系统性地重组回收或暂时地沉淀—善于抽象或简化)。
四、结 论
本文通过“记忆”与“忘记”之间的有趣对比,结合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哲学的传统理论观点,同时运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中的相关理论元素与哲学概念,从一个知识论(特别是德性知识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进行对于“记忆”哲学与“忘”之哲学的探究与讨论。西方整体的“记忆”哲学发展,过度忽略“忘记”这个概念的重要哲学意涵,以至于无法通过“记忆”与“忘记”之间的复杂关联与有效对比,提供记忆哲学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与真实面貌。东方哲学对于“记忆”的哲学研究,则显得十分贫乏。中国哲学的研究学者,特别是对庄子哲学的研究学者来说,虽然对于“忘”这个概念十分重视,但却几乎完全忽略对记忆”这个概念的研究,甚至对知识论的研究丝毫不感兴趣。本文利用“忘记的难题”,试图对当代知识论发展中的内在论、外在论与德性知识论提出问题与挑战,最后尝试论证德性知识论如何可以同时认可“记忆”与“忘记”成为智德的可能,甚至最少可以成为某种意义下的美德。初步建议的做法是,利用“两层认知机制”中的第二序省思与注意力机制,作为同时调解平衡“记忆”与“忘记”两者之间的功能,强调记忆历程中的“记忆”与“忘记”的主动性面向与被动性面貌,使两者可以在人类的认知与心理的过程中得以并存互补,进而享有较高与较好的实践价值与知态地位。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