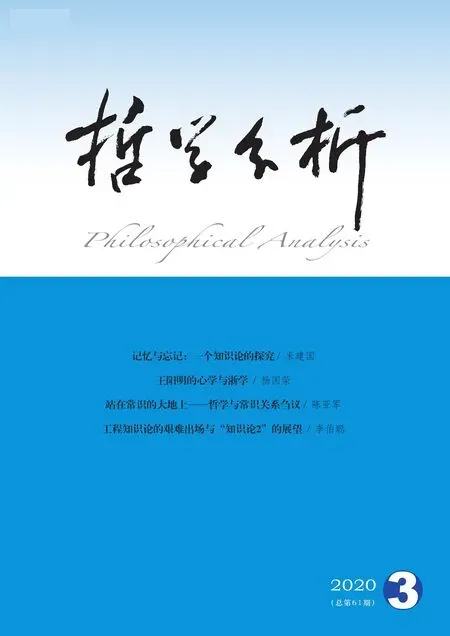工程知识论的艰难出场与“知识论2”的展望
李伯聪
本文将简要讨论三个基本观点:人类的知识包括不同的类型,而工程知识正是其最重要的知识类型之一;知识论包括不同的分支,而工程知识论正是其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由于多种原因,古代知识论乃至近现代的知识论成为了“只研究科学知识而排斥工程知识的知识论” (可谓之“知识论1”),今后,应该在“综合工程知识论、科学知识论、伦理知识论等知识论分支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研究所有知识类型的知识论”,可称之为“知识论2”。这三个观点牵涉的问题很多,本文只能对与其有关的部分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概略的分析和讨论。
一、从知识分类和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谈起
(一)“知识类型”:研究知识问题时必然出现的重要问题
一般地说,哲学家都高度重视人的认知能力并从哲学角度研究知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所有人在本性上都愿求知。”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李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荀子在《解蔽》中也说:“凡可知②原作“凡以知”,据《荀子绎评》 (邓汉卿著,长沙:岳麓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页)、《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 (董治安等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0页)改为“凡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在哲学家普遍高度重视知识的语境中,我们可以说甚至那些知识的怀疑论者也从“反面”凸显了知识的重要性。
知识论(或曰认识论)③对“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关系,我国哲学界的认识不完全一致。本文中对于二者的含义采取不加区分的态度。以知识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知识又包括了形形色色、多种类型的知识。无论从学理方面看,还是从作为知识论研究对象的“知识现象本身的状况”方面看,“知识分类”问题都顺理成章且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知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之 一。
虽然对于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来说,往往主要关注特定类型的知识(例如工匠主要关注“工程知识”),而不关注“知识的整体”;但是,对于古代哲学家来说,由于多种原因,他们大多着重从“整体”上研究知识问题,也就是把知识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于是,哲学领域中的“知识论”主要也就成为了以“知识整体”为研究对象的领域。可是,这里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需要辩证对待的方法论问题,即“整体”和“分类”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进行分类,“整体”就可能成为一个“带有混沌性”的整体,为了走出“混沌”就必须进行分类。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古代哲学家往往都更加关注知识整体性问题,而较少有人明确地意识到“知识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知识论中的重要问题”,知识论领域也很少出现“关于知识分类问题的哲学研究成果”。
当然,“很少”不意味着“没有”。例如,在这方面,欧洲的某些哲学家以及我国北宋的张载都是值得注意的人物。
张载首先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知之分类”问题。他认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是两类不同的知识:“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④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页。程颐也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①转引自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6页。张岱年认为:“德性所知,不是康德所讲的纯粹理性却较接近于康德所讲的实践理性。”②同上,第505页。张岱年原注:“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决非一事。”
在比较中国哲学传统和欧洲哲学传统时,许多现代哲学家都认为中国哲学传统更重视伦理问题而知识论研究较弱。陈嘉明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识论的地位乃是边缘性的。”他又说:“就西方哲学而言,求‘真’的知识论构成了它的主流。其主要哲学家,从柏拉图、康德到胡塞尔等,几乎首先都是知识论的宗师。”③陈嘉明:《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主编的话”第1页。
如果说,古代欧洲哲学家已经高度重视研究知识论问题,那么,近代欧洲哲学史上出现了所谓认识论转向,知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就更加琳琅满目、百花齐放。可是,在琳琅满目、百花齐放的“知识论成果”中,却较少有哲学家“直接指名道姓”地研究“知识分类”问题。
当然,如果不拘泥于“自报家门”,而是就“某个方面的内容属性”来看,我们也可以承认哲学家关于“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的研究——如果从某个侧面看——也是关于“两种知识类型”的研究。可是,就哲学家在研究“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时的“自觉认识”而言,他们很少有人“承认”这是“关于知识分类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就争论焦点而言,我们更难以断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派的论战是有关“知识分类”问题的论战。总而言之,在知识论领域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知识分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没有在“这个方向”进行专题和深入的哲学探索和开拓。
在近现代哲学家中只有少数人“明确地”涉及和关注了知识分类问题。例如,C. L.刘易斯在《对知识和评价的分析》中就明确谈到了“知识的两种类型”:经验知识和分析性知识。④C. L.刘易斯:《对知识和评价的分析》,江传月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虽然在哲学领域中对经验知识和分析性知识的“二分”研究已经很多,因而这种二分式“划分”也不是刘易斯的创见。可是,由于很少有人明确指出“这是知识分类问题”,我们认为,刘易斯能够明确地将其“认定”为知识的两种类型”并且从“知识类型划分”角度对其进行讨论,也可谓是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
如果说,刘易斯只是对“知识类型(分类)”这个“主题”作出了“点题”性的贡献,那么,科林斯就对知识分类问题作出了更具体的分析和更值得称道的贡献。科林斯把知识划分为五种类型:观念型知识、体知型知识、文化型知识、嵌入型知识、符号性知识①成素梅:《技能型知识与体知合一的认识论》,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4页。又,张帆在《科学、知识与行动:科林斯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01页)一书中也介绍了科林斯关于知识分类的思想。,这就使对知识分类问题的认识更加具体化和深化了。
虽然明确关注知识分类问题的现代哲学家并非只有上述二人,但应该承认明确关注知识分类问题的哲学家不多。
(二) 科学知识、工程知识、伦理知识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分类”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方法和主题。如果没有器物分类、行业分类、物种分类、学科分类、图书分类等领域的“类型划分”,人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浓雾弥天的“混沌世界”中。在知识论领域,知识分类问题也是一个不能回避和不能忽视的问题。
“知识分类”是意义复杂、功能多样的问题。为了不同的目的和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会划分出不同的知识类型。例如,可以为了某个“实用性目的”而进行知识分类,也可以“从哲学角度”进行知识分类研究。
在知识论领域,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哲学性”的知识分类?可以具体划分出哪些知识类型?这些都是应该深入研讨而迄今很少深入研讨的问题。但本文无意具体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本文来说,笔者只想简单指出:以承认知识“可以分类”和“应该分类”为理论前提和背景,我们就可以承认工程知识、伦理知识和科学知识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②这个论断只肯定了“这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而没有涉及“知识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标准分类”和“究竟应该具体划分为多少类型”等问题。
在人类知识的发展史上,工程知识的起源最早(自人类起源就有了原始的工程知识③A. A. Harms,et al.,Engineering in Time,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04.),而伦理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形成就要晚很多。
应该怎样认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的相互关系呢?
一方面,不同类型的知识必然有不同的本性(本质)和不同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的本性和特征“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知识,使它们成为了不可混淆的不同类型。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存在的“类型区别”是“界限绝对分明的绝对区别”,相反,应该承认不同类型的知识就“多方面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而言往往出现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嵌套、相互转化的关 系。
在认识“分类问题”时,原先有许多人都重视和强调以上所说的第一个方面,也就是立足于“本质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分类问题。可是,在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的观点和方法以及“反本质主义”观念流行之后,一些人又否认“本质”的“存在”,而只承认“无‘共同本性’的家族相似性”。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和方法呢?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和方法意味着“绝对否认存在‘家族本性’”吗?我们认为,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中,不但蕴含了“家族”和“家族成员”这两个概念,而且蕴含着“不同家族”这个概念。就“家族相似”这个概念和方法而言,它并没有认为“任意的和随机的两个不同事物”都是相似的,而只承认“(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存在相似性。就此而言,可以认为“家族相似”概念和方法并没有否认在“家族成员相似性”的深层”,同时也存在着“家族共性(家族本性)”。
总而言之,在认识“类型划分”和“不同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时(本文关心的是“知识的类型划分”和科学知识、工程知识、伦理知识的相互关系),我们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承认不同类型的知识就其“本性”或“核心特征”而言必定有“明确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知识在“边缘区”往往是模糊的,常常出现交叉、渗透,乃至相互嵌套、相互转化关系。人们不能因为前一个方面否定后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后一方面否认前一方面。例如,从本性上看,工程知识属于“见闻之知”而伦理知识属于“德性之知”;工程知识是关于人工物的创造和使用的知识,也是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知识,而伦理知识是与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的知识,这就使工程知识与伦理知识在本性上有了不可混淆的区别。另一方面,由于工程知识是创造使用价值和为人类谋求福祉的知识,这又使工程知识必然与伦理知识有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的部分和成分,但这个“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关系”并不能成为否认工程知识和伦理知识是“两类知识”的理由,不能因此而把工程知识和伦理知识混为一谈。
这就是说,一方面,承认工程知识和伦理知识是两类本性上有不同的知识不意味着不能承认二者也有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部分或成分。另一方面,承认二者有相互渗透的关系也不意味着可以否认二者在类型划分上有确定性的区别,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除了相互渗透关系,工程知识和伦理知识还存在着可能“相互嵌套”和“相互转化”的关系。
工程知识和科学知识——作为两类不同的知识——的关系,也是“在本性上有明确区别”“在边缘部分往往模糊渗透交叉”“往往多重嵌套”“可能相互转化”的关系。可是,在认识工程知识与伦理知识的相互关系时,人们往往更多地犯“否认二者相互渗透”的错误;在认识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相互关系时,人们往往更多犯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错误。
限于篇幅,本文以下的分析中将更多涉及工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类型区分和相互关系问题。
二、古代知识论的吊诡现象:重视知识但又排斥工程知识
回顾知识论的状况和发展史,人们会看到一个显得吊诡的现象:虽然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已经营造出了一个“(普遍)重视知识”的大环境,在哲学形成后,古代的绝大多数哲学家都“高度重视知识”并且承认工程知识是一个“独立类型”的知识;可是,哲学家并没有采取“同样重视”“所有类型知识”的态度,而采取了只高度重视科学知识和伦理知识而贬低甚至排斥工程知识的态度。更具体地说,工程知识不但没有能够“搭上‘重视知识’的顺风车”而受到重视,反而在“重视知识这个‘大前提’和‘大环境’中”被严重贬低甚至被排斥在“应该重视的知识这个‘思想和口号’”之外,成为了“属于知识但又被严重贬低甚至被排斥的知识类型”,对于这种状况和现象确实需要用“吊诡”来形容了。
由于篇幅有限和为论述简便,以下只讲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两个事例,而不再论及欧洲哲学史的类似情况。
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孔子是一个影响最大的人物。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是他那个时代知识最丰富的人。他不但掌握了丰富的政治、礼教、礼仪、历史、伦理、制度、语言、音乐、射御、书数、草木鸟兽之名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且掌握了颇为丰富的“体力劳动”知 识。
孔子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社会地位没落的家庭,这使得他不得不掌握一定的体力劳动知识;另一方面,他努力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礼乐仁义知识,这就使他因为有丰富的知识而逐渐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甚至成了传授知识的“万世师表”。可以说,孔子就是一个在重视知识的社会环境中因为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而改变命运的典 型。
在孔子同时代的“知识丰富”的人中,许多人只有丰富的关于礼、乐、历史、战争、祭祀等的知识,而在“体力劳动知识”方面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可是,孔子却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那么,孔子是如何看待这种“比较全面地掌握不同类型知识”的状况呢?是否应该“同样和同等”地重视工程知识呢?
根据《论语·子罕》的记载,达巷党人称赞孔子“博学”,并且首先就情不自禁地赞曰“大哉孔子”。太宰也情不自禁地评论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在这段记载中,孔子特别强调了他之所以“多能鄙事”,其原因是“少也贱” (社会地位卑贱)。对于孔子最后两句话的含义,《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君子固不当多能也。”这就又表明孔子本人和历代儒家一致认为“君子”不需要和不应当学习和掌握作为“多能”的“鄙事(之知)”。
什么是“鄙事(之知)”呢?《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这就使一心学习“农业知识”的樊迟碰了一鼻子灰。而更“要害”之点是孔子接下来的一段评论:“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就是说,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不但明确而坚决地在理论上否定了耕稼等工程知识①广义的工程知识包括农业知识在内。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且明确而坚决地在教育实践中排除了工程知识在儒家教育体系中的位置。
到了战国时期,大儒孟子又与治“神农之学”的徐行发生了一场涉及如何认识农业和纺织劳动知识的争论。孟子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现代学者多从劳动分工的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和评论这场争论,也有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这场争论,但从知识论角度看,这场争论也是有关应该如何认识“不同类型的知识”的性质、特征、意义和功能的争论。
工程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工程活动又以工程知识为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②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伴随的关系,没有人能够否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工程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知识类型”。
那么,谁掌握着工程知识呢?《宋书·沈庆之传》云:“治国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于是,在很长时期中,与劳动分工和职业划分相呼应、互为表里,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知识掌握在不同职业的人手中”的状况。
许多现代学者都指出了古代中国哲学传统和古代欧洲哲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可是,二者在贬低工程知识甚至排斥工程知识方面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共同之处。
三、20世纪知识论研究中的三个新认识和新观点
应该特别注意和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上述“吊诡状态”在理论上和哲学史上都产生了严重后果和严重影响。从理论方面看,理论领域中本来应该“以全部知识类型为研究对象的知识论” (可谓之“知识论0”)变成了“‘唯一地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和‘不承认工程知识也是知识论研究对象’的知识论” (可谓之“知识论1”)。从知识论发展史方面看,由于欧洲哲学史上的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忽视了“知识论0”而只承认“知识论1”,这就使得欧洲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的“知识论发展史”主要成为了“知识论1的发展史”①本文不涉及“知识论0”在历史上的萌芽、微弱存在和断续发展问题。。
在这种“限定于以科学知识为全部知识”的知识论——即“知识论1”——发展史上,柏拉图是影响最大的人物。柏拉图提出的关于“知识是经过证实(有人译为确证)的真信念”的思想成为了这种进路的知识论的核心观念,他的这种观点成了在欧洲知识论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②胡军:《知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6页。
对于欧洲哲学史的发展,曾经有人提出近代欧洲哲学史出现了“认识论转向”之说。应该注意,这个观点只是说欧洲哲学史上就“哲学体系”而言发生了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向”,而没有说在“知识论领域”发生了“转向”。相反地,可以说,在知识论领域和知识论的发展方向上,近代以来,从17世纪的笛卡尔和洛克到18世纪的康德,在知识论领域都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认识,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可是,这些知识论研究都是沿着古希腊开创的知识论传统和方向的继续发展,而没有发生什么“知识论领域的转向”。更具体地说,这些都是“知识论1方向”的延续和发展。
这种“以科学知识为知识的唯一类型和忽视工程知识”的“知识论1”在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中达到了一个新高峰,或者说有了极端表现。这个学派不但未能发觉和反思以往知识论传统中“只承认科学知识是知识而排斥工程知识”的缺陷和错误,反而把传统的缺陷和错误更加明确化和极端化了。《新编西方现代哲学》中说,这个学派“强调以科学为模式、以逻辑为手段、以物理学为统一语言,彻底改造哲学,使哲学完全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①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成素梅也说:“语言哲学家艾耶尔在1936年出版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中提出的‘证实原则’认为,‘没有一个经验领域原则上不可能归于某种形式的科学规律之下,也没有一个关于世界的思辨知识的类型原则上超出科学所能给予的力量的范围’。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只能是科学知识。”②成素梅:《“知识就是力量”的跨学科反思》,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
如果说,从古希腊到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学者在研究知识论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自我约束在科学知识领域”而“对工程知识视而不见”,也就是在“知识论1方向上”“不思转向”;那么,在20世纪中期以后,就有一些学者在研究知识论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注意到“整个知识领域”中除科学知识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知识。由于他们“不再局限于科学知识”而“放眼关注其他类型的知识”,这就使他们通过对“其他类型的知识”的研究而提出了一些具有“修正知识论1”特征的新认识和新观点。对于这些新认识和新观点,我们有理由将其称为欧洲知识论发展史上对知识论1”的“转向尝试”。
在这些具有“知识论转向色彩”的新认识和新观点中,20世纪中叶之后提出的以下三个新认识和新观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1)吉尔伯特·赖尔在1946年的论文和1949年出版的著作《心的概念》中,明确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命题性知识(knowing that)和操作性知识(knowing how)。③《心的概念》的中译者徐大建把knowing how 翻译为“知道怎样做” (参见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页),郁振华主张将其译为“能力之知” (参见郁振华的《论能力之知:为赖尔一辩》,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笔者认为译为“操作之知”或“操作性知识”更好一些。(2)迈克尔·波兰尼在1958年出版的《个人知识》一书中提出,除可以言传的“明述知识”外还有“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④参见波兰尼:《个人知识》,徐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离身认知”的基础上,“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范式兴起。叶浩生说:“具身认知目前已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学术思潮,对西方传统认识论和认知科学造成巨大冲击。”⑤叶浩生主编:《具身认知的原理与应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但反映以上三个方面进展的一些重要外文论著陆续被译为中文,而且出版了我国学者研究这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些论著,例如《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⑥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具身认知的原理与应用》⑦叶浩生主编:《具身认知的原理与应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等。
STEP指令直接连接在左侧母线上。STEP在SNXT指令之后,各工序之前配置,表示该工序开始(指定工序编号);在步梯形区域整体的最后配置,表示步梯形区域整体的结束(无工序编号)。
饶有趣味和发人深省的是,以上三种观点都是针对“知识论1中的一个传统概念”而提出了“另外一个关于知识的新概念”,从而形成了“三组”“对待性的知识概念”,分别用于指称“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赖尔针对“命题性知识”而提出了“操作性知识”;波兰尼针对“明述知识”而提出了“默会知识”①国内学者对tacit knowledge的译法有“默会知识”“意会知识”“隐性知识”“隐含经验类知识”等,本文采用“默会知识”。;具身认知范式倡导者针对“离身认知” (disembodied cognition)而提出了“具身认知”②国内学者对embodied cognition的译法有“具身认知”“寓身认知”“涉身认知”“体化认知”等,本文采用“具身认知”。。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认为这“三组观点”的“前支观点” (命题性知识、明述知识、离身认知)“等同于”科学知识,也不能简单化地认为这“三组观点”中的“后支观点” (操作性知识、默会知识、具身认知)“等同于”工程知识;但三个“前支观点”与科学知识有不解之缘而三个“后支观点”与工程知识有不解之缘乃是显而易见和不能否认的。实际上,有些学者在进一步解释和阐发操作性知识、默会知识、具身认知的内容和意义时,已经触及它们与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密切联系。
孔子早就强调“名正才能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逻辑实证主义更反复强调“澄清概念的重要性”。由于赖尔、波兰尼以及倡导具身认知的学者都没有明确提出“工程知识”这个概念,特别是由于我们不能认为“操作性知识”、默会知识、具身知识可以“等同于”工程知识,以及对于“操作性知识”、默会知识、具身认知和工程知识的复杂关系目前也还未能有具体深入的阐释,我们目前还只能说“操作性知识”、默会知识、具身认知的提出意味着工程知识在理论舞台上有了一个“戴了假面具”的“出场”,而不能认为它们是“工程知识”“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在理论舞台上的“正式出 场”。
四、“工程知识”作为哲学概念在工程史学科中的出场
上文谈到,在哲学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许多哲学家都轻视、贬低甚至排斥工程知识。在这种强大的思想传统的影响和压制下,“工程知识”一直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哲学概念”。甚至上文谈到的20世纪中期以来通过操作性知识、默会知识、具身认知等概念而尝试进行“知识论转向”的哲学家也未能明确提出需要把“工程知识”确定为一个哲学概念。
回顾“最近期的历史”,我们看到,首先完成把“工程知识”确立为一个哲学范畴的“理论任务”的是文森蒂——一位工程师兼工程史家。
文森蒂是一名工程师,“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曾任美国航空顾问委员会航空研究工程师和科学家,掌管过国家的超音速风洞实验,在航空与航天飞机的设计上取得过重大成就。60年代以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著有《物理空气动力学引论》,编有《应用力学》 《流体力学年度评论》,并对航空技术史有专门的研究”①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1990年,文森蒂出版了《工程师知道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知道的——航空历史的分析研究》一书。文森蒂在该书第一章第一段就感慨万千地说:“尽管工程研究人员付出巨大的努力与代价去获取工程知识,但是工程知识的研究很少得到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关注。在研究工程时,其他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应用科学。现代工程师们被认为是从科学家那里获得他们的知识,并通过某些偶尔引人注目的但往往智力上无趣乏味的过程,运用这些知识来制造具体物件。根据这一观点,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应当自动包含工程知识的内容。但工程师从自身经验认识到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近几十年来技术史学家们提出的叙述性与分析性的证据同样也支持这种看法。由于工程师并不倾向于内省反思,而哲学家和史学家(也有部分例外)的技术专长有限,因此作为认识论分支的工程知识的特征直到现在才开始得到详细地考察。”②沃尔特·G.文森蒂:《工程师知道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基于航空史的分析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在此书中,文森蒂具体深入地分析了5个工程设计知识的历史案例:戴维斯机翼与翼型设计问题(1908—1945)、美国飞机的飞行品质规范(1918—1943)、控制体积分析(1912—1953)、杜兰德与莱斯利的空气螺旋桨试验(1016—1926)、美国飞机的埋头铆接革新(1930—1950)。这5个案例分别涉及了5个与工程知识相关的理论问题:设计与知识的增长、设计要求的确定、设计的理论工具、设计数据、设计与生产。就整本书而言,文森蒂从多个方面具体而深入地阐释了工程知识——主要聚焦于工程设计知识——的基本特征,比较全面而深入地阐释了工程知识和科学知识是两类不同的知识,强调必须把“工程知识”看作一个独立的理论概念和哲学概念,而绝不能把工程知识看作科学知识的一个子集。该书于1997年荣获了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国际历史与传统中心的工程师历史学家奖。
由于该书在理论上首次明确地把“工程知识”确立为一个理论概念,这就意味着“工程知识”作为哲学概念首先在工程史领域“正式形成”和“正式出场”。工程知识的实际存在发展和工程知识的哲学研究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在古代,一方面,工程知识主要掌握在工匠手中,而古代的工匠又缺乏对自己掌握的工程知识进行理论深化和升华的能力,缺乏进行哲学思维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同时代的哲学家又普遍采取了贬低甚至排斥工程知识的态度,这就使古代乃至近代一直未能形成关于工程知识的比较明确、系统的哲学理论,尤其是未能把“工程知识”明确为一个哲学概念。
在近现代历史上,虽然工匠是直接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力阶层”,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工匠阶层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而“工程师阶层”乘势兴起。工程师阶层兴起后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及现代工程知识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①李伯聪:《工程人才观和工程教育观的前世今生——工程教育哲学笔记之四》,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
如果进行纵向比较,工程师阶层和工匠阶层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果进行横向比较,现代工程师阶层和科学家阶层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果说“近现代科学家阶层”在登上历史舞台后很快就“介入”了哲学发展进程,那么,工程师阶层在登上历史舞台后大多主要关注“工程知识自身”的发展,而很少“介入”哲学的发展进程。
工程师这种“很少介入哲学发展进程”的状况无论对于哲学还是对于工程师自身都没有好处,都是一个“遗憾”。这种状况自然不可能“无限期延续”。现在我们看到,在“首先”把工程知识确立为一个哲学概念这方面,工程师取得了一鸣惊人的成就。
虽然“具体的工程知识”是最早出现的知识,具有科学知识“不可同日而语”的极其久远的历史,但是,就理论概括和哲学升华而言,“科学知识”早就被确立为哲学概念,而“工程知识”不但未能被确立为哲学概念,而且有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习惯性地反对把工程知识确立为独立的哲学概念。由此可见,把“工程知识”确立为哲学概念遇到了非常特殊的境况,成了一个难上加难的任务。在完成这个难上加难任务的过程中,工程师和工程史家发挥了关键性的“临门一脚”的作用。
从工程师阶层和工程职业的发展进程看,工程师之所以能够完成上述难上加难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工程师具有与工匠、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不相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因为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集成性地具有工匠、科学家和哲学家②米切姆认为,工程师是“后现代世界中不被承认的哲学家” (米切姆:《工程与哲学——历史的、哲学的和批判的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三者的特点,这才使得工程师“有潜力”和“有能力”完成“终于使工程知识这个哲学概念正式出场”的任务。
五、工程知识的哲学研究与工程知识论的出场
拉卡托斯有一个模仿康德的著名论断:“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①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毫无疑问,拉卡托斯论断的精神对于工程史和工程哲学的关系也是适用的。
在“工程知识”这个概念在工程史领域明确提出后,虽然仍然有不少哲学专家对工程知识反应迟钝,继续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也有哲学家顺应新潮流,陆续开展了对“工程知识”的哲学研究。
首先是著名技术哲学家皮特于2001年在《技术》杂志上发表了《工程师知道什么》②皮特:《工程师知道什么》,载张华夏、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9页。一文,这篇文章可能是专论“工程知识”问题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如果说文森蒂主要是从工程史角度和历史案例分析方法阐述工程知识是一个特殊类型的知识,那么,皮特是着重从哲学研究和知识论角度论证这个观点。皮特明确指出:工程知识和科学知识是两个不同的知识类型和知识形式。科学知识有两个主要特征:科学知识是受理论制约的;科学知识是被发展来解释世界运转方式的。与科学知识相反,工程知识是任务定向的。皮特承认工程知识具有“食谱知识”的样式。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皮特来说,这不但没有成为贬低工程知识的理由,反而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任务定向的工程知识”需要针对“真实世界中的任务”可能遇到各种意外情况而获取成功,因而,“工程知识似乎更加可靠,更加可信。具有更强的活力。因而,工程师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知道如何去完成任务,首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③同上,第138页。
2005年,在第259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李伯聪也专门讨论了工程知识问题。他指出:“在人类的知识总量中,工程知识——包括工程规划知识、工程设计知识、工程管理知识、工程经济知识、工程施工知识、工程安全知识、工程运行知识等——不但是数量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从知识分类和知识本性上看,还是‘本位性’的知识而不是‘派生性’的知识。”“当前在国内外都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即使可以承认古代的工程知识不以科学知识为前提或基础,但在现代社会中,工程知识乃是(单纯)应用科学的结果。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工程知识解释为科学知识的派生知识’,虽然这种观点相当流行,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工程知识本性的误解。”①李伯聪:《工程创新与工程人才》,载杜澄、李伯聪主编:《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第2卷),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李伯聪的上述文章还不是专题研究工程知识的论文。我国最早对工程知识进行“专题哲学研究”的学者是邓波。他作为第一作者在2007年发表了《试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工程知识》②邓波、贺凯:《试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工程知识》,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0期。,在2009年发表了《工程知识的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③邓波、罗丽:《工程知识的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4期。。邓波强调指出,工程知识是不同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知识类型和知识形态,工程知识既具有科学技术维度,又具有人文社会维度的复杂的知识类型,又具有独特性、地域性、综合性、可靠性、复杂性、协调性、情境性、现场发生性、难言性、不可复制性、优化性、评价的多元性。
2017年,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立项研究工程知识论,组织多位工程院院士和哲学专家参加研究,对有关工程知识的多方面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作为课题最终成果的《工程知识论》④殷瑞钰、李伯聪、栾恩杰等:《工程知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出。将于2020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将成为国内外第一本研究“工程知识论”的哲学专著。
六、多个“知识论分支”的形成发展与“知识论2”的前景展望
(一) 多个知识论“分支”的形成与继续发展
本文开头谈到了知识分类问题,在本文结尾,需要谈谈与其密切联系的“知识论分支”问题。陈嘉明有一本研究知识论的专著《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虽然其最后一章以“(知识论的)方法论与新分支”为标题,但这一章的正文中没有直接而明确地分析和阐述“知识论分支”问题,特别是没有直接而明确地说明所谓“知识论分支”的具体含义和发展前景如何,这似乎又在暗示该书作者对“知识论分支”这个概念持“谨慎态度”。这一章的内容包括三节:“自然主义的知识论”、“德性知识论”和“社会知识论”。⑤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316页。揣摩其内容和文义,其作者似乎意在指出“自然主义的知识论”是知识论研究的“新方法论”,而“德性知识论”和“社会知识论”是知识论的“新分支”。但耐人寻味的是,陈嘉明在正式行文中又没有明确指明“德性知识论”和“社会知识论”是知识论的两个“新分支”,而只明言其为“新方向”。所谓“(学术)方向”与“(学科)分支”,可能是一回事,也可能不是一回事。这里不讨论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以下只讨论与“知识论分支”有关的一些问题。
有鉴于陈嘉明把“新方法与新分支”作为第六章的标题,我们也就“趁势”把德性知识论” (作为第二节标题和内容)和“社会知识论” (作为第三节标题和内容)理解为知识论的“两个新分支”,而不仅仅是“新方向”。
对于作为知识论“新分支”的社会知识论,陈嘉明说:“社会知识论是知识论领域中的一个新方向。”“在社会知识论者看来,传统的,尤其是笛卡儿意义上的知识论属于‘个体知识论’,其个体性表现在集中关注于认识主体孤立的心灵运作。然而,由于知识本身具有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密切协作与互动的性质,更使得个体知识论需要有一个对应物,这就是社会知识论。”①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300页。
可以看出,以上所引文句的核心观点是主张人类的知识需要划分为“个体知识”和“社会知识”“两大类”,从而需要形成“两个不同的知识论分支”。社会知识论者要建立和发展出一个“知识论的新分支”——社会知识论,认为传统知识论只代表“另外一个知识论分支”——个体知识论。
我们知道,对于分类问题,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会划分出不同的“分类系统”。如果说,在进行“个体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两类划分”时,其依据的分类标准是对“认识主体的划分”,那么,如果依据对“认识客体(对象)的划分”而进行知识分类,人们就又可以划分出“科学知识”“工程知识”“伦理知识”这三类知识,相应地,也可以形成“科学知识论”“工程知识论”和“伦理知识论”这三个不同的知识论分
支”。对于“伦理知识论”,上引陈嘉明著作的第六章第二节已经有专题论述,着重介绍了索萨的“德性知识论” (virtue epistemology),最近,我们又看到了新翻译出版的道德知识论》②齐默曼:《道德知识论》,叶磊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版。,这些都表明作为一个分支的“伦理知识论”——尽管难免还“不成熟”——“已经出场”了。
如果把科学知识论、工程知识论和伦理知识论看作知识论的“三个分支”而回顾其历史轨迹和当前状况,可以看出科学知识论的内容最为丰富,其发展和成长过程井然有序,形形色色的成果蔚为大观,作为一个分支的“科学知识论”的理论大厦已经相当牢固。这就是说,科学知识论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称已经发展成为知识论的一个“成熟的分支学科”。
相比之下,工程知识论只有若干点点滴滴和模模糊糊的历史印痕,从比较严格的“哲学研究”的角度看,它在长期的历史上只有偶然留下的个别“雪泥鸿爪”。虽然文森蒂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工程知识”这个概念,但他的著作属于“工程史著作”而不属于“哲学著作”,不是“知识论著作”。皮特的论文虽然是研究“工程知识”的哲学论文,但尚不能认为已经达到了奠定“工程知识论”理论框架的程度。上文谈到,《工程知识论》将于2020年正式出版,从该书的研究过程①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自2004年起,连续而不间断地“科研立项”研究工程哲学,先后出版了《工程哲学》 (第1、2、3版)、《工程演化论》 《工程方法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于2018年立项研究“工程知识论”,即将出版的《工程知识论》就是该项研究的结项成果。从广义上说,《工程知识论》一书是工程管理学部组织有关院士和哲学专家“持续16年研究工程哲学”而在“工程知识论”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作者构成(包括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哲学专家),特别是全书内容和结构(此处不赘言)看,该书的出版将会成为“工程知识论初步形成一个知识论分支”的标志。
可以看出,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成果看,在科学知识论、工程知识论和伦理知识论这三个分支中,科学知识论都是最成熟的分支,而工程知识论只是新诞生的分支,伦理知识论则是幼年期的分支。
以上谈到了多个知识论分支,可以预期,在今后的学术发展中,不但这些分支会有新进展,而且也不能排除会有其他新分支崭露头角。展望未来,这些知识论分支都将继续有新的发展。
不同的知识论分支不但有不同的历史源流和学术现状,而且有不同的未来发展重点、发展路径与发展战略。就工程知识论这个新分支的未来发展而言,今后在研究成员和研究方式方面,应该特别注意加强“工程师、工程管理者和哲学家的学术研究联盟”,使工程师、工程管理者和哲学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从而推动工程知识论——作为一个新的知识论分支——更快、更深入地发展。就研究课题和理论主题而言,不但需要特别关注对工程知识、默会知识、操作性知识、具身知识的“相互关系研究”,而且需要特别关注对工程设计知识、工程集成知识、工程管理知识、工程评估知识等的理论研究。有理由预测,工程知识论有望成为21世纪在知识论领域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
(二) 展望“知识论2”在21世纪的未来前景
知识论——这里主要指欧洲的知识论——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由于多种原因,欧洲的知识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仅仅局限于研究“个体的科学知识”的哲学理论,本文将其称为“知识论1”。
20世纪以来,“知识论1”的一些重大缺陷和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这就促使几个新的知识论分支逐渐崭露头角。在这几个新的知识论分支涌现之后,它们势所必然地要成为人们回顾历史、评估现状和展望未来的“新立足点”。站在“新立足点”上,人们不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传统知识论” (即“知识论1”)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评估知识论的宏观现状与形势,展望知识论的未来方向和前景。
站在“知识论新分支”的“立足点”上分析形势和展望前景,人们会强烈感受到原先那个“知识论1”正面临着“历史性转型”和“学术体系更新换代”的机遇与形势——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知识论1”需要被“更新换代”为“知识论2”了。
在“知识论2”的视野中,不但需要大力拓展和深化各个“知识论分支” (包括作为“传统分支”的个体知识论和科学知识论以及作为“新分支”的工程知识论、社会知识论、伦理知识论),而且需要研究“各个不同分支”的“相互关系”,而更关键之处是需要在全面思考各个分支的性质、特征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和逐步建构“知识论2”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论大厦”——这才是21世纪知识论领域最大的挑战和在展望未来时出现的最激动人心的前景。
如果说传统的“知识论1”把“确证”当作知识论的主要任务,那么,对于“知识论2”来说,就需要更加关注“设计思维”“操作知识”“程序知识”“人工物知识”“评价知识”“制度知识”“社会知识”“知识要素”“知识集成”“知识系统”“知识转化”“知识管理”等问题。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21世纪的哲学家应该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中实现从“传统的知识论1”向“知识论2”的“转型”,努力逐步完成为“知识论2”理论大厦“初步奠基”的任务。在本文最后,我愿与知识论领域中进行学术探索的“同道”共同品味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