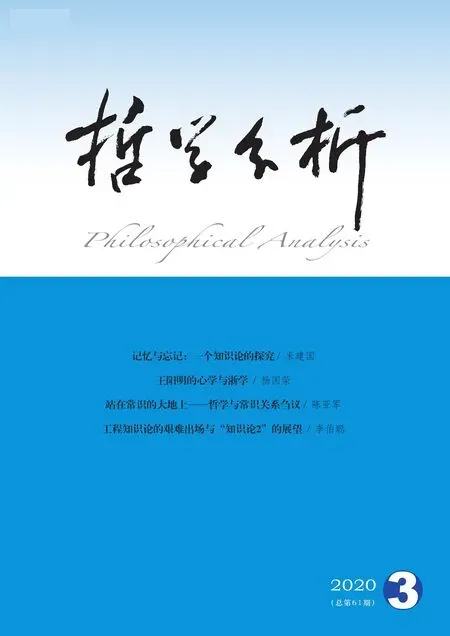理性慎思与实践融贯性
徐向东
在《论真正重要之事》中,德雷克·帕菲特论证说,关于规范理由的主观主义和伦理自然主义会导致道德怀疑论和虚无主义,因此,为了维护真正有意义或有价值的人类生活,就必须拒斥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采纳他所说的客观主义与规范实在论。①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为了方便,以下引用该书页次将直接标注在正文中。帕菲特对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驳是密切相关的,不过,本文仅限于考察他所说的“极度痛苦论证” (the agony argument),不仅因为这个论证在他反对主观主义的总体论证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因为这个论证暗示了道德心理学中的一些有趣问题,例如与实践合理性的本质和理性能动性的构成相关的问 题。
本文试图表明帕菲特按照“极度痛苦”论证对主观主义的反驳并不成功。在第一节中,作为讨论的背景,我将简要地介绍帕菲特在两种理由理论之间所作的区分及其“极度痛苦”论证;在第二节中,我将尝试表明帕菲特用来支持其论证的案例为什么是实践上不融贯的;在第三部分,通过引入人格同一性假设,我将试图表明为什么主观主义者有理由拒斥他所提出的论证。
一、“极度痛苦”论证
帕菲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理由理论:对象立足的(object-based)理论或客观理论认为,行动的理由是由关于欲望对象的事实提供的;主体立足的(subject-based)理论或主观理论则认为,行动的理由是由关于行动者的欲望的事实提供的(I. 45)。在帕菲特的理解下,主观理论具有两种基本形式:按照第一种形式(即所谓的“目前欲望理论”),行动的理由是由一个人目前的欲望或目的来提供的;按照第二种形式,行动的理由是由一个人在理性慎思下所具有的欲望或目的来提供的。帕菲特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者必须将理性慎思限制到程序合理性。他并没有明确说明哪些原则属于程序合理性原则,不过,他对程序合理性提出了如下说法:“我们应当尝试充分地想象我们可能具有的不同行为的重要影响,避免一厢情愿的思想,正确地评估每个可能的行为所发生的概率,遵循某些其他的程序规则。假若我们用这些方式来进行慎思,我们就是程序上合理的。” (I. 62)与此相比,客观主义者则对欲望和目的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应当具有我们在实质上充分理性的情况下所具有的欲望和目的。在这里,说一个行动者是“实质上充分理性的”就是说,为了回应由对象的内在特点(或者关于这些特点的事实)所提供的理由,他必须具有相应的欲望并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因此,客观主义“不是关系到如何选择,而是关系到选择什么” (I. 62)。帕菲特并不否认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都可以采纳他所说的“慎思理论”,即如下观点:我们最有理由做的事情,是我们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经过理性慎思决定要做的事情。对于帕菲特来说,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对理性慎思的条件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主观主义者往往将理性慎思的条件归结为认知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客观主义者则强调说,实质性合理性根本上在于回应对象的内在特点所提供的理由。“极度痛苦”论证关键取决于帕菲特提出的一个基本主张:主观主义者只能采纳他所说的“目前欲望/目的理论”,大致说来即如下观点:只有目前的欲望或目的才能提供行动的理由。帕菲特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主张,只是将它作为其论证的一个规定。不过,为了弄清楚他为什么会作出这个规定,我们不妨看看伯纳德·威廉斯对行动的理由所提出的内在主义论述①Bernard Williams,“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in Williams,Moral Luc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1—115;Bernard Williams,“Internal Reasons and the Obscurity of Blame”,in Williams,Making Sense of Huma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5—45.,因为,帕菲特主要是按照威廉斯的观点来设想主观主义。在威廉斯看来,一个行动的理由必须满足如下基本要求:它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行动者采取行动并因此而说明行动。为此,行动者就必须通过理性慎思将这个理由与其主观动机集合中的某个或某些要素联系起来。主观动机集合是行动者当前持有的所有动机的集合,而威廉斯也对其构成要素采取一种广泛的理解,例如,欲望、偏好、目的、价值观都可以名列其中,只要它们是用威廉斯所设想的那种方式形成的。从威廉斯对“行动理由”的理解来看,行动的可理解性(或者对行动提出的理性说明)就在于行动是来自行动者自己的内在理由。就此而论,一切意向行动(intentional action)都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行动者自身的理性能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帕菲特对于主观主义提出的规定至少是可理解的。不过,我将尝试表明,即使主观主义者接受帕菲特的规定(也就是说,承认只有目前的欲望或目的才能提供行动的理由),他们仍然可以表明一个人现在有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祉,因此可以反驳帕菲特的批评。
“极度痛苦”论证本质上是一个归谬论证:它试图表明主观主义会产生直观上荒谬的结果,因此是不可接受的。这个论证关键取决于帕菲特所设想的一个案例(I. 56):一个人(不妨称之为“德雷克”)很在乎自己未来的快乐或痛苦,却唯独不在乎自己在每一个未来的星期二的感受——即使他准确无误地知道,他在每一个未来的星期二所要遭受的痛苦,远远大于他在未来任何其他时间所遭受的痛苦,但他此时仍然宁愿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帕菲特声称德雷克的古怪偏好显然是不合理的或荒谬的,并对这个案例提出了如下补充说明:“我知道一些未来的事件会引起我具有某个时期的极度痛苦。甚至在经过理性慎思后,我也没有欲望避免这个痛苦。我也没有任何其他欲望,其满足会因为这个痛苦而受到阻止,或者会因为我不具有避免该痛苦的欲望而受到阻止。” (I. 73—74)这个补充说明旨在表明,“我”所具有的那个古怪欲望不仅满足了主观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慎思条件,而且在如下意义上也是自洽的——那个欲望的满足不会挫败“我”可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欲望或目的。因此,如果主观主义者认为,理由是由行动者在理想慎思条件下在当下具有的欲望或目的(或者关于这些欲望或目的的事实)来提供的,那么主观主义就是直观上不可接受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将帕菲特的论证简要地重构如 下:
(1) 我们都有理由想要避免而且尝试避免一切未来的极度痛苦。
(2) 主观主义意味着我们没有这样的欲望。
(3) 因此,主观主义是错误的。
很明显,如果我们确认该论证的第一个前提并希望维护主观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表明主观主义者无需接受第二个前提。下面我将尝试提出两个论证来表明主观主义者确实无需接受第二个论证前提:第一,甚至从主观主义的观点来看,帕菲特的案例也是不能连贯设想的;第二,主观主义者能够正面说明一个人为什么有理由在乎自己未来的极度痛苦。
二、实践融贯性
按照休谟对“可设想性”的经典理解,一切不涉及逻辑矛盾的东西都是可设想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可能的。然而,即使帕菲特的案例是可设想的,我们仍然很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具有那种怪异的心理特征。例如,我们很想知道,如果一个人的确在乎自己未来的福祉,那他为什么唯独不在乎自己在未来某个特定时刻的福祉?当然,帕菲特承认那个人的偏好是任意的,并把这个直观认识当作反对主观主义的一个理由。然而,主观主义者可以拒绝接受帕菲特就此提出的批评。
在帕菲特的案例中,如果德雷克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合理性,那么,既然他提不出任何理由来说明他自己为什么会具有那个偏好,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在每一个未来的星期二的福祉这件事情,甚至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也是不可理解的。也许,星期二对他来说是个很特别的日子,例如,他是在星期二那天出生的,他母亲在生下他后就因难产而去世了,因此他就产生了如下想法:每一个未来的星期二都是受难日,不管在那天发生什么令自己痛苦不堪的事情,他都要忍受,都要毫不在乎——事实上,如果他能够选择一件会让自己痛苦不堪的事情发生,他宁愿选择它在任何未来的星期二发生,将此作为一种自我惩罚,一种表达自恨的方式。这样一种心理特征或许很罕见,但其形成和持有都不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帕菲特不仅没有说明德雷克为什么会持有如此怪异的偏好,反而对其案例提出了一个补充说明,以此来强化他对主观主义的拒斥(参见I. 82)。按照帕菲特提出的补充说明,德雷克的欲望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内在的,也就是说,不是被当作满足任何进一步的欲望或实现任何进一步的目的的手段;其次,拥有或满足这个欲望不会挫败他可能持有的任何其他内在欲望或目的。
在帕菲特对这个案例的特定设想下,具有这样一个欲望确实不是逻辑上不一致的。然而,在实践领域中,并非任何逻辑上一致的思想实验也都是实践上融贯的。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莎伦·斯特里特对帕菲特的案例提出的分析。①Sharon Street,“In Defense of Future Tuesday Indifference:Ideal Coherent Eccentrics and the Contingency of What Matters”,Philosophical Issues,Vol.19,No.1,2009,pp.273—298.斯特里特对规范理由采取了一种主观主义理解,认为规范理由取决于我们的评价态度以及从这种评价态度所构成的实践观点中得出的东西。斯特里特试图表明,对规范理由的这种理解可以很好地把握我们对帕菲特的案例(以及类似案例)的直观认识。也就是说,在帕菲特的案例中,一旦那个“怪异的”欲望的本质得以澄清,持有这样一个欲望实际上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帕菲特承认痛苦的经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感觉,而是一种结构上更加复杂的有意识的状态,是由某个感觉和我们对它持有的评价性态度(例如不喜欢它)构成的。在帕菲特的案例中,如果德雷克持有的那个看似古怪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不变,那么,在某个指定的未来星期二,在他即将遭受的极度痛苦来临时,只要他已经对极度的痛苦有所体验(实际上,只要他仍然具有正常的心理条件),他势必就会感到很害怕,因此很可能会希望那个即将来临的痛苦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偏好将是不一致的——既然他仍然具有基本的理性能力,他就不应该欲求自己在未来某个时刻所要遭受的极度痛苦。但是,帕菲特假设德雷克一致地保持其古怪偏好,因此,既然德雷克此前就对极度的痛苦有所体验,而且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在未来的星期二必定会遭受极度痛苦,我们就需要寻求理解一个关键问题,即他为什么愿意忍受那个痛苦,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为什么会具有那种奇怪的动机结构?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斯特里特设想了一个进化故事。假设德雷克是一个外星人,来自太阳系附近某个星球上进化出来的物种。该星球在很多方面都与地球相似,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在那个星球上,有一种残忍的捕食鸟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是会定期出来进食、交配、锻炼狩猎技能,而它们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折磨生活在那个星球上的人们。只要那种鸟类出来活动,他们就没有藏身之所,而且会遭受可怕的身体折磨和痛苦。不难设想,在德雷克所属的物种的进化环境中,为了幸存和繁衍,他们就在生物学上形成了一种特殊偏好,即在那种鸟类出来活动期间不再担心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实际上变得对遭受这种痛苦无动于衷。而当那种鸟类不出来活动时,他们就像我们那样尽量避免痛苦。
斯特里特的说明并非本质上不同于我们在试图理解德雷克的“怪异”偏好的时候所提出的说明——对于任何具有基本的理性能动性的行动者来说,如果我们发现他持有一种看似怪异的偏好或欲望,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其个性形成的历史或其进化史来说明他为什么持有这样的偏好或欲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其动机结构提出一种更精确的描述,然后按照这种描述来检验我们的直觉。帕菲特对其案例的设想显然是高度抽象的,因此,他试图从其案例中诱发出来的直觉就说不上公正地对待了主观理论。相比较而言,斯特里特的案例显然满足了主观主义者对理性欲望所设想的一些基本要求:首先,那个外星人的痛苦无疑就是痛苦,是由某些感觉和对这些感觉的态度构成的;其次,他确实具有帕菲特所说的那种偏好;再次,这种偏好不是在错误信念或无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这种偏好的形成满足了理性慎思的基本条件,而帕菲特并不否认主观主义者可以有一个理性慎思理论。那个外星人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对我们来说很怪异的偏好,是因为他生活在那种特殊的进化环境中。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了他所生存的特殊环境,那种偏好就以一种符合主观理论的方式变得可理解。如果某个行动者确实具有从我们自己的实践观点来看无法理解的偏好,那么他很可能属于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物种,生活在与人类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但是,这个事实正好表明主观理论是正确的——某种类型的行动者具有什么样的行动理由是相对于其实践观点而论的。相比较而言,在帕菲特的案例中,如果德雷克在未来的痛苦即将来临之际感到很害怕,但口头上仍然坚称自己偏爱那种未来的痛苦,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他的内在动机结构或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或是产生了严重的张力:一方面,他的未来的自我强烈地反对那种极度痛苦,抵制产生该痛苦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确保那种偏好得到服从。如果他在有关问题上是充分知情的并具有正常的人类心理条件,那么,当他处于这种情况时,他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是程序上不合理的,而是在于他根本上不关心自己未来的痛苦——他是在对自己未来的自我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残忍态度。
那么,主观主义者能够表明他不应当具有这种态度吗?提出这个问题就相当于追问主观主义者是否能够将审慎合理性(prudential rationality)原则(或者某个类似的原则)纳入他们对实践合理性的考虑中。至少从威廉斯的内在理由概念的精神实质来看(即便不是从他的理论的实际内容来看),主观主义者有理由把对未来自我的关注纳入实践合理性的范围。在威廉斯看来,当我们说某个人有理由做某事时,我们大概是在说,在经过适当的理性慎思后,他发现那个被赋予他的理由与其主观动机集合具有可靠联系。在满足程序合理性要求的情况下,如果他并未经过自己的理性慎思发现这样一个联系,那么我们就不能将这个理由赋予他。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威廉斯实际上并不认为主观动机集合中的任何要素都能够向一个人提供行动的理由。为了有理由行动,行动者不仅需要具有一切相关的真信念,没有相关的假信念,也需要满足广泛意义上的工具合理性要求,而广泛意义上的工具推理并不只是在于发现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在于对某个问题寻求构成性的解决方案constitutive solutions),例如设法将一个总体目标分解为一系列子目标,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寻求实现每一个子目标的手段。在某些复杂的情形中,行动者还需要通过行使想象力来发现某个理由陈述与其主观动机集合究竟有没有可靠联系。从威廉斯对理性慎思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重要主张。第一,实践慎思是开放的,不限于只是使用某些固定的程序或规则,因此,在帕菲特所说的程序合理性原则和实质性合理性原则之间,可能就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而这个区分对于帕菲特的论证来说是关键的,因为他主要是按照这个区分来设想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差别。第二,我们之所以对于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满足认知合理性的要求感兴趣,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想要成功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或实现拟定的目标。然而,满足欲望或实现目标的活动是在时间上展开的:欲望是一种要求其对象得到实现的精神状态,因此,如果行动者有兴趣满足一种欲望,那就意味着他是在时间历程中来看待其能动性的行使,能够把满足那个欲望的主体鉴定为自己未来的自我。换句话说,就欲望的满足而论,他必须相信自己是在时间上同一的。借助于这两个基本主张,我们就可以表明主观主义者能够回答帕菲特提出的挑 战。
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第一个主张。帕菲特论证说,即使我们是在威廉斯所设想的那种广泛意义上来界定程序合理性,程序合理性原则也不能用于评价内在欲望或目的。然而,这个主张是错误的。从帕菲特对程序合理性提出的说法(I. 62)来看,程序合理性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就类似于人们在从事理论推理时所要遵循的规则,例如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规则和合情合理的推理原则。按照这种理解,在实践推理的情形中,程序合理性原则就是这样一些规则:它们用一种形式上有效的方式制约欲望的形成和修改。例如,在理论推理的情形中,如果一个人实际上有更多的(或更有力的)证据相信命题p而不是命题q,那么,当他接受q而不是p的时候,他就是理论上不合理的。同样,在实践领域中,如果一个行动者明确地意识到,满足欲望p将会挫败对他来说更加重要的另一个欲望q,那么,当他采取行动来满足p的时候,这个行动在实践上就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只要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欲望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或者至少意识到对我们来说具有一定重要性的要素,我们应当让自己的欲望系统保持基本的融贯性。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如下事实:既然我们的认知能力(包括记忆存取能力)和满足欲望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必然会具有某些冲突的欲望。不过,只要我们不打算同时满足实际上会发生冲突的欲望,我们就具有了某些可以潜在地发生冲突的欲望。另一方面,当我们试图满足某个与其他欲望潜在地发生冲突的欲望时,我们就需要适当地调整这些欲望,例如,或是放弃那个特定欲望的满足,或是悬置与之发生强烈冲突的欲望。潜在地发生冲突的欲望可以对欲望满足施加压力,从而迫使我们调整或修改欲望系统,使之在特定时刻变得相对融贯。
在某种意义上说,程序合理性确实是一个内部问题:为了评价某个欲望,我们不仅需要看看我们在形成或持有它的时候是否遵循了某些程序上可指定的规则,也需要将它与我们所持有的其他欲望相比较。不管我们一开始是如何获得某些欲望的,我们在任何时刻具有的欲望构成了一个评价起点,帮助我们形成了某种评价态度。离开了我们所占据的某个评价性立场,我们就不能说某个欲望是否合理。不过,要我们思想开放并具有适当的反思能力,我们就可以将某些新的要素引入欲望系统中,学会调整乃至重塑欲望系统。这些说法表明,我们必须有一种支持欲望系统的融贯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如何形成的是一个复杂问题,或许可以从人类道德心理的进化中得到部分说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冲突的欲望会在物质资源和认知资源的配置上对我们产生很大压力。假若我们总是纠结在欲望的冲突中,无法寻求合理的手段来满足任何欲望,那么我们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进化心理学可能也有助于说明如下事实:一旦我们发现自己的欲望系统(或者甚至整个心理结构)的不融贯超出了某个限度,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自在。此外,只要我们必须生活在社会世界中,社会化机制也会促成我们对欲望系统的融贯性采取一种赞成态度。具有这种态度对于实践生活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广泛意义上的欲望构成了行动的本质动 机。
假若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欲望系统的融贯性,那么,在帕菲特的案例中,只要德雷克具有适当的理性反思能力,他迟早就会发现持有那个古怪的偏好会在其欲望系统中产生严重张力,因此至少就会考虑要不要放弃这个偏好。帕菲特的案例之所以在直观上有吸引力,只是因为他已经假设,对于德雷克来说,持有那个欲望不会与他的任何其他欲望发生冲突——实际上,按照帕菲特对其案例的特设性描述,德雷克根本就不具有任何其他重要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德雷克要么根本就不具有正常的人类心理条件,要么就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物种。现在我们可以表明,在对欲望进行评价的时候,只要我们引入了某些关于人类心理条件的一般考虑,我们不仅很难把程序合理性与实质性合理性截然区分开来,而且也可以从程序合理性原则中推出某些实质性合理性原则。按照对这个区分的一种“标准”解释,如果一种关于实践合理性的理论认为,只有当一个行动者能够从他所持有的信念和欲望中理性地达到某个欲望时,他才有理由持有那个欲望,那么这种理论就是程序性的;另一方面,如果一种关于实践合理性的理论认为,不管一个行动者是否能够从他所持有的信念和欲望中理性地达到某个欲望,他都可以被认为有理由持有那个欲望,那么这种理论就是实质性的。①参 见 Brad Hooker and Bart Streumer,“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Practical Rationality”,in Alfred Mele and Piers Rawling(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Ration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45—56。按照这种解释,实质性合理性概念就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践理由必须被设想为根本上不依赖于行动者的动机条件(甚至不依赖于其主观构成)而具有有效性。然而,就实质性合理性概念而言,这个要求会在帕菲特这里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含义。帕菲特承认程序合理性和实质性合理性都涉及“理性慎思”的概念,对于倡导程序合理性的理论家来说,理性慎思仅仅涉及满足认知合理性和广泛设想的工具合理性要求,因此他们可以对“实践理由”提出一种非循环的定义。然而,对于倡导实质性合理性的理论家来说,我们就不太清楚“理性慎思”中所说的“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指的是程序合理性,那么我们自然会问,满足程序合理性的要求对于具有一个实践理由来说为什么仍然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如果它指的是实质性合理性,那么这个定义似乎就是循环的。就前一个方面来说,实质性合理性概念的倡导者会说,不管行动者如何慎思,一个实质上合理的行动者就是正确地回应他对理由的理性认识的行动者。这个答案显然并没有对我们为什么有理由采取某个行动提供任何实质性说明。在我看来,合理的做法是,我们需要从我们对程序合理性的某些直观认识出发,按照某些关于人类心理和人类条件的考虑来说明我们如何能够是实质上合理的。因此,不管我们如何区分这两个合理性概念,我们不应该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实际上,正如迈克尔·史密斯已经表明的,不仅我们很难将程序合理性原则与实质性合理性原则截然区分开来,而且,只要我们引入了某些假定,主观主义者就可以接受某些实质性的合理性原则。①Michael Smith,“Desires,Values,and the 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in Juss Suikkanen and John Cottingham(eds.),Essays on Derek Parfit’s On What Matters,Oxford:Blackwell,2009,pp.116—143.如果史密斯的论证是可靠的,那就表明帕菲特不能声称主观主义者只能承认程序合理性原则。例如,在尝试将某些实质性合理性原则从程序合理原则中推导出来时,我们只需引入一个普通假定,即行动者具有充分的反思能力。这种能力无需涉及(比如说)经过反思、从一种毫无道德承诺的状态进入有所承诺的状态,只要求行动者能够经过反思发现其心理结构在某些方面是不融贯的。
如果人类理性能力本身就是从人们与周围世界的策略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②对这一点的相关论述,参见David Papineau,The Root of Reason:Philosophical Essays on Rationality,Evolution,and Proba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2006;Samir Okasha and Ken Binmore(eds.),Evolution and Rationality:Decision,Co-operation and Strategic Behavi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程序性”合理性原则与“实质性”合理性原则为什么很难分离开来。工具合理性和欲望系统的相对融贯性表达了实践合理性的最低要求,但是,在如下意义上很难说它们只是程序性的:我们将什么手段看作满足欲望或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不仅取决于经验认识,也取决于一个人对其资源的认识以及对目标欲望之重要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欲望系统是否融贯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部问题,因为为了恰当地评估自己的欲望系统,一个人就需要对相关欲望及其重要性进行理性反思,而这种反思至少要求对外部世界保持开放,正如我们需要引入观察输入才能恰当地判断信念系统的融贯性。在帕菲特的案例中,既然德雷克具有的那个古怪欲望既不是工具性的,也不会妨碍他的任何其他欲望的满足,它就只是其欲望系统中一个完全孤立的要素。人们可能偶然具有这样一个欲望,但是,这种情形显然不是真实的人类生活的常态。现在,假若我们采纳了帕菲特所说的慎思理论,我们就可以提出如下论证(I. 78):
(1) 我们有理由具有任何充分理性的人将会具有的欲望。
(2) 任何充分理性的人都想避免一切未来的极度痛苦。
(3) 因此,我们有理由想要避免一切未来的极度痛苦。
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提出的论述是可靠的,那么这个论证就是主观主义者所能接受的。帕菲特之所以断言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提出这个论证,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客观主义者才能提出该论证的第二个前提。但是,这个判断是错误 的。
首先,帕菲特声称,避免未来的极度痛苦的理由是由这种痛苦的内在特点提供的,因此,只要我们在他所说的意义上是“实质上充分理性的”,我们就有欲望回应我们对这些客观特点的认识。然而,痛苦本质上是一种与我们的主观构成相关的复杂状态——用帕菲特自己的话说,痛苦是由我们在身体上经受的某种感觉和我们对这种感觉所采取的某种有意识的态度构成的。即使人们由于具有类似的生物—心理构成而在正常状况下具有这种感觉,我们也不能在物理对象或性质根本上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意义上,将产生痛苦的因素称为“客观的”,而帕菲特显然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客观性”和“客观理论”。
其次,帕菲特声称,主观主义者只是认为,在满足程序合理性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欲求能够实现某个目的性欲望的必要手段。对他来说,主观主义者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在理性上不被要求具有非工具性的欲望或目的。然而,帕菲特在这里对“理性”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歧义的,或者至少不加论证地预设了其客观主义立场。如果我们在帕菲特的意义上来理解“理性”,即把理性看作按照我们对事物本来就具有的规范特点的认识来形成理由和采取行动的能力,那么主观主义者就不会接受他对规范理由的这种理解。对于主观主义者来说,帕菲特的规范实在论并不是充分可理解的,除非我们假设存在着某种神秘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理性行动者就可以把对这些本质上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规范特点的认识与按照这种认识来行动的倾向联系起来。这种力量要么是超自然的,要么是自然的。主观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拒斥前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希望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来探究这种联系,那么进化的故事就会成为最合理的选择。然而,在按照进化心理学来说明这种联系时,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至少不会支持帕菲特所设想的那种规范实在论。①关于这一点,参见Sharon Street,“A Darwinian Dilemma for Realist Theories of Values”,Philosophical Studies,Vol.127,No.1,2006,pp.109—166。帕菲特声称主观主义者没有思想资源评价内在欲望。然而,主观主义者只是强调价值本质上具有主观起源,本质上依赖于人们已经具有的评价态度,即一种将世上某些东西看作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或坏的、有价值的或无价值的、值得追求或不值得追求的态度。①参见Sharon Street,“What is Constructivism in Ethics and Metaethics?”,Philosophy Compass,Vol.5,No.5,2010,pp.363—384。换句话说,主观主义者只是认为,价值是相对于我们已经占据的某个实践观点而论的。我们为了生存而学会适应周围环境,学会选择性地回应其中的某些特点,由此就形成了一个用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实践观点。价值是以这种方式被构成的,而不是一种本来就存在于世界之中、不能进一步加以说明的规范实体。主观主义者也无需否认,我们可以因为实践观点的收敛而分享某些价值,将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最终认为这些价值具有一种不依赖于任何特定个体的规范权威。这就是说,主观主义者可以说明重要的人类价值对我们来说如何能够具有一种“客观”地位。因此,他们也无需否认人们可以学会评价自己的内在欲望。
三、人格同一性假设与未来的理由
“极度痛苦”论证旨在表明,只要主观主义者采纳了他所说的“目前欲望理论”,他们就无法说明一个人有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祉,而我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理由。因此,为了回应帕菲特的挑战,主观主义者就需要表明我们确实有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祉。现在我将试图表明,主观理论能够满足这个要求。我的论证由两个部分构成:首先,我将表明,就理性能动性的构成而论,目前欲望理论是合理的;其次,我将表明,通过引入人格同一性假设,主观主义者可以说明我们对自己的未来自我的关注。帕菲特论证说(参见I. 73—74),既然主观主义者接受了目前欲望理论,主观主义就意味着我没有理由避免未来的极度痛苦。假若主观主义者确实认为行动的理由只能来自目前的欲望,那么,为了抵制帕菲特赋予主观主义者的那个结论,主观主义者就必须表明,关于未来的欲望的事实能够提供行动的理由。“未来的欲望”这个概念大概可以在两个意义上来理解:第一,一个人目前对在未来即将发生的某件事情有欲望,例如,我的欲望是在2040年消除全球贫困;第二,一个人目前对其未来的自我所处的某个状态有欲望,例如在未来某个时刻不要遭受极度痛苦。在前一个意义上,一个未来的欲望仍然是我当下持有的欲望,尽管只是在未来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帕菲特大概是在第二个意义上来谈论“未来的欲望”。他想要说的是,按照主观主义的观点,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欲望避免未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某件事情。如果我们排除了帕菲特在其案例中作出的特设性规定,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欲望去避免未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德雷克之所以没有欲望去避免自己在每一个未来的星期二所遭受的极度痛苦,是因为帕菲特已经假设持有这样一个欲望不会挫败德雷克可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欲望。帕菲特案例的直观吸引力完全来自于这个假设。然而,一旦我们回到真实世界并考察理性行动者的一般心理条件,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假设并不是充分合理的。首先,甚至一个人目前持有的欲望也是在时间上得到满足的。我喝咖啡的欲望需要采取一系列中间步骤才能得到满足。只要我认识到我的欲望满足活动是在时间上展开的,那么任何当前欲望的满足都要求一个预设,即那个要被满足的“我”就是当前持有那个欲望的“我”。换句话说,欲望满足活动预设了我在时间上是同一的。因此,既然德雷克确实在乎自己未来的福祉,而未来是由在他面前即将展现出来的每一个时刻构成的,因此我们就不太清楚他为什么唯独不在乎自己在每一个未来星期二的福祉。其次,当威廉斯强调行动的理由必须与行动者目前的主观动机集合具有可靠联系时,他不仅是在表达行动的理由必须满足的一个基本要求,即作为行动理由的东西必须能够说明行动,而且也是在表明一个重要主张,即一切慎思都是以目前的动机结构为起点,特别是以我们对重要价值的承诺为起点。如果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承诺,或者对其欲望的重要性不加分辨,那么我们就很难设想他如何能够有意义地进行慎思。①按照科斯格尔的说法,这样一个人并不具有真正的能动性,因此其行为也说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行动。参见 Christine M. Korsgaard,Self-Constit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68—169。既然他不需要规划自己的生活,他就无需慎思。但是,只要我们开始通过慎思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慎思的起点和来源就必然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我们或许在时间的历程中学会调整和修改自己的价值观念,但是,只要我们不希望通过过度反思来摧毁自己的全部价值观念并因此而摧毁我们的自我,我们就必定要以我们目前具有的某些其他价值作为基础。因此,从第一人称的观点来看,实践慎思必定是以“当下”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如果我们有任何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祉,那么这种理由必定是从我们目前的动机结构出发,经过理性慎思而达到的。换句话说,我们关心自己未来的自我的理由,根本上说,来自我们对于人格同一性的信念以及我们对自己目前的自我的关切。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让我简要地考察一下两位作者对帕菲特的回应。戴维·索贝尔拒斥了帕菲特对主观主义的规定(即目前欲望理论),转而认为未来的理由可以通过合理性原则而“传递”到目前。例如,如果一个人后来有理由避免未来的某种极度痛苦,那么他现在有理由采取手段来避免那个痛苦发生。②David Sobel,“Parfit’s Case against Subjectivism”,in David Sobel,From Valuing to Value:A Defense of Subjectiv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75—298.然而,索贝尔的方案在我看来有两个主要缺陷。首先,如果威廉斯对实践慎思的论述是可靠的,那么理由传递的方向实际上是从当下到未来:我们采取未来的任何可能行动的理由都是来自目前的动机结构。其次,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只要我们承诺了某些合理性原则,我们就有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祉;但是,主观主义者并不认为一切合理性原则都应该被纳入行动的理由和理性慎思的概念中。这是他们与客观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差别。在拒斥目前欲望理论的情况下,为了回应帕菲特的批评,索贝尔至少需要预设审慎合理性原则。在索贝尔的解释下,这个原则意味着我们必然有一个当下的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祉。但是,这个结论不太符合一个直觉,即对未来福祉的考虑并不总是能够向我们提供行动的理由,而且,在未能按照这样一个考虑来行动时,我们也无需在实践上是不合理的。这个直觉并不难以说明。尽管我们能够具有关于未来的观念,能够设想自己在未来的生活状况,但我们实际上永远都只是生活在当下。这个事实或许说明了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目前的感受,为什么会觉得目前的感受与我们所能预期的未来感受在心理上是不对称的。这个事实也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得到说明:既然我们只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无法精确地预知我们在未来会遭遇的事情,那么,在进行理性决策时,只要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就会在认知上对未来的欲望或期望“打折扣”。
不过,说“并非任何关于未来的考虑都能向我们提供行动的理由”,并不是说我们在根本上没有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祉。直观上说,在某些情形中,让当下的欲望胜过未来的理由是不合理的或无理性的。因此,我们需要设法说明:即使一切行动理由都是植根于目前的欲望或目的,因此未来的理由并不具有一种根本上独立的规范地位,但是,有时候这些理由必须被认为在我们目前的慎思中具有权威——它们作为未来的理由应当得到考虑。约纳坦·谢默试图按照所谓的“宪政保护”(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来阐明这一点。①Yonatan Shemmer,“Subjectivism about Future Reasons or Guise of Caring”,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online published on 24 July 2019,https://doi.org/10.1111/phpr.12614.在谢默看来,宪法在立法过程中具有优先地位:宪法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优先于常规法律,宪法的修订也需要得到立法机构多数人的批准。如果某项政策属于宪政保护的范围,那么在某些情形中试图推翻它一般来说就是不允许的。谢默认为,某些未来的理由也具有类似地位:相对于某一类欲望来说,它们具有优先性,甚至在被重新考虑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些理由在类似的意义上应当得到一种“宪政保护”。那么,宪政保护本身如何得到辩护呢?谢默试图利用约瑟夫·拉兹所说的“排他性理由”来回答这个问题。②参见 Joseph Raz,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especially pp.35—48。拉兹并不认为理由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冲突都可以通过比较其相对分量来加以解决,转而认为某些理由具有将所有其他相关理由排除出去的特殊地位,因此被称为“排他性”理由。
不难理解某些行动理由为什么会具有这种特殊地位。为了能够有效地行动,我们的自我在任何特定时刻都需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不管我们是出于什么理由来行动,行动的可理解性取决于我们具有一个在时间上相对稳定的自我,其核心要素就是我们已经作出的根深蒂固的价值承诺。当某个当下的欲望与构成自我的核心要素发生冲突时,只要我们是理性的,一般来说我们就不会让那个欲望得到满足。但是,假若我们接受了目前欲望理论,我们就必须说明,在某些情形中,我们现在对某个未来的理由(即应用于未来的自我的理由)的预期为什么能够对某些当下的欲望具有规范权威。谢默并未回答这个关键问题;或者说,他按照宪政模型提出的回答至少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追问某些行动方案为什么应当具有“宪政保护”的地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看来我们就只能诉诸人格同一性假设。既然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会逝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进入另一个当下时刻,因此,如果我相信或假设我的生活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那么,只要我确实关心自己目前的感受,我大概就不能理性地否认我也应当关心自己未来的感受,因为我未来的生活也是我作为一个特定个体将会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既然我们具有时间意识和自我意识,对我们来说,对未来自我的关切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行动总是指向未来;因此,若不假设我们要通过行动来取得的东西也是我们未来的自我将会具有的东西,我们的行动就会丧失要点或意义。由此来看,如果某个未来的理由与构成自我的核心要素具有某种重要联系,那么目前的自我就有理由认同那个理由,即使后者与我当前持有的某个欲望相冲突。①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未来的理由或考虑对我目前的欲望都有规范权威。如前所述,它们是否具有这种权威,不仅取决于它们与我的当前自我(更确切地说,其中的核心要素)的关系,也取决于我按照自己目前所能得到的信息对它们的评价。这也是我们拒斥索贝尔的传递性原则的一个主要理由。因此,总的来说,通过引入人格同一性假设,主观主义者就可以说明理性行动者为什么有理由关心自己未来的福 祉。
剩下来的唯一问题是:帕菲特可以坚持认为人格同一性假设是主观主义者不可得到的吗?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否认主观主义者能够具有和利用这个假设。首先,人格同一性是一个关于我们的心理条件的形而上学假设,在帕菲特所设想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争论中,这个假设是中立的。这个假设在这个争论中的地位,并不类似于帕菲特自己在其他地方对它的利用,即通过采纳一种洛克式的人格同一性概念来支持功利主义。①Derek Parfit,Reasons and Pers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其次,我们的论证并不需要采纳任何特定的人格同一性概念,只是立足于双方都能承认的一个基本假定:人类行动者能够在时间上保持同一性和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只要一个存在者不满足这个基本条件,他就说不上具有理性慎思、规划自己生活和满足未来欲望的能力。我们对未来自我的关注或许是一个关于人类心理的原始事实,但它确实预设了人格同一性的观念:假若我们并不相信自己在时间上是同一的,我们大概就不会对关心自己的未来产生兴趣,因为按照假设,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需要我们在当下去关心的未来自我。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已经具有时间观念和自我意识,能够反思自己在不同时刻的经验和行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可能联系,人格同一性就是一个关于人类道德心理的基本假设。更确切地说,人格同一性,就像自由一样,是一个关于理性慎思的实践预设。②科斯格尔对这一点提出了进一步的论述,参见Christine M. Korsgaard,“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Unity of Agency:A Kantian Response to Parfit”,in Korsgaard,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363—398。既然帕菲特并不否认主观主义者能够具有一个慎思理论,他就不应该抵制主观主义者所能采纳的一个论证策略,即通过引入人格同一性假设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能够具有未来的理由。
《论真正重要之事》是帕菲特的一部鸿篇巨著:在这部著作中,帕菲特不仅试图将三种主要的规范伦理理论“统一”起来,而且也试图为这项规划提供一个元伦理基础。然而,在这样做时,帕菲特不仅低估了人类伦理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他也未能充分正视其在元伦理学领域中的对手提出的论证,以及他们所能具有的思想资源。他对主观主义的反驳只不过是他的整个论证风格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