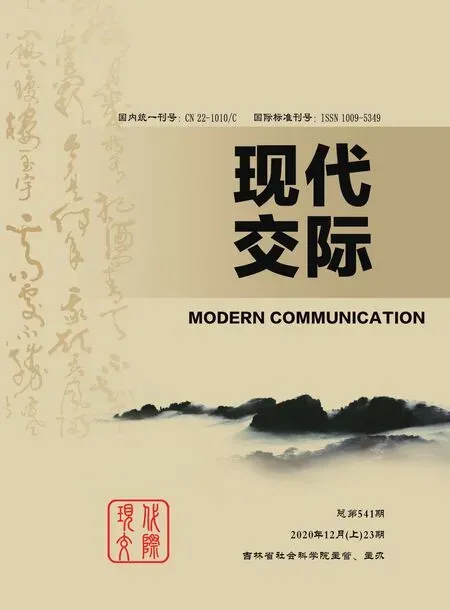《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消费文化解读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提到美国小说家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rancis Fitzgerald,1896—1940),许多读者会将他与“现代主义”“爵士时代”“经济大萧条”等标签联系起来。菲氏的代表作《人间天堂》《夜色温柔》《漂亮冤家》乃至《了不起的盖茨比》长期以来被奉为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国内外学界对菲茨杰拉德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风格,学者们认为菲茨杰拉德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了传记、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多重交叉特征;二是思想主题,学界在小说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文化分析,探析作品涉及的性别、种族、空间、生态等不同议题。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盲区,比如学界对菲氏小说中的消费主义关注尚显不够,二是对作品中的伦理危机及其诱因少有提及。事实上,菲茨杰拉德一直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消费社会的发展保持高度关注,从1919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许多作品均涉及消费文化影响下的伦理冲突。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社会群体之间,彼此的关系往往处于疏离甚至异化的反常状态。
回顾历史,一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谷期之后重又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财富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消费欲望,“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1]1。以物的占有为内核的消费心态导致人际关系被各种物质文化符号所遮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呈现的人际伦理关系为切入点,从消费文化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作者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反思以及作品涵摄的伦理关怀。
一、物欲与区隔:爱情关系的缺位
斯科特·唐纳森在分析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爱情故事时总结出了两类情节模式:一类故事描绘穷苦的年轻人成功地追求到了富有的姑娘,或至少看起来成功了;另一类令人印象更深的故事是年轻人在追求的过程中遭拒,或因此消沉[2]384。细读小说不难发现,主人公盖茨比与黛西的爱情故事无疑属于这两种故事模式的混合体。在双方一波三折的情感拉锯战中,消费主义价值观如影随形,左右着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人命运。
小说中,籍籍无名的盖茨比在路易斯维尔驻军期间结识了大家闺秀黛西,二人一见钟情。但很快盖茨比就意识到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那就是贫富差距、阶级出身与生活品位造成的社会区隔。小说独具匠心地以黛西的家这一极富象征意味的空间意象引出了黛西养尊处优的优越身份以及盖茨比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初来乍到的盖茨比眼中,黛西的家“让他惊奇不已——他从来没进过这样漂亮的住宅,但是其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屏气息声的紧张气氛却是因为她住在那里”[3]134。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过汽车、钢琴、香烟、靠椅、礼服、兰花、银色舞鞋等一系列缤纷物象来说明黛西的家是一个由各种消费品占据的空间。事实上,黛西令人羡慕的生活条件是美国社会繁荣富足的生动显影和文化转喻。主人公生活的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十年。美国经济发达的一个直接表征是汽车制造业前所未有的兴盛。得益于生产线的发明和科技手段的不断改进,汽车工业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基础产业,这一产业不仅带动了钢铁、橡胶、玻璃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直接加速了全美各地城市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中产阶层的男男女女不仅能承担起基本的生活开支,而且尚有余力为了炫耀而消费。小说中,黛西一家的生活习惯就是消费主义浪潮来袭的直接反映,无论是住宅富丽的装修风格,还是室内时髦的摆设布置,无一不彰显出黛西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起盖茨比的尊敬和羡慕。
一般而言,空间既是生产差异和区隔的基本手段,也是个体进行身份想象和实现身份认同的有效中介。反观小说,黛西的家居空间因为盖茨比的在场而生发了不同的伦理面相。具体而言,家居空间作为消费主义的场域,连接着分属不同社会阶层的男女主人公,并对他们的身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一方面,家居空间凝聚着黛西隐而不宣的消费欲望,黛西的身体在物的陪衬下呈现出了某种物化倾向。在消费文化的召唤下,黛西不但吸烟饮酒,而且浓妆艳抹地出入各种喧嚣的舞会。与刻板矜持的传统女性截然不同的是,作为新女性代表的黛西从传统禁欲观念的阴影中走出来,变身成为菲茨杰拉德所说的“飞女郎”(the Flappers)。黛西的卓尔不群的生活理念让盖茨深切地体会“财富怎样帮助人们拥有和保存青春与神秘,体会到一套套服装怎样使人保持青春靓丽,体会到财富怎样使黛西像白银一样熠熠发光,安然高踞于穷苦人激烈的生存斗争之上。”[3]135
另一方面,这一消费空间也是作为访客的盖茨比进行身份想象的隐秘触媒。尽管盖茨比对黛西倾注了满腔热忱,并且一心想给她创造同样舒适的生活环境以作为迎娶她的必备条件,但无法否认的是盖茨比背后缺乏优裕的家庭做后盾,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一文不名的青年”[3]134。盖茨比犹如一个僭越者,闯入了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他者空间,正如有评论指出,盖茨比的现实生活体现为“一种精神,一种对理想的允诺,是对模糊的、还未真正理解的生活之可能性的坚信”[4]217。盖茨比将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黛西的生命气息完美地融为一体,“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绽放”[3]134。需要指出的是,盖茨比对黛西的爱慕之情也杂糅了源自男性无意识深处的征服欲,这与物质文化研究中的“物恋”观念不谋而合,“物恋作为一个客体建构起了与个体的欲望、行为、健康,以及自我认同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或者具有某种力量,对后者加以控制”[5]65。作为他者,黛西的在场一方面让盖茨比意识到自己的劣势,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似乎只有通过物质财富的获得才能有效弥补。另一方面,黛西的家居空间成为盖茨比规划未来的样板和标杆,他急切地需要被豪华之物点缀的房间来安放他的身份和理想。盖茨比对黛西的痴迷以及由此生发的自我意识深深地浸染了消费主义的浓厚色彩。在一个逐利风气盛行的社会,盖茨比唯一的选择似乎只有投身时代浪潮,他对爱情的憧憬不可避免地滑向利己主义。
二、梦想与功利:爱情关系的幻灭
美国学者罗纳德·伯曼指出,菲茨杰拉德将大批量制造的、市场的、广告的和消费的事物引入小说文本内部,“它们是一种新的、扩张性经济的标志,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是转喻”[6]205。伯曼所说的这种扩张性的经济行为在盖茨比从事的致富活动中有着鲜明而直接的体现。
前文已述,年轻的盖茨比因贫穷与爱情擦肩而过,情场失意让他坚信唯有物质上的成功才能帮助他赢回昔日恋人的芳心。换言之,财富与幸福可以直接画等号,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笃信这个“美国梦”,并保持着实现这一梦想所需的浪漫想象和坚韧毅力。根据小说提供的细节读者可以断定,盖茨比在离开黛西数年间一直从事着贩卖私酒的非法活动,并侥幸从中牟利,实现了身份和命运的逆转。1920年美国政府颁布福尔斯泰德法令,俗称禁酒令,旨在杜绝和消除青年群体因大量酗酒而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法令从未真正实行过,“禁酒令为青年人闯入非法领域寻找刺激提供了额外的机会。”[7]54小说中,盖茨比对自己的发迹史讳莫如深,小说通过另外一个空间意象——盖茨比的雅致豪宅对他的奢华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
盖茨比在纽约长岛的西卵地区花重金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现代别墅,这座崭新的建筑宣示了新一代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追求。与之相对的是东卵区的富人聚居区,黛西和汤新婚丈夫姆·布坎南的豪华住宅就坐落于此。叙事空间上的二元对立通过人物性格的强烈反差进一步凸显,同时也为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制造了紧张气氛。在消费主义的逻辑下,财产成为自我的延伸,一切人际关系都蜕变成了交换关系。盖茨比定居西卵的根本意图是唤回他得而复失的恋人。小说通过叙事者尼克•卡拉维的视角向读者描绘了盖茨比对美好未来翘首以盼的浪漫形象:“在五十英尺之外,从我邻居的宅邸的阴影里隐现出一个人的身影。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在口袋里,仰望像撒落的胡椒粉般布满夜空的银色繁星。从他那悠闲的神态和双脚稳健地站在草坪上的姿态来看,他应该是盖茨比先生。他走出来看看我们头顶的天空哪一块是属于他的。”[3]21如何利用手中的资本吸引黛西的注意才是盖茨比当下的核心关切。为此,他在豪宅举行盛大的酒会,这是一个三教九流聚集的异质场域,每天晚上都有大量的食物、饮料、娱乐设施进驻豪宅,翌日清晨,庞大的垃圾则从他的院落运出,盖茨比的宴会成为陌生人恣意狂欢的乐园。参加宴会的宾客实际上是一群摆脱了传统道德的约束的后现代消费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宴会的主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我享受与感官愉悦,盖茨比的花园酒会演变为喧嚣时代的醉生梦死录。
那么,黛西能否接纳实现了华丽转身的盖茨比?事实上,黛西本质上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她既粗俗浅薄,又无知无畏。在尼克的牵线搭桥下,黛西来到盖茨比的新居参观叙旧,其间盖茨比装满西装、领带和各色衬衣的特大衣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突然之间,黛西把头埋进衬衫堆里号啕大哭起来,因为她“从来没见过这么——这么美的衬衫。”[3]83这一反讽场景将黛西的势力和庸俗刻画得入木三分,正如尼克所观察的那样,黛西说话的声调“高高低低带有无穷无尽的魅力,那里有金钱的叮当声。”[3]109在黛西刺耳的号啕声中,盖茨比对爱情的憧憬走向了它的对立面,成为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由此不难理解,在黛西开车撞死汤姆的情妇茉特尔之后,她竟能心安理得地让盖茨比做替罪羊,她甚至在盖茨比被汤姆谋害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情节设计一方面是为了凸显盖茨比的纯真、无辜与可悲,另一方面也讽刺了汤姆和黛西之辈的冷酷无情,“他们是满不在乎的人——他们砸了东西,毁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钱堆中去,退到了麻木不仁、漫不经心,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去,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3]162。盖茨比悲剧命运的症结在于他迷失在了消费主义的神话中,并以一种乐此不疲的激情投入其中,殊不知那个梦已经远他而去。盖茨比的性格缺陷已经溢出个人层面,隐喻了美国梦的致命不足。美国梦固然美丽动人,但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盖茨比缺乏对残酷现实的理智判断,导致他在精神上陷入迷惘,最终导致肉体的毁灭。
三、结语
著名评论家利维斯指出,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肩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8]3菲茨杰拉德以其细致入微的笔触记录了消费时代的崛起以及这个时代孕育的一群特殊人物,他对人物言谈举止、作风气度以及生活环境的刻画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更重要的是,他对消费主义造成的伦理危机给予了警醒和反思。在物质文化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依然要面对物欲与感情的矛盾,梦想与现实的冲突,《了不起的盖茨比》无疑将为读者思考上述问题提供有益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