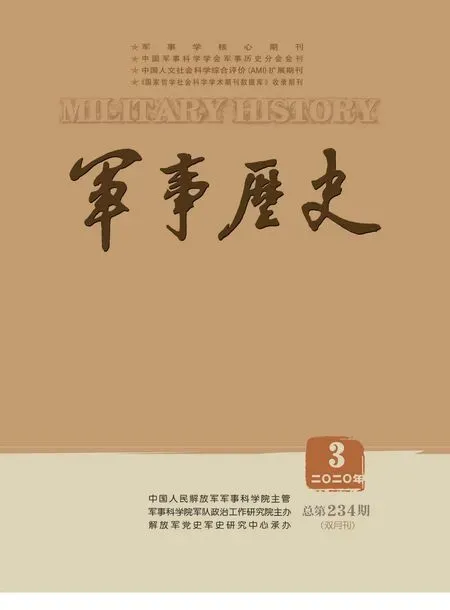宋代兵学刍议*
宋代是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形成了中国兵学史上的第二次高潮。①参见刘庆:《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次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 期。诸如“右文”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辽、夏、金、蒙元等持续的军事角力,宋代理学的兴起,等等,都与宋代兵学密切相关并交互作用。在这众多影响因素之中,最具根本性的是“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②关于宋代这一基本国策,学界一般称为“重文轻武”。陈峰先生认为,“重文轻武”的提法容易造成宋代不重视武备的误解,应该称作“崇文抑武”。笔者认为“崇文抑武”的提法更为准确,故在本文中予以采用。参见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6 章,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宋代立国于唐末五代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之后,如何避免五代“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的乱象,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权,是宋初君臣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宋代“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④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5 页。,围绕防范武人专政这一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收夺统兵大将兵权,使节度使成为虚衔;从藩镇中选拔精锐扩充禁军,使禁军成为国家正规军;建立“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⑤《宋史》卷162,《职官二》。分权制衡的军事制度;实行更戍法,防止武将与士兵、地方相交结,等等。至太宗朝,“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具有纲领性的治国方略。⑥参见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253 页。文臣地位日益尊崇,以儒家治道与封建君主共治天下,武臣则被认为是导致祸乱的潜在威胁,地位逐渐降低。至北宋中叶,“以文制武”体制最终确立,成为支配宋代政治的重要原则。
宋代兵学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及其衍生的一系列制度、观念、文化之下发展变化,呈现出多方面的成就和特征,成为中国兵学史上承前启后而又独具特色的篇章。
一、推崇与贬抑并炽——传统兵学地位的迷思
了解宋代思想史的人,大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宋人对于兵学的推崇和贬抑都十分强烈。推崇者将《孙子》等兵书视为鸿宝,如南宋郑厚在《艺圃折衷》中说:“《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①朱熹:《晦庵集》卷73,《读虞隐之尊孟辨》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贬抑者则对兵家大加挞伐,认为“诈力之尚,仁义之略,速亡贻祸,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②薛季宣:《浪语集》卷28,《拟策一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两种声音长期共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必然地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崇儒抑兵”。宋儒站在意识形态主导者的立场,对传统兵学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
首先,在治道层面上,以儒学为本,以兵学为末。朱熹解释《论语》“卫灵公问阵”一节时说:“夫子去卫之意,盖以兵而言,阵固兵之末,以治道而言,则兵又治道之末也。”③《四书或问》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一观点与王安石高度一致。宋神宗一度对阵法有浓厚兴趣,经常与臣下探讨战阵之事。王安石批评道:“先王虽曰‘张皇六师’,克诘戎兵,其坐而论道,则未尝及战阵之事。盖以为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不足道也。孔子亦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以为苟知本矣,末不足治也。”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庚辰。由此可见宋儒对于兵儒次第这一基本立场的坚守。
宋儒批评兵学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担心兵家“诈谋”影响风俗教化。刘敞反对建武学。他认为,儒家教习“诗”“书”“礼”“乐”,崇尚“文”“行”“忠”“信”,“故贱诈谋,爵人以德,褒人以义,轨度其信”。如果提倡武学,“教之以术而动之以利”,就会使教化渐弱、风俗渐变,进而危及统治秩序。⑤《公是集》卷43,《与吴九论武学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适也认为,武学研习兵书是“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而“授天下以不仁之心,患之大者也”⑥《叶适集》第3 册,《水心别集》卷4,《兵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其次,在用兵之道层面上,反对兵家“诈”“利”思想,主张用兵以正、仁义制敌。宋儒常将儒学与兵学的异质诠释为仁政与诈术、王道与霸道的对立,强调仁政、王道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如程颐说:“若以王道兴兵,则百姓皆修其戈矛,与之同仇矣。”⑦《程氏经说》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敞认为,“仁”“义”既是为政纲领,也是武备根本:“以道德为藩,以礼让为国,以忠信为用,以仁义为力,故守必有威,动则能克。”因此,“战在胜不在多,术在德不在他,是以弃天时与地利,贵王道与人和”⑧《公是集》卷1,《我战则克赋》。。在他们看来,“夫以孙吴之智窥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规圣人之道,固绵远矣”⑨《公是集》卷46,《杂著·师三年解》。。有的儒家学者甚至认为,儒学经传才是用兵之本,价值远在兵书之上。如,吕祖谦认为《孟子》论兵“为兵法之祖”⑩《丽泽论说集录》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薛季宣对《荀子》兵论大加褒奖,⑪参见《浪语集》卷28,《拟策一道》。李舜臣推崇《易》“《师》卦六爻之略”⑫冯椅:《厚斋易学》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等。在这些论述中,宋儒将兵家之重天时、地利与儒家重王道、人和,兵家之尚诈力与儒家之崇仁义,兵家的权谋之术与儒家的王者之师对立起来,将“崇儒”与“抑兵”同时推向了新的高度。
再次,在用兵之术层面上,反对以诈术取胜。例如,秦晋“殽之战”时,晋结姜戎为犄角,控遏殽陵险隘,出其不意,大胜秦军,在战争史上堪称典范。但是,南宋学者黄仲炎却认为,晋虽取胜,却有三罪,“背惠,一也;君丧在殡而主乎战,二也;兵以诈胜,三也”。他说:“兵贵奇胜,圣人恶之。何哉?《春秋》正其谊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与也。夫兵以奇胜者,孙武之术,岂圣人之教哉?”①《春秋通说》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此,儒家的讲求仁义与兵家的追求功利、儒家的以正用兵与兵家的以奇取胜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宋儒论及兵家诈术,虽然未必尽如黄仲炎这般偏执,但大多都持批判态度。如程颐、刘敞都反对用间。②参见《二程遗书》卷18;《公是集》卷47,《伊尹问》。苏洵批评孙子“五间”说:“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智于此,不足恃也。”③苏洵:《权书·用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0 页。
荀子“仁人之兵不可诈”之说,被宋儒进一步引申为“诚可制诈”。吕祖谦反驳“万物皆贱诈,唯兵独贵诈”的观点,说:“盖君子之于兵,无所不用其诚。……用是诚以抚御,则众皆不疑,非反间之所能惑也;用是诚以备御,则众皆不怠,非诡谋之所能误也。彼向之所以取胜者,因其轻而入焉,因其贪而入焉,因其扰而入焉,因其疑、因其怠而入焉。一诚既立,五患皆除,兕无所投其角,兵无所投其刃,曼伯、子突之徒无所投其诈矣。……彼之诈至于万而不足,我之诚守其一而有余,彼常劳而我常佚,彼常动而我常静,以佚制劳,以静制动,岂非天下常胜之道乎?然则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归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无出于君子矣。”④《左氏博议》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言之,不但可以“以诚代诈”,更可以“以诚制诈”,“诚”是天下常胜之道,以诚道自立的儒家君子才是真正的善用兵者。
“崇儒”与“抑兵”是相互激扬的两个方面,兵学越发展,就会招致越激烈的批评。终两宋之世,一直处于与辽、夏、金、元等的军事斗争之中,强兵胜战的迫切需求拉动了宋代兵学的巨大发展。从官方层面看,宋廷兴办武学,开设武举,修纂《武经总要》,校订“武经七书”;从私人著述看,兵书层出不穷,论兵之策汗牛充栋,兵学出现了全方面的繁荣。兵学的发展自然引发了推崇,同时也招致儒学更强烈的压制和贬抑。
应该说,儒家强调“仁政”“义战”的重要性,对于规范战争行为,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兵学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当“崇儒抑兵”贯穿到具体作战指导中,则有悖于军事斗争的规律,滑向了坐而论道、偏颇迂腐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崇儒抑兵”思潮导致了对兵学不恰当的贬抑,奠定了整个宋代兵学发展的基调,对兵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即便对兵学的推崇,也是建立在“儒本兵末”前提下的,而且主要局限在兵学领域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对兵学的评价看似矛盾,其实又不矛盾,因为它们发生的维度不同,贬抑主要是在治道和国家战略层面,推崇则在兵学和军事方面。
二、文人论兵——兵学研究主体的变化
宋代“以文儒立国”,随着“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推展,文人士大夫逐渐掌握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权力。宋英宗时,蔡襄在上书中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⑤《宋朝诸臣奏议》卷148,《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文人官僚为皇帝所倚重,有高度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范仲淹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文人士大夫政治上自觉、自信的宣言。在他们看来,“纬武”和“经文”一样,都是文人士大夫的分内之事。诚如南宋理学名儒张栻所说:“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⑥《南轩集》卷34,《跋孙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仁宗时的宋夏战争为“文人论兵”的勃兴提供了现实契机。据《郡斋读书志》记载,“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2,《万有文库》本。。此后,“文人论兵”风潮一直发展,直至宋亡。
刘庆先生《“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的发展》②刘庆:《“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5 期。一文将论兵文人分为三类:一是研究古代兵书典籍的专门家,二是热心于兵学研究的著名文人,三是直接接触国防问题的朝中枢臣或边防大吏。第一类以兵书和兵学为研究对象,可称为“兵学研究者”。第二类主要是对战争及兵学做评论,可称为“兵学评论者”。第三类是军政要员,所论以边防对策为主,可称为“兵学实践者”。不过,三类之中身份重合的也很多,如梅尧臣,既是《孙子》注家,又是著名文人。又如陈规,既是重要边臣,又有兵书问世,兼具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身份。
“文人论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代兵学的基本面貌。
其一,促成了兵学文献的空前繁荣。《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53 家,790 卷,图43 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133 部,512 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多达347 部,1956 卷,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这固然与宋代雕版印刷大发展的时代条件有关,但大量文人踊跃论兵无疑是更主要的因素。在“文人论兵”潮流之下,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兵书种类,如第一部大型官修兵书《武经总要》,第一部军事制度专史《历代兵制》,第一部军事人物和史事评论集《何博士备论》,第一部分门别类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等等。优秀的论兵篇章更是不胜枚举,如苏洵《权书》《衡论》,苏轼《孙武论》,李廌《兵法奇正论》《将材论》《将心论》,秦观《进策》中的《将帅》《奇兵》《兵法》,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等。
其二,儒学对兵学的批判与改造更加深刻。文人是儒家思想的奉行者,“文人论兵”必然以儒学为本位阐释或议论军事问题,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更加明确地阐释了兵儒间的异质,以及兵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定位;二是在论兵过程中援儒释兵,以儒家思想浸润、改造兵家思想,实现了儒学主导下更深入的融合。
其三,对兵学文献的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文人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论兵之作一般都条理清晰、文辞畅达。苏洵的《权书》、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大文豪的兵论自不必论,就如梅尧臣、王晳等的《孙子》注,许洞的《虎钤经》、綦崇礼的《兵筹类要》,等等,也都具有这样的鲜明特点。文人论兵大大改变了传统兵书或言语支离或隐晦难明的缺点,提升了兵学文献的外在品质,增强了可读性。
三、兵学儒学化——兵儒合流的时代演进
兵家诞生于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春秋末年,在列国争雄的战国时期获得巨大发展,不但与儒家、法家等并峙共荣,甚至成为一时显学。战国晚期,兵家借鉴并吸收其他诸子思想,出现了兵儒合流的现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兵儒合流成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主流。③参见黄朴民:《兵儒合流与学术兼容》,《中国军事科学》1999年第3 期。兵儒合流是兵学与儒学融合的过程,也是儒学对兵学强力渗透和规制下的兵学重构过程。及至宋代,在“崇儒抑兵”思潮之下,儒学以更强势的姿态影响兵学,加之理学的兴起为兵学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兵学儒学化成为宋代兵学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内容。
宋代兵学儒学化的主要方式是“以儒解兵”。文人儒士通过对传统兵学文本和概念的重新解读,或延展、或缩小、或曲解、或引申,或将儒学相似思想嫁接到兵学中,实现了兵学思想的儒学化。由于宋代兵学以孙子兵学为中心,文本研究也以《孙子》注为主,因此,兵学儒学化主要体现在对孙子思想的解读上,在战争观、战略思想、作战指导思想、治军思想等方面最为突出。
(一)战争观
传统兵家并未对战争观作系统的论述,但总体而言,“功利主义”是兵家战争观的核心。兵家“尚利”与儒家“尚义”构成了鲜明的对立,成为先秦以降兵儒冲突的重要论题。宋儒一方面高举“王道”旗帜,将“仁义”置于“诈利”之上,确立了儒家战争观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儒家思想诠释兵学思想,使传统兵家的战争观全面儒学化。
例如,关于慎战思想。儒家、道家都主张慎战,但其出发点是道德主义,重点在于战争“杀人盈野”“杀人盈城”①《孟子·离娄上》。、“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②《老子·第三十章》。等灾难性后果。兵家也主张慎战,出发点却是功利主义。《孙子》首句即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③《孙子·计篇》。《火攻篇》中又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很显然,“合于利”是孙子慎战思想的根基。
在宋儒的诠释中,孙子慎战思想的基础由“利”置换成了“义”。梅尧臣注《孙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句说:“兵以义动,无以怒兴;战以利胜,无以愠败。”在这里,儒家“义”的概念被植入,成为发动战争的先决条件。在解释“非利不动”一句时,他说:“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利于民”也是“义”的表现。在宋儒的这类诠释中,孙子慎战思想的基础由“重利”的功利主义变成了“重义”的道德主义。
又如,关于用兵之“道”的问题。《孙子》中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④《孙子·计篇》。,“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⑤《孙子·形篇》。,“齐勇若一,政之道也”⑥《孙子·九地篇》。,等等。孙子所谓“道”指统一民众思想、提升战斗力的方法,与政治相关,但立足点仍在于军政。
宋儒对《孙子》“道”的解释,基本上等同于儒家之“道”。对于“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之“道”,梅尧臣解为“得人心”,王皙解为“人和”,何氏解为“抚我则后,虐我则雠”,张预解为“恩信”。施子美认为,曹操将“道”解为“道之以教令”,不够准确,杜佑解为“德化”才是正确的。
朱熹的说法更为明确,他说:“且如《孙》《吴》专说用兵,如他说,也有个本原。如说‘一曰道。道者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后造大事,若使不合于道理,不和于人神,虽有必胜之法,无所用之。”⑦黎靖德:《朱子语类》卷8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也就是说,“道”是孙子思想的本原,而这个本原的意涵是君主“合于道理”“和于人神”,与儒家的“道”并无二致。
(二)战略思想
《孙子》是传统兵学中论述战略最详备而深刻的著作,其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宋儒对孙子“全胜”战略的解读同样是“以儒解兵”。
首先,片面强调“不战”,认为“不战”是基于“不忍人”的爱人之心。梅尧臣、张预的《孙子》注,李廌《慎兵论》等都持这种观点。《孙子》主张“全胜”,可能确有不务多杀之意,但本质上是以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胜利,利害权衡是其出发点。宋儒强调“不战”的仁爱动因,忽略对“利害”的考量,使“全胜”与“慎战”一样,被涂上了浓重的道德主义色彩,在实践中则很容易滑向“避战”“畏战”的防御主义。宋代文臣在边防建策中或认为加强战备可使敌人“不战而慑”①《河南集》卷2,《息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或以屈己求和为“不战而胜”②《东坡全集》卷86,《上清储祥宫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都是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曲解的结果。
其次,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同于“仁政制敌”。如李觏认为,“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③《旴江集》卷17,《强兵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一论点显然脱胎于《孟子》行仁政而“一天下”的思想。这样的解读使“全胜”成了儒家“政胜”的注脚,与孙子的本意相背离。
(三)作战指导思想
作战指导思想是兵学理论的核心,诸如“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击虚”“以正合,以奇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等等,一般儒者对这些谲诈之术不以为然,兵学专家对这些内容的儒学化解读也较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理学的发展,宋儒论兵,多援引“心”“气”“性”“静”等理学概念,对“治气”“治心”诸说多有新解。
《孙子》说:“三军可夺气”,又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④《孙子·军争篇》。綦崇礼在《兵筹类要》中立《志气篇》,论曰:“将以志为主,以气为辅,志藏于神而为气之帅,气藏于肺而为体之充,苟气不足以发志,志不足以运气,则何以勇冠三军而威振临敌?故曰:功崇惟志。又曰:志至焉,气次焉。知此则知所谓大勇矣。”这里所讲的“志”“气”关系完全本于《孟子》的“志气论”。《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⑤《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志气论正是宋代理学发扬光大的要点之一。
兵家也讲“治心”。《孙子》说:“将军可夺心”,又说:“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⑥《孙子·军争篇》。綦崇礼《兵筹类要》专立《镇静篇》,文中说:“苟镇静则事至不惑,物来能名,以安待躁,以忍待忿,以严待懈,虽恢诡万变陈乎前而不足以入其舍,岂浮言所能动,诈力所能摇哉?故士不敢慢其令,敌不能窥其际,近取诸身,则心安体舒,内外之符也。”綦崇礼所论“静”和“心”显然是理学式的。
苏洵也论“治心”,重点在于将道。他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⑦苏洵:《权书·心术》,第4 页。而他所谓“养心之法”则是“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办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⑧苏洵:《权书·孙武》,第47 页。,这显然是将儒家的修持之术引入了将帅修养中。
(四)治军思想
治军思想是儒学与兵学较少冲突的一个领域,宋儒在这方面的儒学化解读,重点在将德和御将问题上。这两个问题既关乎兵学理论,也是宋代军事领域现实矛盾的折射。
在将德问题上,宋儒关注的重点在于“忠”。出于对唐末五代“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⑨范祖禹:《唐鉴》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反动,宋儒十分强调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反映在兵学上,就是对将领“忠”节的重视。李廌《将材论》中说:“事君皆以忠,而将之忠为大。盖方其用师也,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将军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图而忘其身,惟国是忧而忘其家,故贵乎忠。忠则无二心故也”,并称“惟信惟忠,乃为建立勋名之权舆,杜塞危疑之关键也”①《济南集》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兵筹类要》中的《忘家篇》《诚实感篇》也都反复申论这一问题。此外,《孙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②《孙子·地形篇》。之语也被宋代注家普遍解释为“忠”。
在御将问题上,兵家主张“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③《孙子·谋攻篇》。“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④《六韬·立将》。。这些思想在宋代显得不合时宜,宋代君主常常“将从中御”,太宗朝尤为严重。针对这一状况,宋儒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对“将从中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李觏说:“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烬久矣。曰:有监军焉,是作舍道边也,谋无适从,而终不可成矣。”⑤《李觏集》卷17,《强兵策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 页。也就是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君主遥制或设置监军违背战争规律,必然导致失败。另一种则基于防范武人、加强军事集权的立场,将“将能而君不御”引申为“将能而君不御”“将不能而君御”。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说:“既曰‘将能而君不御之者胜’,则其意固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也。夫将帅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随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阃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将能而君御之,则为縻军;将不能而君委之,则为覆军。”事实上,所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的情况根本就存在,这种说法完全是为“将从中御”张目。
四、声容盛而武备衰——兵学与军事实践的畸形互动
后世史家称宋代“声容盛而武备衰”⑥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3,《进宋史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说它文教发达但军事积弱。在军事领域,宋代呈现出文事与武备的巨大反差。一方面,各类论兵著作层出不穷,形成了兵学史上继战国之后的又一高潮。另一方面,兵学的发展并未对军事实践产生有效的牵引,军事上颓弊不振、败绩连连。这一局面可以概括为兵学的“声容盛而武备衰”。
(一)兵学与战略
传统兵家讲战略,多讲战略原则,并不会对具体的国家战略有确切的意见。国家战略的制定往往会参考兵家的战略思想,但更多是针对自身安全形势做出战略决策,宋代大量论兵文章讨论的就是这类问题。宋代崇儒抑兵,在军政大计的制定方面,兵家功利主义思想受到排斥,儒家战争观、边防观占居主导地位。
宋代国家战略主要体现为边防战略,以消极防御为基本特征。宋太宗两次北伐之战失败后,战略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由“志在恢复”转为“守内虚外”,对辽边防实行防御战略:利用河渠塘泊构筑防线,以“和戎”为主导思想,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应对之策,等等。这一战略转变有现实政治因素的考量,也有儒家边防思想的影响。两次北伐之战前后,张齐贤、赵普、李昉、张洎、田锡、王禹偁等文臣纷纷上书,劝宋太宗停止北伐。他们的意见大体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内政重于边事。内政为本,边事为末;人民为本,夷狄为末,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夷狄角逐得不偿失。第二,只要内修政理,自会四夷慕化。第三,对待边防威胁,以守御为主,“来则御之,去则勿逐”。⑦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五月丙子、雍熙三年六月戊戌;卷30,端拱二年正月癸巳。《宋朝诸臣奏议》卷129,李昉《上太宗谏北征》,张齐贤《上太宗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等。文臣们的意见固然能在现实政治中找到合理依据,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言论反映了儒家民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民族观以及“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⑧《论语·季氏》。的理想主义态度。这些意见为宋太宗所采纳,成为其“守内虚外”思想的理论基础,也说明儒家思想在边防战略制定上起了主导作用。
此后,宋代边防战略基本延续了相同的思路。在历次重大边防事件中,诸如太宗、真宗时灵州的弃守问题,仁宗时对夏攻守问题,神宗时熙宁开边问题,哲宗时割弃横山诸寨问题,南宋关于和战“国是”的争论,等等,无不存在战略上的激烈论争。北宋时期,除了王安石积极支持王韶经略西夏获得成功以外,大部分时候都是消极防御战略占上风。宋仁宗时,范仲淹曾提出“渐复横山”的积极防御战略,目的是“以河为限,寇不深入”①《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但也只是一个战略构想而已,最终并未实现。其他如刘平、薛向、何亮等基于敌我态势、地理形势等提出的积极防御或进攻战略则大多被束之高阁,甚至在史料中寻不到踪迹。南宋虽然发起过几次主动进攻,总体上还是消极防御甚至委屈求和为主导,即便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战略方案,也无法进入战略决策。辛弃疾《美芹十论》的际遇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宋代消极防御战略是“抑兵”的必然结果。正因为缺乏从功利角度对军事问题的长远观照,宋代君臣在面临边防危机之时,往往一味强调内政与战争的矛盾,强调“以德怀远”的立场,强调“来则御之,去则勿逐”的方针,难以从根本上逃脱“消极防御”的窠臼。
(二)兵学与将帅
孙子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②《孙子·作战篇》。将领是影响战争胜负和国运兴衰的重要力量。宋代的文人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问题,他们一方面“抑武”,严密防范武将,另一方面又希望重塑将领群体,培养、选任既忠于君主又文武兼备的将才。
北宋中期,“以文制武”体制确立。除了南宋初张俊、韩世忠、岳飞、吴玠等武将为大帅之外,两宋时期,文官为帅是常态。文人帅臣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对《孙子》《吴子》等韬略型兵书有所涉猎,建言献策、处理军政事务,也能遵循兵学的一般原则,但是,这些粗浅的知识并不能使他们履行好军事统帅的职责。尤其是具体到作战指导层面,无论范仲淹、韩琦,还是张俊、虞允文,都存在很大的局限。真正在军事上有所建树的文人帅臣并不多,北宋以王韶为首,南宋当以陈规为最。
从宋初开始,逐渐出现了任用“儒将”的呼声。任用儒将的主要方式是“以文换武”,即从文官中选拔有武干的人转为武职。这些人兼具儒者和武将的优点,既能在思想上与朝廷和文官集团保持一致,又有武将的谋略和勇敢,无疑是最理想的将领类型。但是,这些人在换为武秩之后,往往受到种种制约,难以真正建功立业。以张亢为例,天禧三年(1019)进士,“少磊落有大志,博学能文之外,喜读诸家兵法,常慕古大丈夫,立奇功伟节以震暴于当世,不为拘儒龊龊之行”③《安阳集》卷47,《故客省使眉州防御使赠遂州观察使张公墓志铭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任通判镇戎军之时,他预言元昊将反,上疏言西北二边攻守大计,前后上数十章,被换为武职如京使,开始了武将生涯。张亢一直身处西北前线,取得了卓越的战绩,《宋史》评价他说:“张亢起儒生,晓韬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哉!”④《宋史》卷324,《张亢传》。但是,他的仕途却并不顺利,“徘徊于横班者几二十年。及其病也,则又弹射迁逐,曾不得有少安之地!”⑤《安阳集》卷47,《故客省使眉州防御使赠遂州观察使张公墓志铭并序》。张亢们的际遇使真正有武干的文官不愿意换为武职,因此,宋代文官出身的将领很少,并未形成气候。
宋仁宗时开始,为了培养韬略型将领,以富弼为首的文人官僚积极推进武学、武举制度。武学、武举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宋代兵学的发展,但是,从培养军事人才的角度看,武学和武举制度并不成功。先以武学论,武学的规模不大,生员以百人为额,最大规模在200 人左右。武学生入仕的主要途径是武举,这就导致入仕门径狭窄,造成很多沉滞多年的老武生。
武举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名额仅30 人左右。更重要的是,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武举并不能选拔出优秀人才,也不能人尽其用。首先,武举考试“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重文章轻武艺,往往成为落第文人的假途。终两宋之世,这种状况一直是武举的痼疾。其次,武举授官过低,且多与军事不相关。据熙宁六年(1073)规定,武举人授官为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三班差使等最低等的武选官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熙宁六年九月辛亥。。至于其实际职任,则多为监当、管库,或镇寨都监、监押、巡检等基层武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带兵打仗。再者,武举人往往不能很好地融入军队。孝宗时,为了改变武举人“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②《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二九。的弊病,于淳熙七年(1180)推行《武举贡举补官差注格法》,大幅提升武举人授官等第,鼓励武举人从军。但是,从军的武举人“往往自高,不亲戎旅”③《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六。,对于军队中严格的阶级之法,也“不堪笞捶之辱”④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因此,他们大多难以在军中久留,想方设法改为文官。
还有一种类型的将领是行伍出身或者军功世家子弟,他们或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战术战法,或受家族影响,以兵学为家学。这类将领中的最突出的是狄青和岳飞。狄青是范仲淹帅边时期培养的将领的典型,史书上说他受教于范仲淹及其文人幕僚,主要通过学习《左传》提升军事理论素养⑤《宋史》卷432,《儒林二·何涉传》。。岳飞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但他的成功也得益于身边的文人谋士,如薛弼、黄纵、李若虚等,这些人熟读兵书,精通军事,为岳飞出谋划策,对岳家军的成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随着岳飞被迫害致死,这样一种模式也很快宣告结束。
总之,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及“崇文抑武”的影响,无论文人帅臣、以文换武的儒将,还是武学、武举出身的将领,或者行伍、世家子弟,他们在兵学理论的学习和实践方面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即便是个别出类拔萃者,也受制于种种因素,难以展其所长,这是宋代兵学很大的缺憾。
(三)兵学与军事技术的创新
宋代是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火器应用日益普遍,提高了作战效率,增强了杀伤力,也使攻防作战的样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军事技术的进步,理应推动兵学理论的发展,反之,兵学理论也应指导军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宋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反映在兵书著作上,最突出的成就是陈规《守城录》。
陈规(1072—1141)是宋代文人将领中的佼佼者,主要战绩在守城方面。靖康中,金军南下,他以德安府安陆县令摄守事,率军民固守德安。建炎元年(1127),知德安府,多次击败盗贼进攻。绍兴九年(1139),知顺昌府。十年,与将领刘琦协力守城,挫败完颜宗弼数十万金军,取得顺昌大捷。史书说他,“自绍兴以来,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惟规而已”⑥《宋史》卷377,《陈规传》。。
《守城录》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守城机要》讲守城设施和方法,《〈靖康朝野佥言〉后序》是陈规对汴京陷落的评论,汤璹《德安守御录》是对陈规“守城遗事”的追记,三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但记述了陈规守城的器械、方法、组织编制和战略战术,而且反映出陈规对兵学理论的深刻认识。
陈规非常注重火器的运用。他说:“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砲。”砲是攻城利器,也是守城利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虽能者,亦难施设”。为了充分发挥砲的作用,陈规制定了新的用砲之法,如,改城头置砲为暗设于城脚;在城头增设观察哨以指挥砲击;大小砲并用,等等。针对火器条件下攻守城作战的新特点,陈规主张革新城防旧制。如,拆除城门外的瓮城,改进门楼、吊桥等设施;收缩易攻不易守的四方城角;增筑便于掩护和还击的高墙;改传统的一城一壕为三城两壕,等等。《守城机要》中备列攻城备御之法四十余条,就是陈规对火器条件下城防战法的总结。
《守城录》的作战理论完全本于《孙子》。陈规在《〈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中说:“规尝闻《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为,‘兵者诡也,用无中形,诡诈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然而有传之于众而达之于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者,不可不先传也。”他又说:“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人孰能穷之?今止据金人攻城施设略举捍御之策,至于尽精微致敌杀敌之方,虽不惮于文繁,而有所谓真不可示人者未之传也,又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也就是说,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要遵循《孙子》的战争指导原则,诸如诡道、示形动敌、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等等。至于具体的战略战术,则需要将领根据战场实际,精思应变之术。
陈规致胜的关键在于善用兵法、积极防御。他说:“治乱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惟在用兵之人何如耳!”也就是说,势在人为,强弱胜负的变化取决于将帅如何措置。守城作战也一样,真正的善守者不是一味死守,而是要做到“守中有攻”,善用各种方法创造可胜之势。顺昌保卫战就充分体现出积极防御的特点:先是在敌人引退时出兵邀击;继而夜袭敌营,疲扰敌人;金重兵攻城,坚壁不出,待敌气力疲乏,再派兵出击。利用这些战术,宋军以不足两万的兵力,击退了数十万金兵。
《守城录》是一部出色的兵书,但是,对于宋代兵学发展的总体来说,军事技术与兵学理论的良性互动远远不够。文人论兵者不关心也不懂军事技术,难以将军事技术及作战样式的发展理论化;武将大多不通文墨,缺乏理论素养,也难以将军事实践中的战法上升至理论层面。加之武将被防闲,即便有一些兵学论著,也很少见诸记载并流传于世。
结语
宋代兵学是中国兵学史的一个发展高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成就,对后世兵学和军事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儒学成为传统兵学文化的绝对主导。宋儒作为论兵主体,在发展了兵学的同时,也使先秦意义上的兵家归于消亡。在“武经七书”取得官学地位之后,反而再无继承兵学功利主义的理论著作问世。由此,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儒学通过批判、阐释和吸纳兵学思想,规定了战争观、战略思想等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兵学则提供具体战争指导层面的方法和知识。换言之,儒学为主,兵学为从;儒学为体,兵学为用。这种二元结构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儒学统摄兵学,形成了与政治文化相一致的兵学理论,规范着中华民族的战略思维和军事实践;另一方面,兵学地位的降低以及独立性的消解,严重影响到兵学的创新和发展。
其次,加剧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泛和平主义倾向。宋代兵学的儒学化是儒家道德主义对传统兵家功利主义的胜利。儒家从民本主义出发,反对穷兵黩武,强调义战,谋求以非战手段解决争端,铸就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和平主义性格。和平主义固然可贵,但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长期压制,和平主义不可避免地泛化:在战略决策上,道义原则优于利益考量,“慎战”往往成为“不战”“畏战”的托辞。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一味排斥暴力,导致尚武精神沦落,军事发展缺乏持久动力。
再次,强化了国防战略的防御性特征。从兵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国防战略防御性特征的形成与兵学儒学化的过程是同步的。随着兵学被逐出国家战略决策领域,国防战略上的功利色彩逐渐淡化,强调战争对内政的破坏力,宣扬“以德怀远”,主张“来则御之,去则勿逐”。在实力衰落的王朝末世,防御战略更是易于沦为消极防御。这一点在宋明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戚保华
——刘家文
——刘建斌
——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