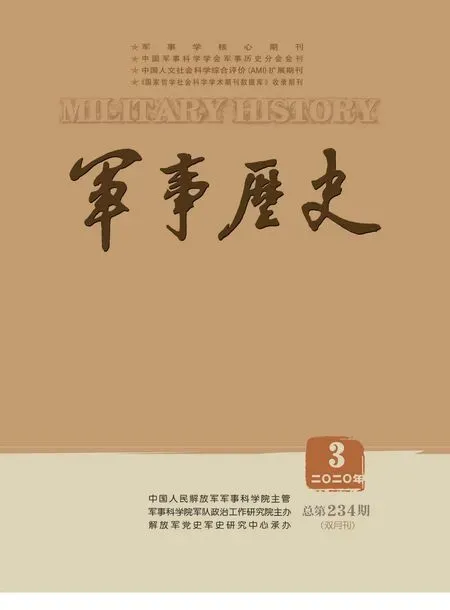秦汉兵学文化的主要成就及其显著特征*
提要:秦汉时期的兵学文化是在秦汉“大一统”中央专制集权帝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背景下形成、发展的,与先秦兵学侧重于兵学理论的学理创新有所不同的是,它更多体现为兵学思想的系统梳理与文化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兵学文化主要成就,反映为有关存世兵书的整理与分类、兵学流派及其特色的分析与总结、兵学实用性问题的注重与强调、兵学理论的学习与普及、兵学主题的重心转移等等。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到秦汉时期又呈现出新的风貌,它对秦汉时期军事活动的理论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对后世兵学的嬗递亦影响深远。
主题词:秦汉时期 兵学理论 兵书整理 兵学流派 文化特征
秦汉时期包括秦(前221—前206),西汉(前206—25,含王莽新朝)和东汉(25—220)三个历史阶段,共计441年。它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全面确立并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兵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秦汉军事及其兵学理论概貌
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全建立继续得到发展,铁制农具广泛使用,冶金技术和手工业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武器装备的改进。当时的主要兵器,如刀、剑、矛、戟等,已普遍由钢铁制作而成。一些不太适应当时作战需要的兵器,如戈、殳、钺等逐渐被淘汰,弓、弩等兵器的性能继续获得改良,杀伤力更为增强。
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与巩固相一致,秦汉王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将它置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协助皇帝负责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官吏,秦和西汉时期为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为太尉。他们均秉承皇帝的意志管理军队,只有带兵的权力而没有调兵的权力。发兵权、统兵权、指挥权开始一分为三,并初步实行监军制度。①参见霍印章:《中国军事通史》第4 卷《秦代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0 页。
秦汉时期的军队一般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防兵三个系统。京师兵即中央军,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是当时军队的主体。地方兵分置于郡县,由郡尉、县尉协助郡守、县令统率,平时维护地方治安,战时由中央统一调遣。西汉初期,诸侯王国拥有军队,后被纳入郡县兵体系之中;东汉时期取消了地方兵系统。边防军主要负责边地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东汉后期,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的办法,屯兵备御。②参见徐勇等:《中国军制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 页。
秦汉时期步、骑、车、舟几大兵种的构成日趋合理和成熟。汉武帝之前,兵种建设实行车、步、骑并重的做法,武帝为了反击匈奴,积极发展骑兵部队,使骑兵成为军队的最主要兵种,中国古代战争开始全面进入骑兵时代。与此同时,车兵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战车通常只发挥屏障性防御功能。舟兵在当时有所发展,往往用于南方水泽湖泊地带的作战。步兵依旧是重要兵种,在数量上占有绝对多数。①参见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第5 卷《西汉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绪论”,第9 页。
秦朝的兵役制度基本上沿袭战国时的郡县普遍征兵制,西汉时期也主要实行征兵制,成年男子一生中按规定都要承担不同期限的兵役和劳役。秦汉时期还经常谪发罪犯或奴隶为兵,称为“谪戍”。募兵制在西汉时只有少量推行,到了东汉,由于豪强地主势力对人口控制的加强,郡县征兵制趋于衰微,募兵制遂成为兵役制度的主要形态。东汉末年,地方州郡利用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广为募兵,培植私人势力,从而酿成群雄并起的割据局面。②参见黄今言等:《中国军事通史》第6 卷《东汉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8 页。
秦汉时期战争频繁,其中统一战争、民族战争依旧占据着战争的主流。当时比较著名的战事有楚汉战争、汉与匈奴的战争、汉羌战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战争、刘秀统一全国战争等。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以汉匈战争为代表的民族战争,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相冲突并逐渐趋于融合在军事上的体现。中原王朝在战争中的胜利进一步确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本质属性,扩大了中华文明的辐射圈,拓展了疆域,维护了统一。另外,秦汉时期还诞生了新的一类战争,即农民起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农民起义,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等等,都在一定程度打击了暴政,有助于协调国家内部的复杂阶级关系。
秦汉时期的战术也有了新的提高,其中比较显著的标志是野战阵法有了一定的改进,“五军阵”的运用更趋成熟。垓下之战中韩信以坚固的“五军阵”彻底击败骁勇善战的项羽大军;卫青攻打匈奴单于主力时运用车、步、骑协同作战大破敌手;河西之役中霍去病越远迂回出击匈奴大获全胜,均反映出很卓越的作战指挥水平。与阵法进步相联系,当时军队的机动性也明显增强,日行军速度有高达160 里者,这是过去日行军为一舍(30 里)的速度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像包围、伏击、奇袭、正面攻击、侧翼突击等野战战法,山地战、河川战、丘陵战、丛林战、荒漠战、夜战、火攻、水战等特殊条件下的战法,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其指挥艺术也有了新的进步。③参见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 页。
秦汉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大统一的新纪元。在这一时期,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并多次引发大规模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和统一战争。这一客观现实,刺激推动着当时兵学的形成和发展。具体而言,秦汉时期的兵学是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历史实现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产物,是当时多次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先秦兵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是秦汉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秦汉大一统时代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统一、建设军队、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等重大基本问题,因而是中国历代兵学的有机构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秦汉时期的兵学思想,与先秦时期兵学兴盛局面相比相对沉寂。当时的兵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的有关章节和兵书《黄石公三略》之中,同时也在晁错《言兵事疏》、赵充国《屯田制羌疏》、侯应《备塞论》、王符《潜夫论》以及桓宽《盐铁论》等篇章中得到反映。虽然这一时期成型与流传的兵学著作数量有限,但是仍在中国古代兵学的建树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突出表现为:一是对先秦至两汉的兵书战策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分类;二是适应儒学独尊和学术兼容的社会思潮,强化了兵儒综合融会的趋势,出现了初步的兵儒合流的倾向;三是受“大一统”政治环境的制约,兵学理论的主题悄然发生变换,由“取天下”“争天下”转变为“治天下”“安天下”,作战指导理论研究相对趋于弱化,更加注重治军理论的探讨与阐发;四是时代感强烈,如屯田、边防思想的阐述受到特殊的重视。①黄朴民:《两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
二、兵书的系统整理与全面校订
与秦王朝仇视和灭绝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不同,西汉王朝的统治者相对重视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尤其是注重对实用性较强的学术文化的提倡。兵学是实用之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否,因此为统治者所关注,校理兵书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
汉代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②《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2 ~1763 页。其实,在此之前,相关汉初的制度建设过程中,“申军法”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与兵书的搜集与整理亦有密切的关系:“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③《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19 页。但是,有关这次整理兵书的具体情况,史无明载,在今天已无法了解其详。大致可以推测的是,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④《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17 页。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未除的肃杀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主要重在搜集和遴选。⑤按:“申军法”属于制度规章的建设,主持者为韩信,“序次兵法”为兵书整理,主持者为张良、韩信。笔者认为两者的主持者其实皆为韩信一人。但由于韩信身为军人,学术文化方面的造诣或许未能尽如人意,故由张良予以配合,厘定和润饰兵书的文字。但由于韩信身背“谋逆”之罪名,于是,“序次兵法”的第一主持人就成了张良,而韩信只能屈就成为第二主持人了。
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兵学的关注自然又提到议事日程,因此,汉武帝除了在中央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提倡儒学之外,还诏令全国,广泛征集包括兵书在内的各类图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⑥《隋书》卷32《经籍志》。。为数众多的古代兵书,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家的藏书场所,于是就有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⑦《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63 页。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同样尚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犹未能备”。
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当时朝廷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在河平三年(前26年)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⑧《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1 页。。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就每部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情况作出全面、系统的介绍,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而后汇总成为一部《别录》。但是,刘向尚未完成这项工作而去世,稍后的汉哀帝又命刘向之子刘歆接替其父的事业。刘歆“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埋头进行了多年的整理,“遂总括全书,撮其指要”,将《别录》所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所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加上总括性的提要性质的《辑略》,是为《七略》。而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是直接渊源于《别录》《七略》。
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两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即刘向、任宏将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由国家集中收藏。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世,为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切实的服务。在这之后,又有《三略》等兵书面世,进一步充实了秦汉的兵学宝库。
三、兵书的分类与学术价值总结
秦汉兵学发展的又一个显著标志,是对兵书的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各类型兵书学术特色的揭示与总结。在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工作,“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大类。其中兵权谋家共13 家,著作259 篇,现存《吴孙子》①即《孙子兵法》。《齐孙子》②即《孙膑兵法》。和《吴子》《公孙鞅》《大夫种》《兵春秋》《庞煖》《儿良》《广武君》《韩信》等,这是兵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兵形势家共11 家,著作92 篇,主要有《楚兵法》《蚩尤》《孙轸》《王孙》《尉缭子》《魏公子》《景子》《项王》等,现仅存《尉缭子》。兵阴阳家共16 家,著作249 篇,主要有《太壹兵法》《天一兵法》《神农兵法》《黄帝》《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地典》《师旷》《苌弘》《别成子望军气》等。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黄帝君臣的作品(如:《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班固自注:“《封胡》五篇。黄帝臣,依托也。《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力牧》十五篇。黄帝臣,依托也。”),现都已散失,只有后世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政书保留有极零星的内容。兵技巧家共13 家,著作199 篇,主要有《鲍子兵法》《伍子胥》《公胜子》《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剑道》《手搏》《蹴鞠》等,亦已基本散失。比较能反映“兵技巧家”的基本情况的,只有后人辑佚的《伍子胥水战法》以及《墨子·城守》十二篇。
在划分兵书种类的基础上,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③《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58 页。。可见这一派主要是讲求战略的,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
“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④《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59 页。。即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从这个定义,结合实战历史,挂名西楚霸王项羽名下的《项王》一书,可能最合乎“兵形势家”的特征了。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求战术的。
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⑤《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60 页。。这表明它注重“时”,注意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浓厚的渊源关系。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盖庐》一书,以及《六韬》中的《五音》《兵征》诸篇,《孙子兵法》中“画地而守之”“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等文字,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计篇》中的“顺逆、兵胜”之类的提法,都可以说是“兵阴阳家”特色之具体写照。
至于“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乃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⑥《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62 页。。这就是说,这一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要领、军事训练等等。从现存的文献看,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蚁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中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和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是“实古兵家之巨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不可偏废的”①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刘歆《七略》中著录的兵书,较之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数量上要多许多。刘歆《七略》的“兵书略”中,“兵权谋”一目下还著录有《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等著作。班固考虑到这些书目已在其他类目中做了著录,出于避免重复计,《艺文志》“兵书略”“兵权谋”一目中便省略未著录。《七略》的“权谋”一目还著录一种《军礼司马法》,《艺文志》则将它移入“六艺略”的“礼”目之中。《七略》的“技巧”一目还著录有《墨子》一家,《艺文志》因其已录入“诸子略”的“墨家”之目,故亦省略不著录。另外又增录《蹴鞠》一家。
任宏、刘向对兵家流派的划分与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②《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而刘歆承其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着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又源于刘向之《叙录》。成为后世兵书撰著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序与指导方针。
四、兵学表现形态的多样化
当时的兵学之表现形态是各式各样、绚丽多姿的,既有以专门著作形式面世并产生巨大影响,为后人收入《武经七书》的兵书《三略》等③有人认为《握机经》也是东汉时期成书的兵书。见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上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04 页。;又有以归纳、总结先秦兵学的基本成就为主旨并加以必要发挥的兵学专著《淮南子·兵略训》;还有零散见于君臣诏书、奏议以及众多文人学士著作中的有关论兵言论;更有通过战争实践活动和军队建设举措所反映的军事理性认识。它们合在一起,共同勾画了秦汉兵学的总体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兵学的实践功能非常突出,它紧贴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较少作抽象的兵学原理演绎,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与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比较强。如晁错的《言兵事疏》针对汉匈战争而作,总结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汉匈双方军力的对比,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晁错认为,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山区作战有惯于涉险,善于骑射,能耐饥寒三个“长技”,即三大优势,而汉军在平原作战,则拥有兵种齐全、装备精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武艺高超等五个“长技”,即五大强项:“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挡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④《汉书·晁错传》。作战指导者应该在实战中避实击虚,扬长避短,夺取战争主动权。同时借力打力,联合边疆地区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抵御匈奴,保卫边塞。晁错认为,鉴于匈奴有明显的三大优势,汉军要避免进行硬拼死打,而是要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借重他们的作战能力,形成双方结合的矩阵优势,从而以长击短,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晁错看来,这种优势互补的做法乃是真正的克敌制胜“万全之策”。这就是著名的“以蛮夷攻蛮夷”①《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第2281 页。的思想,为汉朝实现对匈奴战略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又如赵充国《屯田制羌疏》,针对汉宣帝时西羌诸部北徙,遮断西域商路,骚扰西汉边境城邑的具体形势,主张“贵谋而贱战”,提出“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②《汉书》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第2977、2984 页。的主张,为西汉王朝从事军事屯田,巩固国防提供了高明的策略方针。在中国历史上,赵充国是第一位从战略的高度,系统论述在边地实施军事屯田的战略家,其有关军事屯田的观点,高屋建瓴,切中肯綮,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具有重大的兵学理论价值,在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战略思路与策略举措,为后世的政治家、军事家所高度重视和充分借鉴,引以为守边固防之良策。唐代陆贽有言:“《军志》曰:虽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无粟不能守者。故晁错论安边之策,要在积谷;充国建破羌之议,先务屯田。”③陆贽:《陆宣公奏议》卷8。明代的商辂也指出:“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汉赵充国、诸葛亮,晋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验,著在史册。今日守边之要,莫善于此。”④商辂:载《明经世文编》卷38《边务疏》。这些评述,实可谓是赵充国的异代知音!
再如王符的《潜夫论》,根据东汉时期西羌之乱此起彼伏、接连未断的边防态势,针对东汉王朝在羌乱问题上的应对失误,专列《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有针对性地阐发了有关边疆防御和建设的观点。这包括:一、主张早定战守之策。王符认为面对严重的边患,一味退让与妥协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边疆的稳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⑤王符:《潜夫论·救边》。,退无可退,只能坚决守住。所以,王符强调“救边”:“救边乃无患,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呼吁及时平乱,反对示弱寇敌、“竟割国家之地以与敌”的错误做法,这样,就从战略的高度,确立了治边的基本原则。二、选拔与重用“明于变势”的优秀将帅。王符一再强调“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⑥王符:《潜夫论·劝将》。,主张选拔睿智英明、深富韬略者来担任将帅,“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在此基础上,王符进而对为将者的素质、品德、修养、才干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智以料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料敌则能合变,众附爱则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倍,威令一则唯将所使。”有了这样优秀的将帅,在平息羌变,安定边疆过程中,自然能牢牢把握主动权,左右逢源,收放自如。三、以“利”激励广大士卒奋勇杀敌,一往无前。王符认为,人性上有个共同点,即人人都趋利避害,而当时在边地作战过程中,之所以“士不劝于死敌”,乃是由于“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因此,必须强调信赏必罚,使广大士卒令行禁止,旅进旅退,“必顺我令乃得其欲”。四、迁徙内地民众实边固防。王符正确地理解了“实边”与“固内”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认为只有充实边疆,加强边防,才能够有力地巩固内地,与之相应,也只有内地巩固,才能够使边防建设得到有力的保障,“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王符提出了具体的“实边”策略,强调土地为民生之本,边境地区地广人稀,“不可久荒以开敌心”,而应该从人稠地少的内地迁徙民众实边,使得“土地人民必相称”,并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支持,使实边之民获得补偿,“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这样,“实边”就能真正发挥“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的积极作用,乃是最佳的“安中国之术也”①王符:《潜夫论·实边》。。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秦汉兵学在边防等专题问题上有了新的深化和突破,现实感、时代感明显加强,这正是秦汉兵学在先秦兵学已有辉煌成就基础上的新发展。
五、兵学学习的普遍化
秦汉时期对兵学理论的学习和普及是予以充分重视的。汉武帝鼓励名将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是大家都了解的史实。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当时统治者是将学习经典兵法著作、演习战阵作为培养军事人才,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的:“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习六十四阵,名曰乘之”②范晔:《后汉书》志第5《礼仪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3 页。。另外,像汉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讲司马之典,简蒐狩之事”③《诸子集成》第7册《申鉴·时事》,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9~10 页。等等,也皆表明了朝廷对学习与推广兵学文化的高度重视。
当时的大多数名将都热衷于学习《孙子兵法》等重要兵书,如东汉初年大将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④范晔:《后汉书》卷17《冯岑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39 页。他们对《孙子兵法》等著名兵书中的重要军事原则十分熟悉,背诵如流,经常用来指导自己的军事实践活动。如韩信解释其背水阵破赵之所以大获成功,乃在于正确地运用了《孙子》的“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激励士气原则。又如赵充国强调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达到攻守相宜,收放自如,显然是对孙子基本原则的遵循与贯彻:“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其主张军屯,加强守备,反对轻易出击西羌,依据的也是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⑤《汉书》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第2987 页。
再如,《后汉书·冯异传》云:“异曰:……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引用的同样是《孙子兵法》的作战指导思想,而《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⑥《后汉书》卷71《皇甫嵩朱儁列传》,第2305 页。则显然是皇甫嵩在大段背诵《孙子》“谋攻”“形篇”的相关内容,为自己实施作战指挥寻找理论依据。甚至连那位声名狼藉、人神共愤的残暴屠夫、军阀董卓,对《孙子兵法》的相关内容也是背诵得滚瓜烂熟,稔熟于心,这同样见于《后汉书·皇甫嵩传》的记载:“(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归众勿追。”由此可见,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典兵学在秦汉时期的普及程度。
不但武将注重学习和掌握兵法理论,而且不少文人同样对兵学感有兴趣,致力于兵书学习。汉武帝时人东方朔就是一个例子。他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曾叙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⑦《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41 页。。学兵书与读诗书比重相等(均为“二十二万言”),可见两汉文化人对兵学的重视,当时兵学的普及与发达于此可见一斑。而大学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人对兵学基本原理的重视与阐述,对兵家代表人物的关注与评议,也同样反映了这种文化生态的普遍性。如《史记·律书》所云:“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汉书·刑法志》云:“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也。”皆为其证。
六、兵学主题的转换
随着封建专制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秦汉时期兵学的发展也趋向于理论的整合,并且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政策性研究。
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都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精神,兵学也不例外。秦汉兵学所体现的,就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时代特征,表现之一是学术兼容趋势的进一步增强;表现之二是兵学旨趣由“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的转变。
兵学理论的整合缘起于战国时期兵书综合化趋势。其实从思想渊源上说,兵家学派本来就受到儒、法、道、墨诸家的影响。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的确立,学术上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①郭庆藩:《庄子集释》卷10 下《天下篇》,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9 页。的观念遂成为人们的共识。战国至两汉学术兼容趋势,给秦汉兵学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与政治伦理哲学对兵学理论构建与价值取向的渗透和规范,使当时的兵学不再单纯就军事而言军事,而更普遍的是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融会在一起进行讨论,沿着战国末年《六韬》等兵书所开辟的轨迹,日益趋于综合化和泛政治伦理化。②参见黄朴民:《两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这一点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兵略训》《黄石公三略》《言兵事疏》《屯田制羌疏》《备塞论》,以及《盐铁论》《潜夫论》等有关论兵篇章中的均有显著的体现。如《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其思想特征就是兼容并取,博采众长。除了对前代兵学的继承发展外,《三略》还以黄老之学作为构筑自己整个兵学体系的灵魂和思想纽带,即把《老子》的理论基础——“道”“德”置于最高层次,统辖一切。同时又阐说道家“柔弱胜刚强”的基本原则,使之成为治国安邦、统军作战诸多要务的出发点。对于儒家,《三略》一方面在思想上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施“仁义”之泽于万民:“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③《三略·下略》,《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2,北京、沈阳: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第17 页。另一方面是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④《三略·下略》,《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2,第18 页。。《三略》对法家学说的汲取则表现为:一方面贯彻法家以“一断于法”进行治国、治军的原则,“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⑤《三略·下略》,《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2,第19 ~20 页。。另一方面是坚定申明法家“信赏必罚”的思想,“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⑥《三略·上略》,《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2,第6 页。。由此可见,《三略》是博采兼容各家之长的产物,在继承前代兵学的基础上,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则勒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⑦参见宫玉振:《白话三略·导读》,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1 页。而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一特点正是秦汉兼容博采的鲜明特色。
在兵学理论的整合中,兵儒合流也许是当时最有意义的贡献了。所谓兵儒合流,就是将儒家政治理论与兵家权谋之道相结合,以儒家学说为治军用兵的原则,而以兵家的权谋诡诈之道作为克敌制胜的方法。
秦汉兵儒合流完成的具体标志,就是东汉的创建者刘秀的军事言论与实践。在东汉初年的统一战争中,刘秀注意将儒家的仁义治国之道与兵家的克敌制胜之道进行有机的结合,系统地建立起以儒家战争观念为核心的、融兵儒为一体的军事思想体系。他一方面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帜,“延揽英雄,务悦民心”①《后汉书》卷16《邓寇列传》,第599 页。,倡导所谓的“义战”,以政治优势来保障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同时,他又充分吸取兵家“诡道”的精髓,在战略方针的制定和战役战斗的指挥上,“好谋而战”,灵活用兵,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在军事斗争过程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在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刘秀也做到了兵儒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既息战养民,“修文德”以“徕远人”,又注重实力建设,严边固防,确保军权的集中和政治的安全。刘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兵儒合流的初步完成,这在中国古代兵学文化发展历程中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秦汉时期军事思想贡献于后代的最为集中的体现。
兵学主题的转换,也是秦汉时期值得重视的兵学文化现象。这一特征在秦汉时期唯一流传至今的完整兵学著作《三略》中有集中的反映。《三略》所关注的问题,既包括“取天下”的经验,也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它既是一部兵书,又是一部政论书。书中关于国家大战略的阐述,远远多于对军事战略的阐述。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于阐说兵略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的,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②参见黄朴民:《黄石公三略导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9 ~41 页。。正因为如此,以《三略》为代表的秦汉兵学贯穿着维护大一统、巩固大一统的红线。例如,在战争目的论方面,它所强调的是维护统一的“诛暴讨不义”;在价值取向上,它所强调的是巩固统一的“释远谋近”;在处理君主与将帅关系上,它所强调的是“夺其威,废其权”,“明贼贤之咎”;在对待“战胜”与“国安”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③《三略·中略》,《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2,第15 页。。
这些现象的存在,是秦汉时代精神的客观体现,正所谓“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后,天下基本趋于太平。在一般情况下,战争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当整个社会由崇尚武功转向追求文治,由迷信暴力改为遵从礼乐的时候,人们自然要高度重视政略,而相对地忽略兵略了。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也同样会反映到当时的兵学理论建设之中。换句话讲,从逐鹿中原到统御天下,是国家政治生活一个带根本性的转折,论政略重于论兵略,谈治军优于谈作战,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这就是所谓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也可以说是秦汉时期兵学发展的又一个重大特色之所在。
——刘家文
——徐小林
——秦汉时期“伏日”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