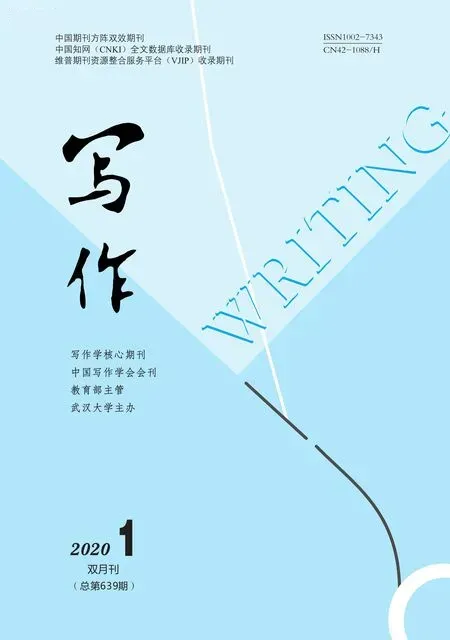科幻创作题材创新的五条路径
刘 洋
2012年,英国评论家保罗·金凯德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一篇书评,对2011年的几本科幻年选中的作品发表了略显刺耳的批评,他认为当前“科幻作为一种文体已经到了近乎枯竭的状态”。随后,“枯竭说”引发了美国科幻评论界的一场大讨论。乔纳森·麦卡蒙特发表了一篇长评,其中说道:“我认为科幻小说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兴趣,与时代脱节,导致了一种既缺乏相关性又缺乏生命力的自恋又内向的文学的出现。”事实上,类似的批评在很早就出现了。在1954年出版的一本美国科幻选集的前言里,编者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今天的许多杂志都离读者太远了。它们已经失去了惊奇感和热情,这正是很多以前的作品吸引读者的原因。它们并没有像真正的科幻小说那样,在作品里把现实的科学理论和那些激动人心的科技进展结合起来。”①Lester del Rey,Cecile Matschat and Carl Carmer Philadelphia.The Year After Tomorrow-An Anthology of Science Fiction Stories.Winston,1954,pp.6-7.在中国,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关于科幻小说“内卷化”的批评,认为现在的作者大多只是在前人开辟的疆域中修修补补,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这些批评或许过激,但的确反映了当前科幻创作中的一种趋势,作为创作者来说,应该要有所警醒。今天的科幻小说早已突破了黄金时代那种单一的风格,在新浪潮运动之后,很多作品在文学性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追根究底,科幻小说这一文类,其最核心和最根本的吸引力,还是来自于题材和设定所带来的惊奇感。所以,如何在题材上有所突破,做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设定,对于今天的科幻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当今创意写作课程逐渐兴起与科幻文学、科幻影视趋热的时代背景下,科幻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创意写作方向,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早在1991年,吴岩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科幻文学类课程,后来逐渐分化出科幻创作的方向,这是我国最早在高校开设的科幻创作课程。发展至今,已经有多所高校开设了科幻创作课程,例如贾立元在清华大学开设的“科幻文学创作”、苏湛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的“科幻文学与影视创作”等。笔者在南方科技大学也开设有“科幻创作”课程。在科幻创作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引导初学者跳脱出一般科幻创作的俗套,启发他们的创意和想象力,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对于初涉科幻的作者来说,第一步当然还是要大量的阅读,从各种经典的文本中汲取营养,同时也让自己对前人开拓的领域有个大致的了解。这样,在自己写作的时候,才能对题材的新颖性有一个合理的评估。其次,他们还应该对当今科学的前沿领域有所了解。当然不必像科学家那样深入,但至少应该大致掌握其研究脉络和相关机理。当你对某个领域产生特别的兴趣,决定以此切入,创作一篇科幻作品时,你就应该对它进行更深入地了解。其实,以当今科学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而言,想要寻找新的创意点并不困难,很多时候科学家已经进行的课题甚至已经超越了科幻作家的想象。作为范例,也为了帮助初学者找到突破的方向,下面我将在五个具体的方向介绍题材创新的开拓方式,并提出一些创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假想科学
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科幻小说一定要基于现有的科学理论来做设定,其实不然。科幻小说的“科学性”不同于学术论文的“科学性”,它更强调的是推想过程的逻辑自洽,而不强求其理论基础严格符合当今科学的认知。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为了故事构建的需要。我们必须强调,科幻小说的首要目标是构建一个具有惊奇感的故事,为了这一需要,当作者不得不引入一些超越科学认知、有时候甚至略微违反科学认知的设定时,他们是应当得到允许的。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基于“宏电子”这一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设定,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伟大的科幻小说,因为在这一设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推演,包括电子的量子特性在宏观下的展现等,都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的逻辑。正是在这一系列设定的基础上,作品才成功地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诡异怪诞、极富惊奇感和吸引力的世界。
另一个引入假想科学的理由是:科学理论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些目前还不成立的虚构的理论,并不意味着今后不会发展成真正的科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阿西莫夫在基地系列里虚构的一个科学理论“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该理论认为,虽然人类个体的所作所为很难预估,但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大众的种种行为——包括人类未来的历史——则可以通过纯粹的统计手段来预测,惟一的前提条件是“人类集团本身不了解心理史学,以便其反应是真正随机的”①原文为“the human conglomerate be itself unaware of psychohistoric analysis in order that its reactions be truly random”。。基地系列的主线情节就是基于这个科学理论而衍生出来的。显然其灵感来源是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在那里,尽管每一个微观粒子的速度和轨迹都无法预测,但表征其整体的物理参量如温度、压强、体积等,却是可以预测与计算的。在阿西莫夫写出该作的20世纪中叶,心理史学当然只是他的设想,但随着近年来一门称为“社会物理学”的学科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越来越接近阿西莫夫所设想的那个虚构的学科了。虽然现在的社会物理学还没有发展到小说里心理史学的程度,但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其未来成为一个真正完备和成熟的理论体系。
引入假想科学作为设定基础的时候要注意避免与当今的科学结论直接冲突,那样容易使作品陷入“伪科学”的漩涡之中。当然,我们必须要明确,科幻小说中的假想科学与一般认为的伪科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故事构建的需要而引入,作者和读者都明确地知道这一点,并不会认为它是真实的科学理论,而后者通常会竭力模糊其与真实科学的界限,其宣传者本身往往声称它们就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宏电子”产生的背景是人们目前对球状闪电的起源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理论解释,而且对电子、夸克这类基本粒子,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同样极度缺乏。“心理史学”同样如此,它并不违反任何已知的科学定律,相反是超前于现有的科学理论。其他常见的科幻设定,如时间旅行、曲率驱动、瞬间传输等,虽然并没有现有科学支撑,但至少并不被科学定律所禁止,从而为假想科学留下了理论上的空间。
通过引入一个假想的科学理论来建构一个虚拟世界,是极具原创性的设定方法,可以开发出极有新意的题材。具体设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丰富假想理论的细节,将其与现有的科学规律融合在一起,尽量减少其假想的色彩,避免其成为一座没有支撑的空中楼阁。
二、异构世界
想要从一个虚构的科学理论出发推导一切的想法往往是极为困难的,大部分时候我们并不这么做。想要达到与其类似的颠覆性的奇观效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比如设想一个处于某种极端环境下的异世界,或者其他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些世界的物理法则和我们并没有区别,但故事通常并不发生在我们熟悉的地球或类地球环境里,那里的众多事物和智慧生物的日常行为也往往与人类截然不同。
一种常见的异世界设定是让故事发生在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有时候我们会借助那些确实存在的星球,比如火星、金星、月球、冥王星等来构建自己的故事,这时作者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让自己对这些星球各方面的状况了如指掌,特别是它们与地球相比有哪些异样之处,因为这些异常点往往才是读者更感兴趣的地方,作者应该围绕这些异常之处来展开故事。在克拉克的《月海沉船》里,故事始终围绕着月尘的特殊物理性质来展开,比如它们的流动性、导热性、电磁屏蔽等,让整个故事显得真实可信的同时又不断产生新的惊奇点。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则围绕火星的实际状况设想了众多对其进行环境改造的方案,以这种巨大的变革为背景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肯·沃特的《地下之上》,该小说发生在木卫二那被冰壳覆盖的液态海洋中,那里产生的智慧生命具有与正常视角相反的上下方向认知:因为生存在海洋里,身上长有气囊的他们同时受到指向星球外部的浮力与指向内部的重力,由于前者大于后者,综合起来的等效重力便成了指向外部的方向,于是它们把这个方向认定为“下”,而把指向星球内部的方向认定为“上”。这种误解带来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比如他们想要突破星球的束缚,向外进发,却搞错了方向,一直向着星球内部挖掘,发现一直无法突破到海洋外部。他们还总结出了一些错误的引力定律,比如高度越“低”引力越大——拟合的数据甚至显示到某个高度重力会无穷大——事实上只是因为越靠近冰层,液体的压力越小,其身上的气囊就越大,从而使其所受的浮力增大了而已。
另一些作品则完全发生在一些虚构的星球之上,或者目前人类尚不明了的遥远星球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不受已知星球的各种特征的约束,在一个更为自由的维度下,根据故事的需要来建构所需的环境,它们往往比既有的、人类较为熟悉的太阳系内的星球环境更加怪异,从而让作品具有更强烈的冲击性。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虚构了一个被沙漠覆盖的干旱星球,却出产能使人产生超感能力的香料;与之类似的是电影《阿凡达》中的星球,它富含奇妙的常温超导物质,因此引来了人类的大举入侵;罗伯特·福沃德的《龙蛋》描写了一个生活在中子星上的种族——奇拉族(Cheela),他们的新陈代谢是基于核反应而不是化学反应,同时因为其星球表面的重力远超地球,他们和人类的时间流速也相差甚远。写作这类发生在虚构星球上的小说时,我们可以先从一系列基本要素开始进行设定,比如这颗星球的半径是多少(涉及到重力的大小),主要组成元素是什么(砖石星球?),星球表面的环境怎么样(是否有固体表面、土壤、大气、液态水),它的自转和公转情况如何(涉及到不同纬度的重力差异、是否有四季及磁场等),它所围绕的恒星是什么状态(是否已经变为红巨星,或者有三颗恒星?),距离恒星的距离是多少(涉及星球表面的温度),等等。切记设定一定要服务于故事的需要,在一开始就要明确自己想写一个什么样的种族或什么样的奇观,以此来指导自己对星球的设计。斯蒂芬·吉列特在《世界建构》(World Building)一书中提出了很多操作性的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
除了外星球,故事还可以发生在其他的奇异世界,例如赛博朋克作品常发生在意识电子化之后的虚拟空间中,另一些作品把场景设置于人或其他生物的体内、二维的平面宇宙、中空的地球内、环绕恒星的戴森环上、原子等微观粒子内部,乃至整个宇宙之外的超空间中。可以说,科幻小说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世界里,不管它们有多么诡异或不合常理。特德·姜的《巴比伦塔》设定了一个在空间上具有周期性边界的世界,人们造了一座极高无比的塔,穿过了天顶,最后发现又回到了地面。格雷格·伊根的《边境守卫》(Border Guards)构想了一个具有三维环面拓扑结构的虚拟世界。玛丽亚·斯奈德(Maria V.Snyder)的立方体之战系列则发生在一个被称为“里面”(inside)的世界,那是一个全封闭的立方体,按照阶层分割为不同的生活区域。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上文我们看到了很多五花八门的异构世界,但这些精巧的设定本身并不直接决定其好坏。评价一个世界的结构设计是否优秀,除了看其创新性、自洽性和惊奇感之外,还应该观察其是否容易衍生出各种戏剧冲突。设计一个完美、和谐、人人幸福的乌托邦世界,在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
三、技术奇观
科幻小说中总是充斥着各种虚构的科技发明,很多科幻小说中常常会出现一个发明家或科学家的形象,通过其口向读者阐释某种新奇技术,并由此带动故事的发展。有的时候,这些发明会带来好的结果,科幻作家对科技的进步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例如在刘慈欣《圆圆的肥皂泡》《带上她的眼睛》《地火》《地球大炮》等小说里,超级表面活性剂等作者设想的技术都带有很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的倾向,故事的主要矛盾在革命性的技术创造中得以解决,是这类作品的典型特征。但大部分时候,科幻小说中的技术创新带来的更多是不好的结果,或者虽然它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但作品重点关注的却是它的负面效应,例如其导致的操纵失控、伦理失序、人类异化、审美缺失等。对技术的警惕和反思日益成为现代科幻作品的主流,这固然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状态与科技伦理思潮的兴起有关,但一个更根本性的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一个关注科技阴暗面的作品,比起那些科技乐观主义的作品,往往更容易构造一个复杂曲折又有深度的精彩故事。
在科幻作品里,构造一个新奇的、震撼人心的技术奇观,是一种常见的题材创新方式。但那些新奇技术其实也并非是作家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通常也带有现实科技的影子。一般而言,科幻作品中的技术奇观,从其创生途径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宏大化。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放大现有的工程尺度,来塑造那些宏伟壮丽的奇观。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描写了一个900英尺长的巨型大炮,这是对大炮这一现有技术的夸张放大。大炮这种技术本身并不新奇,但尺寸上的放大却带来了视野上的另类惊奇感,后来在刘慈欣的《地球大炮》里更是将炮筒贯穿了整个地球,可谓将这一思路用到了极致。这种对宏大奇观的描写在硬科幻小说中常常出现,随口就可以说出无数这样的例子:《天堂的喷泉》里出现的太空电梯、《与拉玛相会》中的巨型太空站、《星球大战》里的死星堡垒、《环形世界》里的戴森环、《流浪地球》里的行星发动机……宏大不仅是技术极端发达的表现,而且也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但要注意的是,不要为了宏大而宏大,或者一味地进行大尺寸空间下的描写,任何宏大之物都需要从细节上进行呈现。
第二类是重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新构建那些我们熟悉的技术,也是一类常见的技术奇观的创建方式。在这类小说里,我们会看到很多略显奇怪的机械或技术,它们源于现实,但又在某些地方偏离了现实。蒸汽朋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一切机械的动力来源都是蒸汽机,包括大型飞艇、机器人及计算机。那些庞大、笨重而又结构繁复的机械喷吐着灼热的蒸汽,在冷硬中却又呈现出另类的美感。另一种常见的重构方式是将机械生物化,例如《无赖殖场》里的生物火箭、《海伯利安》里的树舰、《三体》里的人列计算机等。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重构方式,我在《说书人》里写过用细菌发电的直流发电机,在《流光之翼》里设想了一种利用蝴蝶构建的量子计算机。这类设定将鲜活的生物和冰冷的机械结合在一起,常常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奇效果。
第三类是异化。具体来说,科幻小说中的异化通常又分为人的异化和技术的异化两种,两者都是某种特定的技术发展到极限或失控之后,所涌现的脱离原来预期的产物。很多情况下故事中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灾难,其技术设定的奇观场景在这些悲剧性的灾难爆发过程中得到集中地展现。
人的异化通常与那些应用于人体的生物、医学等方面的技术有关,《弗兰肯斯坦》里面目狰狞的人造人、《羚羊与秧鸡》里基因编辑培育出的“秧鸡人”、《寄生前夜》里由线粒体幻化出的异形人,都是其典型的例子。国内作家也创作过大量这类题材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王晋康的“新人类四部曲”《类人》《豹人》《癌人》《海豚人》,每一部都描写了通过某种基因技术制造出的新人类,以及技术失控下产生的悲剧。另外,刘慈欣《微纪元》里的微型小人、何夕《盘古》里的巨婴、刘宇昆“未来三部曲”里意识上传后的数字人,也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异化设定。
与技术带来的人的异化不同,一些作品重点关注的是技术本身的异化,其通常涉及的是这样几个方面的技术:1.人工智能,如杰克·威廉森的《束手》,描写了一个智能机器人接管一切,人类受到机器无微不至地照料,什么都不用做,却也什么都不能做的可怕场景;2.互联网/物联网,如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虚构了一种可以同时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传播的电脑病毒;3.高能物理,如刘慈欣的《朝闻道》,设想高能加速器的实验会导致真空衰败,甚至毁灭宇宙;4.纳米技术,如麦克·克莱顿在《纳米猎杀》呈现的场景:一个纳米集群失控后逃出实验室,不断进化、复制,并开始猎杀沙漠中的动物乃至人类。还有一类小说并不关注某种单一技术对世界造成的影响,而是着眼于科技与工业发展对全球生态的影响,这就是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所谓“气候小说”(Cli-Fi),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技术异化下的一种奇观展示。
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幻小说里设想一种技术奇观作为核心设定,具有众多的途径和选择对象。建议初学者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入手,尽量大胆地进行推想,然后再用文字细致地勾勒出脑海中那些宏伟而奇绝的图景。
四、奇异生物
在作品里引入现实中不存在的生物并非奇幻小说的专利,在科幻小说里我们也常常这样做。这些奇异生物要么没有智慧,仅凭生物本能做出反应,在小说里通常作为人类探索、研究、斗争的目标;要么具有智慧,甚至处于人类遥不可及的文明等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星人,小说主要通过人类与其交流交往的过程建构故事和冲突。后一类题材在各种科幻小说中较为常见,这里不再过多阐述。我们重点讨论前一类奇异生物的设定和呈现技巧。
我们一开始就要明确自己设定这些生物的目的以及小说的写作方向。如果你要创造的是一个或众多“怪兽”,那么其故事可以非常好莱坞化,展示其侵入人类生活空间、与人类斗争的过程,类似电影《哥斯拉》《迷雾》《汉江怪物》《长城》等;也可以反之,描写人类无意中进入怪物的领地,突出探索和冒险的元素,如电影《黑暗侵袭》《被时间遗忘的土地》《九层妖塔》等。这种题材的生物设定简单粗暴,通常是通过模仿、放大或拼接现实中的生物来塑造怪物的形象,并且让它们具有某种超出普通生物的能力或特征,使其能够对人类造成威胁。设定的时候,除了强调其非凡的攻击能力之外,还要注意为其留下一个致命的弱点,以便故事的主人公能够消灭它们或者从危险之地脱身。
另一些科幻作品中的奇异生物则显得更为神秘,与人类的互动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猎杀和被猎杀。在故事中,常常通过探索或研究的行为来呈现其异常特征。写作这类题材,我们在设定时需要更加大胆、细致,既要突破一般的思维局限,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鲜物种,给读者带来惊奇的阅读体验,同时也要注重其逻辑的合理性,对其奇异特性的由来、所处的环境、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基本的结构特征、生殖发育的过程等方面统合起来考虑,让其奇异之处得到更多基础设定的支撑,以增强其合理性和真实性。以石黑达昌的《冬至草》为例,其中描写了一种奇异的植物,它具有近乎透明的叶片,生长在含铀的土壤中,带有放射性。故事以一位研究员对冬至草的追踪和探究为主线,借助前人的研究笔记为线索,逐渐描摹出这种植物的各方面特性,并最终揭示出背后隐藏的真相。文中对冬至草的很多细节描写值得我们注意:“从茎生出的羽毛一样的叶片娇嫩欲滴……给人一种强烈的透明感”,“根系竟然十分发达,相互缠绕、延绵不断”,“距离墓地越近,冬至草的生长就越密集,而且白色的纯度也更高”,“给它加热,想让它早点干燥,可是它突然间就会烧起来”,“该植物有夜间发光的记录”。这些细节描写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支撑印证,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生物体系。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以奇异生物为核心设定的小说,尤其需要以写实的手法来创作。只有在这样的虚实交织之下,设定和现实的界限才会尽可能地模糊,从而给读者更强烈的震撼感。
五、社会结构
科幻小说常被人寄望于可以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予以预测,甚至给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科幻作品通常会涉及到社会的整体结构在某种科技或极端事件下的调整、震荡与剧变。一部分作品更关注科技本身带来的惊奇感,对其在社会结构上带来的影响常常轻描淡写地带过,或者采用其他的写作技巧以避免让作品在这方面复杂化。而另一部分作品则截然不同,它们的重心恰恰就是对社会结构的设定与描摹。在这些作品里,社会的运行规则常常与我们现实生活迥然不同,从而形成了种种奇特的社会结构。正是这些奇特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结构,给这类作品带来了独特的阅读趣味,它们才是作品的核心设定。而与之相匹配的技术手段,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精巧或酷炫,本质上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往往是为了迎合与匹配那些社会结构而刻意地设计出来的。
这种题材的科幻小说常被归类为“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在欧美的科幻小说里有许多这样的经典作品,如《1984》《美丽新世界》等。近年来性别、种族等题材在欧美科幻小说中逐渐流行,也随之涌现出了一批聚焦女权主义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如厄休拉·勒奎恩的《黑暗的左手》,内奥米·奥尔德曼的《权力》等。在这些作品里,男女的性别及其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被消除或者颠倒了,从而带来了新的社会结构。在中国,致力于建构新奇社会结构的科幻作品相对较少,但也绝非空白。刘维佳的《高塔下的小镇》描写了一个在激光大炮保护下的田园牧歌式的小镇。大炮可以阻挡所有外来者进入,让小镇居民生活在零压力的安逸状态之下,然而这其中也隐藏着进化的危机。王晋康的《蚁生》借助一种从蚂蚁中提取到的激素,建立了一个人人利他的乌托邦农场,最终却因与外部社会的格格不入而走向幻灭。刘慈欣在《超新星纪元》里创造了一个由孩子统治的世界——因为一场超新星爆发,所有13岁以上的人类都相继死去。在之后的新世界里,所有大人们留下的法则和规律都被推翻,甚至连战争都沦为了一场游戏。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作品中,促成社会结构改变的因素,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因为它们并非作品的重心所在。《高塔下的小镇》并没有详细说明激光大炮的建造和工作原理,《蚁生》里也对所谓的“蚁素”语焉不详,至于《超新星纪元》里让所有大人死去的宇宙辐射,其实也完全可以改为其他的致命因素——比如一种只对大人们有效的流行病毒——而对故事的核心毫无影响。
如果说大部分科幻小说的设定是对某种科学技术的思想实验,那么以社会结构为核心设定的科幻小说就是一场社会实验。只要构思精巧,它们往往可以呈现出比普通科幻小说更有吸引力的一面,同时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也容易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在社会结构的设定上发挥自己的创意,也是一种极有意义的题材创新方向。
综上所述,本文从“假想科学”“异构世界”“技术奇观”“奇异生物”和“社会结构”五个方向介绍了科幻创作的创新路径,并提出了写作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科幻产业正逐渐兴起和完善的中国,我们的科幻创作者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开拓这一文类的题材,以更加富有惊奇感的场景、设定和故事吸引读者,让科幻走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被更多的读者接受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