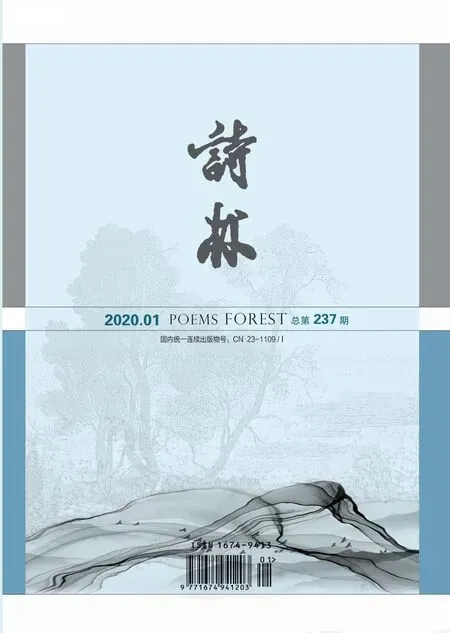闪烁水晶球体的智光灵悟
——孙绍振诗学体系的基本特征
庄伟杰
环顾宇内,学者何其多,多至令人眼花缭乱。但大学者、真学者则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在笔者的心目中,能称得上大学者或真学者的起码要具备三大条件:一者,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诚然,独立思想来自于独立的精神品格,而非是依附于某些存在的客观或扭曲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则应来自于平等开放的现实,而非是为禁锢的被奴役的精神而思想。二者,在孤独的坚守中探寻真理之路。如果说,坚守是一种品格,那么孤独应是一种境界。前者意味的是坚持和耐力,是在一次次的上下求索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修远之路;后者则意味自觉与崇高,是文化人或曰知识分子苦心孤诣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踔厉风发的生命姿态。三者,学贯中西,打通古今,融会贯通,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方式(阐释),建构独立而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学界,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年来,大多数的士人已习惯于被人操纵,仅有少数具有独立人格的“叛逆者”和思想家除外。以此观照孙绍振先生的学问人生,从知识结构、精神结构、心理结构等多重结构因素的合力熔铸而形成的学术成就,可以肯定,孙绍振已然形成自己独具风貌的诗学思想。这里,笔者更愿意并倾向于称之为“孙氏诗学体系”。要弄清这个“体系”到底是怎样的,大致可从三大方面来加以理解。
其一,走近孙绍振主要著作及论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命运际遇和文化语境,所有的路面都是相似的路面,只有舞台不同,各自扮演和拥有不同的角色。在现实的暗流中前行,在时代的浪流中腾跃,时间只留下无声的见证给道路。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冰封解冻的中国大地涌起了文化新潮。1981年春天,孙绍振便以一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率先在《诗刊》上发声,其在当时中国文艺界犹如一声春雷。如此振聋发聩,仿佛为一个新时代的“剧情”留存了最经典的台词,也为命运的种子在抗争时留下花瓣的弧线。于是,在华丽转身中,他坚定不移地把生命中最精彩的元素和最高贵的激情,勇敢而深情地献给了文学理论与批评,“凭借人类文化心智所创造的新知识、新思维与新信息融会进自己长期营造、积淀的‘基督山’”。如果说,“新的美学原则”作为一种陌生的声音诞生了新奇,弹响了“孙氏诗学体系”的第一声音符;那么,随后推出的6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文学创作论》,则演绎了其诗学体系的第一部宏大的新生的交响乐章,连同《论变异》《美的结构》等,包括期间陆续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性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在“百废待兴”的20世纪80年代,孙先生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卓越的思辨力和精湛的学术功力,捷足先登地进入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与批评,对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对美的结构包括形象的三维结构、真善美的错位结构等核心理论进行重新的反思判断,对艺术感觉受到情感冲击而发生变异的感觉传达进行了深层次的梳理论析,从而在延宕中开拓了自己的新美学原则。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与他同时代的一批重要批评家和学者一道,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重建试图求取壁垒一新之气象,而且从文学内部与外部的诸多现实问题出发,为了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唯西方文论是瞻的积习,有效地克服西方文论的局限与缺陷,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富有远见卓识的清醒与睿智,注重对当代现象审视,并梳理流行思潮中那些潜在的问题,重新思考当代文论的本土性建构,从而展开了带有创意性和开拓性意义的深入探索。近年来,孙绍振极力倡导“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并提出“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由此可见,要理解和证实“孙氏诗学体系”构成的关键,窃以为重新解读孙绍振及其诸多重要理论文本包括文学文本,殊关重要。
其二,既博大又精深的孙氏之学。一个学者个人的思想生命远远超过其自然生命,因为自然生命是生物学的,受生物规律支配;个人的思想生命是社会学的,受社会规律支配。真正的学者即智者,只要其思想对学术(思想)史有新的贡献,或者说具有社会存在的需要和根据,那么其思想就会长久发生作用并闪烁永久的辉光。这是规律,也是命定性使然。今天我们仍然在解读庄子、朱熹、李贽,仍然在解读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也仍在解读鲁迅、钱钟书、朱光潜……
虽然笔者无意把孙绍振与以上列举的思想者相提并论,但始终坚信:有实力有思想者自有其魅力。时间是最公正的主人。自20世纪80年代发出“崛起”论至今长达30多年的历程中,孙绍振先生以其罕有的才情和绝对的勤奋,加之至深的颖悟力、超常的鉴别力、犀利敏锐的批判力,偕同亦庄亦谐、出奇制胜的生花妙笔,合力构成其博大而精深、别致而生猛的孙氏风格与特色。可以说,孙绍振现象的出现,是多种罕见因素综合铸成的。因此,笔者称其诗学体系是棱形立体的水晶球状结构。令人刮目的是,他始终保持前倾姿态,勇立潮头,俨然是当代文论界的常青树。难得的是,孙氏之学虽博大,却与看似满腹经纶而实为两脚书橱之类的所谓学者绝不相类。其胸中自有炉锤,善于熔炼、取精用宏,真正臻达“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Seneca席尼察语)。
孙氏之学不仅在视域与内容上“博”而“大”,而且在思辨与解析上“精”又“深”。或先声夺人,善于发前人之未发;或洞幽烛微,长于提出精妙之见解。如果把其诗学体系视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相关成就和事迹就如同它所开的满树奇花和所结的盈枝异果。这棵树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景观;而作为一处风景,所有的远山近岭,只是树的渲染或烘托。有趣的是,有时读一棵树就像读一个人,有时读一个人就像读一棵树,树与人彼此叠映,永远立于风中而独揽空旷,树上缀满了果实,也缀满了沧桑,而且总是牵引或凝聚着注视者的目光,让人惊叹,又让人赏心悦目,令人受益,也令人豁然顿悟。
在当代文论界或学术界,偏于博大者有之,重于精深者有之,既博大又精深如孙氏者,实属鲜见。当年孙先生无愧于“北大才子”的称誉,如今他无愧于作为一个在学术之路上下求索的“行者”——以其坚实的行动,以其深厚的理论涵养,在以往研究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展开学术创新,鲜活地绽放出其学术之树花团锦簇且令人感奋的景象:问题意识的呈现是其生命线路,关键概念的命名是其主要构件,范式的拱体是其自身框架,学理的支撑是其栖居之所,价值的基点是其核心意义。这树、这花根植于文学文化的沃土之中;这土、这人坚定地守护在人生的边缘地带。一句话,其诗学思想生命,远超于自然生命。如此安详和自得,绝非名利权贵能够领略。
其三,在反思、突破和超越中进行体系性建构。从整体上考察,孙绍振诗学思想具有那种超越传统而进行体系性建构的力量,并凭借此力量展开反思判断,具有真正突破性的发现。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所谓的“体系”,无非是建立在对某种知识谱系的阐析和分类上。就阐析之上的“体系”而言,从某一点来看,或许自有其理由,但结合在一起,往往沦为盲人摸象式的以偏概全,甚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抑或只见楼房不见市镇。这正是许多理论观点停留于孤单见解尚有些许价值,整个体系却难以构成的致命原因。就分类之上的“体系”来说,尽管对错综复杂的知识谱系进行分门别类是建构体系的基本手段,历史上某些无所不包且显得整齐划一的庞大体系,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对人类知识的整理和传播的确有利,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时下那些打着某某“美学体系”或“思想体系”为幌子的高头论著,有多少不是所谓“空门面,大帽子之论”?(钱钟书语)有的甚至是西方文论余绪在中国的抽象贩卖。其根本缺陷表现在: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空中盘旋,脱离了实践的推动和纠正机制,带着西方经院哲学传统的“胎记”,造成了文学理论往往脱离文学创作经验,无力解读文本。
那么,如何处理好“理论”(普遍性)与“文本”(特殊性)关系呢?在孙先生看来,理论的价值在于作“文本分析”的向导,但它对所导对象的内在丰富性有所忽略。文本个案的特殊内涵永远大于理论的普遍性。倘若以普遍理论为大前提,不可能演绎出任何文本个案的唯一性。因此,文学理论不可能直接解决文本的唯一性问题,理论的“独特性”只能是一种预设。它只是一种没有特殊内涵的框架。文本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只有通过具体分析,将概括过程中牺牲的内容还原出来。这是一个包括艺术感知、情感逻辑、文学形式、文学流派、文学风格等的系统工程。“可见,推动知识观念发展的动力是创作实践,而非知识观念本身。文学理论的生命来自创作和阅读实践,文学理论谱系不过是把这种运动升华为理性话语的阶梯,此阶梯永无终点。”因为理论并不能自我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准则。只有这样形成的体系才称得上科学的体系。于是,为了改变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唯西方文论是从的积习和有效地克服西方文论的局限,进入新世纪之后,孙绍振极力提倡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及建立中国式的文学批评学,对文论(思想)史上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即体系的内在逻辑,究竟是源于观念(理论)自身还是源于文本(实践)之本然,做出了圆满的回答。而这,应该说是孙绍振自身思想更趋圆融的体现。正如恩格斯所言:“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结构主义大师皮亚杰则认为:“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以此观之,如果说“孙氏诗学体系”确属一学,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一个绕不去的重要话题,且在人文科学中已然成为一种鲜有的奇特现象;那么,其基本特征体现的整体性与开放性交融的“结构”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不妨进一步展开探析。
孙氏诗学体系的理论内容和理论亮点的特殊性,驱使我们有必要把其诗学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生活和文学现状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任何一个理论家的思想都不是思想史的单纯的逻辑延伸。在哲学家那里,往往运用一些超历史的、形而上的语言,面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所要解决的是思想史上的难题。譬如,黑格尔哲学在直接层面表现为一种思想的逻辑,其晦涩的论述要解决的是思想史上的难题,但实际上,所要解决的乃是当时德国的历史难题,即面对英、法等强国,德国应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黑格尔自言:“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哲学如此,同为人文学科的文学亦然。如果不能把黑格尔的哲学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待,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思想史逻辑中的黑格尔,却无法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文化意义。
理解孙氏诗学体系及解读其理论文本,同样有必要进行总体性观照。的确,“解读孙绍振的著作让我们不无激动而又心情复杂地阅读着一个曾经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时代,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个重新竖起启蒙理性思想大旗的激情澎湃的时代。”鉴于中国大陆文化思想界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50至70年代末期)长达二三十年期间,或深受机械论、独断论之害,或备受概念化、公式化之苦,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文学,孙先生一方面自觉抵制那种图解式的“假大空”,另一方面对后来纷纭而至的各种文化理论保持高度的警惕。个体性的觉醒与自我意识的萌发,让他敏感地发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已打破坚冰,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正在崛起……
之所以说孙氏诗学体系呈棱形立体水晶球状结构,究其源在于其对事物整体性的透视。传统人文学科体系几乎是呈平面的线性结构,这恰好印证了“孙学”在体系形态上是区别于传统的。换言之,孙氏诗学体系是不能用传统“体系”标准来衡量和评价的。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正统文学理论强调的是生活与形象混沌一片的一元论,即是典型的单一维度的线性结构。孙绍振在北大学习时,对此就持怀疑态度。黑格尔曾多次提到“内在性相”与“外在因素”这一“二元论”学理也就是孙绍振所谓的两维结构。不过,孙氏把二者区分开来,认为创作就是从摆脱对生活的被动依附开始。由此生发展开,二维结构的概念内涵应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特定生活与特定情感;第二个层面是指作家自我感情的特征和创作内在自由的智能。这一层面的二维结构强化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孙氏认为作家发挥自我的特征尤其是自我感情的特征,获得创作的内在自由,发挥自我表现的智能(包括非智能即本能),把自我的本质对象化了,就是把自我的灵魂用不同的方式给予他的人物。否则,文学形象的胚胎永远不能发育,成为死胎。纵然有了二维结构,形象的胚胎还是停留于现实层面,不可能上升至审美层面。为此,“还得在想象结构中升华,直到形式这一维充分发挥了作用”。把形式作为形象结构的第三维和审美规范之一,哪怕是黑格尔也没有如此明确的界定,他是把内容与形式混为同一单元,即是“没有无内容的形式,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孙绍振的超越之处在于勇敢地突破形象的二维结构而提出形象的三维结构,即情感特征、生活特征和形式特征。诚然,孙先生从不因论证一种观点而排斥其他观点,也不因研究一种现象而忽略其他现象,非此即彼。在他看来,对事物结构或内部规律的把握绝非易事,需从大处着想,从小处入手。在谈艺论文时,他常常“一手持望远镜,一手持显微镜”(钱钟书语),因而其学术著作结构既有棱有形,又具多层面立体式呈现,如同水晶球体总是闪烁着智光灵悟、真知灼见。
孙氏诗学体系的开放性结构源于事物的转换性及自身调整性需要。有专家学者从孙绍振审美创造论出发进行中西比照。认为孙绍振的新美学原则的话语进行了三大转换工程。首先是将权力话语转换为理性话语;其次是哲学话语转换为美学话语;再者是将西论独白过渡到中西对话。既合乎话语形式的转换及自身调整性需要,又有话语形式超越时空的过渡。因为在孙绍振看来,“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的独白史。它导致了民族独创性的遗忘。因此要提倡真正讲平等而有深度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