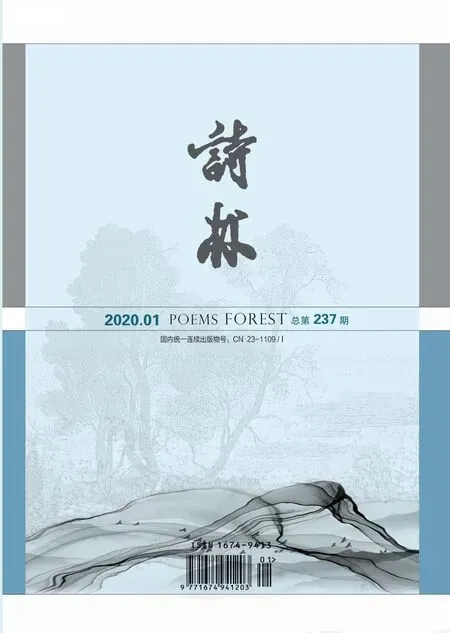关于诗歌流派嬗变过速的问题
孙绍振
在新时期文学中再也没有比新诗引起的争论更为激烈更为深刻的了。早在1980年,所谓“朦胧诗”的冲击,就把读者分裂为拥护和反对的两派,经过几番争辩和这几年的实践,当年所争论的问题,有很大部分目前已不成问题了。可是新诗潮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刚刚在诗坛上站稳了脚跟的舒婷、北岛,很快又被一些后来者视为“过时”了,以致产生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慨叹。舒婷、北岛是在突破传统审美规范的过程中“崛起”的,可是他们没有郭沫若、李季那样雄踞诗坛几十年的幸运,眨眼之间自己又成了被突破的对象。诗歌艺术迅猛发展的声势好像比头几年的那一次更为浩大。1986年,在中国诗坛上公开发表主张、揭起的旗号竟有几十种流派(有人夸张地说不下百种),这可能不但在中国诗史上,而且在世界诗史上也是空前的。旗号的纷纭说明了诗歌艺术的嬗变在加速。从诗歌艺术的发展来说,如果没有发展,没有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新、突破,诗艺将会因停滞而走向衰亡。
任何一种审美形式的发展都要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那就是积累审美规范和打破审美规范。没有积累,艺术会变成生活的粗糙碎片或者情绪的粗暴发泄。但是任何一种规范都是有限的,它只能表现生活和心灵的有限方面,因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越是成熟,它的有限性、稳定性与生活、心灵的无限性和变幻性越发生冲突。诗歌艺术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诗越来越像诗,也就是越来越像已经获得经典性的诗,这就是庞德为什么要说一切诗人所写的诗都是他头脑中记得最熟的几十首诗的翻版的原因;另一方面则相反,越是有创造性的诗人越是要打破既成规范,越是把诗写得不像诗,可后来终于被承认,甚至变成是最像诗的诗。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这两个要素处在同一动态的结构演化过程中,由于结构的有机性,任何一方的变动都要引起另一方的相应调节。这是系统结构的自调节自组织功能决定的。这种调节的过程是一种历史过程,多则几百年,少则几十年,很少是一代人生命限度以内能够完成的,处在这个调节的历史过程中的诗人是非常痛苦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自觉地认清这个过程,因而难免陷入盲目性。有限的时闻视域使人们在诗艺的渐变和突变中失去宁静。这几年纷纭的旗号兔起鹘落,就是部分诗人失去平静而引起躁动情绪的具体表观。
当然,这种躁动主要产生于不能忍受旧的规范的束缚,多方面地寻求突破的要求。他们在创作上,的确也有许多可以称道的突破:江河、杨炼、梁小斌自不必说,就是宋琳、范方、吴晓也都有某些在美学原则上超越舒婷、北岛之处。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意识的纵深层次的深入。如果说,传统的浪漫主义主要在表现人激烈强化的感情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的话,那么象征派、意象派就主要在回避强大的激情,在平静的情绪中用外部感觉和语言的变异、分化,解析和深化来表现人的智性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这两方面,富于浪漫热情的古典美的舒婷、富于现代感觉和智性的北岛已经取得广泛的认同,因而所谓“后崛起”的诗人们就不屑于第二次走上别人踏出的路径了。在他们看来,既然激情、智性与感觉的领域已经有了现成的男女国王,他们就只好到舒婷、北岛遗漏的天地去称雄了。这里涵盖着人的整个生命的过程,他们在生命的全面体验中,包括在潜意识中,在与美相对立的丑中,在深层的本能中发现了一系列崭新的层次。宋琳说:“诗人的艺术行为不仅是一种自觉运动,而且是一种精神本能运动。这意味着,只有把良心、道义、责任以及审美倾向等意识中的自觉转化成本能,才能进入诗的状态。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任何美学上的禁忌都是与他高度自由的天性和意志格格不入的,一首诗就是诗人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瞬间的展开。”作为一种理论,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出许多明显的毛病,但是作为一种情绪,一种在舒婷、北岛的世界以外替代审美的新大陆的情绪,它有历史的合理性。宋琳的确寻找到了一些比舒婷北岛更自由、更带随机性的情绪和更具瞬间性的联想过程。就是在这随机性的不事雕琢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传统审美规范所遗忘了的新大陆。
事实上所谓“后崛起”的诗人不管多庞杂,他们存在的最大合理性就是在通常最不像有诗的心灵深处发现了诗。他们连舒婷、北岛都不追随,就不要说公刘和李瑛了,也许他们选择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把这些不像诗的诗写得比舒婷、北岛更像诗。
扩大诗的审美疆域,提高诗的审美价值,这是历史对他们的要求。他们也心雄万夫,以超迈前贤的姿态自豪地歌唱着,但是这个任务太艰巨了,完成这个任务的必然是一个文化巨人,光有一点得自于天的聪明才智,只能小打小闹一番。要全面超越前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必得囊括前人的审美经验,而这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甚至需要学养的,把这个任务看得太轻易只能使自己的才智的潜在量受损。
任何一个流派都是一种审美经验的定向积累,每一个流派都刻意超越其他流派,但是一切流派是否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主要看它的审美经验积累是否达到某种饱和度。这种饱和度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继承的饱和度,一个是发展的饱和度。互相反对的流派的健康发展是以互相渗透为前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任何一方面的发育不良,都有碍于孕育超越前贤的巨匠。这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是有过经验教训的。
中国新诗对于古典诗歌的艺术革命是一次迟到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艺在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那里远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成熟,成熟浪漫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到临界点,还不具备向自身的反面转化的条件,象征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就吸引了中国新诗领域中最有才智的后来者,如冯至、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和艾青,因而造成了浪漫主义诗艺的发育不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国革命诗人中的殷夫、蒋光慈、蒲风,“七月派”诗人绿原、鲁藜、阿垅都选择了在艺术上发育不良的浪漫主义直接抒情,他们最拿手的是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想象。其结果是这么一大批诗坛精英以毕生精力奉献于激情,却没有为世界浪漫主义的激情诗艺作出新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诗艺领域中,在表现生命体验和生活深度上作出突破的是艾青,艾青比戴望舒更进了一步,他比他同时代的革命诗人在审美体验上有更多的发现和创造。中国的象征主义诗艺不像浪漫主义那样发育不良。艾青正面表现了西方象征主义者表现不了的革命历史内容,他在象征主义的雕塑美与浪漫主义的热情倾诉的结合上,大大超过了拘守于现实主义的臧克家。正是因为这样,他无愧于中国新艺术基础的真正奠定者,同时他的诗又是世界象征主义的独创的发展。但是正当艾青风华正茂、潜在能量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时候,客观形势的发展又推动着艾青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匆忙地进行诗艺的自我否定和大幅度的革新,其结果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艾青的一系列实践性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九叶集》诸诗人如穆旦、杭约赫、陈敬容、袁可嘉、唐湜、唐祁,力图坚持他们原来的艺术立场,迫于政治形势,其结果是不得不夭折。
西方浪漫主义经过上百年的积累才达于成熟,产生了拜伦、雪莱、普希金那样的巨星。我国新诗的浪漫主义诗艺还处在成长阶段,象征主义正在走向饱和,还远远没有达到超成熟的阶段,却由于社会形势的逼迫,过早中断了诗艺的积累过程,因而二者都没有达到饱和。代之而起的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但是李季所开拓的审美体验,也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阶段,客观形势的发展又使李季失去了达到成熟的把握。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轻率地丢开了他驾轻就熟的想象规范,其结果是艺术上陷于困境。李季所开拓的道路后来为几个在才智上远不及李季的诗人所继续,其结果是强制性的行政力量也挽救不了它趋向衰亡的结局,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过分匆忙的更替导致了两败俱伤。
艺术是一种审美心理体验的传达,可是审美心理并不完全像克罗齐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个人自发的直觉,并不是任何直觉都能符合诗的审美规范的。要提高艺术直觉的审美价值,需要一个积累过程,要产生巨星则更要审美经验达到饱和。这个过程有时是缓慢的,特别是在古代,从沈约发现了四声可用于诗律的创造,到盛唐写出成熟的近体律绝来,其间经过了四百年左右的时间,现代的发展自然会快些,可是仍然与生活的发展不成比例。从“五四”时期胡适提出中国古典诗歌以“顿”为节奏单位,闻一多追求诗的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诗人、语言学家陆志韦提出诗行旁边加重点的节奏形式,林庚提出“半逗律”(似从法语诗律演化来),何其芳提出现代格律诗,毛泽东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许多年过去了,新诗连一个外部节奏形式还没有建立起来,至于其他方面如内部情绪节奏、意象、整体结构等等,都无从提上日程。
如果新诗不是这样匆忙地热衷于流派和形式的更迭,如果新诗更注意各种流派审美经验的饱和积累,如果新诗的发展更稳健些,新诗就不用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进行浪漫主义的“原始积累”,也不用在70年代末期重新进行象征派和意象派的启蒙了。
今天我们新诗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各种流派甚至同一流派之内不同风格之间审美经验的饱和度不足的问题。出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今天比昨天更加强调了排他性。不过过去的排他性主要是政治的,而今天则集中在审美范畴之中。历史已证明,没有排他性,不成流派;但过度的排他性必然导致狭隘和肤浅。对于后崛起的诗人们来说,这一点,似乎特别应该引起深思。由于排他性的泛滥,流派变得很小,有时一个旗号下只有几个同道。这样是不利于审美经验的积累的。这就导致了直到今天,后崛起诗人还没有产生一个辉煌的代表,每当我读他们那些闪耀着才智的诗作时,时常想起唐太宗对曹操的评价:“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独树一帜的才气,但是没有一个人让我感到有继往开来的伟大气魄。他们似乎还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个时代全部诗艺的总代表。今天,我们应该呼唤那种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囊括一切流派的大家风度。如果他们有一种百川归海的历史自觉性,他们就不会那么偏激地宣布“舒婷、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审美经验的积累要达到饱和,不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心灵纵深层次的探索和社会生活的探索结合起来呢?孤立地探索心灵固然是对过去孤立地强调外部社会环境的惩罚,但是孤立强调内心深层的探索难道就不会引起另一种惩罚吗?在无情的历史辩证法面前,最聪明的办法是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个主张即使有限地得以实现,我想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当前流派嬗变过速所造成的各种流派乃至风格的审美经验不饱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