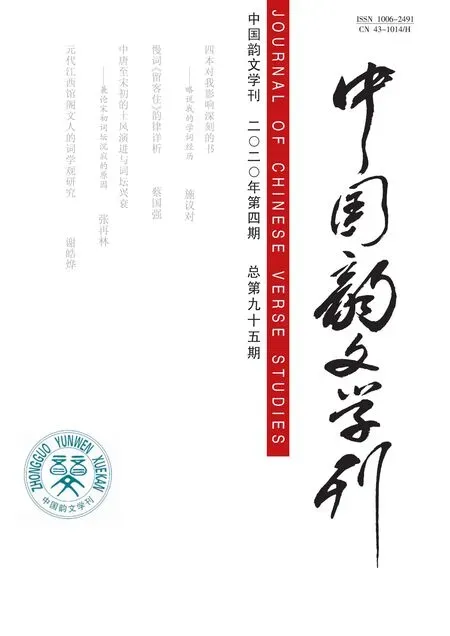新旧之间:刘大白诗经学发微
(1.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湘潭大学 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棪,系“五四”时期著名的“浙江四杰”之一、“浙江文坛三叛徒”之一与浙江一师“四大金刚”之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开创者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在文学创作及诸多学术领域(如文学理论、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学和数学)均有独特贡献。其中,刘大白关于《诗经》及诗经学的探究是我国现代诗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他徘徊于“新”“旧”之间的学术特质颇能代表现代转型时期诗经学的基本面向,但目前学界对此重视程度不够,故有必要进行梳理、厘定,以呈现其面貌,彰显其价值。
一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的转关,也是文化演进与学术思潮的重要节点,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等复杂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学术,面临深度变革与整体转型。随着欧风美雨不断渗入,文化现代性追求成为时代洪流,而数千年传统文化被视为走向现代性的根本阻碍,因此,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借来自西洋的“科学”大旗,猛烈抨击传统思想与学术。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文本载体是古籍经典,因此,具有革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对古籍的质疑辨伪达到了中国历史最高峰。
经是传统文化的根干与核心。《诗经》居六经之列,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刘勰《文心雕龙·宗经》),长期被奉为神圣“经典”,传统学人关于《诗经》的解读、阐释也常被现代知识分子认为带有强烈的封建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疑经辨伪,试图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命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彻底批判与全面怀疑。就《诗经》而言,以古史辨派学者为中心展开了“诗经大讨论”,加之“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关于《诗经》文学研究的卓越见解,揭开了‘现代诗学’崭新的序幕”。[1](P648)作为“现代《诗经》研究的先驱者”(赵沛霖语)的胡适,立论大胆、新见迭出,尤其是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顾颉刚立足考辨,对《诗经》尤其是儒生解经进行了全方位质疑,目的在于“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2](P22)。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等著述中持一分为二立场,肯定《诗经》的艺术性,批判其局限性,他还对《诗经》的时代、编订、流传及孔子删诗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沫若的《诗经》研究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创了《诗经》的今译,其《卷耳集》是第一个《诗经》今译本。郭沫若还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诗经》,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对《诗经》的年代、编订、史料价值及文学价值等进行了阐述。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成果丰硕,他在传统考据学基础上,结合文字学、史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形成了其独有的研究方法与体系,对《诗经》进行了多维考索,并为现当代《诗经》研究提供了具有示范效应的方法范式。由此可见,《诗经》学是当时学术探究的重镇,也是有关传统文化论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刘大白正是在此背景下加入讨论中,成为古史辨派“诗经大讨论”的一员。
刘大白出生于绍兴平水镇一大户人家,作为长子长孙,他被寄予光宗耀祖的厚望,自幼便浸淫于传统文化之中,“三岁起,由祖父教读。六岁时就读于孙旿堂先生,九岁开始学作诗。后从陈莲远师(名畴,旧会稽县学廪贡生)学习制艺试帖律赋”[3](P2)。其父金佩卿甚至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书房,名曰“水晶房”,希冀他走上科举功名之路。由于父亲要求极为严苛,刘大白觉得自己是“监狱”(指书室)中的“小囚犯”,甚至自缢以示反抗。这种严格甚至近乎残忍的家教于其天性或许有不少伤害,但也使刘大白熟读经史子集,对传统文化有非常深入的了解。陈觉民指出:
他幼年在家塾时,《十三经》是成诵的。清末科举,改八股文为策论,我见过大白考书院的试卷,署名还是金庆棪。文章里运用史实贯穿自如,可知于“四书”、《资治通鉴》等书也是寝馈甚深的。至于历代的诗文、词曲专集,在大白房间的插架上,至少在八九百种。[4](P25)
由此观之,刘大白广博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其日后开展传统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石。同时,在枯燥的经史制艺学习之余,刘大白常私下偷阅《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闲书”,这使他对文学的理解日益加深,尤其是培养了他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与鉴赏力。如他读完《红楼梦》后作《读石头记》诗云:
花谢春成劫,风流梦忽醒。
有情方许读,无字不通灵。
悟境参虚白,奇书亦汗青。
美人香草意,俚语续骚经。[5](P2)
由此诗可见,刘大白充分认识到情感思维在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中的基础性地位,文学创作须有所寄托,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情感表达出来。对文学思维的深刻认知,为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与开展文学批评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因为深厚的古文功底,刘大白于1909年考取拔贡,但随着时代风云变幻,他不断接受新思想,走上革命之路:留学日本、加入光复会、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衙前农民运动、倡导妇女解放、提倡白话文、创作新诗,且积极宣传革命理论,推动文化革新与文学革命,因此,传统文化积淀在“五四”时期的刘大白身上成为一种急于摆脱的“负担”,这也显示出他与过去告别的决绝和破旧立新的态度。陈望道指出:
他最憎恨自己因袭的经历,尝把彼比之猛兽,尝对我叹息于摆脱不能尽净。……而他底诅咒一切旧有的不良,据我所知也便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在这一点上,有惊人的胆量,兼有惊人的毅力和能力。[6](P207)
因此,正是由于急于摆脱沉重的文化负担,刘大白义无反顾地加入批评传统文化的时代大潮中,这在其《诗经》阐释中亦有所体现,加入古史辨派有关《诗经》问题的讨论便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刘大白有关《诗经》及诗经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白屋说诗》一书中,另外,《旧诗新话》、《中国文学史》及《中诗外形律详说》也有不同程度论及。
二
胡适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认为,研究《诗经》主要有训诂和解题两个主要路径。而在具体研究中,因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学术造诣、指导思想有别,其切入点与研究方法必然有所不同,刘大白亦从不同侧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究《诗经》。
(一)文学鉴赏
由于刘大白摆脱了经师释《诗》藩篱,视《诗经》为纯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诗),加之其极高的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力,因此,从文学角度进行鉴赏式批评是刘大白《诗经》阐释的主要路径。如《齐风·鸡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
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7](P737-738)
《小序》认为是“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7](P737),刘大白斥责《小序》所言系“白日见鬼”,并从文学鉴赏角度对之进行解读:
这是一位官太太在一个五更头想她上朝去的丈夫,希望他早点回来,再合她一同睡觉。她渴盼她底丈夫回来,有点神经错乱,发生错觉了。她听到了苍蝇之声,以为鸡儿在叫了,这时候朝廷上已经人满了,早朝快要完毕了,她丈夫就可以回来了,然而不然。她看到了月出之光,以为东方日出了,这时候朝廷上已经光昌了,早朝快要散退了,她丈夫就可以回来了。然而又不然。于是她有点怨了。她说“虫飞薨薨的时候,我愿合你再睡一觉;也许你将要回来了吧,希望你不要尽管不回来(疑有讹误——引者注),使我憎嫌你”!这不是怨她底丈夫“孤负香衾事早朝”吗?[8](P9-10)
可见,与《毛诗序》以道德伦理视野、强调政治功用的解《诗》旨归迥乎不同,刘大白通过文学鉴赏、艺术分析来归纳诗旨。他对其他诗篇(如《关雎》《静女》《绸缪》《柏舟》等)的解读亦如是。
(二) 文字疏释
由于时代、地域及文化背景等原因,《诗经》中的很多字词难以被后人准确理解,故文字疏释是解读古代典籍的基础与前提。近代研究者在《诗经》文字疏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少公案得以解决,刘大白就是其中之一。
刘大白有关《诗经》文字疏释影响最大的是关于《邶风·静女》中“彤管”与“荑”的讨论。顾颉刚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七期发表了《瞎子断扁的一例——〈静女〉》一文,拉开了此次讨论的序幕。顾颉刚认为,《静女》诗中“贻我彤管”中的“彤”是“丹漆”,“自牧归荑”中的“荑”则是一种植物,且“彤管”与“荑”为二物。刘大白对顾颉刚的解释提出质疑,并在《语丝》第七十四期发表《关于〈瞎子断扁的一例——静女〉的异议》一文开展讨论,他说:
你把彤字说成丹漆,还难免拘泥于古训。我以为彤就是红色,彤管就是一个红色的管子。这个红色的管子,就是第三章“自牧归荑”的“荑”。[8](P89)
也就是说,他视“彤管”和“荑”为同一物,并引《左传》、《毛传》及郭璞、梅尧臣的诗歌进行论证。郭全和、魏建功、董作宾也参与了这场讨论。刘大白通过翔实、充分的举证和分析,让顾颉刚惊呼“二千余年的曲解,一朝揭破,大快,大快!”[9](P524)刘大白的解释不仅在当时力压众论,极具说服力,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是解释“彤管”“荑”颇具参考价值的观点。
另外,他对《绿衣》《卷耳》《关雎》《遵大路》中的字词也有疏解,且多自出机杼、新见迭出,兹列举如下:
《小序》解释《邶风·绿衣》诗旨为:“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7](P625)朱熹也同意《小序》的解释,并认为“间色”绿色比喻“贱妾尊显”,以“正色”黄色喻“正嫡幽微”。[10](P25)刘大白则认为,二者均系“神经过敏的无稽之谈”,其原因在于,对“我思古人”中“古”字的错误解释,他指出,“古”应做“故”解,因此,《绿衣》可被视作悼亡诗。
《小序》释《周南·卷耳》乃“后妃之志”,刘大白斥其为“向壁虚造”。他认为,“嗟我……”和“我姑……”都是思妇自指,是单数的“我”。而“我马……”和“我仆……”则相当于“咱们”,是复数的“我”,因此,《卷耳》实际上是一首思妇想念外出丈夫的诗。
《周南·关雎》中“左右流之” “左右采之”“左右芼之”的“左右”,旧说解释为方向,刘大白指出,其实“左本作,右本作又。”[8](P12)“左”和“右”应分别是左手和右手,诗句应解释为用左右两手流之、采之、芼之,而不是左右来回的意思。
《毛传》释《郑风·遵大路》 “掺执子之袪兮”的 “掺” 为“揽”, “不寁故也”的“寁”解为“速”,刘大白指出,“掺”“寁”不是动词而应是人称代词,即“我”,二字同字异形,都是假借字,均系女子自称。
(三) 音韵探究
刘大白在诗歌音韵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著有《中诗外形律详说》一书,该书被学界称为二十世纪“第一部现代形态的中国诗学研究著作”[11](P131),在中国诗歌音韵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刘大白除了在该书中讨论《诗经》音韵之外,他还撰有《〈毛诗〉的用纽》《〈毛诗〉以后的停身韵》《从〈毛诗〉到〈楚辞〉》等文讨论《毛诗》的韵律问题。他认为,《毛诗》的用纽包括外形律中的整齐律、参差律、次第律、重叠律及反复律中的纽反复律、韵反复律、语反复律。用韵可分为停头韵、停身韵、停尾韵三类,与之相应,用纽亦有停头纽、停身纽、停尾纽。在《毛诗》时代,用纽的反复律与和用韵的反复律并行,后来被淘汰,同时,停身韵和停头韵、停尾韵本也是并行的,后来也被淘汰。由于刘大白关于韵律的诸多术语多属自创,需结合其特有界定与具体文本阐述方能理解。
此外,刘大白还以《毛诗》中的无韵诗反驳章太炎“有韵为诗,无韵为文”之说,他以《棠棣》《车攻》《清庙》《维天之命》《时迈》等为例,说明旧诗并非全是有韵,此论实际上给当时白话诗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意味着刘大白研究《诗经》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新文化、新文学张本。如胡适曾用《生查子》词调作白话小诗: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12](P48)
胡怀琛认为,诗中双声叠韵的用法和句中用韵不当,胡适则说这是一种尝试押韵法。刘大白从《毛诗》中举出许多例子反驳胡怀琛的观点,认为胡适此诗用韵并无问题。
(四) 民俗解读
《诗经》(尤其是《国风》)中有大量反映民风民俗的作品,但由于古人多以为《诗》有所托寓,故常从政治、道德、伦理角度切入,无疑忽视了其民间维度。近现代《诗经》研究于此有明显突破,刘大白也常以民风、民俗论《诗》。如《小序》释《唐风·绸缪》为“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7](P772),而刘大白对古说不以为然,将其视之为一首闹房诗。他以我国各地民间婚姻习俗为据指出,通读《绸缪》只觉诗中戏谑玩笑味道,未有晋国乱象。他通过征引浙中、北京和山西的闹房习俗,联系此诗中的闹房。刘大白提出,绍兴婚礼中“柴新郎、炭新妇”礼节与诗中“绸缪束薪”相合,一柴一炭正和“束薪”相似,或许正是“绸缪束薪”的遗风,抑或受《毛诗》的暗示演变而来;“至于‘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现在演变而为挂起福禄寿三星图,而被新郎新娘所拜了”[8](P14);诗中“今夕何夕,见此……”“子兮子兮,如此……”分别是赞美新娘和戏谑新郎的话,与闹房情景颇为相似,洞房花烛夜的欢愉喜乐场景跃然纸上。从民俗角度解读《绸缪》虽有推测意味,但与传统研究路径截然不同,对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审视《诗经》颇有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五) 以史证《诗》
诗史互证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常见的批评方法,刘大白常从历史记载中广征博引与《诗经》进行对比、印证。如他引《国语》证《小序》释《鄘风·柏舟》所言不符史实,《小序》言《柏舟》为:
《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7](P659)
刘大白提出,《国语》和《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载与《小序》所称相悖。《国语》称“卫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以自儆”,而据《史记》记载,他在位五十五年,即使九十五岁离世,即位时也已四十一岁,而共伯为武公兄长,年纪必大于他,死时至少四十多岁,这与《小序》所言“蚤死”明显不符。刘大白还指出,《史记·卫康叔世家》说“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小序》却仍称他为“卫世子共伯”,既为君主为何仍称世子?且“世子底妃,又何至为父母夺而嫁之?”[8](P18)因此,他断定《小序》所言与史不符,系穿凿附会之言。另外,在有关《邶风·静女》的讨论中,刘大白也常征引《尚书》《左传》中的历史典故或史料来论证其观点。
(六)现代视角论《诗》为中国诗歌之源
以《诗》为诗学楷式在中国历代诗论中屡见不鲜,其中,视《诗经》为诗类文体的源头更是比比皆是。同时,自汉代起,便已形成“同祖风骚”(风代指《诗经》,骚代指楚辞)的诗源论,这一看法延续至近现代诗学,只是传统以《诗》为式遵循“文本于经”的思维模式,而近现代则仅就文学传统的演进而论。刘大白也将《诗经》与楚辞视为中国诗歌的源头:
《楚辞》本是咱们所认为诗篇底别派,跟《毛诗》并峙,为中国文学底两大河源的。[13](P14)
(《楚辞》与《毛诗》——引者注)为后来一切诗篇,辞赋底祖先。这正如星宿海为北方黄河之源,犁牛石为南方长江之源,是中国两大河流底发源地。[13](P16)
《毛诗》和《楚辞》,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祧之祖。[13](P61)
《诗经》与楚辞犹如长江、黄河之源,溉泽整个中华文苑。《诗经》与楚辞虽然共同被视为中国诗赋类文体的源头,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历代诗论家于此多有阐发。刘大白在前人基础上,从地域、时代、民族、作者、辞采、内容、作者、书写对象、体制诸维度指出了二者的差异:《毛诗》是北方文学的代表,《楚辞》是南方文学的代表;《毛诗》是春秋及以前时代的作品,《楚辞》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毛诗》是汉族文学的代表,《楚辞》是非汉族文学的代表;《毛诗》可称为无名诗人的总集,《楚辞》是屈原等人的总集;《毛诗》质朴,《楚辞》绮艳;《毛诗》多写实际生活,《楚辞》多含玄虚神话;《毛诗》比较整齐,《楚辞》比较参差;《毛诗》较短,《楚辞》较长,这种比较显然较为全面。但与传统诗论通常视楚辞为《诗经》苗裔不同,刘大白认为,二者地域、民族不同,各有渊源,否认楚辞源自《诗经》。
三
刘大白还对诗经学史上的一些学术公案进行了讨论,一方面,他并不认同“六义”说及《小序》,但另一方面,他又赞成“孔子删诗”说。
(一)“六义”新释
“六义”出自《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7](P565)系《大序》作者在《周礼·春官·大师》“六诗”说基础上演绎而来。关于“六义”的具体所指,刘大白继承自孔颖达以来的“三体三用”说,即风、雅、颂是诗歌体裁,赋、比、兴是艺术手法,“风、雅、颂三项,是诗底分类;赋、比、兴三项,是诗底作法”[8](P1)。刘大白还特别注意到“六义”的排列次序并非按照“三体三用”的先后排列,他从音韵学角度对此做出解释,认为《大序》作者依照发音将六义分为两类:
古代没有轻唇音,风、赋两音,都属帮纽,合比字同一发音;颂字本来就是形容的容字,而古代喻纽归影,容读影纽,合雅字也是同一发音;兴属晓纽,和影纽不过深喉浅喉之别。[8](P1)
历代于“六义”语序之讨论莫衷一是,刘大白以发音言之,似前所未闻,虽非不易之论,但为释“六义”提供了一种可能,且符合当时从“科学”角度释古的潮流。
同时,刘大白还对“赋比兴”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赋是敷陈,比是譬喻”,其中,在“赋” 的使用场合,所敷陈事物与诗人情志“混合在一起”,也就是密切相关,如《周南·卷耳》;在“比”的使用境域,所比之物与作者情志“相对列”,但有一点是二者共有的,如《周南·螽斯》中的“螽”与人在多子孙这一点上具有相同性。“兴”最难阐释清楚、明晰,刘大白视之为一首诗的起头:
兴就是起一个头,借着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相接构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换句话讲,就是把看到听到嗅到尝到碰到想到的事物借来起一个头。这个起头,也许合下文似乎有关系,也许完全没有关系。总之,这个借来起头的事物,是诗人底一个实感,而曾经打动诗人底心灵的。[8](P1)
刘大白还举《关雎》《草虫》《汝坟》《燕燕》为例,说明起兴之物与诗人情志无必然联系即是“兴”。以诗中所言之物与作者情志联系的紧密程度来区分“赋比兴”,为辨析它们的区别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且深化了对“赋比兴”的认知,不乏学术价值。但在具体阐释中,情况显然更为复杂,尤其是所谓情感关系的有无与紧密程度亦因阐释者不同而言人人殊。
(二)解《诗》反《小序》
《小序》作为《诗经》汉学的重要成果,是汉唐诗经学解析《诗经》主旨的基本依据,自《诗经》宋学的代表成果——朱熹《诗集传》出现以后,方打破了《小序》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后,儒生解《诗》或袭《小序》,或依朱《传》,或折中二者。但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猛烈抨击,其显著标志便是经学的独尊地位不复存在,《诗经》阐释者迫切希望将《诗经》从经学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传统解《诗》依据招致全面质疑。其中,梁启超、郑振铎等人对《毛诗序》(包括《大序》和《小序》)进行了猛烈攻击:
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矣。[14](P75)
(梁启超)
《诗序》之说如不扫除,《诗经》之真面目便永不得见。[15](P390)
(郑振铎)
由此,民国初年学术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诗序》运动,刘大白曾参与古史辨派关于《诗经》的讨论,因此,他顺应时代潮流,解《诗》也反《毛诗序》。同时,他对朱《传》亦并不认同,显示出他试图与传统经学决裂,这对深受传统文化浸淫的刘大白来说颇为不易,但也显示出其时学术破字当头的底色。
在传统《诗经》阐释者看来,《诗经》是有所寄寓的,尤其是《毛诗序》试图以美刺解《诗》,并以此来实现“正夫妇,成孝敬,美教化,移风俗”之功效。这一经学话语模式与阐释路径影响至深至远,如章太炎认为:
古人作诗托男女以寓君臣,《离骚》以香草美人比拟,也同此意。朱文公对于《诗序》(唐时《本事诗》相类)解诗指为国事而作,很不满意,他迳以为是男女酬答之诗,这是不可掩的过。[16](P27)
由此可见,章太炎依然谨守《毛诗序》话语体系与阐释路径,而刘大白对章太炎这一观点直接进行了批驳,他指出:
自从读古人作品的,存了一个“古人作诗,托男女以寓君臣”的成见,不知埋没了多少抒情诗。……这个“托男女以寓君臣”的成见,实在是中国旧文学中抒情诗的坟墓。如果要整理中国旧文学,使旧体抒情诗底“木乃伊”,有重见天日的希望,非掘去这个成见的古墓不可。[17](42-43)
将《毛诗序》为代表的话语阐释体系视为中国古典抒情诗的坟墓,如欲还抒情诗的本来面目,非掘墓不可,可见其攻击之激烈。刘大白虽然反对朱熹将《郑风》视为“淫奔之诗”,但认为比“托男女以寓君臣”好得多,原因是朱熹对《国风》抒情性的发现,是对《小序》的翻案。可见,《小序》以美刺解《诗》漠视抒情性,是招致刘大白批判的根本原因。
将《诗经》视为文学作品而不是有所寄寓的神圣经书是现代诗经学与传统诗经学的根本分野。近现代以来的反《诗序》运动,其立论基点就是将《诗经》以文学作品视之,《小序》自然在“打倒”之列,鲁迅、顾颉刚、闻一多、张寿林、陈槃等都将《诗经》视为诗歌(歌谣)集。刘大白也不例外,他认为《诗经》是中国旧诗歌的代表,抒情诗是诗中之花,而《诗经》(尤其是《国风》)大多是抒情诗,但是“有些向来被一班腐儒,不是指为淫奔之诗,就是指为托男女以寓君臣,把它们埋没在荆棘中罢了”[13](P35)。由是,他以《关雎》《有狐》《绿衣》《葛生》《鸡鸣》《卷耳》《遵大路》《柏舟》等诗为例,对《小序》妄生美刺和朱《传》“淫奔”之说进行批驳。如他指出,《卫风·有狐》是一首男子出门打猎时忧心家中妻子或未婚恋人的诗歌,而《小序》“刺时”说和朱熹“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均不合诗旨,因为“《小序》和《集传》,偏要凭空弄出些‘失时男女’和寡妇鳏夫来,这个弯子,不知绕到哪里去了”[8](P15)。反对传统解《诗》的穿凿附会,从文学(尤其是抒情)角度分析《诗》旨贯穿刘大白《诗经》阐释的始终,也是其解《诗》的标签。
(三) 赞成孔子删诗说
《诗经》现存三百零五篇,但古说《诗》原有三千余篇,系孔子删定而为三百余篇,故称《诗三百》。孔子删诗之说,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18](P2463)
汉儒信此说,如班固、郑玄都支持孔子删诗说。至唐孔颖达始提出异议:“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7](P556)后世探讨这一学术公案者代不乏人,且争论持续至今。
近现代时期,由于批判传统文化成为时代主流,因此,反对孔子删诗说占据上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顾颉刚、钱玄同等都反对孔子删诗说。但刘大白则支持孔子删诗说,其《中国文学史》明确提出“孔子删诗”,“(《诗经》——引者注)虽然曾经孔子删削,秦火燔烧(专就《毛诗》说),而毕竟因为孔子曾经选成定本,把它教授弟子的缘故,传播较广”[13](P27),其依据是:
我以为周代特设采《诗》的专官,所采的自然不止三百篇;这三百篇的诗,是孔子所选的诗歌读本,把它来教授弟子的。所以“虽多亦奚以为”的这个“多”字,正是指三百篇以外的诗而言;而“诵《诗三百》”就是指自己底选本而言。[13](P29)
采诗官采诗不止三百篇,流传至今的《诗经》是孔子为教授弟子所删选的诗歌读本,这是他对孔子删诗说的基本态度。这与当时主流《诗经》学观点有别,尤其是与古史辨派的基本观点对立。主流话语反对孔子删诗说,一则是认为孔子删诗缺乏充分可靠的文献依据,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试图以此批判以孔子为象征、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刘大白赞同孔子删《诗》,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徘徊于古今之间的文化立场。
另外,刘大白对大小《雅》的划分及风雅正变说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大序》作者认为,划分大小《雅》以政事大小为依据,而刘大白认为,以音乐区分可能更为合理,以音乐划分大小雅实则渊源有自,郑樵、戴埴、惠周惕均倡导以音乐区分大小雅。《诗大序》还有著名的“风雅正变”说,在《诗序》作者看来,变与正相对,时世由盛而衰,政教纲常崩坏,诗歌也随之变化,反映变乱社会的《诗》称之为“变风”“变雅”,但刘大白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可信。
结语
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刘大白的诗经学是现代诗经学转型时期的重要成果。其研究涉及范围广,无论是《诗经》还是诗经学公案均有讨论;研究视角与方法不拘一格,尤其注重运用现代科学理念与方法;在思想倾向方面,刘大白的《诗经》阐释总体而言是为新文化、新文学“呐喊”,但并非一味否定、破字当头,如在孔子删诗问题上便与当时主流观点有别,这显示出他徘徊于“新”“旧”之间的思想立场。以批判传统来显示其文化态度与价值认同,是“五四”知识分子常用的话语建构方式与言说模式,刘大白亦如是。建构新文化是其根本宗旨,解构传统是其基本路径,但急于摆脱传统却又在根本上无法彻底告别,或许是“五四”知识分子面临的文化悖论,当然也由此凸显了其精神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