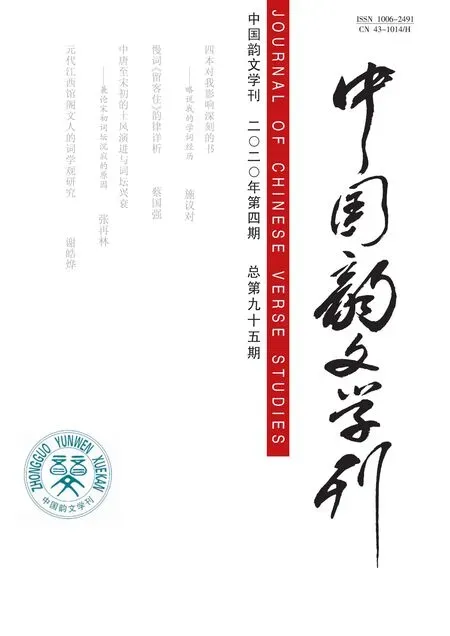成公绥《慰情赋》题名考辨
——兼论汉晋言志赋的体系问题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重庆 400030)
《文选》卷三十谢朓《观朝雨》诗“戢翼希骧首”句,[1](P430)李善于下引成公绥《慰情赋》曰:“唯潜龙之勿用,戢鳞翼以匿影。”同样的注文还出现在《文选》卷三十六,任昉《宣德皇后令》“隐鳞戢翼”句,只是出处却成了成公绥《慰志赋》(李善注前引曹植《矫志诗》“仁虎匿爪,神龙隐鳞”)。[1](P504)“唯潜龙之勿用,戢鳞翼以匿影”为成公绥《慰情赋》仅存残文,全貌如何,惘不可知。可注意之处,唯李善对成公绥赋题产生的舛错。严可均《全晋文》辑录成公绥《慰情赋》,于题下注有小字:“一作《慰志赋》。”[2](P1795)说明严氏对李善注之舛错亦未深思,且于赋题之选择,更偏向《慰情》。又范子烨于其《魏晋之赋首——成公绥考论》一文之注释云,成公赋“实际上构成了从张衡的《定情赋》和蔡邕的《静情赋》到陶渊明的《闲情赋》的中间环节之一”[3](P205),是则径将《慰情赋》置于《闲情赋》谱系中来定位。
林晓光在《〈闲情赋〉谱系的文献还原——基于中世文献构造与文体性的综合研究》一文中将“赋情”作品还原为两大谱系,一以张衡《定情赋》为源头,以陈琳《止欲赋》、应玚《正情赋》、陶渊明《闲情赋》为衍生文本;一以蔡邕《静情赋》为源头,以王粲《闲邪赋》、阮瑀《止欲赋》和曹植《静思赋》为同一谱系下的衍文文本,另又论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江淹《丽色赋》等同一“美妇人”或“赋情”(1)这里的“赋情”之“情”特指对女性之情,下文“言情”之“情”义同。主题的作品实际上并不在《闲情赋》谱系之内。[4](P204-214)成公绥的《慰情赋》若果为《闲情赋》谱系的中间一环,那么它又会是处在哪个环节呢?
览汉至晋赋作,可发现以述宾结构词组命名的赋作数量颇为可观,如《定情赋》《正情赋》《显志赋》《述志赋》等,在成公绥之前,又已有东汉崔篆《慰志赋》,魏陈思王《慰情赋》,李善作注时出现“慰情”和“慰志”的舛错,似乎也情有可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诸如《闲情赋》等系列赋作,虽存在不同谱系,而实际上都是同一母题——“美妇人”之下的文体衍生。从最初的《登徒子好色赋》《美人赋》,到《闲情赋》甚至更后期的作品,经过历代文人的创作或拟作,中古文人渐渐产生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拟题方式,即这些作品大多都以“述语+宾语+赋”的形式来题名。由于以异性的身份表达对“美妇人”的情感,因此“宾语”不外乎“情”“欲”“思”“邪”“愁”“色”等,“述语”则是自如变换的,于是这些赋名便呈现出“述语”和“宾语”之间自由组合的现象,如张衡《定情》、应玚《正情》、陶渊明《闲情》,陈琳、阮瑀《止欲》,曹植《静思》、阮籍《清思》,王粲《闲邪》,繁钦《弭愁》,江淹《丽色》,等等。但无论这些“述语”与“宾语”如何组合,据现存资料观之,“美妇人”母题下的衍生作品没有一篇将“志”纳为赋名中的“宾语”。尽管不能说绝对不存在以“述语+志赋”为名的“美妇人”赋作,可以肯定的是,进行“美妇人”母题创作的中古文人普遍不会用“志”来题名;同样,言志之赋,也普遍不以“情”字作题,凡以“述语+情赋”为题的赋作,多为“美妇人”主题。(2)其中曹植《慰情赋》和傅玄《矫情赋》或属例外,二赋均只残存一句序文。《慰情赋序》曰:“黄初八年正月,雨,而北风飘寒,园果堕冰,枝干摧折。”(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十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15页)无法判断是言志主题还是“美妇人”主题。《矫情赋序》曰:“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赋》,又命陈徐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烂然成章。”(严可均:《全晋文》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25页)当与“美妇人”主题无涉,但此篇当属众汉晋赋少有之例。[2](P1715),[5](P1125)由此看来,“言情”之赋和“言志”之赋,在中古文人的观念中似乎泾渭分明。因此,成公绥所创作的究竟是《慰情赋》还是《慰志赋》,实际上是不可以《文选注》抄写之误而轻率下论的。
那么“言志”之赋,又呈现出怎样的现象呢?是否又如“美妇人”母题言情赋所衍生的赋作一样存在着不同谱系?成公绥赋若是《慰志赋》,会是言志赋中的哪一环节?欲解答这些疑问,可从陆机《遂志赋序》论起。
一 汉晋言志赋体系
《遂志赋序》曰:“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6]陆机作《遂志赋》时,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蔡邕《玄表赋》和张叔《哀系赋》,皆为可供参考的文献。从陆机所提示的言志赋雏形来看,崔篆《慰志赋》虽有“愍予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的时运不济之叹,最后也以“绝时俗”“守性命”[7]的出路为心中的郁愤做出调节,但为这种出路选择做出思想支撑的是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8](P77)的主张,如文中“静潜思于至赜兮,聘六经之奥府”“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扫轨”[7]云云,皆可为证。至如冯衍《显志赋》,同样“悲世俗之险阨兮,哀好恶之无常”,主旨却成了“昭章玄妙之思”。[9](P987-988)自此以后,班固《幽通》,张衡《思玄》,老庄味道愈发浓重。《幽通赋》曰:“所贵圣人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曹大家注:“至论,谓五经六艺所以贵之者,顺天性也。亦当以义断之,不可贪苟生而失名。”[1](P212)则已经把五经六艺纳入自然之义的范畴内。《思玄赋》所论之玄则更具儒学向诸子(老、庄、墨、杂家、方术、阴阳)拓展的趋势,具有“经学图式向义学理性的转变”。[10](P115)蔡邕《玄表赋》仅存残句,观其以“玄”题名,大概不出老庄柔弱全生之旨。
从陆机赋序中梳理的言志赋发展脉络来看,东汉以来名教与自然的界限在这些士人观念中渐渐变得含混不清。在这样的思想变化和士人心态背景下,早期言志赋在悲叹世俗险阨的情感基调下,已经明显体现出以老庄退守全身的思想作为最终出路的发展趋势来,也因此士人所言之志,自然而然地多申返朴自修之意。
迨至梁代萧统编《文选》时,赋类“志篇”所选四篇,除班固《幽通》、张衡《思玄》以外,乃张衡《归田赋》和潘岳《闲居赋》。从这些代表性的赋作来看,汉晋言志赋的文体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归田”体系,从先前仅仅只是“怀退”“思退”的思想的苗头,演变成“归田”“闲居”的实践。《归田赋》曰:“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1](P223),亦不过潘岳“退求己而自省”[1](P227)这类玄儒结合的归途。因此《文选》的选篇虽然说明了言志赋的体系范围有所开拓,大体还是以申“返朴自修”之意为本。
至唐初编《艺文类聚》,汉晋言志赋录有冯衍《显志赋》、班固《幽通赋》在内的14篇赋作,其中沿着冯衍“昭彰玄妙之思”发展的有曹植《玄畅赋》,“归田”一系则有潘尼《怀退赋》、陆机《怀土赋》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唐初类书所呈现的言志赋体系发生了变异。据陆机、萧统所展示的言志赋体系来看,言志赋通常包括“感叹世颓—时愿多违—返朴自修”的模式,但是到了《艺文类聚》的言志赋体系,感遇乞归的作品也被纳入这个原本抒发“士不遇”情怀的体系中,如刘桢《遂志赋》、韦诞《叙志赋》和傅咸《申怀赋》。这类言志赋一反“感叹世颓”之传统,多感怀明主隆恩,表达才不配位的歉疚,进而表达反身初服、乞骨告归之志。如提及感遇,刘桢《遂志赋》曰“幸遇明后”,韦诞《叙志赋》曰“蒙圣皇之宏恩”,傅咸《申怀赋》曰“何天施之弘普,厕瓦砾于琼瑛。备东宫之妙选,奉储君之圣明”。(3)刘桢《遂志赋》、韦诞《叙志赋》及傅咸《申怀赋》俱见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人部十,明嘉靖天水胡瓒宗刊本。[6]《艺文类聚》言志赋体系的这类变异还只是轻微的,更大的变异体现在《艺文类聚》所录的西晋枣据《表志赋》中。《表志赋》亦为感遇之作,但与前面提到的申返朴告归之志恰好相反,这里表明了“愿致主于陶唐”[6]的效力君主之志。于是言志赋体系,在《艺文类聚》的辑录下展示出错综复杂的面貌。
上文提及的陆机赋序和《文选》中所展示的言志赋模式,为“感叹世颓—时愿多违—返朴自修”,如果将这一模式设定为传统模式,陆机赋序体系和《文选》体系则为传统的汉晋言志赋体系,那么事实上《离骚》《九辩》,西汉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及稍后的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文体都符合这一模式。然而《士不遇赋》及《悲士不遇赋》又被《艺文类聚》录在“怨赋”一门,同一门类下尚有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婕妤《自悼赋》、丁廙《蔡伯喈女赋》和江淹《恨赋》。在此之前,《长门赋》《别赋》已出现在《文选》赋类“哀伤篇”中。虽说门类的划分和文章的录入,不同的系统有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从《长门赋》和《别赋》在《文选》及《艺文类聚》的不同定位来看,言志赋所包含的“感叹世颓—时愿多违”的结构模式,既可以为哀伤类赋作所采用,也适用于怨赋,这就使得选家所辟的“哀伤赋”一门和类书编撰者所辟的“怨赋”一门产生了交叉关系。
陆机的言志参考赋作,多申玄思;萧统的入选标准,则主返朴自修之志;《艺文类聚》则又不同。体系面貌如此扑朔迷离,以至于难以分辨哪一个才是汉晋言志赋体系的真面目,哪个是假象。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言志赋体系的建立,或多或少需归因于体系呈现者(创建者)身份的不同。陆机是文坛拟作时风下的创作者,他注重的是拟作的承袭与超越,于是言志赋由儒入玄的衍变,便在陆机的赋序中得到暗示。萧统是选家,作品的思想、辞采以及篇幅长度都是他的衡量因素,于是在众多主“返朴自修之志”的传统言志赋作品中,选中了《幽通》《思玄》这两篇与“玄妙之思”沾边的佳作,以及《归田》《闲居》这两篇“归田”类佳作;而《艺文类聚》作为类书,文本的割裂在此得到包容,文类的划归也都是为提供写作范本服务的,于是“言志”系中又衍生“怨”系,进而再与“哀伤”类作品牵连在一起。无论如何,仅仅从这三个视角来检视言志赋体系,就已经呈现如此驳杂的面貌,何况还有更多未能留存下来的汉晋言志赋未能加以参考分析,遑论言志赋体系的真面目了。
论述至此,可知言志赋体系复杂之程度,已很难像《闲情赋》一样还原出谱系来,因为《闲情》一类,是在“美妇人”单一母题下发生的文体衍生和变异,以中古文人的创作思维来还原谱系,是可以完成的。言志赋则不同,它是同一母题下先分化出不同子题,如由“士不遇”主题分化出“闲居”或“归田”乃至“乞归”主题,“不遇”的主题又演化为“哀怨”主题。同一子题之下的文本又构成互文性,如在“得遇乞归”主题的一脉,表达才不配位,感遇乞归时,魏刘桢《遂志赋》曰:“翼俊乂于上列,退仄陋于下场。袭初服之芜薉,托蓬芦以游翔。”晋傅咸《申怀赋》曰:“莫斯之任,求仁在我。将反初服,毕志训雅。……庶所乞之克从,永收迹于蓬庐。”[6]“初服”和“蓬庐”在言志赋中成了“乞归”的象征。更能加重言志赋体系复杂程度的是,同样的生成机制又发生在不同子题之间,以及母题与子题之间。如在论及黑白颠倒的险恶世道、表达时愿多违时,在传统言志赋中,夏侯淳《怀思赋》曰“信循道以从法,何世路之迍蹇。始絜操以迄今,每适道而靡违”,曹摅《述志赋》曰“纷迍蹇之若斯,何遭运之可常”[6];在“昭彰玄妙之思”言志赋一脉中,冯衍《显志赋》曰“何天命之不纯兮,信吾罪之所生”[9](P989),班固《幽通赋》曰“纷迍邅与蹇连兮,何艰多而智寡”[1](P209);在“乞归”主题一脉,潘尼《怀退赋》曰“何时愿之多违”[6];而在“士不遇”一支中,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曰“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6]。显而易见的是,文人面对生不逢时的情感表达时,似乎非常青睐于这种“何××之(而)××”的范式,在有意或无意中使之逐渐生成了一致的用法,从而加剧了言志赋体系之间的支离和连缀。如此看来,言志赋体系的变异,涵盖了主题、文体及文句三个层面,体系的错综复杂来源于三者的变异及三者之间的变换组合。也因此言志赋恐怕只能以“体系”论之,而很难以“谱系”论之,因为谱系是链条式、平面的,正如林晓光所还原的“美妇人”赋的两个谱系一样;而言志赋体系则是网状结构,如果用更形象具体的说法来说,则是以“言志”为核心而发散成的立体结构。
二 成公绥《慰志赋》及其体系定位
将汉晋言志赋体系梳理至此,再来重新审视仅存数句残文的成公绥赋。其曰:“唯潜龙之勿用,戢鳞翼以匿影”,此恰与表达感遇思效之志的枣据《表志赋》之“接鸣鸾之垂翼,因神虬之光鳞”[6]一句构成了互文性,只不过成公绥反其意而用之,表达的是退而守身之旨,而这正符合传统言志赋“返朴自修”的宗旨。虽然仅凭此残文不能下以绝对之论,但联系成公绥的出身、本传“闲默自守,不求闻达”[11](P2371)语、成公绥诸赋中频频申明的自然之义,以及造成西晋士人多不善终的环境,成公绥此赋为魏晋言志赋体系中之《慰志赋》,是情理之中的。
许结在《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文中将汉晋言志述理赋大致分为三类,分别为纯粹仿骚类,如贾谊《吊屈原赋》、扬雄《反离骚》等;答难论辩类,如东方朔《答客难》、班固《答宾戏》等;及最为丰富的赋体明理类,如写不遇与述行及直言志之类赋作。同时他也注意到,从这三类赋的创作体式来看,“赋史发展到魏晋时代,前两类比量明显减少,……而第三类则大量增多”[10](P115)。而这大量增多的第三类,恰好也呈现出以述宾词组为题名的倾向,这或许说明,汉晋人对言志赋渐渐形成了较为明晰的文体意识,而赋题的逐渐统一当是这种文体意识的体现。这又可以魏晋以来数量颇为可观的《×志赋》(4)如刘桢《遂志》,丁仪《厉志》,曹植《愍志》《潜志》,韦诞《叙志》,枣据《表志》,曹摅《述志》,陆机《遂志》等。为佐证。而李善在《文选》注中援引成公绥的这篇赋作时,前作《慰情赋》,后作《慰志赋》,会出现这样的舛错,恐怕正是其未意识到在汉晋时,言志主题和美妇人主题的两大类赋作往往以述宾结构词组为题,并且美妇人之赋绝不以“志”为题,而言志之赋又几乎不以“情”为题的缘故。明乎此,且又能了解汉晋言志赋体系之流变,严可均恐怕也不会对成公绥的这篇赋倾向于《慰情》之题。
综上所述,成公绥并无慰情之作,实有慰志一赋。观其《天地赋》“唯自然之初载兮,道虚无而玄清”,已是玄虚之义,“于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结体而括囊,浑元运流而无穷,阴阳循度而率常,回动纠纷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强”。[11](P2372—2373)《周易》曰:“括囊,无咎无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可见成公绥对《周易》的辞意非常谙熟,于是其《慰志赋》亦援引周易“潜龙勿用”之意。[12](P10-29)因此成公绥《慰志赋》,很可能是诸“昭彰玄妙之思”言志赋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