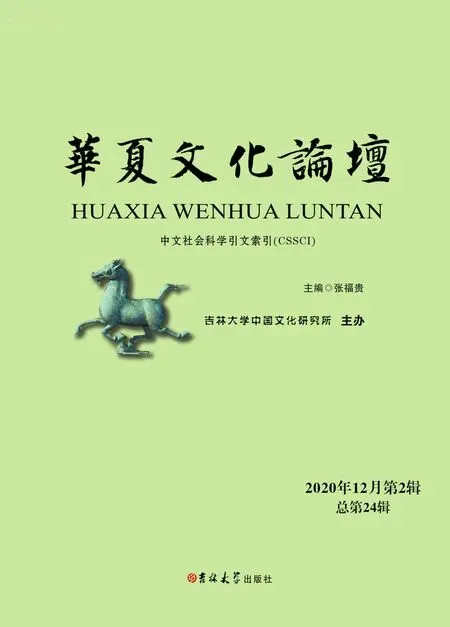屈原赋发生问题补论
【内容提要】据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及六朝人所述来看,屈原之时楚国已有文士燕集与诗赋竞技活动,屈原赋就是在这种创作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春秋末兴起的各国新声则构成了屈原赋崛起最重要的艺术基础与最直接的承变对象。
在《诗经》时代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屈原赋这一文体在楚国突然崛起,产生大量辉煌的篇章,这一点总令后人惊叹不已。近世以来,学界对屈原赋的产生更是多方探索,或归因于楚民间宗教歌舞的影响,或归因于南北文化的交流,或归因于彼时辩士文辞的兴盛。这些探索丰富了我们的认识,但可惜还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我们想补充与强调的是,屈原赋的产生除了上述这些因素,还有更为直接的承变对象与更为具体的创作土壤。
就创作土壤方面说,我们要补充与强调的是,屈原赋的产生离不开楚文人燕集活动及诗赋竞技所形成的艺术沃土。屈原之时楚国已有文人燕集与诗赋竞技活动,前人已有所描述。如董说《七国考·楚音乐》引东晋《拾遗记》云:
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徹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举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忘老,虽《咸池》《箫韶》,不能比焉。每四季之节,楚王常绕山以游宴,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仲春律中夹钟,乃作清风流水之诗,醼于山南。仲夏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①(明)董悦:《七国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31-232页。两汉之交桓谭《新论》尝提及“潇湘之乐,方罄为帝”,未知是否亦指怀王“潇湘洞庭之乐”。
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亦云:“楚襄燕集,而宋玉赋《好色》。”虽然这些记载还都只是后人的描述,但从屈原及其后学的辞赋创作来看,这些描述比较可信。
屈原《九歌·东君》描述楚人娱神,曾谓:“縆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众知,“展”字本就有列呈数物之义,而从诗中所写乐器的纷繁变化来看,“展诗”也很像是多首乐歌的竞奏。虽然屈原对楚人“展诗”活动的具体情况交代得有些笼统,但楚国权贵聚集文士享乐而有诗赋创作方面的竞技,这在《招魂》与《大招》中却有不少表现。
譬如,《招魂》描写楚人乐享,曾云:“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此“造”字,以往多被解为制作之义,然而这些新歌既然在宴飨中有乐舞相配,则显非即兴之作。《诗经·文王》“造舟为梁”,孔颖达疏引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可见,“造”字原有汇集排比之义,而“造新歌”也正不妨理解为汇集排演新歌之意。这些“新歌”既是被汇集排比在一起的,也就不当是一人所作;而既是众人之作被排演在一起,也就难免不引起孰优孰劣的评论。与“造新歌”相比,“展诗”没有强调所展为“新歌”,这大概是因为《东君》所谓“展诗”写的是娱神活动,而娱神的乐歌往往较为固定,所以也就谈不上“新”。不过也不尽然,《东君》所写未必便是国家祭典,如是民间俗祭,也正不妨碍人们各以新歌悦神。况且,即便是国家祭典,也未必不使用新歌。在很多学者眼中,《九歌》正就是屈原为国家祭典所创作的一组新歌。
楚国权贵宴飨时使文士们“造新歌”的竞技性质,《大招》中交代得更加清楚:
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赵萧倡只。魂乎归徕!定空桑只。
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四上竞气,极声变只。魂乎归徕!听歌譔只。
王逸《楚辞章句》以为:“空桑,瑟名也。接,联也。投,合也。诗赋,雅乐也。古者以琴瑟歌诗赋为雅乐,《关雎》《鹿鸣》也。……娱,乐也。乱,理也。言美女起舞,叩钟击磬,得其节度,则诸乐人各得其理,有条序也。四上,谓上四国,代、秦、郑、卫也。言四国竞发善气,穷极音声,变易其曲,无终已也。”众知,王逸解骚很喜欢将屈赋曲解成汉儒喜欢的模样,他的这几句解说亦正有此弊。譬如,“投诗赋”后,诗人紧接着说是“叩钟调磬”,可见配合的乐器也包含着钟磬,怎么能说这里的“诗赋”是“以琴瑟歌诗赋为雅乐”呢?至于“娱人乱只”,与《招魂》所云乐舞活动中的“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明系一事。而据《礼记·乐记》载,子夏曾指出“新乐”表演中“獶杂子女,不知父子”,而雅乐则并不如此。据此来看,“投诗赋”亦应属于“新乐”的范畴,而与传统雅乐无关。至于“四上竞气,极声变只”,逸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四国竞技时所吟唱的“诗赋”,如果按王逸的讲法,指的是《关雎》《鹿鸣》等传统雅乐,则其歌词、唱法与配乐都是固定的,如何可以说是“竞”,是“极声变”呢?可见逸注之不通。“投诗赋”之“投”,学者多从逸注,而王夫之《楚辞通释》则谓:“投诗赋者,如《春秋传》赋某诗之类,授诗命工歌之也。”然而其说亦有未确。《列子·说符》“楼下博者射”,殷敬顺《列子释文》云:“凡戏争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投诗赋”之“投”宜取此义。至少,这样解释可以与后文“四上竞气”之说相一致。至于末句“听歌譔只”,王逸以为“譔,具也”,非本义也。且楚人宴飨既以竞演“新歌”为主,则旧歌旧乐必然有所阙遗,据此,“譔”亦不当解为具备之意。按,《论语·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郑玄注曰:“撰读曰譔。譔之言善也。”《广韵》从其注,亦谓:“譔,善言也。”“听歌譔”之“譔”应取此义,指乐歌词句表达之善者。而“听”则应指审听决断,如《礼记·王制》“听狱讼”之“听”。《大招》前文呼唤“魂乎归徕!定空桑只”,王夫之《楚辞通释》谓:“定,整理其弦柱而鼓之。”细审“魂乎归徕!听歌譔只”之意,应与“魂乎归徕!定空桑只”文句相偶。前者呼唤亡魂回来审定乐器之音调,后者呼唤亡魂回来审定乐歌文辞之善者。屈原《惜往日》自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也许“昭诗”就包括了“听歌譔”这一类的事情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乐舞活动中存在诗赋竞技,楚文士燕集博弈之时还有更为单纯的语言创作方面的竞技,如《招魂》云:
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是文逸注云:“兰芳,以喻贤人也。言君能结撰博专至之心,以思贤人,贤人即自至也。赋,诵也。言众坐之人各欲尽情,与己同心者,独诵忠心与道德也。”其实,从《招魂》内容结构上看,诗歌的这几句明明是接续“菎蔽象棋,有六簙些”等博弈内容而来,解为“思贤”实在过于突兀了。大概有鉴于此,朱熹《楚辞集注》转而解释说:“撰,述也。假,大也。谓结述其深至之情思,为词以相乐,如兰芳之甚大也。极,倾倒竭尽也。赋者,不歌而诵其所撰之词也。盖人各以其所极而同心陈之也。”朱熹的解说较之逸注要好多了,只是“兰芳之甚大”云云依旧有些费解,不如解“兰芳假”为假借兰草等芳草来构思之意。至于“极”,朱熹的解说实际是将其当作竭尽才华之意。这个解说放在前后文中说得通,但细审之,“人有所极”云云不如解为:人们的“结撰至思”常有极限,但大家还是一同用心去描述。这样讲,也有实例为证。如宋玉名下有《大言赋》和《小言赋》,其内容正是描写宋玉等文士燕集于楚襄王之侧而就艰难的题目进行创作竞技。前者写楚襄王出题目,谓:“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然后君臣四人便就巨丽形象的描写展开竞技。后者写: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小大备。能大而不能小,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坐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
文中提到楚襄王评价大家的竞技是“极巨伟矣”,这里的“极”与“人有所极”的“极”不正是一个意思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言赋》与《小言赋》曾被一些人怀疑为后人伪托,现在则基本又被认为是宋玉所作了。而从这两篇赋作的内容来看,在屈原的时代,文士们不仅常燕集于君王之侧以文会友,而且还常常就文学描写的极限同心竞技。这种创作氛围对屈原赋的产生与发展,显然极为有益。
说到诗赋竞技,《招魂》与《大招》也很像是诗赋竞技的产物。这两首诗的作者与题旨,自汉以来就颇有争议。《招魂》或以为屈原所作,而王逸《楚辞章句》则说是宋玉所作,用以为屈原招生魂。此说目前最为可信。《大招》亦明系招生魂,其作者,王逸倾向于认为是屈原,而朱熹倾向于认为是景差。朱说近是。这两篇赋作都是为放流在外的屈原招魂,主题相同,内容相似,就好像命题作文似的,而艺术上同中求异的特征极为明显,又好像在故意争胜。由于两篇赋的作者既是好友,又都是楚襄王身边以文学著称的侍从,而且从内容上看这两篇作品又都写于春季,所以确实不能排除这两篇赋作也是“人有所极,同心赋”的产物。
在新近出土文献上博简中,也有几篇与屈赋体制相近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产生时间上与屈原赋同时或者稍晚,其中《桐赋》与屈原的《橘颂》十分相类。虽然目前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桐赋》乃是与《橘颂》同时创作出来的争胜之作,但若据此说,当日的楚国作家很注意诗赋创作方面的互相学习与赶超,则并无什么不妥。而毋庸多言,这种创作氛围对屈原赋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有益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歌咏方面的竞技似乎不仅存乎贵族生活之中,即使庶民百姓看起来也不乏这方面的娱乐。譬如宋玉《讽赋》载,宋玉尝出行,于旅居之家奏《幽兰》《白雪》之曲,而主人之女为之歌曰:“岁将暮兮日已寒,中心乱兮勿多言。”宋玉又为《秋竹》《积雪》之曲,主人之女又为其歌曰:“内怵惕兮徂玉床,横自陈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谁怨,日将至兮下黄泉。”这种你能弹我能歌的活动,岂不也很像是一种“极声变”而“听歌譔”的娱乐活动吗?至于宋玉《对楚王问》所讲述的“客有歌于郢中者,……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故事,也明显属于诗歌竞技,只是更偏重于演唱技巧而已。至于刘向所编《列仙传》,不仅载有郑交甫邂逅江妃二女后相互间的诗歌问答,并且还指出江汉地方的人“皆习于辞”。诚然,《列仙传》所载属于传说,而宋玉所言也不排除是出于虚构,但即使是虚构,也当是以现实生活常有的娱乐形态为基础虚构出来的。而这种社会现实、这种娱乐风俗也就说明屈原赋的产生具有极为广阔的艺术沃土,并非仅仅局限在楚国宫廷文化的园囿之中。
就承变对象而言,我们要补充和强调的是,屈原赋不但继承着周室《诗经》的传统,吸取了南楚宗教文学的营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妨看作春秋以来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各国新声的继承与发展。以往,由于孔子以来的儒家对郑卫等新声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人们对屈原赋与郑卫等新声的关系不甚重视,这是不应该的。
诚然,屈原对郑卫等国新声的态度,其作品很少明确的反映,但宋玉的《招魂》、景差的《大招》都曾用郑卫等国的新声为屈原招魂。既然是为屈原招魂,也就说明这些新声乃是屈原所熟悉的,至少是能欣赏的,因而这方面的文本状况很值得深入研究。
《招魂》用女乐为屈原招魂的描写如下:
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
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
长发曼鬋,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
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
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
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
郑卫妖玩,来杂陈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
逸注:“郑舞,郑国之舞也。”如果郑舞是郑国之舞,则所吟奏的也就是郑国之音,由此便可佐证《招魂》确实在用郑音所代表的的新兴俗乐为屈原招魂。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逸注又提示:“或曰郑舞,郑重曲折而舞也。”可见这个问题,王逸已不能决。后世学者多认可郑舞为郑国舞蹈之说,唯蒋天枢《楚辞校释》倾向于“或曰”之说,且证之以《淮南子·修务训》所云:“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骛。”其中“鼓舞”,高诱注:“或作郑舞。郑者,郑袖,楚怀王之幸姬。”从《招魂》诗中描写来看,解郑舞为郑重曲折之舞要更好一些,而且不必牵扯郑袖。因为诗中明明写的是“二八齐容”,属于群舞,并非夸美一人。再者,从前后文来看,起始的《涉江》《采菱》及《扬荷》,一般认为是楚歌,其后的“发《激楚》”,一般认为也是在演奏楚歌,而在二者中间,突然出现一段郑国舞蹈,不免突兀过甚。不如说,整个这一段都是在夸述楚国本土歌舞之美。其后“吴歈蔡讴”及“郑卫妖玩”才应是对异国歌舞的描绘。蒋天枢《楚辞校释》亦以为:“郑卫妖玩,即上言女乐中之一部,言楚歌楚舞之外,兼有郑卫妖玩杂厕其间。特举郑卫者,郑卫新声为六国间最流行乐曲,故二国多名倡也。言杂陈,谓倡与乐皆自外地。”其说甚是。总的看,《招魂》这一段关于诗乐舞的描绘,确实是在以新声为屈原招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声中,作者对郑卫等国新声明显好感不多,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楚国“新歌”与“郑舞”的夸美上。末句“《激楚》之结,独秀先些”看似重复,实际则是总结各国新声中唯有楚国的《激楚》最为优异。这种态度,从现有文献看,首先是宋玉本人的态度。如宋玉之《笛赋》曾谓:“夫奇曲雅乐,所以禁淫也;锦绣黼黻,所以御暴也。缛则泰过,是以檀卿刺郑声,周人伤《北里》也。”可见宋玉虽然也喜欢“奇”“锦”,但对郑声的“缛则泰过”实有不满。自然,宋玉的态度未必便是屈原的态度。但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一生倾慕屈原,而《招魂》又是为屈原招魂,所以宋玉在诗中崇新声而不特崇郑卫的态度,与屈原平日所持态度很可能相去不远。
至于《大招》,前文所引“代秦郑卫”“四上竞气”之文,明是在用各国新兴歌舞为屈原招魂。不过,景差在《大招》中并未像宋玉《招魂》那样对各国新声的优劣作一明确判断,也没有明显的扬楚抑郑。此外,《招魂》所写歌舞,明显分为两个表演阶段,从“《涉江》《采菱》”到“发《激楚》些”,很像周王室乐享活动中属于“正歌”的部分,既有比较固定的曲目,表演风格也比较郑重,而“吴歈蔡讴”之下的部分则很像周王室乐享“正歌”之后属于“无算乐”的部分,表演活泼,也比较自由。宋玉将夸美的重点放在“正歌”,而不是带有狂欢性质的“无算乐”部分;而《大招》写歌舞,似乎是略过了“正歌”部分,直奔“无算乐”部分的狂欢而去。这种描写当然反映了二人审美趣味方面的一些差异,但在为屈原招魂方面,二者还并不能说就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宋玉的《招魂》是直接给出了屈原所可能认可的态度,而《大招》则在夸美四国斗胜之后,呼唤屈原的灵魂回来“听歌譔只”。景差这样写,也许是因为他不大认为屈原会采取宋玉《招魂》所表现出的态度,所以也就采取了更为审慎的写法,请屈原本人的灵魂回来作一判断。
《大招》与《招魂》对诗乐舞的描写虽有不同的侧重,但毫无疑问,二者都是在用新声而不是在用《诗经》代表的传统雅乐为屈原招魂,这也就说明屈原对《诗经》之后兴起的新声更为重视,因而其诗赋艺术也必然对这些新声有更为直接的继承。汤炳正《楚辞今注》说:“屈原《九章》有《涉江》,即以旧曲作为新歌。”所谓“旧曲”对《诗经》来说,也正是“新声”。除了《招魂》与《大招》,屈原赋与郑卫等新声的密切关系还可以通过二者艺术方面的共同点来加以佐证。
郑卫等国新声,早已不传,但通过古人的概括仍旧可以对其艺术特点加以了解。据《论语·卫灵公》,孔子曾认为“郑声淫”,要求“放郑声”。而《礼记·乐记》亦谓:“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慢者,怠慢雅乐古法之谓也。《乐记》又载子夏之言曰:“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具体说则是:“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孔颖达疏云:“滥,窃也,谓男女相偷窃。言郑国乐音好滥相偷窃,是淫邪之志也。燕,安也。溺,没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没矣,即前‘溺而不止’是也。‘卫音趋数烦志’者,言卫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烦劳也。‘齐音敖辟乔志’者,言齐音既敖很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骄逸也。”据刘向《新序·杂事》,齐宣王曾云:“听郑卫之声,呕吟感伤。”《说苑》亦载:“晋灵公好悲歌鼓琴,孙息学悲歌鼓琴,即引琴作郑卫之音,灵公大感。”据这些记载来看,郑卫等国新声作为诗乐舞一体的表演艺术,其主要特点:一是内容主于爱情;二是情绪偏于感伤;三是传统道德束缚较少;四是艺术表现自由繁复。
与郑卫宋齐四国新声相比,秦声似乎更为任性而粗率,如《史记·李斯列传》云:“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至于楚声,据前揭《招魂》所谓“目曾波”、“齐容”、“郑舞”、“狂会”、“宫廷震惊,发《激楚》些”来看,似乎多方面吸收了各国新声的艺术营养而又能益之以庄重的态度、激烈的情感与更为强烈的个性。刘向《新序·杂事》载,齐宣王听惯了郑卫之声的“呕吟感伤”,则“扬《激楚》之遗风”。桓谭《新论·琴道》亦载,雍门周曾形容孟尝君一类的贵族享乐,常“扬《激楚》舞、郑妾流声以娱耳目”。可见《激楚》为代表的楚声确实别具格调而能与郑声并行。其格调就后世楚声短歌,诸如项羽《垓下歌》及高祖《大风歌》之流来说,诚然是悲也悲得极有力量。
上述这些新声艺术,大多被《招魂》和《大招》用来为屈原招魂。齐声虽未出现在这两首诗中,但屈原曾长期放居齐国,对齐声当然也是熟悉的。总而言之,这些春秋末叶渐次兴起的新声,较之《诗经》,是屈原直接面对的,更需要超越的文学艺术的高峰。而事实上,屈原的创作也的确多方面承继了各国新声的艺术营养。一者,屈原的作品长于抒写男女之情,《九歌》中的爱情描写尤其细腻缠绵,明显和郑卫之声一样“淫于色”而“比于慢”。二者,屈原赋绝大部分都属于悲音,这也与郑卫等国新声长于抒发悲情相类。三者,屈原赋“露才扬己”,与齐声之“敖辟乔志”相近,所以也曾受到儒者如班固之流的批评。四者,屈原赋常“发愤以抒情”,那高昂的个性精神、激越的思想情感也与楚声的某些风貌相类。就这些艺术上的共同倾向来看,说屈原在创作中充分吸收了春秋以来各国新声的艺术营养,显然是成立的。至于屈原赋对各国新声艺术的超越,则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完成的。
首先是将各国新声的优长结合起来。譬如楚声,虽然抒情常激烈遒越富于阳刚之美,但现存屈原之前与之后的楚声却多是短章,几乎没有什么铺叙,而郑卫之音虽然缠绵繁复,情调却常失于轻浅。屈原赋却多能将郑卫之音细腻的情感描写与楚声激越阳刚的审美风格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是将新声与旧乐的优长结合起来。新声的优点主要是艺术手法繁复,但主题不够雅正,思想不够深沉。而《诗经》虽然留下了关心家国天下的创作传统,但艺术手法却过于简陋。屈原赋则将二者结合起来,既长于铺叙、起伏、照应,并且几乎篇篇都有不同的艺术面目,又能将这些艺术上的技巧用于抒写个体的道德完善,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于批判丑恶的社会现实,用于论证革新楚国的理想以及统一天下的理念,从而在艺术手法上超越了《诗经》的传统,在思想主题上提高了新声的格调。
再次是将新声旧乐的优长与其个人的人生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按郑玄《六艺论》的说法,《诗经》时代的诗歌只是面向政教的“弦歌讽喻之音”,对诗人个性极少展现。新声虽然更加关心个体,但就现存文献而言,也未曾闻有哪一曲新声是讴歌某个人波澜壮阔的个性化生活的。屈原赋则不同,乃是将屈原极具个性批判意识的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以极为个性化的艺术手法充分展现出来。《诗经》之重公义,新声之好私情,为时皆数百年,但就现有文献来看,只有到了屈原手中,诗赋才真正成为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艺术。
总之,屈原赋的产生虽然有多种原因,尤其是离不开屈原的个人天赋,但是旧乐新声的铺垫与楚人普遍热衷于诗赋竞技的创作环境,乃是屈原赋产生不可或缺的艺术条件。